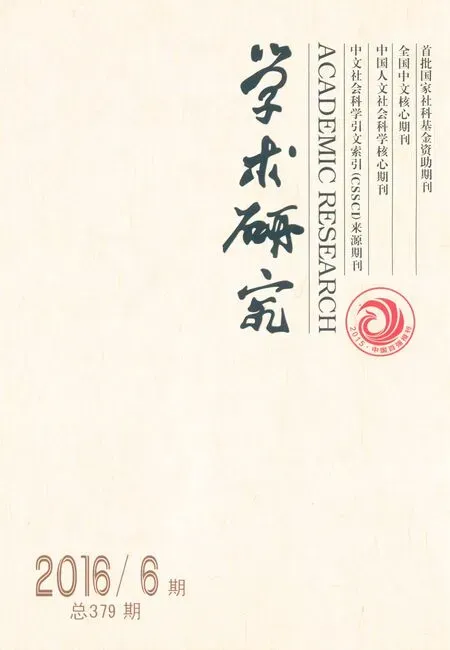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角度及其哲学定位
黄漫 刘同舫
马克思对鲍威尔的批判角度及其哲学定位
黄漫刘同舫
[摘要]犹太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哲学走向分裂的重要标志。鲍威尔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提出的犹太人解放之道被马克思视为一种以启蒙形式再现的哲学兼神学的行动,其哲学在根本意义上无法摆脱自由主义的浓厚色彩。马克思沿着宗教问题、政治批判、市民社会批判再到社会历史批判的逻辑理路,深入社会历史中阐释犹太人经商牟利、自私自利的本质,在批判的基础上揭示鲍威尔将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相混淆而对自由主义局限性及其根源的抽象解读,重新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自由主义政治解放人的解放
19世纪的欧洲,反犹情绪的普遍流行,甚至使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蔓延到人们的一切生活之中。阿伦特直言,“只有最后大灾难的恐怖,甚至只有当幸存者无家可归(homelessness)并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犹太人问题'在我们的每日政治生活中显得重要起来。”[1]犹太人问题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对这一问题不同立场的争论使得深受鲍威尔影响的马克思第一次公开批判他的挚友,在理论道路上与鲍威尔分道扬镳。马克思批判深处自由民主制国家中的鲍威尔无法超越自由主义的视域来审视国家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在神学中游离的行动。尽管有学者从激进的变革精神与神学倾向认为鲍威尔是反自由主义的战士,是持保守的态度对待犹太人问题,①美国学者大卫·英格拉姆认为,反自由主义是鲍威尔的主张,也可归结为精英主义、保守主义,缘于鲍威尔关于国家是公民的精神中心的黑格尔式观念及其哲学实践自身的局限性(参见[美]大卫·英格拉姆:《权利与特权——马克思和〈论犹太人问题〉》,李旸等译,《国外理论动态》2015年第11期)。实际上,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与黑格尔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驳斥启蒙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其批判仍然局限于自由主义框架内。我们基于文本梳理展示马克思对鲍威尔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定位的论战:马克思在现实国家历史处境中揭示犹太人矛盾潜在的社会动因和问题的根本,透过现代国家的本源性问题及其解放的限度揭示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本质区别,完成对自由主义的根本性批判,为犹太人解放乃至普遍的人的解放奠定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从理论前提与论证逻辑的角度批判鲍威尔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针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观点进行公开驳斥的论文,其驳斥“不仅体现在犹太教的性质上,而且也体现在流行的政治异化概念及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2]鲍威尔基于自我意识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将政治解放作为消灭宗教的自由问题,以恢复自我意识的自由来实现人的本质统一与回归的激进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实际上是在宗教范畴内以启蒙的形式再现的斗争方式,这种批判的视野仍然陷入启蒙哲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之中。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鲍威尔理论本身的局限,致使其所致力的犹太人解放最终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动”,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只是一种抽象的幻想。马克思肯定鲍威尔看到宗教束缚德国犹太人自由的现实,甚至赞赏鲍威尔的阐释尖锐与极致,但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定性为宗教问题的启蒙思维和自由主义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不满和抨击。基于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不同立场,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过程中将其哲学定性为自由主义哲学,尤其体现在其理论前提和论证逻辑两个方面上。为了揭示犹太人问题的实质,完成对宗教和政治的彻底批判,进而完成对自由主义的根本性批判,马克思深入犹太人问题的本质,以至于《论犹太人问题》被麦克莱伦称为“是批判自由派的国家和人权观点”[3]的著作。
在理论前提上,鲍威尔以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原则与国家观念为起点,在现代政治国家的框架之内敞开对犹太人问题的洞见,使其哲学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局限性。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于排他性的宗教信仰本质,国家之于犹太人是一种异己且无力抵抗的因素,只有废除宗教才能使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从废除宗教到政治批判,鲍威尔将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等同于对国家本身的批判,对政治国家理解的缺失使他在论证逻辑上陷入了前提性的自我缺陷中。他没有认识到犹太人问题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表述,对神学的批判在犹太人问题已然成为世俗问题的一些共和制或民主制国家中失去了批判的意义,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中,宗教与国家可以共存。当宗教的统治地位转移到国家之后,国家随即构成问题的实质,鲍威尔恰恰在此回到了自由主义之中。国家在鲍威尔看来无异于一个理性中立的存在,服务于任何政治势力或组织,它是自由和人性的高度表现,这与黑格尔将国家视为实体意志、伦理观念和自在自为的绝对理性在本质相一致。在基督教国家中,宗教使得人与人的本质相分离,教会成为异化了的国家的本质。因此,要使得每个人作为公民获得解放,国家应该废除出身、等级等差别,人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当公法领域与私法领域、公人与私人区分开来,宗教进入私法领域成为原子化的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精神选择和纯粹的个人事务而以差别的本质取代共同性的本质时,国家和个人就会脱离宗教,真正获得政治解放。一方面,鲍威尔追求人的解放所获得的所谓公民人权或自由权利,实际上是近代自由主义自然权利的思想要求,甚至被麦克莱伦称为是“利用启蒙运动的语言来表达黑格尔的思想”。[4]这也正是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的表现所在,以自然权利性质的抽象自由视为人得到解放、人性得到自由的标尺显现出理论自身的尴尬与荒谬。另一方面,尽管鲍威尔承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及其必然性,但其作为理论前提的国家观未能从根本上认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下的世俗对立。他寄希望于哲学与神学的批判在政治上的激烈变革方式而以政治解放实现人的解放,满怀信心地等待历史的评判,这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显得苍白无力。
在论证逻辑上,鲍威尔对犹太人解放问题的探索中,将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宗教,试图废除宗教建立自由的价值追求以实现人的解放,这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家聚焦于推翻宗教神权以恢复人的自由权利的努力在本质没有差别,从神学中漫游到神学的行动成为鲍威尔画地为牢的整个视野。与理性主义者一样,鲍威尔将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对自身生活理智能力理解上的欠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人的现实的不自由包括意识形态所呈现的一切特点,犹太人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废除宗教成为鲍威尔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但是,鲍威尔废除宗教的解决方案仅仅停留在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以及谁更有能力获得解放的问题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使得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成为最终的批判。鲍威尔神学视角下的哲学批判试图找到政治解放本身的本质产生的条件以走向自由的尝试显然是行不通的。他将犹太人问题归纳为“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5]认为无论是对于消除顽固宗教对立而得到政治解放的犹太人,还是解放他人而使自身获得解放的基督教国家,废除宗教都是其政治解放的先决条件。犹太人的狭隘本质与其生活于普遍关系中的公民义务相矛盾,国家生活只是犹太人本质之下的外观。只有犹太人放弃犹太教,国家不以宗教为基本前提,犹太人才能得到救赎。这意味鲍威尔将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等同于宗教的完全废除,犹太人在政治上的解放等同于人的解放,他以自由主义政治原则为理论前提的政治批判止步在基督教国家中对纯粹神学问题的研究。鲍威尔的论证逻辑使得他获得了与自由主义思想家同样的结果,由宗教批判而实现的解放是一种局限性的解放,人所获得的政治自由是一种抽象的自由。
尽管对宗教的批判是马克思和鲍威尔关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共识前提,但鲍威尔在纯粹的宗教视角范畴之中探讨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甚至被卢格称之为“最后的神学家”。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影响的鲍威尔尽管致力于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将克服精神异化作为实现政治自由的前提,旨在“摧毁基督教国家,把自由提高到力量和权力的水平,从而避免蹂躏社会和国家的危机”。[6]他废除宗教的强烈诉求归根到底是一种恢复自我意识的自由解放斗争,却陷入“单凭精神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现存事物,并把政治活动归结为对制度和教义的简单批判”,[7]其哲学批判囿于启蒙主义视域之内,没有脱离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范畴。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深入犹太人问题的根源,在与鲍威尔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激烈论战中完成对自由主义的根本批判,从而揭示了解放与自由的真正本质和内在关系。
二、马克思与鲍威尔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不同理路
对犹太人问题哲学立场与关注兴趣的不同,决定了马克思与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形成两种不同的论证理路。身处自由民主制统治世界的社会形态之中,鲍威尔无法超出自由主义的视域来审视国家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其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陷入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之中。面对现代国家的历史处境,马克思把关注点指向与鲍威尔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上,在汲取鲍威尔思想的基础上,深度剖析鲍威尔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不可行性,把对犹太人问题的阐释推至更深层的理论境遇。
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的逻辑进路贯穿着神学的主线,秉持黑格尔政治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原则,他在宗教神学的框架中以特权的视角批判犹太人及其宗教,犹太教所具有的排他性特质与自由主义民主制国家的普适性相矛盾,公民身份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必然相应地要求犹太人舍弃宗教信仰。他提出犹太人问题首先是宗教解放问题,进而才是政治解放问题。犹太人问题的普遍意义根源于宗教特权对人的奴役和束缚,只有消除特权思想,才能消灭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犹太人与基督徒的不平等),走向人的自由。在尚未获得政治解放的基督教国家——德国,宗教对立下基督教的普遍统治使得犹太人寻求政治解放的诉求成为几近绝望的事业。破解这一问题首要的是必须通过废除宗教达至消灭宗教对立,破除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宗教关系,变为批判的、人的关系,人放弃宗教而作为公民得到解放。
按照鲍威尔的逻辑,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不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也成为获得政治解放的国家,因此,当人摆脱了宗教的约束时,意味人不仅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且获得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宗教的奴役和异化是国家走向政治解放的根本障碍,只有废除基督教作为国教的统治地位,“国家才超出特殊的教会而达到思想的普遍性,即它的形式上原则,并使这个普遍性达到实存”。[8]鲍威尔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撇开对政治国家的批判来理解政治解放,使得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被混淆为同一个过程。他将宗教和原子化的市民社会结合起来,认为以需要作为强大动力的市民社会表现为每个人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利己主义和完全主观性的基督教成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宗教不但没有被彻底废除,反而构成市民社会的精神。鲍威尔看到基督教国家中政治异化之下人的状况,却将其视为当然。作为人具有优先性的基督教幻想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在民主制国家中却只是一种外在感性的世俗准则,这使得鲍威尔企图区分公私生活以使宗教被视为私人事务,从而将国家和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方案难以实现。市民社会的成员与其公民身份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其在宗教上的表现也仍旧持续存在。
尽管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犹太人享有公民权,也不代表犹太人能够要求并得到普遍人权。鲍威尔指出,人权不是天生所具有的,是历史偶然的嘉奖,“是教育的结果,只有争得和应该得到这种权利的人,才能享有”。[9]人权是作为人同他人相结合基础上的权利,犹太人没有人权可言,因为犹太人狭隘的本质将压倒那种把犹太人作为人而同他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使犹太人同非犹太人分割开来。人为了能够得到普遍人权,必须以牺牲信仰特权为代价。但问题在于,在利己主义的原子式市民社会中,鲍威尔自然权利性质的特权视角下,普遍人权或自由权利和人与人相分隔的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不相符合,他并没有理解人权的真正实质,这种权利本质上无异于黑格尔作为自由主体践行自我意志的“抽象权利”。
对鲍威尔而言,人从宗教中得到救赎,意味着人对一切宗教的自由。由于自我意识是他所追求的自由的实质内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就是人摆脱宗教的压迫,使宗教成为个人的问题,使人自身成为拥有普遍自我意识的主体,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自我意识所创造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鲍威尔力求实现的自由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自由,他所向往的自由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与马克思普遍的人的解放意义上的自由具有本质区别。鲍威尔的论证逻辑透露出他对犹太人问题理解的片面性,即过分注重宗教影响的研究而将犹太人问题视为一个纯粹神学的命题,导致其脱离现实世俗而在神学的视域中判定犹太人的本质。正如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中,他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关系的考察转化为“对获得自由的能力”的关系一样,认为犹太人由于利己主义、粗陋感性需要的限制较之于在宗教的表象之下已包含完善的人的形象的基督徒,更难以获得解放。[10]鲍威尔将安息日的犹太人当做犹太人的全部特性,将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理想的抽象本质看做犹太人的全部本质,势必使其无法触及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经商牟利和金钱。这种哲学批判和神学行动在国家的解放上没有触及国家作为最高秩序的权威,在人的政治解放上缺乏世俗的现实根基,在市民社会中以宗教意义上确认人的政治特性和权利,从根本上无法真正把握犹太人问题的真实本质。鲍威尔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一旦超越宗教的范围便失去了立足点。尽管废除宗教的统治地位与启蒙运动政教分离的愿景异曲同工,但始于自由主义国家至上的政治原则而在神学中游动的鲍威尔,其批判及结论终究难以超越自由主义体系的局限。
马克思没有停滞于批判鲍威尔的神学方式,他将批判的目光投注到整个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沿着从宗教问题、政治批判到市民社会批判直至社会历史批判的逻辑理路,把犹太人问题回归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展开现实批判。马克思认同鲍威尔的宗教批判,但反对将犹太人问题神学化,宗教批判在德国已经完成,批判的现实任务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并没有以自由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国家观的政治原则来探讨政治解放问题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他区分了政治解放程度不同的国家(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关于犹太人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本质性差异,尤其以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美国为例,用美国宗教所表现出来的朝气与生命力的事实直接拨开宗教与国家相矛盾的迷雾。他否定犹太人问题的神学规定,指出宗教是一种缺陷的存在,是世俗局限性所表露的现象,这种缺陷的根源必须追溯到世俗基础国家的本质之中。只有将神学问题转换成世俗问题,才能通过消除世俗的局限来消除宗教的局限。厘清了鲍威尔错误的症结点——在批判基督教国家中废除宗教、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将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转换为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把批判矛头指向国家本身,指向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从政治解放的限度阐述市民社会中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的真实现状。政治解放限度最直接的表现是宗教与国家之间不存在矛盾,即使人仍然受到限制未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也不影响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中,国家只是代替宗教作为中介使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人以间接的方法实现对宗教超越的有限解放,但仍未实现人的普遍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11]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国家没有消除人的真实差别,政治解放自身的内在矛盾依然无法破除。
从政治解放的限度看,政治解放不仅不是人的解放,反而加剧了人的异化。政治解放的完成确立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使得宗教从国家精神转变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马克思颠覆了黑格尔对国家作为市民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的判定,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中,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等同于政治国家克服市民社会的方式,国家不得不承认并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以保证自身的存在。人被分为公人与私人而具有双重意义,马克思将人的现实生活形象比喻为“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政治国家中,人作为想象主权中的虚构成员被视为类存在物,在虚幻的生活中享有“非现实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以原子式的个体进行活动、追求私利的人是尘世存在物,将他人与其自身都降低为工具层面,成为异己力量的因素。马克思既批判人的“非现实的普遍性”,也批判市民社会中受制于利己主义精神控制的人的现实状态,政治解放不仅没有完成人的解放,反而加深了人的异化。
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的根本特性对“人权”的理解既是对政治解放的深化剖析,也是对鲍威尔普遍人权及近代自由主义自然权利理念的有力批驳。他认为,人权“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12]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市民社会利己的人的范畴,也即没有超出追求私利、自我封闭的人。鲍威尔不予批判的政治权利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裂的二元对立中有其固有缺陷,受到市民社会中私人财产和需要的制约,正如近代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普遍和永恒准则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安全、私有财产权利)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原子式个体个人主义的表现。
政治解放不可能直接跨越到人的解放,政治解放的限度最终归结为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指责鲍威尔将犹太人的本质束缚于宗教之中,提出必须从世俗基础的社会历史视角来审视犹太人及其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犹太人以自身的方式获得了解放,并非因为“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性”,而是金钱作为世俗化的神成为世界势力,犹太精神成为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其经商牟利的真正本质得到普遍实现,是一种“高度的经验本质”。犹太教实际需要、利己主义的宗教基础表明,犹太人的解放体现了在市民社会中摆脱商品和金钱的统治,人必将成为丧失了自我的人,因为“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13]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关键不在于废除宗教而获得的政治解放,而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得到解放、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得到解放。
三、自由主义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的哲学定位
基于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论证的出发点及其问题根源的深度探究,马克思将鲍威尔哲学定位为自由主义。对鲍威尔哲学延展到对整个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所要完成的极其重要的任务。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论路径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矛盾体”自我阐释的过程,这种自我矛盾尤其体现在鲍威尔将“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宗教与政治所展开的批判上。
近代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开启的现代政治原则,将政治国家视为外在于社会的最高统治秩序,政治国家所能达到的秩序形态是人的自由状态所能实现的限度。尽管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启蒙先哲透过自然状态的假说,依据被认为普遍而永恒的基本价值准则的自然权利构建起国家以外的共同体,宣称社会先于国家存在,国家是人民意志之下的理性产物,其职责是调和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以维持国家统治的稳定有序,甚至如洛克所认为的,国家是以实现自然状态之下的自由、平等权利为目的的社会工具。黑格尔保留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准则和国家至上的现代政治原则,其市民社会概念尤其融合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观点,认为体现原子式的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但由于伦理上的不自足而需要外在的国家作为普遍利益代表的公共机构加以救济,[14]他赋予国家独有的伦理普遍性,使国家超然于市民社会之上,同时具备缓解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能力。鲍威尔沿袭了黑格尔主义的国家概念,以自由主义启蒙形式的理论先见作为神学视域下探讨犹太人问题的出发点,过度的宗教“情怀”和现代政治原则的内在局限成为其深入理解国家本质的根本限制,以对基督教国家的批判代替国家本身的批判,试图通过政治解放来实现市民社会的解放,实现普遍的人的自由。这种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误解使得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成为不证自明的同一过程。
马克思指认鲍威尔将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相混同陷入自由主义的逻辑缺陷,对国家的本质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理解。他认为,厘清这两者的关系必须追溯到政治国家的本源性问题,还原政治国家的本质性起源领域,通过透彻地把握现代统治秩序的基本特征和内在局限来洞悉人的自由的真实界限,揭示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应然关系,重新奠定普遍的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基础。
在完成政治解放的现代民主制国家中,人和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而在政治上获得自由,人拥有双重身份,宗教则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公民的私有财产、平等和安全等自由的权利受到国家保护。然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世俗分裂使得头戴主权光环的人们只是异己的存在物,成为外化了的人,市民社会成员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政治解放的现实局限在个体真实的人身上失去了自由的原有意义。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世俗分裂与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容忽视的政治革命,政治解放是同人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旧社会解体的过程,政治革命与市民社会革命本质上具有相似性。
旧的市民社会(即封建的旧社会)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财产和劳动等生活要素以领主权、等级和同行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要素,以此规定个体在社会中同他者相分离或相排斥的政治关系。具有政治性质的生活机能和条件使个体同国家分隔开来,个体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被赋予普遍性,国家自然演变成为与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特殊事务。当旧的市民社会无法克服其自身的矛盾时必然爆发革命与解放的强烈诉求。政治革命在推翻国家的统治地位、消灭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过程中,政治国家被重新组成普遍事务的现实的国家,市民社会则被分割为个体和构成其生活内容与地位的物质、精神要素。散落于旧市民社会之中的政治精神得以汇聚,重新构成共同体回归人民的普遍事务领域。特定的生活活动和地位不再具备同国家的普遍关系而降格到个体意义,公共事务也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解放无非是市民社会走出普遍内容的假象。结果是“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15]政治国家的建立与市民社会分解为原子式的独立个体是在政治革命同一行为中实现的,在完成了的政治国家中,独立的利己的人及其所生活的领域构成政治国家的基础。这对于自由主义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运转机器与黑格尔保守倾向的国家观中将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纳入国家最高统治秩序范畴之内的观点,是一个有力的回击。黑格尔所认为的市民社会“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16]作为高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机构来调和市民社会中无止境的私利追求而造成的矛盾的国家,其所做出的防止市民社会面临崩塌危险的努力,在马克思看来是错误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国家概念的巩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市民社会的某种表现,以市民社会为前提和基础的国家无法消除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所产生的矛盾,只有深入世俗结构本质之中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消除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将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的却不是人的解放,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利己的人,其自由受到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精神要素的制约。人获得信仰和财产自由、经营自由,却没有实际摆脱宗教、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束缚。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本质由于其以需要、私人利益等领域作为自身持续存在的自然基础而得以规定,它的成员表现为自然人或自然对象,是具有感性的、直接存在的人。以利己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的国家,其性质、结构及其所表征的职能是由市民社会的本质决定的,是一种异化的类生活,它通过政治行为的方式以人权使人成为抽象的政治人。实现政治解放人,既是以利己的个体存在的市民社会成员,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法人。这与鲍威尔看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向往的解放在根本上相一致,其中公民的人权观点更是资产阶级的典型观点。马克思认为,鲍威尔不予批判而以此作为终极追求来寻求普遍的人的解放,显然没有真正认识政治国家基础之上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马克思充分肯定从宗教批判走向政治解放的意义,而政治解放不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人的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政治解放只是其阶段性的完成。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既不能使现实的个人将抽象的公民复归于其自身,使其作为个体在现实的生活和关系中成为类存在物,也不能使人在社会生活中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其自身的限度表明人的本质仍然囿于现实的异化而没有得到根本的释放,人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必将从政治解放走向更为深远的社会解放。
对犹太人解放与自由问题的探讨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政治国家的基础上审视世俗生活,确立犹太人解放与自由问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批判和否定鲍威尔带有宗教色彩的自由主义哲学观点,而是以历史的眼光追寻问题本身,深入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置于对整个社会彻底批判与改造的高度,批判鲍威尔在神学视域中从宗教批判走向政治解放所实现的犹太人的自由与解放呈现的自由主义局限性;他深入犹太人问题的根源性中,洞察犹太人世俗生活的社会关系;他指明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根本界限,社会解放之于人的解放的必然性。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回归人自身。犹太人的解放实质上是现代人的自我解放,是犹太人从经商牟利的本质中解放出来使其自身作为普遍的人回归到现实的人的本质之中的社会实践。神意和抽象的自我意识不是开解犹太人问题的枷锁,现实的革命与实践才是犹太人走向解放与自由的根本路径。
[参考文献]
[1][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7页。
[2][6][波]兹维·罗森:《布鲁诺·鲍威尔和卡尔·马克思——鲍威尔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王瑾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05、142页。
[3][4][英]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夏威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69页。
[5][9][11][12][13][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8、28、40、49、45页。
[7][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王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8][1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79、197页。
[10][德]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李彬彬译,《现代哲学》2013年第6期。
[14]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导论第1页。
责任编辑:罗苹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6-0017-07
作者简介黄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东广州,510631);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