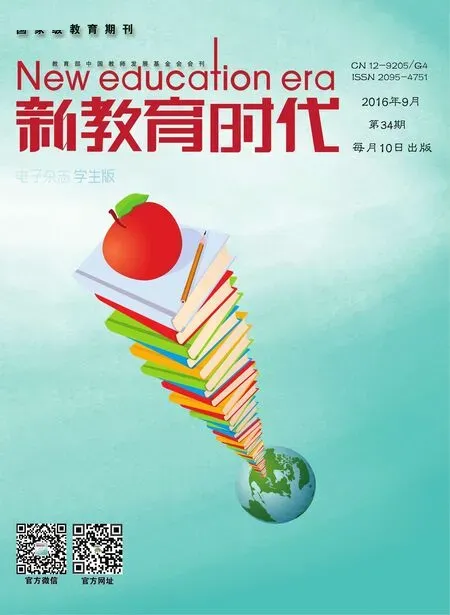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兴盛缘由探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王冰青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兴盛缘由探析(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
王冰青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天津 300387)
教会女学从创办伊始,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层次逐步提升,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且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与办学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教会女学的兴盛发展是19世纪40~70年代教会女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传教士舆论宣传的引导息息相关,也是中国社会风气日开的产物。
近代中国 教会女学 兴盛缘由
自1842年8月鸦片战争失败,中国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西方侵略者获得了许多特权。传教士在华办教堂宣教便是其特权之一。为了辅助传教工作,传教士把兴办教育作为一种传播方式和媒介。于是各类教会学校在中国纷纷建立起来,其中也包括教会女子学校。
近代中国教会女子学校的发展,从空间上呈现出一个由中国外围向本土发展的趋势,从时间上以1844年为发端,19世纪70年代为分界,后期呈现出兴盛发展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一是办学规模扩大,层次提升。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的初期阶段,由于民众普遍的反侵略情绪和一开始传教士对办学兴教重视不足等因素,教会女子学校的数量相对较少,办学层次较低,还一度面临招生困难的窘境。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传教士们普遍认为较低水平的办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的状况,于是改变策略,逐渐提高办学水平和层次,建校规模也不断扩大。在大会过后,一批教会女子中学,如圣玛利亚女校(1881年),镇江女塾(1884年),上海中西女塾(1892年),贝满女中(1895年)相继出现。至20世纪初时,教会女中已基本发展成熟,客观上呼唤着更高水平的女子学校的出现。1905年5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决定要在中国建立4所女子大学:华北、华中、华西、华南各建一所。虽然后来只有三所成立了,但纵观中国教会女学的发展,办学层次依然实现了从小学—中学—大学的提升。另一方面,在规模数量上,据数据显示,1876年,教会女学校有日校82所,学生1307人,寄宿学校39所,学生794人。至1907年,单在江南地区,天主教会就有女校697所,在校学生15300人。到1925年时,教会女子学校中的女生人数已经达到116251人。[1]总之,在这一阶段,教会女学不仅数量有所增加,规模扩大,办学层次也实现了阶梯式提升。
二是学校课程趋于全面化。在教会女子学校初期发展阶段,由于办学经验不足,师资力量缺乏等因素,教学课程突出强调基督教教义,并辅助以西方科学知识,课程体系不够全面。为了使教会女子学校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传教士们在授课内容与课程设置方面做了一定的调整。注重中西文化的贯通与衔接,把儒家文化引入课堂,将《四书》、《孝经》等经典列为必学课程。同时,学校仍十分重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授,并把它们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到20世纪初一系列教会女子大学出现时,学校课程设置已经趋于全面,课程体系已逐渐完备。如1925年《华南女子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教授的科目有生物学、化学、国文学、教育、英文、历史、家政、美术、算学、音乐、体育、物理、宗教教育、社会等14门类,共76科,并规定“体育、唱歌为一至四年的必修课”,且注重社会实践。
三是教育组织与管理近代化。教会女子学校初创之时,传教士的教学、组织及管理水平低下且不规范。但发展至19世纪末期时,教会女学已开始采用近代教育组织形式,实行班组授课制,建立了严格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就是这一典范,其《上海中西女塾章程》对学校组织与管理做了各项明文规定。如严格的时间规定,quot;女生来馆肄业……本塾每日八点三刻进塾,十二点放饭。西五月起下午一点半进塾,五点钟放学。西十月起下午一点钟进塾,四点半放学。”严格的考试规定,quot;本塾每年考课四次,考后各给分数单一纸。该生之品行与所习各项课程,以及到馆日数足否,皆注明分数,俾该生父母,一览了然。”[2](P83)
四是教育体制完善化。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以19世纪40年代创办小学为发端,70年代相继出现中学,20世纪初大学层次的女子学校陆续建立,之后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及成人教育纷纷出现。教会女校从小学、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到高等学校,形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其中,女子师范教育开女子职业教育之先河,1908年上海圣玛利女校开设师范科。此后,福州、北京、武汉、成都等十几个城市都设立了女子师范学校。另一类女子职业教育是医专或护校。从1870年广州的一家教会医院正式招收学生始,到1921年时,教会系统面向女性招生的医专有5所,私立4所,官办1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中国教会女子学校之所以呈现出兴盛发展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19世纪40~70年代教会女子学校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1877年第一届全国新教传教士大会决定改变低层次建学模式为分水岭,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教会女子中学的出现,以及20世纪初中国教会女子大学的相继创办,这是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教会女子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从初级学校到高级学校教育体制发展规律的结果。
就比如从20世纪初教会女子大学的萌发来看,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学院都是从中学发展而来。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由贝满中学发展而来,华南女子学院是由福州硫英女子学校发展而来。由此看出,教会女子学校初级阶段的发展,为中国教会女子中学和大学的相继创办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再者,教育体系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教会女子小学的出现、发展与完善客观上要求中学水平学校的出现,待中学发展成熟后,也必然呼唤着教会女子大学的产生。从金陵女子大学创办原因看:当时江浙地区大部分教会女子中学日益发展,许多女中学生在毕业后升学无门,这就需要更高水平的学校出现,满足众多学生的升学需求。而且,教会女子中学的蓬勃发展急切需求女中师资的培养和补充。据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20年代初,仅江苏一省就有美国教会女校22所,学生达到2068人,[3]但是大学程度的中国女教师却根本无从寻觅。所以,教会女子大学的出现一方面解决了女中的师资问题,一方面满足了中学毕业生的升学需求。而它的出现也正适应了教会女学的发展规律,是学校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二、传教士舆论宣传的引导作用
在受男尊女卑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社会,女子能接受的教育就是在闺阁里进行德行教化,而知识教育体系一直将女子置之门外。所以,当传教士们来到这样一个国度,并希冀通过兴女学对女性进行宗教感染,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出乎意料。为此,传教士们不遗余力地做了诸多努力。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报刊杂志,介绍西方女性观,论述女子接受教育对后代、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性。如《万国公报》的创办者林乐知在提倡女子接受学校教育,革除落后的男尊女卑观念上做了很多努力,他在其《重视教育说》里谈到,女子接受教育与否,是中国与西方存在差别的关键所在。“女人无学,终不能得真实之兴盛。西国教化之文明,未始不由于振兴女学之功,此则尤有厚望于当国者也。”[2](P418—419)在其《中国振兴女学之亟》里,他认为“男女等人耳,何分缓急,夫欧美女子,为农、为工、为商、为士、为官署之父案,为报馆之记者,为学堂之教员,为医院之医生,且有人红十字会者,皆亲历枪林炮雨之间,而伤兵病卒之治疗看护,为其专职,虽不与当兵之役,而已过半矣。”[2](P235)林乐知在其文章中认为,中国社会应该男女平等,女子同男子一样,可以从事各种行业,对国家同样可以有重要的贡献。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谈到“人有读书之父,固可因父而开知识,如有读书之母,更可因母而益聪明,况引孩提入学问之途,莫善于母”。从文章中可看出,狄考文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对后代的培养成才有重要作用。传教士韦廉臣1899年在其《治国要务论》里,把女子接受知识教化与国家兴旺发达相提并论,认为“妇女失教,非惟家道不成,而国亦坏其强半矣”,“坏其男半,几将通国之人而尽坏矣”,“教训妇女一端,尤国之所万不可缺者矣”。[4]因而女子接受教育是国家万万不可缺少的。
西方传教士对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和创办女子学校进行的竭力宣传,有助于中国的有识之士重视女学和倡导女学,有助于整个社会风气渐开,有助于鼓励更多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最终有助于从舆论上推动教会女学的兴盛发展。
三、中国社会风气日开的产物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从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甲午战争后的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以及20世纪初期反封建反旧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涤荡冲击着人们的头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化,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因而社会风气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随着愈来愈多教会女学的创办,自洋务运动开展后,一批受到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社会风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女子走出家庭樊笼,走向社会,去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已经渐渐被社会所接纳。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如郑观应在1892年发表《女教》,认为中国应仿照西方,提倡女学与男学并重,倡议增设女学。而维新派更是把兴女学、办女教提升至“强国保种”的高度,梁启超将女子教育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5]在维新人士思想言论的影响下,上海、广东、苏州、湖南等地私立女子学校纷纷建立,兴办女学成为了当时一股社会热潮。
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对兴办女学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先是于1906年2月,慈禧太后发布了关于振兴女学的谕令。随后第二年3月,《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便公布于众。[6]从此,中国官办女学开始出现。中国朝野上下对兴办女学态度的转变,更是为20世纪初教会女子大学的相继成立提供了契机。1911年,美以美会在华教育秘书盖蒙韦尔洛敏锐提出:“近年来在中国的急速变化,需要受过高级训练的妇女来担任教育工作的要求日益迫切。”[7]中国社会风气日开这样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教会女子学校的兴盛发展。
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女大学生毕业人数日渐增加,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女学生选择赴中国传教,女传教士数量的增多也有助于教会女子学校的开办。同时,男子教会学校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创建,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校的开办起到了激励和参照的作用。
教会女子学校在中国的建立与成长,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虽然由于其宗教传播的办校初衷致使其发展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它作为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先声地位还是比较中肯的。它的出现,动摇了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给予了中国女性打开知识大门进入社会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为国人自主兴办女子学校树立了样板,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1] 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215.
[2]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3] 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城研究——江苏省[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85:574.
[4] [英]韦廉臣.治国要务论[J].万国公报,1889—2(复刊1):10164.
[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论女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9:43.
[6] 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50.
[7] [美]华惠德.初创时期的福建华南女子大学[J].教育评论,199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