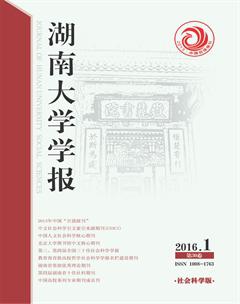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
姜哲
[摘 要]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 经学;现代化;小学;第二朴真;诠释学;后经学
Canonical Interpretation and Belief Reconstructio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JIANG Zhe
(Liberal Colleg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Qianjia School” in Qing Dynasty has seemingly suggested certain possibility of modernization of Confucianism. Nevertheless, it latently exert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xegesis of Confucianism, which identifies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words in scripture, linguistic rules, and textual criticism with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Canons. “Gushi Bian Schoo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rther endeavors to drastically overthrow Confucianism by reasoning historical sources from Confucian Canons. In our times of post-criticism, however, Ricoeurian “second na?veté” can help us to retrieve our beliefs of Confucianism. Moreover, western modern hermeneutics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ies to turn Confucianism to meta-Confucianism.
Key words: Confucianism; modernization; textual criticism; second na?veté; hermeneutics; meta-Confucianism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经学的现代化至少可以追溯至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经学以“朴学”而闻名,尤精于小学、考证,即所谓“实事求是”、所谓“无征不信”。“乾嘉学派”主张“由小学入经学”,将经学之本立于小学,其确实渗透出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而且似乎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某种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小学”毕竟不是“经学”,“考据”也无法取代“解经”。“乾嘉学派”所标举的“实证方法”,既是其本质性的特征,也是其无法超越的“限度”。因此,在反思“朴学”的治经理路之时,我们还需要为经学之现代化开出新的路向。
一、前现代的现代性因素:经学之小学化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有言:“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P370)王念孙在《说文解字注·序》中更是以一种“独断”(dogmatism)的口吻道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的断语。[2](P1)由此可见,清代经学“小学化”的诠释路向,其以“实证”和“归纳”为核心,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乾嘉学风的形成在学术界尚存争议——这种“前现代的现代性(modernity)因素”究竟是中国传统经学及学术的自然演进,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所传播的天文、地舆等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及其技术理性的影响?这一争论虽有逐渐升级的趋势,但迄今为止尚没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出现。而且,无论其争论的结果如何,其实都不会对我们反思“乾嘉学派”的“小学化”经学研究路向构成本质性的影响。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指出:“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成大国了。”[3](P204)实际上,“小学”在清儒手中非但已成“大国”,且更有殖民“经学”以降为“附庸”之势。日本学者池田秀三在《训诂的虚与实》一文中比较了高邮王氏父子在治学方面的差异,他认为王念孙的学问“其根底里尚存有对经之大道的信仰”,而其子王引之则“舍弃大道,以小学本身为终极目标”。[4](P18)具体而言,王引之几乎将“语助”或“发声”的规定发展到了“极致”的程度,其不再是为了注经之用,而是“小学的自我目的化”,[4](P19)即所谓“为学问而学问”。[5](P36)因此,五经文本或《十三经》文本也随之由“圣经”的地位降格为与史、子、集同科,并沦为王引之文字学理论的“注脚”。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回溯“小学”与“经学”在经学史中的关系,以期了解二者等级序列(hierarchy)关系“倒转”的某种缘由。“小学”之名古已有之,其为“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之一,[6](P38)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载,此“九种”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和“小学”。由是可知,“小学”最初确实附属于“六艺之学”,也即“经学”。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现在被视为小学之重要文献的《尔雅》,在《艺文志》中并未被列入“小学”,而是被归于《孝经》类。这一归类是否妥当,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小学”在《艺文志》中所收录的多为“字书”,其范围较为狭窄。后来,“小学”随着经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仅将《尔雅》一类的注经之书囊括其中,也逐渐形成了文字、训诂、音韵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艺文志》中的“小学”不录《尔雅》又可看出,“小学”与“经学”实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为其日后“蔚成大国”甚至脱离“经学”之轨范早已埋下了伏笔,即二者等级序列关系“倒转”之可能性已经被预先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