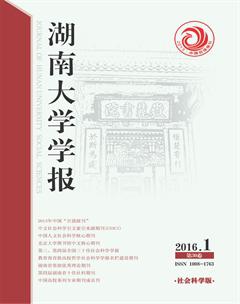欧洲与亚洲对二战的记忆反思
[摘要] 简要介绍了欧洲二战记忆研究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探讨欧洲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 并以中日为例子来谈东亚二战记忆的历史性演变。二战在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亚,二战与区域事务还是有着紧密且消极的联系。这是因为欧洲各个“中介”的良性“谈判”使得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别在过去70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个“中介”“谈判”的不顺畅则使得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不断扩大。
[关键词] 欧洲二战记忆;东亚二战记忆;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1—0133—05
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同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离二战胜利结束已有七十载,由于学术传统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欧洲无论在二战记忆的研究上还是在如何记忆二战的实践上,都走在了东亚前面。本文将详细谈谈欧洲的二战记忆研究及历史现实经验给东亚带来的启示。
一集体记忆研究理论及方法
进行国家性或区域性战争记忆研究的理论核心是“集体记忆”,指的是为一个群体所共享并且可以被代代相传的记忆。欧洲对“集体记忆”的研究由来已久,堪称此类研究的鼻祖。 通过不断的改进更新,“集体记忆”已成为流派众多且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集体记忆”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其先驱是法国社会学家M. Halbwachs。风行于当时的认知心理学认为记忆是一种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个体行为,因而“集体记忆”的众多观点算是对权威的一种创新和挑战。M.Halbwachs1925年著作的英文翻译本: Maurice Halbwachs and Lewis A. Coser,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对集体记忆的理论性讨论,见:Anne Whitehead, Memory (Routledge, 2009).可是Halbwachs的一个观点自提出以来已遭受过无数批判,即:个人的记忆只能反映集体记忆。这一观点过分地强调记忆的集体性而忽视了个体进行记忆的能力。甚至有学者指出,“集体记忆”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因为不是所有人对某一事情的记忆都一样,这个词却企图将不同个体的行为思想以“集体”的名义囫囵个儿地弄成一个表面上的整体。
那么,到底如何才能联结“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呢?虽然这个问题至今都没得到彻底完美解决,但很多学者提出过一些可行的应对之策。比如,学者J. Winter和E. Sivan认为应将重心从“记忆”或者“想起”这一行为的结果 (collective memory) 转移到“记忆”或者“想起”这一行为本身(collective remembrance)上去。
J.Winter and E. Sivan (ed.), 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虽然这两个英文词条都翻译为“集体记忆”,但两者的含义却大相径庭。后者指的是一种群体集结过去的碎片并将它们在公共空间中拼凑的行为,而前者则是这一行为的产物。
根据这一思路,联结“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则是“中介”(home agens,行动中的人)的行为。个人,组织,国家政府,跨国家机构,以及对集体记忆进行过“塑造”的任意一方都可以被定义为中介。Winter和Sivan认为,中介的行为并不是总是服从于自上而下的指挥,很多的纪念是社会性的、自发的,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之后。再者,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中介通过“谈判”来实现其对集体记忆的构建塑形。在二战记忆领域,这种谈判常常被描述成各团体个人为其独特的记忆而抢夺话语权的战场。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6年第1期杨婵:欧洲与亚洲对二战的记忆反思
总之,以“中介”行动为研究对象的“collective remembrance”理论体系现在被广泛地用于西方二战记忆的研究中,它对东亚二战记忆研究也极具指导意义。
将集体记忆理论用于研究国家性及区域性战争认知花了很长的时间。代表性学者有上面提到过的J.Winter, 他的研究集中在一战记忆,及小范围的战争记忆及跨国战争记忆;以及研究犹太人大屠杀记忆的James Young。
比较研究被誉为分析的基本工具,常常被欧洲二战记忆研究者使用。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找出那些看似地方性实则为各地共用的经验,也可以找出那些真正极具地方色彩的二战记忆。
D.Collier,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n A. W. Finifter(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 (Washington, DC: Amer Political Science Assn,1993), p.105.H. William Sewell, ‘Marc Bloch and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6 (1969), p.211; V.E.Bonnell, ‘The Use of Theory, Concepts and Comparis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 (1980), 156-173. 因此,比较东亚不同国家间,以及东亚区域和其他区域间二战记忆的异同,对理解东亚地区在记忆与反思二战方面的独特性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团体越大,就越难找到一种对所有人来说都共有的记忆。如何才能有效把握国家乃至区域层面二战记忆的脉络呢?西方学者常用的方法是以一个小范围地区为案例研究来以小见大地洞悉整个国家及区域的二战记忆。《Beyond Berlin》一书收录了多篇关于德国首都柏林之外城镇二战记忆的研究报告,充分深刻地展示了德国地方与国家性二战记忆的多样化互动以及战后德国社会与纳粹遗留做斗争的细节,是这类小范围案例研究的代表著作。G.D. Rosenfeld and P. B. Jaskot, Beyond Berlin: twelve German cities confront the Nazi past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2. 通过研究一批东亚代表性城市的二战记忆活动来把握整个东亚区域二战记忆的方法是可行的。
做记忆研究,应该从哪着手呢?欧洲二战记忆文献提到过很多影响国家及区域性二战记忆的因素,如诸多无法预见和控制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中介”的行为以及二战记忆的话语体系都受到这些背景的影响。这些背景可以是国际化的,比如冷战,也可以是国内的,比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氛围以及语言和文化传统。所以,在探讨东亚二战记忆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东亚的国际关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东南亚国家华人和当地人的矛盾等背景性因素。
法国历史学家P. Nora的概念“记忆之界(realm of memory)”的意义也很深远。他主张,当记忆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环境已经消失的时候,记忆之界就产生使记忆得以延续留存。他承认在各种“界”中所保留的记忆事实上已经是某种历史,但它还是有记忆的特点,那就是主观性的情绪化附加,这将它与客观的无情绪的历史区别开来。“记忆之界”非常的广泛,可以是物质的,象征的,或者是实用的。 J.Ass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tique, 65 (1995),125-133. 欧洲二战记忆研究的具体切入点也往往是这些“界”,如:回忆录,烈士及死难者纪念物,国歌,战争纪念日,教科书,博物馆, 歌曲、电影、小说等战争文艺及学术作品。东亚的二战记忆也可以通过这几种记忆之界来研究。比如,使用纪念建筑及博物馆的见 B. Niven and C. Paver, Memorisalisation in Germany since 1945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使用电影资料的见:M.A. Bracke, ‘From Politics to Nostalgia: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 memories in France during the 1960s-1970s,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41 (2011), 5-24.
二欧洲二战记忆
学者Lagrou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在1945年和1965年间二战记忆演化做过一项比较研究。
Lagrou, Pieter, ‘Victims of genocide and national memory: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1945-1965, Past and Present, 154 (1997), 181-222. 通过比较,他发现了这三个国家的一些相似点,比如因为这一时期盛行的反犹太主义,国家自信危机,和冷战造成了关于犹太人二战记忆在这三个国家二战记忆中的缺失。他还发现了每个国家二战记忆的特别之处。比如,他指出,作为一战中立国荷兰并没有纪念大战的经验,而解放前的严冬使得荷兰国内居民和抵抗者的艰辛差不多。因为这些特殊情况,所以与法国和比利时相比,关于二战中抵抗者的记忆在荷兰并不流行。
也就是说,在二战结束之初虽然欧洲各国对那场战争的记忆有相似之处,但就连同属西方阵营的国家间他们的二战记忆都有很大不同。可现在的欧洲却建立了一种使各国都相对满意的共同二战记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归功于各个“中介”, 在战后漫长的七十年中他们通过良性“谈判”,依次建立了欧洲各国国内及整个欧洲范围内相对统一的二战记忆。
二战结束后, 各种关于占领、抵抗、逃亡等战时经历的个体记忆盛行。而且当时的欧洲仍然很混乱,没有哪国政府能够迅速建立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官方二战记忆。因而,这一时期多种非官方记忆和官方记忆能够在一国内得以并存。 但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及个体都曾用尽了各种方式来避免触及二战中的黑暗面,比如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投降叛变经历。而国家政府也开始利用二战记忆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比如苏联结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记忆来宣传共产主义政权的先进性,但这种宣传被苏联政府刻意控制淡化以提醒苏联人民虽然一场战争已经结束,革命还在继续。
Thomas C. Wolfe, Past as Present, Myth, or History? Discourses of Time and the Great Faterland War, ed. Richard Ned Lebow and Wulf Kansteiner,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Richard Ned Lebow, 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ibid.. Unless specially cited,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Lebows collection and Jan-Werner Müller, Memory& Power in Post-War Europe: Studie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冷战开始后,东欧和西欧都想构建一种为本阵营国家所共有的身份认同,二战记忆被有意识地利用以致歪曲。虽然都打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旗号,可是东欧和西欧的二战记忆却被分别贴上了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标签,最具代表性的是关于集中营的记忆。东西阵营的二战记忆都越来越“神话化 (mythologised)”,并且逐渐变得不同。在西欧,个人记忆和逐渐建立起来的官方记忆都倾向积极向上和容易被接受的东西。比如军民齐心完成了敦克尔克大撤退的故事在英国就广为流传,而空袭的惨剧及对德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则被选择性“遗忘”。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也逐步建立起了以受难或者英勇抵抗为主旋律,带有明显共产主义特色的官方二战记忆。Müllern, 2002, Memory & Power, p.4; David Cesarani, Lacking in Convictions: British War Crimes Policy and Natioanl Mem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ed. Martin Evans and Ken Lunn, War and Mem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g 1997).
但欧洲各国的官方记忆绝不是不受挑战且一成不变的。 在西欧,二战记忆的争议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民权社会”(civil society)比较弱的东欧,不仅很多非官方的二战记忆未能被强大的国家记忆所吞噬,一些非官方记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塑造了国家二战记忆,比如个人回忆对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的塑造。Frank Biess and Robert G. Moeller, Histories of the Aftermath: The Legac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ed. Berghahn Books (Berghahn Books 2010).
冷战结束后,在西欧和东欧都有一个解冻二战记忆的过程。非官方与官方记忆都被从意识形态思考方式及敌友模式中解放出来。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之前不备推崇的记忆,如对少数民族的迫害,汉奸行为等等都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但是,二战记忆,特别是新发掘的记忆仍然继续被国家政府利用以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比如,对因政治经济改革而产生动荡的东欧国家,重新构建官方二战记忆尤为重要。像匈牙利就重新建立了一种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迫害为核心的二战记忆。一些新纳粹主义份子,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制造的事件丑闻也使得欧洲整体真诚反思二战的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不可否定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开始真真正正重新客观地省视它们以往的二战记忆。欧洲的融合也促进欧洲公民缩小彼此之间二战记忆的差距,一种使各国都相对满意的共同二战记忆得以逐渐建立。
三欧洲记忆二战经验给东亚的启示
虽然,二战历史问题在欧洲还是存在的, 但二战在欧洲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可是在东亚,二战与区域事务还是有着紧密且消极的联系。比如,二战历史争端问题总是使得中日关系如履薄冰。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欧洲各个“中介”的良性“谈判”使得欧洲国家间二战记忆的差别在过去七十年的演变中不断缩小,而东亚各个“中介”“谈判”的不顺畅则使得东亚各国在二战记忆方面的鸿沟不断扩大。以中国和日本为例。
在1945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无论在物质层面(如重建,战犯法庭,申请褒恤款项等)还是在精神层面(如纪念抗战烈士,看抗战电影等), 抗日战争都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因而各种个体抗战记忆并存。再加上当时中国尚未统一,抗战记忆也因地域而异。不过像战后欧洲一样,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其实也结合人民对二战的犹新记忆进行政治宣传,比如,当时共产党的报刊就有大量将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的残暴和侵华日军的惨无人道做类比的宣传。《日寇屠杀人民办法蒋贼悍然加以运用》,《人民日报》1947年9月9日; 《蓄意内战不顾一切!国民党用高官厚禄收留日寇屠杀同胞》, 《人民日报》1946年9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的官方二战记忆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以及中国人民努力下的悲壮抵抗,和对日本暴行的痛斥。改革开放后,国民党军队抗日的经历也被逐步接收,成了主流官方二战记忆的一部分。
值得一说的是,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在毛泽东时期的新中国,抗日记忆,特别是悲惨的抗日记忆是不被鼓励的。可如果仔细研读这一时期的史事资料,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日军暴行记忆是新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斗争中的一把利刃。比如每当中日或者中美政府交恶时,中国政府就会大量地揭露或鼓励民众回忆日军暴行,用以进行谴责(在美国支持下的)日本政府军国主义复辟行径的宣传。比如1958年中日长崎国旗受辱事件发生后中日交恶,国内立刻掀起了一场诉说日军侵华惨痛记忆的高潮,1960年5月9日到15日间全国有33座县市结合日军暴行记忆开展了反美日安保协定的大规模集会。
关于1958年后日军暴行记忆的高潮见这一时间段人民日报的报道。《全国已有近九百万人集会示威支援日本人民正义斗争》,《人民日报》1960年5月15日。 日军暴行记忆在新中国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万人坑,杀人塘之类等为数众多的阶级斗争阵地以及诸多以日军暴行为中心的民众自述的忆苦思甜故事,都是这种地位强有力的证明。
比如,南京在文革期间组织的忆苦思甜会,夏季乘凉会上就总是有老贫农关于“日本鬼子”奸淫掳掠或者自身手指及双耳被日本人割掉的控诉,《忆苦》,《新华日报》1969年11月24日《认真搞好两忆三查》,《新南京日报》1970年5月17日;《一定不忘阶级苦》,《新华日报》1976年12月18日。
日本方面,只看到日本人自身在战时战后所遭受的苦难而忽视对其他民族人民所造成的伤害的“受害者意识”一直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共有。但就二战记忆具体内容来说,日本各个“中介”在国内的“谈判”仍未完成,一个统一的日本二战集体记忆仍未建立。
战后初期的日本,曾兴起过一段对其战时行为和战争责任的讨论热,这种讨论非常的多样化且总体上是很进步的。
如:《“戦争責任者”とは何か 大勢に流れても“罪”の枠に嵌る》,《読売新聞》1945年11月1日; 《戦争責任の究明 人民自らで処断 作れ》,《読売新聞》 1945年11月29日。1952年占领结束后,日本保守政府通过一些强硬手段逐步取代进步力量在二战记忆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 比如,日本文部省颁布了有关教科书审查制度的法令以求遏制左翼教科书的出版。所以,军国日本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就几乎从日本教科书中消失了。
Yoshida Takashi,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日本政府也开始了利用战争纪念日及仪式,如始于1963年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来建立一种以相同二战记忆为基础的国民纽带。但其他非官方二战记忆并没有消失并且不断地挑战着甚至取代过官方记忆。各流派 “中介们”所支持的二战记忆互相竞争这一日本二战记忆的特性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竞争性”充分体现在战后日本政府与非政府群体人士二战记忆,以及全国性与地方性二战记忆之间的冲突对立中。 比如虽然广岛原子弹爆炸经历总是被日本国民当作是日本在二战中受害的象征,但是广岛的地方记忆是独特的,并且与日本其他地域以及国家二战记忆并非总和谐一致甚至时有冲突。
讨论广岛原爆记忆的文献:L. Yoneyama, Hiroshima traces : time, space, and the dialectics of memory (Berkeley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奥田博子:《原爆の記憶》,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10年. 广岛地方政府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広島県(编):《原爆三十年》, 広島県, 1981年;中国新聞社(编):《ヒロシマの記録》,中国新聞社,1986年. 地方媒体对广岛记忆的宣扬,见:中国新聞社(编), 《 NHKと中国新聞の原爆報道》,NHK, 2003年.
再来看看中日两国间关于二战记忆的“谈判”,则更是不顺畅。首先,冷战使得东亚各国间的二战记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因而产生差异。1972年中日建交常常被看作是东亚冷战体系松动的第一步。可是东亚各国战争记忆的差异并没有因为各国恢复正常交往而缩小。
中日之间二战记忆的差异在1972年建交谈判时就已引起轩然大波。田中角荣首相几次三番将日军侵华说成是给中国“造成了麻烦”,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最后,两国在建交公报中的互相妥协看似完满地解决了此事,实则只是对这种差异无可奈何的暂时搁置。
张香山: 《中日复交谈判回顾》, 《日本学刊》1998;姬鹏飞:《饮水不忘掘井人》, 安建设(编) 《周恩来最后的岁月》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説》,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 2002。中日两国失去了缩短二战记忆鸿沟的黄金时间,以后又因为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芥蒂,这种鸿沟不断扩大。众所周知,自建交后,两国因二战记忆之差所起的矛盾其实是源源不断的,如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成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就话题不断的“靖国问题”,以及日本政客在二战历史方面的屡次“失言”等等。
总之,经过战后近七十年的演化,东亚各国对同一场战争的记忆逐渐变得不一样,且对外人来说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日本人来说,中国战争记忆的问题在于对“日本鬼子”的极端仇恨和丑化,以及对中国人民英雄主义的过度赞扬 (这点在饱受诟病的中国抗日神剧中尤为突出)。而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战争记忆的问题在于:民族主义群体对“大东亚战争”的美化,修正主义群体对日军暴行的否认,一般民众的侵华战争“健忘症 (amnesia)”,以及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受害者意识。东亚各国间二战记忆的不同导致了这些国家在二战历史方面的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又常常与现实争端(如中日钓鱼岛/尖阁诸岛之争)纠结在一块,愈发不可调和。在二战胜利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如何在二战记忆方面求同存异,是摆在东亚各国面前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欧洲记忆及反省二战的实践以及研究二战记忆理论,总结了一些对东亚有用的相关经验。东亚各国对于七十年前那场旷日持久伤亡惨烈战争的记忆不可避免的有不同之处,但作为二战记忆的“中介”,各国民众团体、政府及区域内跨国机构应该进行“良性谈判”以缩小各国二战记忆的差别。任何歪曲历史事实及否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行为言论只会大大减缓建立融洽东亚二战记忆的速度,以及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