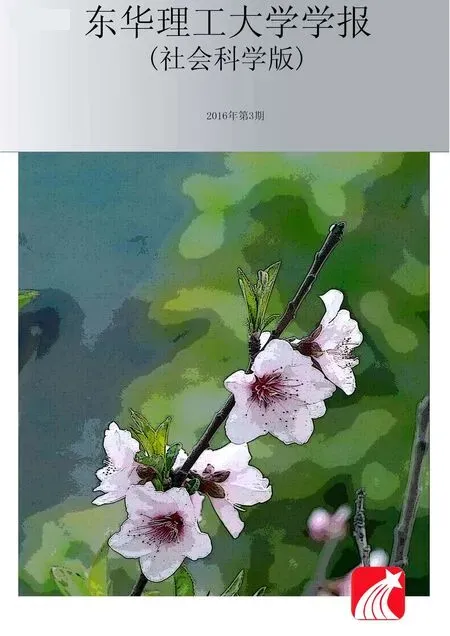从《劝善记》到《牡丹亭》
——晚明思潮与戏曲出口
罗丽容
(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222)
从《劝善记》到《牡丹亭》
——晚明思潮与戏曲出口
罗丽容
(东吴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222)
晚明通俗文学勃兴,传统将戏曲、小说、民歌视为小道的狭隘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些通俗文学的艺术魅力与社会功能有如猛虎出柙、洪水泛滥一般,席卷了宋元明以来,被程朱理学控制,长达数百年的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牵系着旧社会中的每一颗人心。追根究底,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明代正德、嘉靖后兴起的理学别支——心学,有莫大的关系。明正德间王守仁倡“致良知”、“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等观念,吹起了心学的号角,也使得士大夫之间的风气,由心驰魏阙,竞逐外务,纷纷转往内心世界的探索。同时,心学左派领袖,号称阳明弟子的王艮,也发展出一套与程朱理学相悖,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欲的泰州之学。此风靡当代的心学,蔚为一股社会人文思潮,解脱了几百年来,被理学所束缚的苦闷人心,开拓了当代人的眼界,在文学与艺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在当时所流行的戏曲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上,这股力量,后代人是绝对不能轻估的。以《劝善记》《还魂记》两本传奇剧本为主,探讨在心学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下,代表着当代普罗大众思想的通俗文学创作家如何抨击、维护中国传统思想,并且以一种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劝善记;牡丹亭;郑之珍;汤显祖;晚明思潮
罗丽容.从《劝善记》到《牡丹亭》——晚明思潮与戏曲出口[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10-224.
Luo Li-rong.From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to The Peony Pavilion——Outlet of ideological trend and Chinese opera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10-224.
元末明初,文风浮滥,出于治国之需,朱元璋起用宋濂、方孝儒、刘基等人,这些文臣注重实际,强调事功,因为重实际,阐发文道合一之主张不遗余力,所以思想主流又退回程朱理学的老路子,然因彼等所学较为驳杂,非执一之论可概括,徐渭论宋濂曰:“金华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于学也以文。”故文、道二端实为明初论文之根本。认为只有合于先王之道,能经世致用的才是好文章,故以“明道”为文,以“致用”为本,此即为明初论文宗旨,虽然嘉靖、万历后阳明心学勃兴,成为晚明思潮的主流,然拥护程朱思想之支脉却从未消歇。
嘉靖、万历后,通俗文学勃兴,传统社会将戏曲、小说、民歌视为雕虫小技的狭隘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与挑战,这些通俗文学的艺术魅力与社会功能有如猛虎出柙、洪水泛滥一般,冲毁了宋元明以来长达数百年,所充斥的程、朱理学的风气,牵系着旧社会中的每一颗人心。追根究底,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明代正德、嘉靖后兴起的理学别支——心学,有莫大的关系。明正德间王守仁倡“致良知”、“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等观念,吹起了心学的号角,也使得士大夫之间的风气,由心驰魏阙,竞逐外务,纷纷转往内心世界的探索。同时,心学左派领袖,号称阳明弟子的王艮,也发展出一套与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教条相悖,充分肯定自我、肯定人欲的泰州之学。此新兴之学风靡当代,蔚为一股人文思潮,解脱了几百年来被理学所束缚的苦闷人心,开拓了当代人的眼界,在文学与艺术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映在当时所流行的戏曲小说的创作与批评上,这股力量,后代人是绝对不能轻估的。
传统儒家教育特重诗教,所谓的“兴、观、群、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社会道德角度来评论诗歌的观点,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不知不觉的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观点,文学艺术中所该有的独立性与美学价值,被传统的道德教化功能所取代,沦落为附庸地位。这种情况受到晚明心学的影响,慢慢地产生了变化,表现在戏曲小说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但是也有些创作完全无视于这股新兴的心学潮流,仍然稳定的走着程、朱传统的老路子,这种一新一旧的对比,十分明显,但也同样的贴近民间。
本文主要以两本明代传奇剧本:《劝善记》(此系《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之简称,下文皆采用简称)与《牡丹亭》为主要探讨对象,观察在晚明思潮纷腾的影响下,代表普罗大众思想的戏曲作家,如何面对、如何反映当代思想的面貌,并且以一种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1 晚明思潮的重要人物:从陈白沙到王阳明
1.1 陈白沙与心学
陈白沙是陆象山心学过渡到阳明心学的桥梁人物,也是士人道德修持上寻求回归自我为本位的先声人物,其学说重点归结如下:
(1)与儒家思想相合之处。以“学习圣人”为人生理想,然并非墨守成规。
夫士何学?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而奚陋自待哉[1] 28。(《古蒙州学记》)
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1] 20。(《道学传序》)
可知陈白沙虽谨守《六经》之书,然而要求学者学习经典要取其神髓而弃其糟粕。神髓者,读其书而能求诸吾心之机,察于动静、致养自身;糟粕者,徒诵经典而已,只知表面之言,外混乱于闻见,内支离于耳目,则读书抑犹如玩物丧志之事也。
(2)与道家思想相合之处:主张“克去有我之私”。陈白沙云:“大抵虚己极难,若能克去有我之私,当一日万里,其它往来疎数不计也。”[1] 162此处的“私”,所指为何,许多学者认为白沙没有明说,其实白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一个“我”字,一个人如果处处以“我”为出发点,就无法谦虚下人,如果克除了“我”的偏狭观念,所有的修为“一日万里”都有可能,更遑论其他人我往来的小节了。
此处的“克去有我”受到《庄子》的影响随处可见,如《庄子·大宗师》云:
颜回……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2] 284-285
此处借着孔门师生对话,说明克去我私(忘我)必须要形若槁木(堕肢体)、心若死灰(黜聪明)、冥同大道,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方能够旷然与变化为体,无不通达。
又如《庄子·应帝王》云: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2] 287
此言有虞氏不免怀藏仁心,以要结于他人,虽能得于人心,但是未必超然于物外;而泰氏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任人呼己为牛马,皆不与之计较,他的所知是真实的,他的道德是真实无伪的,超然物外的。
陈白沙所谓的“克去有我之私”应该与此有关,只要打通“有我”此一关节,则名利私欲一概不在眼中话下了。
(3)与佛家思想相合之处:强调人与禽兽之别,在于“心”与“理”。陈白沙《禽兽说》云:
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1] 61。
他非常反对人只凭靠本能过日子,他认为我们身体的组合是:“浑是一包脓血里一大块骨头”,争权夺利之外,穿衣吃饭、好行淫欲、喜怒哀乐,全凭气血指挥,如果再不肯在“心”和“理”方面下功夫,跟禽兽相较,其实是没有两样的。这种思想受到佛教“不净观”的影响颇深,例如:
复次,诸比丘!比丘于皮覆包充满种种不净物之此身,观察此身,上至头发,下至跖底,知:“于此身有发、毫、爪、齿、皮、肉、筋、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肠、肠间膜、胃、排泄物、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液、唾液、黏液、关节液、尿。”诸比丘!犹如两口之袋,填进种种谷物,即:稻、粳、绿豆、豆颗、胡麻、糙米,具眼者开解之,得观察:“此是稻、此是粳、此是绿豆、此是豆颗、此是胡麻、此是糙米。”……如是,或于内身,观身而住;于外身,观身而住;又于内外身观身而住。或于身,观生法而住;于身,观灭法而住;又于身,观生灭法而住。尚又智识所成及忆念所成,皆会“有身”之思念现前。彼当无所依而住,且不执着世间任何物。诸比丘!比丘如是,于身观身而住。(《大念处经》)[3] 278
复次,比丘观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随住,随其好恶,从头至足,观见种种不净充满,我此身中有发髦爪齿、粗细薄肤、皮肉筋骨、心肾肝肺、大肠小肠、脾胃抟粪、脑及脑根、泪汗涕唾、脓血肪髓、涎胆小便。犹如器盛若干种子,有目之士,悉见分明,谓稻、粟种、蔓菁、芥子。……如是比丘观内身如身,观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见,有明有达,是谓比丘观身如身。(《念处经》)[4]
不净观为四念处中的身念处,又可分为观察自身以及墓园九观两者。由墓园九观又发展出所谓的“白骨观”。根据《俱舍论》卷二十二、《大智度论》卷十九等载,修此禅观能对治:贪爱色身、男欢女爱等欲望。方法是在禅定中观想,自身与他身之污秽不洁,修此禅观,以消除对人世间的贪恋,坚定出示修行的决心。
以上论述可知陈白沙之学,已经倾向于揉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炉,而特重自身之体悟,所谓悟道的功夫,也就是读书人的涵养以及境界的高下:
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与贺客恭黄门》)[1] 133
然尝一思之,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复张东白内翰》)[1] 131
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脗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丽案:当为卸)衔勒也。(《复赵提学佥宪》)[1] 145
道可以自我追求而得,如果未得,盖心与理未能吻合之故,此时就要用静坐对治,静坐可以澄心,澄心可以养出端倪,精神处于完全自然的圆融状态,不粘不滞,不执着,达于“与道为一”的精神境界。
1.2 王阳明心学之生发与传播
陈白沙之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出现阳明心学,这是继宋代程朱理学之后,对中国思想界引发重大影响的思潮。王阳明正式讲学是在贵阳文明书院讲知行合一开始,然则讲学之影响扩大则始于滁阳,正德八年(1513)学生已有数百人之多,《年谱》云:“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地请正,踊跃歌舞。”[5] 1236这种讲学的特色就是真情加上高度的热情,才有数百人环龙潭而坐、随地请益,踊跃歌舞的情况。其后阳明学说传播四方,造成嘉靖年间士大夫争相仿效学习的风气。归纳其学之所以影响重大的原因如下。
1.2.1 朝廷无理的抑压,造成反弹
朝廷将阳明之学定调为“伪学”,《明世宗实录》云: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殁后恤典,俱不准给。都察院仍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朝廷之所以会禁止王学的原因,充其量只是害怕王学的流播,影响朝廷统治者的地位,因为陈白沙、王阳明之学,提倡只要自我修持,人人都可以为圣人,对传统儒学做了新诠释,使得自明初以来只尊程、朱的朝廷,备感威胁,只想打击王阳明,重新回归程、朱的老路,对统治者来说是比较安全的。然而这种无理的打压,却造成了一股另外的潮流,朝廷当然也不愿意让步,冲突之下,阳明心学名气日益壮大,追随他的人反而更多。
1.2.2 从龙场驿贬谪中,对死生问题大彻大悟
庄周云:“死生亦大矣”,一个人不管生前是荣华绕身,或者穷困潦倒,死生问题是每个人最终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责无旁贷。王阳明无罪被谪龙场驿,面对的是居无房、食绝粮、病痛缠身的窘况,举凡生活所需,皆须亲自动手、重新打理、从头做起、生死只是一线之隔;他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看破生死,大彻大悟,阳明学说的核心价值:致良知、格物致知、吾性自足,都在这种情况下悟得。原本宠辱皆惊、自伤自叹、有志难伸、病翼难飞的心境,都在一悟之间被彻底摧毁。从犹疑不定转向泰然自信,从自怨自艾变成万虑皆抛。之后在龙冈书院、文明书院讲学,将这样积极、自信、凡事求诸良知良能、去天理存人欲的体悟完全传达给他的学生,“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何不将求富贵浮名的心态转而求道,况且此道不难,求诸自心的良知良能而已矣,这样的核心价值也间接影响了士人面对生死的观念。
1.2.3 “致良知”学说的考验
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功高而谤毁随之而来(如太监张忠、安边伯许泰等挟天子以邀功,蜚语中伤王阳明与宸濠是故交,及王阳明攻破南昌,进入宁王府后,曾烧毁一批书牍之类),对王阳明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他可以处变不惊、坦然以对,心中所依靠的就是“致良知”的信念,他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俱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5] 1278-1279“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6] 59此种思想的核心价值,成功的通过了现实对王阳明的考验,士人因此更加信服。
1.2.4 朝廷不肯重用王阳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间接促成王学的发展与流播
王阳明平宸濠之乱,功劳之大,满朝文武,无有异议者,但是正德、嘉靖两朝却对他的能力有所忌讳,不肯重用,嘉靖皇帝甚至昧着良心说他是“中材”,既要用他,又不肯信任他,还诋毁他为中等之材,蔑视之情,莫此为甚,他人看在眼里,也都为他抱屈,直接间接的也促进王学的传播。然而再恶劣的环境都挡不住一个圣人的出头,王阳明在这种“朝廷不找,无事困扰”情况下,晚年反而有功夫补足了王学的完整性,他将王学归纳为四句表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5] 1307;“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5] 1307。可见王学所特别强调的自性自足之外,就是知行合一的功夫,阳明原始的初心也在于改变世风、提升道德的修持,这在晚明也形成了士子之间竞相学习的风气。
1.3 晚明心学的反动
王阳明虽然平定宸濠之乱,事实上朝廷并不信任他,朝臣反对奖学之风,《明武宗实录》甚至说平定宸濠之乱的首倡者是伍文定,而非王阳明:
庚辰,吉安知府伍文定及提督南赣汀漳军务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讨宸濠。初,守仁奉命勘事福建,以宸濠生日将届,取道南昌贺之。会大风,舟不得前,至丰城,知县顾佖以变告。守仁大骇,遂弃官舟,取小艇,潜迹还赣;时宸濠与其伪国师刘养正谋,使人追之,不及。文定闻守仁还,急以卒三百迎于峡江,至吉安,进曰:“此贼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其势必无所成。公素望重,且有兵权,愿留镇此城,号召各郡邑义勇为进取,图贼不难破也。”守仁初不许,既而深然其言。
此记载完全抹杀了王阳明的事功,也同时影响了其他人的看法。谈迁《国榷》、李实《明一统志》等书籍,都参照了《明武宗实录》的说法,认为伍文定的功劳在王阳明之上,可见朝廷对他猜忌之深。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种状况下,顺着朝廷的意旨,露脸出来打压王阳明的投机者也不在少数,主修《明武宗实录》的杨廷和,因为不满兵部尚书王琼,又王琼支持王阳明,也一并贬低王阳明之功劳。太监张永甚至逮捕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入锦衣狱,严刑逼供,要他交代王阳明是否为宸濠的同党人,元亨终无一言,惨死狱中。
嘉靖元年(1522)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倡议论劾王阳明心学之非;二年(1523),南宫策士亦公然贬抑王学,朝廷对王学的非议日甚一日,最主要的是皇帝的不重用与猜忌,《明世宗实录》云:
士大夫学术不正,邪伪乱真,以致人材毕下,文章政事日趋诡异,而圣贤大学之道不明,关系治理,要非细故。朕历览近代诸儒,惟朱熹之学醇正可师,祖宗设科取士,经书义一以朱子传注为主,诚有见也。比年各处试录文字,往往说诞支离,背戾经旨。此必有一等奸伪之徒,假道学之名,鼓其邪说以惑士心,不可不禁。礼部便行与各该提学官及各学校师生,今后若有创为异说,诡道背理,非毁朱子者,许科道官指名核奏。
这里所提到的“伪学”指的即为王阳明的心学,最怕的是王学兴盛后,对朝廷的统治造成危机,而程、朱的道学,相对比较稳当、有利于朝廷的统治基础。所以阳明死后即下令禁止王学,另一方面程、朱理学固有的价值观仍然处于正统的地位,对阳明及其弟子之心学有激烈的批评,甚至公然鄙薄讲学之风与讲学者之程度,罗洪先《别萧曰阶语》云:“始端升就外傅,先太史公命之曰:‘吾不愿汝讲学,世之讲学者,皆可知也。吾愿汝立好心、行好事,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做得十分便,是十分好人矣。’端升不敢忘。先生何以教之?以庶几不辱。”[7] 648可知当时对心学兴起后的讲学之风是大有非议的。在这股反对心学、拥护程朱理学的潮流下,所兴起的最贴近民众、最具有教化价值的文学艺术创作,最经典的代表就是郑之珍《劝善记》了。
2 《劝善记》与“程朱阙里”
郑之珍生于正德戊寅年(1518),卒于万历乙未(1595),徽州祁门县清溪村人。徽州是程、朱理学传播的重要地区,时人称之为“程朱阙里”,郑之珍自幼所接受的教育也离不开程、朱理学之范围,所以《劝善记》中处处有维护儒家程、朱思想的痕迹:
2.1 从《劝善记》之主旨观察
《劝善记》以“劝善”为主旨,以“救母”为情节,分上中下三卷,主要在阐发程朱理学中,调和儒释道三教的新儒家主张,而使天下民心重归于程、朱,其用心可谓良苦矣。兹引下列序文之片段,更可认清郑之珍写《劝善记》之主旨与动机耳。其一,郑之珍《自序》云:
时寓秋浦之剡溪,乃取目连救母之事,编为《劝善记》三册,敷之歌声,使有耳者之共闻;着之象形,使有目者之共覩。至于离合悲欢,抑扬劝惩,不惟中人之能知,虽愚夫愚妇靡不悚恻涕洟、感悟通晓矣,不将为劝善之一助乎!……余学夫子不见用于世,于是惧之以鬼道,亦余之弗获已也。盖惧则悟矣,悟则改矣,改则善矣,余学夫子之心亦少慰矣[8] 1。
其二,叶宗春《叙〈劝善记〉》云:
盖自释老出而圣道三分,吾无取焉耳。及其清静无为,绝业缘而度苦海,吾有取焉耳。彼目犍连者,释而翘也。夫释氏无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而连也,急急于父母之恩,死生之际相甚矣,何释之道也?高石郑子世儒哉,乃取而传之,神似轮回,幻似鬼魅,鼓以声律,舞以侏儒,诚不啻传注之训圣经,然是遵何儒哉?郑子曰:“……其术也,吾岂儒而互释哉?吾以此劝善也!夫人之恶生于忍,忍生于吝,而吝生于无所感,夫戏,圣人所以象感也。……感傅相之登假,则劝于施布矣;感四真之幽囚,则劝于悲慈矣;感益利之报主,则劝于忠勤矣;感曹娥之洁身,则劝于烈节矣;感罗卜之终慕,则劝于孝思矣,此其小也。人之所崇者释,而释亦急亲矣,释之乱者无亲,而急亲则儒矣。由是而夷不乱华,墨可归儒矣,是余之心也。”[9] 500-501
由此可知,郑之珍写《劝善记》的用心有二:一则,困顿场屋多年,屡试不中,想藉戏曲深入民间的力量,达成教化民众之初心,亦等同于当父母官之职责矣。再则,藉此流传于民间甚久的佛教故事,宣扬程朱理学(也就是儒家学说)中孝道的部分,由是而“夷不乱华”、“墨可归儒”矣!也就是说儒家思想还是中国的正统,佛教思想不可能顶替儒家思想,墨家的兼爱也可以由儒家思想来涵盖了。
2.2 从《劝善记》目连故事流传广泛的情况观察
郑之珍《劝善记》将明代以前的目连故事做总集结,借着更加完整的目连救母故事,宣扬儒家的孝道思想,使之更深入民间。《劝善记》首刊行于万历壬午年(1582),前此,目连故事已经是长期流传、影响广泛的戏曲及讲唱文学的题材:(1) 《洛阳伽蓝记》卷五记载城北石窟有目连窟。(2)唐代敦煌变文有《目连缘起》《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盂兰盆经讲经文》。(3)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云: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10] 49。(4)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有“打青提”之名。(5)明初《录鬼簿续编》有无名氏《行孝道目连救母》剧目。(6)明中叶以前的宋元南戏剧目中,有《目连尊者》的剧目。(7)明中叶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山西上党区迎神赛社演出的哑队戏有《青提刘氏游地狱》[11] 50。(8)万历年间,沈德符《顾曲杂言》“杂剧院本”条针对目连戏有所评论,云:《华光显圣》《目连入冥》《大圣收魔》之属,则太妖诞[12] 215。(9)万历年间刊行之戏曲选本中,目连戏所属内容,大都有被选入,可见流行之一斑。此类选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劝善记》刊刻前的,一是《劝善记》刊刻后的,一是刊刻于万历年间,而切确时间不明者,说明如下:
第一,《劝善记》刊刻前,有三本:《风月锦囊》选《尼姑下山》《新增僧家记》(嘉靖癸丑年即1553年刊刻);《词林一枝》选《尼姑下山》(万历元年即1573年刊刻);《八能奏锦》选《尼姑下山》《元旦上寿》《目连贺正》(万历元年即1573年刊刻)。
第二,《劝善记》刊刻后,有三本:《群英类选》选《六殿见母》《和上下山》《挑经挑母》(万历二十四年即1596年刊刻);《歌林拾翠》选《花园发誓》《诉三大苦》《六殿见母》(万历二十七年即1599年刊刻);《乐府精华》选《尼姑下山》《僧尼调戏》(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刊刻)。
第三,无切确年代者:万历间《徽池雅调》选《刘四真花园发咒》;万历间《大明春》选《罗卜思亲描容》《罗卜祭奠母亲》;万历间《歌林拾翠》二集选《花园发誓》《诉三大苦》《六殿见母》。
由以上可知,目连故事从南北朝开始到明代,有一段很长的流传与形成过程,而且无论在哪个时代,这个故事化身为各种文类,在民间不断发挥着它的影响力。郑之珍深谙此道,除了让故事更具有完整性之外,还添加了许多与故事无关的,盛行于民间的小戏,主要目的还是怕民众看目连戏时,过于枯燥乏味,故添加一些趣味性的小戏,以飨观众,可谓用心良苦矣!
2.3 从《劝善记》吸收许多与目连主题无关的小戏观察
郑之珍借着小戏的通俗性吸引民众,达成寓教于乐的目的。《劝善记》剧本中穿插了许多与目连救母无关、却在当时非常流行的出目,例如上卷:《博施济众》(此出又名《哑背疯》)、《观音生日》(此出属名为“新增插科”,可见乃郑之珍所新添之出,非搜集旧有者)、《尼姑下山》《和尚下山》《拐子相邀》《雷公电母》《观音劝善》《插科》;中卷的《匠人争席》《斋僧济贫》《过黑松林》(此出又名《观音戏目连》)、《过烂沙河》;下卷的《三殿寻母》(此出又名《三大苦》)。这些都是宋代以来民间耳熟能详的戏码、长期累积的歌舞、表演形式,对民间百姓尤其具有吸引力,举例如下。
上卷《观音生日》之出,旦扮观世音在舞台上千变万化,或为飞禽走兽、或为武将文人、或为鱼篮千手观音,尤其后者,需要后台配合,“先用白被拆缝,占坐被下,内用二三人升手自缝中出,各执器械,作多手舞介”[8] 43,可说是作者煞费苦心,想借着娱乐,将儒家思想的精华传递给民众,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又如《社令插旗》之出,警示意味更浓:小扮社令上云:“世间善恶不同流,祸福皆因自己求。天把恶人诛几个,使人儆省早回头。自家社令是也。昨蒙玉旨勅令城隍,转委卑职捡察一方善恶,善者插一青旗,天公佑之;恶者插一红旗,天雷击之。不免用心,一一捡察。”[8] 111利用民间相信雷公电母雷击恶人之心理,极尽劝善惩恶之能事。
中卷写目连西行救母。唐代敦煌变文中并无详述目连西行救母的情节,只是概略说明目连想报母恩,唯有出家最胜。而郑之珍则掺入民间盛行小说《西游记》的情节,其出目中有《经黑松林》《过火焰山》《过烂沙河》,所出现的人物有白猿、沙和尚、观音等,几乎都与大唐三藏取经有关,可见郑之珍汲取民间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充实自己的创作,构成救母情节中重要的一环节,贴近民间的同时,劝善及宣扬儒家孝道的旨意也就更容易达成了。例如:中卷《过黑松林》又名《观音戏目连》。观音知道罗卜前往西天救母,途中必须经过黑松林,林中多虎豹,观音一方面保护罗卜,一方面也想试探罗卜的道心是否坚定。于是幻化出一间林中小屋等待罗卜前来投宿,自己则变为一妇人佯称丈夫出外经商四、五年未得音讯,对罗卜百般挑逗,先诱惑之以“共枕同衾、凤倒鸾颠”,再威之以猛虎,劝之以酒肉,百般无效,最后哀告之疾病,罗卜道心坚定,皆不为所动,最后观音现身,赐罗卜以观音圣像,嘱咐罗卜,去西天途中若遇苦难,高叫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可解厄。此出主题更贴近民间对观世音菩萨的认知与形象,劝善的效果就更浓了。
下卷《三殿寻母》叙述目连之母刘青提因违誓开荤,打僧骂道种种行径,必须到阎罗三殿受苦的情状。其中借刘青提之口唱了三大段的【七言词】,说明身为妇女的三大苦,首段说明怀胎十月、乳哺三年的辛苦;次段说明妇女养育儿女直到长大成人娶媳妇的心路历程;末段谈论父母身后,子女争产,无人追荐做斋做七,只能身赴地狱受灾殃之苦。案【七言词】并非传统曲牌,应该只是明代流行于民间的小唱,配以七言之词句者,然内容感人、真情流露,充满浓厚之民间气息:
未有儿时终日望,堪堪受喜尚难凭。一月怀躭如白露,二月怀躭桃花形。三月怀躭分男女,四月怀躭形相全。五月怀躭成筋骨,六月怀躭毛发生。七月怀躭右手动,八月怀躭左手伸。九月怀躭儿三转,十月怀躭儿已成。腹满将临分解日,预先许愿告神灵。许下愿心期保佑,岂知一旦腹中疼。疼得热气不相接,疼得冷汗水般淋。口中咬着青丝发,产下儿子抵千金。……痛儿一似心上肉,爱儿一似掌中珍。儿那儿,一日吃娘十次乳,十日百次未为频。……日日抱儿在怀内,难开肉锁重千斤。日间苦楚熬过了,夜间苦楚对谁论。儿睡熟时娘不睡,心心又怕我儿醒。若是夜啼儿吵闹,三更半夜起吹灯。左边湿了娘身睡,右边干处与儿临。右边湿了娘又睡,左边干处把儿更。(飞白)若是两边都湿了,抱儿在胸上到天明[8] 372-373。
乳哺三年将满日,见儿断乳甚孤恓。纔得些些好滋味,省口留下与孩儿。儿能说话娘心喜,儿能行走母提携。母若有事向前去,恐儿又在后跟随。行一步时回一首,好似母鸡顾小鸡。一怕孩儿身上冷,二怕孩儿肚中饥。三怕孩儿遭跌扑,四怕痲痘不疎稀。五怕孩儿犯汤火,六怕孩儿水边嬉。七怕孩儿远处去,八怕孩儿上高梯。九怕孩儿心性懵,十怕孩儿有灾危。……六岁七岁渐乖觉,送儿入学去从师。文房四宝都齐备,一日三餐不敢迟。……做得文章应得考,望儿夺取锦衣归。又虑孩儿年长大,与儿婚配正当时。……一愿媳妇人品好,二愿媳妇好威仪。三愿媳妇心性好,四愿媳妇好奁资。若是般般都好了,愿他百岁乐怡怡。如此和谐三五载,他哝哝唧唧要营私。儿子祇说老婆是,开口便说老娘非。娘亲祇望儿长大,儿全不念老娘衰。老娘身似枯柴样,儿子心也不惊疑。祇道老娘身长在,从容行孝不差池。岂知一旦娘身死,去了没有转来期。燕子衔泥空费力,毛干大时各自飞。奉劝世间人子听,及时行孝养亲闱。孝顺还生效顺子,檐水点点不差移[8] 373-375。
这类型的内容在舞台上演出,既可深入民间与百姓打成一片,又可宣扬儒家孝道的宗旨,可想而知,此剧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
2.4 从《劝善记》的情节编排上观察
《劝善记》全剧凡104出,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34出,写目连小名“罗卜”,自小家道甚殷,敬重三宝,斋僧布施;父亲傅相乐善好施,一心向佛,死后升天;母亲青提夫人,姓刘名四真,本已向佛修行,丈夫死后听信他人怂恿,支使目连外出经商,自己在家则做出了:破戒开荤、打僧骂道、烧毁斋房、用狗肉馒头斋僧等等,许多得罪神灵的脱序行为,其间僧道尼姑、李公等昔日道友前来劝善,皆为刘氏恶婢女金奴所打骂而去。其子罗卜经商获利回家,问起修道情况,刘氏则诓骗罗卜莫听旁人差错之言。中卷36出,写目连之母刘青提种种恶行,天理难容,死后魂魄为城隍起解至地狱受苦。其子罗卜抛开一切家业,辞官辞婚,一头挑母一头挑经,欲至西天见佛,救母脱离地狱之苦。下卷34出写目连十殿寻母、救母,终致达成心愿、一家人受玉帝封诰的事迹。由此三卷可看出郑之珍情节安排之端倪。
2.4.1 儒释道三教合一,而以儒家为先
儒家思想发展到宋代,不得不因应时代变迁而加入佛家与道家思想于其中,揉合成为一个新的思潮,思想史上称之为“理学”又称为“心性之学”。但是无论如何,儒学出身的郑之珍总是对儒家文化精神,多了一些强化,“百善孝为先”,孝道是儒家的重点思想,郑之珍的劝善更是把“劝人行孝”字摆在第一位,下卷《盂兰大会》【永团圆】云:“一家今日皆仙眷,喜骨肉共团圆。感得天天相怜念,愿已遂,缘非浅。这隆恩盛典,感谢情何限。我而今奉劝、奉劝人间,须是大家为善,善皆如大目连。父母劬劳也,须是追荐,追荐共登仙,不枉了平生愿。三教由来本不偏,万古永流传。”[8] 499由这支曲牌所述,可以将作者的企图心看得更加清楚。
2.4.2 借用程朱理学,将释家道家思想纳入儒家体系
郑之珍此剧并不仅以劝善、劝孝为满足,反而借用程朱理学中的“心”、“性”之说,作为统摄三教的基础,巧妙的将释家道家的思想纳入儒家的体系之中。
(1) 上卷《斋僧斋道》出,郑氏藉傅相等人之口,说明儒释道三教个别的特色皆在修善心,然后以儒家思想的孝道演绎此善心:“昭昭三教皆天授,善事天时在自修,修善工夫只在性内求”[8] 15。
【阅金经】释家大要在华严一经,大抵教人明此心。心明时见性灵。心和性,释同儒混成。
【前腔(阅金经)】老君大要在道德一经,大抵教人修此心。心修时炼性真。心和性,道同儒混成。
【前腔(阅金经)】圣人遗下四书五经,大抵教人存此心。心存时在性明。儒释道,须知通混成[8] 13-14。
(2) 除了孝道之外,还弘扬理学家“节烈”与“忠义”观念:节烈的代表人物就是罗卜的未婚妻曹赛英。罗卜因为要西行救母,怕耽误曹女的青春,故而退婚,曹女之继母也逼曹女下嫁前来求婚的富豪段公子,然皆为曹女所拒,剪发出家,以明心志:
【风云四朝元】吾心节义,须臾不可离。叹庸臣恶妇,自把心欺,自将欲蔽,自使行多乘(案:当为乖之误字)戾。卖国欺君,甘心降贼;失节忘夫,甘心再适。真是无羞耻。禽类与蛮夷,夷有君臣,禽有雌雄配。比蛮夷尚不如,视禽兽当知愧。因此上要扶人纪,刚刚决决,忘身殉理。殉理心非僻,心存理亦存。理当今日死,身死理犹生[8] 386。
以上从曹赛英口中所说出来的观念,活脱脱就是宋代理学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翻版,郑之珍对女性节操的要求标准,完全采取与程、朱统一的观点,可说是宋明理学最佳的传声筒了。
此外,“忠义”的代表人物则非罗卜家的忠仆益利莫属了。首先观察这个忠仆的名字,他叫做“益利”,刚好就是“利益”二字的颠倒,可见作者中心思想就是不谈利益,孟子《梁惠王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与利益相反的就是“仁义”,将此二字倒反当作这个忠仆的名字,也就是借着他在舞台上的行动,宣扬儒家的中心思想“仁义”二字了:中卷《主仆分别》出云:
东人,盖闻家主,分同君父之尊;若论仆人,义犹臣子之比。今东人为母而参禅,任重而道远,正老奴报主之秋,犹臣子效力之日。奈代行不允,同去不从,使益利虽有报主之心,亦无庸力之地[8] 259。
可知益利这个人物的塑造,与曹赛英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郑之珍手中宣扬儒家教化的两颗活棋子,昭示大众,程朱理学所要求的人格标准,女性节烈,男性仁义,则天下庶几可相率而为善矣。
(3) 郑之珍《劝善记》剧本中,则穿插有《思凡》《下山》的桥段,表面上好像在歌颂这种追求自由的灵魂,讽刺清规极严的佛家门墙中,也有着追求世俗爱情的蠢动,但是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水仙子】我本不是路柳与墙花,奈遇着风流业主冤家。凭着他眼去眉来,引动我心猿意马。到不如丢了庵门撇了菩萨,学僊姬成欢成对在碧桃前,学神女为云为雨在阳台下,学云英携了琼浆玉杵往那蓝桥。”[8] 78事实上这对思凡的和尚尼姑,最后在地狱中都遭受到了惩罚,为追求自由、不守清规理法,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在地狱中受苦刑,这就是典型的“去天理、存人欲”的下场。
3 《牡丹亭》与阳明心学
若说《牡丹亭》是汤显祖在阳明心学影响下的产物,其实也不为过。汤显祖一生受到三个人之影响颇深:一是泰州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近溪,二是达观禅师,三则是李贽百泉,而此三人与《牡丹亭》之创作思想息息相关,对照说明如下。
3.1 罗汝芳与汤显祖《牡丹亭》
罗汝芳乃阳明左派泰州学派之第三代传人,自其开山祖师王艮创立学派始,即以反传统、反统治阶级之异端姿态出现,影响所及,上自士大夫阶级,如徐樾、何心隐、罗汝芳,下至贩贾走卒,如颜钧、韩乐吾、朱恕,莫不受其感化;其间亦有不见容于统治阶层,而被迫害至死者,如何心隐、颜钧等人。然而泰州子弟赤身担当,愈挫愈奋、愈战愈勇之精神,实非一个“死”字可以了得。其学派之宗旨,大略如下。
3.1.1 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
王艮《心斋语录》曰:“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13] 316反对传统章句诵习,教人放下书本,不必依靠经传支撑,凡讲经说书,多发明自得,谓之“心悟”、“独解”,跳出传统经学拘泥于注疏之范畴,所讲内容平易近人,人人乐与之亲。耿定向《王心斋先生传》云:
寻商贩东鲁间,……经孔林,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孝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门高第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昕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14] 348-349。
故王艮之说除“心悟”外,尚主张“实践”,以为六经传统特印证我心,既已“心悟”、“实践”,则经传不复用矣。
《牡丹亭》第七出《闺塾》老学究陈最良初次给杜丽娘上《诗经》,就完全依照毛注来讲解,惹得杜小姐不耐烦了,说:“师父,依批注诗,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可是陈最良的“敷演一番”还是离不开毛亨的范围:“【掉角儿】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娃,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没多些,只无邪两字,付与儿家。”[15] 2085汤显祖在此意有所指,将这个只会依毛诗讲解的儒者陈最良,迂腐的模样灵活灵现地描写出来,十分传神。而这些腐儒的眼界似乎还没有一个闺中小姐的眼界宽广,例如春香拿文房四宝出来,陈最良问小姐这是什么砚?小姐说:“鸳鸯砚。”陈最良又问:“许多眼?”小姐答:“泪眼。”陈最良居然答非所问地说:“哭什么子?”其实泪眼是端砚上的砚眼,有活眼、泪眼、死眼之分,活眼最好,其次为泪眼、死眼,但是无论如何跟“哭”的泪眼是扯不上关系的;此处不知道是否利用插科打诨,讽刺程朱理学造就出来的腐儒——陈最良的狭隘。
3.1.2 宇宙一元论
王艮以为“天地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混沌一元”,故而主张宇宙一元论,天地、万物、人皆为一体,故可称之曰“自然”或“天”,“人性之体”即“天性之体”,皆为“自然”之同义语。故曰:“天性之体,本自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13] 316故人性中饥思食、渴思饮、男女之爱,亦为活泼泼之“人性之体”,无可忽视。因此人学习之目的即发展自然之乐,学习方法须简易快乐。由此而衍生“自然论”与“乐学说”。王艮认为人心本诸自然,即能快乐,其仲子王襞《东崖语录》云:“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13] 320以此诠释自然说最为贴切。
《牡丹亭》第九出《肃苑》ㄚ鬟春香说道,小姐自从读了《毛诗》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后,“悄然废书而叹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春香为遣小姐之愁怀,而有游后花园之提议。先支开塾师陈最良,说是老爷的指令,陈最良无可奈何的说出自己的心声:“【前腔(一江风)】……春香,你师父靠天也六十来岁,从不晓得伤个春,从不曾游个花园。(贴)为甚?(末)你不知,孟夫子说得好: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但如常,着甚春伤?要甚春游,你放春归,怎把心儿放?……”好个陈最良,就是个标准程朱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样板人物。汤显祖越写他的言行,越可以看出他对程朱理学禁人欲的不满。
而三传弟子罗汝芳亦对充满天机之自然亦有所体悟,《近溪语录》云:
不追心之既往,不逆心之将来。任他宽宏活泼,真是水流物生,充天机之自然,至于恒久不息,而无难矣[13] 338。
又云:
我的心,也无个中,也无个外,所用功夫,也不在心中,也不在心外,只是童子献茶来时,随众起而受之,从容啜毕。童子来接时,随众付而与之。君必以心相求,则此无非是“心”,以工夫相求,则此无非是“工夫”,若以圣贤格言相求,则此亦可说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也[13] 340。
学习之目的即回归自然。至于学习方法则必须以“快乐”为主体,王艮《心斋语录·乐学歌》云: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13] 318。
罗汝芳亦发展出一套近似乐学之理论:
学问须要平易近情,不可着手太重。如粗茶淡饭,随时遣日,心既不劳,事亦了当。久久成熟,不觉自然有个悟处,盖此理在日用间,原非深远,而工夫次第,亦难以急迫而成。学能如是,虽无速化之妙,却有隽永之味也[13] 338。
学习不可操之过急,当以平易从容之心为之,大致符合“乐学说”之主旨。《牡丹亭》的腐儒陈良的课后规矩,一不许杜丽娘荡秋千,二不许杜丽娘逛花园,三杜丽娘每天放学后要守砚台、跟书案、伴诗云、陪子曰,不能有一些差错。杜母在第十一出《慈戒》【征胡兵】也点出:“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工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去花园怎么?”[15] 2101汤显祖点出这种矫揉做作、违背自然的学习,跟泰州学派的乐学有相当大的差距,泰州学派做任何事都讲求一个心,用心去体会当下,动静不失其时,随时随地快乐的学习,这样就够了。
3.1.3 政治理想
王艮袭用王阳明之观点,将政治分为三种不同类型,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景象,彼向往者乃羲皇时代之生活和谐、列坐咏歌;而最深刻不满者则是五伯之世纷争扰攘。可见泰州学派在政治上所追求者,乃为平等、自由、快乐、免除剥削压榨,“只是相与讲学”之世界,故泰州子弟人人注重讲学,如何心隐、颜钧、罗汝芳之辈,皆有“入山林求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之胸襟理想”,所谓“隐逸”、“愚蒙”即是社会地位低下,文化教养缺乏之下层百姓,故所至之处,“无贤不肖,皆赴之”,例如《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提及何心隐讲学,奔走四方,南至福建,北达京师,东到长江下游,西走重庆,而至京师之时,“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可见其盛况。而讲学之目的即是传播政治上人人平等、自由、快乐之理想,故泰州学派主张“出必为帝者傅,处必为天下万世师”,拒绝在朝为官,充当爪牙,例如:王艮于其五子之教育方式乃为“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故弟子徐樾为追随王艮而解官,因受王艮之赞赏,而传授“大成之学”( “大成之学”乃为泰州学派之精华思想,只传予诸弟子中,成材而为老师所赏识者)。
3.1.4 淮南格物说
此为泰州开山祖王艮重要学说,约而言之,主要论点有三:
(1)从“天地万物为一体”做出发点,故人己平等,爱己身即须爱人身,故强调“明哲保身论”,王艮《心斋语录》云: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13] 317。
同时亦反对“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势必至于“适己自便”、“利己害人”,而他人亦将以此报我,则自身不能保矣;一身之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家国哉!
(2)安身说:首先人须顾及到吃饱穿暖,此乃基本物质条件;人若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亦失其本而难以学,待自己与天下人皆能饱暖,亦达安身之先决条件矣。故《心斋语录》云:
安身以安家而家齐,安身以安国而国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就此失脚[13] 316。
可见安身为安天下之本。
(3)成己成物说,此为安身说之延伸。人不仅止于做到物质条件之安,更须进一步对天地万物负责任,故首须严格要求自己,《心斋语录》云:
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絜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13] 316。
所以先正己身才能“内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亦方能担起“一夫不获其所,即己不获其所,务使获其所而已”之重责大任。
凡此学派之宗旨,在晚明造成了“掀翻天地”之局面,而汤显祖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卒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当时泰州学派正盛行于汤显祖之家乡江西省,而他十三岁始即入泰州之门,终其一生,皆受其影响,遂令此原本可握麈毛而登皋比之才子,舍弃荣华,走向反压榨、反剥削之不归路,泰州学派之神力可谓大矣。黄宗羲于《明儒学案》评论泰州学案之语,颇值深思: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有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之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13] 311。
黄宗羲从传统观点出发,将泰州视为洪水猛兽般肆无忌惮,殊不知此即为其特色:“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显现其急欲摆脱传统束缚之勇气;“非名教所能羁络”,表现其冲破名利网罗之决心;“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说明其牺牲奉献,不惜殉道之精神。凡此皆属泰州学派躬行实践之功夫,而泰州子弟,个个皆是热血沸腾、担当一切之好汉,即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精神,为汤显祖树立大丈夫之典范。
3.2 达观禅师与汤显祖《牡丹亭》
真可和尚,字达观,号紫柏。他与汤显祖之相识,颇富传奇性,据《莲池坠簪题壁二首》诗序云:
予庚午(隆庆四年,1570)秋举,赴谢总裁参知余姚张公岳。晚过池上,照影搔首,坠一莲簪,题壁而去。庚寅(万历十八年,1590)达观禅师过予于南比部邹南皐郎舍中,曰:“吾望子久矣。”因诵前诗[15] 577-578。
依此,达观在万历十八年(1590)于南刑部邹元标家中初遇汤氏之前二十年,即因二首《莲池坠簪题壁诗》 (《莲池坠簪题壁诗》其一曰:搔首向东林,遗簪跃复沉。虽为头上物,终是水云心。其二曰:桥影下西夕,遗簪秋水中。或是投簪处,因缘莲叶东。)饶富禅意而知汤氏其人,故初遇时即曰:“吾望子久矣。”二人之交自此始。根据达观《与汤义仍》书信所载,彼二人交往过程中,有所谓“五遇”:
第一遇,野人追维往游西山云峰寺,得寸虚(指汤显祖)于壁上(指题壁诗),此初遇也。
第二遇,至石头(南京),晤于南皋(指邹元标)斋中。
第三遇,辱寸虚冒风雨而枉顾栖霞。
第四遇,及寸虚上疏后,客瘴海,野人每有徐闻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买舟绝钱塘,道龙游,访寸虚于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绝境,泉洁峰头,月印波心,红鱼误认为饵,虚白吐吞。吐吞既久,化而为丹,众鱼得以龙焉。故曰,龙乃鱼中之仙。唐山,禅月旧宅,微寸虚方便接引,则达道人此生几不知有唐山矣。
第五遇,今临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云水相逢,两皆无心,清旷自足[16] 1040。
而自汤氏之诗文集观之,每有论及与达观交游者,如《达公忽至》《达公舟中同本如明府喜月之作》《达公过旴便云东返,寄问贺知忍》《达公来自从姑过西山》《得冯具区祭酒书示紫柏》《达公来别云欲上都二首》《拾之偶有所缱,恨不从予同达公游,为咏此》《谢埠同紫柏至沙城,不肯乘驴,口号》《别达公》《章门客有问汤老送达公悲涕者》《归舟重得达公船》《江中见月怀达公》等诗,皆可看出达观在汤氏心目中之份量。
达观禅师在第二次遇汤显祖时,尝言曰:“十年后,定当打破寸虚馆也。”[16] 1041然汤氏终其一生,究竟未能舍弃红尘,因此,在汤氏思想领域中,达观禅师究竟占何比重,即成为众所瞩目之焦点。欲解决此问题,必须先了解达观,万历三十年(1602)御史康丕扬疏劾达观之文,或可了解达观行止之一斑:
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如广平太守蒋以忠拜参,公然坐受。先吏部尚书陆光祖访于五台山,盘桓十余日,地方官无不俟候。抚臣欲行提问,彼惧而随光祖归。后再至真定,从讲益多。甚有妻女出拜,崇奉茹斋,跪进饮食。指以五台刻经,借取重利。复令吴中极无赖之缪慕台者,鼓舞人心,捐财种福,一时收受数盈三万。其自南入都也,贵人争候,倒屣恨迟,入见跪伏,转相慕效。识连中外,交结奥援。近有一大臣,雅负时望,身止一子,缘其崇信流僧,遂即祝发从游,父死不奔丧。滥觞之极至此,况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始而由丹阳、金坛归于燕,继而由五台、留都再归于燕,终由真定、五台卒入于燕,意欲何为?夫尽人咸可说法,何必朝省?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为伍者何耶?(见《明神宗实录》)
据此可知达观在当代传教情形,已深入一般百姓生活中,乃至达官王侯皆“倒屣恨迟、入见跪伏、转相慕效”;而相对的朝廷却视之如洪水猛兽,鄙见之官吏如御史康丕扬在弹劾文中,再三强调其居心叵测,耸动百姓。此与当日泰州学派广遍天下,引起朝廷疑惧之情况颇为类似;换言之,达观虽为方外之士,然而乃是禀性刚烈,喜怒形诸言表,颇有侠士风之佛教大师。曾经感慨平生有三大负:
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16] 631!
“老憨”即指明末高僧憨山大师德清,此人为达观生平最相契之道友,二人曾合计修《传灯录》、复兴曹溪禅源、修复琬公塔、复刻方册大藏等佛教界大事。而德清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弘法被诬入狱,达观曾多次营救不成,后德清被遣戌雷州,达观反因营救德清,引起神宗不悦;而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因妖书事件*此事史称“癸卯冤狱”。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有人撰写《忧危竑议》,离间郑贵妃与皇长子常洛,此书以焚毁了事。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又有人续撰《续忧危竑议》,言郑贵妃将以亲生子常洵取代常洛为东宫太子。帝震怒,下旨严查妖书出处。而达观之弟子沈令誉遭株连被捕,御史康丕扬自其宅搜出达观予沈之信札,其中言及营救德清及帝毁海印寺之事,帝怒,达观因之系狱。参阅释果祥:《紫柏大师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6月,页36-43。被牵连而入狱。而所谓“矿税不止”,则指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为充实内帑、营建内殿,下诏开采银矿,广征税收,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奸人假开采之名,乘势勒索民财,若有富家良田美宅,则指下有矿脉,或诬以盗矿,或率役围捕,甚且辱及妇女。万历二十八年(1600),南康太守吴宝秀拒缴矿税,为中使劾奏入狱,吴妻哀愤自缢,达观时在匡山,闻说此事,策杖出山,多方调护营救,并授吴宝秀《毘舍浮佛偈》令其持诵十万遍,后蒙神宗饬赦出狱。而矿税之危害天下,直至达观死前犹未消止。此即达观之“生平三大负”。观此“三负”无一为己,皆为天下众人之事,故《中国戏曲通史》评之曰:“是个恨众生不能成佛而见义勇为的和尚,由于他的无畏和舍生,以及对程朱理学的攻击,也被当权的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更被迫害至死。”[17] 542关于此点,汤氏《滕赵仲一生祠记序》有更深入之描述:
后一年,而紫柏先生来视予,曰:“且之长安。”予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体貌,固不可以之长安矣。”先生解予意,笑曰:“我当断发时,已如断头。第求有威智人可与言天下事者。”予曰:“若此,必赵君可。”久之,则闻朝士大哗,而赵君去。又久之,几起大狱。而紫柏先生死矣[15] 1079!
推论至此,当可知汤显祖与达观投缘之因,乃为个性、思想之接近而惺惺相惜,彼此效慕,行谊在师友之间,汤氏欣赏达观勇敢无畏忠于理想之精神,一如崇拜其恩师泰州学派罗汝芳;而达观赏识汤氏如水云心般之禅机与才华,又见其《莲池坠簪》诗未出仕即有归隐心,以为有宿缘,故再三劝其皈依佛,而汤氏亦受记(受记,又名受莂,由佛受当来必当作佛之记别也)于达观。汤氏结识达观后,更坚定其思想上以“情”反对程朱理学之决心,故达观对汤显祖之影响当属此类;而非一般所云,必斤斤计较于《南柯》《邯郸》中所呈现之佛道思想,而曰汤氏必受达观之影响,凡此皆属浅见。若果汤氏之佛道思想必待达观而后有,如此,则当日未遇达观而具有之佛道思想,又从何而来耶?
3.3 李贽与汤显祖《牡丹亭》
李贽,号卓吾、笃吾,别署温陵居士、百泉居士。师事泰州学派祖师王艮之子王襞,论辈份,当与罗汝芳、何心隐同,并与罗汝芳友善,曾撰《罗近溪先生告文》以吊罗汝芳。汤显祖早慕其名,《寄石楚阳苏州》书信云:
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15] 1325?
此为万历十八年(1590)之事也,而《焚书》即于此年刻于麻城,麻城为当时苏州知府石昆玉(楚阳)家乡之邻县,汤氏此时已知此书,故以此信殷勤求访,其对李贽之倾慕有如此者。至于二者之间是否有会面之事,颇难知其究竟。根据《汤显祖集》所附之简易汤氏年谱,并无提及会面之事。而徐朔方所编之《汤显祖年谱》乃系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之下,曰:
李贽来访。《临川县志》卷十李氏正觉寺《醒泉铭序》云:万历己亥,余与汤西儿正觉寺后作系念。寺之伯用材上人邀余茶话[18] 386。
案汤西儿为汤显祖之子,殇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距生年仅八岁。而依《临川县志》所云,李贽来访事,必当不假,然彼时距汤西儿之殇已一年,亦不见汤氏有诗文与李贽唱和往返,而于汤氏全集中,仅得一首《叹卓老》之诗,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于狱中自杀之后,诗云: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15] 621。
准此,李贽对汤显祖之影响仅止于其行事风范及其著作思想,不若罗汝芳及达观上人之亲炙也。然李贽亦为泰州一派之传人,其行事作风几与泰州无异,试观万历三十年(1602)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劾李贽之疏可知: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缪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足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乱于后,世道幸甚。(见《明神宗实录》)
依此,朝廷目之为“妖人”,降罪于李贽之原因有二:其一,为思想上之毁圣叛道、批驳谑笑、攻古君子之短、护小人之所长,且刻为书籍,广为流传;其二,为行为上之好刚使气、行复诡异、快意恩仇、急乘缓戒、细行不修、任情适口、鸾刀狼藉,影响所及,士人庶民皆望风披靡。殊不知李贽之书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轻重,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窾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19] 5。公安派袁中道云:“世间一种珍奇,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书;而其人之“才太高、气太豪”思想超越当代太远,又不能“埋照溷俗”、“为人所屈”,遂得罪于名教,祸逐名起,卒就囹圄,而毫无惧色,此正为泰州学派之特色风范之所在,抑且为汤显祖一心向慕之所在!
汤显祖之生平行迹,其虽自认“天资怯弱”,精神、才力、体貌皆不如人,故在行事上不如罗汝芳、达观、李贽之风雨江波、慷慨激昂;然其早年不屈于张居正之笼络、悍然拒绝名利诱惑;中年无惧于权贵如日中天之势,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给事中杨文举,皆可谓之得泰州学派之真传;至于思想上创“主情说”以对抗当日盛行之程、朱理学,无惧于名教之攻讦,更可谓得泰州学派、紫柏上人及李贽之神髓,即此足以令汤氏不朽矣,更何况艺术上还有至今搬演不辍的《牡丹亭》。
汤显祖《牡丹亭》的主旨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跳出了程朱思想中对情、对人欲的漠视,勇敢地诠释“情”字,《牡丹亭》第一出《标目》云:“【蝶恋花】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 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15] 2067明明白白地揭示“情”字,在人生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而“情”的提倡与诠释,在明代有甚么重要性呢?其实一代有一代的思潮、风气与面貌,就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而论,同一题材,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诠释与处理,甚至表述出完全不同的观点,读者与观众也受此外在环境的影响。从现代人的观点看,《牡丹亭》最后借着杜丽娘的还魂,又与柳梦梅团圆,未免落入俗套,构不成悲剧的条件。但是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意谓一个人如果只执着在“理”的范围内看待事情,他就无法理解在“理”以外的“情”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事了;更简单地说,即一个人太执着于理,就会不通人情、缺乏圆融了。从汤显祖的时代背景来看,要冲破明代程、朱理学所产生的层层束缚,他只能借着杜丽娘为梦中之情而“死”,又为梦中之情而“生”的事件来做象征,说明无论是杜丽娘的“死”或“生”,都是因为有“情”,才会产生“勇气”去追求生命中的“幸福”。汤显祖肯定一个人有“情”,是为至高无上的境界,在人可以为情而“死”,而又可以为情而“生”的前提下,还可以更进一步,从有“情”的“个人”,进而建构出像唐朝一样有“情”的“社会”,因为整个社会有“情”,唐太宗可以容忍魏征的劝谏;因为整个时代有“情”,唐玄宗可以亲拭李白之秽物。面对长期受到程朱理学束缚,越来越无“情”寡“欢”的明代社会,汤显祖做出彻底的决裂,他安排杜丽娘必须以“生命”相换,才能得到幸福;就像西方童话中的《人鱼公主》,为了得到王子的爱情,她必须牺牲掉自己甜美的嗓音;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认识柳梦梅,即使要私奔,也无从找出这个人在哪里。一如明代理教对人心的束缚,一般人根本无法察觉哪里不对劲,但它是一种无影无形的枷锁,一旦戴上了,若非圣贤,一辈子的思想行为举止都被牵着鼻子走而不自觉,何况是深闺弱质又兼少不更事的杜丽娘呢?所以在汤显祖的安排下,想要得到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必须以死相换;亦即面对束缚人心的理学,除了豁出生命与之抗衡外,别无他法。而杜丽娘的死,换得了生命的更新;也象征着一个社会若想挣脱束缚,那么它的人民必须连死都不畏惧,才会像杜丽娘一样得到重生;而杜丽娘重生之后,并不是马上得到幸福,她必须通过一连串的磨难与考验,才能与柳梦梅团圆。所以“死”是破坏,“重生”是建设,唯有透过“死”与“重生”,杜丽娘才能找到自己幸福,所以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幸福是要付出代价的;象征着晚明的社会也唯有通过“破坏”与“建设”之后,人民才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汤显祖在安排杜丽娘与柳梦梅的幸福结局中,也微微透露着他对晚明社会还抱着一丝丝的希望,希望借着《牡丹亭》幸福的结局,能为这个正在无限沉沦中的明代找到一线曙光。
4 结语
明代文学创作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之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前代文学创作承传之制约,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产生明显之改变,传统文学主要形式之诗歌散文,在经历汉魏六朝以至唐宋一千多年之发展后,已难别开生面,而历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通俗文学,如戏曲、小说、民歌等,却有着如日中天的声势,散放出蓬勃之生命力,约而言之,明代是文学体裁雅俗交替之时期,时代的审美观、文学艺术的创作、文学批评皆产生了不同之面貌与观点。哲学上王阳明之心学盛行,随之而来的是禅宗与禅悦之风盛行,士大夫转而向内心境界追求,与理学路线相悖,肯定自我、重视人情物欲之观念,弥漫整个社会,反映出当代百姓之情趣与审美观念,促进了通俗文学之发展,也为文坛艺坛的创作带来生气。但是在心学盛行的当代,也不可忽视潜伏在旧社会中,从未消失过的程、朱理学的支持者。
《劝善记》《牡丹亭》分别是在这种新旧交替的风气之下所产生的,前者代表依然潜伏在各处的,却由民间表达出来的程、朱思想的拥护情况,后者代表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阳明心学,所产生的美丽花朵。
就文学艺术的内涵而论,第一,应该以历史性的眼光看待文艺作品的主题,接受其在各个时代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以从单一主题来论断,坚持正确答案只有一个,这样的方式作为判断作品高下之标准是会出问题的。以追求爱情而违背礼教的文学作品而论,从《诗经》开始,就已经存在,究竟孰是孰非,难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去下定论;《牡丹亭》也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环结而已,应该在历史的眼光探究其根由,不当以其本事中“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情节,即认为其不合于今人观点,而遽下荒谬之断语。同样的,《劝善记》并非鼓吹此一解放之风气,从和尚、尼姑死后下地狱、受惩罚的结果,也可以明了郑之珍的苦心,必须从警惕当时人欲横流,不守理法,造成社会混乱的观点去思考。
第二,当如何看待《牡丹亭》颠覆的传统礼教,而《劝善记》却想维护礼教的问题。三纲五常的观念是传统礼教的基础,君为臣刚,父为子刚,夫为妻刚,欲以此彰显人伦中,君臣、父子、夫妇之名份,以推动五常中的仁义理智信,达到稳定社会及教化百姓之需求。然在人类社会中,一种制度行之久远,一定会产生质变,如何在新的观念与旧的质变中,产生一种调和性的思想,汤显祖及郑之珍都在著作中给了答案。汤显祖用的是彻底摧毁理教绳索的大破法,郑之珍则利用民间流行敬畏鬼神的思想来慢慢修补。是非对错,是否有标准答案?就等着后代的读者在自己身处的环境中从容思考。
后世与此相关的评论,从明清至今,都是该二剧接受史的一部分,代表着每个时代的社会制约、价值观念与审美标准,因此所谓的“作者本意”其实只是那个时代的读者或批评家、观众的本意而已。自从1960年代,接受美学理论开始发达以来,读者或观众对作品的意见,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个理论主张,任何文学艺术的本文都具有未确定性,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是一个多层面开放式的图式结构,任何人都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必须通过这些,才能将作品的空白处填满,才能确定其文学或艺术作品的价值。所以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主题,每个人理解作品的角度与方式不同,它可以使作品源源不绝的拥有丰富的结构与内涵,从而具备了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条件。
因此所谓《劝善记》《牡丹亭》的主旨,除了作者自身的经历与当代的社会背景等条件的配合之外,作品因流传而产生的接受史,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因为一个开放性作品的意义,都是在不断的生发出来的意见中产生,每个时代的读者,都依照自己当时所处的环境、审美观念来阅读或观赏艺术作品,故作者本意也只是众多的接受史中的一种,完全无法替代其他接受者的意见,因此文学创作的意义,实不应该汲汲于它的内容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容的产生,这才是本文要探讨《劝善记》《牡丹亭》的重要意义所在。
[1] 陈献章集[M] .孙通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 .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
[3] 元亨寺汉译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汉译南传大藏经[M] .高雄:元亨寺竹林出版社,1994.
[4] 瞿昙僧伽提婆.大正新修大藏经[M]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 王阳明全集·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王阳明全集·语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 罗洪先集[M] .徐儒宗,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8] 郑之珍.劝善记[M] //朱万曙,校点.皖人戏曲选刊·郑之珍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
[9] 叶宗春.叙《劝善记》[M] //朱万曙,校点.皖人戏曲选刊·郑之珍卷.合肥:黄山书社,2005.
[10]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 .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
[11] 曹国宰.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M] //中华戏曲:第3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 沈德符.顾曲杂言[M] //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13] 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M] .台北:世界书局,1961.
[14]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台南:庄严文化事业公司,1997.
[15] 汤显祖.牡丹亭[M] //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
[16] 释德清.紫柏尊者全集·与汤义仍[M] //卍续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7]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18] 徐朔方.汤显祖年谱[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19] 袁中道.李温陵传[M] //李贽.焚书.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4.
From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to The Peony Pavilion——Outlet of Ideological Trend and Chinese Opera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LUO Li-rong
(ChineseLiteratureDepartment,SoochowUniversity,Taibei222,China)
Popular literature ros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traditional and narrow concept viewing Chinese operas, novels, and folk songs as secondary literature was hugely impacted.The artistic charm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such popular literature swept every corner in China that was controlled by Cheng-Zhu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for centurie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n an overwhelming manner, and affected the mind of every person in the old society.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this phenomen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rising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gde and Emperor Jiajing in the Ming Dynasty-Neo-Confucianism-school of mind.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Zhengde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Yangming promoted the concepts, such as “attaining conscience,” “mind is principle,” and “my nature is self-sufficient and I don’t need the assistance from others,” which initiated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school of mind and gradually changed the atmosphere of pursing wealth and fame among the scholar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world.Moreover, the leader of left wing of school of mind, Wang Gen, who was acclaimed to be the pupil of Yangming, also developed Taichou School that fully affirms selves and desire of human beings and is against Cheng-Zhu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School of mind that was popular at the time became a social and cultural ideological trend, which got rid of the depressed mind of people chained by Neo-Confucianism, expanded the vision of modern people, and had a huge impact on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This ideological trend was reflected in the creation and criticism of Chinese operas and novels that were popular at the time.Such a power should never be underestimated by later generations.This study mainly focuses on two legendary Chinese operas,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and The Peony Pavilion to investigate how the popular literature creators representing the ideas of general public at the time protected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 and Cheng-Zhu school of Neo-Confucianism and reflected it using artistic methods.
Instructions on Morality; The Peony Pavilion;Zheng Zhizhen;Tang Xianzu;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2016-08-10
罗丽容(1954—),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戏曲理论、文艺理论、戏曲文物研究。
J805
A
1674-3512(2016)03-02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