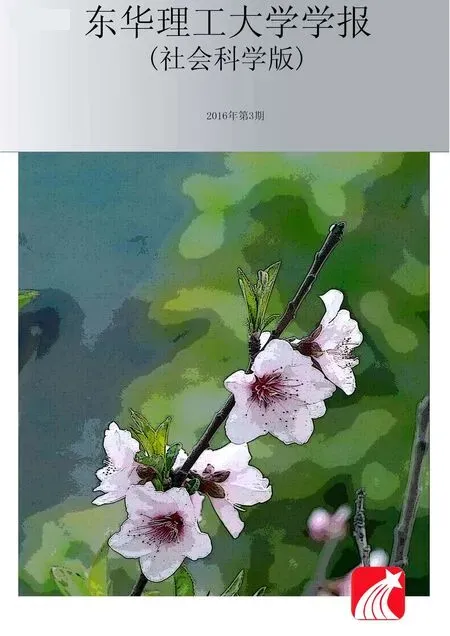唐涤生版《牡丹亭·惊梦》的岭南传播及戏曲史意义
徐燕琳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42)
唐涤生版《牡丹亭·惊梦》的岭南传播及戏曲史意义
徐燕琳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42)
香港仙凤鸣剧团唐涤生改编的粤剧《牡丹亭·惊梦》,以忠实原著、服务演出、增加表演和戏剧性为主旨,在语言形式、剧作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富于岭南情趣,深具本土性民间性,广为观众喜爱。是剧为唐涤生改编的第一本明清传奇,也是唐涤生和仙凤鸣班主白雪仙改革粤剧的重要一步,促进了香港粤剧新局面的开创和香港粤剧特色的形成,成为岭南戏曲和粤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作为《牡丹亭》演出传播史的组成之一,粤剧《牡丹亭·惊梦》融合了多剧种多文化精华,是南北戏曲艺术在岭南的共同绽放,亦或对今天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有一定影响。
汤显祖;牡丹亭;唐涤生;任剑辉;白雪仙;岭南文化;戏曲史;戏曲传播;香港粤剧
徐燕琳.唐涤生版《牡丹亭·惊梦》的岭南传播及戏曲史意义[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55-260.
Xu Yan-lin.The propagation of Tang Disheng’s version of an amazing Dream in the Peony Pavilion in Lingn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drama history[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55-260.
汤显祖名作《牡丹亭》,问世以来即历演不衰、家传户诵。它的演出史,也是一部文本的改编史和舞台再现的演变史。这首先是由于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多向度的再创造;同时对于戏曲文本来说,通过编、演将其形诸舞台,并在观众的眼光和评判中进行检验和调整,则是一个大规模和长时期的过程。另一个原因,汤显祖此作本身即有“案头之书,非筵上之曲”(臧懋循《玉茗堂传奇引》)之嫌,虽有演出考虑,但并不专为演出而写,排演时自然会有所阻滞。故在各种改编和演绎中,尽管水平不同,大部分改编者的初衷还是“布置排场,分配角色,调匀曲白”(吴梅《顾曲麈谈》)“以便登场”(明朱墨刊本《牡丹亭·凡例》),而不可能是文本的完全再现。当然,在经典面前,改编往往黯然失色,因此“割蕉加梅”(汤显祖《答凌初成》)者有之,“截鹤续凫”者有之(明朱墨刊本《牡丹亭·凡例》),“点金成铁”者也有之(吴梅《顾曲麈谈》),佳作不少,但也不无遗憾。
《牡丹亭》的演出史也是不同声腔剧种的演绎史。其中既有影响至今的吴伶的昆腔演出(因此才会有“云便吴歌”的“吕家改本”),亦有汤显祖本人嘱托的“宜伶”*笔者原以为宜伶用赣语演唱,2016年4月在浙江遂昌汤显祖莎士比亚会议中请教黄振林先生后修正,应为宜黄艺人模仿海盐腔演唱。(《与宜伶罗章二》),以及各地不同的风格和演绎。岭南是《牡丹亭》故事的重要发生地,剧中人柳梦梅就是一个“岭南秀才”。在岭南(以两广及港澳为主)和海外粤语地区广泛流传的粤剧,其用粤方言演唱是从清后期开始(一般认为这是粤剧形成的标志),所以流传至今的《牡丹亭》改编本并不多。现存最早的粤剧《牡丹亭》文本是清末人寿年戏班肖丽湘小生聪演出本,由位于广州状元坊内太平新街的以文堂板行。以后影响较大的有1956年香港仙凤鸣剧团演出唐涤生的改编本,以及1957年广州太阳升剧团演出的谭青霜改编本等。这些剧本,是我们研究《牡丹亭》近现代岭南传播的文献依据。
1 唐涤生改编的宗旨和特点
唐涤生(1917—1959),广东珠海人,粤剧史上最有才华和成就的编剧之一。他生于上海, 1938年因日寇侵华流徙香港,加入名伶薛觉先领导的“觉先声剧团”,开始编剧生涯,声誉日隆。1956年,唐涤生与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等组成“仙凤鸣”剧团。他撰写的剧本《落霞孤鹜》《紫钗记》《帝女花》《蝶影红梨记》《再世红梅记》等曲词优美情节动人,演出后名满香江,远及海内外。
在《牡丹亭·惊梦》一剧的改编过程中,唐涤生的态度非常明确。
首先,是忠实原著。唐涤生对《牡丹亭》这部经典大作充满敬畏,又沉醉偏爱。原著曲折绵长,并不适合一般的粤剧演出,删削在所难免。唐涤生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原著之精华”。仙凤鸣剧团开山泥印本中编者语:“汤显祖原著《牡丹亭》长凡五十五场,而精警处乃从第二十八场幽媾起。今编者竭其心力,将原著改为六幕,除尽量保持原著之精华外,故不得不忍痛删削。故开场由训女起演至夭殇止,其中曾含游园惊梦、寻梦、描容等回目。除借助于旋转舞台优点外,只求能使观众明白《牡丹亭》之缘起,除举世皆知的游园惊梦一节不敢草率外,戏从幽媾起始着力描摹原著之精华,故开端情节与时间性与原著颇有出入,祈识者能谅之。”*叶绍德编撰、张敏慧校订:《唐涤生戏曲欣赏》一,香港:汇智出版社,2015年,第162页。另这套唐涤生作品集是张敏慧据叶绍德1986年汇合刊行唐涤生剧本之本意,以开山演出时的泥印本为依据重加订正,更能够反映作品及演出原貌。承香港浸会大学朱少璋先生惠赠,此谢。这说明,唐涤生的改编,尽管不得不删,但一定是努力围绕着原著题旨进行,务要体现作者精神用意,把握全剧脉络。正因有这样的认识,他的改编不同于肖丽湘小生聪演出本的许多胡乱发挥、自行创造,而能够让读过原著的文人认可。
不仅场次删削考虑到原著文本精华,就是在整个剧中,唐涤生时刻都在琢磨用怎样的舞台和表演,才能体现原著的意趣。第五场《拷元》,唐涤生对“画堂梅苑景”即有个说明:“假如此场用普通之厅堂,即不能表达《牡丹亭》原书所刻划拷元之雅趣。”因此他设计:“此场分内外两层布景,内层为画堂,画屏琴几,面积小,只做陪衬之用。两边有矮红栏,竹帘铁马,两旁梅树,红日相映,红栏外有柳树。衣边角有小角瓜棚,棚顶有天窗吊绳,以作吊打状元之用。”[1] 254为了更好地表现原著,他甚至还描绘他心目中的故事场景:“最好能使此景有浓厚之汉画气息。”唐涤生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画工了得,他甚至为此另附图作为参考之用,可见态度之认真端正。
第二,服务演出。唐涤生的戏有明确的创作对象,就是为仙凤鸣剧团的演出而写。因此,不仅文本,他甚至将舞台布置、人物表演等通盘列入考虑,兼编、导、美、灯光等于一身。比如他所作《牡丹亭》改本第一场《游园惊梦》的场景春禧堂、花园闺房,即有说明:“先布春禧堂,画栋雕梁、银彩银屏,备极华丽。衣边角有画墙辕门。辕门封闭。从辕门出即转台牡丹亭景。亭用平台布在衣边侧角,有短栏杆曲折一路布开台口(即芍药栏)。什边台口用短红栏布藕莲塘,旁有湖山石。衣边台有丝绒绕花之秋千。底景用纱隔住。内于梦境时用灯砌一‘梦’字后即五彩云浮动,如烟如雾,使人有身在梦乡之感。”“舞台旋转直入香闺,香闺有大帐,衣边台口长画台,上有文房。画台近窗,有梅花从外直伸入。”在编剧时精心构想场景,目的是为演出服务,体现原文旨趣,塑造人物形象。这两处,唐涤生还有细致指导,要求切合原著:“此景每一点都不能疏忽,因与原著有极大关系。”“什边红绢红屏风,寓红艳于清幽之中,方能托出杜丽娘之性格。”
在人物的表演上,甚至最普通最简单的“白”和“介”,唐涤生也从演出出发,作具体说明。如第三场《幽媾回生》,写杜丽娘半夜敲门,“丽娘用最微弱的叫声白:梅郎,开门。”柳梦梅以为是小道姑,故而不可,“丽娘轻轻顿足略觉不耐介白:开门来。”剧本里这种种细致指示,可谓罕有。其目的,全为更好地体现原著精神、服务于演出需要。
在全剧照应上,粤剧研究者叶绍德盛赞唐涤生“对任何细节绝不疏漏”。《探亲会母》一场,一段戏完了,“唐涤生很巧妙安排石道姑入屋,而丽娘留场盼望梦梅,这些小环节处理得很花脑筋,虽然是一两句口白,要做到自然不留痕迹,绝非容易。”[1] 231
唐涤生和仙凤鸣剧团虽不完全迎合观众,但对观众反馈的意见也很注意。《牡丹亭·惊梦》刚开始演出时效果不甚理想,1958年重演时检讨,发觉主要是剧本问题。因为唐涤生太过忠实原著,开场后一个小时,演完了“春香闹学”、“黄堂训女”两场后,“戏迷情人”、柳梦梅的扮演者任剑辉才有戏上场,观众方能见到自己的偶像。是年仙凤鸣着手浓缩剧本,开场未几就让任姐上场,观众这才高兴了。[2] 193
第三,增加表演性戏剧性。唐涤生的改本与汤显祖原著的极大不同,在于他是为“演”而写,甚至因人设戏,特意配合仙凤鸣大老倌任剑辉、白雪仙两位的艺术特点来设计。因此,舞台效果就是他突出考虑的对象。为了提升舞台效果,除了一些删削外,他还作了不少补充和发挥,令舞台生动活跃,色彩缤纷。
原著第三十五出《回生》,其中写柳梦梅带领疙童、石道姑启出丽娘,其中具体过程仅35个字:“[前腔] (丑净锹土介)这三和土一谜锄。小姐呵,半尺孤坟你在这的无?(生)你们十分小心。(看介)”。而在唐涤生的笔下,此段紧张万分,波澜起伏,十分有戏。先是将石道姑定下来的、平淡而过的时刻交代“(看介)恰好明日乙酉。”发挥为剧中一再强调的匆促紧急的时限:
(丽娘恳切地催快)柳郎……柳郎,你若肯明日未过辰牌,碎剜桐馆,尚可再续姻缘之份。
(丽娘将入场闻语一才回头急走埋紧执梦梅手介白)柳郎,丽娘再有叮咛,愿君记取。你既以我为妻,不能误我辰牌时分,否则过了冥期所限,即今生,(一才)……恐无重见之日矣。[1] 222
在这个过程中,三次以“鸡啼”催促杜丽娘下场,气氛一层紧似一层。这部分与原著大异其趣。原著第三十二出《冥誓》和第三十五出《回生》之间有《秘议》和《诇药》两出,讲柳梦梅找石道姑帮忙,石道姑又去找陈最良寻所谓“定魂汤药”烧裆散。这固然是情节发展的需要,亦有民俗考虑,也在令人略感不安的气氛中造成了调笑和舒缓。但这样的张驰,反面的效果是不够紧凑,情节略有拖沓。唐涤生的改编,则是在杜丽娘下场后,“更散天露微光”的紧迫中,柳梦梅毫不耽搁一分一秒:
(手忙脚乱拈花锄,急从衣边小辕门下,舞台旋转牡丹亭梅树青坟莲塘景)(天幕红日初升)
删掉了两出的篇幅,将“明日”变成了“即刻”,舞台一转,紧接着,就是最直接的行动。这个“辰牌”,是时间的压缩,也是舞台气氛的紧逼。正因为时间紧,所以,接下来的情节,成为对柳梦梅这个角色的渲染和加强,场上的“戏”层出不穷:
(梦梅拈花锄先锋钹扑埋青坟处,情急一手□开石道姑蹲地,再一手□开韶阳女蹲地,举锄狂掘介)
(梦梅一路掘,一路抹汗白)妙传……而家你问我乜嘢我都唔会答你叻……(口古)几时至係辰牌时分,希望你将我提点一下。
(韶阳女口古)秀才,日上牡丹亭角就係辰牌时分叻。……(天幕红日逐渐上升)
石道姑和小道姑韶阳女的出现完全是偶遇。柳梦梅发启杜丽娘,直到这里,也完全是独立的行为。时间愈紧,梦梅愈急,观众也愈加心切:
(梦梅回顾天幕红日介白)唉吔。(琵琶急奏双星恨中板猛力掘坟介)
(红日再升与亭角距离只两三尺介)
(梦梅喘息花下句)……拜一拜(介)佛如来,你为我拖延红日莫使亭边挂。(一路求助于石道姑与韶阳女,一路以双手跪剜坟土介)
(天幕红日已升至牡丹亭角介)
(梦梅回顾大惊重一才视双手鲜血淋漓,痛极蹲地狂呼丽娘……)……回生梦,转眼化烟霞。破碎了指头无力剜,惊心红日挂亭枒。不若闯死碑前(正花)不罢还须罢。(先锋钹欲闯死介)[1] 223-225
唐涤生在写剧时,考虑的是演出,是演员怎么演,是演出效果如何。我们看到,从35个字的柳梦梅看着别人掘,变成自己亲自动手掘;从石道姑韶阳女束手旁观,变成被他的一片赤诚感动而“帮手掘”,扮演者、作为票房号召的主演任剑辉因此有了大量的表演机会,完全可以将他“七情上面”的表情、传神生动的“做手”带进戏里,并更好地体现了他对杜丽娘的一往深情。舞台上波澜迭起,峰回路转,演员有戏可“做”,剧情也因此更紧凑更可观。
2 唐涤生改本的岭南风格
艺术家的创作,都基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理解,也往往成为当时当地社会生活的反映。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一般来说,感觉亲切、与自己关系度大的作品,更容易得到受众关注。唐涤生版粤剧《牡丹亭》,即是一个这样具有独特岭南风格、地域特色的古典名著改编作品。
《牡丹亭·惊梦》本土化的外在表现,是语言形式上的岭南情趣。
富有个性和情趣的口白,是唐涤生编剧的一大长处。叶绍德曾向唐涤生请教怎样才能编写粤剧剧本,唐涤生笑着回答:“写曲填词你不用操心,当你写口古口白写得好的时候,你的剧本便成功了。”[1] 34唐涤生写《探亲会母》中的人物语言能够“戏味浓郁”、“令人拍案叫绝”。这其中,方言俗语的使用功不可没。如丽娘说:“我又唔相信咁紧要啫。柳郎,你一言一语,都係甘生鬼嘅。”梦梅回答:“生鬼就唔似你叻。”“生鬼”两字在粤方言里是机灵生动的意思,同时字面上又恰好与杜丽娘“返生”的经历契合。杜丽娘说柳梦梅,是取第一意;而柳梦梅说杜丽娘,则兼有两意。故叶绍德介绍,每次演出这个情节,观众反应都非常热烈,因为“生鬼”两字形容杜丽娘,真是非常贴切[1] 232。
后面杜丽娘送柳梦梅赴淮扬寻亲,临行依依不舍,反复嘱咐,还有两次叫住、两段白榄:
(丽娘白)慢。(白榄)郎此去淮扬,莫自惭衾影。未为榜上魁,早沾鸾凤鼎。论衣冠,须齐整。头须鄂,腰须挺。未登白玉堂,先熟我爹娘性。
(丽娘再牵袖介白)慢。(白榄)叮咛复叮咛,似完还未罄。宰阁认乘龙,当有鸳鸯证。你莫愁无证物,我留得有丹青[1] 239。
白榄,又名数白榄,是念白的一种,来源于民间艺人上街卖白榄时惯常表演的快板。表演者通常自击竹板和节子(在粤剧粤曲中则由掌板师傅代击),按较快的节奏念诵唱词。唱词押韵,或间以说白,节奏感强;形式灵活,通俗易懂,能叙事、说理和抒情。剧中这两段白榄虽是家常俗话,但桩桩件件交代清楚,情真意切,字字叮咛,为“伶牙俐齿,最擅口白”[3] 372、口白“全香港最好的”[2] 195白雪仙度身打造,念来如雨打芭蕉,莺莺呖呖,着实动人。
剧作思想、人物形象的岭南旨趣,也是唐涤生版《牡丹亭·惊梦》的重要特点。
粤剧《牡丹亭·惊梦》既然编、演于岭南,是给岭南人看,必然贯穿着浓浓的岭南思想岭南意识,人物形象也必然体现岭南人思想行为的特点。以陈最良为例,原著中他号称“腐儒”,十分迂腐,虽然也有许多科诨,但总的形象,还是一个老成、规矩的读书人的样子。但在唐涤生的笔下,他一出场,就溢起了浓浓的岭南市民情趣。
比如陈最良的“老成”,汤显祖《牡丹亭》第四出《腐叹》是这么说的:“(见介)陈斋长报喜。(末)何喜?(丑)杜太爷要请个先生教小姐,掌教老爷开了十数名去都不中,说要老成的。我去掌教老爷处禀上了你,太爷有请帖在此。”第五出《延师》,杜宝说:“我杜宝出守此间,只有夫人一女。寻个老儒教训他。昨日府学开送一名廪生陈最良。年可六旬,从来饱学。一来可以教授小女,二来可以陪伴老夫。”而唐涤生则是这样介绍:
(春霖口古)春香,蜀中不少名师,何以偏偏请着个冬烘,使人生厌。
(春香口古)表少,你唔嘅知叻,个先生样样都唔好,独係有一样好,就係够晒老[1] 164。
小春香口无遮拦,经她宣告,陈最良的唯一优点竟是老。这便予陈最良这个角色很大的发挥余地,大可放下冬烘架子,成为一个本色的人物。于是听说太守设宴,他不请自到;美酒在前,他津津有味。他的上场诗最坦白:“春天不是教书天,饭饱茶香正可眠。”这分明是比小学生还懒的先生。但他又充满现实关怀:“太守堂中一顿酒,半载村童俸学钱。”将别人宴请的饭菜,折合成自己口袋里的钱,性质上与“一丈毯,千两丝”这类计算,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贫富对比完全不同,一方面说明他惜物俭省,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本人颇有经济头脑。这样的思想和诗句,出现在商品经济兴盛的岭南,既自然,又有趣,很可以让观众会心一笑。
随着剧情的发展,这个老冬烘就更有趣了。先是在柳梦梅的糖衣炮弹下失守,敞开庵堂大门容留柳梦梅,然后在杜丽娘柳梦梅欢会之时搅局:
(最良白)哼,送茶送茶,你估真係送茶递水个茶呀,乃是查房嗰个查,快啲开门[1] 214。
陈最良的出现,富于戏剧性,也是一般粤语片最喜欢制造的桥段。据叶绍德说,唐涤生绝顶聪明,他也常从电影中“偷桥”[2] 195。这横生一笔,灯光掩映中,一个要看一个不给看,一个看得到一个看不到,明里暗里的表演,花样迭出,让场面惊险刺激,也更吸引普通观众。这种调动观众心理的方式,富于戏剧性,也有利于传播和接受。
3 唐涤生改本的动因、影响和戏曲史意义
唐涤生的创作是仙凤鸣剧团的重要支柱。《牡丹亭·惊梦》是唐涤生对明清传奇经典剧作改编的第一部戏,同时也是粤剧吸取众长、走向雅化的重要开始,促进了香港粤剧的形成。
粤人好歌,粤俗好戏。凡有庆典宴会,或乡社酬神,例必演戏。民俗和娱乐需要,为粤剧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般认为,粤剧是广东艺人吸纳外省入粤戏班带来的昆腔、弋阳腔、高腔、京腔等戏曲声腔,加以易语而歌并融进本地的歌谣、小曲而形成的剧种。明成化时,粤中各地已有乡俗子弟以演剧为生。清雍正年间出现被称为“土优”的本地戏班演唱“广腔”,所谓“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咸丰年间艺人李文茂起义失败,粤剧及艺人受到残酷镇压,被迫流落四乡三十多年。这些情况,决定了这些终年漂泊在珠三角及西江、北江、东江一带江河沟汊、乡野圩镇的“红船艺人”和演出的民间草根性。清末,戏院在城市中陆续修建,经营演戏的班主和公司相继出现,为吸引观众请来了开戏师爷(编剧)编出大量生旦戏、言情戏,结束了粤剧无编剧的历史。以后革命党人的志士班推动的改良运动,以宣传革命、深入民心为目标,推动了粤剧的地方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从20世纪初在广州、香港、澳门巡回演出的省港班乃至后来的“薛马争雄”等,粤剧不断发展,也呈现出话剧化和通俗化趋向。其戏曲语言多用生动、形象、浅显的方言俗语、口头语、歇后语,传统的文雅而陈旧的戏棚官话逐渐消失;大量吸收民歌音乐、说唱甚至西洋音乐;题材广泛繁富,古今中外、市井生活无所不包。
戏曲的通俗化、大众化,既有助于剧中人物直接地、真实地抒发感情、表达思想,也有助于观众理解剧情、领会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剧本思想。但到四五十年代,因为过于追求票房、迎合一般小市民观众,造成粤剧舞台的纷杂乱象:部分剧目荒诞离奇,情节胡编乱凑,互蹈巢臼,庸俗色情,媚俗邀宠;舞美光怪陆离,丑相百出,不堪入目;行当各争戏份,“唱塞死做”,传统表演精华丧失。*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31-41页;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0年,第71-74页。很多戏是“梗桥戏”(提纲戏),只有人物上下场和故事大概,演员要临时“爆肚”。舞台上检场出出入入,舞台下卖花生卖马蹄,嘈杂不堪。
1956年创立的香港仙凤鸣剧团的班主白雪仙的艺术追求谨严。她吸收京昆特点,力图革新劣质粗疏的陋习。她与唐涤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感,就是借助演剧的吸引力,提升粤剧观众的审美水平,而非只求迎合一般戏迷的口味。*卢玮銮:《梦见繁华谁愿醒:“仙凤鸣”五十年》,见叶绍德编撰、张敏慧校订:《唐涤生戏曲欣赏》一,香港:汇智出版社,2015年,第317页。她以改革粤剧为己任,广邀当时香港粤剧界、音乐界精英,不断推出新剧、新形式,而《牡丹亭》则是她的夙愿:“年来,我有一个奇趣的愿望。希望能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在我的浅薄的认识中,《牡丹亭》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精警绝世的词曲,同时,有人向我详细说过昆剧的《游园·惊梦》和《春香闹学》,杜丽娘的影子便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白雪仙《我怎样去演〈牡丹亭〉里的杜丽娘》)白雪仙在演完《红楼梦》后,有意排一部传统和雅致的粤剧,其友京昆票友孙养农夫人胡韺特意送给她一本玉茗堂的《牡丹亭》,恰与白雪仙对昆曲《牡丹亭》的印象契合。数日后白雪仙将原著交给唐涤生,唐涤生说:“假如不是从她手里交给我一部玉茗堂的《牡丹亭》,我会怯于杜丽娘的难演而减低了改编《牡丹亭》的兴趣的。”(唐涤生《编写〈牡丹亭·惊梦〉的动机与主题》)唐涤生也有改革粤剧的宏愿。他有感于粤剧的落后,不满当时粤剧庸俗化的做法,欣然接受重任,两个月后编写完成《牡丹亭·惊梦》,年内首演于香港铜锣湾地标剧院“利舞台”。以后唐涤生每年推出改编自明清戏曲的创新演剧,如《蝶影红梨记》《帝女花》《紫钗记》和《再世红梅记》等[4] 518-522,如一股新风吹进剧场。
《牡丹亭·惊梦》初演其实惨败。叶绍德介绍,由于曲词深奥,演出进步,当时粤剧观众追不上,甚至名伶何非凡这样的行家也说:“戏是好戏,但不容易接受。”因此每晚演出卖不出六行前座位,令白雪仙化妆时总要追问大位(即前座票)卖出多少。但仙凤鸣并不因此降低艺术水准,而是继续提高粤剧水平,得到了文化界的支持。伴随市民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采用字幕说明等的辅助手段,《牡丹亭·惊梦》愈演愈旺台,甚至成为后继于仙凤鸣之“雏凤鸣”剧团的镇班戏宝,至今常演不衰[1] 299,[2] 193。在此之后唐涤生改编汤显祖另一作品《紫钗记》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誉为唐氏代表作。香港大学教育学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2009年出版《紫钗记教室——搭建粤剧教育的互助学习平台》一书,配以碟片,以《紫钗记》的教学为中心,为已经进入了香港中小学音乐、通识、文化、文学等正规课程的粤剧教育提供参考[5]。
唐涤生粤剧《牡丹亭·惊梦》的改编和完善,是《牡丹亭》演出传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也是岭南戏曲和粤剧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白雪仙“打破传统,请唐涤生把‘古典文学’的明清传奇剧搬上粤剧舞台,使粤剧的格调大大提高了”,“把香港粤剧推进了一大步”,在剧本撰作、舞台面貌上出现了很大的不同。香港粤剧“越来越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并有了自己在省港粤剧历史上某些最高的成就”[2] 204-205,白雪仙、唐涤生以及他们与任剑辉等艺术家打造的《牡丹亭·惊梦》等优秀作品功不可没。
粤剧《牡丹亭·惊梦》是南北艺术在岭南的共同绽放,亦有赖于当时香港文艺界有识之士的沾溉哺育。它的创作直接源于白雪仙身边京昆票友胡韺的推荐,当时亦有梅派京剧刀马旦张淑娴、名角孟小冬亲授白雪仙等以演艺。唐涤生还有一位贤内助,就是他的夫人,曾经的上海京剧名角郑孟霞[2] 192-193。他们还诚心向当时的学者和文艺界请教,如文人词家御香梵山、戏剧家胡春冰、文化人何建章等人,使剧本、曲词、场面调度等日臻完善。*卢玮銮:《梦见繁华谁愿醒:“仙凤鸣”五十年》,叶绍德编撰、张敏慧校订:《唐涤生戏曲欣赏》一,香港:汇智出版社,2015年,第311-312页。
唐涤生版的《牡丹亭》,亦或与今天香飘四海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有一定关联。据容世诚记述,白先勇曾说粤剧之中最喜欢《紫钗记》。他追问“仙凤鸣”的《牡丹亭》,白先勇说:“睇过!白雪仙的《牡丹亭》当然睇过!在‘利舞台’演出吖嘛。好睇!《游园》一场有个千秋架从上面吊下来。后来白雪仙的学生演《牡丹亭》,我都有睇。”[4] 517当年“利舞台”的演出,曾经给今天青春版《牡丹亭》的创作者留下如此深刻和美好的印象,“仙凤鸣”的诸位前辈,应可笑慰。
[1] 叶绍德.张敏慧.唐涤生戏曲欣赏(一)[M] .香港:汇智出版社,2015.
[2] 叶绍德,黎键.白雪仙对香港粤剧的贡献:兼论《白蛇新传》与李后主的讯息[M] //黎键.香港粤剧口述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3] 黎键.香港粤剧叙论[M]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
[4] 容世诚.还魂之旅——汤显祖、白雪仙、白先勇.华玮[M] //昆曲·春三二月天: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5] 徐燕琳.岭南戏曲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香港粤剧的实践与经验[J] .戏曲艺术,2012(4):53-58.
The Propagation of Tang Disheng’s Version of An Amazing Dream in the Peony Pavilion in Lingn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Drama History
XU Yan-lin
(DepartmentofChinese,HumanitySchool,SouthChinaAgricultureUniversity,Guangzhou510642,China)
The Cantonese opera An Amazing Dream in the Peony Pavilion,which was adapted by Tang Disheng who worked with Xian Fengming Drama Troupe(HongKong), is intend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suitable to perform, rich in performativity and theatricality.It is welcomed by the audience because of its Lingnan features in language form, theme, and personalities of the characters as well as its aboriginality and popularity.It is the first Ming-Qing drama that Tang Disheng adapted and it was also an important step of Tang Disheng and Bai Xuexian-master of Xian Fengming troupe to reform the Cantonese opera, which contributed to a new situation of Cantonese opera in HongKo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Cantonese opera in HongKong.It becomes the mileston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opera and Cantonese opera.Meanwhi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rformance and propagat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An Amazing Dream in the Peony Pavilion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multiple drama types and cultures.It glows in Lingnan with the art of both North and South dramas and may have made an impact on the modern vers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 by Bai Xianyong.
Tang Xianzu; the Peony Pavilion; Tang Disheng; Ren Jianhui; Bai Xuexian; Lingnan culture; the history of drama; the propagation of drama; Cantonese opera in HongKong
2016-08-10
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二五规划项目“岭南戏曲海内外传播影响及发展研究”(15Y22)、广东高校创新强校工程特色创新项目“艺术中国的家土构建:岭南戏剧生成发展研究”(2014WTSCX015)。
徐燕琳(1971—),女,广西桂林人,文学博士,教授兼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戏曲史论、艺术史论、岭南文化等研究。
J805
A
1674-3512(2016)03-025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