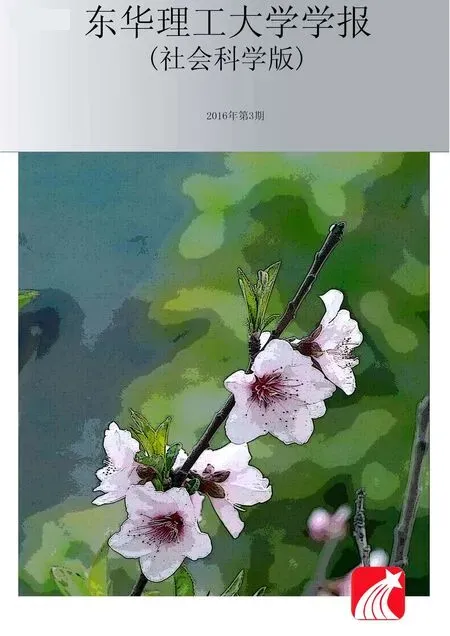越调吴歈可并论 汤词端合唱宜黄
——清初南昌李明睿沧浪亭观剧活动一瞥
苏子裕
(江西省艺术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越调吴歈可并论 汤词端合唱宜黄
——清初南昌李明睿沧浪亭观剧活动一瞥
苏子裕
(江西省艺术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剧作家汤显祖是李明睿的座师,李明睿又是吴伟业的座师,李明睿是个戏曲鉴赏家,无形中形成了一条光灿夺目的戏曲师生链。清顺治年间,李明睿回到家乡南昌,从扬州带来高水平的昆腔女伶,经常在南昌沧浪亭演出。演出最多的是其老师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弟子吴伟业的《秣陵春》,看客留下众多观剧诗记载当时的演出盛况。在沧浪亭的演出中,还有以泰生为首的、以演唱临川四梦为看家戏的宜黄腔戏班——得得新班。宜黄腔是由海盐腔在宜黄繁衍而来的戏曲声腔,由于它源于海盐腔,宜黄、临川一带仍称其为海盐腔。而海盐腔发脉于浙江海盐县,故又有“越调”之称。汤显祖的“四梦”在南昌沧浪亭演出,既有李明睿家庭戏班的昆腔,又有得得新班的宜黄腔,这两种声腔的演出水平都不错,所以观剧者给予“越调吴歈可并论”的评价,更有观剧者认为“汤词端合唱宜黄”。
汤显祖;临川四梦;宜黄腔;越调;李明睿;吴伟业
苏子裕.越调吴歈可并论 汤词端合唱宜黄——清初南昌李明睿沧浪亭观剧活动一瞥[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61-267.
Su Zi-yu.Yue Melody and Wu Ballad can be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Yihuang Tune is suitable for Tang’s Plays——On Li Mingrui’s opera activities at Canglang Pavilion in Nanchang in Early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61-267.
沧浪亭,是明末清初南昌人李明睿(1585-1671)所建别业。李明睿,字太虚,处于明清交替之际,经历了社会的重大变故,仕途上几经起落。晚年长期在失意和避乱的处境中度过。他回到南昌老家隐居,购弋阳王府旧邸,建阆园,并特意在城西蓼水旁修建了一座园林,名曰“沧浪亭”。园林取名“沧浪”,出自屈原赋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表示自己在众多的物议之中,修生养性,保持高洁。他蓄养了一批昆腔女伶,组成家庭戏班。而演出的地点就在沧浪亭。
李明睿是汤显祖的及门弟子,又是著名文学家吴伟业、谭元春的座师。谭元春是李明睿典试湖广时的乡试第一名,吴梅村是会试榜眼。李明睿上有名师,下有高徒,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名望。汤显祖、吴伟业都是著名的戏剧家,李明睿蓄养家庭戏班,是戏曲鉴赏家。就这样,由明至清的三位戏剧界人士结成了一个光辉夺目的戏曲师生链。追溯沧浪亭的观剧活动,对研究明末清初江西的戏曲艺术及汤显祖、吴伟业两位戏曲作家的剧作是很有有意义的。
1 汤显祖—李明睿—吴伟业
关于李明睿的生平及其与汤显祖、吴伟业的师承关系,施祖毓教授《李明睿钩沉》[1]、郑志良教授《吴梅村与汤显祖师承关系的文献考述》都做过详细地考证。郑教授提出:“汤显祖—李明睿—吴伟业构成了一个师生的链条”[2]。
李明睿的门生黎元宽《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署尚书事前翰林院士阆翁李公墓志铭》一文中对此有过简略的记叙:
师姓李氏,讳明睿,字太虚,即以署号,世无有不知太虚先生者。晚复号阆翁,以阆园故名。师籍同我南昌县,而乡于滁汊(槎)。环滁大姓李为之冠。……而师雅从汤临川先生游。其从游汤临川者多有人,而先生独醉于师、授之文诀。玉茗堂赠句,今脍炙焉。小子逮事吾师,在壬子、癸丑岁,屈指六十年矣。师门人满天下,则必以宽为之椎轮。……师以辛酉、壬戌缩取高第,遂上蓬山,所谓阆风基于此矣。宰相之事,进贤为大。师典楚试,得谭子元春而首之。南宫领房,得吴子伟业而大首之。……师著述之富,无冬无夏,月可得诗文百叶,或复倍之。《四部稿》国语过于弇山。师殁康熙辛亥八月十八日戊时,距生万历乙酉二月初八日戊时,得世寿八十有七[3]。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
(1)李明睿生平。李明睿生于明万历乙酉十三年(1585),殁于清康熙辛亥十年(1671),享年八十有七。江西省南昌县滁槎乡人。所谓“辛酉、壬戌缩取高第,遂上蓬山”,是指明天启壬戌二年(1622)李明睿三十八岁时,考中进士。殁于康熙辛亥十年(1671),享年87岁。
(2)李明睿是汤显祖的得意门生。李明睿曾从汤显祖游,其《临川汤师问业多年,芙蓉馆是其藏修之地》诗深情回顾在临川求学时的情景,对老师无限敬仰:
光照临川日已矄,纵横彩笔赋凌云。
芙蓉馆内春风盎,玉茗堂前淑气氲。
七岁熟精骚选理,经年常缬雪霜文。
晚于道眼饶窥破,香沁瞿昙齿颊芬[4]。
李明睿立雪玉茗堂,其《甘子纡见访》诗云:
千里相思愁命驾,百年多病懒闻喧。
文昌桥畔潺爱水,玉茗堂前雪夜门[4]。
黎氏谓李明睿“从汤临川先生游。其从游汤临川者多有人,而先生独醉于师、授之文诀。玉茗堂赠句,今脍炙焉”。氏所说“玉茗堂赠句”,即汤显祖《柬门人李太虚》一信,在这封信中,汤显祖对这位立雪求教的门生有极高的评价:
雪中屏去杂景,读书寒舍,足称男子矣。不佞得太虚,固前有光而后有辉。太虚得不佞,犹欲日有就而月有将也。夜间口占以拟:少年豪气几时成,断酒辞家向此行。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5] 1387。
李明睿著述甚丰,郑志良教授据光绪《南昌县志》卷五十二“艺文”所载,说李明睿的著述有《孝经笺注》、《阆园四部稿》、《白鹿洞稿》。其《阆园四部稿》又名《阆园山人四部稿》,现仅存8册。黎元宽说“师著述之富,无冬无夏,月可得诗文百叶,或复倍之。《四部稿》过于弇山”,弇山即明代著名文学家王世贞,其《弇州山人四部稿》乃鸿篇巨著,多达174卷,其《续稿》有207卷。而《阆园山人四部稿》比之有过,则可以想见其内容之丰富。
(3)李明睿为吴伟业座师。吴伟业受李明睿提携,领南宫第一,高中榜眼,自然对座师满怀感激之情,写有《寿座师李太虚先生序》。李明睿的《阆园山人四部稿》,署“门人湘江赵开心、娄江吴伟业梓”,是由其门人赵开心、吴伟业刊刻的。该书有吴伟业的点评。
(4)吴伟业的《秣陵春》与汤显祖的《牡丹亭》。吴伟业与汤显祖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他入清之后,开始戏曲创作,写了传奇《秣陵春》和杂剧《通天台》、《临春阁》。清人对其剧作评价很高,如梅村友人冒襄说:“先生寄托遥深,词场独擅,前有元四家,后与临川作劲敌矣”[2]。乾嘉时期文人郭麐(字祥伯)《灵芬馆词话》卷二有:(梅村)“于曲独工,曩见《秣陵春》传奇,以为玉茗之后殆无其偶。”[2]这些评价究竟是否合适,姑且不论,但《秣陵春》的艺术构思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受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如《秣陵春》剧中写黄展娘与徐适在宝镜与玉杯中分别看到各自的身影,黄展娘也是一灵咬住,魂魄离开躯体,寻到徐适而成亲,两人被冲散后,展娘归家还魂,从如幻如梦中苏醒,后二人终成连理。此中心情节与“牡丹亭”杜丽娘返魂十分相近。近代曲学大师吴梅说:“梅村乐府,嗣响临川。南部梦华,记诸幻影。艳思哀韵,感人深矣。”[2]郑志良教授对此做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考证。
清顺治已亥十六年(1659),李明睿的挚友熊文举《良夜集沧浪亭观女剧演新翻〈秣陵春〉,同遂初、博庵赋得十绝,呈太虚宗伯拟寄梅村祭酒》诗,把汤显祖、李明睿、吴伟业的这种师承关系说得明明白白,其云:
紫玉红牙许共论,临川之后有梅村。
可知宗伯名师弟,孝穆兰成早及名[6]。
2 李明睿家庭戏班
李明睿在政治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据清同治《南昌县志》载:
(李明睿)明天启壬戌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坊馆,罢闲六七年。廷臣交荐擢中允。时闯贼复秦,京师震动。总宪李邦华疏请太子监国南都,备不测,上疑未决。而明睿疏请面对:“太子幼,必上自出乃有可为”。不用其策。寇逼,范景文重理前说事,不及矣。入国朝(笔者按:清朝)摄政王询于廷臣曰:“汉官何人最贤?”众以明睿对。乃起用为礼部侍郎,署尚书事。未几,以病乞休,卒年八十有七[7]。
李明睿为何“罢闲六七年”?县志上没有记载。吴伟业《座师李太虚先生寿序》道出其中原委:“先生性强直,为台谏所中,隐居白鹿。讲授生徒”。李太虚隐居庐山白鹿书院讲学,还“摭拾累朝故实,抄撮成书,凡数百卷,欲以成一代之良史。”[8]后来由于“廷臣交荐擢中允”。
中允是正六品官,是主管太子和皇室宗亲日常生活的。他能直接面见皇帝,上疏献策。李自成占据陕西,震动朝廷,李明睿建议迁都南京,崇祯皇帝犹豫不决,朝中大臣怕丢失在京的家财,反诬李明睿主张逃跑是没有骨气。等到李自成兵围京城,范景文重提南迁之事,李明睿说,来不及了。结果是崇祯皇帝煤山自缢,明朝灭亡。入清后,清摄政王闻李明睿贤能,任命其为礼部侍郎。但李明睿在位半年,不适应满清朝廷的政务,因“朝参,行礼不恭,命革职为民。”[1]大概因为其在职时间较短,《清史》所列157名贰臣中,竟无其名。清顺治初年南昌反清复明的战斗并未停歇,尤其是顺治五年金声桓、王得仁之兵变,李太虚革职后,并没有立即回到南昌,而是流寓扬州、杭州。吴伟业有《座主李太虚师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八首》诗记其事[8]。李太虚在扬州蓄养了一班女乐,孙枝蔚清顺治十二年(1655)在扬州写的《太虚宗伯园中观女乐》对此有记载:
已看风景美林泉,更右佳人伴谪仙。
妙舞清歌世间少,不因诗句那得传。
曾闻水调每关愁,岂意神仙爱客留。
不是行觞仍玉女,何缘得见古扬州[9]。
(注:神仙留客、玉女行觞皆炀帝曲台)
大约在清顺治十三年,李明睿回到南昌,购得弋阳王府旧邸,改造为阆园,并在南昌城西一里的蓼州修建了沧浪亭。
裘君弘辑《西江诗话》卷十记载:
李明睿,字太虚,南昌人,天启进士,历官少宗伯,归里构亭蓼水旁,曰“沧浪”。家有女乐一部,皆吴姬极选[10]。
李明睿家中蓄养的女乐,大概是从扬州带来的戏班,是“吴姬极选”,唱的是昆腔。
在清顺治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年这几年间,沧浪亭经常有演出活动,观剧者留下不少观剧诗。《西江诗话》卷十记载:“公尝于亭上演《牡丹亭》及新翻《秣陵春》二曲,名流毕至,竞为诗歌,以志其胜。”[10]
从大量的观剧诗中,我们得知其家庭戏班的基本情况:
(1)女乐有八人。李明睿的门生黎元宽观剧诗云:
萦怀底事聊凭禊,作语生香仅八奁。
座上风光今正好,明朝又怕雨帘签[10]。
奁,本是指女子的梳妆用具,此处代指女伶。八奁,即八个女伶。这八个女伶所担任的戏曲行当,在李元鼎的观剧诗中有记载,分别是:生、旦、小生、小旦、末、外、净、丑。
(2)较为出色的演员有:迴雪、烟波。李明睿有诗云:
清风明月人间有,玉管冰壶天下无。
回雪临风吹玉管,烟波弄月濯冰壶[10]。
(注:回雪、烟波,公二妓名)
还有晓寒,朱中楣《初春寄宗伯年嫂并忆烟波、晓寒诸女伶》诗云:
又值阳春景物和,怡怀谁解晓寒歌。
年光荏苒闲愁剧,风雨凄其感咏多。
玉茗尚然迷柳梦,沧浪空自锁烟波。
花繇锡九应增艳,忆掐檀痕唤奈何[9]。
尤其出众的是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但好景不长,李明睿解散了戏班。清顺治十八年方文《闻李宗伯家姬并遣伤之》诗云:
霓裳一部本群仙,祗合文人裕结缘。
底事同归厮养卒,酸风腥雨哭婵娟。
闻说登舻涕泪频,烟波迴雪更悲辛。
章江游子肠先断,况是虔州纳彩人[9]。
(注:烟波、迴雪,二伎名,虔州友人曾以千金聘烟波不可得)
当年虔州(今江西赣州)友人出千金下聘求娶烟波而不可得,如今却无可奈何地给了“厮养卒”。个中缘故不得而知,但若无权势所迫,李明睿不会割舍这些朝夕相伴的歌姬。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的遭遇,清康熙南昌人刘健《庭闻录》的记载,似乎透露了个中消息:
八面观音与圆圆并擅殊宠,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儿十数辈,声色极一时之选,而八面为之魁。其曹四面观音亦美姿容,亚于八面,先公(按:作者之父)曾于宗伯弟见其歌舞,果尤物也。宗伯老,为给事高安所得,以奉(吴)三桂。辛酉城破,(陈)圆圆先死,八面归绥远将军蔡毓荣所得,四面归征南将军穆占[11]。
既然是给事高安把八面观音和四面观音奉献给气焰熏天的吴三桂,李明睿只好忍气吞声地割爱了。
(3)参与观剧者,多是江西地方名流,或为李氏之门生,如黎元宽;或为在京为官时的同僚,如熊文举、李元鼎。吴伟业的老师张漙是复社领袖,吴伟业是复社中坚,而熊文举、黎元宽、朱遂等均为复社成员。这些人在明代都是响当当的名仕,而明朝灭亡后。清政府对前明官员采取留用政策,这些人又同李明睿一样,仍然当官(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吴伟业),被人视为“贰臣”。而清初民间舆论对“贰臣”们极为反感。“贰臣”们多数留恋旧朝廷,在朝为官,也是身不由己,对异族统治不习惯,弄不好就会遭到贬谪,在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状态中过日子。他们很多人都是像李明睿一样,或以病乞休,或以照顾父母亲为由,回乡隐居。正好李明睿有这样一个观剧的聚会场所,而主人又非常大方,所以大家乐得寄情戏曲,写点观剧诗,聊以遣怀。
(4)据目前所见观剧诗中,李明睿家庭戏班在沧浪亭演出最多的剧目是老师汤显祖的《牡丹亭》和门人吴伟业的《秣陵春》,还有《拜月亭》、《燕子笺》等。
吴伟业认为戏曲是文人真实思想感情的体现。他在《北词广正谱序》中声称,戏曲作品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还说:
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8]。
吴伟业在《秣陵春》一剧中,表达了何种“抑郁牢骚”呢?李明睿的挚友熊文举顺治十六年(1659)写的《良夜集沧浪亭观女剧演新翻〈秣陵春〉,同遂初、博庵赋得十绝,呈太虚宗伯拟寄梅村祭酒》诗歌就说得非常清楚,吴伟业是带着明代遗民、旧臣的哀痛来撰写剧本的:
哀音亡国不堪闻,谁过鸣銮念故君。
想见娄江吊双影,伤心如读战场文[6]。
吴伟业对前明朝的这种深深眷恋之情,与其获得会试榜眼的风波有关。当时有人不服,告到崇祯皇帝那里,崇祯皇帝亲自批阅,书“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平息了这场风波。对皇帝的这种知遇之恩,怎能不铭刻于心?听说崇祯煤山自缢,吴伟业也在家中上吊,为家人发现,才免于一死。吴伟业曾是明末复社的党魁,在政治上是颇有一番雄心壮志的。后来又在南京弘光朝任少詹士,满怀匡扶社稷之志。但因受到马士英之流的排挤,只得辞职回乡,研究学问,潜心著述。《秣陵春》大约撰写于清顺治七年(1650)左右,在清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出山任国子监祭酒之前。剧中演绎的徐适的遭际,正有吴伟业自身的投影:深切的亡国之痛,夹杂着一些侥幸和希冀。吴伟业《秣陵春》所塑造的徐适这一艺术形象,映射出明清之交朝代更替时留职人员的矛盾心态。任职四年的“贰臣”生活,是吴伟业人生中最不光彩的一段经历。清康熙十年(1671)吴伟业与他的老师李明睿在同一年告别人世。他在弥留之际,写下了四首辞世诗,其一云:
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还不如[8]。
这是吴伟业晚年愧疚、负罪、屈辱心情的真实写照。前引熊文举《十绝》诗之一,也道破了这一隐秘:
亭外山河照酒樽,玉人低唱易黄昏。
南唐往事犹如此,应为孤臣更怆魂[6]。
写诗的熊文举和李明睿等一班“孤臣”大概都有此复杂的心路历程。
3 越调吴歈可并论,汤词端合唱宜黄
李明睿偶尔也邀请民间戏班到沧浪亭演出。以演出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看家戏的得得新班宜伶泰生便在沧浪亭演出过。
清顺治庚子十七年(1660),熊文举在李明睿家观看宜伶演出,演出剧目为汤显祖的《紫钗记》和梅鼎祚的《玉合记》,写了《宜伶泰生唱紫钗、玉合,备极幽怨,感而赠之》诗五首[6]。其一云:
宛陵临汝擅词场,钗合玲珑玉有香。
自是熙朝多隽管,重翻犹觉艳非常。
按:宛陵,安徽宣城旧称,梅鼎祚是宣城人,宛陵代指梅鼎祚。临汝,即江西临川,此处代指汤显祖,汤为江西临川人。汤、梅二人自青年时代起即为挚友。“钗合玲珑玉有香”,“钗”指《紫钗记》,“玉”指《玉合记》。
其二云:
四梦班名得得新,临川风韵几沉沦。
为君掩抑多情态,想见停毫写照人。
按:“四梦班名得得新”,是说演出“临川四梦”的戏班,名为“得得新”。
其三云:
凄凉羽调咽霓裳,欲谱风流笔研荒。
知是清源留曲祖,汤词端合唱宜黄。
(注:宜黄有清源祠,祀灌口神,义仍先生有纪,予拟风流配填词未绪)
按:宜黄县是明清时期江西著名的“戏窝子”。诗注云“ 义仍先生有纪”,是指明万历三十年左右,汤显祖应宜黄县艺人邀请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清源师为宜黄县艺人所供奉之戏神。《庙记》中详细记载了宜黄县戏曲声腔的演变过程:
此道有南北。南则昆山,之次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諠。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5]。
据考证,谭纶自浙江请海盐腔艺人到宜黄县教戏是在明嘉靖末期,到汤显祖写《庙记》时,海盐腔在当地已经流行四十多年,唱海盐腔的艺人已有千余人。在这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海盐腔已经在宜黄“地方化”,称为“宜黄化”的海盐腔,即宜黄腔(参见笔者《汤显祖梅鼎祚剧作的腔调问题——兼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两种宜黄腔:海盐腔支派与二黄腔本名》等论文,见苏子裕《戏曲声腔剧种丛考》,2009年)。
熊文举在南昌沧浪亭观看宜伶泰生演唱汤显祖的《紫钗记》,写诗赞道:“汤词端合唱宜黄。”这就是说,汤显祖的“词”(当即“临川四梦”),用其它声腔来演唱也是可以的,但用宜黄腔来演唱是最合适不过的。熊文举给予这个评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李明睿的昆腔家班是“吴姬极选”,演员十分了得。她们演出汤显祖的《牡丹亭》等剧,受到观剧者的高度评价,熊本人也写了多篇诗歌予以赞叹。沧浪亭的主人李明睿既是熊的挚友,又是昆腔戏班的主人。如果对宜伶泰生演出的评价过高,会使李明睿没面子,也会使其他观剧者扫兴。他能写出“汤词端合唱宜黄”,说明这是观剧者(包括李明睿)的共识。
汤显祖的剧作为什么用宜黄腔来演唱是“端合”呢?因为汤显祖的剧作是用宜黄腔进行创作的,答案就在这里。李明睿是汤显祖的学生,又是戏曲鉴赏家,对此情况不会不清楚。汤显祖的剧作用宜黄腔进行创作,“汤词端合唱宜黄”是一个铁证。另外,明代戏曲家也有人知道这个事实。一是化用宜黄土音。范文若《梦花酣·序》在提及《牡丹亭》时说: “临川多宜黄土音,板腔绝不分辨,衬字衬句凑插乖舛,未免拗折人嗓子”[12]。临川,代指临川人指汤显祖。临川话与宜黄话虽同属临川语系,但并不完全相同。汤显祖是临川人,但其创作的《牡丹亭》不用临川土音,而“多宜黄土音”,正好说明汤显祖是用宜黄腔来撰写剧本的。
但不少人对此心存疑窦。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汤显祖自己就只记载了海盐腔,没有记载宜黄腔,认为汤显祖用海盐腔创作是可以的,但说他用宜黄腔创作,根据不足。这种疑虑是难免的。一种新的戏曲声腔或剧种诞生以后,总是在它流传到外地之后才会获得新的名称,起初,人们会以地名称呼这种戏曲,如湖北黄梅县的采茶戏,流传到安徽怀宁之后,被称为黄梅调、黄梅戏,而在黄梅县本地却仍然称为采茶戏。又如,京剧在北京称为二黄戏,流传到上海以后,被称为京戏、京剧。同样,宜黄腔产生之后,在宜黄、临川一带仍然被称为海盐腔,只是流传到外地以后,才被称为宜黄腔。
笔者还可以补充一些资料,在抚州地区直到清初,只有海盐腔、或“越调”、“越吹”的记载。如清乾隆五年(1740)刊本《临川县志》记载:
吴讴越吹,以地僻罕到,飨官长则呼土伶,皆农闲习之。拙讷可笑。近官长多自蓄之[13]。
文中记载的“吴讴”是指昆腔;“越吹”是指海盐腔。说明在清乾隆以前,临川还有演唱海盐腔的民间戏班。临川戏班所唱的海盐腔,应当就是宜黄腔。只不过沿袭当地人的习惯,仍称其为海盐腔。
与熊文举观剧写诗唱和的,还有李明睿好友同年进士李元鼎及其夫人朱中楣(1622—1672),她在《宗伯年嫂相期沧浪亭观女伎演秣陵春,漫成十绝》诗之一写道:
越调吴歈可并论,梅村翻入莫愁村。
兴亡瞬息成古今,谁吊荒陵入白门[9]。
诗中的“越调吴歈”与《临川县志》所记之“吴讴越吹”都是一个意思:吴歈、吴讴都是指昆腔,越调、越吹都是指海盐腔。李明睿家庭戏班演《秣陵春》,唱的是昆腔,宜伶泰生演《紫钗记》、《玉合记》唱的是“越调”(海盐腔)。南昌在万历初期就有海盐腔,万历十六年(1588)宁王府海盐腔戏班演出《绣襦记》[14]。朱中楣是宁王后裔,明宗室辅国中尉议汶次女,当然知道府中常演唱的海盐腔,她认为宜伶所唱的腔调与王府中所演唱的“越调”(海盐腔)是同一类腔调。她认为“越调吴歈可并论”,是说宜伶泰生所唱的“越调”与李明睿女乐所唱的昆腔可以相提并论。
但毕竟宜黄腔与南昌的海盐腔有所不同,是“宜黄化”了的海盐腔。生活于明万历、崇祯年间的南昌诗人万时华把宜黄腔称为“新谱”。其《棠溪公馆同舒苞孙夜酌二歌人佐酒》诗云:
野馆清宵倦鲜装,村名犹识旧甘棠。
松邻古屋霜华净,虎印前溪月影凉。
寒入短裘连大白,人翻新谱自宜黄。
酒阑宜在嵩山道,并出车门夜未央[15]。
按:棠溪,村名,在南昌市郊区罗家集附近。歌人所唱“新谱”传“自宜黄”,当是宜黄腔。其在南昌乡间有歌人演唱,在南昌城内盛行自不待言。为何诗人把歌者所唱的腔调称为是传自“宜黄”的“新谱”呢?那是因为,南昌有海盐腔“旧谱”,而宜黄腔系从海盐旧谱演变而来,所以被称为“新谱”,宜黄“新谱”,就是由海盐腔演变而来的宜黄腔。
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资料看来,宜黄腔之名,是在流行到南昌之后才有的,如万时华的诗句所言。如此看来在汤显祖的诗文中,只有海盐腔的记载,没有出现“宜黄腔”的字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汤显祖开始进行戏曲创作的时代,海盐腔在宜黄已经流行了三十多年,“宜黄化”的过程也已完成,也就是说宜黄腔已经形成。在汤显祖的诗文中,多次出现“宜伶”、“小宜伶”的记载。所谓“宜伶”,不是指“宜黄县艺人”,而是指“宜黄腔艺人”。“宜伶”这一称呼的出现,标志着宜黄腔的诞生。汤显祖说“曲畏宜伶促”[5] 565,证明他是为宜伶而写戏。既是为宜伶而创作,当是用宜伶所熟悉的声腔——宜黄腔。
宜伶不一定就是宜黄籍的演员,如同“海盐子弟”不一定就是海盐人,《金瓶梅》所记载的苟子孝,就不是海盐人,而是苏州人。清乾隆时,北京人唱戏的很多,只有京腔班的演员才被称为“京伶”,如吴长元《燕兰小谱》所记之京伶八达子、京伶冯三儿。明代吕天成《曲品》所记之“弋阳”、祁彪佳《远山堂》所记之“弋优”都是指“弋阳腔”,而不是专指弋阳县艺人。宜黄腔不可能仅在宜黄一县打转,与之紧临的临川,当得风气之先。临川是抚州府治所在地,自元代以来就是戏曲盛行之地。宜黄腔传入临川是十分便利的。明万历三十年汤显祖《庙记》中所记当时海盐腔艺人有千名之多,据清康熙十八年(1679)知县尤稚章主修《宜黄县志》三卷《户口》记载,万历十年全县人口只有18 795。一个这样的小县,不可能容纳一千名海盐腔艺人。这一千名海盐腔艺人,就应该包括临川地区的海盐腔艺人。在汤显祖时代,临川地区既有宜黄县的戏班,也会有临川县的戏班,他们都是唱宜黄腔。
汤显祖的诗文中所记之宜伶,都和汤显祖保持密切的联系,可以由汤显祖派遣到外地为朋友演出,如《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5] 799《遣宜伶汝宁为前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5] 757中的宜伶,汤显祖甚至可以由“宜伶相伴酒中禅”[5] 766。这说明这些宜伶都是长期生活在临川的。汤显祖辞官回乡隐居之后,生活日益贫困,他哪里有钱蓄养家庭戏班。没有家庭戏班,却又能派遣宜伶赴外演出,是因为这些宜伶是由他培养出来的,汤显祖不是经常“自掐檀痕教小伶”演唱《牡丹亭》吗?[5] 735教师派学生出外演出,才可以不花很多钱。汤显祖在临川培养“小伶”,当是临川本地人,总不会特意到宜黄去招收学员吧?另外,他还劝临川友人帅机之子帅从升兄弟找些“小宜伶”在园林中演唱“四梦”,《帅从升兄弟园上作四首》诗记载:
小园须着小宜伶,唱到玲珑入犯听。
曲度尽传春梦景,不教人恨太惺惺[5] 730。
汤显祖所记的这些“宜伶”、“小宜伶”,都在自己身边,大多数应该是临川当地的宜黄腔艺人。而不是宜黄县籍的演员。有人把汤显祖所记载的“宜伶”,统统看成是宜黄县的艺人,这就不恰当了。临川当地有宜黄腔戏班,何必非要到宜黄去请艺人[16]。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
(1)清顺治末期李明睿在南昌沧浪亭经常有观剧活动。他有自己的家庭戏班,拥有非常优秀的昆腔演员。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老师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和门人吴伟业的《秣陵春》。汤显祖是明代剧坛巨擘,吴伟业是清代剧坛高手。李明睿拥有家庭戏班,是戏曲鉴赏家。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戏曲师生链。
(2)沧浪亭的观剧者,多是李明睿的昔日同僚、学生、乡友。不少人是明朝仕宦,入清之后又为清朝廷留用,被视为“贰臣”。这在清初一些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文人看来,是没有骨气,颇受鄙视。而其本身在朝为官,也不太习惯满族统治,稍有不慎,便遭贬谪。失意、屈辱、愤懑等复杂的情绪挥之不去,只好寄情于观剧、写诗等文艺活动,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而吴伟业的《秣陵春》所表达的“南唐往事犹如此,应为孤臣更怆魂”正是这个特殊文人群体中大多数人心态的写照。
(3)在沧浪亭演剧的还有宜伶,演出的剧目有汤显祖的《紫钗记》和汤显祖好友梅鼎祚的《玉合记》,唱的是宜黄腔。“汤词端合唱宜黄”,这便宣示了汤显祖剧作是用宜黄腔创作的。
[1] 施祖毓.李明睿钩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34-139.
[2] 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探考[M] .北京:中华书局,2014:274.
[3] 黎元宽.进贤堂稿(清康熙刻本):卷二十二[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4] 夏云鼎.前八大家诗选:卷五之六[M]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8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 汤显祖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6] 熊文举.雪堂先生诗选[M] .清康熙刻本.
[7] 陈纪麟,汪世泽.南昌县志[M] .清同治九年刊本.
[8]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9] 纪宝成.清代诗文集汇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 裘君弘.西江诗话[M] .清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11] 刘健.庭闻录[M] //笔记小说大观.台北:台湾新兴书局,1988.
[12] 范文若.梦花酣·自序[M] //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第二册.济南:齐鲁书社,1989.
[13] 李绂.临川县志[M] .清乾隆五年刊本.
[14] 陈士业.江城名迹记[M] .清乾隆刻本.
[15] 万时华.溉园诗集[M] //丛书集成续编.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8.
[16] 黄金亮.汤显祖导演艺术初探[J] .抚州师专学报,2000(3):28-32.
Yue Melody and Wu Ballad can be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 Yihuang Tune is Suitable for Tang’s Plays——On Li Mingrui’s Opera Activities at Canglang Pavilion in Nanchang in Early Qing Dynasty
SU Zi-yu
(JiangxiProvincialAcademyofArts,Nanchang330025,China)
The ancient Chinese playwright Tang Xiangzu was the chief examiner of Li Mingrui, a connoisseu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while Li was the chief examiner of Wu Weiye.Their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ormed a splendid chain in Chinese opera history.During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Shunzhi in Qing dynasty, Li Mingrui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Nanchang bringing a troupe of high-caliber Kunqu opera actresses.The troupe often staged operas at the Canglang Pavilion in Nanchang, among which the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written by Li’s teacher Tang Xianzu and Spring of Moling by Li’s student Wu Weiye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performed operas.The grand performances were recorded in a number of poems by the audience members in those days.Another troupe which performed at Canglang Pavilion is Dedexin Troupe, a troupe featuring Yihuang tune singing and notable for its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led by Tai Shen.Yihuang tune evolved from the Haiyan tune that was introduced into Yihuang area.In Yihuang and Linchuan areas, it is now still called Haiyan tune because of its origin in Haiyan area.Haiyan tune, which originated in Haiy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is also known as Yue melody.The performance of the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at the Canglang pavilion in Nanchang featured the Kunshan tune from Li Mingrui’s family troupe as well as the Yihuang tune from Dedexi troupe.Both the tunes reach a high level of excellence, thus winning the reputation of “Yue Melody and Wu Ballad can be mentioned in the same breath”.Some audience even believe that Yihuang tune is more suitable for Tang’s plays.
Tang Xainzu; the Four Dreams of Linchuan; Yihuang tune; Yue melody; Li Mingrui; Wu Weiye
2016-08-10
苏子裕(1944—),男,江苏江宁人,研究员,主要从事戏曲声腔史研究。
J809
A
1674-3512(2016)03-02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