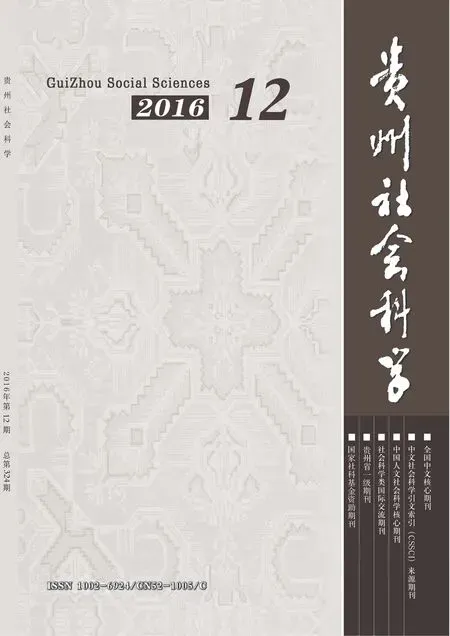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
张 箭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金鸡纳的发展传播研究
——兼论疟疾的防治史(上)
张 箭*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疟疾是一种很常见且危害性很大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但美洲却独有能抗疟退烧祛病的金鸡纳树(皮)。印第安人率先发现了这一秘密,到17世纪20年代,在美洲的欧洲人也知晓了这个秘密。他们于17世纪30年代把金鸡纳树皮作为药材传入欧洲。在罗马教皇、天主教会和耶稣会士的支持和倡导下,服用有特效的金鸡纳树皮治疟渐渐瓦解了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各种偏见,传播开来。欧洲各国开始向南美洲派遣科考队(组)去寻找、认识、考察、调查金鸡纳树林。随着金鸡纳树皮的需求量大增,野生金鸡纳树资源开始萎缩。欧洲人遂开始大规模引种移植。其栽培地是南亚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林场和种植园。历经各种磨难和挫折,欧洲人的移植引种行动一步步取得成功。19世纪10年代,葡萄牙医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金鸡宁,几年后法国化学家又从树皮中分离出奎宁。这些现代抗疟西药的出现大大方便了疟疾的临床治疗。到19世纪末,亚洲种植园的树皮产量已占绝对优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医学家们发现和揪出了疟疾致病的罪魁疟原虫,弄清了疟疾通过按蚊叮咬而传播的路径,为大规模防疟开辟了道路。20世纪中叶以降,药学家们相继研制成功阿的平、氯喹、青蒿素等抗疟新药。金鸡纳—奎宁在抗疟战线独尊的地位才降为与它们平分秋色。17世纪末,金鸡纳树皮传入中国,旋即被接纳为传统中药材。其西药成药金鸡纳霜(奎宁)发明后不久也传入中国,但国内解放前一直无奎宁生产。金鸡纳树皮和奎宁撑住了中西抗疟大局几百年,至今仍是抗疟主力药物之一。
金鸡纳树;疟疾;寻觅和科考;移植与栽培;种植园;爪哇和印度;金鸡纳霜/奎宁;入华历程
美洲新大陆不仅向世界贡献了玉米、马铃薯、甘薯、烟草、橡胶、花生、向日葵、可可、西红柿、菠萝等重要的粮、经、果、蔬等农作物,还贡献了一些独特的药用作物(药材),其中最重要最著名功绩最大的便是医治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奎宁。但国内学界对金鸡纳的发展传播应用史缺乏研究甚至没有研究。例如,据查,农史四刊25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中,便没有一篇论金鸡纳发展史的文章。[1]又如,《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这本专著也毫无论及。[2]只有一些短小的知识普及通俗文章对此有所提及(将在行文中随出随注)。国外的有关研究则要分语言文化圈简述。日本学者星川清亲著有《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一书,并出了1978年初版和1987年改订增补版两版。[3]该书论述了许多栽培植(作)物的传播史,包括二十来种美洲植(作)物的传播史,但未涉及金鸡纳。苏联—俄罗斯方面,据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和70年代出版的第三版“金鸡纳树条”,前者文末列出的参考文献中有两本俄语书:一本是波兹尼亚克(Позняк А.Д.)的《金鸡纳树及其栽种》(列宁格勒1936年版);另一本是莫洛多日尼科夫(Молодожников М.М.)等人的《苏联亚热带地区的金鸡纳树》(苏呼米[Сухуми,格鲁吉亚城市]1938年版)。[4]后者文末列出的参考文献中有三本俄语书:即《苏联药用植物地图集》(莫斯科1962年版);茹科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 П.М.)的《栽培植物及其亲缘植物》(列宁格勒1971年版);穆拉维耶娃(Муравьева Д.А.)等二人的《热带和亚热带药用植物》(莫斯科1974年版)。[5]从书名可知它们都主要研究金鸡纳的人工种植和剥皮制药而非它的发展传播史。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最主要的继承国俄罗斯正在编纂《俄罗斯大百科全书》,[6]但目前尚未出齐,故难以从中窥探当今俄罗斯对金鸡纳史的研究情况。笔者因不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而不知这些语言文化圈的有关研究情况。而英语圈是有一些研究的。据笔者搜集,20世纪以来主要有几本专著和若干篇论文。不过,我觉得它们在论述金鸡纳的作用和意义上强调不够。鉴于国内没有研究,故本文拟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论述金鸡纳的发展传播应用史,并兼评它与疟疾的防治及它在三个多世纪中所发挥的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一、疟疾的危害与金鸡纳的发现
要讲清金鸡纳的重要性,就得先讲清疟疾的危害性。疟疾是一种很常见危害性很大病理很复杂的传染性寄生虫病,以间歇性发高烧为主要病征。在1949年以前,中国每年约有3000万疟疾病人,现在每年仍有几十万人罹患疟疾。[7]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6年全世界有2.47亿人患疟,100万人(因此)病亡。[8]疟疾的病原体是疟原虫,传染媒介是被带虫的疟蚊属蚊子叮咬。不过,这些是到现代才搞清楚的问题了。
疟疾过去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参与毁灭了一些古老文明。现代史家和医家根据历史文献和病案判定,一些英年早逝的历史名人伟人系遭疟疾戕害。他们中间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图拉真、首次攻占“永恒之城”罗马的蛮族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但丁、教皇英诺森八世、克伦威尔,[9]4,9,11,56穆罕默德,[10]郑成功,[11]527,224等等。疟疾在近代以前长期在旧大陆各地区肆虐。例如,14世纪发生过罗马教廷避居意法边境意方小城长达69年的所谓“阿维农之囚”(1309—1378)。大的背景是亲法教皇们惧怕意大利等国贵族的反对,想就近得到法国的支持与保护;但现代的研究表明,还有担心染上所谓“罗马热症”(Roman fevers)便避开疟疾流行区罗马一带的重要因素。因为在这段时期驻阿维农的教皇们先后(病)死了六个,而在上个世纪的同一段长的时期(69年)驻罗马的教皇们则先后(病)死了十二位。[9]11-12所以在罗马受到疾病特别是疟疾的威胁要大得多。又如,1639年,一场凶险的疟疾突然蹂躏英国造成劳力锐减,乏人收割,严重歉收。[9]15
疟疾也是人类最早去努力认识的疾病之一。在公元前1500多年的埃及纸草和公元前7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泥板文书中已记述了病人脾脏肿大和周期性发烧(热),大概即指疟疾。[12]2最早把沼泽、湿地、积水地与损害健康联系起来的意识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波斯和巴比伦。[13]5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其《流行病之书》中已注意到疟疾有不同的热型,并有日发疟、间日疟和三日疟三种。[14]他确认在收获季节(晚夏和秋天),发热病和苦难便接踵而至。希波克拉底认为,这些周期性的发烧病归因于人身四种体液(血液、痰液、黑胆汁、黄胆汁)的紊乱,而体液紊乱是由饮用从沼泽地打来的停滞的水引发的。[12]2有的古代学者怀疑,它是由沼泽地内恶劣有害的空气引起的间歇性发烧。印度吠陀时代(前1500—前800年)的文献把秋疟归为“诸病之王”;[12]2印度古医籍《妙闻集》则已提到蚊子与疟疾有点关系。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作家、农学家、图书馆长瓦罗(M.T.Varro)在《论农业》中猜测,沼泽地中滋生着一种极小的看不见的生物,它通过口、鼻进入人体引起发病。[15]32罗马时代的学者意识到排干积水有时能控制间歇热的流行。以后人们不时提及瓦罗的猜测。中世纪的意大利人多把该病归咎于有害的空气。人们以为,在易发热病的夏季,雾气从沼泽地四散开来,罗马热(the Roman fever)就复发流行起来。[12]3所以西方各国表“疟疾”一词多为malaria,均源自意语。其中,male表示“有害,恶劣”,aria表示“空气”。这有些暗合中国俗称的瘴气。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对疟疾的防治均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药物。
在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有无疟疾尚不清楚,没有定论[9]18近年来的研究细致深入了一些,有学者认为,“白人到来之前,疟疾似乎不太可能存在于北美和秘鲁”,[15]170意思是说美洲的这两个地区原无疟疾。还有学者指出:“金鸡纳树原产于高耸的雨量充沛的安第斯山麓,而那一带从未有过疟疾。”[15]XVIII再如,“具有最大讽刺意义的是,诞生了天然治疟药物的新大陆,并未受到疟疾的折磨,直到欧洲定居者把它传入”。[16]142复如,“在英国人的殖民地弗吉尼亚,疟疾杀死了更多的殖民者。也有许多本地的印第安人,死于这传入的疟疾”。[16]146“皮萨罗带了100多个士兵进入秘鲁,一举摧毁了这个文明古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士兵因(服用)土著人的金鸡纳树皮才逃脱疟疾的魔爪,而土著人却因为这些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而几乎灭绝”,[16]164意思是说秘鲁原无疟疾,等等。综上可知,近年来的趋势是讨论白人到来之前,美洲的某个具体的地区有无疟疾,而且意见不一致。但总的意见仍是:1492年以前美洲有无疟疾,疟疾是否是从旧大陆传入的;如果原来就有那印第安人是否已利用金鸡纳治病——均不能确定。[17]而一些论著则说白人殖民者把疟疾传入了美洲。比如,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讲,“……但是白人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疾病,这些疾病引起了真正可怕的后果。最坏的病症有……,也许还有结核病、疟疾和梅毒。这些病症在白人到达以前,美洲是很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见“美洲土人”一九四六年四月号)”。[18]又如,小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称,“当然,土著人也有自己的传染病。……但他们似乎从未经历过旧世界的疾病,例如……疟疾……以及几种蠕虫感染症”。[19]霍布豪斯的《变化的种子》讲:“大概西班牙人随己带来了此疾病,大概在西班牙人占领了一段时期之后,疟疾才在南美大陆成为地方病的。”[13]20西方研究抗疟史的权威谢尔曼在其最新的专著中多次提出,在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并无疟疾病。[12]3我认为不能轻易说欧洲人把疟疾传入了美洲。因为即便美洲原无疟疾,欧洲疟疾患者带病到了美洲,但他们也不能传染、传播给别人。因为疟疾并不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染传播,而主要通过疟蚊叮咬传染传播,也可通过输血而感染(患者血液输入健康人体内),但当时并无输血技术。直到20世纪初发现血型、接着又发明了输血前献血者和受血者的血液凝聚试验,这才诞生现代安全的输血技术。[20]还有一种先天性疟疾,可以在生育前或生育期间由带病母亲传给胎儿或婴儿。[21]疟疾病人死后,体内的致病元凶疟原虫也就跟着死亡。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欧洲人很难把传播此病的媒介按蚊—疟蚊随己飘洋过海带到美洲。所以,美洲原来有无疟疾尚需继续研究。问题似乎也可转为美洲原来有无按蚊(疟蚊)。而有的学者认为,美洲新大陆自来就有按蚊(疟蚊,Anophelesmosquito)。[16]143还有的学者列出了美洲疟蚊的具体种类和分布地区。[11]143-145谢尔曼的总结为,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有疟蚊,没有疟疾病。这种病是欧洲人来到美洲后被美洲的疟蚊叮咬而传开的。[12]42我认为这种新说比较客观合理,而且带病(无意识)传播者应该还包括被白人驱使的非洲黑人,因为长期以来黑非洲的疟疾情势更严重。
不管怎样,旧大陆的人们不断在探索寻觅防治疟疾的有效方法和药物,但一直没有重大进展。而美洲新大陆的印第安人,从他们遭到其他热病和疟疾危害之日起,也在摸索寻找能抗疟退烧的药物和方法。
由于大自然的原因,美洲独有能有效抗疟退烧的金鸡纳树。金鸡纳树(Cinchonaledgeriana)为茜草科金鸡纳属常绿小乔木。新枝方形,叶对生,椭圆状披针形或长椭圆形。夏初开花,花白色,有强烈气味。顶生或腋生圆锥花序。蒴果椭圆形。金鸡纳树高约2.5—6米,树皮黄绿色或褐色。适宜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拔800—3000米的山地。主要用种子等法繁殖。生长约七八年后可采割树皮或根皮。若十年后采割,则此时奎宁含量最高。金鸡纳树皮含有30多种生物碱,其中主要为奎宁,其次为奎尼丁等。奎宁为抗疟特效药,其制剂能消灭各种疟原虫的裂殖体,终止疟疾的发作,对间日疟疗效尤好。金鸡纳属中有二十几种树种,其中红金鸡纳树(C.succirubra)、药金鸡纳树(C.officinalis)和黄金鸡纳树(C.calisaya)的树皮和根皮亦可提制奎宁和奎尼丁等。[22]在近代化学制药工业发明前,用上述金鸡纳树的树皮根皮熬药汤内服或磨成药粉内服也能非常有效地退烧抗病杀疟。
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印第安人已在社会生活实践中药用金鸡纳树皮。比如,秘鲁印第安人当身处潮湿之地感到寒冷时,有时便喝用金鸡纳树皮浸泡的热饮料,以镇住冷颤。后来卖苦力于西班牙人办的矿山的印第安人矿工也常常咀嚼金鸡纳树皮,以便忍住因部分身体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而引起的冷颤。[12]50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印第安人发现了金鸡纳树皮能抗疟这个秘密。这方面流传着一些神奇的传说。一曰秘鲁的印第安人常见山里的美洲狮(cougar)患了热病后,总要跑遍山林寻觅此树,啃嚼它的树皮“医治”自己并能治愈,土著人从而知道了此树(树皮)能治病退烧的药性。[9]24美洲狮或山狮(mountain lion)发现金鸡纳的故事最早出自18世纪上半叶法国博物学家孔达明记载下的一个传说,尽管他对此表示怀疑。[17]2此说传开辗转传入中国后又演变为,印第安人发现猴子打摆子(时冷时热)时便爬上金鸡纳树大啃大嚼树皮,之后就康复了。于是印第安人发烧时也予以模仿,从而发现了金鸡纳树(皮能治病)。[23]以上两则故事可归结为动物发现金鸡纳说。还有一类即人类发现金鸡纳说。一曰有个印第安人患疟疾病得很重,又烧又渴,已奄奄一息。他爬到一个池塘边喝了许多水解渴。池塘的水虽很苦涩,但喝后病情减轻许多。他经观察发现,池塘边有许多同样的树,其树根已蔓延生长浸泡在池塘里。他判断一定是这种树救了他。于是发现了金鸡纳。[24]印第安人患者无意中发现金鸡纳的故事在流传中其发现的主人公又演化为殖民地初期的西班牙士兵患者,[17]2并进一步演化为耶稣会士有意识地嚼尝各种树皮以分辨树种,于是发现了金鸡纳。[9]25这样,印第安人变成了白人,无意变成了有意,有些神农尝百草的意味了。不管怎样,印第安人率先发现了金鸡纳树皮能退烧治病抗疟的秘密,欧洲人晚于印第安人知晓此树。这是因为,欧人在16世纪关于美洲的两本专著尚未提及该树该药。一本是德·拉·维加(Garsilaso de la Vega,1539—1616年)的《印加人王统考》(Royal Commentaries on the Incas),另一本是德·雷昂(Pedro de Cieza de Leon)的1553年出版的《秘鲁编年史》(Chronicles of Peru)。[25]774不过,服用金鸡纳树皮能退烧解热治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未成为印第安人社会的一种常识和共识,而只限于少数部族、部落、家族知晓,属于他们要保守的秘密。染上热病能服用树皮退烧解热的患者也限于印第安人中的上层、中层及其他一些人数不多的群体。[9]25后来推广开后,一些地区的印第安人囿于古老的医学药学观念和患病治病理念,拒绝服用金鸡纳树皮抗疟退烧。在南美的一些印第安部族甚至到1890年仍谢绝服用免费的金鸡纳—奎宁。他们相信退烧的良方便是多喝冷饮。[13]16
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则把金鸡纳药物传入欧洲的动人故事。西班牙驻秘鲁总督—伯爵的妻子金琼(Chinchón)在欧人中因患疟最先服用金鸡纳药奏效,她便予以推广和传播。1638年,当时住在利马的伯爵夫人患病发烧。总督府医生卡尼萨雷斯(Canizares)用尽了各种方法和药物治疗但均无效。绝望中,总督同意这位医生用土法土药试试,即服用从遥远的北方劳克斯阿得到的土药金鸡纳树皮。医生让伯爵夫人喝下了混合着金鸡纳树皮粉的葡萄酒。令人欣喜的是,伯爵夫人的病情很快好转并最后完全康复。[16]145于是,1640年,伯爵夫人带着许多树皮回到西班牙,住在马德里东南40公里金琼(Cinchon)地区丈夫的庄园里,用这些树皮治疗一些发烧发热的病人,金鸡纳(树皮)从此在西欧传开。[16]145后来,瑞典大植物学家林奈为了纪念金琼夫人,在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中就以她的姓氏为该药材树命名,称之为Cinchona,中文一般译音为金鸡纳。林奈的命名拼错了一点点,掉了一个h。正确的写法应为Chinchona。尽管后来有人(如1778年有两个西班牙植物学家,还有后来的英国植物学家马克汉姆)要求将它改正,与金琼一致,[13]4但1886年的国际植物学大会讨论后决定将错就错,不再更改。故此名便沿用至今。
现代以来一些学者对这一树皮传入的说法提出质疑,其中较著名的哈吉斯于1941年考证指出,当时秘鲁的西班牙总督夫人金琼从未患过疟疾,而且在返回西班牙途中不幸于哥伦比亚北部港市卡塔赫纳病逝。所以她不可能把金鸡纳树皮传回欧洲。[25]774其证据为,发现于1930年的伯爵日记披露,在那个所谓患疟治疟时期夫人其实很健康没病,而且更没有回到西班牙传播金鸡纳这一福音,而是在途中病死在哥伦比亚,可能死于黄热病。[12]23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西班牙秘鲁总督、驻利马的德·波巴迪拉伯爵(D.L.G.C.de Bobadilla)在利马任职十年期间,本人患过疟疾并有幸康复。1641年他返回西班牙,途中在巴拿马逗留,等待来接他的西班牙舰船队。在巴拿马期间,他的妻子唐娜·弗朗西丝卡·金琼(Dona Francisca Chinchón)伯爵夫人不幸染病不治逝于此地,葬在了巴拿马城,[9]23丢下了个11岁的男孩。虽然其死地有差异,但她死在了美洲没回到欧洲无疑。尽管伯爵夫人金琼没有亲自把金鸡纳树皮传回欧洲,但她丈夫总督大人在利马患过疟疾并有幸治愈。金琼夫人肯定参与了对丈夫的照顾护理,参与了对医生治疗方案和药物的选择,对金鸡纳被人们认识、发展、传播、开发利用等有所贡献。于是人们才会纪念她,只不过在纪念中有所夸大和吹嘘。
与传说中的金琼夫人用上金鸡纳树皮治病的年代几乎同时,17世纪30年代的欧人文献开始明确记载了金鸡纳能治热病一事。一位叫卡尔兰察(Callancha)的奥斯定会修士于1633年用西班牙语写了一本论述奥斯定会编年史的书,于1639年在西班牙出版。书中提到:“有一种他们叫‘退烧树’(the fever tree, arbol de calenturas)的树生长在劳克斯阿(Loxa)国,其树皮呈黄棕色。磨成粉,每次用两枚小银币那么重的药粉兑成一种饮料服用,可治发烧和间日热(疟)。该药在利马已产生了神奇的疗效。”[15]58这条关键史料的另一个翻译文本为:“抗烧树生长在……秘鲁,其树皮磨制成药粉后,……掺入饮料中(服用)可治间日热(疟)。”[12]24仅晚于卡尔兰察之文献的是耶稣会士伯纳比·科波(Bernabe Cobo)的著作。他从1599年起就住在利马。他于1639年写的《新世界通史》(出版很晚)有一节叫“治疟之树”。其中写道:“在基多(Quito,今厄瓜多尔首都)主教区的劳克斯阿城地区,生长着一种大树,具有黄棕色的树皮,有点粗糙,味很苦。把它(树皮)磨成粉,给那些患疟的人。仅用此药可以祛病。这些药粉必须在打寒战(开始)前夕服用。把两枚小银币重的药粉兑于葡萄酒或其他饮料服下……”[15]59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美洲的欧洲人了解到接触到金鸡纳树皮并用它治病抗疟,当略早于17世纪30年代,可能是一六二几年。《在线天主教百科全书》(the online Catholic Encyclopedia)也称,耶稣会士们从土著人那里了解到金鸡纳树皮能抗疟当在1620—1630年间。[26]最早把金鸡纳树皮传回欧洲的不是金琼伯爵夫人而是伯爵本人。据当时身涉此事的热那亚医生塞巴斯蒂安·巴多(Sebastian Bado)所说,1541年总督—伯爵德·波巴迪拉回到西班牙,带回了一大批树皮。他免费向患热病的穷人分发,还送给需要该树皮做研究和考察的医生与药剂师,并持续了较长一段时间。[9]29-31他回到西班牙才两年,第一份提到“奎宁”(quinine)的欧洲(医学)文献便出现了,即德·黑登(Herman van de Heyden)于1643年出版的小册子《抗腹泻胃痛诸论》(Discourse et advis sur les flus de ventre douloureux)。[25]774以上是就金琼夫妇传入金鸡纳树皮说这一路线和故事而论。也有学者认为最早是由耶稣会主教德·科伯(Barnab de Cobo)于1632年将树皮传入西班牙和罗马的。[27]235最新的研究又认为,耶稣会在秘鲁首府利马的圣潘布洛(San Pabluo)学院和教堂最早从事向欧洲发送金鸡纳树皮药物的工作。据新近发现的当时的(1626年开始记载)一本西班牙语手抄本《府库公差钱粮账簿》(El libro de Viáticos y Almacén)记载,[28]早于金琼夫妇把树皮传入欧洲的是神父阿·米·维勒嘎斯(Alonso Messia Venegas)。他离开利马圣潘布洛学院和教堂赴欧时,从学院和教堂的库房领走了一些树皮。当他1631年到达罗马时便随身带了一些树皮,以便在疟疾经常流行的罗马供病人治疗服用。[15]78这样一来,金鸡纳树皮传入欧洲就要比传统所说又早了几年。
二、金鸡纳在欧洲的缓慢拓展
金鸡纳初步传入欧洲后,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身边的西班牙籍红衣主教德·鲁果(de Lugo)因得过疟疾有幸被治好而热心于推广他的同胞从美洲秘鲁传回的奇药。他指示教皇御医和收治有疟疾病人的罗马圣灵医院的医生,仔细研究秘鲁树皮的药用成分和对疟疾病人试用的疗效。[12]24奉命行事的西班牙籍御医丰塞卡(Fonseca)发现树皮中含有许多能退烧的有效成分而无任何有害成分,临床疗效也好。[9]42教皇御医们的结论颇具权威性,促使怀疑抵制金鸡纳的欧洲医药界态度有所改变。为了促进人们了解这种新药,在征得教皇同意后,德·鲁果主持向罗马圣城居民中的疟疾患者免费分发金鸡纳药物,即干燥的金鸡纳树皮。[15]58因此,这种新药材曾一度得名“红衣主教德·鲁果药粉(树皮)”。[9]43到1650年,秘鲁树皮已成为罗马城受欢迎的药物,许多朝圣者来到罗马购买一些树皮回家。由于耶稣会士积极经销和推广此药,红衣主教德·鲁果大力支持宣传此药,“秘鲁树皮”又获得“耶稣会药粉(树皮)”的称谓。[9]431651年,在罗马出版了一本《罗马计划表》的小册子,由耶稣会发行,书上还有几位罗马名医的签名表示已审阅。除了介绍该药,这本小册子还教人们如何用树皮下药。而最简便的用药法便是用树皮煎汁熬汤服用,与熬服中药类似。每次半杯,一天三次。[16]143
但金鸡纳在欧洲被接受和认可的进程也有反复,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有几起。17世纪初,跑遍世界的荷兰海员开始把鸦片混着砒霜吸食,认为可预防疟疾。[11]XVIII1652年,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Leopold)患上三日疟。御医用秘鲁树皮给他治疗并很快治愈,但一个月后疟疾复发。这本应继续服用金鸡纳树皮药粉并加大剂量,但大公感到受到了冒犯,竟斥责金鸡纳树皮为假药,并命令他的御医写了一本小册子《揭露出自美洲新世界的退烧药粉》,于1653年出版,告诫他的臣民别用这靠不住的药。[9]45同时期还有一位(今比利时)卢万大学的医学教授、著名学者普列姆皮乌斯(V.F. Plempius)。他原来是个新教徒(而且是加尔文教徒),因种种原因才皈依天主教。出于反对罗马教皇、天主教会和耶稣会,也猛烈抨击诋毁耶稣会树皮。他著书立说,对树皮的推广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但这些波折,终究阻挡不了正确的科学的事物逐渐被人们理解、认可和接受。秘鲁印第安人异教徒发现的在当地生长的解热树皮对治疗疟疾有奇效,使得欧洲的体液派医师自愧弗如,感到无用武之地。这个学派秉承公元2世纪罗马时代希腊裔医生盖仑的体液学说,一贯认为,只有排除不健康的致病的体液才能治愈疟疾,为此便应让病人呕吐、排尿、排便、出汗、适量放血等。这些疗法实际上不仅无用,还会使病人更虚弱。
耶稣会士极力把秘鲁树皮传往世界各地,以扩大耶稣会和天主教会的影响,同时也藉经营此药赚钱赢利。金鸡纳树皮推广传开后价格不断攀升。1648年,有个从美洲返回的西班牙医生在疟疾流行的塞维利亚省城出售他带回的金鸡纳树皮,每盎司1沙弗林金币(面值1英镑),合20世纪末的75美元/盎司。[13]13这大概是已知的欧洲药市上最早的树皮价格,17世纪末在欧洲市场上已从25法郎1磅(1磅约合454克)上涨到100法郎1磅。[9]83而治疗一个病例差不多要用去5公斤树皮,病愈后还要连续服用一周予以巩固,每天0.5公斤,[29]165以防复发。所以也只有富人和殷实之家才买得起治得起。虽然如此,耶稣会的努力在疟疾多发的国家和地区仍获得成效和成功。但在新教国家和地区,却因推广者是天主教会耶稣会士,而一度遭到抵制。克伦威尔染上疟疾后,因拒绝服用“耶稣会树皮”而于1658年命丧黄泉。[30]欧洲的医师们在引进的同时也对金鸡纳疗法进一步改善,以增强疗效,减小副作用,即耳鸣、重听、头昏、恶心、呕吐、头疼、幻影等所谓金鸡纳反应。[12]159英国的塔尔博尔(Talbor, Sir Robert)于1672年出版了一本医学专著《发烧学》(Pyretologia)。书中提倡在打摆子发高烧时服用以金鸡纳树皮为主药的复方合剂,但秘而不宣他的配方。直到塔尔博尔在1681年去世后不久,他的药方才公诸于众,原来是金鸡纳树皮粉、玫瑰叶、水、柠檬汁、欧芹(persil)汁的混合物。[31]506
欧洲医药界和社会受习惯的影响,对金鸡纳的怀疑和轻视只是在缓慢地减弱。17世纪60年代的英国,医学界认为金鸡纳树皮能解热退烧,但不能治愈疟疾。[9]57直到1676年欧洲医药界才改变了一些态度。这年,名医托玛斯·西顿汉姆(Thomas Sydenham)在他新出版的《医学观察》一书中详论了新药金鸡纳,坚定认为它是唯一能治三日疟的药物。至于间日疟,他仍推荐用排泄排汗法治疗。[9]70这一态度比之以前积极多了。西顿汉姆对金鸡纳态度的转变是欧洲医药界态度转变的一个风向标。医药界的态度转变影响到政界顶层。而政界顶层的用药尝试使金鸡纳最终登上大雅之堂。1682年,塔尔博尔用他的复方合剂为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治好了疟疾,被国王赐予“医生”(Physician)名号。一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世买下了这个秘方,救了罹疟的王子一命。心存感激的路易十四赏了塔尔博尔一大笔退休金和2000金路易的奖金。塔尔博尔后来在1680年又治好了患疟的西班牙王太后、摄政(王)玛丽娅·安娜。[31]506由于塔尔博尔为大国君主治疟有“方”,促成了金鸡纳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治疟良药,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种欧洲国家药典包括官方的伦敦药典。[16]1451682年,法王路易十四还资助出版了一本医著,该书当年就被译成了英语在英国出版。其英语书名为《英国药物,或塔尔博尔的惊天秘方,用于治疗疟疾和发烧》。该秘方其实就是用耶稣会药粉与各种饮料混合后服用。[9]81所以,塔尔博尔治疟成功是用金鸡纳抗疟获得广泛认可的关键一步。
到1711年,意大利医生弗朗西斯科·托蒂(Francesco Torti)发表论文,把“疟疾”(malaria)一词正式引入医学文献,确立它作为此病的正式名称。[9]94从此,欧洲各国(英法德意西葡荷俄)对此病的称谓渐渐统一起来,皆为malaria,俄语为малярия。例如,1740年英国作家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访问游览了圣城罗马。他给朋友写信说:“这里有一种可怕的病叫疟疾(mal’aria),它每年夏天来袭扰罗马并斫丧一些人。”[15]35该词从此进入英语词汇库。而此前英语称疟疾一直为ague,意为“寒颤”。
金鸡纳传入欧洲后其称谓更加紊乱,除了前面提到的秘鲁树皮(药粉)、德·鲁果树皮(药粉)之外,还有伯爵夫人树皮(药粉)、塔尔博尔树皮(药粉)、印度树皮(药粉),甚至还有称支那(China)树皮(药粉)的,因为一些人相信该药来自遥远的中国。[9]97当然也有很多人叫它金鸡纳(quinquina, or quina-quina)。这个名称听起来像美洲印第安土著人的名称。因为很久以来,南美的印第安人各部族便称其为基那基那(kinakina),[27]235意思是“万树(皮)之(树)皮”(bark of barks)。[12]23随着时间的推移,“疟疾”的称谓渐趋统一,其克星“金鸡纳”一词亦渐占优势。到18世纪林奈之时,“金鸡纳”作为该树、该树皮、该药的正式名称才确定下来,并得到普遍接受。
进入18世纪后,金鸡纳作为抗疟良药已被欧洲、世界广泛接受了。有的地区有的时候甚至走到极端,出现了金鸡纳崇拜。18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学者鼓吹,只要穿上衬垫有金鸡纳树皮的药背心,也能治疟。英国有关当局也曾介绍和推荐金鸡纳药背心。[32]由此可见人们对金鸡纳的推崇程度。穿药背心实际上是无效的。金鸡纳出名和推广开后,需求量大增,药价飞涨。18世纪80年代欧洲市场的金鸡纳树皮价为1英镑1磅。此时治好一例疟疾病人的用药量比过去减少了一些,要用去2磅;在巩固期的一周中用药量比过去减少较多,只用去1磅。[16]145这应该归功于18世纪时人们已意识到并有意采割奎宁含量高的树种的树皮。但18世纪末1英镑的购买力相当于20世纪末的100英镑。[13]19所以也只有富人和全面小康之家才买得起用得起。
前已论及,大概在17世纪30年代初,金鸡纳树皮传入欧洲作为抗疟药物供病人服用。金鸡纳种子或树苗何时传入欧洲进行栽培尝试则尚在研究探讨中。1668年,在伦敦郊外泰晤士河边建起了一座药用植物园。1680年,约翰·瓦茨(John Watts)被任命为植物园主任。他上任后很快就在植物园建起一大间可加热(类似烧炕)的大暖房,用以栽培热带亚热带植物。1685年8月,约翰·伊夫林爵士(Sir John Evelyn)参观访问了植物园。爵士在1685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植物园的新暖房中生长着“许多珍稀植物……特别是除了许多一年生珍稀植物之外,还栽着长出耶稣会树皮的那种树子,它已治愈过一些疟疾病人”。[15]108这似乎是在美洲以外的旧大陆、在欧洲栽培金鸡纳的最早尝试。但它(们)是由何人、具体在何时、怎样传入的,传入的是种子还是秧苗或二者皆有,已无从查考了。这些金鸡纳树的寿命和后代如何也不得而知。到18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当时的植物园主任菲利普·米勒(Philip Miller)编写并于1731年出版了著名的《园艺家辞典》。但其中没有金鸡纳树或耶稣会树等的记载[15]110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此之前,植物园的金鸡纳树均已死去,所以该辞典才无载。
三、考察和认识金鸡纳树
欧洲人在称呼和服用“秘鲁树皮”一个世纪后,还没有谁见过金鸡纳树。好奇心、求知欲、科研兴趣和经济利益驱动着欧洲人去寻找、见识、考察、调查这一宝贵而重要的药材植物。1735年,法国派出科考队去南美赤道地区测量地球的经线。孔达明(M.D.L.Condamine)等几位科学家是科考队的主力队员,故史称孔达明科考队。全队共13人。植物学家兼医生德·朱塞乌(J.D.Jussieu)也加入其中。他前去的目的就是要考察研究退烧树。[15]112队员们在南美不知所属国度的不知名的山林里一起度过了七年。1737年2月,孔达明到了金鸡纳的故乡,具体在今厄瓜多尔南部边境劳克斯阿(洛哈)城一带,在那里呆了三天。孔达明在这里首次亲眼见到了金鸡纳树,当地土著称为奎奎那树(quinquina)。他写了一篇关于金鸡纳树的描述(考察报告),画下了它的枝、叶、花、子实,寄给了法国科学院。该报告第二年在科学院学报上发表。[15]117孔达明描述了白、黄、红三个品种的金鸡纳树,并得知红的退烧性最强,白的最弱。他还指出金鸡纳成年树其树干有人体粗。[15]117那份报告很快送了一份副本给林奈。林奈依据此报告运用他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分类体系,正式命名它为金鸡纳(Cinchona)树。[9]103这是金鸡纳发展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虽然孔达明的报告有点简略和不很内行,但因为它是欧人首次目睹了生长着的金鸡纳树后写下的描述和报告,又有比较逼真的插图(当时无照相术),一度成为当时植物学药物学上的经典论著。
1744年,孔达明本人返回法国,随身带了一些他找到的退烧树的幼苗,想放到法国植物园的暖房里栽培,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不料在横渡大西洋时遭到大风暴袭击,这些树苗在风暴中丢失了,估计是被狂风巨浪从甲板上刮下海了。[33]1这是有史可考的人类首次向美洲以外的旧大陆移植金鸡纳树的尝试,但可惜受挫。尽管当时还主要出于求知性、研究性、观赏性的目的。
孔达明科考队的德·朱塞乌则在劳克斯阿(洛哈)呆了几年,仔细研究金鸡纳树。他把金鸡纳树区分为红、黄、白、灰四个品种,指明每种树的抗疟药性很有差异。朱塞乌撰写了详细的研究报告,细致论述了金鸡纳树的四个品种,它们的人工栽培问题,焙制(炮制)药物的最佳方法。朱塞乌独特地最早考虑到神奇药材林的保护问题。因为他看到印第安人砍倒树木剥取树皮而感到吃惊。他还教印第安人识别药性最好的金鸡纳树品种,教他们如何制药自用。[9]105朱塞乌的拉丁语报告使人们对金鸡纳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当孔达明科考队1744年返回法国时,朱塞乌却决定继续留在新大陆,想深入考察退烧树的地理分布,并尝试就地人工栽培。他在南美的丛林和安第斯山区一呆就是十七年。除了金鸡纳,他又考察了对于欧洲知识界新奇的其他植物、动物、矿物,还考察研究了各个印第安人部落和文化,成了一个博物学家。朱塞乌积累了大量的科考数据,包括各种手稿、地图、图画、动植物标本、矿物标本等,并小心地锁存在一些木箱里。他长期请了一个印第安人仆人帮忙。1761年,朱塞乌终于决定要回法国了。得知此消息,那个仆人竟偷走了那些木箱潜逃,他以为里面装的是钱和金银珠宝。那一大批珍贵的科考资料从此消失,没有再现过。[15]118朱塞乌被迫留在南美追查他的宝贵资料,一追又是十年却一无所获。当1771年他终于回到巴黎时,他因凝聚着其一生心血的珍贵科考资料被窃而气得已精神失常。[9]107这时他已是67岁的老人了。屈指算来,朱塞乌已在南美度过了36年(1735—1771年)。朱塞乌又活了八年于1779年去世。此事酿成金鸡纳发展史上的一大悲剧,对金鸡纳的发展传播和人工栽培有所迟滞影响。
在朱塞乌的宝贝箱子被窃的1761年,一位西班牙青年医生塞勒斯廷诺·木提斯(Jose Celestino Mutis)在西属新格拉纳达王国首府波哥大(今哥伦比亚首都)给林奈写信,介绍金鸡纳的情况。1764年,他又向林奈寄送从劳克斯阿丛林中找到的金鸡纳树的枝叶标本和自己的有关绘画。1773年,木提斯托人捎给林奈一个包裹,内装他在新格拉纳达发现的一种波哥大金鸡纳树的干枯叶子和花朵。[9]1141763年,木提斯又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写信说道:“陛下的美洲不仅富有金银、宝石和其他宝藏,而且富有价值最大的天然产品,……那里有奎宁(quinine,按,指用金鸡纳树皮制成的药),无价的资产。陛下是它唯一的所有者,是上帝为了人类的福祉而赋予您的。很有必要研究金鸡纳树,以便能以最低的价格向公众出售药性最好的树种的树皮”。[9]114信中他还提醒和担忧,如果砍倒树木剥取树皮的作法继续下去,这一宝贵药材资源将在短期内枯竭。[9]115
多少受到木提斯的影响,1777年,西班牙也向南美派出了科考队,主要考察自然资源,特别是金鸡纳资源。队长为青年植物学家鲁伊兹(Hipolito Ruiz Lopez)。全队有好几个队员,还有法国专家。鲁伊兹等在秘鲁和智利科考调研了十一年,收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大多数是金鸡纳标本。鲁伊兹发明了金鸡纳药浆,将金鸡纳树皮用水浸泡,再用文火反复熬药,滤去渣滓,直到药浆浓度达到半流质,然后盛入用金鸡纳木料制作的木盒里密封以防潮,最后运走出售。[15]125鲁伊兹十二年后自豪地写道:“从那时起,……有4万多磅的药浆用船运回欧洲。其药效颇有口碑,价格也相对低廉……”[15]125鲁伊兹浓缩药浆的发明,类似于用传统方法和工艺制作的中成药,在储藏、运输、销售、服用方面比起原来用树皮熬汤或药粉兑酒都方便了一些,疗效亦有提高价格也有降低。而且,这一创新使产地从输出药材(树皮)到开始输出成药(药浆),充分利用了原来废弃的金鸡纳木材资源,故有一定的价值和贡献。1787年,鲁伊兹等向西班牙新发了一船货,其中有许多植物样品、标本、药物、种子、树苗(living plants)等,笔者认为,其中必然有金鸡纳树苗。可能他想把它栽培在马德里植物园的暖房里供研究和观赏。但很不幸,在横渡大西洋时,一场风暴掀起的巨浪卷走了船上30多个装着秧苗树苗的货箱(containers)。后来在葡萄牙海岸附近船又触礁搁浅,近2/3的船员和乘客遇难,残存的各种秧苗种子(包括金鸡纳的)和标本等也都损失殆尽了。[15]126人们移植金鸡纳,把它引种于欧洲的第二次尝试再次失败。
鲁伊兹等一直到1788年才回到西班牙。尽管遭到多次不幸、危险和损失,仍带回大量的资料手稿画稿等。到1792年,鲁伊兹决定先出版一本专论最重要的金鸡纳树的图鉴《秘鲁的金鸡纳树》(简称Quinología)。[15]127这是继孔达明1738年发表介绍金鸡纳树的简短文章后,西方第一本论述金鸡纳树的著作。鲁伊兹在考察中已感觉到野生金鸡纳树在减少,亦较难找到了,故率先明确呼吁发展种植园人工栽培金鸡纳。[17]4
一直在南美做植物考察和研究的西班牙医生木提斯(J.C.Mutis)终于得到高层的器重。1783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任命木提斯为“新格拉纳达王国(哥伦比亚)植物科考队”的首席专家,拨给他和科考队一大笔资金。[9]121科考队的首要任务便是在山林中搜寻金鸡纳树。科考队在森林边的一个小镇马里奎塔(Mariquita)安营。木提斯在营地建了一个小植物园,尝试着栽培金鸡纳树,这个小植物园兴盛了一段时间。到1787年,木提斯已有了好几个助手、林业工人以及从基多(Quito,今厄瓜多尔首都)来的画家。这个营地和小植物园渐渐发展成“新格拉纳达王国植物研究所”,拥有十来个科学家、十几个画家和一些工人园丁。[9]122-123这是欧洲人首次人工栽培金鸡纳树并有所成功,有一定的意义。不过,其生长地仍在金鸡纳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故其价值有限。1792年和1793年,木提斯出版了两本论述金鸡纳树和药物的小册子。后一本论述了金鸡纳树的可药用的四个品种,比孔达明的三个增添了一个。[9]122-123木提斯于1808年逝世,他的其他众多遗稿手稿著作因缺钱未能出版,留下遗憾。其中包括他的大部头专著《植物志》(Herbarium),书中描写、绘图、分类、考释了两万多种植物。[9]134到1818年,西班牙有关部门又准备出资出版木提斯遗稿中论述金鸡纳的一本专著,派植物学者拉·嘎斯卡(La Gasca)负责整理。但嘎斯卡在加的斯整理时当地发生暴乱,嘎斯卡的家被抢,木提斯的这本手稿被毁。[9]134金鸡纳认识和研究史上类似于朱塞乌的遭遇再次发生,所幸这次损失要小些。
木提斯离开和去世后,卡尔达斯(F.J.de Caldas)接任植物研究所所长。他很早就加盟研究所,也为考察研究金鸡纳树做了许多工作,比如绘制了详细的各种金鸡纳树的地理分布图,注明了它们各自适宜的气候、海拔高度、湿度、日照、降雨等。[9]1271810年,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革命和独立战争在新格拉纳达爆发,卡尔达斯和研究所的大多数同事参加了革命和独立运动。但卡尔达斯后来在西班牙军队的反攻中被捕,1816年10月被处死。[9]1271817年,在玻利瓦尔麾下的革命军的再次反攻下,西班牙当局下令把植物所的全部科学资料撤回西班牙。但西班牙政府已无资金和精力来出版这些科学著作了。
17—19世纪,治疟渐渐有了较好的药物——金鸡纳及相关办法,但对防疟仍束手无策,故这仍是疟疾肆虐和猖獗的时代。于是导致人们对金鸡纳树皮的需求持续增长。到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金鸡纳资源的锐减表示担忧。德国博物学家洪堡(Humboldt)在179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金鸡纳树的砍伐量已超过每年2.5万棵,[13]17这将导致药材资源的萎缩以至枯竭。于是,一些人士开始疾呼在旧大陆大规模地引进种植栽培金鸡纳树,而非在植物园的温室中作观赏性实验性的养种。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首任主任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年)便于18世纪末呼吁英国政府在各英属旧大陆殖民地建立金鸡纳种植园,进行引种、移植、栽培,以保障这种重要药材的供应。[16]147他的规划是,要把邱园建成尽可能大的植物园,办成植物收集、识别、分类、种植的研究中心。为此要向世界各地派遣植物猎手(plant hunters),去寻觅、采集、找到珍稀植物的种子、秧苗等,把它们引种于邱园,再移植到气候适宜的各英属殖民地去。在殖民地选址,建立种植园,以保证英国的利益和满足社会的需求。班克斯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3]23故其建议很有影响。其他西欧国家也有类似的呼声。于是,官商结合公私连手的有规模的采集、移植、引种、栽培金鸡纳树的行动开始了。它不同于以前的科研性考察和旨在温室中作研究性观赏性的养种。从此拉开了金鸡纳发展史上崭新的一幕。
四、觅种移植和种植园栽培
班克斯向世界各地派出了植物猎手,他们各有斩获。其中一个是颇有名气的洛克哈特(D.Lockhart)。他参加了霉运笼罩的1816年的刚果探险队。在这次探险中56名队员就死了21人,大多死于疟疾(因金鸡纳没带够)。这一悲剧刺激了班克斯更强烈地呼吁搜寻金鸡纳种子建立种植园以保障药材供应,也促使更多的人关注支持这一设想。也是在1816年,外科医生乔治·格万(G.Govan)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在印度萨哈兰普尔植物园试种金鸡纳树。后来,受罗伯特·福琼(R.Fortune)在印度建立茶叶种植园成功的鼓舞,植物学家约·福·罗伊尔(J.F.Royle)在其《喜马拉雅山区植物学图解》一书中提出,应运用相似的策略在印度试种金鸡纳树,确保“继中国茶叶之后,能有更重要的植物引种于印度”。[16]148尽管尚未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支持,罗伊尔还是把自己想方设法找到的6株金鸡纳小树苗给了罗伯特·福琼。它们运抵加尔各答时,其中5株还是活的。不幸的是,在难以预测的转运途中,又有两株死去。最后3株虽然种在了大吉岭(Darjeeling)植物园,但最后也夭折了。[16]148这是人们继1744年孔达明、1787年鲁伊兹后,第三次向美洲以外的地区移植金鸡纳树,仍遭到失败。不过,比起上两次还是前进了一点:毕竟在旧大陆栽下去了,只可惜没有存活;其目标也不再是温室养种,而是大田栽培。
正当欧洲国家有关人士担心金鸡纳资源枯竭,准备向旧大陆移植、栽培金鸡纳之际,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绝大部分拉丁美洲地区爆发了反对欧洲人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和战争,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独立国家。这些拉丁美洲新兴国家都逐步走上了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中出产金鸡纳的国家对国内的金鸡纳资源也予以一定的保护甚至加以垄断,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例如,1844年玻利维亚便禁止出口金鸡纳的种子和树苗,因为该国当时15%的税收来自树皮出口。[12]29于是,欧洲的引种行动与它们的保护和垄断政策也有了一定的矛盾和抵牾,致使移植“工程”除了自然风险之外又增添了人为的不确定因素。此外,独立后,这些新兴国家的土生白人、混血人、印第安人中也有人参与了引种移植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由于欧洲商人和美洲土生白人、混血种人教士、商人连手,大量收购金鸡纳树皮,出产金鸡纳的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的山林印第安人形成了一个金鸡纳树皮采割者群体,西班牙语称cascarilleros。他们常常全家结队去林中山上寻找金鸡纳树,找到后或砍倒剥皮,或不砍倒剥皮。约一周后回村,带回一定数量的树皮。[9]144他们把剥下的厚树皮在篝火上烤干,最厚的烤干后再压平。从枝丫上剥下来的薄皮晾干后则卷成管筒,然后打包或装入麻袋。[12]17这种作法一般都导致树子死亡。而新兴美洲国家百废待兴,忙于各种急务,所以只能很简单地应对这一问题。比如,玻利维亚政府就开始限制金鸡纳树皮出口,特别是限制其中最适合提炼萃取奎宁硫酸盐的黄金鸡纳(Cinchonacalisaya)树皮出口。但是这需要大批警力来限制印第安人采药者进入山林滥采。故限采限割出口令收效甚微。
法国也是最早想到并实行人工栽培金鸡纳、为子孙后代储备药材资源的西欧国家之一。1843年,法国再次向南美派出科考队,队长是位伯爵。他们循着孔达明科考队的路线,先在巴西登陆,然后一边考察一边穿越巴西。两年后科考队抵达玻利维亚,然后沿乌鲁班巴河向秘鲁挺进。这时,一位科考队员威德尔(H.A.Weddell)申请离开大队独立考察获准。威德尔花了两年时间考察安第斯山地区。他请了当地向导,还带着骡子驮行李。1847年威德尔到达了秘鲁的库斯科省。从那里他去探察与玻利维亚相连的森林,寻觅著名的黄金鸡纳树。在库斯科威德尔碰到了也来寻觅黄金鸡纳树的法国同胞德隆德勒(M.Delondre)。德隆德勒是首批从事工业化生产奎宁硫酸盐的企业家之一。为了解决药材供应问题,此时他已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建了近代化的药厂,准备就地工业化生产奎宁硫酸盐。但玻利维亚政府为了抑制金鸡纳树皮的消耗量,已实行出售采割树皮特许证的制度,每年只允许剥取一定数量的树皮。于是他俩便决定一起去寻觅树林,也请了向导,牵了骡子。他们跋涉在秘鲁南部和玻利维亚北部的深山老林中,历尽艰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山林中找到了黄金鸡纳树。德隆德勒事后回忆道:“当我们精疲力竭时,忽然传来斧头砍(金鸡纳)树声。这是我们胜利的信号。这一惊喜恢复了我们的力气。很快我们走到了那棵高大壮丽的树子跟前。我是首次见到,它成为我梦想的目标已经很久了。我欣喜若狂,凝视着它那漂亮的银色树皮,绿褐色的硕大叶子,散发着略甜芬芳的花朵,令人想起了丁香花。”[9]150威德尔和德隆德勒完成了考察、调研、采集工作后回到库斯科,受到当地上层的盛情接待。他俩其后到了秘鲁省城阿雷基帕。威德尔从这里的沿海港口搭船回法国,德隆德勒则回到他在智利瓦尔帕莱索的药厂。由于药材供应受限和欧美商人、公司之间的竞争(美国已于1776年独立),德隆德勒的智利奎宁药厂在一年后无奈关张。[9]151
威德尔于1848年回到法国并很快出版了一本(法语)书《金鸡纳的自然史》。这是第一本全面深入研究金鸡纳的学术专著,论述了19个金鸡纳品种,比之木提斯的论著全面丰富深入得多。知识界对金鸡纳的认识和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特别重要的是,威德尔还带回一些黄金鸡纳树的种子。法国人用这些种子在暖房中育出了树苗,并希望移植到当时(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属殖民地去,并特别对北非阿尔及利亚寄以厚望。但法国人未能使其发展成药圃,更未发展成种植园。[34]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种植栽培行动是通过耶稣会士团体和个人进行的,以期发挥个人和宗教团体的积极性,但仍未成功。[35]是故只能限于在温室内试验栽培。法国只好分出一些种子给了英国政府。这样,在巴黎和伦敦的植物园的暖房中,第一批金鸡纳树开始生长。[9]151育种出苗长了一点后,法国又匀出一些给了荷兰政府。[9]151这是金鸡纳树首次在美洲以外的旧大陆长期存活生长,意义非凡。荷兰人待自己植物园暖房中的幼苗稍长大一点后,又将它们的大部分移植到荷属亚洲殖民地、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在那里,那批黄金鸡纳树苗幸运地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繁殖出健康后代。[9]154珍贵神奇的金鸡纳树终于初步冲出美洲,走向世界,散布开来。法国植物学家威德尔和制药家德隆德勒在这次引种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
法国移植引种金鸡纳树的初步成功刺激了荷兰人。荷兰人也很快派出了自己的科考队、植物猎手和冒险家。1853年,荷兰植物学家、曾任荷兰在爪哇的贝腾宗(Buitenzorg)植物园主任的哈斯卡尔(Justus Karl Haskarl)伪装成德国商人,化名为卡洛斯·米勒(Jose Carlos Muller)前往南美。[15]2121854年3月他来到玻利维亚与秘鲁交界的西那镇(Sina)。这一带出产质量优良的黄金鸡纳树。一个叫亨利奎兹(Henriquez)的玻利维亚籍人(可能是混血人)加入了米勒(哈斯卡尔)的科考组。1854年6月,亨利奎兹搞到了400株黄金鸡纳树的小树苗,交给了在桑迪亚(Sandia)的米勒(哈斯卡尔),得到一大笔酬金。[9]174亨利奎兹从此隐居,以免被当地人唾骂或滋扰。米勒(哈斯卡尔)小组历尽千难万险,在林中小径拖运树苗走了150英里(240公里),才到达秘鲁省城阿雷基帕,然后到了秘鲁的卡亚俄港(Callao)。在那里,一艘荷兰商船把他和他的货物行李装船起运,于1854年12月驶达爪哇。[9]175哈斯卡尔(米勒)因弄到金鸡纳树苗有功受到荷兰当局奖励并被任命为金鸡纳种植园的主任。但不幸的是这批树苗在漫漫旅途中几乎都死了(当时蒸汽机轮船尚未普及),只有两株还活着。有幸的是他为了保险也带回了一些其他品种的金鸡纳树种子。哈斯卡尔(米勒)对金鸡纳树种植园的选址又出现失误,一年后剩下的金鸡纳树苗都长势很差。[9]175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帕胡德(Charle Pahud)出于战略利益考虑仍决心要建金鸡纳的人工栽培种植园。1856年,他免去了哈斯卡尔的职务,任命植物学家江胡亨(Franz Junghuhn)接替植物园主任职务。江胡亨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便是把残留在爪哇的半死不活的那些金鸡纳小树移植到更适合的地方——印度西南海岸的马拉巴尔(Malabar)山区。这一花费昂贵技术复杂的移植工程居然成功了。四年后的1860年,这批小树长成了近百万棵健康的能开花结果的树木。[9]175-176但事情还有跌宕。除了数千棵黄金鸡纳树,这近百万棵金鸡纳树都出自哈斯卡尔收购采集到的种子。经荷兰植物学家化学家德·弗里杰(De Vrij)检测化验,这绝大多数的金鸡纳树其树皮中有效成分奎宁的含量少得可怜。[33]2那少量的黄金鸡纳树也长得很差。只有极少数原由威德尔带来的树种及其后裔长得较好,但它们树皮中的奎宁含量也只有玻利维亚产黄金鸡纳树的一半。到1860年,在爪哇的金鸡纳栽培尝试完全失败。[9]176尽管如此,荷兰人在印度总算还有点长得差的质量低的人工栽培的金鸡纳树林在顽强生长着。
法国人和荷兰人引种金鸡纳的有限和局部成功刺激英国人加快了步伐。1858年,英国印度事务处和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达成协定,邱园派出科考队到安第斯山脉的四个地区搜集八种金鸡纳树的种子或秧苗。印度事务处为每个地区支付500英镑(共支付2000英镑)。[16]150于是,时任邱园主任的威廉·胡克(William Hooker)组建了植物猎队。他请马克汉姆(Clements R. Markham)前往南美,订下合同聘请已在南美的斯普鲁斯(Richard Spruce)加盟入队。斯普鲁斯从1849年起便在南美考察收集植物。胡克还给他俩各配一个邱园培养出来的助手,威尔(Weir)给马克汉姆,克劳斯(Cross)给斯普鲁斯。[16]150
马克汉姆科考组于1859年12月离开英国奔赴南美,他们搭船在秘鲁的利马登岸。不久科考组到了秘鲁玻利维亚边境秘鲁一侧的桑迪亚,他们决定在这一带的塔姆博帕塔(Tambopata)山谷寻找采集。在这里,科考组遇到秘鲁退役军官混血人曼努埃尔·马特尔(Manuel Martel)的阻挠。他放出狠话,谁胆敢把金鸡纳种子或树苗偷运出境,他就要把谁抓起来并砍掉其双腿。[33]2科考组不惧威胁,忍着蚊虫蜂蚋的叮咬,击退各种野兽的袭击,在这一带山谷的卡拉瓦亚(Caravaya)森林找到了金鸡纳树林。到1860年5月上旬,他们已收集到四大捆金鸡纳小树苗共500多株,这已足以栽满他们预备的育苗箱了。[15]2325月12日科考组钻出森林启程返回,路上不流血地闯过了一些秘鲁人的阻挠,并绕行弯路以避开马特尔及其追随者的拦截。[33]2科考组用几头驴驮着树苗和行李,在雇请的当地向导的引领下,走了两周多,才到达海边的伊斯莱(Islay)港。但秘鲁刚刚开始执行禁止金鸡纳种子和树苗出口的政令,故他们的苗木被拦下了。经过马克汉姆的奔波和“公关”,才得到放行。[15]234当马氏一行于1860年8月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时,已有近一半树苗死去。马克汉姆力主,不要把剩下的树苗移植皇家植物园邱园,而应继续前航,直奔印度孟买,直接移植到正在印度西南部尼尔吉里丘陵创办的金鸡纳种植园的大田里。马氏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是一个冒险的错误的决定。因为就算为了稳妥也应留下一小部分移植入邱园的暖房里,以备不测。为了争取时间节省路程,他们不走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这条传统航线,而是从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航行到了埃及,登岸水陆联运(时苏伊士运河尚在修建中未通航)再航行到红海印度洋。在新的漫长航程中,种种不顺接踵而至。10月初在穿越埃及和红海时,又有一批幼苗被酷热烤死。[36]4直到1860年10月中旬,这批树苗才经卡利库特上岸陆运到迈索尔(Mysore)附近的英印政府种植园。[15]235在当时的园林技师威廉·麦克伊沃尔(William McIvor)的协助下,马克汉姆等把树苗移植到大田里。但已为时太晚,算来离他们走出森林开始返回已有五个月多点了。到12月,这批好不容易运出来的珍贵树苗全部死亡,一棵不剩。[15]235英国人的这次引种移植栽培金鸡纳的行动完全失败。虫害、气候、海拔高度等都是马克汉姆的树苗在印度全部夭折的原因。[17]5
斯普鲁斯是个自学成材的植物学家,醉心于研究苔藓和欧龙亚草,与邱园胡克主任保持着联系。他喜欢独自工作,希望去收集考察植物。他的理想于1849年6月实现。当时决定派他到南美尤其是安第斯山和亚马孙河地区的森林中去。斯普鲁斯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连续工作,探险考察收集研究,定期向邱园寄送包裹。当时的南美比较混乱缺乏法纪,斯普鲁斯雇用的当地印第安居民多次企图谋财害命于他。所幸他已学会几门当地的土著语言,偷听到并听懂了他们的密谋,故每次都得以逃脱,化险为夷。[16]152斯普鲁斯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抵达预定的采集种子地区,安第斯山麓属于厄瓜多尔的奎托利安(Quitolian)地区,在一个废弃的甘蔗糖厂建立了收集考察站。克劳斯也赶来这里会合,并带来了一些育苗箱(Wardian case)。这是类似盆景的小木箱,上部有玻璃罩子,可透光和保暖。[15]226由于密封,还可以保持水分潮湿,减缓土壤中的养分损失,挡住外来的可能危害植物的病毒、真菌和病菌。它由英国医生兼植物学家沃德(N.B.Ward)于19世纪30年代发明,故又称沃德箱。[13]26-27它们属于便携式微型温室,专用于从海外运送热带亚热带作物秧苗。[36]3此时斯普鲁斯的健康状况已较差。但他仍一直在采集、晾干、压缩、制作植物标本并寄回伦敦。[16]152
斯普鲁斯采集金鸡纳树种子的具体作法比较聪明稳妥。为确保采种权利和工作顺利进行,他先用当地流通的美元400元租下将要考察的一大片区域,很快就发现这一带有大量长势良好的短柔毛(C.pubescens)金鸡纳树。从1860年8月起的三个月中,斯普鲁斯小组爬上树采集了许多成熟的种子,并就地开辟小型苗床进行育苗。9月,他们把约1000株育种幼苗和插枝幼苗用潮湿苔藓裹住根部,有的幼苗栽在克劳斯带来的育苗箱里,把一大批种子和幼苗用牛驮着运出山林来到河边,再用木筏顺流漂航到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Guayaquil)地区。[15]227途中既有遭到自然障碍的惊险,也有碰上土匪的危险。但他们都沉着应对,履险如夷。1860年12月31日,仍活着的600多株幼苗和10万颗种子在瓜亚基尔港装船起航,开往英国,抵达后交给了邱园的胡克主任。[16]153劳克斯随船押运种子和树苗回国。1861年秋天劳克斯返回南美厄瓜多尔,又从斯普鲁斯处运出走私了一大批金鸡纳树种子。[16]154斯普鲁斯则呆在南美继续考察采集研究,到1864年才回国。此时他已半身不遂留下残疾。[33]2又过了21年,1885年,斯普鲁斯的专著《安第斯山脉亚马孙河上游流域的苔(藓)纲植物》出版,书里记录研究了700多种苔藓类植物,经他亲手采集过的就达500多种。[16]154
斯普鲁斯等西方博物学家在南美采集金鸡纳树种子、育苗、运出原产国的移植引种活动,以及类似的其他美洲作物向外传播的人为活动,包括橡胶等,在当时和今天的史学界,对其评价是有分歧的。一些人认为这是偷盗行为,因为在当时,秘鲁的金鸡纳种子和植株是不许出境的;而玻利维亚的地方法规也不允许重要的种子或植株出境;厄瓜多尔也于1861年通过了禁止重要作物种子和植株出境的法规,等等。[29]171笔者以为,这就要看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看问题了。站在南美洲人的立场上,自然会指责欧洲人偷走了他们宝贵的植物资源。站在欧洲人的立场,自然会辩解,这是为了科学事业,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医药的发展。笔者认为,这些活动即便不合当地的法律、当时的法规,但也合情合理。因为金鸡纳的外传和人工栽培不仅欧洲受益,非洲澳洲亚洲和中国也受益;不仅上层富人受益,中层小康之人和下层穷人也受益。金鸡纳树传开了、发展了、增多了、普及了,按照供求规律其药价必然大跌。这样,除了上层富人和中层小康之人,下层穷人也可能用得起了。也就是说,不管西方移植者引种者的动机如何(比如为了赚钱、赢利、个人出名、掌控重要药材资源等),其客观效果都是造福人类了。所以,对欧洲人移植引种金鸡纳等美洲作物的活动,应该认可,无可厚非。
我们在此不妨再多说几句。汉代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随即引进一批西域作物,如葡萄、苜蓿、芝麻、大蒜等;新航路开辟发现美洲后,明清之际中国又引进一大批美洲作物,如玉米、甘薯、马铃薯、烟草等。其中一些也是违反引出国法规的。最著名的例子便为甘薯。例如,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越南),当地首领用一种叫白薯的土产招待他,味道甘美。陈益“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未几伺间遁归”。[37]接着,“万历中,闽人又得之外国”。说的是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了岛国吕宋(今属菲律宾)。“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然恡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38]再下来,“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蔓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39]以后还有,“吴川人林怀兰善医,薄游交州。医其(边)关将有效。因荐医(其)国王之女,病亦良已。一日,赐食熟番薯。林求生食者,怀半截而出,亟辞归中国。……过(边)关,为关将所诘。林以实对,且求私纵焉。”[40]邻国守关之将左右为难,“遂赴水死(自杀)。……林乃归,种遍于粤”。[41]上述中国明清之人引进甘薯之举均违反当地当时法律,均系“偷窃”。中国史学家和农史学家论及上述引进甘薯之事时,无不津津乐道、肯定有加、毫无微词。因为它有利于中国和中国人。郭沫若还曾填词赞颂:“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42]所以,对欧洲人从美洲往外移植、引种、传播美洲作物,包括金鸡纳等,也应予以理解、认可和尊重。
西欧人除了在南美寻觅金鸡纳种子和树苗向旧大陆移植之外,也一度希望在黑非洲能发现类似金鸡纳能抗疟的某种或某些植物。19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在中南非洲多次探险、考察、旅行、传教的英国著名探险家利文斯通(D. Livingstone)便在科考途中努力寻找,并找到了一些以为可替代金鸡纳的野生植物,如夹竹桃科植物。但这些植物像其他几种疑似植物一样,虽有退烧解热的成分,但不含奎宁或其他类似的生物碱,不能杀疟。[43]欧洲人为提取奎宁研究过试验过的其他植物还有冬青等,但都不成功。[44]他们一度还研究和以为,西非黑人有咀嚼当地土产的可拉果的习惯,可拉果(kola or cola)能抗治疟疾,可用之于防疟抗疟。结果一推行就贻害不轻,误死了不少患疟的黑人和白人。[13]311,361于是,欧洲人更专注于在旧大陆移植和人工栽培金鸡纳。
[1] 黄淑美,伍慕义,编.《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数据目录索引(1980—2004)[J].农业考古,2005(3):243-404.
[2] 王思明,等.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
[3] 星川清亲.栽培植物の起原と伝播[M].东京:二宫书店,昭和53年初版,昭和62年改订增补版.
[4] Хинное Дерево[Z]//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57 ,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 Том 46 , С. 188 .
[5] Хинное Дерево[Z]//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78 , третье издание , Том 28, С.288.
[6]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Москва : Науч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00.
[7] 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931-933.
[8] Products of the Empire, Cinchona: A Short History[EB/OL].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rcs /cinchona/html. 2013-10-21,下载打印后p.5.
[9] M.L.Duran-Reynals. The Fever Bark Tree: the pageant of quinine[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46.
[10] 恩·博伊姆勒.药物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56-157.
[11] Charle C.Mann.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M].New York: Knopf, 2011.
[12] Irwin W.Sherman. Magic Bullets to Conquer Malaria, from Quinine to Qinghaosu[M]. Washington: ASM Press, 2011.
[13] Henry Hobhouse. Seeds of Change, six plants that transformed mankind[M]. London: Papermac, 1999.
[14] Arturo Castiglioni. A History of Medicin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7, Vol. 1:164.
[15] Fiammetta Rocco. The Miraculous Fever-Tree, Malaria and the quest for a care that changed the World[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3.
[16] Toby & Will Musgrave. An Empire of Plants, People and plants that changed the World[M]. London: Cassell & Co, 2000.
[17] Weiner Louis. Quinine’s Feverish Tales and Trails[EB/OL].Americas, Sep./Oct. 2003,Vol.55, Issue 5,从数据库下载打印后.
[18]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0-41.
[19] Alfred W.Crosby, Jr..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233-234.
[20]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外科学基础卷[Z].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24-25.
[21] 叶金.人类瘟疫报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48.
[22] 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72.
[23] 段振离.动物行为与新药发现[J].医学文选,1998(1):10;范良智.妙药的发现[J].科学启蒙,1998(4):55.
[24] 梁祖霞.金鸡纳树的发现[J].聪明泉,2006(6):27.
[25] Norman Taylor. Cinchona[Z]//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hicago: William Benton Publisher, 1964,Vol.5.
[26] Products of the Empire, Cinchona: A Short History[EB/OL]. Wikipedia,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rcs /cinchona/html. 2013-10-21,下载打印后,p.1.
[27] 世界大百科事典:第七卷[Z].东京,平凡社:1983.
[28] http://www.cervantesvirtual.com/obra-visor/la-biblioteca-nacional-del-peru-aportes-para-su-historia/html/ff3f0240-82b1-11df-acc7-002185ce6064_2.html#4[EB/OL].
[29] 托比·马斯格雷夫,威尔·马斯格雷夫.改变世界的植物[M].太原:希望出版社,2005.
[30] Otto L. Bettmann. A Pictorial History of Medicine[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Pub Ltd., 1956:283.
[31] 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2] 蒋亦凡,译.奎宁治疟疾的欧西历史[J].上海中医药杂志,1955(8):32-33.
[33] Elliot Charles.Hunting the Fever Bark Tree[J].载Horticulture, Sep./Oct. 1998, Vol.95, Issue 8, 从数据库下载打印后.
[34] 佚名.The Cultivation of the Cinchona[Z].Friend, 1861-09-03,Vol.34, Issue27, p. 212, 美国国会存档期刊回溯数据库,2011-11-22查阅.
[35] 佚名.Peruvian Bark in Algeria[Z].London Lancet, Oct.1851, Vol.2, Issue 4, p. 311, 美国国会存档期刊回溯资料库,2011-11-25查阅.
[36] Honigsbaum Mark.In Search of the Fever Tree[Z].Geographical (Campion Interactive Publishing), Nov.2001, Vol. 73, Issue 11, 从数据库下载打印后.
[37] 宣统《东莞县志》卷十三《物产·薯》[Z].
[38] 明何乔远《闽书》卷一五〇《南产志·番薯》[Z].
[39]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树艺·蓏部》[Z].
[40] 光绪《电白县志》卷三十《纪述六·杂录》[Z].
[41] 光绪《电白县志》卷三十《纪述六·杂录》[Z].
[42] 郭沫若.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N].光明日报,1963-06-25(4).
[43] 佚名.Introduction of the Cinchona into India[Z].American Druggists’ Circular & Chemical Gazette, Sep.1859, Vol.3, Issue 33, p.199, 美国国会存档期刊回溯数据库,2011-11-22查阅.
[44] 佚名.Cinchona Trees on Their Travels[Z].Science and Art, Vol.61, July 1864, Issue 3, pp.368-371,美国国会存档期刊回溯数据库,2011-11-23查阅.
[责任编辑:翟 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5—19世纪的全球农业文明大交流”(13AZD044);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15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全球农业文明大交流”(编号skqy201215,批准号skzd201407);九八五工程三期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民族创新基地”项目。
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农史等。
K03
A
1002-6924(2016)12-061-074
——“零疟疾从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