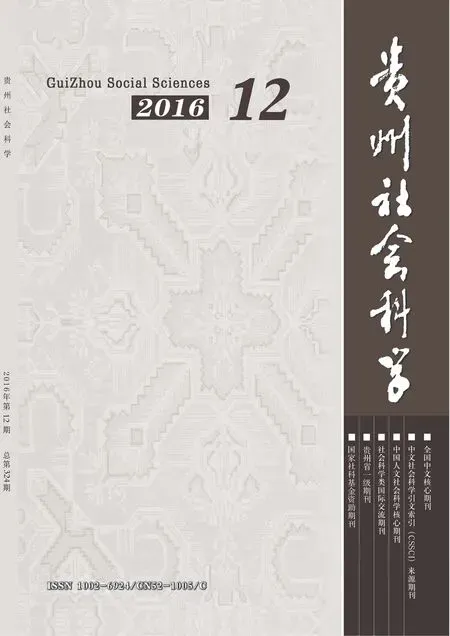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困境——基于独山县基长镇的调研与思考
王莺桦 吴大华
(1.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西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法治化困境
——基于独山县基长镇的调研与思考
王莺桦1吴大华2*
(1.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的城镇化与现代化,法律之治的实现是城镇化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西南民族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形成的民族性因素及治理惯习等多方面原因,乡村治理法治化难度系数较大,也对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现提出了多重挑战。在探寻现代形式理性法治方向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法制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有利于更好推进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的有效实现,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重要保障。
新型城镇化;法治化;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如何在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现代法律之治的有效融合?如何在新型城镇化中推进法律之治的同时,融合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治理优势,从而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村庄公序良俗有效形成?如此等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一、新型城镇化法治之需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数目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城镇数目的增多、人口规模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空间、社会、生态环境的城镇化[1],是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城镇化,而并非“去农村化”[2]的城镇化。这便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以民生、可持续发展和质量为内涵,以追求平等、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为核心目标,以实现区域统筹与协调议题、产业升级与低碳转型、生态文明与集约高效、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为重点内容的过程。[2]事实上,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我国社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也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3]这个最大的结构调整对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南民族地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城镇化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而国外比较成功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在城镇化治理模式的选择上,法律治理是普遍选择。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法律之治的实现是城镇化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但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因其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历史上形成的治理惯习和自我治理传承得到一定程度的沿袭等多方面的原因,新型城镇化这一最大的结构调整更增加了对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难度系数。
二、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实践逻辑及其实践问题:以基长镇为例
有研究表明,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优势明显,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梯度分布。传统意义上的西南民族地区为云贵川三省,其中,四川和云南新型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30%,贵州则与甘肃成为31个省区中新型城镇化总体水平最低的地区。[1]
事实上,西南三省民族地区由于区位、历史、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原因,其传统治理相较于其他地方或具有相对独立性,或自成系统,省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征。因而,其新型城镇化实现难度较其他省份更大,贵州尤甚。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2013年3月贵州省独山县在西南民族地区较早展开新一轮的撤乡并镇,以期通过产业集聚,使当地村民就地就近就业,逐步实现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转变,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2013年,独山县行政区划调整中,撤销原基长镇、水岩乡建制,设置新的基长镇。2015年2月,原独山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正式更名为基长新区。现独山县基长新区(基长镇)位于独山县城东南面,辖8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150个村民小组,12432户55182人,国土面积279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2万亩,荒山荒坡10万余亩。主体民族包括布依族、水族、苗族、汉族等,其中汉族占大约22%,布依族占约37%,水族占25%,苗族占7%,其他占9%。*数据来源:基长镇政府2016年8月提供的基长新区(基长镇)简介。可以看出,基长镇为农业型乡镇,距离县城较近,区位优势明显,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并以少数民族杂居为主的乡镇。同时,基长镇地势平缓,土地肥沃,是贵州少有的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之一。
2015年11月15日-20日,笔者一行4人到基长镇进行了为期5天的调研,以期对其新型城镇化中的法治之需对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进行深入探讨。
(一)国家权利如何有效行使
访谈中,提到基长镇发展基金的时候,基长镇党委书记表示:“乡镇压力也大。在部门是责任大,在乡镇是压力大。乡镇的压力大就是管的事务太多太杂,部门相对单一。”在探讨乡镇撤并放权及新型城镇化的压力时,书记说:“(上面放权)放得挺多的。比如文化部门这一块,对广电的监控还是没有执法权,像我们维护中心两个人。要省人民政府的法制办发出来的执法证才是规范的,才有资格,要不然你去执法就是违法。”
访谈中还发现,民族地区乡镇工作人员必须懂得当地民族语言,懂得当地风俗习惯,否则工作很难开展。
社区X主任:现在到我们乡下去,他们讲的话你们听不懂的,他们讲的是布依话。
书记:乡镇工作……关键是你要懂群众语言,不同的人差异很大。如果你没有群众语言,你用机关的作风是做不下去的。
这一实践治理状态显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工作需要得到更多法律上的保障与支持。同时,如何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如何实施具体工作,如何监管国家权力在西南民族地区的有效行使等问题,成为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挑战之一。
(二)经济发展压力下村民行为选择
1.经济发展上的务实
作为西南民族地区山区的典型样态,基长镇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经济发展上仍以农业为主。作为农业示范镇的基长镇各村所做产业推广,多为农业产业项目。农业产业项目的推行便涉及到所种农产品选择,如引进大型农业生产企业,则涉及大规模土地流转等问题。但大多村民更愿意外出务工,诚如S支书所言,“这几百块钱等你,等你现在出去这些物价又高,没人愿意做(农业产业项目)。”同时,基于就近就业的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外出务工与在家做农业产业项目的收入差,两相比较村民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外出务工赚钱后回来在镇上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买宅基地建房,有一定稳定收入后,回归正常生活。这一过程中,偏远山村更多村民迁出,小城镇得到迅速成长。这便是村民务实选择的实践逻辑。这一务实选择也成为小城镇持续发展的根源所在。
2.“敢和干部对着干”的实践逻辑
派出所Y所长:在农村就是这样,你敢和干部对着干,别人就佩服你,人家都会说这个人惹不得。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在寨子里的威信。
不得不说,Y所长指出了一个权威失落后,正式权威受到挑战、村庄自组织能力不足、村民有一定权利意识后,非常规性寻求权利实现出口、村庄自治实现难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阳地3·12”案(见后文案例分析部分)原初便与这一“敢和干部对着干”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3. 家族发展、民族文化传承的实践逻辑
在阳地布依族文化村,可以看到保留完好,且翻修一新的廖氏祠堂,祠堂出来不远处即是家族知名人士捐修的亭台。来自外省的人大T主席对基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发展潜力颇为肯定。他说:“基长是一个非常有空间有潜力的地方。这边有经商的传统,还有民族艺术种种文化,是非常有优势的。这边的群众很讲道理,在经济发展这块很有空间。相对周边来说比较突出。”
在多个少数民族杂居的背景下,当地村民不少会几种少数民族语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族传统、民族文化得以很好保留,有利于促进乡村社区自组织,有利于提高农村社区自我治理能力,有利于团结力量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各种利益协调难度,以及因此而引发各类纠纷,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风险。这便提出了在加强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同时,如何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法治当如何保障自治等问题。
(三)现代化冲击下的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
郑永流对国家法、自然法、民间法有效性及其有效运行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权威的失落是影响当代中国各种法不被实际遵从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但权威为何失落?其认为,权威在中国的失落,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正在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4]就此,亨廷顿亦认为,落后国家不稳定原因不在于落后,而在于现代化。[5]
现代化与城镇化持续推进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传统权威受到极大的冲击与瓦解,但在部分偏远乡村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法持续推进并试图重构权威,但困境重重。在纠纷与社会稳定上主要体现为:
1. 大量青壮年人口外出务工背景下,纠纷集中化,政府维稳压力集中化。就政府管理层面而言,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带来了大量老人、孩子留守现象,也使得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呈现出时间上的集中化特征。春节期间大量青壮年返家,带回来务工期间收入的同时,也带回来诸多情绪。有了钱的村民春节回家期间相约赌博、相约喝酒,一较高下的情绪下,一些平时积累的小矛盾集中爆发,由此也带来了乡村纠纷与当地社会稳定压力的集中化。
司法所C所长:每年那些打工的年轻人过年回来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回来,父母就会有点冲,再加上情绪激动,一喝点酒就容易出问题。
派出所Y所长:现在的老百姓都在外面打工,留在家的都是老弱病残。我们的维稳压力基本上是在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听到家里有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去闹事。
面对这一纠纷与社会稳定压力集中化的压力,基层政府除加强防备,及时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之外,也较难采取有效措施。
2. 多民族杂居场域下的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基于基长镇多民族杂居的现实,考虑当地的民族、宗族、家族治理传统及文化传承等多重影响因素,其乡村纠纷与社会稳定也难免带有民族性、地方性特点。这一点在当地发生的“阳地3·12案”中即有所体现(后文作为案例将进行深入分析)。除此而外,诸多日常纠纷也往往或多或少掺杂了民族性、地方性因素。
比如访谈中X主任说到偷牛盗马现象在水岩村和江寨村比较严重。基长镇水岩片区紧邻三都水族自治县,主体民族为水族、布依族。三都水族过端节期间一般会杀牛,一些村民或因养牛不足,或因经济困难便会产生偷盗行为。
3. 纠纷解决方式上,寨老等民间力量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但越靠近县城,寨老可能发挥的作用越小。因为乡镇撤并,距离县城较远的水岩乡合并进入基长镇。水岩片区公共基础设施相对较差,除外出务工,村民对外接触较少。一方面其治理传统相对保留较好,社会自组织能力较强,通过寨老等民间权威力量的发挥,邻里纠纷能很好得到及时解决。因而,X主任说,“我们这里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打架斗殴的事件很少。”另一方面,传统治理规则一定程度得到保留。
X主任:(这里有村规民约,也有)家规、族规,过后演变成一个祠堂,……祠堂不存在以后呢,就形成一个自然寨,就立成一个条约,拿石头刻成一个碑,每个寨都不一样,其他地方就用书写的格式。
镇政法L书记为原水岩乡的派出所长,很了解水岩片区情况,对水岩片区寨老力量的积极作用也很认同,认为在乡村和社区纠纷解决与社会稳定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因而当地政府在进行诸多纠纷调解时,也会邀请寨老参加。
L书记:(乡镇和村庄)撤并之后纠纷少了,老百姓有一种心理,我拿水岩举例,以前是一个乡,以前6个村合成2个村,以前的时候纠纷也比较多,现在合并以后,那边的纠纷少了,现在有小的纠纷政府也远,难跑,包括寨老和家属大家在一起讲好就行。
问:现在还有寨老?
L书记:有的。就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他是一个正能量。包括我们调解的时候也要把一些人列入进去。我们下去的时候还要经常和他们接触叫他们帮忙处理纠纷。他们处理主要是用情感来处理。因为他是双方都能想相信他。比如在处理邻里纠纷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讲好就行了,讲好以后在一起吃个饭喝点酒就好了。
但一直在基长镇工作的司法所C所长认为,村里纠纷找寨老的比较少。同时,寨老不是村里调解委员会的成员,也不便于管理。
问: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案子,村里面协调不下来,然后去找寨老出面解决。
C所长:找寨老的少。一个是寨老年纪大了,一个是有热心调解的。像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热心调解的老人家,寨子里和周边有什么事情他就会去调解,但是他不是寨子调解委员会的。
事实上,这也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现代化冲击下,如何协调发挥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的作用、民间权威如何参与纠纷调处等问题。
4. 村支两委、调解委员会等的调解往往法律支撑不足,司法所、派出所、派出法庭等正式权威作用发挥得到极大提高,但人少事多,法律服务持续跟进难。村支两委、村调解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以当地政治经济发展精英为主,他们了解当地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历史沿袭等,但并未经过专门的法律培训,在纠纷调处中以当地传统方式,更多还是情理方面的疏导,或借助国家权力进行压制。但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当地村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增强,村干部的调解受到极大的挑战。
C所长:我们经过接触发现,村里面的干部调解,不是他们能力不行,而是他们缺乏一些法律知识,你知道法律了你才知道怎样去做两边当事人的工作,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涉及村里面的人,偶尔和当事人是很熟悉的朋友或亲戚,这样要想调解成功的话,调解人必须公正,不能偏,如果有偏的话要想调解成功就比较难。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们的观点也对,但是和当事人不知道怎么讲。
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普及,乡村纠纷最终进入司法所、综治办、派出所、派出法庭的比例极大提高。2015年1月至11月,镇政法委大致统计的纠纷量为270余件,但大多在村里就化解了;司法所调解的纠纷量有登记结案的每年最少为30多起,多时达70余件;派出法庭M庭长个人案件量2015年截至11月达到115件。就此,乡镇主要的法律工作者普遍认为,村民法律意识增强,纠纷量上升。
问:你工作应该有20年了?你觉得农村的纠纷发展有没有一种趋向性的特点?它是往哪个方面发展?
C所长:对,20年了。农民的法律意识是觉得比以前好,但是纠纷量绝对是上升的。因为我2000年开始转司法,我(所)在乡镇上基本没有什么纠纷,以前很少看到哪家叫调解纠纷,现在纠纷太多。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是越来越高,但是法律水平维持在比以前高一点点的水平。
在纠纷的处理中,正式权威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同,其作用发挥得到极大的提高。
C所长:每个纠纷两边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对,我们都是分开给他们讲。我们镇里面稍微有点大的纠纷,只要我们法庭、派出所、司法三家在的话基本上都能调解成功。
但实践中,基长5.4万人的乡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为2人,派出所民警为18人(其中包括交通警察2人),派出法庭工作人员为2人(该派出法庭服务的乡镇除基长镇外,还包括玉水镇),开庭的时候,除简易程序案件外,开庭还需从其他派出法庭借人才能完成。
由于专门法律工作者不足,乡村其他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知识缺乏,村支两委未接受专门法律知识培训。因而,镇政法L书记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分管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访维稳。就是哪里急抓哪里。”人少事多,法律服务跟进难。
三、案例分析
2014年3月12日,基长镇阳地村阳地组、打浪组两个村民小组之间因为修筑水坝发生纠纷,由于双方不能正确进行处理,引发了四、五百名村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阳地组村民400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持农具、铁棒、木棒,佩戴白布条,对打浪组的村民、房屋实施打砸和伤害,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20余间房屋受损,社会影响恶劣,涉案的12名被告人分别以故意伤害罪和聚众斗殴罪被提起公诉,接受公开开庭审判。[6]
基于调研所需,笔者进一步了解了案件具体情况。
阳地村位于独山县基长镇,为布依族民族文化村,全村900余户,4000多人。村中阳地组(也称阳地寨)为廖姓,打浪组为陆姓。黑石头河流经打浪组和阳地组,打浪组在河的上游,阳地组在河的下游。上世纪50年代,为用水便利,阳地组在寨门口筑了水坝,控制了用水。打浪组因此与阳地组因用水问题常起争端,即在黑石头河上游筑坝。阳地组认为打浪组搞坝中坝,破坏了阳地组风水,要炸毁打浪组筑起的水坝。争端就此而起。
工作人员A回忆:(2014年)3月9号就开始有这个苗头的。那天早上七点过就接到镇里面的电话说是有事情。那天阳地的已经去打浪修水库的那里并且双方已经发生了冲突,有两个人已经受伤了,……9号镇里面就成立了工作组,我们两边都去做工作。这几天的协调会双方都参加的。县里面的说对于水坝该不该起由县里面水电部门现场看了再说,请两边先冷静下来,等待政府来处理。(虽然政府)都已经说了,但是阳地的是个大寨子,并且阳地在那一带人多势众,所以他们觉得那个水坝一定要炸。阳地的有点欺人,打浪的人说水多的时候他们就堵水我们被淹,水少的时候他们就放水我们没有水用,水过我们这里我们想用都被你掌控。所以打浪想修水库。阳地的就说你打浪的在我上游修坝,想搞一个坝中坝,这是在坏我的风水。他们就不同意搞水坝,政府协调也不听,就说政府偏心打浪,……11号他们在外打工的400左右人就回来了。在打工的回来之前,每一家都同意出钱买黄色的安全帽,买了一些木棒。所以一到就强行冲打浪,就出现了12号早上的3·12事件。
访谈人员L与村民甲和村民乙的对话:
L:我们今天去看了那个阳地新村,没有好多人住噻?
村民甲:那个(阳地新村)是政府修在阳地村的。阳地(组)的人有点霸道,政府的也有点烦了。那次打了一次群架,别人不敢骂他们。
L:他们那里修的房子好像没有人买呢?
村民乙:有人去那里买房子的时候,去那条河里洗衣服、吃水都不给。
村民甲:他们不给(买)。
L:他们那个寨子有寨老没有呢?
村民乙:听人家讲,他们那个寨子打群架了之后,如果你娘家在那边有事情都不准去看,如果你是那个寨子的人,打群架你不去就会遭排挤。之前有人去那里买房子嘛,去那儿吃水、洗衣服都不给,所以那里的房子卖不(出)去嘛。
但对于案件宗族势力的认识,司法所C所长有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对阳地进行民族文化村打造,大量资源投入后,阳地村民内心膨胀,加之村民传统上相互制约的一些习俗,部分村民过于强势,部分村民被动参与等,多种原因导致了阳地3·12案的发生。
C所长:实际像阳地来讲上升到宗族势力的这种概念太高了。因为阳地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打造他们那里的民族文化村,给他们投入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就给他们那里的人形成一种没有阳地基长镇就发展不下去的想法。就是给得多了就有点膨胀了。他们寨子提出过规矩,寨子上有什么事情你不来,到时你家有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帮忙。实际很多人都知道是不对,但是就是迫于寨子里不成文的内部规定,所以你讲上升到宗族,我觉得高了。
由此可见,出现阳地3·12案的关键性因素还包括如下方面,一是由于县里考虑到阳地寨民族文化保护较好,决定以此为基础打造阳地布依族民族文化村,以推动基长小城镇建设。其认为镇里发展离不开阳地,心理优势明显。二是阳地组廖家历史以来有不少大人物,当下也有许多人在州县上班,且人丁兴旺,有较强优越感。三是阳地组廖家宗族祠堂仍在,族内凝聚力较强,寨内50多岁的老人仍具有较强号召力。四是在镇政府主持的多次协调会上,其认为政府偏心打浪组。五是作为大族,族内认为其权威受到挑衅,面子上过不去。六是族内因为多种原因形成的熟人社会的各种牵制,大量村民被裹挟其中。在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后,阳地寨老组长与组内几位有权威的老人遂决定召集在外打工的寨里人回家,争取共同的利益。
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场法治与关系的较量,是一场多方利益博弈,也是一次传统地方治理模式与现代法治要求的正面激烈的冲突,同时这也是一次掺杂了民族因素、家族因素的地方治理中的大事件。所幸事件得到及时处理,事态得到及时控制,最终经由法院通过公开宣判等方式对当地村民进行了深度法治教育。但这也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转型期民族地区乡村如何实现秩序的稳定、如何实现法治化治理、现代法治实践如何尊重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
四、结论
韦伯将法律制度分为四类,一是形式理性的,二是实质理性的,三是实质非理性的,四是形式非理性的。在对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法的讨论基础上,韦伯认为中国法是实质非理性的。他指出,在中国,裁判的非理性,是家产制的结果。[7]
当下新型城镇化的法治之需,是现代法治之需。即便西方现代法治进入中国,在法的移植过程中,根据中国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大调整,但其形式理性的本质并未改变。即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家产制很大程度上受到瓦解,但实践中形式理性的现代法治不能否定中国传统法文化实质公平的需求。
事实上,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西南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封闭,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大潮的冲击没有那么猛烈,其治理传统以及传统法治文化得以一定程度的保留。虽然由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传统,当地乡村干部法治知识储备及法治实践能力的不足,以及往往生长于当地的实际等多方面的原因,基层政府依法治理难免受到传统法治文化的影响甚或挑战,乡村纠纷解决与社会稳定的实现难免会受到民族、家族及其治理传统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否定依法治理在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
如何在探寻现代形式理性法治方向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留传统法治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从而更好推进形式法治与实质公平的有效实现仍是当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实现的重要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 王新越,秦素贞,吴宁宁.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测度及其区域差异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4):71-77.
[2] 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J],城市规划学刊,2013(2):22-28.
[3] 李克强.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EB/OL].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10/13092718_0.shtml.
[4] 郑永流.法的有效性与有效的法[C]//转型中国的实践法律观——法社会学论文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85-123.
[5]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42.
[6] 独山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基长镇阳地村“3·12”群体性事件[EB/OL].http://sjj.dushan.gov.cn/Item/43226.aspx.
[7] (德)马克思·韦伯.法律社会学非正当性的支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8-255
[责任编辑:李 桃]
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西部与边疆课题“撤乡并镇背景下西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法治化问题研究”(15XJA820003)。
王莺桦,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院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社会管理法治建设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法社会学、民族法学、经济法学;吴大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民族法学(法律人类学)、犯罪学、循环经济。
O920.0
A
1002-6924(2016)12-109-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