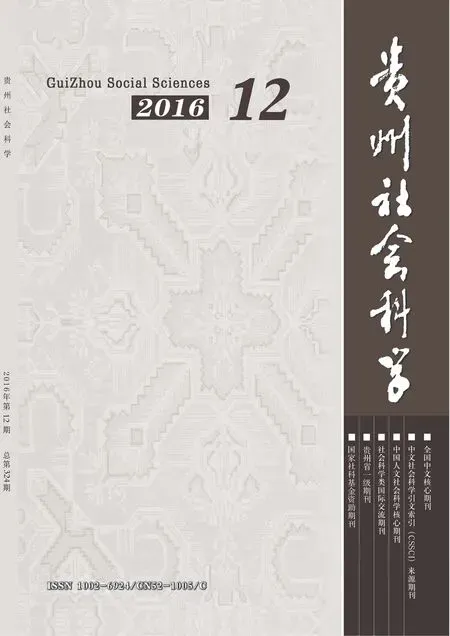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及养老策略
李 俏 陈 健 蔡永民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及养老策略
李 俏 陈 健 蔡永民*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试图呈现和解释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及其与农业养老之间的内在关系。社会流动、代际分工和可持续生计三重动因作用下的“路径依赖”形塑了“老人农业”的现实。但在本质上,“老人农业”并非单一的农业生产问题,而是同时牵涉到农业与养老两个异质性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老人农业”的一体两面,同时也决定了“老人农业”问题的基本性质。由于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村养老保障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与养老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并没有形成制度上的合力,从而导致老人农业与农业养老之间存在现实矛盾。在此背景下的农村养老策略应是力促农业与养老相结合,创新农业养老的实践形式。
老人农业;农村养老;农业养老;代际关系;农业社会化服务
一、问题的提出
“老人农业”是21世纪中国农业生产场景中的一道独特景观。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尚在从事职业性劳动的农村老人比例高达54.6%,不愿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超过六成,出现了“被迫留守”的状况。[1]如此普遍的“老人农业”现象日渐受到社会各届的关注,并在学界引发了争论。许多学者认为,“老人农业”现象已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难题,这一问题的出现将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不利影响,[2][3]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影响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并对农户经营体制、农村劳动力开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提出全面挑战。[4]二是构成了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障碍,[5]导致土地粗放,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6]与此观点相反,一些研究发现,由于生产决策趋同和农业机械“外包”服务的普及,现阶段“老人农业”不仅没有对中国的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7]而且是有效率的。由于中老年农民群体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很低,他们种田基本不计算自己劳动成本,从而具有任何资本下乡进行规模经营都不可比拟的优势。[8]已有研究观点为深入解读“老人农业”现象提供了有益思路,但尚存在可挖掘的空间。一是过往研究多将关注的重心放在“老人农业”的影响上,而缺乏对“老人农业”生成机制的系统分析;二是学界对于此问题的分析还多处在现象描述阶段,对“老人农业”问题的性质认识不足。“老人农业”并非单纯的农业问题,它与养老问题联系在一起,还涉及到农民、农村问题;三是针对“老人农业”与农业养老之间的矛盾,已有研究鲜有涉及。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通过对“老人农业”性质的深层解读,分析“老人农业”与农业养老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老人农业”的生成逻辑及其性质
(一)路径依赖:“老人农业”生成的一般逻辑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老人的晚年境遇深受其前半生生活经历的影响,如健康风险、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收入水平、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等。[9]结合实地调研发现,“老人农业”的生成实际上也是生活惯性的结果,许多农村老人表示其晚年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完全是对一种劳动习惯的坚守,证明自己即使年龄大了也还是有用的,“保持少量劳动是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土地不能闲,更不能丢,好地种起来容易”,“不种地还能干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俨然成为一种农民自然而然的本能,[10]这种基于过往经验的劳动形式可称之为“路径依赖。尽管这种路径依赖可能是迫于现实的无奈,“老人农业”却在社会流动、代际分工、可持续生计的情境中不断地被加以重塑和强化,从而使从一种生活方式转移到另一种生活方式上变得越来越困难,放弃耕作已变得极不现实。下文将从社会、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对“老人农业”生成的惯性因素进行细化分析。
1.社会流动是路径依赖的结构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与工商业经济收入的差异,以及农村与城市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置、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距日趋明显,为了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发展空间,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进入城市务工或创业。而农村中老年劳动力由于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不佳、文化程度较低且缺乏社会经验和必要的技能,就业竞争力不强,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被挤出的弱势地位。另外,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多,伴随农村年轻劳动力的源源流入,必然会有部分老年劳动力从城市就业市场中被淘汰出来,或未能成功融入城市而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会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农业收入却是一份相对稳定且兼具保障功能的收入,会重新在农民晚年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流动出去的多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而农村老年劳动力很少会放弃农业生产而随子女迁入城市,即便是迁入也多是暂时性的帮子女照看孩子或经商,对于他们而言,留村经营自己的土地是最踏实自在的。
2.代际分工是路径依赖的内部动因。当前在各地农村普遍盛行的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11]即通过子代进城务工经商和父代留村务农来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考虑到全家迁移到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放弃土地耕种的机会成本,绝大多数家庭都会选择由父代留守从事农业生产,以降低生活成本。在这一模式中,务工经商收入和留村务农两项收入都必不可少,前者收入较多,对于子代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建房、迁移、投资等意义重大,而后者虽然收入较少,却必不可少,发挥着自给自足、维持日常用度和贴补家用的功能。随着买房、教育、婚嫁等消费支出的增加,农村老人多对子代所面临的生活压力表现出体谅的态度,并力图在有能力的范围内坚持经济独立和养老自主,强调“趁自己能动就多干点”,不愿意拖累子女,更不想增加子女的生活负担。[12]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既能实现就业,又能确保双重收入,保持较少的生活支出,并使老人从中获取尊严和满足,从长远角度看也是农村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13]
3.可持续生计是路径依赖的个人动因。“老人农业”一直被视为“被迫留守”的结果,但事实上,“老人农业”是诸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并非完全是被迫的,也有自愿的成分。其中,可持续生计便是农村老人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个人动因。在这里可持续生计不仅指参与农业生产获取经济收入上,还包括获取精神满足与意义诉求上。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完善,在许多农村地区,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购买已变得极为便利,甚至有些基层农资供销商会直接将农用生产资料送到家里或田间地头,费用可以延迟到收获季节补交。另外,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在小麦、玉米种植等领域,除了灌溉、植保等环节需要人力外,播种、翻地、收割等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从事农业生产已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和太多的技术,种田变得简单轻松,劳动强度也大为降低,农忙的时候也就几天就可以把活干完。尽管种地得来的收入不多,却可以使得老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保持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自由度,并从中获取生活的意义。相关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老年人是否参加农业劳动的影响不显著而年龄和健康是农村老人参与农业劳动最明显的决定因素。[14]由此可见,土地对于农村老人具有多重含义,既可维持生计、贴补家用,还可以平衡家庭内部资源,维护老人的权威和尊严,在精神上成为娱乐休闲的重要方式。但实际由于农村老人对于土地的特殊情感,农业劳作实际上已经成为其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一种调剂、一种寄托。
(二)农业出路与养老情理:“老人农业”的一体两面
“老人农业”并非中国独有,在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也都一定程度地存在,但由于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撑,“老人农业”并未对社会发展造成太大影响,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反观“老人农业”在中国,三重动因作用下的“路径依赖”形塑了“老人农业”的现实,不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加突出了中国“老人农业”的二重性,即“老人农业”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遭遇的由于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短缺而引发的农业生产问题以及附带产生的养老问题。它在本质上并非单一的农业生产问题,而是同时牵涉到农业与养老两个异质性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老人农业”的一体两面,同时也决定了“老人农业”问题的基本性质。
1.农业走势:“老人农业”的显性问题。由于留村务农的老人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多靠传统经验耕作,现代农业生产知识缺乏,有的因为身体原因甚至无力经营,导致农田季节性抛荒、耕地复种指数下降、农地粗放经营、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应用不足等弊端突显,“老人农业”的隐忧倍受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关注,[15]也引发了社会各届对于“明天谁来种地”等问题的讨论。[16]面对务农劳动力老龄化的挑战,未来农业的基本走向如何?怎样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现实而又迫切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农业、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这是“老人农业”的显性问题,直接涉及农业生产的稳定,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养老情理:“老人农业”的隐性问题。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老人农业”带来的显性经济影响时,另一个隐性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农村养老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在其他出现“老人农业”的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但在社会保障尚不健全的中国却表现得极为突出。伴随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土离乡,造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农村社区变成了“无主体熟人社会”。[17]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进一步破坏了家庭养老的道德环境,传统养儿防老方式堪忧。另外,农村老人没有退休金,一般只能靠土地维持生计,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由此可见,农业发展只是“老人农业”冰山之一角,而其中所隐含的农村养老需求与养老问题则是需要加以重视和解决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拷问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何能让农村老人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能从农业耕作中获得相应的补偿性收入,消除相对剥夺感,并使后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中找到归属、看到希望、解除晚年的后顾之忧,这不仅是涉及到农民情感认同的文化问题,更是融情于理的社会问题。
三、老人农业与农业养老的现实矛盾
(一)生产成本上涨与收益分配的短期性
结合实地调研资料发现,现实中农村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动因可分为三类:基本生计、日常消费和养老筹划。基本生计主要是为满足口粮需求,一般情况下每个老人每年500斤粮食就足够了,因此,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农村老人的这一需求都能得到保障。日常消费主要包括油盐酱醋等副食开支、娱乐休闲开支和人情交往开支。养老筹划则是从事农业生产动因中最为长远的,主要是在满足基本生计和维持日常消费的基础上,为自己的晚年生活积累和储蓄资金,以备疾病和失能时动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农村老的硬道理,即便目前子女孝顺、生活无忧,农村老人多半还会在心里盘算如何趁自己能动攒点以备不时之需,因为久病床前无孝子,谁知道将来自己不能动或有病的那一天子女是否还能始终孝顺如一。但想法归想法,随着生产成本的上涨,农业生产收益并不高,导致依靠农业养老只能是部分农村老人的理想,而现实中囿于土地经营面积的狭小,多数老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还主要停留在维持生计和满足日常生活消费层面,远没有达到为晚年积蓄资金的效果。收益分配的短期性使得老人农业只能成为农村老人养老图景中的权宜之计。
(二)劳动的阶段性与养老的接续问题
根据国际上对于老年人的一般定义,将 60岁视作老年的开始。若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将老人的年龄阶段划分为60-69岁、70-79岁和80岁及以上三个时期,便可发现,年龄在60-69岁的农村老人一般还没有完全退出农业劳动领域,自我养老和土地养老是其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而对于年龄在70及以上的农村老人而言,由于身体的原因,参与农业劳动的比重在下降,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是最为主要的养老方式。相关研究也证实,随着年龄增大,老人对于家庭和政府社会保障的需求度上升。[18]事实上,只要有土地,一个身体尚好的老年人多少都会种点地、养点猪、养点鸡,加上每月的养老金,养老问题不大。然而,现行的农业养老方式只能够解决那些年纪较轻、尚有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而年龄较大的失能老年人则会因为无法从事农业耕作而失去这重依靠。由此可见,老人的生命周期决定了劳动的阶段性,从事农业生产是有时限的,8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基本上还是在依靠子女贴补以及新农保、农业补贴的钱养老。因此,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在打工潮对于家庭养老构成巨大冲击的现实背景下,失能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土地流转虽然能使失能农村老人每年获得少许收入,但并不足以解决其生存和养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现行土地政策在制度改革上还存在较大的空间。
(三)农业生产与晚年福利的断裂关系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及规定在农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2009年开始实施的“新农保”和其他社会救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老人的养老压力,但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及社会保障水平普遍较低,[19]且在筹资方式、管理机构设置及与城市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20]受缴费能力的限制,农村老人的基本养老保险等级尚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21]“新农保”规定,农村老人从60岁起,每月可领取55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但前提是其子女必须参保,保费分100-800元多个档次,多缴多得,缴费满15年后,可享受养老金。但目前此种缴费方式仍主要可调个人积累,收益也较为有限,完全不能与城市工作同日而语。农业与工业虽然同属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不同行业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却千差万别。工人年轻时从事工业生产可以计算工龄,晚年退休后即可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对于从事一辈子农业生产的老人而言,农龄很长却不具任何经济含义,并不能如工龄一般换来实际的福利待遇。在这一点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村是不对等的,导致农业生产与晚年福利间呈现断裂状态。对此,国家应在调整城乡社会福利待遇、制订社保改革政策时考虑到农村老人的养老境遇与实际困难,适当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和福利水平。
(四)老人农业的自主性与农业养老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历史背景下,老人农业是应对家庭养老弱化、社会养老无力的特有方式,也是化解农村老人自身养老困境的一条现实出路和一种理性选择。因而,老人农业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借此可以维持老人的经济独立、生活自由和人格尊严。但相比之下,农业养老的稳定性不高,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人年龄、身体状况、家庭状况、土地流转等方面的变化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二是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又势必会影响到农业的投入与收益。近年来,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生产资料成本不断增加,而农产品价格却涨幅不大,农业收益本来就较低,如果再遇到旱涝灾害或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就必然会面临损失。应该说,农村老人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是有明确预期的,但各种风险的存在共同指向了农业养老的不确定性。
四、老人农业下农村养老的自我调节
相关研究显示,目前中国农民的养老体系主要由劳动收入、养老金、社会救助、家庭成员供养和财产性收入等五个部分组成。[22]但此分类标准仍主要是从经济供养的角度来划分,而实际上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目前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在经济供养层面问题不大,而在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方面的难处较多。如果需求层次再降低一些,那么生活照料则是多数农村老人晚年养老最为需要的方面。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农村老人对于养老资源的调配无不出于这样的考虑:在身体条件尚好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农业生产、储蓄、打零工等手段为自己积累养老资金,以备不时之需,而到了身体最为虚弱的阶段才开始调动能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的养老资源。这种分阶段的养老选择与方式,只为尽可能地降低子女的养老成本,同时提高养老资源的利用率和养老的效果。因此,针对当前农村养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农村老人实际上是最有感知力的,而且也是认识得最为清楚的,他们往往根据其自身的年龄、健康、劳动能力、经济来源等情况而对其所拥有的养老资源进行调动与分配,达到降低养老风险和实现养老资源利用最大化的目的。这种“自我调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横向养老资源的调配
根据实地调研发现,农民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按性质划分主要包括:家庭养老资源、潜在的社区养老资源(如邻里互助、村集体提供的各项补贴或救助等)、政府提供的公益性养老资源、市场化养老资源(购买商业保险或养老服务等)。若按收入来源则可划分为:农业生产收入、打零工收入、从事个体经营所获的收入、土地流转的租金、子女提供的资助、新农保养老金、村集体分红或补贴、各类社会救助(低保)等。一般的农民都会拥有其中1-2项收入,个别农民则会同时拥有3项以上的收入,因此,实际上农村老人在晚年养老方面是存在较为明显的个体差异的,这种分化是伴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对于自身同一时期所拥有的多种养老资源,农村老人一般并不会同时加以使用,为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他们会在实际动用中有取舍、有所侧重。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农村老人普遍认为过早地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依赖其生活,往往会给子女带来生活负担或制造摩擦,不仅不利于亲子关系的培养,而且可能还会降低家庭养老的效用。农村老人普遍把家庭养老当成晚年最后的归宿,不到最后阶段一般不会提前动用,这也在一个侧面体现出农村老人对于横向养老资源的理性调配。
(二)纵向养老风险的应对
对于一个农村老人的生命周期而言,在农村养老方式上,70岁以下只要身体条件尚好,一般都会强调在可承受范围内进行自我养老或土地养老。随着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从而导致两重后果,一是子女养老负担的加重,二是农村老人所能获得的养老资源和养老支持的减少。对此,农村老人对子女多表现出体谅的态度,尤其是70岁以下的农村老人对子女赡养的期望相对较低,认为子女现在生活不容易,主张在有能力的范围内进行自我养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身体条件的改变,农村老人一般无法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或其他劳作,生活自理的程度逐渐下降,对家庭照护的依赖逐渐增强,这时养老的主动权已逐渐转入到子女的手中。相关研究也证实,随着年龄增大,老人对于家庭和政府社会保障的需求度会上升。[23]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老人在年纪相对较轻且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时候,基本都是依靠土地或打工进行“自养”,而其中土地养老是最为重要的养老方式。只有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才考虑由家庭养老。这种养老策略反映出农村老人对于纵向生命历程中可能遇到的养老风险的应对。
五、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思路:农业与养老相结合
如上文所述,老人农业实质上是农业和养老的双重问题,但由于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村养老保障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提升,农业与养老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形成制度上的合力,从而导致老人农业与农业养老之间现实矛盾的存在。这要求政策制定者从提高农业收益和拓宽养老资源两个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力促农业与养老相结合,为“老人农业”提供支持保障。
(一)创新农业养老实践形式
尽管农业比较效益低并不是“老人农业”生成的直接动因,但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通过农业组织化和产业化的形式提高农业收入,却是缓解“老人农业”和实现农业养老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对此,各地应紧扣国家政策文件精神,首先,大力发展农民专业技术协会、股份合作社、农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改变传统的分散经营模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产业化程度。其次,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推进土地流转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完善,探索土地托管、经营权入股等形式,切实保障农村老人能从土地的转移中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再有,通过开发农村二三产业增收空间,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可以尝试引入农业的多功能元素,结合地方的资源禀赋与战略规划,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等价值,将完善农业养老与发展休闲农业结合起来。另外,还应鼓励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增加农村老人的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通过农业的“接二连三”实现产业整合,进而达到增进农民晚年福利的目的。
(二)探索农村社区养老模式
坚持自愿、自助、自立的原则,采取集体出资、政府扶持、村民互助、自我参与等形式,鼓励将农村独居、留守、空巢老人集中起来居住,建立农村社区养老机构,并组织专人为其提供配套服务。作为入住条件,农村老人可缴纳相关费用或将土地交由养老机构统一经营和管理,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还可以参与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其收入除用于缴纳必要的养老费用和管理费用外,剩余部分将以储蓄的形式交归老人自己管理。这种模式可以较好解决和实现农业养老的接续问题,一方面,农村老人不必离土离村就可以和熟悉的老乡亲们集中居住在一起,在生活方面既没有空间上的距离,也没有心理上的隔阂,有利于在互帮互助的氛围中实现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这种模式融农业与养老于一体,充分发挥了农业的多种功能,老人在休养过程中通过参与和指导农业生产的方式,始终与农业保持一定关系,这种模式既充分发挥了老人的主体性,丰富老人的闲暇生活,也重塑了老人的晚年尊严和社会地位,较好地实现了对居家养老的具体实践。
(三)拓宽农村养老服务资源
考虑到实际情况,将农龄折算计入养老帐户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不大,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提高农业补贴,尤其对于从事大田作物生产的农民,应提高农业补贴的标准。其次,需要外部服务资源的不断流入,[24]而服务的供给主体可以是公共机构、非盈利组织、商业组织、公司、志愿者等,如:农机合作组织为超过70岁的农村老人减收作业费用;社区服务中心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社区为农村老人建立养老档案,分类为老人提供相应服务。再有,应转变将农村老人视为单纯服务接受者的观念。事实上,农村老人具有较强的自养能力和服务能力,通过整合非正式支持,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农村社区中养老服务提供者。[25]对此,可以通过集体化的途径,形成互助小组,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实现“老老相助”。农村老人普遍都具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互助意识也较强,因此,可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将土地耕种集体化,促进不同年龄老人间的互助,增进邻里感情。同时,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制将土地整合承包出去,采用商业化的形式运作,邀请老人参与生产指导和定期分红。另外,通过壮大村集体经济来强化农村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福利的功能,探索完善农业集体化养老模式。
(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伴随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人口老龄速度的加快,“老人农业”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有可能加剧。需要辩证看待这一问题,虽然“老人农业”蕴含着农业生产向小农经济倒退、经营规模缩小、农业技术推广难等一系列隐忧。但同时,又孕育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契机。事实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对于机械化生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化服务手段的应用创造了条件。相关资料显示,欧美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遭遇了“老人农业”问题,但并没有对农业生产造成任何风险,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从而形成了对优质劳动力的替代。[26]因此,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因地制宜地发展多元化的社会化服务项目,将有效缓解“老人农业”带来的消极影响和提高农村老人的自养能力。具体包括:第一,提高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社会化服务功能。[27]第二,继续推进农用机械的普及,提高农机服务质量,降低农机服务价格。第三,探索多样化的基层农技推广形式,提高农技培训活动的针对性等;第五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制度,完善承保机制,规范工作流程,降低农业风险。第四,完善农业信息服务,探索“互联+农业”的实现形式,建立网上销售的多方渠道或农产品电子商务,使分经散、少量、单一的农产品交易规模化、组织化,为老人务农提供便利和保障。
[1] 曹鹏程.让老年人生活得更有尊严[N].人民日报,2015-06-10(05).
[2] 张红宇.“老人农业”难题可以破解[J].农村工作通讯,2011(14):37.
[3] 徐娜.张莉琴.劳动力老龄化对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4(4):227-233.
[4] 李澜,李阳.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研究——基于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6):61-66.
[5] 郭晓鸣,廖祖君,王小燕.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态势、影响及应对——基于四川省501个农户的调查[J].财经科学,2014(4):128-140.
[6] 李旻,赵连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0):12-18.
[7] 胡雪枝,钟甫宁.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7):29-39.
[8] 贺雪峰.老人农业有效率 不必担忧谁来养活中国[EB/OL].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jj/201310/t20131030_761805.shtml, 2012-07-05.
[9] Burholt, V. , Dobbs, C. Research on rural ageing: Where have we got to and where are we going in Europ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4): 432-446.
[10] 贺雪峰.应对老龄化的中国农业[EB/OL].http://www.snzg.net/article/2015/0720/article_41206.html,2015-07-20.
[11] 夏柱智.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J].人文杂志,2014(7):112-116.
[12] 李俏,朱琳.农村养老方式的区域差异与观念嬗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94-101.
[13] 贺雪峰.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分析[N].学习时报,2015-07-20(A3).
[14] 庞丽华.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J].经济学,2003(4):721-730.
[15] 吴兴南,孙月红.“老人农业”的隐忧和对策思考[J].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4(3):35-39.
[16] 颜珂.农村调查:务农老龄化效益低 明天谁来种地?[EB/OL].(2012-12-23)[2015-09-0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3/c_124134040.htm.
[17]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J].读书,2011(1):19-25.
[18] [23]王世斌,申群喜,余风.农村养老中的代际关系分析——基于广东省25个村的调查[J].社会主义研究,2009(3):84-88.
[19] 穆怀中,沈毅,樊林昕,施阳.农村养老保险适度水平及对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分层贡献研究[J].人口研究,2013(3):56-70.
[20] 彭希哲,宋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研究综述[J].人口学刊,2002(5):43-47.
[21] 党国英.统筹城乡土地规划 提高农民养老水平[EB/OL].(2014-02-09)[2015-09-05].http://theory.rmlt.com.cn/2014/1209/356653.shtml.
[22] 沈毅.土地养老缓解农民压力[EB/OL].http://www.cssn.cn/sf/bwsf_tpxw/201410/t20141006_1351853.shtml,2014-10-06.
[24] 李俏,李久维.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93-99.
[25] Kieran Walsh and Eamon O’Shea. Responding to rural social care needs: older people empowering themselves, others and their community [J]. Health and Place, 2008, 14(4): 795-805.
[26] 胡小平,朱颖,葛党桥.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探析[N].光明日报,2011-12-23(11).
[27] 李俏,王建华.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服务农户的特点与挑战——基于陕西16村的调查[J].商业研究, 2013(3):198-204.
[责任编辑:申凤敏]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研究”(15CRK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苏南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研究”(JUSRP1501XNC)。
李俏,管理学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陈健,江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蔡永民,博士,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律社会学。
F323.89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12-158-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