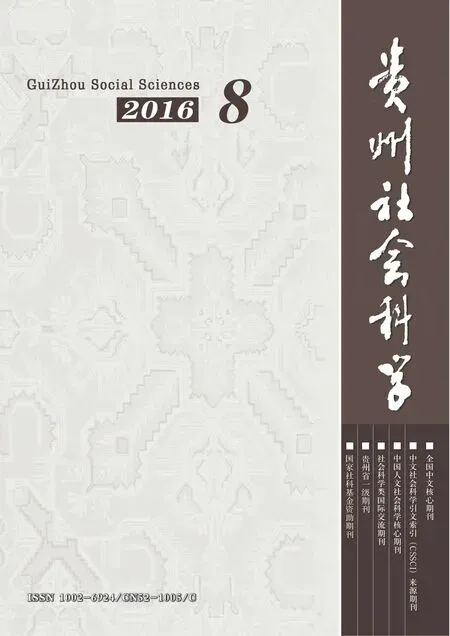《别赋》:人间爱别离苦的佛学观照
饶峻妮 许云和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 昆明 650224;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别赋》:人间爱别离苦的佛学观照
饶峻妮许云和
(西南林业大学,云南昆明650224;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275)
《别赋》是江文通被贬至吴兴时创作的作品,在经历了生死离别的痛苦之后,他在吴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期间,他读经、参禅,逐渐接受了佛教的人生观。因此能够运用佛教爱别离苦的思想来审视滚滚红尘中芸芸众生的离别之痛,从而稀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别赋》开篇的“黯然销魂”,乃是对佛教“爱别离苦所谓命终”的另一种阐释,而其“别虽一绪,事乃万族”的总结,则与经中所说的“颠倒上下不可经纪”一脉相承,其对富贵别、侠客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妻别、方外别、情人别等各种离别场景的精心描写,就是对这一思想的一个尽情演绎。结末的 “有别必怨,有怨必盈”,讲的就是一个苦难世界人生痛苦盈积堆垒的佛理,其“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者,则又是众生离别因“怨咎集会”而“身心烧然”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此而论,《别赋》展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世的离别因缘,寄寓了一种超脱恩爱苦海,获得解脱的愿望。
《别赋》;江淹;宗教文学;赋;
以赋的形式专门敷写人世的离愁别恨,在文学史上江文通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就曾有不少以离别为题材的赋作出现,诸如徐干的《哀别赋》、陆机的《别赋》、傅咸的《感别赋》等。而在江文通同时,也有刘孝仪写过《叹别赋》,张纉写过《离别赋》。但是,能对后世人们的心灵产生强烈而永久的震撼、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经典的,却是江文通的《别赋》。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别赋》何以会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芒、取得这样高的文学成就?从接受史上来看,人们对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别赋》“音制一变”,[1]1以极富概括力的笔调,抒写了生离之悲这种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以及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的永恒的缺憾,这就是它为其它赋作所不及的原因。毫无疑问,将《别赋》的成功归结为“极富概括力”是非常准确的。所谓艺术概括力,不应只是一个艺术层面的问题,本质上它还是一个作家是否具有集中总结和概括某一生活现象的意识问题,而这种意识又通常是在某种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从这方面来讲,《别赋》在创作上有总结和概括别离这一生活现象的意识就绝非偶然,其背后必有一种新的强大的思想力量的驱动,它使作者站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以全新的思想和方法在审视、理解眼前这个世界的事和物。
一、劫波之后对离别因缘的深心思惟
叶舒崇尝云:“江文通之著作,别绪居多;庾开府之生平,间关不少。”[2]394已切中了江文通作品多写离愁别恨的实际,而观江文通全集,又可发现其写离情别绪的作品,又以贬谪吴兴时为多。此时以离愁别恨为题材的作品,前期计诗有《古离别》、《望荆山》、《秋至怀归》、《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仙阳亭》、《游黄蘖山》、《还故园》、《寄丘三公》、《卧疾怨别刘长史》、《采石上菖蒲》、《无锡舅相送衔涕别》、《征怨》、《清思诗》等;赋有《泣赋》、《去故乡赋》、《思北归赋》、《哀千里赋》、《知己赋》、《伤友人赋》、《娼妇自悲赋》、《四时赋》等,文有《被黜为吴兴令辞建平王笺》,辞则有《山中楚辞五首》。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记录江文通自己作为逐臣的去国怀乡之悲,叙写其辞家国、别亲朋的身心感受,极为清晰地反映了江文通告别京师后个人的情感轨迹和心路历程。如:
淹乃梁昌,自投东极。晨鸟不蜚,迁骨何日。一辞城濠,旦夕就远,白云在天,山川间之,眷然西顾,涕下若屑。(《被黜为吴兴令辞建平王笺》)
他的担心在于,此一去是出有日而还无期,一旦离开了帝都,就是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但远离亲人、远离繁华,更远离自己毕生的理想和追求。被贬途中,他的这种离别痛苦可谓是更行更远更生,为了寻求感情的慰藉,是以在其赋中尽力将思绪引向有过同样遭遇的古人,诸如齐景公、荆轲、孟尝君、司马迁、李陵、伍子胥等,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情感支撑。
眷徐扬兮阻关梁,咏河兖兮路未央。道尺折而寸断,魂十逝而九伤。欷潺湲兮沫袖,泣呜唈兮染裳。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视。镜终古而若斯,况余辈情之所使哉。(《泣赋》)
而在初至吴兴的岁月里,他的离别痛苦并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稍有冲淡,相反倒是挥之不去,逐日而深,此期间,他常常是“思旧都兮心断,怜故人兮无极”、“何尝不梦帝城之阡陌,忆故都之台沼”,以至于“轸琴情动,戞瑟涕落,逐长夜而心殒,随白日而形削”,到了“魂气怆断,外物非救”(《四时赋》)的地步。按照他自己的叙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沉浸在这离别的痛苦中而不能自拔,终日以泪洗面,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泣故关之已尽,伤故国之无际”,“情婵娟而未罢,愁烂漫而方滋。切赵瑟以横涕,吟燕笳而坐悲。”(《去故乡赋》)“自出国而辞友,永怀慕而抱哀,魂终朝以三夺,心一夜而九摧,徒望悲其何及,铭此恨于黄埃。”(《哀千里赋》)离别的痛苦是这样地折磨人,以至于他深感无可奈何,对能否活着回到京师表示了深深的绝望。此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死后不会弃身异乡能够归灵上国,倘若能够如愿,即便是受尽万般辛苦也在所不辞。《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就充分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
历隐忧而不去,心汤汤而谁告,魄寂寂而何语,情枯槁而不反,神飜覆而亡据。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犹储精于沛乡;奇略独出之君,尚婉恋于樊阳。潘去洛而掩涕,陆出吴而增伤。况北州之贱士,为炎土之流人。共魍魉而相偶,与蟏蛸而为邻,秋露下兮点剑舄,青苔生兮缀衣巾。步庭庑兮多蒿棘,顾左右兮绝亲宾。忧而填骨,思兮乱神。愿归灵于上国,虽坎轲而不惜身。
然而,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是,《别赋》虽然同样创作于被贬吴兴期间,内容也同样是写离别,但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目。这主要表现在,赋中基本上是消失了作者自己的身影,写的离别经历完全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有的只是自己对他人离别情形的体味和咀嚼。这一点,陶元藻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其赋别也,分别门类,摹其情与事,而不实指其人,故言简而该,味深而永。”[4]552所谓“不实指其人”是说《别赋》摹其情与事,并不涉及现实生活中某个具体的人,这也同样是意识到了《别赋》中没有出现作者自己的身影。原因何在?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前述例举作品都写在他被贬的初期,而《别赋》则写于被贬的晚期。时间的不同,作品角色的转换,从某种程度上讲实际上已经凸显了作者思想情感轨迹的深刻变化。到后期,作者不再戚戚于自身的遭际和命运,镇定、超然了许多,已然是走出了痛苦的深渊。此时,他彷佛是一个入定的老僧,看透了人世离别的秘密,以一个劝世者的身份在向世人讲述着人世离别悲欢的种种法相,让世人晓谕其中的内涵和意义。这一立场的变化与他在被贬闽中后的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江文通本人的记述,可知其在被黜吴兴的三年之间,曾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是“与道书为偶”(《自序传》),潜心研究佛学;一方面是“立孤台于山岫,架半室于江汀,累青杉于涧构,积红石于林棂”,筑就了一个习禅的禅窟,在禅窟中“躭禅情于云径,守息心于端石”(《构像台》)。因接受了佛教思想并有了习禅的宗教体验,江文通的人生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在与《别赋》同期的诗文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吴中礼石佛》云:“幻生太浮诡,长思多沈疑。”是说自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一切皆悉无常,不过就是一场无而忽有之梦而已,而“轩骑久已诀,亲爱不留迟。忧伤漫漫情,灵意终不淄”云云,则又说自己此时已经不留恋势位富贵,对于自己所遭受过的生死离别之苦,也已经看得很透,不复挂于胸怀,如此通脱、旷达,当然是他面对佛陀,用佛教的思想世界观来思考现实世界,体悟自己的人生历程的结果。《别赋》对人生离别的认识和表达之所以不同于以往,或归因于此。显然,当江文通接受了佛教人生一切皆苦,“合会恩爱,必有别离”[5]198的思想之后,再来思考“离别”的问题时,就不再是限于自身,而是推己及于他人,及于满世界的芸芸众生了。这时候,他不仅是忏悔者,同时也是一个布道者。因此,他在文中咀嚼的就不只是自身的不幸,而是整个人世的不幸了。
二、“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与“爱别离苦所谓命终”
《别赋》开篇第一句“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历来以为是开宗明义,为一赋之纲领,是全文的主旨所在,刘埙云:“江文通作《别赋》,首句云‘黯然而销魂者,别而已矣’,词高洁而意悠远,卓冠篇首,屹然如山”。[6]60关于它的内涵意义,《文选》李善注多有阐发,云:“黯,失色将败之貎。言黯然魂将离散者,唯别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则形毙,今别而散,明恨深也。”[7]237据李善注的发明,显然,“黯然销魂”所包蕴的意思就是:离别乃人世的深恨,能够使人达到魂不守形,形容失色的命终般状态。从文学史上来看,将离别视为人类生命情感中最大的剧痛,江文通并不是始为之者,古来早已有之,屈子就说:“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据此而言,江文通对离别之痛的认识似乎就只能说是承袭了古人的看法而非个人独到的体会。但显然江文通的赋是专门为铺写离别而来,仔细体味《别赋》的“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其认为离别是人类生命情感最大的剧痛,古人只说别离是人生最为痛苦悲伤的事情,而江文通则将这种痛苦提高到“黯然销魂”的高度,此则是古人的意识尚未究极的层面。将人世的离别之痛上升到“黯然销魂”的高度来认识,在那个时代能够作尽心关注的恐怕只能是佛教的思想而非他。佛教就认为,爱别离苦是人生最大的苦难,且是人生苦难的根本,《大般涅槃经》云:“迦叶,云何菩萨摩诃萨住于大乘大涅槃经观爱别离苦,爱别离苦能为一切众苦根本。”《佛说解忧经》云:“爱别离最苦,忧火镇烧然。”《佛说未曾有因缘经》云:“苦中之甚,莫若恩爱离别之苦。”为什么爱别离苦是众苦之最甚者呢?在佛教看来,这主要是别离能“因爱生忧,因爱生怖”,“爱因缘故则生忧苦,以忧苦故则令众生生于衰老,爱别离苦所谓命终”。别离之所以为苦,乃在于它会使人的情感过程产生“忧”和“怖”,这“忧”“怖”能对人的神气达到最大程度的摧伤。《佛说大乘稻秆经》云:“恼心故,名忧。”《舍利弗阿毘昙论》云:“心惊毛竖,是名怖 。”说明“忧”和“怖”是人的痛苦在内心的壮热和烧燃,由于“忧”、“怖”是作用于人的内心,于人的内心达成对人情的烧然,所以它不仅会使人颜色愁惨,呈现恼苦难胜之状,同时更使人精神飘浪,魂魄幽冥,如命终一般。江文通所说的“黯然销魂”,刻画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形容失色将败、魂将离散的忧怖恐惧之状,即命终般状态,包含了作者对苦难世界一切众生别离“忧怖悉充满”的全部理解。
正因为“黯然销魂”是从佛教的思想人生观的层面提出来的思想,是众生离别时忧怖恐惧之极的命终般状态,所以《别赋》为了深入体现它的具体情状,紧接着就通过详细描绘一男女夫妇在离别过程中的诸多“忧”、“怖”景象来进行展示。就行人而言,其可忧怖者,一是“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不知道路几千,由此给人带来前路难测的深深忧虑;二是“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暂起”,“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物色变化无端,给行人带来无穷的身心刺激,因感物伤情,“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忍受着极大的内心煎熬,由是产生了不忍离别的焦虑和不安,此时,仿佛是“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身心极为迷闷,生出了无穷大苦恼,以至于“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为之神伤不已。行子如此,思妇也同样是处于忧怖之中,别时艰难,难舍难分,已感为怨难胜,与斯人别后,精神也常常是处于“惕寐觉无见兮,魂廷廷若有亡”(《长门赋》)的状态,到了夜晚,“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看到的景象更是伤怀,百无聊赖中,她“巡层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在无可奈何的痛苦中消磨着美好的青春年华。居人是魂廷廷若有亡,而行子也复离夣踯躅不进,别魂飞扬不安,这就是“忧”、“怖”给世间有情人在情感上造成的巨大摧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众生离别忧怖的根源,佛教将其直指我执、法执、七慢、三毒、五欲,认为众生愚痴,陷于其中而不能自知,故如行于漫漫长夜,受尽恐惧忧怖的煎熬。所以,只有斩断乐欲,才能免受这样的煎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江文通在此极写离别的忧怖,就明显还有深层的用意,这就是以广说离别的忧怖情景而见示法相,由此直戳人世离别忧怖的根源。
明代的任广曾从创作的角度解释了这段文字的语义关系,认为《恨赋》第一段描写的这些男女离别的种种痛苦情景实际上就是对“黯然销魂”的一个阐释,他说:“别恨曰‘黯然销魂’,又曰‘恍若有亡’,又曰‘离梦踯躅’。”[14]560这个解释无疑是准确的,不过,任广却没有能够从佛学的层面体会出江文通行文中的这一层深意,不知道江文通之所以深情委曲,致力于“黯然销魂”情景的刻画,乃是为了刻意表现世间一切“有著男女,有恋妻妾,未称所求,多生忧怖”[9]369的情形,描绘一个“在陆地一切众生于夜暗中遭恐怖”[9]369的苦难世界,其境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阔大得多。
三、“别虽一绪,事乃万族”与“颠倒上下不可经纪”
在以形象的描写阐发了“黯然销魂”的佛学涵义之后,《别赋》又特别指出人世间的“别虽一绪,事乃万族”,这一提法,明显带有总结的意味,而细味这一总结,显然又与佛教的思想立场不无关系,因为这一总结已不是“凡夫以世俗眼,见有去来”[10],所睹唯实,而是以关怀终极人生的广大胸怀,向众生示“有去来今”。这已然是站在了一种眼观色境的高度,其着眼处自不是一切染法境界,而是一切善法境界,这一点,又恰好是佛教的人生观所具有的思想境界和高度。《修行地道经》论及人世的悲欢离别时,对此就曾有过特别的说明:
愁恻之痛叵具说言。从累劫来与父母违,兄弟离阔,妻子之乖,涕泣流泪超于四海,饮亲之乳踰于五江四渎之流。或父哭子或子哭父,或兄哭弟或弟哭兄,或夫哭妻或妻哭夫,颠倒上下不可经纪。种勤苦根愚痴之元,修行见然皆患厌之,但欲免斯生死之病,昼夜精进,不舍道义,求于无为。
其言离别是“从累劫来”所有,其间“兄弟离阔妻子之乖,涕泣流泪超于四海,饮亲之乳踰于五江四渎之流。或父哭子子哭父,或兄哭弟或弟哭兄,或夫哭妻或妻哭夫。颠倒上下不可经纪”,又言“天下世间别,生死之展转。譬如于车轮,父子兄弟乖。妻息子离戚,涕哭泪流下,超于四海水”,这已是从宇宙、历史的视角,把人间的离别之苦视如深渊流出成河,弥满世界,流向三界。佛教的这一思想,诸经中也多有体现,《正法念处经》就强调人世间“有无量种恩爱别离”,《佛说大般泥洹经》云:“世间诸亲戚,眷属皆别离。”《舍利弗阿毘昙论》说:“云何爱别离,若爱喜适意,若父母兄弟姊妹妻子,若亲厚诸臣眷属,适意色声香味触法,众生若不共彼居不亲近独不杂异不相应别离,是名爱别离。”《正法念处经》也谓:“亲爱及兄弟,亲友皆别离。”此种种广说,无不是跨越历史的时空,用佛教的人生观来对无始生死以来有情一切恩爱合会,皆悉离别的情形作出总结。就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而言,《别赋》“别虽一绪,事乃万族”的强调,与之不能不说是一脉相承,其言别离而指其事过万,就明显是以另外一种眼界来直视人间,穿越的自也是历史的时空,着眼的自也是无始生死以来人生一切皆苦的历史和现实。正是有了这一思想为基础,所以《别赋》接下来对人世富贵别、侠客别、从军别、绝国别、夫妻别、方外别、情人别等各个离别场景的描写,用意就显得极为明确。显然,其对各种离别场景作生动形象的描绘,真正的目的乃是为了对这一思想作出尽心的演绎,以能感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作出强有力的印证,使读者透过艺术描写对此更能获得更为真切的体会,而这种表现形式,也是佛教说法惯用的形式,所谓“真如离相,不可说尽”[11]846即此之谓。这表现在,它一方面铺写的是让人肝肠寸断、不能仰视的离别景象,一方面却又不忘对离别痛苦的根源作深刻的挖掘,力求对一切恩爱合会,皆悉离别的思想作生动、形象的展示。富贵者之所以有离别之痛,乃是缘于同僚间平日的交谊,富贵相交,恩荣共荷,固然可意悦心,一旦分别,却也不免“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此种场景,正佛教所谓“朋友为苦,心不分离故”[12]138。侠客之所以有离别之痛,一者是缘于“惭恩”、“藉友”的游侠心肠,一者则缘于深厚的骨肉之情,故非但有暂离之痛,更有永诀之悲。从军者之所以有离别之痛,一者牵于妻子的恋慕,一者缠著父母的恩爱,情无纵舍,故《仁王护国般若经疏法衡抄》以偈的形式专门描绘了这种情景,以提醒世间有情:“爱别情偏苦,生离最可伤。子行五百里,慈母半千强。衰声彻心骨,泣泪洒襟裳。痴贪无慧解,寸寸断肝肠。”《慧远外传》更以一则故事来讲述这种母子离别的痛苦,说明爱别离苦为何种境象:“相公是夜又为夫人说其爱别离苦者。如是家中养得一男,父母看如珠玉。长大成人才辩东西,便即离乡别邑,父母日夜悬心而望,朝朝倚户而至啼悲,从此意念病成。看承眠药何时得见,忽至冬年节岁,六亲悉在眼前,忽忆在外之男,遂即气咽填凶,此即名为爱别离苦。”绝国者之所以有离别之痛,那是他生于斯长于斯,除了故土的情怀,亲人的深深依恋,更有生离成死别的隐忧,故“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由此生出的恩爱愁苦,远山遮不住,长河隔不断。夫妻之所以有离别之痛,则是因“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婚姻欢会,如兄如弟,彼此心怀恋慕,无时或离。有此爱欲因缘,故所致痛苦尤为深重,所以《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缘经》说:“夫妇别离,恩爱至悲。”指出他们的痛苦之深乃根源于男女不能自拔的爱欲。而《佛说菩萨修行经》更是对此作出强调,认为夫妻离别之痛是“三界恼之甚”,为诸种离别之痛所不及。“有妻子贪离别,所作行当自受,便独趣随苦毒,彼无有代痛者。斯三界恼之甚,莫若如妻与子,本爱时规与乐,反成忧罪恼根。缘受三恶道苦,毒辛酸惨痛生,若当被诸恼根,妻及子无伐者。”而“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之句,更强调了就是神仙也有离别之痛的原因。因此,佛陀出家,虽意志坚定,但真正到了离别父母时,也不免“悲感泣流泪”,感到千难万难。情人之间之所以有离别之痛,乃在于男女目挑心招,为情颠倒,可谓是“缘交染境”[13],沉迷爱欲,不知有极,一旦分别,自是“思心徘徊”,黯然神伤。关于情人之间的这种恩爱离别因缘,因是“多欲人男女集会更相染爱,于念念中起于无量妄想思觉,随彼境转无有尽极”,[14]795在人世间显得特别的典型,故佛教对它曾有过特别的关注,《大宝积经》云:“男女爱欲欢会分离而去,识身和合,恋结爱著,味玩悭悋,报尽分离,随业受报,父母因缘中阴对之,以业力生识获身果,爱情及业,俱无形质,欲色相因而生于欲,是为欲因。”说明世间男女愚痴,并不知道“情爱不恒,爱恋须臾”[15]436的道理,而实际上,“男女爱如初月轮,皆随喜舍归圆寂”[16]657,最终只能是“暂有亦复归灭。”[17]775可见,江文通精心演绎的这一个个离别场面,并非是为专门叙写各种离别的悲情而设,供人们咀嚼玩味,博取世俗的眼泪和共鸣,旨在说明,这人世的离别不是个案,而是众生皆有;因而,这离别的痛苦也不是只集于个别人之身,而是滚滚红尘中的众生之身,且是弥满世界,流向三界。更为重要的是,江文通描写的这一个个离别场面中的离人,似乎人人都是耽于爱欲,贪著恩爱而有恨于离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的提示,表明江文通在试图说明这样的问题,即众生“为无明爱之所覆蔽”,以至于“长夜轮转不可觉知以是因缘”[18]675。
如前所言,专门铺写某种离别场景,之前的作家并不是没有尝试过,也不是不能够感动人心,但是,这些作品却不能够像江文通的描写一样获得更多共鸣,原因就在于《别赋》站在一个能够引人思考的思想高度,这就是无始生死以来的历史时空,人生一切皆苦的思想基石。在这个基石和高度上观察和形成的人间离别场景,其对世间有情的震撼自是非同凡响,它唤起的不只是世俗的人们对此无可奈何的永恒的缺憾,而是内心的自省和精神救赎的希望。
四、“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与“恼由爱别离生”
在分陈了人世间的七种离别之苦后,江文通最后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虽渊、云之墨妙,严、乐之笔精,金闺之诸彦,兰台之群英,赋有凌云之称,辨有雕龙之声,谁能摹暂离之状,写永诀之情者乎?
“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承前“事乃万族”而言之,表面看来,讲的似乎只是一个“人生有各种各样的离别,离别的原因也多种多样”的常理,但由佛教的角度观之,却又觉得其中胜义无穷,妙理可观。其“别方不定”者,申述的不就是佛教“世间无常,悉皆离别”[19]400的观念么?其 “别理千名”者,不就是在强调人生离别是由种种因缘促成的么?而后面的“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如果按佛教的思想寻绎下来,则又可视为佛教“恼由爱别离生”[20]的另一种说法。《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云:“爱名为怨,依此而转,或诸烦恼皆名为怨,彼依此转故名怨路。”是知怨即烦恼,“有别必怨”即是离别而生烦恼,这种烦恼却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且逐日而多,逐日而深,故又言“有怨必盈”。关于离别所生烦恼的永恒和无穷,《别译杂阿含经》曾借佛陀和众比丘的对话作过十分形象的描述。
生死长远无有边际,无有能知其根源者。一切众生皆为无明之所覆盖,爱结缠缚,流转生死无有穷已。过去亿苦无能知者,譬如恒河流注四海。复告比丘,生死长远于昔过去受形已来,忧悲哭泣所出目泪为多?为恒河多?时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生死长远,目所出泪踰彼恒河亦多四海。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所集目泪实多四海,诚如汝言。
所谓“生死长远,目所出泪踰彼恒河亦多四海”,讲的就是苦难世界人生痛苦的一个盈积堆垒,它充塞于天地人间,流转于无始生死以来。可见江文通的“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实本佛教教义而衍之,说的正是离别能给有情世间带来诸多烦恼,而且这种烦恼是无穷无尽的。更为重要的是,江文通的“有别必怨”不只是停留在这一层含义上,他还有进一步揭示离别因缘,劝诫人世的意思。《妙法莲华经文句》云:“世者名怨,以不生佛性故,则烦恼怨生,烦恼怨生故不见佛性,不生烦恼即见佛性。”说明人生的痛苦烦恼乃由众生不见佛性而生,不见佛性,即众生愚痴,为无明所覆,不能认识到人生痛苦的根源所在,故爱结不断,不尽苦边。所以“有别必怨,有怨必盈”,强调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世者名怨 ”,说明众生未能渡十二因缘河,犹如兔马,以此警醒世人,爱即是离别痛苦的根源,应早渡爱河而登彼岸,免于为诸烦恼势力所食。
在叙说了人世的“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之后,江文通最后又特别强调别离的怨恨烦恼能“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这句话,也同样是对佛教思想的一个衍说,这就是离别时众生的“身心烧然”,具体则如《阿毘达磨法蕴足论》所言:“说爱别离为苦,谓诸有情,爱别离时,领纳摄受种种身苦事故。广说乃至。领纳摄受种种身心烧然事故。”这烧然的情形,按照佛教的比喻,是“如堕刀火烧其身心受大苦恼”。[21]341江淹之所以煞费苦心地用“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来形容它,当然是期以在文学上对它获得一个透彻的表现。虽然江文通的这个造语堪称精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人生痛苦的至深至极,但他也还是觉得并未尽情,认为离别的痛苦情状太难于描摹,即便是像王褒、扬雄、严安、徐乐、司马相如和邹奭那样的大手笔,也未必能够曲尽其情。这一点,作为弘扬佛法的佛陀更有深刻的体会,他说:“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自病至死,其苦无量。心恼积罪,生死不息,其苦难说。”[22]723那么,这些难以言状的痛苦究竟达到什么程度,体现在哪些地方呢?佛教认为,“复次爱别离时,受三种苦,一者苦苦,二者行苦,三者坏苦,故名爱别离苦。”[23]480所谓苦苦,《大乘义章》云:“从彼苦缘,逼而生恼,名为苦苦。”说的是有情之身心,本来即苦,复加以饥渴、疾病、风雨、劳役、寒热、刀杖等众苦之缘而生之苦,故曰苦苦。《别赋》开篇所描写的风霜雨露对行人身心的刺激,就属此类。行苦,是说因一切有为法迁流三世,而无刹那常住安稳,见诸法无常,而感逼恼。亦即除可意非可意以外的舍受法,为众缘所造,难免生灭迁流,故圣者观见之,于身心皆感逼恼,是以称为行苦。《别赋》中所描写的离别场景,几乎都有这种当事人观见人生无常,别离时“于身心皆感逼恼”的一瞬,比如:“造分手而衔涕,感寂寞而伤神”;“金石震而色变,骨肉悲而心死”;“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沾罗裙”,“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与子之别,思心徘徊”等等。坏苦又作变异苦,有三种。一指乐境变坏的苦,即对所爱的人或物,因死亡破坏的变化所生起的苦感;二指身中地、水、火、风等四大互侵、互坏之苦;三指诸可意之乐受法,生时为乐,坏时逼恼身心之苦。[24]1546,2850《别赋》所写固然都是离别的场景,但这场景无一不是由乐境变坏而来,如夫妻、情人、母子、朋友之间,都是由共居、同处、无间的快乐而走向无可奈何的分别远离的境地的。至于这三个方面的痛苦对世间有情身心的戕害的程度,诸经中多有论说,而尤以《中阿含经》的描述最为可观:
诸贤,说爱别离苦者,此说何因。诸贤,爱别离苦者,谓众生实有内六处,爱眼处,耳、鼻、舌、身、意处,彼异分散,不得相应,别离不会,不摄、不习、不和合为苦,如是外处。更乐、觉、想、思、爱,亦复如是。诸贤,众生实有六界,爱地界,水、火、风、空、识界,彼异分散,不得相应,别离不会,不摄、不习、不和合为苦,是名爱别离。诸贤,爱别离苦者,谓众生别离时,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诸贤,说爱别离苦者,因此故说。
即此可以看出,三种苦给人带来的身心戕害,不仅在于它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刺激,更在于更乐、觉、想、思、爱等情绪、意识对它的唤起。而且,这种痛苦还有“身受苦受、遍受、觉、遍觉;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身心受苦受、遍受、觉、遍觉”的无穷折磨,让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领纳摄受着种种身心苦事,种种身心热事,种种身心燃烧事,以至于忧悲苦恼,痛苦无穷。这样看来,江文通将离别的痛苦程度用“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来形容,就不能不说是在对佛教的这一思想有所认识的情况下对人世离别的痛苦程度作出的深刻体悟,它凝集的不只是高度的艺术匠心,而且还凝集了一个充满血肉的佛旨真谛,无怪乎它会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五、从江文通的《别赋》到释真观的《愁赋》
在《别赋》写成后115年,隋代高僧释真观写了著名的《愁赋》,这篇赋虽是残篇,但仍可以看出模仿江文通《别赋》的痕迹。如前所言,《别赋》选择的是生离之悲这种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为敷写对象,去生动形象地演绎人世的“离别因缘”。在《愁赋》中,释真观也同样选择悲愁这种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为敷写对象,如此,他所赋的“愁”是否也如《别赋》一样,赋予了佛教人生观的色彩呢?虽然《愁赋》并没有直接的表白,但与之相关的几件事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释真观本是高僧,精通佛理教义,且有相当的宗教体验,因此,对于人世间这种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他是难以回避人生一切皆苦的佛学思考的。《续高僧传·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叙其事云:
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以观名声昌盛,光扬江表,谓其造檄,不问将诛。既被严系,无由申雪,金陵才士鲍亨谢瑀之徒,并被拥略,将欲斩决。来过素前,责曰:“道人当坐禅读经,何因妄忤军甲?乃作檄书,罪当死不?”观曰:“道人所学,诚如公言,然观不作檄书,无辜受死。”素大怒,将檄以示:“是尔作不?”。观读曰:“斯文浅陋,未能动人,观实不作,若作过此。”乃指擿五三处曰:“如此语言,何得上纸。”素既解文,信其言也。观曰:“吴越草窃,出在庸人,士学儒流多被拥逼,即数鲍谢之徒三十余人,并是处国宾王,当世英彦,愿公再虑,不有怨辜。”素曰:“道人不愁自死,乃更愁他。”观曰:“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为深虑耳。”素曰:“多时被絷,叵解愁不?”索纸与之,令作愁赋。观揽笔如流,须臾纸尽,命且将来,更与一纸。素随执读,惊异其文,口唱师来,不觉起接。即命对坐,乃尽其词。
显然,《愁赋》是在杨素听完真观关于生死的看法后,又想了解真观对自己被拘执时所受愁苦的看法的情况下写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真观所谓“生死常也,既死不可不知,人以为深虑耳”,乃是从一个出家人的立场来说的,意思是说“生死常道,转相嗣立”[25]275,而自己则是早已勘破生死,不会像一般俗人那样“以为深虑”。真观解生死既如是,那么,杨素问“叵解愁不”?接着令真观作《愁赋》,显然就有这样的意思,这就是要求真观对“愁”作佛学的体悟,讲出一个出家人心中的愁。从这方面来讲,真观所赋的“愁”,自然不会是尘世一般俗人眼中的愁,而是一个高僧慧眼中的愁。这就表明,《愁赋》与佛教之间,无疑是有着深刻的联系的。二是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对于“愁”的铺写,差不多就是对人世“愁忧因缘”*关于愁忧因缘,尊婆须蜜造,僧伽跋澄等译《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卷第4《三昧揵度首》云:“或作是说:愁忧因缘则是彼缘,若已生愁忧彼则有生,是故愁忧中间当言愁忧因缘。”《大正藏》第28册,第753页。的一个精心演绎。关于“愁”和“愁”的因缘,佛教是这样阐述的:“于爱迷惑贪著热恼故名愁。”[26]820又云:“死时离别,愚迷贪恋,心胸烦闷为愁。”[27]194说明人世间愁的根源乃是贪和爱,是众生的贪和爱,铸就了自己无尽的愁和恨。真观赋愁,就特别注重这一因缘的揭示,为此,他不惜笔墨,借用《别赋》的叙事模式,通过大量的历史人物的不幸遭遇的描写进行体现,分陈了这些人物的去国之愁,不遇之愁,怀人之愁,征戍之愁等等。当我们咀嚼这些人物的不幸和愁怨时,总会在情感和心灵上布上浓浓的乌云和愁惨,为这些人物的遭遇一洒同情之泪,但是,同情和眼泪却又会使我们陷于深深的历史追回之中,禁不住要问,屈子何愁?荆轲何怨?这样,就难免不沉浸在人事因果的思考和推想之中,如果屈子不是心向往于郢都,荆轲不是心系于仇恨,其愁怨又从何而来?可见,真观虽然着眼的是愁这种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生活体验的描绘,却又不忘从佛教的人生观出发对人世间愁恨的根源作深深地挖掘,揭示出贪欲是人世众生愁苦的渊薮、不幸的苦海。尽管只得半幅,但就其与佛教的关系而言,此半幅有力地表明,在杨素的刀剑威胁下,真观所要表现的就是一个人世的愁忧因缘,藉此向人间强权者传达一种佛门勘破世事而不忧不惧的正气。
在此基础上,再来审视真观对江文通《别赋》的模仿,为《别赋》给出了一种重要的读解。正是真观了解到了《别赋》的写作动机,认识到了《别赋》赋别是为了演绎一个人世的离别因缘,且其敷写这一内容的方式都曾做过精巧的设计,觉得极为可取,所以才刻意地进行模仿,用这种方式演绎出一个人世的愁忧因缘,说出佛门对人世愁恨的理解和认识。换言之,重新认识《别赋》与佛教的关系问题,真观的《愁赋》无疑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参照。
[1]张溥.江淹集题词[M]//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8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5册.
[2]佚名.词原序.《曝书亭集》原序[M]//曝书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7册.
[3]姚思廉,撰.江淹传[M]//梁书: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3.
[4]陶元藻.书江淹恨赋后[M]//泊鸥山房集:卷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续修四库全书》,第1441册.
[5]法显,译.大般涅槃经:卷中//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出版部,1990:第1册.
[6]刘埙.古赋二[M]//隐居通议: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6册。
[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1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任广,撰.书叙指南:卷15[Z].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0册。
[9]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68[Z]//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九,《大正藏》第10册。
[10]传灯,著.维摩诘所说经无我疏:卷第8[Z].卍新纂续藏经:第19册.
[11]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52[Z].大正藏,第7册.
[12]僧伽跋澄,等,译.僧伽罗剎所集经:卷下[Z].大正藏,第4册.
[13]怀素,撰.四分律开宗记:卷第6[Z].续藏经,第42册.
[14]般若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29[Z]//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大正藏,第10册.
[15]法天,译.妙法圣念处经:卷第6[Z].大正藏,第17册.
[16]毘舍佉造,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颂:卷下[Z]//下明于十七跋窣覩等中述其要事[Z]//大正藏,第24册.
[17]竺佛念,译.出曜经卷:第30[Z]//梵志品之二,大正藏,第4册.
[18]阇那崛多,等,译.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4[Z]//相好品之余.大正藏,第21册.
[19]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第38[Z]//第八门第十子摄颂说涅槃之余.大正藏,第24册.
[20]怀素,撰.四分律开宗记:卷第6[Z].续藏经,第42册.
[21]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第58[Z]//观天品之三十七.大正藏,第17册.
[22]迦叶摩腾共法兰,译.四十二章经[Z].大正藏,第17册.
[23]尊者大目乾连造,玄奘,译.阿毘达磨法蕴足论.卷第6[Z]//圣谛品第十.大正藏,第26 册.
[24]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书店,1991.
[25]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卷下[Z].大正藏,第12册.
[26]不空,译.慈氏菩萨所说大乘缘生稻喻经[Z].大正藏,第16册.
[27]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37[Z]//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四第六地.大正藏,第10册.
[责任编辑:郑迦文]
饶峻妮,西南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许云和,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汉魏六朝乐府,佛教与中国文学、出土诗赋文献。
I207.99
A
1002-6924(2016)08-019-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