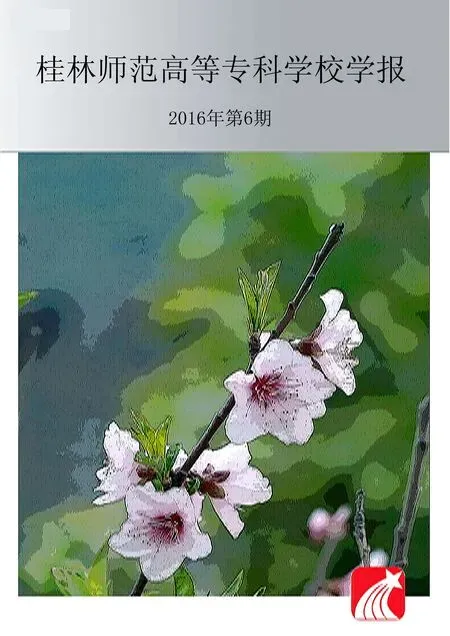追寻边缘族群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广西恭城碑刻集》简介
江田祥,邓永飞,杜树海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2.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追寻边缘族群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广西恭城碑刻集》简介
江田祥1,邓永飞1,杜树海2
(1.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 541001;2.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广西恭城碑刻集》作为南岭历史地理丛书的一种,为学界提供了一份不算丰富但较为可信的文献资料。该书的特色在于:一是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二是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且分布相对密集、时空序列明晰,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恭城地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三是揭示恭城地域社会历史特点,凸显恭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广西恭城碑刻集》;边缘族群;多元一体
《广西恭城碑刻集》这本书的最初确定缘于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主持的“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课题。2008年初,我们三人参加了课题组,在科大卫、刘志伟两位老师的建议下,选择桂北作为研究区域,随后我们对桂林各市县的文献数据进行摸底。2009年暑假,两位老师还亲自带领课题组成员来到广西梧州、贺州、桂林的田野点进行现场指导,不仅为我们勾勒了“惊心动魄”(科大卫语)的研究主旨,也确定了我们的课题任务,即整理《广西恭城碑刻集》。
我们在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始于2009年2月。在恭城瑶学会会长莫纪德先生指引下,我们多次来到风景秀丽的恭城,行走于乡间小径,跋涉于瑶山大岭,寻访到不少散落民间的碑刻,加上合作者莫先生收藏的碑刻拓本,辑成了这本恭城碑刻集,共收录了166通碑刻与1块木牌。
恭城,地处广西东北部,位于南岭西段,“介于荆楚”,“为楚南紧相接壤之境,气候恒燠,地介五岭之间,峰峦回合”(光绪《恭城县志》卷四《气候》)。“峰峦回合”指恭城东、西、北三面峰峦迭嶂,其东部为都庞岭南段的花山山脉,北部为都庞岭中段的两支脉,西部为海洋山南段山脉。峰峦中间为河谷、平地、丘陵交错地带,茶江纵贯县境,形成一条南北走向的河谷走廊,境内水系支流纵横密布,通过官民修筑堰坝而形成良好的水利灌溉系统,河流沿岸的小冲积平地土质肥沃,农业相对发达,民众“资生以耕,耕之外无他业”(光绪《恭城县志》卷四《风俗志》)。
与南岭地区一些州县相比,恭城立县的历史比较久远,可上溯至隋末唐初,但其历史文献记载并不丰富,碑刻资料则可稍稍弥补这一缺憾。恭城建县时间,一说乃隋末萧铣所置,一说在唐武德四年(621),199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恭城县原有行政区域设置恭城瑶族自治县。毋庸置疑,在中国历史的大舞台上,恭城并不起眼,官修史书中也没有浓墨重彩。只有在唐宋以来的全国总志、《广西通志》、《平乐府志》,以及正史、实录、政书、文集、档案等文献资料上,留下了恭城历史的些许纪录。恭城县志的修纂则始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重修于天启年间,清康熙年间两次补修。由于“旧乘烬于兵燹”,如今仅流传有光绪《恭城县志》与民国《恭城县志》两部志书。或许已有文献可以勾画出恭城地域的历史轮廓,但“躯干”不够丰满,“枝叶”也不繁茂,历史本真面貌须进一步廓清,太多历史细节的缺环需要进一步充实。
无疑,这正是近些年来碑刻、简牍、经卷、族谱、契约、科仪书、账本、戏曲、唱本、书信和传说等民间历史文献受到学界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下之新材料”释证、补正、参证“纸上之材料”,已是当今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法门。中国各地旧有及现存大量的碑刻铭文,是历史文献的基本形式之一。古今众多学者已对历代碑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碑铭资料,发表了丰富的学术成果。近些年,学界对广西石刻的整理与研究亦颇有起色,《广西石刻总录辑校》《桂林石刻总录辑校》《灵川历代碑文集》等书陆续出版,为学界提供了可靠的碑刻文本数据。
我们整理的恭城碑刻集共收录了166通碑刻,其中元碑1通,明碑3通,清碑110通,民国碑刻21通,时间不明者28通,附录恭城、阳朔交界山区碑刻3通。本碑刻集具有哪些特点,如何利用这些碑刻,其学术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呢,下面从三个方面略作介绍:
一、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恭城人文蔚起当始于五代末北宋初的周渭。北宋后期,地方官员邹浩在《天與堂记》一文感叹道:“昭州四邑,惟恭城士人最多,合平乐、立山、龙平之数而校焉,曾不足以当其半。自御史周公以来,以力学知名、以决科入仕者,每每不乏。”(《粤西文载》卷三十)遗憾的是,现存宋元时期恭城的文献资料仅此《天與堂记》一篇,保留下的文化遗迹也很少。
就恭城碑刻资料而论,清朝汪森辑录的《粤西文载》与谢启昆编纂的《粤西金石略》二书皆阙载,其中《粤西文载》所录的《天與堂记》是否刻碑尚存疑。清雍正、嘉庆《平乐府志》收录恭城碑文并不多,光绪《恭城县志》也仅收录了七八篇碑文,民国《恭城县志》则专辟“碑铭”一栏,共收录了49篇。当代整理恭城的碑文资料数量也不多,《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料集》仅收录了1篇,《瑶族石刻录》收录了21篇,《恭城瑶族历史资料》收录了7篇,《广西石刻总录辑校》所录恭城碑刻虽有不少,但大都是依据已有成果进行辑校,新增的石刻并不多。
本碑刻集旨在收集整理恭城所存碑刻,保存恭城历史文献资料。因此本集在整理时尽可能完整地照录碑文,录入文字用字遵照原碑用字,不作任何标点。为了更好地保留碑文信息,整理时尽可能完整地记录碑文格式,并按碑文格式排版出版。同时,与以往的资料相比,本集所收录的大部分碑刻都是首次发表,尽可能做到一碑一图,标明来源与存立地点。综合而言,本碑刻集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恭城历史文献内容,可谓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二、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且分布相对密集、时空序列明晰,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恭城地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在本碑刻集中,元碑只有1方,明碑也仅3方,清代与民国碑刻占绝大多数。从碑刻地点分布而言,本集按县城、恭城镇、观音乡、栗木镇、嘉会乡、西岭乡、莲花镇、平安乡顺序进行编排,其中县城、观音、栗木三地皆有四十来方,碑刻较为集中的地点有:县城文、武庙,新、老周渭祠与湖南会馆,栗木镇街及大合村周围,以及观音乡观音河沿岸杨梅、水滨、焦山村等。
本碑刻集涵盖内容非常广泛,类型多样,包括官府告谕、会馆、宗祠、庙宇、会社、田产、合同、墓志、水利、山场诉讼、修路兴学、赋役分摊、合伙置业等内容,兹择要略作介绍:
(一)庙宇碑刻。恭城庙宇很多,除了官方在县城建立的文庙、武庙、周王庙和文昌宫之外,还有百姓在乡村建立的各种庙宇,如周王庙、广福庙、朝水庙、锁水庙、坐山庵、月岩庵、白马庙、高龙庙、福兴庵、观音庙、凌云寺、银山庙、雷王庙等。可见,宗教信仰在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庙宇碑刻记录了这一地区丰富多彩的宗教信仰文化,如信众捐资建庙,捐施田地租银,以及人们为了保证祭祀和演戏的费用而设立的各种会社等信息,如西岭乡周王庙《诚延堂碑》《保安会碑》,观音乡水滨村月岩庵《观音会碑记》、坐山庵《会田碑记》等。
(二)宗族碑刻。清代以后,恭城一些大姓开始修建祠堂、祖墓,制定族规宗派,购置或捐置族田,建立宗族。宗族碑刻记录了这一地区宗族建设、祠堂建造、族规族产、宗族纠纷等情况。如恭城镇庄子埠彭姓宗祠《祠堂规约碑记》《宗祠碑记》,栗木街卢氏宗祠《建造祠堂碑记》,栗木镇碛头村田氏祠堂《鼎建祠堂碑记》等。
(三)会馆碑刻。清代恭城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外地客商纷纷在恭城建立会馆,著名的有湖南会馆、粤东会馆和江西会馆。会馆碑刻记录了外地客商在恭城的活动及其与当地社会的情况,如县城湖南会馆的《宝胜会记》《永新财神会碑记》,现存文庙的《重修粤东会馆碑记》《会馆捐资碑》等。
(四)环境保护碑刻。恭城东部、北部属于南岭山区,为了防止山洪暴发和旱灾,人们十分注意保护水源林木,并向官府请示立碑保护,如观音乡的《六姓封禁神山碑记》《严禁长山场四至碑》,栗木镇的《封禁白马垒山场碑》《封禁栗木白马垒山场告示碑》等,这些碑刻记录了人们为保护水源环境所做的努力。
本碑刻集所收碑刻内容较为丰富、形制多样,而且重要的碑刻一般都安置在城乡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如寺庙、祠堂、神亭等)。这赋予了碑刻在特定空间中的象征性与文字权力,使它们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性建筑。在年复一年的仪式活动中,碑刻成为建构城乡民众历史记忆、凝聚认同意识的凭证。通过深入解读这些分布相对密集、时空序列明晰的碑刻,人们将会更为完整地理解恭城地域社会变迁的历史图景。
三、揭示恭城地域社会历史特点,凸显恭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意义
南岭是我国南方最具地理意义、历史特点与文化特色的内地边缘区域,“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刘志伟先生语,见《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丛书总序)恭城地处南岭都庞岭中南段,也是南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恭城县境内“民戍杂居”“猺獞杂居”,如今汉族、瑶族、壮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如何阐释南岭区域整合的历史结构过程,挖掘恭城地域社会历史特点,也是我们在整理本碑刻集时着力思考与探究的问题。
我们认为,恭城历史是自明以后才逐渐明晰起来的。明初,湖广、广西交界地区的统治秩序尚未稳定,“猺獞”频繁起事,官府征调了湖广等地卫所军,拨发了桂林中、左二卫,还发动当地民众从外地招抚了许多土兵,既有从庆远府招募来的“狼兵”,也有从湖广永州府永明县、广东肇庆府封川县招来的瑶兵等,来到恭城县驻守屯田,添设寨堡,把守隘口,才逐渐稳定了地方局势。
本碑刻集中不少碑刻都追溯到明初这一政治背景。如西岭乡《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记载了明初七姓良瑶来到恭城屯守山隘的过程,“之因洪武下山,景太元年润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贼首退散,给赏良猺把手山隘口,开垦山场,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口”。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今恭城镇同乐洲韦氏《重修延祥祖庙》记曰:“尝谓祖原系庆远府河池州宜山县,祖祭延祥古庙,于洪武年间照招祖前到茶城,镇守隘口,惩静地方宁息。”同治三年(1864),今栗木镇源头村上源头韦氏《始建宗祠碑记》亦记曰:“我鼻祖考韦讳公对,原系本省庆远府河池州人氏,自大明洪武十六年与弟公员、公德奉旨从总戎张指挥并廖公洞、蒙公改、石公禄、王明显等,带领兵勇来永明、恭城与灌阳三县地方,将群丑剿灭殆尽。”我们或可对这些碑刻所追溯的历史真实性存疑,但据此重建这些声音背后的历史情境却是可行的。
入清以后,碑刻集中官府告谕、山林纠纷诉讼、赋役合同、宗族建设、族群身份、祖先故事、祠庙会社等内容持续增多。这可透视出,随着恭城人地资源的日趋紧张,地方主导力量及其抗争者,以及湖南、广东客商等外来力量对山地资源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争夺过程中各自采取了不同策略,而官府是他们竞相藉助的重要力量。恭城山地社会内部不同姓氏以及同姓各房支之间的关系由此趋向紧张,原有地方社会秩序逐渐发生裂变或重新整合,这以观音乡平川源上、下五排尤为典型。不同族群于是塑造出不同版本的祖先故事,除了栗木镇周氏、卢氏与欧阳氏等声称宋元时即已迁居恭城外,大多数祖先故事的始迁祖都是明以后到来的,如观音乡水滨蒋家“祖籍山东青州府乐安县”,栗木镇上枧村潘氏“原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红桥村人”等。居住在平地的汉人、壮人多创立祠堂、建设宗族,来提升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而山地瑶人则多通过建造神庙,甚至虚构一个汉人祖先或攀附千家峒、珠玑巷传说,来凝聚族群意识与加强族群认同。
兹举观音乡狮塘村的《鼎建杨氏宗祠碑记》为例,这块碑刻讲的是一个盘姓改为杨姓的故事。他们声称其祖先本姓杨,原籍湖北武昌,后南逃至永州府,洪武年间来到平川源定居改姓盘,此后“其子若孙竟忘其乃祖为杨姓者”。直至清末民初,族内前辈庆兰叔公到湖北访问道友,竟由道友告知其先祖姓杨。庆兰公回家后翻出数页旧草谱,于是便确认其祖先姓杨,其族人“莫不欢欣鼓舞”。这个故事与其他地方家族用占卜方法确定祖籍一样神奇,至于他们为何改姓,是真正的追宗溯源还是出于某种现实考虑,背后的历史逻辑则须回到地方社会内在脉络中才能理解。
当然,也不应忘记县城中的地方官员们,恭城文庙、武庙及周王庙中的大量碑刻提醒我们,地方官府从明后期积极倡行地方文教,修缮文庙、协天祠与周渭祠,推广文昌、关帝、周渭等正统信仰,崇尚儒学教化,设立社学,从而使得更多瑶民逐渐向化。至清光绪年间,恭城县内“东、北两乡诸猺咸编户受约束,委顺服从,尽皆纳税,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惟西乡之大源、小源、高界三猺,虽经编户,而花衣短裙,俗未变更,尚俟化导耳。”(光绪《恭城县志》卷四《猺獞》)至民国年间,恭城的少数民族“竟与汉族同化,或有过之无不及焉”,民国《恭城县志》卷一《民族》记载曰:“明末清初之时,恭城猺獞獐叛复无常,语言各异,即起居、饮食、衣服及冠、婚、丧、祭等等,亦远逊于汉族。自势江源设立舍学,而诸猺獞之藏焉、修焉、游焉、息焉,遂代有入胶庠而食廪饩,今则学校林立矣,且有出外求学,出外从戎,竟与汉族同化,或有过之无不及焉。”
关于明清时期恭城地域整体史的变迁脉络,本碑刻集还不足以全面揭示,但依然可由此找寻到历史的一些轨迹与多元面相,并形成这样的认识:边缘族群的华夏化并非仅仅来自朝廷自上而下的文化教化或武力征服,他们基于自身环境而进行主动的文化创造应是华夏化的内在动力。本集所收录的碑文,或许还可以让我们把目光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转到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上,从人的行为及其交往关系出发去研究历史,去倾听这些边缘人群的声音,从而为阐释恭城边缘族群如何融汇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一些思考。
上述内容简要地介绍了本碑刻集的三个特点,也包含了我们整理时迸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为学术同行利用本书时提供一点参考,读者亦可从不同学科、视角发现兴趣点与问题。限于时间与精力,我们还有些碑文未能及时放入本集,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继续调查与整理,走遍恭城山山水水,增添补充更多碑文。(刘志伟主编,邓永飞、江田祥、杜树海、莫纪德整理辑录:《广西恭城碑刻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Seek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Group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Edge Areas of China——An Introduction to A Collection of Guangxi Gongcheng Stone Inscriptions
Jiang Tianxiang,Deng Yongfei,Du Shuhai
(1.School of History,Culture&Tour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1,China; 2.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s one of the series of Nanl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A Collection of Guangxi Gongcheng Stone Inscriptions”provides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for the academic circles,not rich but credible.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book:first,having the precious valu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second,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the social changes in Gongcheng;third,revealing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ongcheng and highlight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Gongcheng in China.
"A Collection of Guangxi Gongcheng Stone Inscriptions”;groups of people living in the edge areas;multi-dimensional body
K29
A
1001-7070(2016)06-0009-03
(责任编辑:韦国友)
2016-10-10
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承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项目协作研究金计划“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研究成果。
江田祥(1981-),男,江西贵溪人,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邓永飞(1973-),男,湖南永州人,历史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杜树海(1981-),男,四川南充人,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