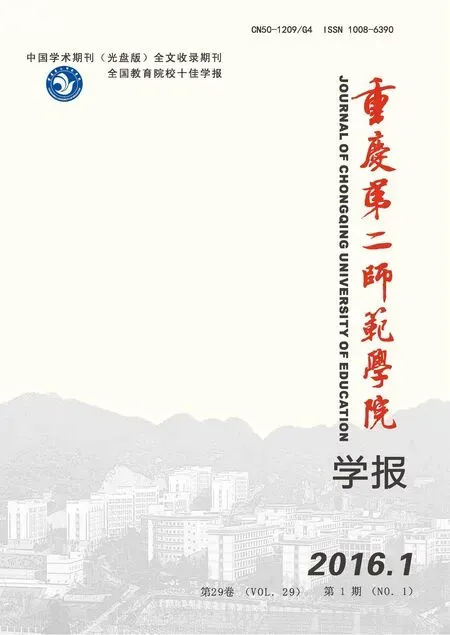从“逃避”到“认同”:《桑尼的布鲁斯曲》之人物形象和成长主题解读
曹小伟,程明亮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从“逃避”到“认同”:《桑尼的布鲁斯曲》之人物形象和成长主题解读
曹小伟,程明亮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
摘要:通过解读小说中“我”和弟弟桑尼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分析“我”对桑尼痴迷布鲁斯曲从反对到理解的态度转变过程,揭示“我”对黑人文化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从“逃避”到“认同”的曲折历程。
关键词:桑尼的布鲁斯曲;人物形象;成长主题;身份认同
一、引言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是美国杰出的黑人作家之一,在小说、戏剧和散文方面著作颇丰,共著有六部长篇小说,四部剧本以及十余部散文集,与拉尔夫·埃利森和理查德·赖特并称为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作家三巨头”。他自称“看透宗教的虚伪”(王家湘,2005)[1],认为宗教是用来奴役黑人的。他的人生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的主题上,如反对种族歧视,争取黑人解放和自由平等,呼吁黑人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批判宗教的虚伪性等等。鲍德温的经典短篇小说《桑尼的布鲁斯曲》正是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
詹姆斯·鲍德温认为,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中,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一种“难言之痛”。小说的核心矛盾在于桑尼对布鲁斯音乐的迷恋和“我”认为成为黑人音乐家是不务正业的表现,后来“我”认识到桑尼对布鲁斯音乐的痴迷其实是对美国黑人文化传统的坚守。“我”对黑人音乐的认识经历了从文化身份的迷失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并最终摆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实现了自我成长。此外,鲍德温有意识地将黑人音乐融入到作品中,视其为“揭示黑人复杂人性,悲惨经历和历史变迁的重要手段”(王家湘,2005)[1]。关于鲍德温的创作技巧,马科斯·克莱恩(Marcus Klein)曾指出《桑尼的布鲁斯曲》虽未能将布鲁斯音乐翻译成小说,但是却达到了鲍德温的创作目的[2],即表明布鲁斯音乐是黑人民族思想和感情的载体。本文通过解读《桑尼的布鲁斯曲》中“我”和弟弟桑尼两个鲜明人物形象,以揭示“我”对黑人文化身份的认识经历了从“逃避”到“认同”的曲折过程。
二、主要人物形象解读
《桑尼的布鲁斯曲》从第一人称视角“我”讲述了“我”和弟弟桑尼之间因不同的人生观而产生隔阂的故事。小说将插叙和倒叙交织在一起,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两类黑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我”受到白人文化的侵蚀,盲目摒弃黑人文化和身份,希望被美国主流文化接纳,最终成为一名中学老师,过上了稳定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我”变得安于现状,刻意逃避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公正待遇这一悲惨现实,从“他者”的视角来观察黑人同胞所遭受的不幸[3]。弟弟桑尼却与“我”截然相反,他不满种族歧视的社会现实,无法逃脱黑人悲惨历史的阴影,看透了白人社会的虚伪,这都表现出桑尼的反叛精神。之前他为了逃避毒品而参加了海军,海军退役之后发现哈莱姆地区依然如故,终因参与买卖和吸食毒品而被捕入狱,这触动了“我”内心积存的“坚冰”。出狱之后,黑人音乐成为了他发泄情感,唤醒黑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的途径。和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我”知道了酷爱音乐的叔叔是如何惨死在一群白人醉鬼的车轮之下,而且“如今的世道并没有改变”,因此母亲始终放心不下弟弟桑尼。最后,在“我”真正融入到桑尼的世界中,“我”才逐渐理解了弟弟桑尼对布鲁斯音乐的痴迷是对黑人文化身份的一种坚守与认同,“我”与桑尼之间的矛盾与隔阂涣然冰释。与此同时,“我”也不断走向成熟,认识到以布鲁斯音乐为代表的黑人传统文化是黑人民族生存的希望,也是寻找“黑人性”的根本途径。本部分将着重分析“我”务实的人生态度和对黑人同胞的怜悯之情以及桑尼的反叛和执着精神,以服务于美国黑人文化身份认同这一主题的呈现。
(一)叙述者“我”
在小说的开头,叙述者“我”难以相信弟弟桑尼因买卖和吸食海洛因被捕入狱这一事实,因为“我”始终认为桑尼不仅是一个“好孩子”,而且“有头脑”,同时,我也“害怕”桑尼会同哈莱姆地区其他孩子一样沾染毒品,最终一生碌碌无为。细读文本,很容易注意到这一细节:当最后一节的下课铃响后,“我”发现“我浑身湿透”,如同“穿着衣服洗了桑拿浴”。表面上,可能是由于劳累以致汗水将衣服浸湿,但实则可能是由于“我”的精神过于紧张,一则担心弟弟被捕入狱,二则担忧整个黑人青年群体的命运。尽管我和弟弟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分歧,但这一细节足以折射出“我”对弟弟桑尼前途的担忧和兄长般的爱意。
“我”在回家途中,遇到了桑尼的朋友,文中并没有具体透露他的名字。尽管他已经成人了,却仍旧穿得破破烂烂,每天好几个小时都在街区之间游荡,浑浑噩噩。他每次都能编造一个极好的理由向“我”要钱,“我”也毫不吝啬地满足他的要求,却“不知道到底为何这样做?”一次遇见他,因他看“我”时“像狗一样或是狡猾的眼神”而突然憎恨他,但和他一路聊天到最后分开时,“我”心中突然有一种“东西喷涌而出”,与此同时,“我”也突然变得不再恨他,并且“哭得像个小孩”。[4]“我”通过迎合美国主流文化而暂时逃离了哈莱姆地区,谋得一份稳定安逸的教师职业,但哈莱姆地区却丝毫没有发生变化,依旧破败并处处“充满隐蔽的威胁性”。“我”和桑尼朋友的交流以及对他的态度前后出现的巨大反差,刻画出哈莱姆地区黑人青年悲惨的生活状况,也流露出“我”对自己同胞的深切怜悯和关心。
在母亲葬礼后,“我”和弟弟桑尼坐在“空荡荡的厨房”。“我”尝试问他将来的打算,他说想成为音乐家。在我意识中,“成为鼓手适合于其他人而不是我的弟弟桑尼”,因为“我”始终认为“爵士乐手就是父亲所说的那些好吃懒做的人”[4],最重要的是,将来很难靠音乐谋生。于是“我”劝他道:“桑尼,你知道,人总不能顺着性子来做事”“你已经成人了,应该开始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了”。[4]从这些话语中,“我”务实的人生态度以及“我”对黑人音乐不屑一顾的神情暴露无遗。因此,读者不难体会为何“我”难以理解桑尼痴迷黑人音乐的真实原因。“我从没正眼看过爵士乐,也从来没有人叫我去欣赏黑人音乐”[4],这种对黑人音乐表现出务实和不屑一顾的态度折射出“我”忘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想要通过逃避黑人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融入到白人主流社会。但是这一努力却是徒然的,这可以从母亲讲述酷爱音乐的叔叔是如何惨死在一群白人醉鬼的车轮之下得到体现。在桑尼的眼中,三个小女孩所唱的“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使他想到了“咖啡因在血管里时”给人的感觉,忽冷忽热,感觉到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一样”[4]。从小就在教堂布道的鲍德温看透了宗教的虚伪,认为宗教是用来奴役黑人的,而不能给黑人的悲惨处境带来任何变化。因此,“我”却不认同弟弟的看法,认为他的那些朋友都“飞快地堕落了”[4],这同时折射出“我”想刻意“逃避”黑人的文化身份,与弟弟桑尼的坚守自己黑人文化身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二)“反叛”而执着的弟弟桑尼
桑尼本是个寡言少语的孩子,但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人生道路的坚守和对黑人音乐的痴迷。
一方面,他能够听从自己内心而不是屈从于残酷的现实,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在母亲葬礼后,桑尼在回答关于未来工作打算时,曾说:“我认为人们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不然活着还有什么意思?”[4]这与“我”安于现状,追求安逸人生形成鲜明的比照。他对黑人音乐的痴迷和执着也表露出其对人生追求的真性情,并且这种对本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性是值得称赞的。另一方面,他在敢于为自己的音乐梦而舍弃其他东西时表现出来的反叛性却是有消极意义的。在弟弟想退学去参加海军时,“我”曾告诫他“你一定是疯了,傻瓜,你到底为何要参加海军?如果你想成为音乐家,在军队里面你又怎么学习?”但桑尼却回应说“反正我去学校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且我厌倦了这些臭气熏天的垃圾桶”。[4]最终桑尼还是不辞而别参加了海军。从桑尼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反叛之心。
另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去参军的时候,桑尼勉强在嫂子伊莎贝拉家安顿下来。他可以在钢琴前呆上整整一天,直到大家都睡了,才停下来。伊莎贝拉甚至觉得自己“就如同和声音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一个人。而她理解不了这种声音”,“桑尼就和上帝或魔鬼一样”。[4]桑尼对音乐痴迷似乎是对精神压抑的一种释放,而他对音乐的执着在“我”看来是不理智甚至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在桑尼入海军服役归来之后,发现哈莱姆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黑人音乐就成了桑尼逃离令人窒息的哈莱姆地区、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在“我”观看了他的一次音乐表演并且真正地融入黑人群体之中后,“我”才意识到桑尼对布鲁斯音乐的痴迷和执着其实是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从“逃避”到“认同”——“我”的成长主题的呈现
巴赫金曾指出,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根本动力[5]。莫迪凯·马科斯曾经将成长小说分为两类:一是年轻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过程,另一种是对自我身份与价值的认识,并不断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6]。在《桑尼的布鲁斯曲》中,从“我”试图“逃避”黑人文化身份到认识黑人音乐是“黑人性”的典型代表,突出地反映了“我”经历了从文化身份迷失的困惑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折射出了“我”的曲折成长历程。本部分将从布鲁斯曲和小说中的文学意象来详细解读,分析《桑尼的布鲁斯曲》是如何呈现“我”的成长主题的,即“我”对黑人音乐这一代表黑人文化身份事物的艰难的再认识过程。
深入了解布鲁斯音乐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对理解《桑尼的布鲁斯曲》中“我”的成长主题的呈现大有裨益。从词源学上讲,布鲁斯源于英语词汇“蓝色的恶魔”(blue devils),意为悲哀和痛苦。布鲁斯音乐成型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是一种由美国黑人创造,用以排解生活苦闷和思乡之苦的民间音乐演唱形式,源于黑奴的劳动歌曲、灵歌和田间号子。由于其悲怆和忧伤的音调,布鲁斯音乐也称作蓝调。作为美国的“民族记忆”,布鲁斯音乐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延伸和美国黑人悲惨经历的见证,而且包含着生存哲理和“文学潜能”。由于布鲁斯音乐自身凝聚着非裔美国黑人的精髓与精神沉淀,很多黑人作家,如拉尔夫·埃里森、兰斯顿·休斯、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盖尔·琼斯等渐渐发现了布鲁斯音乐中的文学潜能,纷纷在其文学创作中添加了布鲁斯音乐元素,成为一种借助音乐抒情来表现黑人情感的文学叙事手法。布鲁斯音乐是一种传递文化信息的符号语言,因此被看作是对美国非裔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象征。布鲁斯音乐成为黑人抒发内心情感和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利器,其忧伤的旋律可以传达出美国黑人坎坷的生活经历,抵抗种族歧视的努力以及如拉尔夫·埃里森所谓一种“超越苦难的生存哲理”[7]。在《桑尼的布鲁斯曲》中,“我”对布鲁斯曲漠然的态度以及“我”通过各种努力搬出哈莱姆地区,都可以映射出“我”背离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身份。此外,弟弟桑尼对黑人音乐的痴迷在“我”看来是“难以被人接受”和不务正业的表现。在“我”受桑尼邀请去观看了他的表演并且真正融入到黑人群体中后,才发现布鲁斯音乐竟然与“我”产生了共鸣。“我”把酒吧描述成了“桑尼的世界,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王国”,认为“桑尼的血管里毫无疑问有着贵族的血统”。“我”开始把黑人音乐看作“黑暗”中的光明,认识到克里奥尔并没有让弟弟桑尼“陷入困境”而是在祝福他成功。通过“我”对周围环境和切身感受的刻画,“我”真正地找到自己的“黑人性”,并且这种特征不会因为刻意地逃避而消失。作为黑人音乐的典型代表,布鲁斯曲能够给予美国黑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情感和情感依附,堪称是他们的情感纽带。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哈莱姆地区黑人的生活处境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有任何改观,这使得“我”和桑尼痛心疾首。同时,桑尼也只能把热爱黑人音乐当作逃离哈莱姆地区现实生活的一种方式。深受桑尼音乐表演触动之后,“我”将黑人的麻烦描绘成“比天还高”,而且还意识到黑人“如同饥饿的猛虎一样”[4],向往的自由近在咫尺。而黑人音乐能够帮“我们”实现这种自由,只要“我们”乐意倾听。这里的潜文本其实是强调,只有美国黑人从真正意义上认同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才能增强种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实现“与白人种族分庭抗礼”。整个小说以“我”和弟弟桑尼之间的故事为主要线索,以“我”深刻理解了布鲁斯音乐这一代表黑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事物的真正含义为主旨,凸显“我”从“逃避”到“认同”本民族文化的曲折成长历程。
此外,文学意象对“我”的成长主题的呈现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从报纸上得知弟弟桑尼因吸食毒品而被捕入狱的消息后,感觉到“我被困在陷阱之中,外面的黑暗呼啸而过”。在哈莱姆地区,吸食毒品和酗酒成为黑人青年走向堕落的最主要方式。这里“我”对弟弟桑尼被捕入狱的担心其实也暗指了“我”对黑人青年自甘堕落这一现象的深深关切。同时,通过形象地描写我听到消息时的感受,使读者深刻感受到了因黑人在美国社会遭受到的严重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带来的压抑感。“冰”这一意象在小说中总共出现了三次,而“冰”在文中象征着“我”内心深处对生活中的苦难、威胁和不安全的恐惧和逃避。“我”从“他者”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黑人的生活境况,而强烈感受到内心积存的“坚冰”也在暗指“我”开始认识到作为黑人群体中的一员,虽然通过努力逃离了哈莱姆地区,但是黑人遭受到的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仍然会像“坚冰”一样积存在我的内心。重要的是,“我”似乎在试图说明“逃避”自己的“黑人性”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黑人社会地位低下的问题。此外,在小说的开始,鲍德温使用了两个隐喻“现实可能性的天花板”[1]和“两种黑暗(一是生活中的黑暗,这种黑暗处处笼罩着他们;二是电影的黑暗,这种黑暗是他们对生活的黑暗视而不见)”[4]来表现黑人青年的生活境遇。尽管“我”与弟弟桑尼在人生道路选择上存在分歧,但都试图通过逃离哈莱姆地区来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这种“逃避”并不会切实改变黑人的生活处境以及作为黑人的典型民族特征。虽然“我”暂时逃离了黑人区并臆想逃避黑人的文化身份,但小说中使用大量的文学意象和修辞手法反映出“我”深刻关切美国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文学意象对整篇小说表现“我”的成长主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我”从刻意“逃避”到“认同”黑人文化身份的成长历程。
四、结语
作为鲍德温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桑尼的布鲁斯曲》表面上讲述“我”与弟弟桑尼在人生道路上的分歧,实则为了凸显一些美国黑人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困惑这一深刻主题。本文主要解读了叙述者“我”和“反叛”而执着的桑尼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以及“我”对弟弟桑尼痴迷布鲁斯曲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理解的曲折过程,从而揭示出“我”曲折的成长之路,即“我”经历了从文化身份迷失的困惑到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并最终摆脱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实现了自我成长。布鲁斯音乐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同时,鲍德温还意识到了黑人音乐的“文学潜能”,并成功地将其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走出了自然主义对抗文学的窠臼,这对黑人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参考文献:
[1]王家湘.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2]宓芬芳,谭惠娟.黑人音乐成就黑人文学——论布鲁斯音乐与詹姆斯·鲍德温的《索尼的布鲁斯》[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4):51-57.
[3]谷启楠.一曲强劲的黑人觉醒之歌——论《桑尼的布鲁斯曲》的深刻内涵[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5):67-70.
[4]Baldwin, James. Sonny’s Blues[M]//George L McMichae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5]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Mordecai Marcus.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J]. Journal of Aesthetics & Art Criticism, 1960, 19(2).
[7]Jerry Gafio Watts. Heroism and the Black Intellectuals: Ralph Ellison,Politics,and Afro-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M].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
[责任编辑亦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6)01-0093-04
作者简介:曹小伟(1989- ),女,河南信阳人,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英语);程明亮(1990- ),男,山西长治人,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