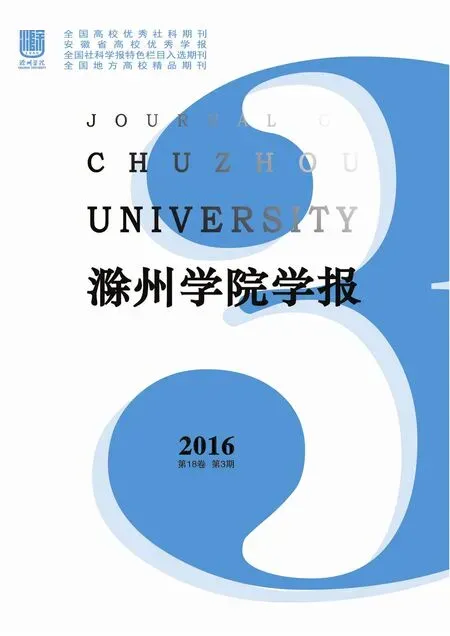“微缩社会”的人间万象
——从《深深的河流》看秘鲁二十世纪社会面貌
谷 音
“微缩社会”的人间万象
——从《深深的河流》看秘鲁二十世纪社会面貌
谷音
摘要:《深深的河流》是秘鲁“新土著主义”小说家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将秘鲁山区的一所教会学校构建成一个虚拟的“微缩社会”,通过描绘教会学校中暴力横行、种族歧视等各种乱象,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秘鲁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通过塑造主人公的典型形象表达了其社会变革的积极愿望。
关键词: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深深的河流》;微缩社会
乌拉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里奥·贝内特帝(Mario Benedetti, 1920-2009)曾评价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创造一个“微缩社会”,以反映发生在“宏观社会”的现实问题具有更高的叙事效率。[1]的确,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使叙述的过程更加凝练,主旨的表达更加形象。在颇具代表性的秘鲁小说——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深深的河流》中,作者通过刻画教会学校这一“微缩社会”的乱象,表达了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黑暗面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来自秘鲁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学生在这封闭的空间里共生共存,他们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念和思维相互碰撞冲突,使得矛盾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积聚而爆发,达到了很强的艺术效果。
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José María Arguedas, 1911-1969)是秘鲁“新土著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杰出的人类学家,对秘鲁文坛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代表作有《水》、《深深的河流》、《所有的血》、《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等。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凡以印第安人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均称“土著小说”。[2]但阿尔格达斯认为前人的这类作品都没能真正体现出印第安人的精神本质和文化精髓。他采用一种深入印第安人内心世界的独特视角描绘他们的生活,探讨印第安克丘亚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作用而产生的“文化移植”或“文化渗透”(transculturación),并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剥削印第安人的抗议。因此有人认为印第安人真正进入秘鲁文学是从阿尔格达斯开始的。《深深的河流》被评论界认为是阿尔格达斯的巅峰作品。在这部自传体小说中,他首次成功地运用了克丘亚语与西班牙语相结合的新语言风格,从形式和内容上均有创新。小说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安第斯山区中南部城镇阿班凯,围绕小主人公埃内斯托离开父亲,在寄宿学校中的生活展开:为了逃离校园里充斥着的各种暴力和种族歧视事件,敏感而内心丰富的埃内斯托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和善良的印第安人那里寻求慰藉,排遣远离父亲的孤寂感;而与印第安人结下的友谊使他认为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最后他决定捍卫印第安人的权利,支持他们为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奋起抗争。小说以教会学校这样一个“微缩社会”为切入点,描绘了校园里充斥着的恃强凌弱和种族歧视等人间乱象,较深入地揭露了秘鲁社会的黑暗面。
一、教会与军队和贵族阶层结为联盟,控制着世俗社会
由于历史原因,教会和军队一直是控制拉美社会的两股强大势力。他们共生联合维持着整个社会的既有秩序。这种同盟关系可以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时期:当哥伦布踏上新大陆的土地后,西班牙军队和天主教会分别拿着枪杆、福音书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殖民征服与传教活动。 这种现象并没有随着西班牙殖民的倒台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至今。早期教会更是秘鲁教育事业的创办者:“殖民统治期间,尽管有宗教裁判所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阻碍,文化的传播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宗教和贵族的属性。教育和文化的资源集中在教会手中。天主教修士们对总督管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传播福音和打击异教徒,而且还致力于教授技艺、农事等。在总督辖区还是一片穷乡僻壤之时,教士们在这里创立了美洲的第一所大学……”[3]141。
《深深的河流》中刻画的教会学校正体现了天主教会在世俗生活里的支配地位。作者着力刻画了一位统治阶级压迫力量的代言人——神父林那莱斯。教师的父权属性和神父这一最为接近上帝的身份使他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村镇里都具有天然的权威。当时秘鲁落后的山区封建庄园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印第安人多沦为雇农或佣工,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神父时常用宗教作为工具与乡绅贵族等权力阶层拉近关系,为其剥削压迫印第安人保驾护航。在布道时他评价庄园主是国家的基础、社会财富的栋梁,赞扬他们对宗教的虔诚。而对位居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则鼓吹顺从与忍让,强制他们皈依天主教,主张他们平静地生活并在卑微的工作中度过一生。主人公埃内斯托的伯父唐马努埃尔是个大庄园主,代表着陈旧腐朽的大庄园经济制度。他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对印第安佣人和雇农极其苛刻吝啬。而神父却十分认同和推崇唐马努埃尔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严格而又宽厚,是个伟大的天主教徒”。并禁止埃内斯托和印第安人往来,命令他要服从庄园“工作、沉默和虔诚”的纪律。此外,神父还经常利用讲道的机会表达他对邻国智利强烈的仇恨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向学生灌输复仇的使命:
“神父开始布道时总是轻柔缓和的。他用动人的话语颂扬圣母玛利亚的美德,他的声音是那样和谐和柔软。但是很快开始情绪激愤。他仇恨智利,并总能找到恰当的方式将谈话主题从宗教引向对国家和英雄的赞美。宣扬未来对智利开战。号召青年儿童做好准备,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职责是达成复仇的使命。提及庄园主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精心维护祭坛,强制印第安人忏悔、受圣餐、平静地结婚生活并在卑微的工作中度过一生。最后再次放低声音,诵读耶稣受难的某一篇章。”[4]204
在神父的“爱国主义”言论煽动下,学生之间常开展一种带有军事色彩的游戏:学生被分为“秘鲁人”和“智利人”两派进行格斗,只有看到“秘鲁人”取得胜利神父才会露出满意的笑容。小说的最后,当奇恰酒娘起义,将偷来的食盐分给贫苦的印第安人时,神父更是明确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坚决地站在军队的一边,支持对起义者的镇压。他严厉地谴责她们是十恶不赦小偷,并以上帝的名义为军队的权威护道,颂扬将军的“慷慨、节制和正直”,认为军队“履行了他的职责惩罚了过错的一方,给城市带来了安宁”。不仅如此,当得知埃内斯托在起义中追随了奇恰酒娘,神父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狠狠地用皮鞭抽打小主人公作为惩罚。作为库斯科最神圣的演说者和精通数学和西班牙语的老师,他用娴熟的演讲技艺,怂恿温顺的印第安人交出他们得到的食盐。与此同时,军队进驻城市追击起义的奇恰酒娘。因此再一次印证了教会和军队这一自古形成的“神圣同盟”。
二、暴力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元素
与天主教宣扬的爱与忍耐相违背的是,《深深的河流》所描绘的教会学校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恰恰是对秘鲁社会现实的忠实反映。多夫曼(Ariel Dorfman)在其文学评论《美洲幻想与暴力》中指出,暴力是拉丁美洲的根本性问题,它已成为人存在的本身,因此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个问题。不向暴力投降要么意味着死亡或失去生存的尊严,要么意味着放弃与同类的接触:“我就是暴力的,我从内心感受到它的存在,它已成为了我的个性……”[5]根据多夫曼的分类,在这部小说中存在两种形式的暴力——纵向的暴力和横向的暴力。纵向暴力是指自上而下实施的暴力行为:小主人公埃内斯托因为追随起义的奇恰酒娘而遭到神父的鞭打作为惩戒;米盖尔兄长因为受到两名学生的冲撞,把他们打到浑身是血,并命令他们在地上爬行。而“横向暴力”则存在于同级别的群体之间:学生间打架斗殴、以强凌弱的暴力事件更是无处不在。在这遵循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学生中“强者”和“弱者”的形象形成强烈的对比。学生自行推选出身强力壮的学员去欺负弱小的学生。莱拉斯便是其中“强者”的代表,他因为功课落后而留级了三年,却仗着年龄和体格的优势经常寻衅滋事,几乎欺负过学校所有的同学,甚至打败了村镇里前来挑战的年轻人。与之相反,学校里最胆小害羞的学生是帕拉西奥斯,一名来自印第安村落说不好西班牙语的学生,时常被其他同学看不起。一次他被同学要求与痴呆的厨娘欧帕发生性关系,这噩梦般的经历让他越发胆小怕事,从此不敢正眼看任何人。厨娘欧帕更是沦为学生泄欲的工具,最终被学生佩鲁贾在学校的庭院中强暴。这样的性暴力更是令人不寒而栗。
三、种族主义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
种族主义同样是拉丁美洲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在殖民时期,印第安人遭到了西班牙殖民者的野蛮虐杀和残酷剥削,面临几近灭亡的悲惨命运;独立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土著居民仍旧是二等公民,受到白人不公正的对待。由于历史、政治、地理条件等原因,秘鲁这片曾孕育出古老繁荣的印加文明的土地是一个沿海与内陆、白人与土著种族对立并存的二元社会。马里亚太基将秘鲁划分为三个地区:沿海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以及丛林地区:“丛林地区从社会经济的方面来说仍缺乏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沿海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确实是两个在领土、人口等方面相区别与分离的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是印第安文化聚集的区域,而沿海地区是西班牙或混血人种文化占优势的区域”。[3]167-168因此,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既相互交融产生“文化移植”的繁荣局面,同时又激化了种族主义的社会矛盾。
《深深的河流》中的教会学校位于发展相对落后、印第安人聚居的山区。因此,当来自发达沿海的少校的儿子出现在这所山区学校时引起了一阵骚动。他显得气质非凡与众不同,很快成为了其他学生的领袖,却又同时遭众人嫉妒。巴尔加斯·略萨在其关于阿尔格达斯的著作《古老的乌托邦: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和土著主义小说》中指出:“种族主义在阿班凯是无处不在的:白人瞧不起印第安人和美斯蒂索人②,美斯蒂索人看不起印第安人的同时又对白人暗暗抱有一种不满。他们所有人——白人、印第安人和美斯蒂索人,都歧视黑人”。[6]在《深深的河流》中,“乔洛人”“印第安人”是一种对非白种人的侮辱性称呼,其中暗含其为劣等种族的含义。在奇恰酒娘爆发起义之后,学校的孩子们有一次针对这次事件的争论,其中一个学生辩道:“我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也要骑在印第安人头上……”。[4]328而黑人作为社会的最底层,是最为人唾弃的一个群体。教会学校的黑人牧师米盖尔兄长被莱拉斯等人咒骂为“该死的黑鬼”“肮脏的黑人”。他们宁愿逃离学校也不愿意向其道歉。这种对黑人的憎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即使是对印第安人充满同情和爱的主人公埃内斯托也疑惑,为何身为黑人的米盖尔兄长能做完美的布道。
四、社会阶层间的巨大鸿沟加深了阶级矛盾
除了种族主义以外,拉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和隔阂也在小说中有所体现。在《深深的河流》中,教会学校里的学生几乎囊括了秘鲁社会的所有阶层:帕拉西奥斯来自山区的印第安村落;佩鲁贾是理发师的儿子,属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安特罗是庄园主的儿子;赫拉尔多来自沿海地区,是司令官的儿子……小说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对立以主人公埃内斯托、安特罗和赫拉尔多的关系为代表。尽管埃内斯托的父亲是一名白人律师,但他自小在印第安仆人的照料下长大,对下层人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以自己属于印第安人的群体感到自豪。一开始安特罗带来了安第斯山区的传统游戏——陀螺,并把它赠送给了埃内斯托,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并且二人都反对莱拉斯的暴力行为,惺惺相惜。可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二人逐渐因为对雇农的态度而产生嫌隙。在奇恰酒娘的起义中,埃内斯托站在奇恰酒娘这一边,而安特罗则支持庄园主对奇恰酒娘的镇压。埃内斯托为向来温顺驯服的雇农们终于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而欢欣雀跃,而这正是安特罗所担心害怕的,他表示会毫不犹豫的杀了这些起义者。他对埃内斯托说道:“对印第安人应该紧紧地捆住他们。你不会明白的,因为你不是庄园主”。[4]328他的态度让埃内斯托大为震惊。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分歧来自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属性。二人自此渐行渐远,但他们关系的彻底决裂是因为安特罗和赫拉尔多交上了朋友,并且跟他学会了轻视女性等一系列恶习。埃内斯托愤怒地将作为友谊见证的陀螺还给了安特罗,这段友谊最终画上了句号。而安特罗和赫拉尔多,大庄园主和军队司令官的儿子的友谊,更从某种意义上象征了秘鲁这两个压迫阶层的联合。
《深深的河流》中,阿尔格达斯通过刻画教会学校这一“微缩社会”折射出整个秘鲁大社会中的各种乱象:教会学校里道貌岸然的神父利用天主教教义归化印第安人,煽动学生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与权贵和军队沆瀣一气;看似乖巧的学生们暗地里打架斗殴、拉帮结派,与我们想象中天真无邪的孩童世界有着天壤之别,这正是秘鲁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隐喻。然而,作者在鞭挞社会黑暗和不公的同时,也寄托了自己改变世界的乐观主义态度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在污浊的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的小主人公埃内斯托和奇恰酒娘是富有反抗精神的,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奋起反抗;他们代表了力求改变的新生力量,是秘鲁社会的希望。总之,《深深的河流》是一部社会批判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伟大作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
[注释]
①1879年至1883年,智利同秘鲁、玻利维亚争夺南太平洋沿岸硝石、鸟粪产地阿塔卡马沙漠,爆发南美太平洋战争,又称硝石战争、鸟粪战争,最终智利获胜。此战过后,秘鲁与智利在签订了《安孔条约》,将塔拉帕卡省割让给智利,并将塔克纳和阿里卡两地区交给智利管辖10年;而玻利维亚则失去出海口,成为内陆国,严重阻碍了其经济发展。
②Mestizo,即白人与美洲土著的混血人种,又称乔洛人。
[参考文献]
[1]Benedetti, Mario. "Vargas Llosa y su perfil escándalo". Letras del continente mestizo [M]. Montevideo: Arca Editorial S.R.L., 1969: 241.
[2]赵德明,赵振江,孙成敖,段若川.拉丁美洲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67.
[3]Mariátegui, José Carlos. Siete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 [M].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S. A., 1976.
[4]Arguedas, José María. Los ríos profundos [M]. Madrid: Ediciones Cátedra, 2012.
[5]Dorfman, Ariel. Imaginación y violencia en América [M]. Barcelona: Editorial Anagrama, 1972: 15.
[6]Vargas Llosa, Mario, La utopía arcaica, José María Arguedas y las ficciones del indigenismo [M]. Madrid: Santillana Ediciones Generales, S. L., 2008: 222.
责任编辑:李应青
The microcosms in Deep Rivers of José María Arguedas——On the social conflicts of Peru in the 20th Century
Gu Yin
Abstract:Deep Rivers is the masterpiece of José María Arguedas, Neo-indigenism writer from Peru. In the novel the catholic boarding school is presented as a virtual microcosms that faithfully reproduce the social conflicts of Peru in the 20th century, such as the violence, the racism, etc.; meanwhile the author expresses his good will of social changes by creating some typical main characters.
Key words:Deep Rivers; microcosms; social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794(2016)03-0038-04
作者简介:谷音,上海大学外语学院教师,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拉美文学 (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ZZSD15058)
收稿日期:2016-01-09
——玛利亚·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