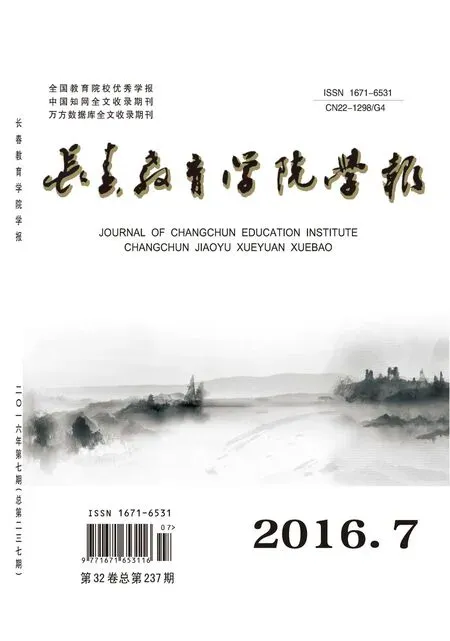论儿童幸福与儿童权利*
刘英
论儿童幸福与儿童权利*
刘英
摘要:在由成人主宰的世界,成人文化占据了主流,这在某种程度上压抑着儿童的文化,剥夺着儿童的权利,这种情况下,儿童幸福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从幸福的含义入手解读儿童的幸福,从成人对儿童权利剥夺的角度分析影响儿童幸福的原因,探寻还给儿童游戏的权利,保障真实快乐和给予对话交往的权利是儿童通向幸福之路的途径。
关键词:儿童的幸福;成人文化;儿童权利
刘英/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贵州贵阳550018)。
优质的教育在于创造幸福,优质的生命在于创造幸福并享受幸福,二者是人的义务,同时也是人的权利,幸福建立在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基础之上。人总是希望自己或亲人能够接受教育、创造幸福,并拥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因此,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在为追求幸福而努力。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由成人主宰,成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标准、思维方式居于主导,成人文化在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儿童的权益时刻处于被成人所忽视和剥夺的危险之中。当一个生命体的权利被剥夺,只剩下一个虚壳,他还幸福吗?什么是幸福?儿童的幸福又是什么?在成人文化居于主流的社会,儿童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还是在追求成人所认同的幸福?如何才能让儿童幸福?
一、对儿童幸福的阐释
幸福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每个时期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价值取向形成对幸福的认识。克利伯里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1],他探讨了自由与幸福的关系,认为自由是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亚里士多德提出“幸福为心灵的活动”[2],他认为幸福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而马克思则认为幸福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条件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感受和理解到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3],他把幸福同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劳动创造联系在一起,提出了科学的幸福观。在这些对“幸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幸福”至少应该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自身重大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其二是重大需要和欲望满足后给自身带来的快乐心理体验;其三,幸福以自由为条件。
儿童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其身心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幸福理解的单纯化、简单化与具体化。儿童的幸福是什么?在他们看来,幸福就是“妈妈买了好吃的给我”“带我去公园玩”“与小朋友一起做游戏”“老师表扬我,我很开心”“到外面滑滑梯”等等。尽管从表面上看,儿童对幸福的理解是感性的、粗浅的,但仔细分析,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已经接触到幸福的本质,“好吃的”是对物质需要的满足;“开心”是一种快乐的心理体验;“玩”“游戏”“到外面滑滑梯”则是对自由的追求。因此,儿童的幸福应该是以自由为条件,以精神创造为基础,对物质需要、精神需要以及人际需要得以适当满足的一种心理体验。
二、儿童是否幸福
当谈及儿童是否幸福的问题时,多数人常常默契地达成一种共识:“当今的儿童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想吃啥有啥,想买啥咱就给买啥”“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玩具就有几箱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成人的文化中,儿童的幸福就是对物质生活的享受与满足,幸福与拥有物质相等同。然而,在儿童的世界,拥有物质就幸福吗?显然,根据对“儿童幸福”内涵的阐释,满足物质需要还不足以说明儿童是幸福的。
那么,儿童自由吗?在幼儿园我们经常可以听见这样的话语,“小手手放腿上,小眼睛看黑板”“一二三,看谁坐得端又端”“谁能像我这样做”“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也经常看见幼儿就连上厕所、喝水这样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也要向老师汇报等等。幼儿园教师用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标准束缚着幼儿身体活动的自由、言语的自由,以及满足生理需要的基本自由。在家中家长也常这样告诉孩子“不许出去玩,外面车多”“练完钢琴才可以玩”……在家长的看管下,儿童失去自由游戏的权利。在社区,林立着高楼大厦,大厦之间是装饰性的亭阁小溪,之外是车来车往,儿童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看来,儿童的生活受制于成人世界的约束,并没有自由。
儿童快乐吗?学英语、练钢琴、练书法、练舞蹈……兴趣班不是幼儿的兴趣班,而成为强制班,家长常陪同幼儿从一个兴趣班出来,又匆匆进入另一个兴趣班,没有兴趣的孩子筋疲力尽,培养孩子兴趣的家长则焦头烂额。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一个没有游戏的孩子,一个被抹杀了天性的孩子快乐吗?另外,家长疲于工作,很少有时间主动与幼儿交流;幼儿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太少,又缺少交往的伙伴,每日与电视、电子游戏相伴,没有伙伴的儿童快乐吗?在幼儿园,儿童的游戏往往是教学式的,教师为了吸引幼儿注意,将游戏作为完成教学任务的辅助手段,儿童丧失了游戏的自主权,没有游戏的童年快乐吗?
幸福需要物质生活的满足,需要快乐的心理体验,需要自由的生活。不自由、不快乐,儿童还幸福吗?那么儿童的幸福去哪儿了?是谁剥夺了儿童通向幸福之路的权利?
三、谁剥夺了儿童幸福的权利
儿童本应该是幸福的,因为他从来到人世就从周围吸取材料,开始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他们用材料造就未来的人。对儿童来说,不受任何阻碍地投入到自己的创造活动之中,并在创造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积极的、快乐的心理感受,就获得了最大的幸福。然而,儿童并不幸福,因为创造活动总是不断地受到成人世界的阻挡,成人剥夺了儿童通向幸福之路的权利。
(一)成人剥夺了儿童游戏的权利
《儿童权利宣言》指出:“儿童应有游戏和娱乐的机会,应使游戏和娱乐达到与教育相同的目的;社会和公众事务当局应尽力设法使儿童得享此种权利。”由此可见,游戏是儿童的一种权利。享受游戏权利的过程应该是愉悦的过程,也是幼儿主动构建精神世界的过程,游戏是孩子童年幸福的源泉,如果剥夺了其游戏的权利,也就破坏了他们童年的幸福。然而,成人是社会的主流,成人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儿童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成人文化支配儿童文化。因此,成人总是以建立在自己规定的价值、理念和标准之上的文化去施予儿童以爱,在这一点上,他们就像儿童一样似乎还没有摆脱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他们以种种理由限制儿童游戏,并相信儿童会因此而幸福,迫使儿童在成人的施加下筋疲力尽,在没有“剩余精力”的情况下,儿童逐渐远离了游戏。实际上,这种凌驾于儿童之上的做法正是对儿童游戏权利的隐性剥夺,儿童为此所追求的幸福是成人认为的幸福,它并不属于儿童。游戏是儿童的生活,对儿童游戏权利的剥夺即是对儿童生存需要的剥夺,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儿童何来幸福。
儿童的幸福潜藏在儿童自己的文化中。这种文化的精神实质就是游戏精神,即“一种自由想象和创造的精神,一种平等的精神,一种过程本身就是结果的非功利精神”[4]。这种游戏精神贯穿于儿童的一日生活,贯穿于儿童的所有活动,在自由的游戏过程中主动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是儿童幸福所在,因为这种幸福是非功利性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
(二)成人剥夺了儿童交往与对话的权利
交往与对话是人类充分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同时也是通向幸福之路的条件。儿童作为精神独立的个体,需要在与伙伴、成人的社会性交往和对话中获得发展,因为在这种真实的对话与交往情境中儿童可以感受到被关注和理解,同时获得宣泄自我、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机会,从而获得一种愉快的心理体验和精神享受。然而,在充斥着成人文化的世界里,成人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一方面使成人盲目地让儿童以学为主,他们每天像一根上了发条的机器,不停地忙碌,减少了与同伴对话和交往的时间;另一方面,家长、教师忙于自己的事情,很少有时间与儿童交流,也很少关注孩子的感受,倾听孩子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孩子大部分时间与没有生命的机器相伴,或玩电游或看电视。此外,成人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感无形中影响到孩子间的亲密感,“出去玩,被人骗走……”“下次他(她)打你,你就给我狠狠打他(她)”。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在的,成人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儿童人际交往的需要,使儿童再次丧失体会幸福的资格。
四、如何让儿童幸福
儿童的幸福与成人的文化世界紧密相连,正是由于成人对儿童世界的干预使儿童没有充分感受到幸福。成人应该把握好儿童幸福的内涵,理解、接纳儿童的文化,给予儿童在自己的文化里充分自由表现的机会,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化,还其应有之权利。任何无视儿童文化的存在,时时处处以成人的文化标准来要求儿童,对儿童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此,成人应该协调好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保证儿童权利与幸福的关键。
(一)还给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
儿童文化的核心是游戏精神,因此,保证儿童的游戏精神,给幼儿以自由和平游戏的权利是正视儿童文化,使儿童享有幸福的最基本条件之一。自由应该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状态”,正如儿童游戏一样,没有外界势力的阻碍才是真正的游戏,才能充分发挥儿童游戏的精神,为儿童本性和潜能的实现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因此,没有自由,儿童很难获得高度的幸福体验,一切违背儿童成长内在力量的、外在强加的活动对儿童来说均无幸福可言。
(二)保证儿童真实快乐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依成人的价值标准判断,儿童总是“快乐的天使”,然而这是一种“伪快乐”。成人总是错误地将物质条件的满足作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你考一百分,我就带你去儿童乐园”“好好表现的小朋友,听话的小朋友,老师就奖励他一朵小红花”,儿童的快乐是有条件的,要获得这种快乐就要牺牲本应该自然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成人对儿童廉价的许诺,然后儿童为快乐而努力,结果却常常是努力了也并不快乐;即便成人兑现了对儿童的许诺,儿童的快乐也如昙花一现,怒放片刻很快凋谢。真正的快乐,应该是儿童内在的需要参与其中的,是儿童发自内心的一种由里至外散发出的快乐,这种快乐既刻在脸上,也在写在心里。
(三)给予儿童交往与对话的权利
雅斯贝尔斯认为:“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我只有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才能存在着。”[5]在对话和交往中,儿童能够拓展社会学习经验,习得交往技能,克服自我中心,实现个性、社会性的和谐发展,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儿童要成为一个有幸福体验的主体,成人应该抛弃急功近利的追求,给儿童交往与对话的机会和权利,同时给予关注和指导,帮助他们提高人际交往的技能,促进个体社会化。比如,抽出时间与孩子谈心,更好地了解孩子的精神世界以及学习与发展状况,这比一份考试成绩单更能了解孩子;陪孩子亲近大自然或访亲串友,这可能比一个科学活动或一节社会性教育课更生动。所以,作为成人如何看待儿童的生活,如何看待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作用,事关儿童的幸福,可以说,今天儿童的幸福取决于成人,而非儿童自己。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35.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64.
[3]唐凯麟.简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316.
[4]边霞.论儿童文化的基本特征[J].学前教育研究,2000(1):16.
[5]涂成林.现象学——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M].广州:广东出版社,1998:91.
责任编辑:贺正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531(2016)07-0075-03
*基金项目:贵州省第二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贵州师范学院学前教育专业)(黔教高发<2013>446号);卓越教师教育人才培养计划(黔教高发<2014>37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