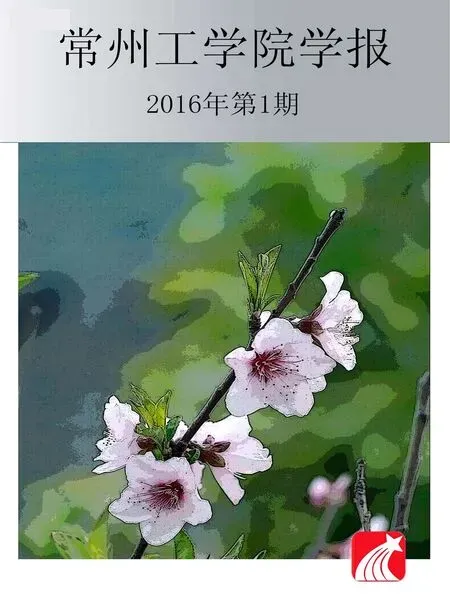郑板桥咏竹诗文的生态解读
彭庭松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浙江临安311300)
郑板桥咏竹诗文的生态解读
彭庭松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浙江临安311300)
摘要:郑板桥咏竹诗文富于生态精神,表现为有呈现心统万象的真气、映射理想人格的真意、洋溢世俗情味的真趣,折射出郑板桥为人的真性情。咏竹诗文重视对“生”态的描摹与表现。通过动态变化写自然轨迹,描绘生命的活跃神采,构筑“生”态意境,赋予“生”态人文精神,郑板桥鲜明的创作个性因此彰显。郑板桥仁人爱民,深具民胞物与的生态情怀,这使得他体察竹性竹情,向自然学习写竹之法,因而在艺术上取得较高成就。
关键词:郑板桥;咏竹;诗文;生态
郑板桥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诗、书、画号为“三绝”。他一生酷爱竹,留下了很多竹画和咏竹诗文。以今人眼光观之,他的咏竹诗文中蕴含有生态情怀和旨趣,体现了传统的生态智慧。从生态的角度对其咏竹诗文进行解读,不失为一项饶有新意和趣味的工作。
一
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里,真是价值论中最核心的特征之一。儒家伦理要求做人须真、善、美统一,将真放在首位,将正心诚意置于修身的最前端。道家认为大道本真,真受命于天,是不可改变的“性”,真实自然庶几成为最高美学法则。佛家也要明真心见真性,以真如求真谛,不欺神明不欺己。这种文化反映在创作中,就要求言为心声,情与景不隔,意与境融合。
读郑板桥作品,没有人不为其真率坦诚的表达而震撼。张维屏在《松轩随笔》说:“板桥大令有三绝:曰画,曰书,曰诗。三绝之中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此评论切中肯綮。郑板桥的咏竹诗文,可谓真气酣畅,真意弥满,真趣淋漓。
郑板桥“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题画竹》),从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除了表现竹子的真态外,还要写出其真气,将竹子的艺术生态完美呈现。在郑板桥的笔下,竹子有清气,“清香一片萧萧竹,里面阶层终绝尘”(《题画竹》);有野气,“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栽”(《题画竹》);有寒气,“从今不复画芳兰,但写萧萧竹韵寒”(《题画竹》);有狂气,“扫云扫雾真吾事,岂惜区区扫地埃”(《题画竹》);有灵气,“闲写湘筠个个灵,萧疏清韵玉珑玲”(《题兰竹》)。天地之气生万物,四时之法成众相,竹在天地四时作用下可谓气象万千。竹子的真气离不开心气的观照表现。郑板桥胸次开阔,真率灵动,境界直通宇宙人生,得心应手顺乎道,因而竹之气象生态才能真实、真切呈现在艺术王国里。
郑板桥善于在日常细微处寻找艺术创作灵感。他在《竹》中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枝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画意”不只是创作冲动,当然有借物写意的更高需求。何谓“意”,《说文解字》云:“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可见“意”是心志意图在形象基础上的理智表达。郑板桥表达了对竹君子节操的肯定与赞美,《竹石》云“不须日报平安,高节清风曾见”,《题兰竹石》云“满堂皆君子之风,万古对青苍翠色”,这正是作者人格理想的写真写意。而《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云“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则写出了不合时宜的孤傲与愤意。《竹》诗云“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则表达了守节自赏、远避世俗的清静雅意。借物抒情,托物言意,是我国古老的创作方法。郑板桥将真我与“此君”相知相契,满纸洋溢的是忘言的真意。
郑板桥画竹追求根于世俗的真趣。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矜持,他独钟于人间的活泼情趣。郑板桥认为画要雅俗共赏,为此他对有人刻意避俗不以为然。他旗帜鲜明,认为“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在练习过程中,要破除先问雅俗的成见,因为“技艺只分高下,不别雅俗”(《再复文弟》)。他的笔端总将那些竹看成寻常百姓,时常鼓舞着欢趣与机趣。“山僧爱我画,画竹满其欲,落笔饷我脆萝卜”(《题画竹》),萝卜换画,俗中有雅,率真情趣可爱至极;“邻家种修竹,时复过墙来,一片青葱色,居然为我栽”(《题画竹》),不烦动手,便得悦目,透露的是“捡便宜卖乖”的谐趣;“新栽瘦竹小园中,石上凄凄三两丛。竹又不高峰又矮,大都谦退是家风”(《题画竹》),将竹看成是自己的孩子,既像安慰,又像鼓励,亲切又风趣。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才是真实的社会生态。
创作中的真,是与为人的真辩证统一的。郑板桥是性情中人,《清史》本传云其“性落拓不羁”,《扬州府志》云其“有奇才,性旷达,不拘小节”。苏东坡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1]以此来看,二人有着高度的相似。郑板桥一生经历了卖画为生到科举入仕再到卖画为生的过程,一路走来从不委屈自己,嬉笑怒骂任由性,心系民生名利轻,所以在官场只能是个难以见容的异类。他为穷人画画可以分文不取,但对于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他也就用不着虚伪矫饰了。他曾自定“润格”,明码标价,“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并在文后附诗一首:“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板桥润格》)如此真率直爽,爱憎分明,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对他的耿介为人肃然起敬。“抽毫先得性情真,画到功夫自有神”(《题兰竹》),这一夫子自道,正好为“心声心画”“文如其人”的传统艺术观作了很好的注脚。
二
中国生态哲学历来重视探讨万物生成、生命状态和生态价值。有学者认为,“‘生’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2]。郑板桥特别重视对“生”态的描摹与表现,本质上与生态精神是相通的。
郑板桥的《题兰竹石》俨然是一篇艺术创作大纲。文中云:
盖竹之体,瘦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
要画好竹子,“神”“生”“节”“品”四因素缺一不可,亦不可分割视之,四者构成了一体天成的和谐境界。
在动态中见“生”态,捕捉变化中的轨迹,这是郑板桥创作的重要手法。将事物的动态予以准确传神表现,这其实是体察大道的方式。郑板桥尽管也静观竹子,写他们的清姿逸态,但即使这样,也还是能静中见动。如《题画竹》云:“茅屋一间,新篁数竿,雪白纸窗,微浸绿色。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此处描写的环境确实幽静,然作者盼友论艺的心显然是欲静还动的。在摹写动态时,郑板桥尽量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文学笔法来为竹写生。有直笔正写,如“春雷一夜打新篁,解箨抽梢万尺长”(《为无方上人写竹》);有虚拟想象,如“竹里秋风应更多,打窗敲户影婆娑”(《题画竹》);有高下对比,如“两支修竹出重霄,几叶新篁倒挂梢”(《题画竹》);有物我并绘,如“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栽”(《题画竹》)。读其文字,想见其驱遣丹青时的潇洒灵动和酣畅淋漓,一定会是如其所言,“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乱兰乱竹乱石与汪希林》)。
描绘生命的活跃神采,构筑“生”态意境,这是郑板桥创作品位的重要体现。郑板桥认为创作的秘诀应是“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题画竹》),“活”与“生”同义,“生”的最佳状态是富于活力。对于写竹而言,活力的极致呈现状态是“怒”,因此,“古人以喜气写兰,怒气写竹。盖物之至情,专以意似,不在形求”(《兰竹》)。他对自己所画劲竹有力扫千军之势不无自豪,曰:“板桥之无成竹,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盖大化之流行,其道如是。”(《题画文》)正是站在体物达道的高度,郑板桥赋予笔下的竹子以无限力量和活力,这与传统文人画路数两样。“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题画竹》),不仅写出了饱满的活力,而且让人体会到一种敢于向强大恶势力挑战的豪情。“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竹石》),更是写出了身处逆境不肯低头的倔强生态,其精神至今鼓舞着咬紧牙关奋斗的人们。其全部咏竹诗文,都是在为秀劲的竹子写生画像,也是刚直不折的士大夫的传神写照。
以强烈的主观情态贯注,使“生”态更富于人文精神,这是郑板桥鲜明个性的彰显。眼中有竹,心底有人,无往不在皆是情,郑板桥以其接地气的深厚情感在艺术创作中渗入人文关怀,别开生面。“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3],心中有了丰沛的感情,才不得不发而为文。郑板桥这种因情而造文的写作态度,使得作品充溢人情味。“满砚冰花三寸结,为君图写旧清风”(《题画竹》),这是怀旧之情;“万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韬光庵为松岳上人作画》),这是自勉之情;“饮得西江一杯水,如今清趣满林遮”(《题南园丛竹图留别质田先生四弟芸亭先生二首》),这是赏识之情;“好待来年新笋发,满林清绿翠云湾”(《题画竹》),这是展望之情;“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题画竹》),这是鼓励之情;“墨竹一枝酬远意,江南风景近如何”(《题兰竹》),这是牵挂之情;“瑟瑟萧萧风雨夜,赏音谁是个中人”(《题兰竹》),这是落寞之情;“若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出纸一竿》),这是愤慨之情;等等。郑板桥的创作自畅其性情,艺术个性璀璨夺目。
郑板桥宣示:“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他的咏竹诗文正实践了这一主张。文字动若风过竹林,神韵有如竹竿凌霄,情怀正似雨后春笋,郑板桥的诗文如同竹画一样,神完气足,生机盎然。艺术精神和生态精神完美结合,他的作品正像那常青竹,给人以光景常新的享受。
三
朱熹《仁说》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以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人能善待自然,在于他本身有一颗仁爱之心,并能将光辉扩展到宇宙一切。天地万物一体为仁,这是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孜孜以求的境界。
郑板桥是个有仁爱之心的清官。他推崇杜甫,所作诗文,“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板桥自叙》)。他不屑于做一个孤芳自赏的文人画家,公开宣称“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勒秋田索画》),这也是他竹画为何总多民间情、人间味的主要原因。以此标准,他表达了对王维和赵孟頫的强烈不满,他指责说:“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五书》)
郑板桥深知民生艰难,因此一有机会做官,就会将百姓冷暖记挂在心。他曾作《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著名的诗,将风吹竹响疑为百姓疾苦声,并告诫为官者时刻不忘体察民情,爱民之心有如天地日月。他最后丢官,也是因为开仓放粮拯救饥民而得罪了上司。据《清代学者像传》记载,“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人民记住了这位正直廉洁的父母官,这也给了他以极大的安慰。艺术家和大众站在一起,才会如竹靠青山,踏实安稳。在这点上,中西是相通的。西方画家凡高曾说过:“从对普通人的爱之中,不仅找到某种可供画画的东西,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给自己以安慰和恢复元气。”[4]在告老还乡时,郑板桥作《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其中表白了已尽心力、问心无愧的心迹,也写出了心无挂碍、两袖清风归去来的潇洒。
对人有仁爱恻隐之心,必推广到自然万事万物中去,这就是儒家所言的天下之仁。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西铭》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对于这一著名命题,郑板桥深表赞同。他在《题画竹》中写道:“《西铭》原有说,万物总同胞。”“民胞物与”说承认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人与自然是平等一体,自然与我不可二分。
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说道:“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在郑板桥看来,竹就是性情所钟,灵气所在。竹是天生知音,总能在心灵的天地中保持默契。《题竹》云“一峰石,六竿竹。倚行窗,对华屋。半清淡,陪相读”,此为君子之交;《题竹石》云“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此又似夫妻与共;《题画》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竿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此像是长幼情深——感恩老一辈的扶持,展望新一辈的强大,意切切,情殷殷。
人心通于自然,才会像诗人描述的那样,“我们个体之心灵是宇宙之心保持和谐颤动的琴弦”[5]。郑板桥正是有一颗与自然情投意合的心,所以他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宗法自然。他在画竹时,总是在不断揣摩竹情竹性,力主画出天然之态和原本性情。只有亲竹近竹,才能画出灵竹活竹,因此最好的老师是自然之竹,而不是画匠们的纸上之竹。他在《题画竹》中坦承:“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后园竹十万个,皆吾师也,复何师乎?”。掌握了自然之道,加之勤学苦练,他的竹画日臻化境,达到纵横自如的境界。所以他自信地说:“画兰画竹已多年,竖抹横涂总自然。”(《兰竹石三首》其一)不管是眼中竹、胸中竹还是手中竹,最后都得与自然竹神韵生机冥合,郑板桥在他的诗文中都在反复陈说这个道理。
郑板桥的笔墨充溢着对生命关怀的仁爱之心,竹与人一样,都在生生不息的仁德之道中运行。“竹劲兰芳性自然,南山石块更遒坚”(《题兰竹石》),郑板桥在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中,致力于实现人性与物性的自然统一。无论是真实性情的展露,还是生命活力的张扬,都饱含着仁效天地的生态情怀。“本是同根复同气,有何卑下有何高?”,回味郑板桥《题画竹》中的这两句,更激发了我们内心的生态悲悯。只有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自负,生态文明才会有乐观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G].北京:中华书局,1962:33.
[2]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
[3]龙必锟.文心雕龙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83.
[4]平野.凡高:插图本书信体自传[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401-402.
[5]刘湛秋.泰戈尔文集:IV[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50.
责任编辑:赵青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1-0021-04
基金项目:2013—2015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生态文明制度研究”创新项目子课题(stcx009);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项目(205512000109)
作者简介:彭庭松(1971—),男,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5-07-28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