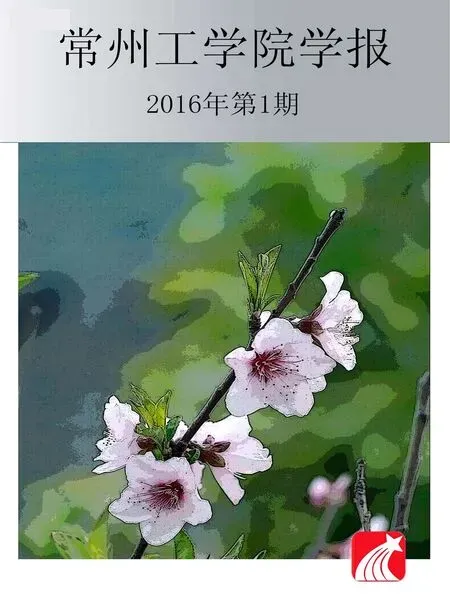由《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孤独”
王悦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由《一句顶一万句》看“中国式孤独”
王悦华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反映了千百年来被人忽视的“中国式孤独”,文章试图通过作家的创作个性以及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特点总结出刘震云笔下“中国式孤独”的基本内涵。结合小说文本分析“中国式孤独”的文本表现、形成原因和研究意义,以期对国民精神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中国式孤独;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
引言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1]自面世以来一直深受学界好评,尤其是小说中描写的中国式的孤独体验更是万众瞩目,雷达这样评价小说文本表现的孤独感:“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2]随后涌现的对这种“中国式孤独”的研究不乏佳作,例如《千年孤独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3]、《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4]、《找寻那触动心神的一颤——浅析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己意识》[5]等等,这些研究对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孤独”体验都做了有理有据的梳理,也谈及了重要关键词,如中国、语言、知己,这种“孤独”的产生原因和具体表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作为工具和知己作为对象的沟通也的确能有效地缓解这种“孤独”,但是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依然没有准确定义刘震云笔下“中国式孤独”的含义和特点,在成因方面也缺乏深入客观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式孤独”是产生在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中,对自我认知产生困惑的情感体验,基于此,笔者将结合文本,探究刘震云笔下“中国式孤独”的表现、成因和研究意义,以期对国民精神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一、“中国式孤独”的基本内涵
“中国”“语言”“知己”这些关键词是对“中国式孤独”表层内涵的挖掘,而其深层内涵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的挤压下对自我认知产生困惑的情感体验。
外国文学中很早就有对孤独的讨论,卡夫卡通过对土地测量员、公司小职员等“边缘人”形象的刻画来表达孤独的自己,在他看来个体与世界完全对立,每个人都孤独、绝望地生活在异化扭曲的世界中,纵观他的生平和写作,性格和生活压力可能是造成他精神孤独的主要原因;麦卡勒斯笔下的孤独主题同时关乎肉体和灵魂,从爱到恨,从生到死,孤独和灵与肉的纠葛浑然一体,这某种程度上是她独特的人生的感悟而形成的浓郁又挥散不去的孤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农奴、退休公务员等小人物的孤独往往是在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产生的,带有无法挣脱的悲剧色彩,这样的写作主题可能是由俄国的历史和作者的个人经历共同作用形成……可以说,外国文学作品中孤独的人是多阶层的,甚至是以底层小人物为主要构成。这样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方的价值体系中个人处于主导地位,对个体的关注是丰富而深刻的;其次心理学在19世纪末的西方成立,也进一步帮助人们更加理性地认识这种神秘的心理体验。
而中国文学中虽然也有不少对孤独的提及,但这种孤独的表达是不完整的。《观沧海》中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未尝不是政治家面对理想形单影只的孤独;“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实质是陈子昂怀才不遇、对知己的渴求之情;鲁迅的孤独是他的独醒和依旧昏沉的社会之间的对立;《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细腻的女性孤独实际上是丁玲在先进的自我与社会对抗中落败之后难以言说的孤独感……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学中对孤独的表达大多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
文学作品中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孤独表达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更准确有效地认识普通国民的精神和心理,而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创造性地将对孤独的审视视角从知识分子移向了以普通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孟繁华曾高度评价刘震云的作家身份,他认为:“在当下中国作家中,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有想法’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想法’包含着追求、目标、方向、对文学的自我理解和要求,当然也包含着他理解生活和处理小说的能力和方法。”[6]刘震云从早期作品《瓜地一夜》到成名作《一地鸡毛》和后来的《手机》《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等长篇小说,都选择以民间为叙事立场,描写底层人民的悲喜生活和人性善恶,致力于对“人的困境”的理解和刻画。所以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对孤独的表达也是立足于民间,真实地表达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更具有代表性的孤独感。
在前人的研究中对“语言”和“知己”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沟通对于孤独感的产生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对沟通的渴求本质上是对自我认知的渴求,孤独感的产生更深层意义上是自我认知产生了问题。“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具体形态之一,孤独意识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7],用经常词不达意的汉语作为交流工具的沟通是很难准确和深刻的,加之中国社会关系具有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是很难形成的,这就导致了孤独的产生。而中国人自我观的核心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常常通过社会对自我的评断来定位和认识自我,这一点孙隆基在其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在中国“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即“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8]。在缺乏深度沟通的情况下,这种有关自我认知的社会对应关系必然受到影响,进而自我认知步入瓶颈,所以,“中国式孤独”在中国民众中大范围产生和长时间存留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对自我认知的困惑。而这样的产生原因也让“中国式孤独”作为中国国民精神状态的一部分更具有了中国的特色和研究的意义。
二、“中国式孤独”在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文本表现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结构创新、人物个性分明、社会关系复杂,在这里,“中国式孤独”被作者极力放大并精彩演绎。
首先,刘震云笔下的“中国式孤独”存在模糊性,是难以名状和难以准确将其定位的。老蔡把老裴在家里挨她骂的情形说给外人听,“但这话传到老裴耳朵里,老裴又装作没听见”[1]12;老汪在讲解《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时候,“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1]26;牛爱国到咸阳找姥爷吴摩西给母亲曹青娥留一句话却未果,半夜睡不着在院中大槐树下看到的“一个大月亮,缺了半边,顶头在半空中”[1]356。老裴的沉默、老汪的伤感、牛爱国的思念,这些难以捕捉、难以名状的感受可以说都是“中国式孤独”,它们虽然鲜明又强烈,却又难以表达。
其次,刘震云想要表现的是,“中国式孤独”具有普遍性,并且强力解构了以天伦和人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关系。“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五伦(父子、君臣、兄弟、夫妇、朋友)在某种程度上锁定了整个社会关系。‘五伦’之中的父子、兄弟是家族血缘关系,属天伦;君臣、朋友是社会伦理关系,属人伦;夫妇则是生理性的男女关系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的同一,介于天伦与人伦之间”[9],天伦和人伦奠定的中国社会关系在面对“中国式孤独”时被彻底解构,传统的天伦和人伦根本无法缓解或者拯救这种孤独,小说中用“说得着”来表示人与人之间可以进行深度的交流进而缓解人际交往中的孤独感,反之就是“说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五伦被简化成“说得着”与“说不着”,也就是能否进行深度的交流,对应的社会关系能否有助于自我认知的建构。以主人公杨百顺的社会关系为例,就天伦而言,杨百顺和父亲老杨、兄弟杨百业、杨百利都说不着,老杨喜欢的卖豆腐、打鼓他都不喜欢,对父亲的印象是“过去他也知道他爹不是东西,没想到他这么不是东西”[1]45。兄弟们也与他志趣不投,以至于他16岁离家至死未回,小说中只依稀提及许多年后他与自己的一个孙子罗安江“说得着”,“何玉芬自嫁给罗安江后,就知道罗长礼和老伴说不着,跟儿子们说不着,跟儿媳们说不着,孙子辈中,跟其他人也说不着,唯独跟罗长礼说得着”[1]353。就人伦而言,杨百顺一辈子结交了许多所谓朋友,却只有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和他有过心灵相通的感觉,老詹留下的教堂图纸背后有“恶魔的私语”五个字,虽然说不清楚,但看了图纸和字让杨百顺(此时已改名为吴摩西)觉得“老詹的这种感觉,倒和吴摩西心中从没想到的某种感觉,突然有些相通”[1]178,可笑的是,此时老詹已经去世,而老詹生前,吴摩西是和他说不着的。而夫妻关系作为延续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关系纽带,本该是相互陪伴拯救孤独的,而在小说中杨百顺和先后两位妻子都说不着,小说中这样写他和第一任妻子吴香香的相处:“在外面不会说话还在其次,两人回到家里,不管是发面,或是揉面,或是蒸馒头,吴摩西也皆无话。”[1]160“五伦”被解构之后,社会关系变得尤其简单,作者通过对传统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解构来表达“说不着”是社会关系的常态,而“说得着”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些伦理关系构成了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维系社会稳定运转的纽带,但它们却依然拯救不了甚至触及不了蔓延在中国大众之间的孤独感。
最后,《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中国式孤独”具有顽固性,几乎是无法排遣的。这种顽固性在小说中具体有两种表现。第一是消解这种孤独的途径极其脆弱,吴摩西和巧玲说得着,而巧玲却转眼就丢了;吴摩西心里终于有了来自老詹的一道亮,老詹却死了。短短五年的分别,各自不同的社会经历就让牛爱国和曾经“说得着”的杜青海“说不着”了;牛爱国二十几年的好朋友因为十斤猪肉闹掰了……可见“说得着”对时间、地点、环境的要求近乎苛刻,而生活又总是充满变数,消解这种孤独的可能变得微乎其微。第二是小说中当这种孤独带来的苦闷不断积累,承受不了的当事人排解的方式总是倾向于毁灭。其一是自杀,老汪在失去女儿之后对东家老范说:“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1]31其二是杀人,曹青娥怀牛书道的孩子去找当年的拖拉机手侯宝山,对同学赵红梅说:“我光想杀人,刀子都准备好了。”[1]267牛爱国知道庞丽娜和小蒋的事情之后,不光想杀庞丽娜,还想杀小蒋的儿子,还想着最后自杀同归于尽。其三是出逃,为了抵抗心底巨大的孤独,老汪走到了宝鸡,吴摩西到了咸阳,牛爱国到了延津。自杀是对自我的毁灭,杀人是对自我社会关系的终结,笔者认为基于中国的自我定义往往依靠社会关系的个人观点,对社会关系的毁灭其实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杀,前述当事人关于杀人之后与受害人“同归于尽”的想法也能很好地验证这观点,而出逃,实质也就是与自己过去的社会关系一刀两断,实质是对旧我的自杀。而这三种方式对“我”的杀害正好也反映了“中国式孤独”产生的深层原因是自我认知的困惑,当当事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时,摧毁自我的意图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而自我的毁灭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消解孤独,吴摩西去了咸阳却依然记挂巧玲一辈子;曹青娥最后没有杀人如愿找到了初恋情人侯宝山,可“曹青娥突然明白,她找的侯宝山,不是这个侯宝山,她要找的侯宝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了”[1]268;牛爱国回了延津感到久违的亲切,却依然要开始新的找寻。而笔者相信,恰恰是“中国式孤独”顽固和不可排遣的特质鼓励学者去不断探求其更深意义的成因和意义。
三、“中国式孤独”的形成分析
“中国式孤独”作为一种国民意义上的精神症候,在经过刘震云富有表现力的表达后,显得尤其生动、复杂,故而随后在考量它的成因时其深刻性也是我们必然会意识到的。
第一,“中国式孤独”的模糊性首先是因为孤独感作为一种心理感受的确是多变、难以描述的;其次是国民本身受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无法对孤独感作出准确的描述和定义,而有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少数群体,又常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10],与民众主体长期脱离,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孤独感得到了恰当的表达而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孤独受到长期忽略的原因。
第二,“中国式孤独”的普遍性主要是因为长久以来传统价值观中对“重群抑己”概念的过度强调形成了国人现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自我观。首先,“重群抑己”的群己观念是几千年来儒释道等各家思想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儒家作为几千年来统治阶级推崇的主流思想,它对“重群抑己”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余英时在谈及传统的群己观念时也肯定了儒家对“重群”观念形成的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更重视群体的秩序,名教纲常便是它在这一方面最极端的表现,而且和儒家结有不解之缘。”[11]而儒家作为统治阶级推崇的思想,对“重群抑己”观念的宣传和强调几乎是极端的,在《中国之伦理精神》一书中,作者甚至直言:“儒家伦理精神是一种群体本位的伦理精神。”[12]几千年来,儒家主要通过推崇“礼”和“仁”来强化对个性的抑制。“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13],儒家通过推广等级森严的“礼”来强化对个体的压抑,加强国家统治;通过“仁”将“礼”的约束内化为为人之德,甚至将传统道德提升到与生命同在的高度,故而个人利益和情感在集体面前常常失去存在的合法性,自我人格的发展受到长期的压抑和打击。其次,由“重群抑己”观念推动形成的中国化的自我观对“中国式孤独”普遍产生起到了直接作用。顾名思义,自我观是人对自己的认识,“自我”是沿用了英文self的翻译,但其实在中国语境之下,自我也就是自己的意思。“自我,又叫自我意识,指个人对自己的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识、情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有关自我的各种思想倾向和行为倾向)”[14],长期受到“重群抑己”价值观的浸染,中国人在对自己进行价值判定或者说身份确认时也难以脱离集体概念,经常需要利用自己与社会群体中人的相互关系来认识和评判自我。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关于“人”的定义方面,中西方的差距在于,新教下产生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只要在褪去社会角色,以自我为“基地”对社会角色做出内省时,自我存在将会显现;而中国恰恰相反,“人”需要在社会关系中成为有人格的自我,自我需要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肯定,才有意义。这样的自我认知方式往往导致在缺乏和人深度沟通的时候,对自我的认知产生严重的问题,“中国式孤独”背后是自我认知问题的精神困境。所以,在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几千年以来,“重群抑己”的价值观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式孤独”的普遍产生,并且具有解构传统伦理精神的表现。
第三,长久以来,中国人有圣贤却无信仰,西方社会的人神关系为所有人提供了倾诉的主,但中国的人人关系却远比人神关系复杂和脆弱,真正意义上的倾诉和交流变得尤其困难,这就导致了“中国式孤独”的顽固性。小说中,老詹在延津几十年只发展了8个教徒,但他依然坚持奔走于传教路上,从未言弃,为何?因为他信主,主能伴他左右,他会灰心、失落但他终究不觉得孤独。“子不语怪、力、乱、神”,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认为“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15],中国人对道德的崇尚实质上是一种人伦理性,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间无疑是对立的,而放弃了与神的交流,也就失去了精神交流最忠诚和永恒的对象,因为人人关系要比人神关系复杂得多,神是不变的,但人却因为环境、身份、经历等等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小说中老詹曾试图将人神关系转化为人人关系来劝杀猪的老曾信主:“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1]95老曾回答:“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1]95幽默却准确地强调了中国社会中人人关系比人神关系复杂得多的观点。
四、“中国式孤独”的研究意义
毫无疑问,刘震云在其作品《一句顶一万句》中对“中国式孤独”的发现和描写是具有极大意义的。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才具有更具说服力的普遍意义上的国人身份,在君主和官吏“务农重本,国之大纲”[16]的政治观念之下,“小农经济”曾作为中国特色化的经济模式长期占据中国历史,农民曾是中国的“全民身份”,刘震云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对国民的精神有更大范围和更深度的理解。
其次,长久以来,大众的孤独感与自觉自知的知识分子的孤独感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弱势的孤独,当知识分子已经可以准确地定位这种感受并且找到原因时,非知识分子作为感受主体很可能对孤独的感受依然难以名状并且为此长期苦恼。而它的普遍性和顽固性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这种深刻却模糊的弱势孤独感从潜藏到显露、从混沌到自觉的过程通过作家的发现在文学上的表现无疑是急需的,“中国式孤独”需要被关注,然后被尽量积极地引导。
最后,当终于有人正视“中国式孤独”,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精神的更深处,必然还有我们未曾挖掘的共性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久地游荡,这就需要我们善于发现和总结,为国民精神和文化的健康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林贤治在谈到民族文化传统时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物质与精神,精神与精神,彼此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即使为了便于观察,使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把每一个别、具体的东西分割开来,也无法消除其中与整体相联系的或明或暗的标志。”[17]笔者深以为是。可想而知,面对“中国式孤独”这样的国民性的精神症候,无论是它的内涵、特点还是形成的原因都必然是极其复杂的,因为它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等方面已经紧密缠绕,难以分割,关于“中国式孤独”的诠释还需不断丰富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雷达.《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EB/OL].(2009-06-12)[2015-10-08].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09/2009-06-12/59293.html.
[3]张晓琴.千年孤独中国经验:论《一句顶一万句》[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2):45-52.
[4]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当代文坛,2010(6):102-104.
[5]李存.找寻那触动心神的一颤:浅析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的知己意识[J].名作欣赏,2010(15):37-40.
[6]孟繁华.“说话”是生活的政治: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09(8):43-45.
[7]田晓明.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孤独意识的哲学理解及其成因、功能分析[J].江海学刊,2005(4):223-229.
[8]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37.
[9]颜琳,刘宝杰.论血缘文化的锁定及其突破:中国传统伦理的近现代转换[J].齐鲁学刊,2012(4):31-34.
[10]刘禹锡.陋室铭[M]//刘禹锡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二卷 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9.
[12]林存阳,刘中建.中国之伦理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1.
[13]王云五,朱经农.礼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35.
[14]汪凤炎,郑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增订本.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71.
[1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6.
[16]房玄龄等.晋书[M].上海:中华书局,1980:1132.
[17]林贤治.中国新诗五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13.
责任编辑:庄亚华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1-0032-05
作者简介:王悦华(1991—),女,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15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