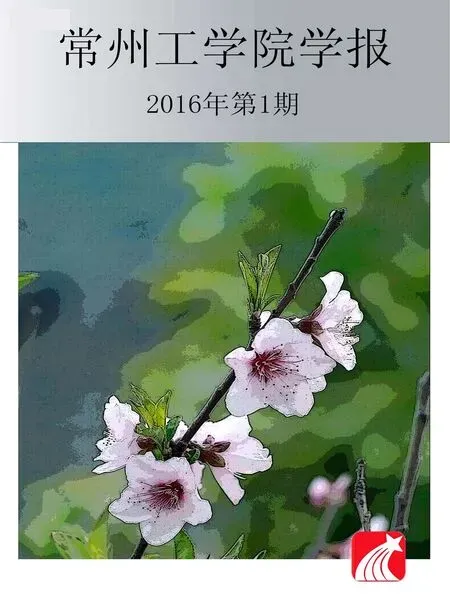论神魔小说中的“识破”观念
张天羽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论神魔小说中的“识破”观念
张天羽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西游记》中石猴对自我的认识与突破,及对其所处社会环境本质关系的探问都是一个“识破”的过程。这一“识破”模式同样存在于其他神魔小说中,以狐怪类小说为例,“识破”是故事叙事的转折点。对“识破”从叙事模式到意识观念的溯源,可以探知这一观念存在于《左传》《山海经》等书中,包涵着上古朴素唯物观和世界观,可以从新的角度理解神魔小说情节结构,把握小说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识破;妖与人;神魔小说
《左传》《山海经》等书中包涵着上古朴素唯物观,先民在解释周遭环境时形成一套认识逻辑,即消灭百兽的前提是要认识百兽万物的真实面目。这一观念在魏晋时被修道文人及道士带入道教书籍及涉道小说,在故事中道士成为关键人物,凡人要认识妖怪及破除妖怪的侵害都必须依靠道士及道术。唐以后,这些神魔小说中,道士及道术的重要性被爱情及其他情欲所替代,作者们通过故事宣传的不仅仅是道教思想,还有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一、何为“识破”
“识破”观念,总的来说,依旧遵循着“问题出现—寻找解决的方法—问题解决”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是小说叙述中的惯用模式。然而之所以还被单独提出来阐述,是因为笔者认为这一观念可以上溯到上古先民的世界观,而后成为涉道类小说,特别是精怪神魔类小说的常用叙述模式,因为已经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观念而不再被强调。
《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1]744后世对“楚子问鼎”故事的分析更多是从儒家角度入手,而较少注意到王孙满所述中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介绍。百物被人认识后,没有了迷惑人的招数,人因此得以躲过灾害。而在更早记录“远方图物”的《山海经》中,对待这类精怪的态度稍有不同。《山海经》略显于汉而盛于魏晋,特别是经过郭璞注后,为当时方士经常提及的书籍。然郭璞的注将此书的解读从地理博物引向道教方术的道路[2]110,可以确定的是《山海经》在其所诞生的年代,对于“青丘国……其狐四足九尾”[3]256,“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启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3]230是个相对严肃的态度,书中描绘各种奇物精怪会食人会变幻,这些东西是矗立在上古先民对面的自在之物[4]373,是人可以用语言描绘却无法掌控的神秘、独立个体,相比之下,先民的力量是那么微弱。后世将《山海经》所录只当作神话看待,却忽略了“神话”一词之来源:“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10神话最初是先民解释周遭环境的语言,所包含的是上古先民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它是先民对周遭的认识,只是随着认知能力的提升,后人渐渐改变了原先的观念,这些古籍的实用性减弱乃至被忽略,书中曾经有的严肃性也被后人解读时产生的神秘感奇幻感所淹没。而“识破”的观念却留存了下来,虽然它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人对百物精怪的态度,从最早的仰视、害怕、恐惧到后来渐渐以一种平视的角度审视之,觉得可以识而避之,而到了魏晋涉道小说中,就完全变成可以运用方术而破之。
万物可以被识而破之,还包含着一个唯物观的思想,即《列子·汤问》一文中所论述的朴素的唯物观:“天地,亦物也。”《列子》一书虽是后人伪作,但其中唯物观却是承接先秦,至两汉仍未有大的变化,又如王充在《论衡》之“订鬼”篇云:“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为人,亦有未老,性能变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气,有与物同精者,则其物与之交。及病,精气衰劣也,则来犯陵之矣。”[6]1384王充的思想被视作东汉思想之异端,《论衡》凡八十五篇(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主倡无神无鬼论,然其辩驳思想仍属于传统唯物观的范畴,这种唯物观与近代的唯物观不大相同,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王充用以解释世人所认为鬼者时的名词,如“精”“气”,是汉代人所认为的人之为人、物之为物的组成,也是万物可以相互变幻的关键。而这一概念同时广泛存在于古代其他行业,如《伤寒论》卷二“伤寒例三”开篇就说了天地有四季之别:“《阴阳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7]2四季之“气”有别,使得人的精气也随之变化。
既然天地及四季,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由“物”“精”“气”所构成,那么万物就可以相互转化。明代文人笔记《五杂组》云:“狐千岁始与天通,不为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精气以成内丹……南方猴多为魅,如金华家猫,蓄三年以上辄能迷人,不独狐也。”[8]183“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5]14神祇人鬼虽然有所分别,但是却可以相互变幻,其可以转化之关键就是因为四者都是“物”,“物”会因“精”“气”之变化而变化外形。这就使得人死而可变成物,如《精卫填海》,或变成神鬼,这种观念又与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及道教修行道化“无缝对接”,有了人因前世善恶而或入仙班或变牛马的观念。
二、等级观的渗入
“识破”观念包含着上古的世界观和唯物观,并且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化。对精怪的态度由恐惧变为学会识而破之,这个过程中还伴随着等级观的渗入:精怪开始向往人类的世界,人类识破精怪需依靠道家方术,因为记录识破精怪的书籍只有道士及得道之人才能读懂。
《山海经》中的青丘国九尾狐在后世“食人之传渐隐,为瑞之说终张”[3]257,人们从最初对周遭的好奇,到后来改造精怪传说为自身服务,是人与精怪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上文说到郭璞注《山海经》将对《山海经》的解读由地理博物引向道教方术,道教中还有类似记录精怪的书,都是为了道士驱邪避怪的实际操作而作的。“葛洪认为躲避鬼怪精灵的方法之一,就是‘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泽图》《九鼎记》,则众鬼自却’。”[4]379从《山海经》诞生的年代来看,《山海经》曾经有过实际的用途。从道教的发展过程来看,《白泽图》等书也曾经具有严肃的实用性,只是它的使用者是道士,也并非完全只有装神弄鬼的欺骗性,早期“在他们的主观上,也许还存在着虔诚的信仰”[2]118。而道术及道士的出现,使得原本独立于人之外的精怪们开始向往进入人类的世界,体验人类的生活及情感,这背后包含着人对动物精怪的视角由原来的仰视变为俯视。
涉道类小说很好地呈现了这一转变。狐怪(暂以狐作为代表性动物讨论)故事最早约出自干宝的《搜神记》,此后狐化作人样,或引诱男女,或称为大仙天狐,频繁地进入人类社会。如《搜神记》:“南阳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则有祸……语未竟,鬼在前,大贤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贤遂杀之。明日视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无妖怪。”[9]223六朝以实记怪,“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5]14。笔者认为六朝小说中的“实”就含有对教义宣传的虔诚态度。并且可以看到这类小说将上古的识破观念转化为故事的叙述模式。在这里,道士拥有的方术成为故事的关键纽带,“一方面在人神之间沟通,一方面在人鬼之间阻隔”[4]389。凡人无法仅凭肉眼认识妖怪,更无法仅凭自身的能力除去妖怪,而凡人同时看不透的还有得道的仙人。
首先,为什么狐类要穿上人的衣饰?这个情节在《西游记》中也同样出现,石猴来到人间先做的事是抢人衣服穿,很显然,这是作者加诸动物精怪身上的第一个社会性标志。其次,为什么狐类要历尽艰辛变成妖,继而幻化成人的模样进入人类社会?先民进入青丘国很可能遇见食人的九尾狐,而在涉道类小说中任何身份的人都可能遇见幻变后的狐类,并且幻化后的狐妖在道士面前显得很脆弱,这种脆弱背后其实是狐怎么修炼都无法成为真的人类,在等级上低于人,以妖对人类社会的向往,展示道术对妖、人、仙沟通的控制。掌握了《山海经》《白泽图》等,代表着对生存意识的经验积累。这是“识破”观念中“识”的基础点,其目的是存活,一旦目的发展为享受生之乐趣,那么其基础点也已发生了变化。
在“有意识为小说”的唐代,涉道类小说由注重降妖的结果变为注重降妖的过程,并且作为纽带的法术道士让位于爱情,使得“识破”成为狐类故事的转折,而非直指结尾。最典型的如《任氏传》中,郑子知道任氏乃狐,并未远离任氏,反而二人有了进一步相处:“任氏……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郑子曰:‘虽知之,何患?’对曰:‘事可愧耻,难施面目。’郑子曰:‘勤想如是,忍相弃乎?’对曰:‘安敢弃也。惧公之见恶耳。’郑子发誓,词旨益切。”[10]3693在这里狐的身份第一次被识,但二人关系更为亲密。《任氏传》整篇,任氏对郑子以死相报的情谊,无它,唯郑子知其真身而不弃。“识破”情节的第二次出现同样带来故事的转折:“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欻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10]3694任氏见犬而现出原形,遂而逝去。作者以“爱”的名义将任氏的“人性”取代了之前狐妖身上的“妖性”,充分展示了作者蕴涵“人不如狐”的寄托。在这个阶段,人类表现自身高于动物的方式之一,便是展示人间有“爱”,由于有“爱”的欣赏眼观,精怪开始变得可爱,令人爱之。类似郑子的人类角色,也为发现并欣赏这种可爱的精怪而生,但这个时期的神魔小说更多是充满男性欲念,女性狐怪的出现更多是为了填补男性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缺失。
三、披着精怪外衣的人类社会
而到了《西游记》中,“识破”观念就由展示某个人或某类人的需求变为展示一个完整的社会复杂性。“识破”的对象虽然还是精怪,但其更多时候只是披着精怪外衣。“识破”由观念渐渐变成一种外在的形式,较显著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石猴进入人类社会的原因是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二是对所处社会关系的探求。
在第一回,石猴“与群猴喜宴之间,忽然忧恼,堕下泪来……猴王道:‘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众猴闻此言,一个个掩面悲啼,俱以无常为虑。只见那班部中,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厉声高叫道:‘大王若是这般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11]14百物均有对死的恐惧,而拜师学艺是石猴对自身寿命束缚的一个破除,却又引来连环的束缚。在这个“识破”过程中,它完成了从石猴到齐天大圣的第一步。石猴的自我实现包括内在的自我实现和对外的自我实现,这也是作者在《西游记》中要呈现和要认识的对象,即人类自身。
在《西游记》降妖中遇碍时,孙悟空常常问土地山神或者上天入海,就是为了探求妖精的名号来历而寻它的主公,或者找到可以制服它的神仙。对妖精的名号及它的主公的询问和追寻,是孙悟空对所处社会环境本质关系的探问。如第十七回黑风山遇“黑汉”,行者看到“黑汉”给老主持的帖,说:“你看那帖而上写着‘侍生熊罴’,此物必定是个黑熊成精。……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他有这个禅院在此,受了这里人家香火……我去南海寻他,与他讲三讲。”[11]194早期的涉道小说要找寻的是妖精的“原身”,要认识的是妖精幻化前的面貌,而在这里孙悟空要认识的是精怪所处的社会关系网。如第四十九回遇金鱼精,行者百斗无法,道:“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属,捉了他的四邻。”[11]580孙悟空因为不知其妖名无法找到降妖的“主”,亦不知以何法除妖,只好又一次求助观音。以探问外在关系来确立自身所处的真实环境和地位,作者调遣着孙悟空一次次在这似戏似幻中呈现那个社会关系网。主公出现在云端高呼自家异兽这个细节很值得一提,如第五十二回:“那魔轮枪就赶,只听得高峰上叫道:‘那牛儿还不归家,更待何日?’那魔抬头,看见是太上老君,就唬得心惊胆战道:‘这贼猴真个是个地里鬼!却怎么就访得我的主公来也?’”[11]617青牛怪之所以能威风凛凛,一是靠着盗来的主公的宝物,二是靠着无人知晓它从何而来,多少神仙奈何不得它,而知晓它的如来,只是托人传话给孙悟空,“罗汉道:‘如来吩咐我两个说,那妖魔神通广大,如失了金丹砂,就教孙悟空上离恨天兜率宫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11]616,作者非要太上老君出来降妖,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太上老君对青牛妖知根知底,青牛怪无法伪装,而作者同时赋予了青牛怪羞耻感,让它无法在主公面前再“装模作样”了。
四、结语
文章阐释了何为“识破”观念,等级观的渗入对识破观念的影响,及识破观念完全由观念变为一种叙述形式。曹萌认为模式之所以是“有意味的形式”,“在于它凝聚了丰富的文化艺术蕴涵”[12]35。“识破”从观念到形式的转变,涵盖了最初的朴素唯物观和世界观,潜移默化成为古人认知事物的惯性思维,并且由于被道教文人接受,融入涉道小说中,成为神魔小说中重要的叙述模式之一,这其中等级观的渗入又使得道术及爱情先后成为神魔小说情节转变的关键,而动物与人的等级关系也最终由各自独立转化为精怪对人类社会的向往。在《西游记》这部神魔小说的代表作中,作者依旧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识破”模式,然其认识的对象由妖完全变为人类,作者所要认识和呈现的完全是一个披着精怪外衣的人类社会。
[参考文献]
[1]左丘明.左传[M].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3]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袁华忠,方家常.论衡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7]张仲景.注解伤寒论[M].王叔和,撰次.成无巳,注.汪济川,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12.
[8]谢肇淛.五杂组[M].傅成,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李昉.太平广记:第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2]曹萌.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模式研究[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赵青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1-0025-04
作者简介:张天羽(1988—),女,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7-24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