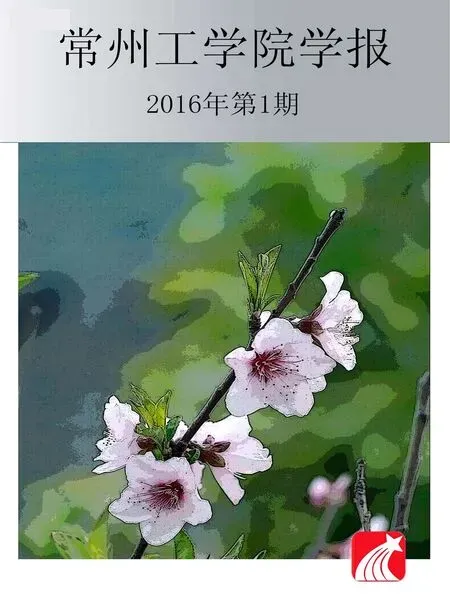论霍桑的“无意识”人性观
乐传勇
(安徽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22)
论霍桑的“无意识”人性观
乐传勇
(安徽建筑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22)
摘要:美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其小说和人物刻画大量运用了心理分析技巧。文章借助荣格的无意识理论,特别是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以及从众求同原型和阴影原型等概念来分析霍桑笔下的人物形象,探究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在他们身上的体现,进而揭示小说家的“无意识”人性观,说明霍桑的文学创作思想与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有高度相似性。
关键词:霍桑;荣格;“无意识”;人性观
美国19世纪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深受加尔文教的影响,其作品充斥“罪”“恶”“罚”等宗教问题,其思想反映了矛盾的善恶观。一直以来,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大都钟情于研究霍桑的宗教情结,较多地探讨其矛盾的人性观和宗教伦理思想。其实,霍桑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文章借助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等概念来探析霍桑多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深究他们的社会心理历程,进而揭示霍桑的文学创作思想与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的相似性。
一、集体无意识“原型冲突”与霍桑“人性善恶冲突”
在分析心理学体系中,“心灵”被当作人格的总体,具有与生俱来的整体性。“心灵是涵盖了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在内的一个概念。”[1]234在荣格的心灵结构理论中,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原型”,而对人类发展影响最深刻的两个原型为从众求同原型和阴影原型。从众求同原型是社会和团体生活的基础,它表现为人格面具,即一个人戴着面具去扮演他人,这有利于他与别人和睦相处。当我们把自己完全等同于人格面具并受其主导时,难免会在心理上美化自身;可我们自身却很难一直扮演他人角色,这样内心冲突便会产生。另一原型即阴影原型,它与从众求同原型相对立,可比喻为人格中的阴暗面,即人性中“恶”的一面。对立冲突往往出现于从众求同原型和阴影原型不能和睦相处之时。荣格主张,一个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人能把“善”与“恶”结合进自己的整体中,否则我们就会投射出这些恶的想法[2]65。
霍桑的作品中人物充斥着这两种原型的对立与冲突,尤其是牧师。《教长的黑面纱》中的胡珀牧师与全体教民关系融洽,备受他们的尊敬,可自从牧师戴上黑面纱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面纱和它背后所隐藏的秘密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纷纷对牧师产生怀疑,认为他在极力掩盖巨大的罪孽。也就是说,牧师在掩盖人格中的阴暗面,这就是阴影原型。牧师戴面纱是为了体现从众求同原型,这面纱便象征着人格面具。但是,这象征人格面具的面纱并没有掩盖住人格的阴暗面,反而泄漏了“恶”,因此它们两者其实是对立的。
换个角度看,戴上面纱后的牧师不觉得自己有“罪”了,思想上也没有任何阴影,他一如既往自信又温和地对待工作和教友们。黑面纱其实象征着众人的人格面具,人人都有罪,人人都可以戴上黑面纱。牧师在所有的人都远离他时这样说:“难道这仅仅是因为我戴着黑面纱吗?难道它所代表的模糊的神秘真那么可怕吗?看看这个世界啊!这世上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块黑纱。”[3]78这正体现了从众求同原型的重要性,如果每个人都能为了社会和团体的发展,为了与他人和睦相处而去扮演非自己的角色,那么这两个原型之间原本的对立冲突关系便会缓和,甚至消除。对于胡珀牧师来说,他是全体教民的精神导师,旨在引导他们向着天国和上帝,戴上面纱后,他可以在某些时刻更好地扮演上帝的角色,指引他们驱除心中恶念,压制阴影原型。然而他不能完全等同于上帝,至死也不肯摘下那具有“神力”的面纱,就连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也未能说服他,最后离他而去。胡珀牧师的悲剧说明我们很难用从众求同原型去压制和消除阴影原型,两者的对立冲突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同胡珀一样身为牧师,也是个正派、善良、热情、博学和备受尊敬的人。他严于律己,把自己视为上帝虔诚而圣洁的使徒,努力宣讲教义,造福芸芸众生。他要一直佩戴这一人格面具,虽然这一面具让他感到无上的荣耀,受到崇高的赞誉和顶礼膜拜,但事实上,他的心中也一直充满着罪恶感,他不敢承认自己对海斯特所犯下的“罪”,因为他不能放弃他的人格面具。他所犯之罪是人格的阴暗面,是阴影原型。他只能靠压制这阴暗面去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角色认同,维护他的人格面具,保持着从众求同原型。这两种原型的冲突使他过着一种行尸走肉的生活,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使他内心极其痛苦。作为一个笃信上帝的牧师,信仰的铁栏“一面在囚禁他,一面却也在支持他”。在海斯特示众之时,他的“训诫词”细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有逃避罪责的内疚,又有对惩罚降临的恐惧。最终,牧师脱去人格面具,向他的教民们坦白实情,勇敢地展露他的人格阴暗面,让两种原型的对立趋于和谐,使心灵的塑造趋于完整。。
这两位牧师的悲剧在于过分强调从众求同原型,意欲美化他们的人格面具,压制心灵暗影。诚然,牧师的心理矛盾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承载上帝精神的导师,他们一贯备受教民尊敬,虔诚引导他人向善,而自己却放纵身体,心灵从恶,内心无论多么强大的人也难挡压抑感。不难看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冲突其实就类似于霍桑在其作品中表达的人性善恶之冲突。霍桑的作品喜欢刻画牧师是因为牧师身上体现的这两种原型冲突更为深刻和激烈。
二、多种情结之“并存”与人性善恶之“并存”
集体无意识中的两种原型形成一定程度的和谐,有助于人格的统一。而自我情结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和谐统一。因为具有内驱力的情结是个体一切意识行为的主体。它具有无意识和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如同两种真实、两种意愿的冲突之间的个体,似乎要把个体撕成两半。而这种自主结构的情结就是个体无意识的表现。而情结,事实上是“人格碎片”,它从完整、和谐的人格内部分离了出来,失去了与人格整体活动的一致性,可以被视为“人格断面或次级人格”[1]51这个独立的人格子系统,通常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内在自主性、情绪黏贴性和动力性[4]63,其自主性表明情结不易受意识控制,或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控制。当这一个个的“人格碎片”存在于整体的人格中时,就形成多种情结并存的情形。
这种并存就如同人性的善恶并存,因为情结具有自主性,这样就会导致人性善恶皆有可能,而且善恶会在冲突中形成某种程度的平衡与共存。虽然霍桑一直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出人性本恶的思想,但实际上支撑他罪恶观的两大支柱是加尔文清教主义神学观和人道主义道德观,因而他本人并不相信绝对的善与恶,也不完全认同清教徒的极端思想。因为“清教徒不能区别从善到恶之间的许多层次,而是相信极端的走向,非白即黑,非黑即白,不能妥协而接受相宜的事物”[5]12;况且,他还受到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是有善心的,在人的心灵中存在着一种内在能力,这使得人与上帝进行交流成为可能,而人神交流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这种内在的能力就如同情结的内驱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人的恶念,从而形成人性善恶并存的状态。
在《好小伙布朗》中,主人公布朗本质上是个好人,内心向善,他刚刚结婚,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期盼。但即便如此,他最终还是未能禁得住魔鬼的诱惑,抛下挽留自己的妻子,赴了魔鬼之约。让布朗感到震惊的是,自己的道德和精神引路人教长和古金执事竟然也赶去赴魔鬼之约。不过,布朗还是心存善念,决定维护世间的纯洁,他大声疾呼:“苍天在上,费思在下,我决心坚定不移,不受魔鬼所惑!”[6]21然而当他发现妻子费思背叛他,在深夜和魔鬼聚会时,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善念的驱动力荡然无存,他最终走上罪恶之路。在布朗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人性的善恶并存和冲突,只是他的个人意志不够坚定,让外因主宰了自己。各种意念并存如同各种情结的并存,而意念冲突就如同情结的驱力中心发生了偏移,各个部分自行其是地独立活动,就会影响自我的发展。荣格在《心理能量》(1928年)一文中提出情结的核心要素由两方面组成:第一是由经验所决定,并同环境有因果关系的因素;第二是个人性格所固有,并由个人意向所决定的因素[7]11。而情结具有无意识性,它也是个体无意识的表现,由于个体的不同,也会“无意识地”产生区别。它具有潜意识特征,而潜意识心灵又可以帮助情结去影响自我,能使人格发生认同于情结的潜意识变化。人性的善念与恶念也具有同样的潜意识特征,具有一种平衡性,只是在一定外因和内因的影响下,会发生“个体无意识”的变化。在《红字》中,海斯特虽然不愿意承受宗教对她的折磨,有着抵触的“恶念”,但是她起初一心只想着忏悔赎罪,因为她内心的“善念”让她羞愧于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这种“善念”与“恶念”形成了一种平衡,让海斯特对发生的一切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然而,戴上红字、日甚一日的折磨和没完没了的凌辱在不知不觉中动摇了她这种平衡的心态,她心中反抗和叛逆的意识日益增强。她以轻蔑的态度批判牧师、法官和教会,同时也以“局外人”的立场看待人类的各种制度,内心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玩世不恭的态度。她甚至不顾丁梅斯代尔的处境而鼓动他跟自己一起跑到“看不到白人的足迹”的地方去“自由”地生活。在内外因的影响下,海斯特身上的“善念”与“恶念”的平衡也会发生无意识的倾斜,只是并没有达到完全失衡的程度。
三、人格整体性与霍桑的人性观
对于人格产生的根源,人格理论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形成了人格的六大流派,而其中精神分析流派强调人的无意识心理对他们行为方式的差异起着很大的作用[2]3。作为人格总体的“心灵”涵盖了意识、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具有与生俱来的整体性。“多种情结并存”与“人性善恶并存”都是为了维护人格的完整性和心灵的整体性,具有稳定性,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发生内部变化过程,这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个体的不同,其中个体的无意识尤为重要。
精神分析理论家们不仅对人格进行描述,而且以多种方式就人本身及有关人的古老哲学命题提出许多新思想。他们关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宗教长期关注的问题相一致:人性本善还是恶?荣格的父亲是瑞士的一位牧师,从荣格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宗教问题进行苦苦思考。“他指出每个人在其集体无意识中都继承了上帝的原始意象,因而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接受上帝,但是现在宗教已经发明了他们的一套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教堂可以采用忏悔、免罪、宽恕来象征性地帮助信众们协调自己身上的善恶冲突。”[2]73可见,其实荣格也认为善恶是可以并存的。
而霍桑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受到清教主义熏陶甚深,他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准则,他认为人性皆恶,人人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和罪恶。在很多作品人物身上可以看出这种阴影原型,尤其是在牧师身上,如胡珀和丁梅斯代尔,因为他们是信徒的精神导师,承载着上帝的原始意象,深刻体现着从众求同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主要内容的这两种原型的冲突要形成某种和谐,因为这样才能把善与恶结合到自己的整体中。霍桑和荣格都出生在宗教环境中,他们也一直在探索人性的善恶问题。霍桑虽然受“内在堕落”思想的影响,一直主张人性本恶,但其思想和作品中却又展现出善恶并存。这种人性善恶并存就如同荣格的多种情结并存的状况,都是为了实现人格的统一,维护心灵的完整性,让人类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型形成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保障人类的健康发展。作为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从精神分析层面来看,霍桑一直在探索两种平衡:多种情结的平衡及从众求同原型和阴影原型间的平衡。而他人性观的发展也是从单纯的善恶对立到善恶冲突,再到善恶并存,最终形成一种平衡与和谐,这也符合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对于人格整体性和完整性的描述。
四、结语
霍桑擅长从心理分析角度去剖析人的内心,他主张通过善行和自我忏悔来净化心灵,从而得到拯救,但是他写的并非都是黑暗,他在揭露社会罪恶和人的“恶念”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些人物身上的“善念”。虽然“善”与“恶”会有冲突,不过它们也会形成并存,甚至平衡的状态。而且,霍桑的人性观也是变化发展的。从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无意识角度来看,两种原型冲突如同人性善恶之冲突,多种情结的并存如同霍桑的人性善恶之并存,而霍桑人性观的发展也类似为了维护人格的完整性而不断进行的自我完善过程。
[参考文献]
[1]STEIN M.Jung′s map of the soul:an introduction [M].Chicago:Open Count Publishing Compang,1998.
[2]BURGER J M.人格心理学[M].陈会昌,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3]霍桑.霍桑经典小说[M]//世界著名短篇小说集:第17卷.魏明,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4]莫瑞·史坦.荣格心灵地图[M].朱侃如,译.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9.
[5]史志康.美国文化背景概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6]孙铢.英美短篇小说荟萃[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7]JUNG C G.On psychic energy:collected works of C.G.Jung[M].New York:Princeton Press,1971.
责任编辑:赵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887(2016)01-0037-04
作者简介:乐传勇(1978—),男,讲师。
收稿日期:2015-04-26
doi:10.3969/j.issn.1673-0887.2016.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