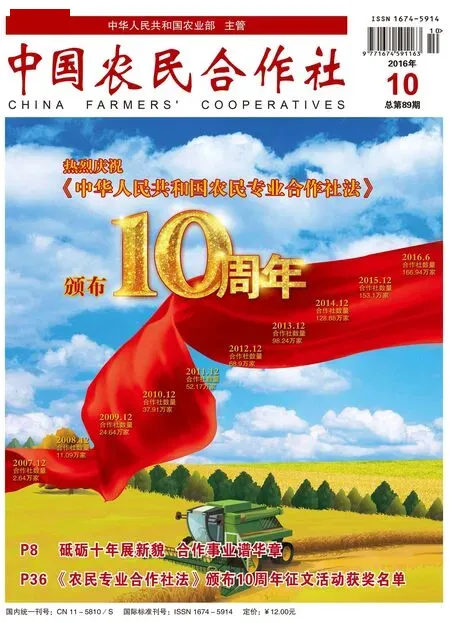论中国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必要性
■ 文 / 马彦丽
论中国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必要性
■ 文 / 马彦丽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后,中国的合作社数量激增,然而,与此相伴的是人们对合作社“异化”的广泛质疑。合作社质的规定性(自我服务和民主控制)正在发生漂移(黄祖辉等,2009),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广泛存在“名实分离”(熊万胜,2009),有很大比例的合作社出于追求“政策性收益”目标而成立,大股东控股而普通成员受益不多的情况普遍存在,农民对合作社表现出茫然和漠然(潘劲,2011),邓衡山(2014)的研究甚至认为,中国绝大部分合作社都不具备合作社的本质规定,其本质仍旧是公司或“公司+农户”等其他类型的组织。对合作社异化这一现象学术界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存在“包容论”和“规范论”两类观点。前者对合作社的发展成就较为乐观,认为应该理解合作社发展初期的生态多样性,多扶持、多包容、少批评,可以先发展、后规范;后者则对合作社的异化深表忧虑,认为名实不符侵蚀了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亟需通过修法以及政策调整等手段纠正合作社的异化。本文的观点更接近后者,认为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亟需规范发展。
一、对“包容论”观点的简单概括
“包容论”者的主要观点可以简要概括如下:(1)“经典”合作社不存在论。认为国际上合作社判定的标准一直在发生变化,真正经典的合作社已经很少存在。作为一种章程自治的组织,实践中很难找到两个制度一模一样的合作社,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苛责更无必要。(2)利益提升论。认为只要能给农民带来好处(调研可见,很多公司都能为农民提供一些技术服务以及市场进入的机会),就不必深究他是不是合作社,如果因为组织不够规范而不被认可的话,恐怕利益受损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农民自己。(3)“先发展后规范”论。认为首先要力促合作社的大发展,造出声势,至于规范,可以先上车后补票。(4)合法注册论。认为合作社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工商部门依法注册成立,各位学者有什么理由说某合作社不规范甚至是“假”的呢?(5)“泛”合作论。认为无论真假,某经济组织在与农民的交易中的确存在着与农民合作的因素,该组织收购了农民的产品,也向农民提供了信息和技术服务。既然有合作,就应该是合作社。
二、对上述观点的讨论
上述观点均有有待商榷之处。关于“经典合作社不存在论”,本文认为,所谓“传统”(或经典)的合作社虽然越来越少,但并非不存在,这里的重要分歧是如何认定“传统的”的合作社。如果照搬罗虚代尔原则或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原则,“传统的”合作社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恐怕没人会这样想并这样做。合作社的本质是成员所有、成员控制和成员受益,与此相适应,成员的经济参与(出资)、民主控制和按惠顾额返还盈余被认为是合作社的核心原则,符合上述原则就是所谓的传统合作社。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出现了比例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等新的合作社类型,但合作社最核心的内核——合作社“所有者和惠顾者同一”没有变,突破了这一点,合作社就彻底不能称其为合作社了。有人提出“中国特色”论,“不希望今天的农民合作最终一定要遵循西方的合作社标准才算规范,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农民合作能够创生出他们自己的规范标准,形成我们本土的合作社土生标准来”(刘老石,2011)。问题是中国真的有那么多异于他人的所谓特色吗?是基于什么不同的背景导致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合作社彻底不一样?这种不同是否需要我们将合作社的最底线也放弃呢?
“利益提升论”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有人用“猫论”来佐证其正确性,但逻辑上站不住脚。因为虽然黑猫白猫都可以抓老鼠,但不必让黑猫伪装成白猫。即便是一个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农民在与其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获得效益的提升、福利的改善,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的。在各国农业发展实践中,除了合作社,还可以存在各种性质的经营主体,包括投资者所有的公司和非营利组织,他们适应不同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以不同的方式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合作社都不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所以,如果某个组织是投资者所有的,那就直接光明正大的注册为投资者所有的公司,一样可以与农民合作,创造福利。
“先发展后规范”的提法很有市场,其另一种形象的表述就是“先上车、后补票”。如果一开始鼓励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中国现有的体制机制能使其自动纠错吗?令人印象深刻的“先上车、后补票”论的应用是在中国股市,然而中国股市创立将近30年了,目前还不能有效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这难道不是深刻的教训吗?事实上,中国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一直在提,为此颁布过一系列的文件,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等,并举办一系列的示范社的评比活动,但显然效果不佳。
“合法注册论”的问题在于合法注册不能代表某组织具备合作社的本质。中国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要“抓紧研究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足见人们对目前法律的漏洞和缺陷是有共识的,认为其不足以规范合作社的发展。即使合作社合法注册了,是否合作运作也无从可知。从调研情况看,很多合作社在完善治理机制以及盈余分配机制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这也正是学术界质疑合作社“异化”的重要理由。
“泛合作论”的问题在于合作社作为一种组织,依合作社法注册成立,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无限推广,就失去了合作社作为一种特定的商业组织形式的意义。有人引用汉斯曼(Henry Hansmann)的观点,认为合作社是更为一般的概念,商事企业(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只是合作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是投资人的合作社。但是在汉斯曼的理论中,我们常用的合作社是指生产者合作社,除此之外还有消费者合作社、雇员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与公司(汉斯曼认为是投资者的合作社)都是并列的组织,不同的组织之间仍然是泾渭分明的。
三、为什么要重视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问题
需要申明的是,之所以要重视合作社的异化问题,绝非对非合作社的农业经济组织有任何歧视,也不是要否定合作社对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潜在作用,而是认为当前农民合作社的异化可能损害合作社的发展前景,必须正本清源,勇于直面问题和挑战。
从实践看,在各类合作社扶持政策的激励下,许多合作社出于寻求政策性优惠而成立,产生两类不健全的合作社:一类依赖政策生存,得不到优惠政策就偃旗息鼓,成为休眠合作社、挂名合作社,完全没有自生能力;另一类本来不是合作社,但是将自己包装成合作社以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这类合作社多数是由公司、能人或事业单位领办,往往同时拥有几个牌子,如龙头企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合作社等,以便随时争取国家的各类优惠政策。“大股东控股普遍而普通成员受益不多”说得正是这类合作社。从后果看,后一类的示范效应更加糟糕,不但压制了真正的合作社发展空间,而且对政府扶持政策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例如,由于此类合作社的益贫性很弱,很难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三个允许”(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转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正当性。此外,这类合作社本身也存在较大的隐患:一方面必须以合作社的面目来包装自己,而后又在所谓一系列的规范政策下承担一系列政策风险和财务风险(如一些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为了突出合作社的固定资本、流动资产规模,把公司的资产记入合作社,为了所谓规范把本来挂名的合作社成员的账户要做“实”,加入相关主体主张权利,会非常尴尬)。
异化的合作社也给理论研究带来严峻的挑战。从研究的需要来讲,如果不能严格定义合作社,也就无所谓合作社理论的存在,已有的公司理论就可以涵盖一切。农民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经营合作社可以理解,而学者则必须追求名实相符,否则,理论和实践就会脱节(邓衡山,2016)。如果我们抱着这些没有合作社性质的“合作社”来搞研究,搞得再深入,方法再先进也只能是自欺欺人。
实际上,“包容论”和“规范论”分歧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其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合作社异化的程度认识不同,但是二者对合作社的异化以及异化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共识的。至于如何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本文则暂不讨论。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3BJY104)和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HB15YJ067)的资助〕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栏目编辑:孙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