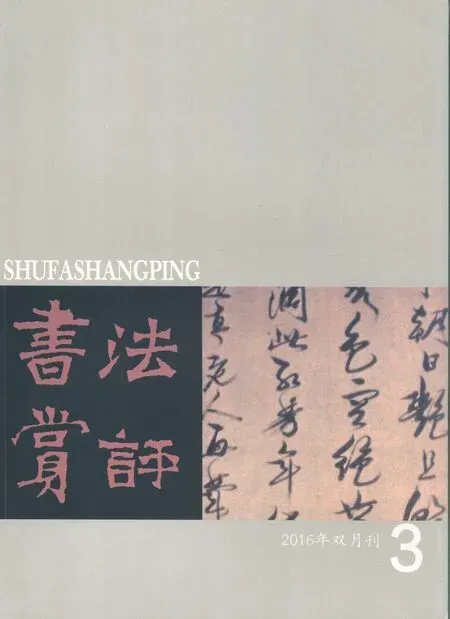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碑派书法研究[1]
■王守民
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碑派书法研究[1]
■王守民
一、明清闽、台地区碑派书法发展的阶段及代表人物
清代碑学是从滥觞到发展、复兴,最后形成了与帖学双峰并峙的局面。事实上,单从数量上来讲,碑学的人群从始至终都是出于少数,帖学始终不处于优势。在碑学发展中,闽、台地处东南一隅,虽然文人的生活、学习都受到地域的局限,但是逐渐形成了以本地文风、书风为主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明末清初碑派书法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闽台地区也逐渐孕育并发展起来。
如果要追溯闽地碑学的源头,笔者以为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张瑞图等人。张瑞图在崇祯以后,谪居闽南乡野,其笔底的生拙气、金石气浓郁,从学者如流;周亮工在闽地为官,以篆隶笔意作楷书、行书,方中见圆,古拙朴茂,与帖派殊异,碑派书法的笔意十分明朗。可以说,周亮工是闽地碑派书法从滥觞到发展的关键性人物……闽台碑派书法正滥觞于此时。清中后期,以厦门玉屏书院为中心,周凯、郭尚先、吕世宜、叶化成等师徒成为闽地书学发展的中坚,力扛书学之鼎。在吕世宜、叶化成到台湾以后,台湾帖派书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金石拓片的输入和碑学思想的影响,文人书风翕然而从吕氏碑风;帖派书法也从早期明末遗贤的藩篱中挣脱出来,独青睐于王羲之书风。与此同时,何绍基隶书、碑派行书的影响在台湾日益增大,追随者众多。郑贻林、陈蓁、庄俊元等书家激流而上,在后期的碑学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台湾碑派书法的发展,为台湾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接受日本的碑派书风打下基础。日据时期的五十年,正是台湾书法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台湾本土书家的成长、大陆、日本书家的双面影响,都是促成台湾书法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日式教育与中式私塾教育的双重影响下,书家早期处于隐逸状态,书法活动局限于诗会诗社的活动中;日据中、后期,随着报纸、展览会日益增多,碑派书家活动频率增加,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本土书家李学樵、李逸樵、庄士勳、郑蕴石、施梅樵、李葆英等人在碑派书法创作思考方面比较深入,其作品也具有典型的碑派风格特征。
在日据后期,由于政治政策方面的原因,闽台、闽粤等地区的交往日渐增多,不少台湾的居民渡海来到大陆,也有一些原来在闽粤的台湾居民返回岛上;展览会的举办,邀请大陆书家来台,也是闽台、闽粤书法交流的重要途径。没有这种交流,大陆的书风不可能影响到台湾,台湾的书家也不会影响到大陆。区建公、赵蔺等书家的赵之谦碑风在当时很受青睐,影响很大。他们是清代后期台湾碑派书法发展的推手。
二、闽、台地区碑派书法的发展、传播及流派特征比较
学界认为,明以前台湾无书法。台湾书法肇始于明末郑成功入台之时。“台湾文士有关书法创作文化活动叙述,乃以郑成功入台为起始。其后台湾之望族亦相继聘请大陆饱学之士入台为西席,教育子弟。台湾望族对台地的文化推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
台湾望族是台湾书法传播的主体——以板桥林本源、雾峰林文察、大龙峒陈维英为首,他们为流寓台湾的文人提供优越的条件,使书家潜心书艺研究与创作中。渡台文人中多进士举人、除了精通经史辞赋之外,更有着良好的书法基础。他们也自然形成了闽台书法传播的主力。
明末清初的台湾书坛,南明儒士书家的审美取向是很明确的。他们取法崇尚骨力、劲健厚重的颜真卿、朱熹书风。在明末,无论是从人格上还是从其书法的审美上,颜体书风能满足当时文人的心理需求,审美上符合当时文人的审美趋向。因此,在明末的书坛,楷书取法颜真卿的书家甚众,朱术桂就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台湾地区碑派书法的发展与大陆碑派书法一样,经历了滥觞、萌芽、发展、成熟的四个阶段。碑派书法的萌芽阶段,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大陆书法已经出现了像王铎、傅山、张瑞图、黄道周等大家。在这些大家之中,出现了隶书、篆书创作作品。在他们的隶书、篆书作品中,异体字和参照篆隶的做法,都显示书家的金石、文字学功底。
此时台湾地区的明遗老宿儒,笔底流淌的却没有碑派的笔调。自明郑入台,崇尚二王、赵、董、颜真卿的书风,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果说碑派在台湾有滥觞的话,那么朱术桂可以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宁靖王朱术桂大字用笔上的恣肆,源自于的朱熹,结字内擫,骨力峭拔,颇具碑派书法的气度;他的行书与楷书一样,用笔与结体均与碑派书法暗合。明末注重个性张扬、重视自我表达,这主要缘于明代阳明心学及其泰州学派的影响,建立了以 “童心说”为中心的哲学本体论。明代末期浪漫主义思潮泛滥。“进入清代,启蒙思想家高扬性情,提倡个性,更是如火如荼。”[3]
明末清初的书学上开始出现离经叛道的反向审美思潮。同样,这种提倡个性艺术发展的闽台两地的书学思潮,掀起了闽台地区书家从 “古人”到 “自我”之间的持久战。
康、乾之际,闽地书家周亮工,在风格上独树一帜,成为碑派书家最为杰出的代表。周亮工以隶书笔意入楷、行草书,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周氏精研金石篆刻,下笔屈曲如劲铁,拙而有趣,又不乏灵动。在明末清初的书坛,颇具个人特色。刘恒先生说:“作为书法家,周亮工喜欢收藏,凡书画碑拓、古墨印章,糜不搜集,且精于品评鉴赏。尽管当时金石之学与碑派书法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周亮工的书法已经显露出碑刻书法平实方折的特点来。”[4]受周亮工的影响,闽地书家许友,学米芾而书写中带有生拙气,气息高古而不乏新意。可以认为是碑派书法的滥觞了。
与此同时的台湾地区,在碑派书法发展上尚落后于大陆,在此时尚没有出现如周亮工一样有着明显碑派书法风格的作品。笔者根据统计,发现在清代康、乾、嘉时期,台湾的留存与可靠碑刻中,学习晋唐楷书的书家,占绝大多数。其中有 “碑味”的刻石占10.8%,在这些有 “碑味”的刻石作品中,有将近一半的作品是由于斑驳产生的效果。
台湾碑派书法的发展是滞后于大陆的。刘恒在论到乾、嘉时期的碑派书法时说:“承袭清初风气,隶书创作因临习汉碑做法的普遍而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众多文字学家的喜好和介入,则使篆书创作迅速复兴。隶、篆二体书法的繁荣,使碑派书法创作力量已经壮大成为足以与帖学相抗衡的潮流。乾嘉时期大陆碑派书法已经相当繁荣,在台湾却不是这样,碑派书法多来自于流寓书家之手,尚未真正在当地普遍传播开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金石学家吕世宜的到来才得以改变——碑派书法在台湾真正登上舞台,普遍传播开来,也是在此时,碑派书法逐渐走向与帖派书法分庭抗礼的道路,书法风格开始多元起来。
在乾、嘉、道时期,台湾本土书家张朝翔是学习魏碑书法,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的代表。 “其字法朱文公,大字尤为擅长,纵横烂漫,无纤茖态,当时论台湾书家者,皆尊其为宗匠。”[5]张氏应该算是台湾书法碑派代表人物。他的大字 “高山仰止”胎息褚遂良,用笔顿挫明显,放浪泼辣。劲爽方折中饶有碑派韵味。张朝翔 《孔子定六经》轴中的魏碑味道,十分明显。可以说,张朝翔是台湾碑派书法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他的碑味源自用笔,结体基于唐楷造型。这是台湾本土碑派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典型特征。此一时期另一个台湾本土书家陈维英,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创作。他同样是把褚遂良的书法写出新意,出现了碑味。但是从运笔上增加了内擫,结字上疏下密,重心下移,或许是受了张瑞图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与张朝翔接近,在结字特征上都是源于唐楷褚遂良的布局。
道、咸、同时期,大陆书法已经完成了碑派书法从隶书到魏碑的发展转化。魏碑在包世臣的提倡之下,发展态势如火如荼。此时的台湾书坛则是由于吕世宜的到来,才开始金石学的研究与传播,台湾碑派书法的隶书创作的时代已经到来。以台北板桥林家为中心,向周边辐射。除了板桥林家的教授学生这一传播方式之外,文人雅士结社雅集,唱酬吟诵,挥毫题字,成为当时书法传播的重要方式。
以吕世宜为中心的吕派书家群的形成,是台湾碑派书法走向成熟的标志。碑派书家吕世宜以隶书为主的书法创作,与伊秉绶双峰并峙,成为闽台碑派书法的主要代表。吕氏博闻强记,过目的法书名品不胜枚举。他在其在厦门玉屏书院读书时,老师周凯曾为其母撰写 《黄孺夫人墓志铭》,[6]为表答谢,而吕氏将自家珍藏的清画家王原祁的山水画赠与周凯。吕世宜也将这篇墓志用篆书重新书写出来。此方墓志篆法类汉篆,方笔居多,大概是受到汉代的砖瓦陶文的影响。吕世宜的收藏甚富,这对于他的书画鉴赏及书写水平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吕世宜来台湾后,为台湾的金石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蒙昧的蛮荒之地,在吕氏的开拓下,文化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吕世宜是闽台隶书书法的巨擘。1924年的 《台湾时报》(第1期)曾如此评论:“有清一代篆书,至邓完白、吴昌硕尚矣,若隶书,则完白之外,陈曼生、伊墨卿、桂未谷、叹观之矣。而吾台则仅知有吕西村而已。”[7]吕世宜在隶书方面颇为自信。他说:“去年夏六月破三日工夫:解衣盘礴,为小山五兄作大隶千文,……兴致酣适,动与古会,五百年后,定成百金之物……小山自云渠在省邸仿予隶法,一纸可值数百钱。”[8]
吕世宜隶书在台湾的影响可见一斑。吕世宜隶书是继伊秉绶之后的又一重要书家。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他是以伊秉绶隶书的朴茂、敦厚、古拙为基础,进行改造,使隶书的笔画更加灵动飘逸,古拙中不乏生动,古朴中乃见篆意。
吕世宜的碑派书法传到台湾以后,追随者甚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书家有郑用锡、杨浚、郑贻林、郑鸿猷、陈蓁、林占梅、林士传、王石鹏等。陈蓁、郑贻林、林占梅继承吕世宜的书风,颇得其神韵。学习吕世宜隶书的书家日渐增多,吕世宜书风在吕派书家的推广下影响日益增大,吕世宜隶书书风在台湾影响大于内陆。首先缘于清代大陆文化生态环境中碑派书法已经非常成熟,金石考据、收藏鉴赏推波助澜,把碑派书法促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其次是在台湾地区,帖派书法虽占主流,发展态势远逊大陆;碑派书法处于被忽视的劣势,总体上是滞后于大陆的。台湾碑派书法在吕世宜和吕派书家的传承与传播下,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优于大陆的态势来。
台湾碑派书法的发展,除了受吕世宜碑派书法影响之外,以何绍基为代表的碑派书家群逐渐形成,成为与吕派书家群分庭抗礼的碑派传承、传播团体。何派书法从大陆辐射到台湾,在道、咸同时期是碑派书法发展的另一重要支脉。何绍基以碑意入楷行,把颜体写得古朴生拙中带有灵动,是帖派书法发展中的创新推动者。他的追随者沈葆桢、吴鲁、陈祚年、江国栋、章炳麟、林纾、龚植等文士,成了清后期台湾碑派书法发展传播的中坚力量。
后来日据时期的苏镜潭、张希衮、萧联魁、洪以南、许南英推波助澜,把何氏书风升华。吕世宜书法传播,开始就是个人行为。碑派书法的输入,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是小范围的传播,并没有造成对台湾本土明清以来帖派书法的影响。
台湾地区的明遗民书家与原住民书家,是组成台湾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明郑政权的消亡,碑派书法的传入。吕世宜碑派书法的传入,是台湾碑派书法发展的开始。这个过程相当缓慢,尤其是在帖派已经广泛传播的大环境之下,碑派书法的传播,并非主流,没有改变台湾帖派书法发展的方向。日据时期,日本碑派书法的传入,同样受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随着教育与影响的加深,书学交流的增加,书法传播逐渐顺畅,闽粤台三地的交流频繁,书道展览会上的交流更是增加交流的方式。碑派书法出现了真正的成熟期。但是台湾碑派书法从来都是受到大陆碑派书法及吕世宜书法的影响。也就是说,日本书法影响是有其限度的。
正如孙春英所说:“主流社会对少数族群的同化,并不能彻底割断少数族群的文化与历史的根系。”[9]台湾本土书法源自明郑遗风,作为遗民书家为主的族群,其文化语言、宗教、习俗、都无差别。这个族群接受文化的能力是很强的。他们作为台湾文化的族群,在接受大陆主流文化时,是不会全部接受,甚至存在着抵触现象,这主要体现在与大陆文化主流的错位上——如台湾在碑派书法的发展相对滞后于大陆碑派的发展。
三、明清时期闽、台碑派书法的审美观比较及其衍变
明末清初的大陆书坛,崇尚质朴、率真,崇尚个性发挥,张扬。从赵、董书风中走出来,开始转向篆、隶书的创作研究与金石考据。明郑时期的审美,受到宋朱熹、明陈白沙的影响,书风遒劲、爽朗有神。
由于在金石考据学的引导之下,书法的审美取向逐渐向崇尚 “骨力”过渡。清人杨宾认为:“书贵有骨,然骨存其人,非可强而致也。”[10]又说:“学书先取骨力,骨力充盈乃遂变化。收藏至于潜伏不露,始为精妙。”[11]崇尚骨力的碑学观,是从明人就已经开始了。如大陆的周亮工,张朝翔的书法,可以看作早期碑派书法的中坚、代表人物。
明代台湾的南明遗老,下笔铮铮骨气,备横扫六合之势。这是书法审美崇尚瘦硬清劲的结果。此时的这种审美取向是自发的,在大陆碑派书法传入之后形成的。
清中期,吕世宜的隶书风格的形成,也是基于重 “骨力”、崇尚 “瘦硬”的审美思潮而形成的。吕世宜的篆、隶书追求气韵生动,他在 《西狭颂》跋中写道:“书以韵胜,尤以气胜。舍气胜求韵,便弱而无骨,虽文亦然。此碑韵极好。”[12]
毫无疑问,这种审美取向与清代主流审美思潮是一致的。与伊秉绶相比,吕世宜的书法有韵味,有别样的趣味。吕氏的趣味缘于他的广泛的取法。譬如在铜壶铭文、权量铭文、砖瓦陶文中的浸淫,也是他的篆隶书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吕世宜的出现,在台湾很是震动;吕氏出现后,大陆碑派书法在台湾的影响远超帖派,成为书学者争相效仿的对象。与伊秉绶相比,吕世宜的书法胎息秦汉古碑,气息纯古。运笔上饶有新致,趣味盎然;伊秉绶则朴拙厚重,大气磅薄。他在书写上拥有自己独到的审美观:他以少量的楷书笔法入隶,使得隶书有了新的趣味;他的创造还在于笔法上,平铺直叙的笔法,加上大疏大密的空间,更使得其风格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吕世宜在风格上继承之,获得了其结构布局之法,运笔变得灵动飘逸起来。
“尚瘦硬”的书法审美观在邓承修的书法上体现到了极致。在吕世宜之后进入台湾的书家如邓承修,就是把碑派书法审美的取向推波助澜,以篆隶笔入楷,实现了碑派书风传播过程中由隶书向篆书书体的转变。邓承修的这种以篆隶书笔意入楷书的做法,是缘于邓石如以碑的笔法入楷。邓石如格调高古,而邓承修清劲过之,气息乏古,就略逊一筹。
实际上,在碑派书法的传播过程中,颜、欧、柳等唐人书体已经掺杂了碑味,具有碑帖结合的倾向。台湾现存碑刻中有许多唐楷石刻作品都具有明显的碑味,直到日据时期六朝书风的传入,才逐渐转师北碑笔法,碑派书法的审美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综而述之,台湾碑派书法的萌芽、发展到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与大陆碑派书家的交流与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台湾碑派书法审美的倾向性逐渐显露,书学观衍变的脉络日渐清晰,以致碑派书法的格局日渐稳定成型。尤其是在日据时期,大陆书家与台湾书家的交流日益增多,碑派书法在台湾的传播日将增多。当时台湾成为亚洲书法传播的重要阵地,可以代表亚洲书法的整体水平。大陆的书家尤其是闽粤浙等地书家非常活跃,来台湾的书家日渐增多,交流也比以前频繁。台湾碑派书法思潮,日益成熟与强大,逐渐成为引导台湾20世纪早期碑派书法的先锋。
注释:
[1]本研究为泉州市社科规划项目 “明清时期闽台书法研究”(项目号2015D46)研究成果。
[2]崔咏雪 《翰墨春秋—1945年以前的台湾书法》国立台湾美术馆2004年版第27页。
[3]凌继尧 《中国艺术批评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470页。
[4]刘恒 《中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3页。
[5]崔咏雪 《翰墨春秋---1945年以前的台湾书法》国立台湾美术馆2004年版第27页。
[6]此拓本属民国拓本,现存厦门市图书馆古籍部。
[7]卢嘉兴 《台湾金石学的导师吕世宜》见 《台湾研究汇集》第一辑第28页。
[8]吕世宜 《爱吾庐题跋》林静毅定静堂发行1975年版第50页。
[9]孙春英 《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326页。
[10]清杨宾 《大瓢偶笔》见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第581页。
[11]同上第553页。
[12]吕世宜 《爱吾庐题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第179页。
作者单位:福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