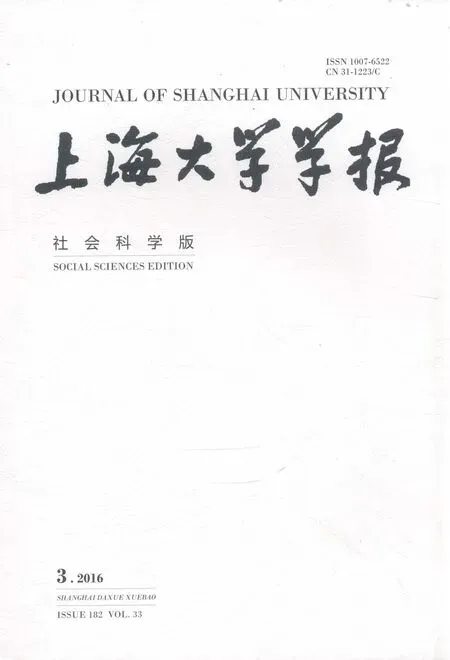从扬州到上海:近代转型期的江南城市书写
——以《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为例
景 春 雨, Rania Huntington
(1.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2.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东亚系, 美国)
从扬州到上海:近代转型期的江南城市书写
——以《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为例
景春雨1,Rania Huntington2
(1.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200444; 2.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东亚系,美国)
摘要:晚清小说《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分别以扬州和上海为叙事背景,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城市意象的展示,揭示了近代转型期江南城市的不同转变。前者对扬州城市意象的书写反映出作者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怀,向传统价值观念的回归。而后者对上海城市意象的书写中则表达了作者对现代都市生活形态的认可,对现代都市价值观的认同。在这两种不同的城市书写中,一方面反映了近代转型期江南城市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作者对现代都市价值观念的某种认同。
关键词:《风月梦》; 《海上花列传》; 江南; 城市; 转型
作为晚清世俗小说的代表作,《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以极具地域色彩和时代气息的形式分别展现了19世纪晚期中国江南城市的特定生活景象。尽管因其题材的特殊性,后世的小说研究者大都把这两部作品归入“狭邪小说”一类,但还是有研究者认为,《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并不同于一般的狭邪小说,其重要性和研究价值也并不仅限于其特定类别的题材这一方面,其独特的城市意象书写为我们研究近代转型期的江南城市文化及其价值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美国汉学家韩南(Patric Hanan)甚至认为,就其叙事背景而言,《风月梦》堪称“中国第一部不折不扣的‘城市小说’”,而且“《风月梦》还构成了第一部上海小说《海上花列传》写作和阅读的文学语境”。[1]而《海上花列传》也在问世后得到了较高评价,胡适称其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张爱玲则认为“《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我们不难发现,《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这两部作品同属近代转型期江南文化语境下的产物,无论是以扬州为背景的《风月梦》,还是以上海为背景的《海上花列传》,讲述的都是发生在城市里的风月故事。雷蒙·威廉斯认为:“city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定居地,并且隐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现代意涵,是从19世纪初期才确立的……这个词所强调的现代意涵可以从其形容词的用法日渐抽象化(摆脱‘特殊地点或行政体系’的具体观念)及对于大规模的现代都市的描述日渐普遍化两方面看出。”[2]在这两部作品中,城市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产物,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意象。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两部作品中的主要城市意象,进而分析这些城市意象的意义所在。
一、《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的城市意象
据考证,《风月梦》大致成书于1848年,署名为“邗上蒙人”,1883年由上海申报馆印刷出版。作品以当时扬州混迹于妓家的几个特定人物为故事主线,以扬州的城市风貌为背景,重点展现了发生在这样一座城市中的欢场纠葛。按书中第一回“浪荡子堕落烟花套;过来人演说风月梦”中所表,作品主要目的是要揭露风月场中的种种毒害情状,以警示世人。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品以“风月”为题,却并未完全将笔墨集中于“风月”之上,展眼处皆见扬州的城市风貌和市井人情,不啻一部晚清扬州的生活志。作者用主人公的行动轨迹作为导引城市地理空间转换的主要手段,将其细化到具体的街巷名称和宅院处所,主人公的每一次活动都是对这个城市某个区域、某类生活情境的表现。这种设置手法不仅揭示出城市的空间意象与主人公的亲身体验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城市意象具有了更加深切的文化符号功能。
在《风月梦》中,五个主要人物分属于不同的群体,他们穿梭于教场茶坊和进玉楼、九巷强大家这两处烟花地之间,这些游乐场所和风月场所是其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接点。《风月梦》的几个人物中,陆书是唯一的外来客,扬州的城市意象在他的关注下显得格外真切。第三回中,陆书从住处去袁猷家拜访,一路行来,“但见那:门名宝钞,乃水陆之冲途。衙属行辕,辖扬由之关部。连楚接吴,达淮通鲁。络绎行人,稠密烟户。税务房稽查越漏,悬虎头牌示以扬威;门兵班严拿奸究,挂狼牙箭袋而耀武。旅店灯笼,招往来之过客;铺面招牌,揽经商之市贾。进城人出城人,呵气成云;背负汉肩担汉,挥汗如雨……男装女像,抹粉涂脂,人作兔畜受人拘;强讨硬化,乞丐玩蛇,车载驴驼装货物。大商小卖做生涯。真是十省通衢人辏集,两江名地俗繁华”。[3]14即便在这样的盛景下,城内的商业也已显出颓势,在一条名为埂子大街的商业街上,陆书见到有许多戴春林香货店,但是有的柜台前许多人买香货,买油粉的,纷纷拥挤,但也有的柜台外冷冷清清。在陆书随后所到之处,如“太平马头”“小东门”“大儒坊”“南柳巷”以及“北柳巷”等具有扬州特质的城市意象中,也是在繁华中夹杂着落败的景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扬州作为江南重镇由盛转衰的文化变迁。
早在清代中期,李斗穷30年心血所作《扬州画舫录》中曾多次提及“湖上泛舟”的美妙和惬意,使其成为时人心中扬州的经典城市意象,后人对扬州的想象也多由此而生。在《风月梦》第五回中,贾铭在行船途中向陆书介绍说:“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小虹园,夕阳红半楼,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碶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冢。”陆书接口说:“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哪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3]31作者通过船行的路线将扬州此时的城市风貌勾画出来,今日尚还有如此景致可看,遥想当年更不知该如何繁盛,今昔对比中更添苍凉没落之感。此处以景衬人,似为后文中各人的遭际埋下伏笔。在第十三回中,时值端午,陆书因其贪恋的妓女月香要看龙船,故而花大价钱雇了船,邀约其他几人带着各自相熟的妓女同游。“众人打扮得金翠辉煌,衣衫华丽”,“那些大小游船纷纷来往,又听得锣鼓喧天,远望旌旗蔽日,各色龙船在水上如飞而至”。各个龙船上也都有人表演杂耍把戏以助兴。按作者所言:“今日是端阳佳节,扬州风俗,八鸾聚齐,两岸游人男男女女,有搀着男孩,有肩着女孩,那些村庄妇女,头上戴着菖蒲,海艾,石榴花,荞麦吊挂……各种小本生意人趁市买卖,热闹非常。”[3]94主人公陆书也陶醉在眼前的光鲜表象中,忘乎所以,对朋友的欺罔和女伴的不忠全然未觉。这种城市意象与个人亲身体验之间的应和在第十六回中被推到了极致。因六月十八日月香要到观音山还愿,陆书又不惜重金雇船邀众人前往,他在朋友的怂恿下极力铺张,为博女伴欢心一味将场面做大,一路大肆吹唱玩闹引得众人围观。在这种银钱硬撑起来的光鲜景象中,陆书的虚荣心和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发展到了极致,他的亲身体验似乎也在扬州的盛景中达到了最完满的状态。陆书对这座城市的空间性介入是在追逐声色体验的过程中完成的,他与这座城市之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是完全由金钱支撑起来的。可以说,陆书现有的城市观感和消费行为与他自己曾有的“扬州梦”构成了一种互文性,这种现实感的缺失为其后来在落魄中离开扬州埋下了伏笔。
无独有偶,在《海上花列传》中也有对于城市意象的类似表述。1892年《海上花列传》单行本问世,作者署名花也怜侬,实为当时上海文人韩邦庆。尽管作者在小说第一回中也表明了劝诫之意,但从小说的整体叙事情态来看,作者的所谓劝诫之意远不及《风月梦》中来得明显。相反,《海上花列传》中呈现的诸多现代城市意象不仅冲淡了作者开篇言明的立意,而且也使得其认同之意远甚于劝诫的意图。早在《风月梦》第二十五回中,妓女凤林在寻出路时对恩客贾铭道:“前日有人向我说是上海地方,有人在扬州弄伙计,情愿出四十块洋钱代当。他叫我去,我却未曾允他。”而凤林的恩客贾铭却说:“你是为何不去……去走一晌,恐其那里比扬州好些,弄几两银回来,岂不好呢。”[3]182彼时上海即以一种较好的前景召唤着这些渴求出路的人,到了19世纪末,上海更显出了与江南地区其他城市不同的特质。相较于扬州,19世纪末的上海移植了更多的外来文化因素(本土的与异国的),其整体文化底蕴也不复为单纯和整一的 “江南”品性所能概括的。由周边地区涌入的新移民带来了多面的“江南”品性,而“租界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对物质生活享受的欲望。所有这些享受又必须以金钱为条件,于是,传统的道德体系的约束力便逐步瓦解,渐次由新的价值标准所取代。如时人所批评的,上海人只耻衣服不华美,只耻逛二等妓院,耻外出坐小车,耻去戏园坐二等,唯独‘身家不清不为耻,品行不端不为耻,目不识丁不为耻,口不能文不为耻,而独耻数端,亦可谓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甚矣’”。[4]113这种以消费性为导向的城市品性在《海上花列传》中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揭示。
如果说,在《风月梦》中,作者对扬州城市意象的展示多依傍于传统的江南生活形态,主人公往来于其间的各种城市空间也都具有传统江南城镇的典型特征,如教场里的说书表演、龙舟会上的杂耍,堂会中的戏法和双簧表演,还有颇具诗书氛围的文人迷社“红梅馆”等。那么在《海上花列传》中,上海这座新兴城市的空间意象则是由颇具现代观感的马路及具有现代意味的空间符号织就的。1861年,太平军占领江南一带后开始实行禁娼的举措,其势力所及之处,南京、扬州、苏州等地原操此业的女性有很多都避走上海。她们到了上海后又重操旧业,寓所主要分布在租界内的大马路、二马路再到五马路之间所形成的街区内,由于居住地较为集中,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遂成大观。《海上花列传》中提及的几位主要女性人物的居所都在这一带。如陆秀林的书寓聚宝堂位于西棋盘街,沈小红的书寓在四马路荟芳里,周双珠的书寓在三马路旁的公阳里,张蕙贞和吴雪香的书寓在四马路旁的东合兴里,黄翠凤的书寓在四马路旁的尚仁里等。这几条马路是租界内的主要交通干道,除了数量众多的风月场所外,另有洋行、戏院和菜馆等密布其间。这些现代都会的城市意象一方面通过鲜明的个人体验揭示出个体与城市之间的关联,另一方面又通过其间发生的社交行为揭开了城市公共生活中的一隅。《海上花列传》中第六回描写商人葛仲英带相好的妓女吴雪香和娘姨小妹姐去位于大马路上的亨达利洋行购物,“踅进洋行门口,一眼望去,但觉陆离光怪,目眩神惊。看了这样,再看那样,大都不能指名;又不暇去细细根究,只大略一览而已。那洋行内伙计们将出许多玩意儿,拨动机关,任人赏鉴。有各色假鸟,能鼓翼而鸣的;有各色假兽,能按节而舞的;还有四五个列坐的铜铸洋人,能吹喇叭,能弹琵琶,能撞击金石革木诸响器,合成一套大曲的;其余会行,会动的舟、车、狗、马,不可以更仆数”。吴雪香要了一只嵌在手镯之上的时辰表。出了洋行后,一行人又乘钢丝马车游玩,“比及到了静安寺,进了明园,那时已经五点钟了,游人尽散,车马将稀……从黄埔滩转至四马路,两行自来火已点得通明”。[5]44-45资料显示:“在19世纪70年代,若由洋泾浜弃船登英租界,首先进入的繁华街区是被称为‘夷场华人街’的宝善街,沿街设有茶楼、戏院、酒肆、栈房、妓院、赌窟等,都是些纯‘老中国’式的休闲娱乐场所。但这些传统消费样式,在由南向北作蔓延之势时,很快和一种由东向西扩展的消费模式及生活方式纠合起来,在80年代的四马路上,汇聚成了一种与传统判然有别的文化景观……而这时期最能代表四马路消费特征的,依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三楼’——茶楼、酒楼与青楼。但无论在其规模、设施、功能及文化内涵上,都已经现出一种别样姿态。”[6]26而这些极具时代文化特质的城市意象正是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所依托的地理空间。自19世纪60年代起,租界设立的工部局便开始在上海这座城市的相应区域内对道路、街区、照明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建造和管理,这些举措使上海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逐步显现出一座近代城市的轮廓来。这些具有现代地理空间意义的城市景观不仅使这座城市呈现出更具现代性的都会意象,而且也催生出一种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如丹尼尔·卡瓦拉罗所言:“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所以,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的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7]
二、《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的城市与人
与城市的地理空间相对应的,是活动于其间的人,他们不仅是构成城市意象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特质的代言人。值得一提的是,《风月梦》的成书年代正值扬州的传统产业——盐业的衰落时期,而小说中提及的各色风月场中的女子似乎已取代原有的产业,成为此时扬州这座城市的唯一特色,主人公之一的陆书即是专程到扬州来买侍妾的。有学者认为:“提及晚明和清代扬州有关的社会现象,其中最常见的就有姨太太和妓女。对她们的频繁描述,部分意义上乃是出自于她们所占据的社会位置的一种功能。对于书写她们的男人而言,这些女人相对显眼、可亲近,而且由于她们所受的训练,有时还能亲自写作,尽管其素材不一定与男人所写的相同。她们与城里的某些社会空间和特定社会行为相连。将她们与另外那些更不显眼的扬州良家女子放在一起来思考,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洞悉该城的籍贯等级,该等级与当地经济行为的关系,以及关于这座明清时期大都市的历史记忆中呈现的矛盾心态。”[8]192这些女子所从事的特殊职业赋予了这座城市以特殊的印记,当这座城市所能提供的只是这些被物化的女性时,它的衰败也就不难理解了。《风月梦》中的一众女子尽管身世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是因自己的亲人之故才走上这条路,其名曰“做生意”,而所持资本则是自己的身体。这似乎是当时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家庭所采用的最便捷的解除困境的方式。陆书中意的妓女月香是被自己的叔父捆到扬州,卖入妓馆;与袁猷相好的妓女双林由舅舅卖入妓馆;魏壁中意的妓女巧云则是由自己的父亲卖入此间的。与贾铭相好的妓女凤林由婆婆带入这个行当中,担负着养活一家的重任,而她的丈夫和大伯则靠她赚来的钱每天出入烟馆,游手好闲。与吴珍相好的妓女桂林也是被婆婆和丈夫逼迫着从事这种职业,他们时常自乡间来探视她,每每找到她“不是吵着闹着非要十千就是八吊,还要买这样那样,盘缠、礼物,住在这里的房饭钱,零用钱”。[3]173这些风月场中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一面用自己的才情和鲜亮的洋布衣裙点缀着城市空间的迷离幻景,显示着自身的物化特质;一面又受制于传统的道德枷锁,不得不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双林为袁猷殉节显示出对传统道德的固守,凤林弃贾铭而去则显现出一种在抛弃过往生活时的决绝,而桂林与巧云的出走则可视为一种暂时的逃避。《风月梦》中女性在逐利与守义间徘徊,她们的不同抉择昭示着这座城市在近代转型期踯躅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暧昧与犹疑,而这些特点在其后的《海上花列传》中明显地被弱化了。
在洋行、公园、马车疾驰的大马路所建构的城市空间内,《海上花列传》中的个人生活体验比此前《风月梦》中的传统江南城市更加丰富,也更具现代气息。在这种城市意象所营造出的氛围里,一众妓女的寓所不仅是追逐声色的欢场,更是展现城市生活多样性的重要空间要素。这里不仅为私人间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较为稳妥的交易场所,还为士绅和官、商的社交行为提供了较具私密性的保障。“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9]参店老板洪善卿、古玩掮客庄荔浦、洋务官员王莲生、候补知县罗子富、退居官员齐韵叟、帮闲文人尹痴鸳、旧家子弟华铁眉等人都是在这种社交场合下纠合到一起,他们活跃在上海的多重城市空间中,营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现代生活方式。或者也可以说,正是近代转型期的上海所提供的多义性城市空间才塑造了这种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生活。对生活于其间的作者而言,《海上花列传》只是一种现代城市生活体验的表达形式。
同《风月梦》一样,《海上花列传》中也有一群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也是构成上海城市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时而穿梭于各个局会之间,为各种社交场合增光添彩;时而乘坐时兴的钢丝马车在城市的繁华盛景中留下自己的倩影;她们更可以堂而皇之地与男伴一起游公园,逛戏园。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在1880-1890年代,妓女是公共娱乐区人数最多、活动范围最广、个体消费最活跃的女性群体,她们带有个体取向的消费选择已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10]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海这样的特殊空间语境下,这些女性的特立独行已显现出具有不同以往的个人价值取向,彰显出某种特殊的城市文化品性。她们谙熟上海这座商业城市的生存法则,在逐利与守义间显得并不那么踌躇。尽管她们也不能在任何处境中随时随地做到游刃有余,但至少她们在做出抉择时的个人意向是十分明确的,即是说,具有更加清晰的自我意识。第二十三回中,妓女卫霞仙抢白前来书寓兴师问罪的姚季莼之妻说:“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啥人个家主公!耐个家主公末,阿是勿许倪做嗄?老实搭耐说仔罢: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轨迹?”[5]187这样一番说辞,竟使因道德优越感而盛气凌人的姚奶奶败下阵来。卫霞仙的胜利也是她所倚仗的商业法则的胜利。在这种法则中,赤裸裸的逐利原则堂而皇之地击退了传统的伦理和道义。另一位颇有个性的妓女黄翠凤本为老鸨黄二姐的“讨人”,但她并不甘于任人摆布的命运,在老鸨体罚过后以吞生鸦片烟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后来老鸨对俚跪仔,搭俚磕头,说:‘从此以后一点点勿敢得罪耐末哉。’”[5]48黄翠凤才作罢,并以此争得了自己的自主权。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及价值,善于利用罗子富对她的情感和信任为自己谋划较好的出路,她不仅在后者的帮助下赎身成为自由人,更在其后与老鸨黄二姐合谋敲诈了罗子富一大笔银钱,极力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在黄翠凤的行为中,逐利的商业生存法则是第一位的,情与义只在为利所用时才会被拿来进行装点。在她的行为方式中体现了与现代商业都会的文化品性相一致的特点。她们清楚自己身份的物化特性,也善于利用这种特性,这些摆脱了传统价值观念束缚的女性与《海上花列传》中展现的现代商业都会是相伴而生的。在对这座城市、这群人物的白描中显露出作者对这种行为方式的赞赏和对这种现代城市品性的某种认同。
三、《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的价值取向
由于文化传统及经济发展态势的原因,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名镇,其繁华程度及文化声名远不及苏州、扬州及江宁(今南京)等地。就在开埠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海迅速崛起,至19世纪70年代,上海已渐取代其他城市成为当时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与此同时,晚清时期的扬州这座以盐业为生的城市,由于官方盐业政策的多次调整,航运重心的转移等原因而逐步走向衰败。在《风月梦》之后,以扬州为故事背景的文学作品逐渐减少,而以上海为背景的作品却日益增加,这其中除了江南作家大量涌入上海这一原因外,两座城市间的盛衰差异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作为传统江南城市的扬州虽因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从地理空间上呈现出衰败的迹象,但其传统江南文化的精神品格却在社会群落的聚合与流动中被带入了上海这一新兴城市。“租界的早期繁荣,以四马路上传统‘三楼’的兴盛为表征。位于该路上的青莲阁、一品香、荟芳里等消费场所,虽添进了若干西方元素,但其运载的基本文化形态,却不脱江南城镇生活之特点。传统‘三楼’在早期上海租界的华人移民群中,曾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社会整合’功能,它将一批批来自传统中国的‘陌生人’,聚合于他们共同熟悉的空间,并借此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6]78可以说,上海这座现代商业都会的繁盛是传统江南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共同建构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几乎被视为近代转型期传统江南文化向现代转变的成功范式。有学者甚至认为,“上海连同其外国租界、大型建筑、铺砌整齐的道路、自来水、电、汽车和无轨电车,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新扬州形象提供了一般的背景”。[4]280
在《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中都涉及了城市和乡村的某种对照性视角,并以此来显现作者自身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态度。在《风月梦》中,袁猷的乡下表弟穆竺在为自己的婚事采买零碎用品的时候初到扬州,他被吴珍等人强拉到他们常去的九巷强大家,他的反应处处显出与这类典型城市消闲方式的格格不入,最后几乎是在窘迫中落荒而逃。小说结尾处,穆竺因要为自己的新生儿买银锁与银镯而再次来到扬州,他刚巧目睹了为袁猷殉节的双林因节烈被官府批准入家祠的仪式,他对这样的热闹场面依然“不知何故”而无动于衷。在作者笔下,穆竺以务农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与城市的联系仅止于有限的经济行为,他因远离城市生活而得以保全自身,没有如陆书一般被卷进城市的漩涡中无法自拔。尽管穆竺在全书中仅出场两次,但这一人物的设置显然具有极强的对照作用,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作者本人对城市生活方式与传统乡土文化价值间的取舍。
如果说,《风月梦》的作者是通过“乡下人”穆竺的生活圆满与袁猷等人悲剧性结局的对照来显示乡村道德价值的优越性,从而表明退守乡土、放弃城市文化价值的立场的话,那么《海上花列传》的作者则是通过赵氏兄妹在上海的挫折与坚守显示了与现代城市特质相关的优越性,间接表达了对城市文化价值的认同。在《海上花列传》中,生活在乡间的赵氏兄妹从一开始就对上海有着无限的向往。赵朴斋虽然无法在上海安身立命,但他宁愿做朝不保夕的洋车夫,留在上海做城市生活的看客,也不愿回乡下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妹妹赵二宝打着寻兄的旗号来到上海,结果一头扎进城市的五光十色中不愿回身。当遭遇到经济困境后,她更是毅然说服母亲主动开起堂子做倌人。“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5]290在落魄后遭舅舅洪善卿冷遇时又理直气壮地放言:“俚末看勿起倪,倪倒也看勿起俚!俚个生意,比仔倪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仿勿多。”[5]545她自认为自己开堂子做倌人和舅舅做生意从本质上说并无二致,因此也无需为此感到矮人一等。尽管和其他妓女比起来,赵二宝的结局较为凄惨,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在上海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意愿,并且从未将自身的受挫归咎于这座城市。在赵氏兄妹身上,体现出舍弃乡土世界的决绝和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与眷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态度。至少在叙事形态上,作者对这种因盲目投身于城市生活方式而不去追问道德正确性的行为并没有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批判,仅以近乎实录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谈到清末狭邪小说的时候,鲁迅认为:“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已;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11]不能不说,在“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态度背后,显现的是作者对现代城市价值观的某种认同。
在从《风月梦》到《海上花列传》的城市意象转换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不断被强化的自觉的城市书写意识。这种城市书写意识的增强反映了近代转型期江南传统文化与现代都会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就其内涵而言,江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交织着多种要素的复合性文化概念,它与众多类似的文化概念共同打造了文化意义上的传统中国。江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性形态,在近代转型期遭遇了多重挑战,既有来自异质文化的冲击,也有来自同一文化情境内部的挤压,它们共同促成了传统江南文化的现代转变。上海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现代江南的代表形式,也即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对现代都市文化形态采取了一种主动介入的姿态,通过建构具有多义性的现代城市空间的方式,缓冲了传统要素与现代文化形态之间的冲突。也正因如此,较之于《风月梦》而言,《海上花列传》中的城市书写意识显得更为自觉,这种自觉的城市书写意识所彰显的现代价值取向也逐渐成为转型期江南文化认同的最终指向所在。
自《海上花列传》之后,大量以“海上”为叙事背景的小说所展示的上海城市意象,正说明了一种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江南城市书写意识的形成过程。如李欧梵先生所言:“如果我们如此审视当时晚清的通俗小说,只要牵涉到维新和现代的问题,几乎每本小说的背景中都有上海。而上海的所谓时空性就是四马路,书院加妓院,大部分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四马路,因为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大都住在那里,晚睡迟起,下午会友,晚饭叫局,抽鸦片,在报馆里写文章,这是他们的典型生活。从这个方向重新勾画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就会关涉到晚清小说所真正代表的那个层次——都市小说读者的世界,他们的世界也正是小说文本试图展示的世界。”[12]身在其中的感受性已超越了对这种情境的道德批判性,由此,在这种对现代江南城市的书写中逐渐显露出一种自觉的认同意识,这种认同意识是更加趋近于现代而背离传统的。
结语
从《风月梦》到《海上花列传》,由传统江南文化代表的扬州到现代都市文化代表的上海,这种城市书写重心的转移反映出近代江南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某种价值取舍。如前所述,在《风月梦》中已有妓女舍弃扬州投奔上海而去的情节,而在《海上花列传》中,上海已然成为江浙一带最具吸引力的城市。无独有偶,在稍晚于《海上花列传》成书的《海上尘天影》这部作品中,其主要人物如顾士贞、庄伯琴及吴冶秋等,也无不纷纷弃扬州而取上海,去拓展自己的事业及交游空间。在作者对这些人物的事业、情感及生活的演绎中,我们更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彼时上海城市生活中现代性转变的某种认同。
每一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大致都可以从物质、社会及文化这三个层面去把握,“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及使用和消费方式等,形成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互动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化娱乐、信息交换等,形成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13]而转型也即意指在这三个层面上的特定转变。对于中国近代的城市社会形态而言,所谓转型的重要标志还在于,人们的交往原则除了早期的“情”与“义”之外,又增加了“利”这一重要的制衡要素。在《风月梦》与《海上花列传》所展现的城市意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物质生活方式、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这三个层面的转变。但相较于《风月梦》和《海上花列传》而言,《海上尘天影》对这三个层面的转变以及城市各阶层生活中的逐利性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入的描摹。与此同时,除《海上尘天影》外,同一历史时期以上海为叙事空间背景的其他作品,如《海上繁华梦》《上海游骖录》《上海春秋》等,不仅在对城市现代化特征的展现方面表现出更为自觉的主体性,对因“利”而起的现代城市发展的复杂性也有了更多的触及。这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现代城市生活变迁的关注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转型期城市生活对作者的影响更趋深入。
可以说,正是在作者展现这些城市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中,扬州与上海这两座江南城市分别显现出了现代转型期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而显现出一种现代化进程中的程度差别。在愈加明显的“现代”价值观照体系中,扬州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分别具有了落寞与繁华的身份特征,也进而分别代表了“江南”的前世与今生。这种差别的形成一方面揭示出转型期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同因素对城市发展方向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演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文化价值认同的建构过程。“江南代表了一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经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洋泾浜文化最初形成之际,这种地方性的经验对于上海城市文化品格的塑成和定型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全球化、一体化语境愈发浓厚的当下语境中,厘清上海城市文化中的‘江南’质素,也即从现代化、城市化的普遍经验中提取出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因子,无论是对于上海城市文化今后的发展路径,还是对于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和借鉴价值。”[14]
参考文献:
[ 1 ]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M].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30.
[ 2 ] [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44.
[ 3 ] 邗上蒙人.风月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4 ] 叶小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 ] 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6 ] 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7 ] [英]丹尼尔·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64.
[ 8 ] [澳大利亚]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M].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 9 ] 张爱玲.海上花落[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319.
[10]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与社会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8.
[1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宁: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177-178.
[12]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6.
[13] 李长莉.晚清上海:风尚与观念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5.
[14] 许纪霖,罗岗.城市的记忆:上海文化的多元历史传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63.
(责任编辑:李孝弟)
Depictions of Yangzhou and Shanghai as Cities South of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TakingDreamofRomanceandBiographiesofFlowersinShanghaias Examples
JING Chun-yu1,RANIA Huntington2
(1.CollegeofLiberalArts,ShanghaiUniveristy,Shanghai200444,China; 2.DepartmentofEastAsia,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Madison,theUnitedStates)
Abstract:Dream of Romance(Fengyue Meng) and Biographies of Flowers in Shanghai(Haishang Hua Liezhuan)were late Qing Dynasty novels set in the cities of Yangzhou and Shanghai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t city images during different times revealed urban changes in the south of theYangtze River in the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 Dream of Romance conveyed a nostalgic reminiscence of the traditional lifestyles andvalues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the images of Yangzhou. Biographies of Flowers in Shanghai, however, carried a different tone and expressed the writer’s recognition and approval of Shanghai as a modern metropolis filled with urban lifestyles and values. The depictions of the two cities not only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ies in south of theYangtze Riverin the modern transition period, but also convey the writer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modern urban value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Dream of Romance; Biographies of Flowers in Shanghai;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cities; transition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3.009
收稿日期:2014-10-24
作者简介:景春雨(1977-),女,辽宁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3-0093-10
Rania Huntington(1968-), 女,美国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明清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