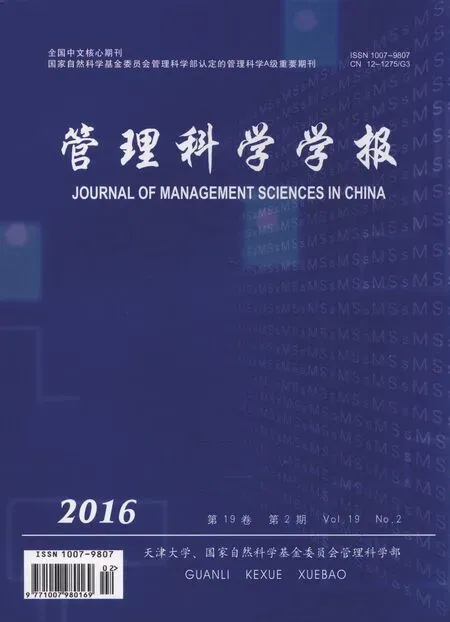御用会计师:合作抑或合谋①
孙 亮, 刘 春, 柳建华
(1.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广州 510275)
御用会计师:合作抑或合谋①
孙亮1, 刘春1, 柳建华2*
(1.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 广州 510275; 2.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承销商与某家会计师事务所形成固定组合共推IPO的现象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该文将与承销商形成固定搭配的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承销商的“御用会计师”,并选取IPO核准制实施之日至2011年12月31日所有IPO的公司为样本,对“御用会计师”现象究竟是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合作的结果还是发行公司、承销商以及审计师三方合谋的产物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御用会计师能够显著地抑制发行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这种制约效果随合作次数的增加而加强,在约6次左右达到最大值.研究结论表明,御用会计师是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多次博弈有效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关系能减少中介机构之间联合生产的交易成本,降低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御用会计师; 合作; 合谋
0引言
2009年IPO重启、创业板开板和随之而来的公司上市后的业绩变脸,将肩负定价和鉴证功能的中介机构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再一次推至风口浪尖.尤其是对于承销商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之间长期多次合作的情形,更是引起猜测无数.
的确,承销商对于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存在着明显的偏好.例如,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睐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2009年至2011年间,广发证券共承销45家IPO业务,其中与正中珠江合作10家,约占其承销业务总额的22%,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作5家,与其余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则偶一为之.无独有偶,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此期间却对于与原“天健系”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作情有独钟*所谓原“天健系”的会计师事务所是指由原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辽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共同组建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后经分拆合并形成如今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共获得93笔承销业务的平安证券与原“天健系”会计师事务所合作29次,合作比例高达31%.其中,与华普天健合作11次,与天健正信及天健也分别有9次合作.
并且,上述承销商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合作的偏好并非个别承销商在特定时期的特殊现象,而是广泛存在于我国IPO市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根据本文所做的统计,自2001年5月18日IPO采用核准制后至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前,有41家券商存此偏好;2005年至2008年间,有此偏好的券商为37家;而2009年至2011年间,有此偏好的券商数量增加到了72家.
本文将这种承销商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长期多次合作的偏好称为御用会计师现象.有趣的是,对于御用会计师现象原因和结果的理解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即合谋假说与合作假说.其中合谋假说认为,基于IPO所带来的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有着与发行公司相同的行为动机,都希望尽可能的协助发行公司包装上市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此时,承销商当然愿意向发行公司推荐那些更加“听话”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利于更方便更默契的对发行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合谋假说预期御用会计师将导致更低的承销质量.与此不同的是,合作假说则强调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曾经愉快的合作经历,强调彼此之间工作方式和执业质量的认可和信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双方在业务上更加平滑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因此与合谋假说恰恰相反,合作假说认为,御用会计师将带来更高的承销质量.
那么,御用会计师究竟是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合作的结果,还是发行公司、承销商以及审计师三方合谋的产物?显然,甄别上述两种假说对于监管IPO市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来说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此的讨论也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其一,既有研究大多侧重于讨论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IPO过程中各自的行为选择及其经济后果[1-3],却甚少考虑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博弈,因而也就忽略了团队联合生产这一IPO过程中中介机构活动的基本特征,更忽略了对这些中介机构的联合生产行为进行组织、协调以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将有助于强调IPO过程中各中介机构之间协调和适应的混合型治理结构问题[4],从而为该领域提供新的更加逼近于现实世界真实活动的研究视角.其二,与西方已有文献侧重于讨论在询价制度下承销商与参与报价的投资银行之间在新股定价、配售及之后的股价稳定方面的关系不同的是[5-7],本文重点探讨了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承销商并不具有超额配售权的现实极大的削弱了其与投资银行在IPO过程中的利益关系,而审计师所审定的拟上市公司的每股盈余却是承销商为IPO公司发行定价的重要依据,因此,承销商与审计师在IPO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更值得探讨.本文为此增添了新的知识.其三,尽管关系型契约在协调组织间活动中的治理作用很早便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4,8],以其为主体的适应理论也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成为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的经验证据却依然十分少见[9-10].因此,通过增添新的来自IPO情境下金融中介联合生产行为的经验证据,本文也丰富和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合谋假说及其悖论
由于发行公司与潜在投资者及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也由于IPO的发行价是以发行公司当前的每股盈余和行业的市盈率为基础来确定,因此招股说明书中的财务信息是否准确非常重要[11].而为了成功通过发审委的审核,也为了尽可能的提高IPO的发行价格,发行公司往往有着强烈的高估盈余的动机[12-14].所以,诸如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旨在帮助投资者鉴别发行公司质量的中介机构便承担起了资本市场“看门人”的重任.
然而,我国频繁爆发的欺诈上市案却让社会各界对于上述资本市场“看门人”们的职业操守和能力产生了极大的质疑,首当其冲的便是居于IPO利益链条中的重要中介承销商和审计师.在这样的情形下,御用会计师现象,即承销商偏好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搭档并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更是引起猜测无数.其中,最直观的解释无疑就是合谋假说.在合谋假说看来,以帮助公司成功上市并推高发行价格从而获取高额发行费用为共同的利益基础,承销商、审计师和发行公司有着通过IPO前盈余管理等手段粉饰和包装发行公司的共同的行为动机,御用会计师现象正是这种共同动机和诉求的产物.
然而,看似有理有据的合谋假说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承销商与资本市场中的监管者和投资者并非简单的一次性博弈关系,而是一个长期的重复博弈的过程.值得强调的是,企业向上操纵的盈余会在未来发生反转[15],其结果是投资者将因此而招致严重的损失[16].所以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承销商当前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其未来的市场份额减少、收费水平下降,甚至产生严重的法律风险[17-18].
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随着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逐步提高,承销商的声誉已经能够帮助其在未来获得更多数量以及更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的认可[19].亦即,良好的声誉为我国资本市场中承销商所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大.同时,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媒体等外部治理机制也得到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其积极的监督功能日渐显现[20-26],兼之证监会等政府监管部门还极大地加强了对于IPO财务欺诈的惩罚力度,所以承销商、审计师和发行公司之间若存在合谋行为,被揭穿并受到惩罚的概率也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形下,成本收益的双向变化势必会使得逐渐减少合谋成为理性选择.因此,如果合谋假说成立,则本文应能够观测到御用会计师呈明显的递减趋势.但与此相悖的是,承销商和审计师这种固定搭配的比例却一直比较稳定.
另一个明显的悖论来自对于合谋对象的选择.可以预期的是,如果承销商的首要目标是与会计师事务所及发行公司合谋,以便于对发行公司进行包装和粉饰,那么当然会倾向于选择更“听话”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固定搭配.因此,无论是从声誉损失还是市场竞争压力的角度而言,小的会计师事务所都更有可能成为其合谋的对象.然而现实却再次与此相悖.根据本文的统计,高达48%的御用会计师属于更加重视自身声誉的国内10大或国际4大会计师事务所.
1.2合作假说
合谋假说的诸多悖论意味着御用会计师现象的本质远比其表象复杂.实际上,它涉及到包括证监会和发审委、承销商、审计师以及发行公司在内的多种利益主体之间一系列激励与制约的互动,以及各利益主体在短期收益与长期合作价值之间的权衡.
具体而言,在我国资本市场典型的IPO过程中,发行公司能否成功上市需要得到证监会和发审委的核准.就承销商而言,由于承销商当前和未来所执行的全部IPO项目都必须经过证监会和发审委的核准,所以在承销商与证监会及发审委之间形成一种重复的无限博弈关系.与有限博弈不同的是,无限博弈将促使交易各方重视未来合作的价值,同时以未来合作价值为基础缔结起长期的、不成文的、隐性的关系型契约[27].并且关系型契约一旦订立,便因其未来交易取决于过去行为这一机制对当事人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28].在这里,承销商可以预期的与证监会和发审委之间未来合作的价值至少包括建立在声誉基础上的信任,及至更加便捷的审批.然而,一旦出现公司IPO后业绩变脸等媒体和投资者广泛关注的影响证监会及发审委声誉甚至相关官员仕途的负面事件,证监会就非常有可能通过延长审核时间、降低审核通过率等方式,极大程度的压缩被他们主观判定为违反了之前所达成的意会性的关系型契约的承销商的未来市场份额和经济收益.例如黄春铃[29]的研究表明,麦科特事件中证监会的严格稽查对南方证券随后的市场份额产生了非常重要的负面影响.而平安证券的例子则更为直接.当胜景山河事件在2011年底爆发后,由于被审核的尺度越来越严,平安证券2012上半年1/3的IPO保荐项目遭到证监会否决,从而转眼便从“保荐承销王”沦为“IPO杀手”*更详细的报导可参见经济参考报:平安证券承销项目1/3被否,昔日保荐王沦为IPO杀手..
与承销商和证监会及发审委之间的重复博弈关系不同的是,由于超过90%的我国上市公司在SEO时都将更换其IPO时的承销商[30],承销商与发行公司之间的交易往往表现为一次性博弈.在这样的情形下,很显然的,承销商违反其与证监会之间的关系型契约所导致的损失将远高于其单次机会主义行为所能够获得的收益.所以,承销商的理性选择将是在主观上倾向于对IPO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以防止其上市后发生诸如业绩变脸或股价暴跌等危及其与证监会之间关系型契约的不利事件的发生*最近的一些文献也为上述逻辑提供了相应的佐证.例如,利用美国数据,Lee 和 Masulis[31]发现承销商能够抑制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却没有发现审计师的类似作用.更重要的,Chen等[3]利用中国IPO公司的数据,同样确认了承销商的治理功能,也同样没有发现审计师有类似的抑制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功能..
然而,财务会计知识和时间精力的有限性又迫使承销商严格核查发行公司财务状况的愿望客观上必须依赖于与其搭档的审计师.但对于审计师来说,最关心的却是其与发行公司之间业务关系的长期可持续性.事实上,以提供令发行公司满意的审计服务为基础,审计师也通常都能够在发行公司上市后继续负责其年报审计工作,从而构成与发行公司之间重复的无限博弈关系.因此对审计师而言,为了维系其与发行公司之间关系型契约中所约定的未来长期合作的价值,即保持与发行公司之间业务关系的长期可持续性,鉴于发行公司尽可能调高盈余从而成功通过审核并实现更高发行价格的愿望,其理性选择将是在满足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最低监管要求下对其执行较为宽松的审查.很明显,此时审计师的行为与承销商的需求相悖.这意味着,如何激励作为联合生产过程中重要合作者的审计师,对于承销商维护其与证监会之间关系型契约非常关键,也成为决定联合生产的结果即IPO承销质量的重要因素.
为此,给予审计师御用会计师的地位,即承销商通过向审计师提供一份关系型契约,承诺未来优先将其推荐给自己所承销的客户,从而将二者的交易类型从有限博弈转变成无限博弈,就很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一方面,由于承销商手中握有推荐通道这一稀缺资源且其潜在的IPO客户非常多,一旦发行公司拒绝承销商所推荐的御用会计师,将很可能面临承销商的延迟推荐甚至辅而不荐的情形.所以,尽管发行公司在理论上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承销商所推荐的审计师,但基于承销商在IPO相关事项决策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由此而拥有的远远高于发行公司的谈判权,现实中接受承销商的推荐却往往是发行公司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承销商完全有能力为其御用会计师争取到更多的业务,其承诺是可以置信的.
另一方面,对于审计师来说,在审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形下,与承销商达成关系型契约从而获得其所推荐的新业务无疑将极具诱惑力,关系型契约中内含的未来合作价值即新的一系列的IPO业务以及这些发行公司上市后的年报审计收费无疑也将高于审计师维护单个业务所能够获得的收益.也就是说,承诺御用会计师地位的激励将改变审计师行为函数中的成本收益结构,从而促使其在权衡利弊之后适度提高审计质量以达到承销商对公司从严审查的需求.甚至更进一步的,在未来合作价值的激励下,审计师将有动力去理解承销商所要求的审核风格和关注重点,并致力于提供更多有助于承销商后续工作的信息.这些事前的专用性投资都将降低承销商与审计师联合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联合生产的效率并实现更优的联合产出即承销质量.而这又将反过来提高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关系型契约的适应能力[27].同时,由于审计师和券商在形成固定搭档之前行为取向相异,为了保证承销质量和降低每次IPO执业时与不同审计师沟通的交易成本,对于券商来说,与达到其所要求之审查水平的某些审计师展开长期合作显然也是更优的策略.于是经过多次博弈以后,承销商与某些会计师事务所便形成固定的搭档,产生御用会计师现象.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合作假说.
进言之,既然御用会计师现象是承销商与审计师合作的结果,则应当可以观测到与御用会计师相伴随的是发行公司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而如果是这样,也可以甄别与合作假说相互替代的合谋假说.因此提出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其他条件相同时,御用会计师能够降低发行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在配额制下IPO公司必须事前获得政府审批,承销商的作用和责任都很有限,所以本文选取核准制下IPO的公司为初始样本.对初始样本,本文执行了以下筛选程序:第一,剔除了金融类公司.第二,剔除了研究期间内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的研究涉及IPO公司发行后的业绩表现,这要求公司至少在2011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同时2001年5月18日“用友软件”为核准制下首家IPO的公司,故本文将2001-05-18~2011-12-31作为研究期间,并剔除该期间内数据不全的公司.经此筛选,最终样本为1 225家IPO公司.在检验过程中,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对所涉及的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IPO公司上市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以及股价交易数据全部来自CSMAR金融研究数据库,财务数据均来自WIND金融研究数据库.对于部分可疑的数据,本文使用CCER、WIND和CSMAR进行了交叉核对.本文的数据处理全部采用Stata 11.0计量分析软件进行.
2.2模型设定和主要变量的定义
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1)来考察研究假设1即御用会计师与公司IPO时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
EM=a0+a1King+aj∑Controli+
fixed effects+ξ
(1)
其中EM表示公司IPO前1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对此,同时采用了基本Jones模型、调整的KS模型以及修正的DD模型来估计[32-35].夏立军[36]的研究表明,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后的KS模型是更加适用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估算方法.但它们都是通过估计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正常应计额来进行推断,原理非常相似.因此,本文也同时使用了利用应计项目与现金流之间关系来推断的修正的DD模型来估算盈余管理程度.本文相信来自不同估算原理的模型所得到的盈余管理程度可以更好的实现互补和相互验证,从而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具体而言,基本Jones模型如下
其中GAt是公司在第t期的扣除非经常性项目后的应计额,以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来计算;ΔREVt是公司在相邻两年间营业收入的变化值;PPEt是公司在第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ASSt-1表示公司第t期的期初资产总额.上述参与估计的变量均以其进行平滑以消除规模的影响.在分行业拟合上述模型后所估计出的误差项μt即反映了总应计额偏离经济交易的未预期部分,即研究中所需的盈余管理程度.
调整的KS模型如下

a3Costt+φt
其中GAt和PPEt的定义与之前相同;REVt和Costt分别表示公司在第t期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同样的,所有参与估计的变量均以样本公司的年初资产总额进行平滑以消除规模的影响.最后,模型所估计出的误差项φt即为研究中所需的盈余管理程度.
修正的DD模型如下
GAt=a0+a1CFOt+a2CFOt-1+a3CFOt+1+
a4DCFt+a5DCFtCFOt+ξt
其中GAt的定义与之前相同;CFOt、CFOt-1以及CFOt+1分别是公司在t、t-1和t+1期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DCFt是虚拟变量,如果第t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化值(CFOt-CFOt-1)小于零取值为1,否则为0.与前述两个模型不同的是,拟合修正的DD模型时,要求以第t期的平均总资产而非年初资产总额对GAt、CFOt、CFOt-1以及CFOt+1进行平滑以消除规模的影响.与前述两个模型相同的是,所估计出的误差项ξt即为研究中所需的盈余管理程度.
回归模型(1)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表征御用会计师现象的变量King,分别由king1和king2组成.具体的,本文将在研究期间内与承销商搭档次数最多,且搭档次数占该承销商所有承销业务量的比例不低于20%的会计师事务所定义为御用会计师(King1)*大部分情况下,20%是衡量是否具有重要影响的常用分界点,La Porta等[37]曾以此判断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存在性,会计实务中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也以此作为是否对被投资方有重要影响的界限.因而本文也以20%来衡量某会计师事务所在某承销商全部IPO客户的审计业务体系中的重要性.同时,在敏感性测试中,本文还分别以15%、25%和30%作为重大影响的分界点重新进行了检验,研究结论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本文也考虑扩大对于御用会计师的定义范围,新的定义不再要求搭档次数最多,而是将在研究期间内与承销商搭档次数占该承销商所有承销业务量的比例不低于20%的会计师事务所均视为御用会计师(King2).此外,考虑到当承销商在研究期间内所获得的IPO承销业务量过少时御用会计师的“御用”性质较难体现,本文将承销商在整个研究期间内所获得的IPO承销业务小于5次的情形排除在御用会计师的定义之外.
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分拆和更名等事项在整个研究期内频繁发生,因而为了准确的界定御用会计师,本文详细的整理了各会计师事务所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沿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相应的追溯调整.对于合并而成的会计师事务所,本文以最新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和成员为基础,将之前参与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视同为一家会计事务所.而对于分拆而成的会计师事务所,本文将分拆前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其出具报告的分部特征逐一分拆至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例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2001年由北京天健,深圳天健、浙江天健,厦门天健,重庆天健,辽宁天健组成,在2005年分拆.其中,北京天健和深圳天健并入德勤,浙江天健在合并东方等所后形成了现在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天健和厦门天健组成了现在的天健正信,而现在的华普天健则以当时的辽宁天健为班底.因此本文根据审计报告中事务所分部的名称,将已经不存在的老天健会计师事务曾经的业务分拆,并与德勤、天健、天健正信以及华普天健等逐一对应..
模型(1)中本文最关心的是御用会计师King的估计系数α1的方向和统计显著性.如果α1显著小于0,则表示经御用会计师审计的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御用会计师更可能是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合作而非合谋的结果.在拟合模型(1)时,本文也参考之前的研究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对盈余管理程度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38,39].模型(1)中的Controli便是用于表示这些控制变量的向量.它们主要包括发行公司的规模、风险、成长性、会计绩效、经营性现金流量以及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同时,考虑到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自身声誉对本文研究结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也都进行了控制.为了与被解释变量即盈余管理程度的计算期间相一致,所有变量的计算口径均为公司IPO的前1年.最后,本文还控制了IPO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影响,并在统计检验时使用经White稳健性修正的t值以控制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更具体的,模型(1)中所涉及主要变量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可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定义
3实证结果
3.1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了研究期内御用会计师的年度分布情况.不难发现,从2001年到2005年前,御用会计师无论数量或比例都呈上升趋势,2006年后虽略有下降,但也一直保持在10%的比例范围之内.这表明,本文所称的御用会计师属于我国IPO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现象,而非源于个别承销商或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
表3是对御用会计师在行业间分布的描述.可以看到的是,御用会计师也并非某些行业的独有现象.相反的,其行业分布十分广泛,且比较均匀.其中,出现御用会计师最多的是高达37家的机械、设备和仪表行业.

表2 御用会计师的年度分布

表3 御用会计师的行业分布
表4按年度描述了御用会计师的规模分布情况.其中,大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国际4大及在中注协的排名中居于前10位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中注协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排名始于2004年,故表4的统计期间为2004年-2011年.可以看到的是,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整个IPO审计市场中的业务份额为38.16%,这说明有超过六成的IPO业务是由国际4大和国内10大之外的会计师事务所来执行.同时还可以看到,御用会计师中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例为47.54%,这说明御用会计师在大所和非大所中的分布也比较均匀,并未出现大量集中于国际4大或国内10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形.

表4 御用会计师的规模分布
表5报告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A组报告的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特征.其中表征御用会计师的变量King1、King2,以及表征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声誉的变量big4和BUR是虚拟变量,其余均为连续变量.由于部分样本公司发行前财务数据存在缺失的情形,因而最终能够估算出IPO前1年盈余管理程度的观测值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可以看到的是,样本中约12%的发行公司系由本文所称的御用会计师进行审计. B组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其中,下三角部分是Spearman相关系数,上三角部分为P值*King1、King2是虚拟变量,故此处使用的是Spearman而非Pearson相关系数.作者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的提醒和建议..可以看到,表征御用会计师的变量King1和King2与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变量EMJS、EMKS和EMDD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零.但是,由于影响盈余管理程度的因素众多[41],因而King1、King2与EMJS、EMKS和EMDD之间的相关系数大多表现为边缘显著.这说明非常有必要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执行更为严格的多元回归检验*此处计算和检验的是统计学所称的简单相关系数.只有在两个变量之间关系比较单纯即较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时,简单相关系数才能较好的反映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因而使用可以更为有效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将更准确的俘获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

表5 描述性统计
3.2多元回归分析
更正式地,表6报告了模型(1)的多元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的是,尽管检验中使用3种不同的模型估算公司IPO前1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并作为回归子,且同时使用两个不同的指标刻画御用会计师并作为回归元,但检验结果都是基本相同的,表征御用会计师的变量King1和King2的估计系数在全部6个回归中均显著小于零.这与本文的基本研究假设相符,说明御用会计师的确拥有降低发行公司IPO时盈余管理程度的治理功能.

表6 御用会计师与盈余管理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中所使用的连续变量均经过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统计检验时,t值已经White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回归中不存在需要引起关注的共线性问题.
3.3敏感性测试
本文也考虑改变模型(1)中因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衡量方式以执行敏感性测试.首先,前文研究中的因变量是IPO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但由于任何关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都是对于盈余管理估算模型的有效性和具体研究假设的联合检验[38],所以尽管本文已经使用了3种不同的方法估算发行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但仍然希望能够从其他的角度对其敏感性执行进一步的检验.由于盈余管理的反转效应[15],如果发行公司在IPO时进行了向上调整的盈余管理行为,则其很可能会出现IPO后业绩变脸的情形.所以,本文也使用发行公司IPO事后业绩变脸的概率表征其事前盈余管理的程度重复表6的检验.具体来说,业绩变脸的表征变量BL分别由BL1、BL2和BL3组成.当发行公司IPO后2年平均营业利润增长率<-0.1时,BL1取值为1否则为0;当发行公司IPO后2年平均净利润增长率<-0.1时,BL2取值为1否则为0;当发行公司IPO后2年平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均<-0.2时,BL3取值为1否则为0.
表7报告了该项敏感性测试的结果.由于对于BL的计算要求样本公司至少已经上市2年,因而此处参与回归的有效观测值减少至618个.不难发现,在以发行公司IPO后的业绩变脸替代其IPO时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因变量的全部6个Logit回归中,表征御用会计师的变量King1和King2的估计系数依然全部显著小于零.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比较稳健,并未受到因变量选择和衡量方法的实质性影响.

表7 御用会计师与发行公司IPO后业绩变脸的概率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中所使用的连续变量均经过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统计检验时,t值已经White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回归中不存在需要引起关注的共线性问题.
其次,为了进一步测试研究结论的敏感性,本文也考虑改变核心解释变量的定义方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改变御用会计师分界点的定义.具体的,本文将某会计师事务所参与审计的承销业务占某承销商总承销业务比例的分界点由原来的20%分别缩小或放大至15%、25%和30%,分别以King3、King4和King5表示,并在此基础上重复表6的检验.其二,鉴于研究中御用会计师的表征变量均为哑变量,因此本文也考虑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比重(Ratio)这一连续变量,即某家会计师事务所与某承销商搭配审计总单数/某承销商承销IPO单数之和,并以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复表6的检验.表8报告了上述敏感性测试的结果*为节约篇幅,表8没有报告以调整的KS模型所估算的盈余管理程度(EMKS)为因变量时的情况.其回归结果与表7所显示的情形相似,全部4个新的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小于零.除此之外,本文还执行了一些未在表8报告的敏感性测试,例如,仅使用2005年实施询价制后的样本进行检验,以及改变控制变量的衡量方法等.概括来说,这些敏感性测试均不会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难发现,在改变御用会计师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定义方式后,除回归(2)外,其他全部7个回归中表征御用会计师的新的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小于零.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未受到核心解释变量定义及衡量方法的实质性影响,是比较稳健的.

表8 改变对于御用会计师的定义方式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中所使用的连续变量均经过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统计检验时,t值已经White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回归中不存在需要引起关注的共线性问题.
3.4稳健性测试:考虑内生性问题
虽然前述回归结果已经表明御用会计师是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合作的结果,但如果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拒绝承销商所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则本文所观测到的研究结论就将存在偏误.为了缓解上述可能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所导致的内生性困扰,本文采用Heckman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测试.具体的,Heckman方法要求先拟合一个含工具变量的概率选择模型,再将第一阶段拟合时所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Mills)放入第二阶段的回归中以控制所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因此参考Lee 和 Masulis[31]的基本思路,本文以发行公司IPO募集资金总额的自然对数作为第一阶段拟合时的工具变量并执行上述Heckman程序重复表6的检验.表9报告了该项稳健性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到的是,在全部6个回归中,表征御用会计师的变量King1和King2的估计系数依然全部显著小于零.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未受到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实质性困扰.

表9 御用会计师与盈余管理的Heckman两阶段分析

3.5替代性解释: 承销商或审计师自身声誉的结果?
表6的结果还可能存在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即认为所观测到的御用会计师对发行公司IPO时盈余管理程度的制约作用并非来自关系型契约的治理功能,而仅仅是承销商或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声誉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因此,尽管本文在模型(1)的回归中同时控制了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已经部分的拒绝了上述替代性解释,但为了进一步的排除其对于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也考虑在分别剔除大承销商或大会计师事务所样本的基础上重复表6的检验,从而执行更加严格的测试.表10报告了该项测试的结果*为节约篇幅,此处仅报告了以King1为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在以King2为解释变量时,表10的实证发现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不难发现,在剔除大承销商或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样本后,本文的研究结论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说明本文所指的御用会计师机制的治理功能并不依赖于承销商或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机制,而是属于其以关系型契约激励为基础的自有功能.

表10 剔除大承销商或大审计师样本后的回归结果

4进一步的研究: 是否存在最优合作次数
既然御用会计师是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期合作博弈的产物,那么本文还希望追问的是:是否能通过无限次的合作将盈余管理降到最低,即是否存在最优的合作次数?
理论上,随合作次数的增加,承销商与审计师所投入的专用性投资的累积效应将使得双方的信息摩擦越来越少,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其结果应是合作质量的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合作次数的增加也会增强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的社会关联,并且承销商与审计师不断追加的专用性投资最终还会造成一种双边锁定的情形.此时,不仅是审计师,承销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被锁定在双方的关系型契约中.而这又将使得承销商放弃关系型契约的成本大幅增加,从而导致其向审计师所发出的解除契约的可置信的威胁程度大幅减少,并进而导致关系型契约的治理功能下降[42].这意味着,御用会计师的治理功能将随着承销商与审计师之间合作次数的增加而逐渐增强,但在合作次数超过一定界限后的进一步增加却也会削弱其治理功能.此时,尽管仍然拥有优于非御用会计师的治理功能,但却并非其所能够实现的最优状态.因此,沿着这样的理论逻辑可以预期的是,御用会计师对发行公司IPO时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应随其与承销商合作次数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形关系.
对此的考察也可以为本文的基本研究结论提供进一步的支持.因此,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2)以考察御用会计师与承销商之间的合作次数对其治理功能的影响
EM=β0+β1Time+β2Time2+
βj∑Controli,t+fixed effects+ξ
(2)
其中因变量EM的定义与之前相同.核心解释变量Time是御用会计师与承销商之间合作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因为本文预期御用会计师对发行公司IPO时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应随其与承销商合作次数的增加而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模式,所以在模型(2)中同时引入了Time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以拟合这种抛物线型的关系.本文预期模型(2)中核心解释变量Time的一次项估计系数β1应显著小于零,二次项估计系数β2应显著大于①模型(2)中的因变量EM反向表征着御用会计师的治理功能,即盈余管理程度越低时表示御用会计师的治理功能越强.所以模型(2)的拟合结果应是一条U形抛物线.


表11 合作次数与御用会计师的治理功能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中所使用的连续变量均经过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表中数据为各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括号内的数据为t值.统计检验时,t值已经White异方差稳健性修正.回归中不存在需要引起关注的共线性问题.
5结束语
在我国的IPO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承销商与某家会计师事务所形成固定组合共推IPO的情形,即本文所称的御用会计师现象.对此的理解有两种完全相反的逻辑:合谋假说与合作假说.本文为甄别上述两种假说提供了相应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以我国IPO核准制实施之日至2011年12月31日所有IPO的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御用会计师能够显著的抑制发行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同时,这种制约效果随合作次数的增加而加强,在约6次左右达到最大值.并且,上述研究发现在一系列敏感性测试、考虑可能的样本自选择问题以及控制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自身声誉的影响后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御用会计师是承销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多次博弈有效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关系能减少中介机构之间联合生产的交易成本,降低公司IPO时的盈余管理程度,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本文突破了既有文献大多侧重于讨论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在IPO过程中各自的行为选择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因而既强调了团队联合生产这一IPO过程中中介机构活动的基本特征,更强调了在对这些中介机构的联合生产进行组织、协调以降低交易成本的过程中,关系型契约的重要治理功能.在此基础上,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其重要的政策涵义.具体来说,一方面,对于资本市场监管者来说,应适当鼓励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长期合作,并适当增加对于承销商与其非御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偶尔式合作的监管力度*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互不熟悉的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作与IPO公司更高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与此相符的是,来自现实世界的诸多案例也表明,承销商与其非御用会计师之间“拉郎配”式的偶尔合作常常与重大财务欺诈案相联系.例如耳熟能详的绿大地案,其承销商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该项业务中便是与此前从未有过合作的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搭档,而并未使用其御用会计师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又如胜景山河案及万福生科案,其承销商平安证券在这两项业务中也均未使用其御用会计师即原天健系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是分别与并不熟悉的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搭档..另一方面,对于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来说,应充分利用关系型契约在联合生产过程中的协调和适应功能,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执业风险、提高执业质量,从而更好的发挥其在资本市场中应有的鉴证功能.
参 考 文 献:
[1]王兵, 辛清泉, 杨德明. 审计师声誉影响股票定价吗——来自IPO定价市场化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09, (11): 73-81.
Wang Bing, Xin Qingquan, Yang Deming. Whether auditor reputation influence share pricing: Evidence from IPO marketing in China[J].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11): 73-81. (in Chinese)
[2]郭海星, 万迪昉, 吴祖光. 承销商值得信任吗——来自创业板的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 14(3): 101-109.
Guo Haixing, Wan Difang, Wu Zuguang. Do underwriters deserve trust: The evidence from china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J]. Nankai Business Review, 2011, 14(3): 101-109. (in Chinese)
[3]Chen C, Shi H, Xu H. Underwriter reputation, issuer ownership, and pre-IPO earnings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2, 42(3): 647-677.
[4]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9, 22(2): 233-261.
[5]Cornelli F, Goldreich D. Bookbuilding and strategic alloc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1, 56(6): 2337-2369.
[6]Cornelli F, Goldreich D. Bookbuilding: How informative is the order book?[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3, 58(4): 1415-1443.
[7]Jenkinson T, Jones H. Bids and allocations in European IPO bookbuilding[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59(5): 2309-2338.
[8]Klein B, Crawford R G, Alchian A A. Vertica l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8, 21(2): 297-326.
[9]Gibbons R. Four formal(izable) theories of the firm?[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5, 58(2): 200-245.
[10]Gillan S L, Hartzell J C, Parrino R. Explicit versus implicit contracts: Evidence from CEO employment agreemen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9, 64(4): 1629-1655.
[11]Dechow P M, Kothari S P, Watts R L. The relation between earnings and cash flow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8, 25(2): 133-168.
[12]Teoh S H, Wong T J, Rao G R. Areaccruals during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opportunistic?[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1998, (3): 175-208.
[13]林舒, 魏明海. 中国A股发行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过程中的盈利管理[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0, 2(2): 87-130.
Lin Shu, Wei Minghai. The earning management by Chinese A-share firm in the IPO process[J].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2000, 2(2): 87-130. (in Chinese)
[14]Kao J L, Wu D, Yang Z. Regulation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post-IPO performance: The Chinese eviden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9, 33(1): 63-76.
[15]Aharony J, Lee C J, Wong T J. Financial packaging of IPO firms in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38(1): 103-126.
[16]Ducharme L L, Malatesta P H, Sefcik S E, Earnings management, stock issues, and shareholder lawsui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 71(1): 27-49.
[17]Fang L H, Investment bank reputation and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underwriting servic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60(6): 2729-2761.
[18]Hanley K W, Hoberg G, Litigation risk, strategic disclosure and the underpricing of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2, 103(2): 235-254.
[19]徐浩萍, 罗炜. 投资银行声誉机制有效性——执业质量与市场份额双重视角的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2): 124-136.
Xu Haoping, Luo Wei. Reputation effect of investment banks: Research from aspects of market share and service quali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2): 124-136. (in Chinese)
[20]程书强.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 (9): 129-136.
Cheng Shuqiang.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and accounting earring informa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06, (9): 129-136. (in Chinese)
[21]薄仙慧, 吴联生. 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 盈余管理视角[J]. 经济研究, 2009, (2): 81-91.
Bo Xianhui, Wu Liansheng. The governance roles of state-owned controlling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 A perspective of earnings managemen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2): 81-91. (in Chinese)
[22]姚颐, 刘志远. 机构投资者具有监督作用吗?[J]. 金融研究, 2009, (6): 128-143.
Yao Yi, Liu Zhiyuan. Dose institution investor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09, (6): 128-143. (in Chinese)
[23]李培功, 沈艺峰. 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 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0, (4): 14-27.
Li Peigong , Shen Yife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role of medi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 (4): 14-27. (in Chinese)
[24]杨德明, 赵璨. 媒体监督媒体治理与高管薪酬[J]. 经济研究, 2012, (6): 116-126.
Yang Deming, Zhao Can. Media monitoring,media governance and managers compens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2, (6): 116-126. (in Chinese)
[25]李培功, 沈艺峰. 经理薪酬、轰动报道与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J]. 管理科学学报, 2013, 16(10): 63-80.
Li Peigong, Shen Yifeng. CEO compensation, sensational coverage, and media govern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3, 16(10): 63-80. (in Chinese)
[26]黄俊, 陈信元. 媒体报道与IPO抑价——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J]. 管理科学学报, 2013, 16(2): 83-94.
Huang Jun, Chen Xinyuan. Media coverage and IPO underpricing: Evidence from China’s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2013, 16(2): 83-94. (in Chinese)
[27]Baker G, Gibbons R, Murphy K J.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1): 39-84.
[28]Levin J. Relational incentive contract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3): 835-857.
[29]黄春铃. 证券监管效率和承销商声誉——基于南方证券“麦科特事件”的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05, (7): 129-138.
Huang Chunling. The efficiency of securities supervision, and underwriters’ reputa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05, (7): 129-138. (in Chinese)
[30]罗炜, 饶品贵. 盈余质量、 制度环境与投行变更[J]. 管理世界, 2010, (3): 140-149.
Luo Wei, Rao Pingui. Earning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underwriter switching[J]. Management World, 2010, (3): 140-149. (in Chinese)
[31]Lee G, Masulis R W. Do more reputabl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duce earnings management by IPO issuer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11, 17(4): 982-1000.
[32]Jones J J. Earnings management during import relief investigat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1, 29(2): 193-228.
[33]Kang S, Sivaramakrishnan K. Issues in testing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approa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5, 33(2): 353-367.
[34]Dechow P M, Dichev I D. The quality of accruals and earnings: The role of accrual estimation error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 77(s-1): 35-59.
[35]Ball R, Shivakumar L. The role of accruals in asymmetrically timely gain and loss recogni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6, 44(2): 207-242.
[36]夏立军. 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J]. 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 2003, 5(2): 94-153.
Xia Lijun. Application of earning management measuring models i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J]. China Accounting and Finance Review, 2003, 5(2): 94-153. (in Chinese)
[37]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9, 54(2): 471-517.
[38]孙亮, 刘春. 什么决定了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 公司治理还是经营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中国会计评论, 2008, (1): 79-92.
Sun Liang, Liu Chun. What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earning management difference: Corporate governance or perform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securities market[J]. China Accounting Review, 2008, (1): 79-92. (in Chinese)
[39]刘娥平, 刘春. 盈余管理公司治理与可转债绩效滑坡[J]. 管理科学, 2011, 24(5): 78-88.
Liu Eping, Liu Chun. Earnings manage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under performance after issuing convertible bond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1, 24(5): 78-88. (in Chinese)
[40]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度报告[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Fan Gang, Wang Xiaolu, Zhu Hengpeng. NERI INDEX of Marketization of China’s Province 2011 Report[M]. Beijing: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1. (in Chinese)
[41]Dechow P, Ge W, Schrand C. Understanding earnings quality: A review of the proxies, their determinan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 344-401.
[42]Dur R, Tichem J. Social Relations and Relational Incentives[R]. Rottendam: Erasmus University, 2012.
Underwriter-accountants: Collusion or cooperation
SUNLiang1,LIUChun1,LIUJian-hua2*
1.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2. Lingnan(University)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The 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derwriter and the auditor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We define the auditor who serve as a fixed partner of an underwriter as the underwriter-accountant, and use Chinese IPO firms from 18 May 2001 to the end of 2011 as our sample toinvestigate whether the underwriter-accountant is the result of cooperation or collusion. We find that the underwriter-accountants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degre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of IPO firms, and that the restriction effect, reaching the maximum in about 6 times, would be strengthened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oper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underwriter-accountant represents an effective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repeated game between the underwriter and the auditor. In this way,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joint production among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can be reduced,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of IPO firms can be restricted, an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s can be enhanced.
Key words:underwriter-accountants; cooperation; collusion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07(2016)02-0109-18
通信作者:柳建华(1980—), 男, 江西玉山人, 博士, 讲师. Email: willow0703@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71302104; 7140219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2YJC630112; 13YJC790124); 广东省自然科学博士启动基金资助项目(S2013040016771).
收稿日期:① 2013-03-01;
修订日期:2014-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