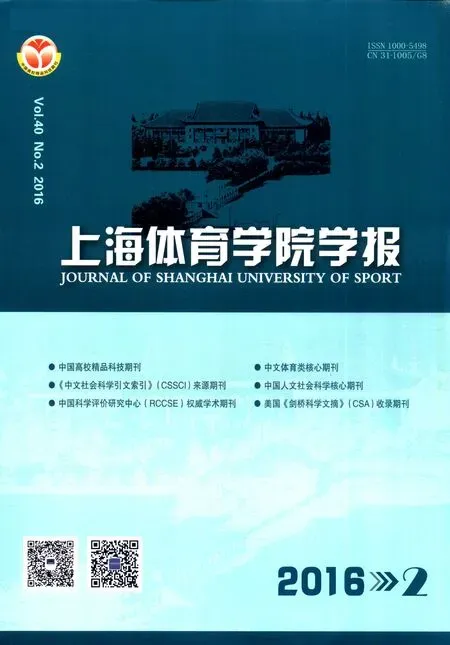近代武术价值观的变迁与思考
李 岩, 王 岗
(1.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2.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近代武术价值观的变迁与思考
李岩1,王岗2
(1.苏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2.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近代武术价值观及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发现:外患内乱是中国武术价值观在军事领域颠覆的外在动力,武举制的废除导致武术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转移,成为武术向大众防身、健身价值转移的内部推动力,国粹主义的时兴使中国武术担负起强国强种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近代; 价值观; 武术价值观; 变迁; 思考
DOI10.16099/j.sus.2016.02.008
Review of the Change of Modern Chinese Wushu Value
LI Yan1,WANG Gang2
AbstractThe study adopte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o explore the modern wushu value socially,politically and culturally.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foreign invasion and civil strife are 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for the Chinese wushu value to subvert in the military field.And the abolition of Wushu Examination System led to its transfer from the upper society to the lower,which became the driving force of self-defense and body-building for ordinary people.The popularity of “Studying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s and preserving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Guo Cui Zhu Yi”) gave Chinese wushu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and race.
Keywordsmodern;value;wushu value;change;review
Author’s address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21,Jiangsu,China;2.School of Wushu,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1840年当清王朝睥睨天下、“举国方沉酣太平”之际,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强行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沉重的帷幕,帝国主义的炮声惊醒了天朝大国士人的迷梦,国人逐渐失去了上国大邦的安闲心态。此次西方文明的传入不再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补充或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从本质上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中西文明的激烈对撞加速了中国从传统文明形态向现代文明形态的转变。这种新旧文化的冲突必然酝酿着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激变。中国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的发展自然也受这种价值观的变迁影响。传承了上千年的中国武术军事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中逐渐演进,人们对武术价值功能的认识也自此发生了改变。鉴于此,对近代中国武术价值观的变迁进行历史学意义的回眸和思考,既是对中国武术价值观进行梳理的根源性研究,也是揭示武术价值观发展的问题和把握武术未来发展方向的起点研究。
1相关概念解读
1.1近代按照学术研究的分期习惯,近代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段时间。
1.2价值观价值观本身是一定群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长期的价值活动过程中,逐渐积淀、升华而形成的反映价值关系的社会意识[1]。
1.3武术价值观武术价值观是在长期的武术活动中,人们形成的对武术价值功能的认识,它影响着武术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据前人对武术和武术价值观的相关研究成果,武术价值观大致可分为内涵、外延和中间层3个层面。内涵层主要指人们对武术所包含的文化特性的认识,包括武术的修心养性、道德教化、精神教育等;武术价值观的外延层指人们对武术作用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以及人类身体价值的认识,包括武术的军事、强体防身、健身养生等价值观;而武术价值观的中间层指人们对武术具有的传统美学价值的认识,包括身体之美、情感之美、真善之美等价值观。
2近代武术价值观变迁的社会因素
2.1“坚船利炮”是武术军事价值观颠覆的外在动力在农耕文明的主导下,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生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不仅供养了古代中国世世代代的子孙,也导致了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闭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中国人安闲于现状,从未滋生向外发展的欲望。相反,工业革命的开展和不断革新的进步思想却推动了西方对海外市场的扩张。1840年,英国借由鸦片贸易冲开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堡垒。鸦片战争最直接呈现于中西之间的较量便是武力的竞争。在此之前,武术与军事可谓是同源之水,两者一直密切联系,融合贯通。漫长的冷兵器时代让武术成为军事战场上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并且这种价值观一直是人们最信奉的价值观。到了清朝末年,虽然清政府军队在编练新军中不断配置洋枪、洋炮,但是传统武术在军事战场的重要性早已根深蒂固;因此,传统的武术习练仍在很大范围内作为练兵的手段在军中盛行,特别是弓马长矛、藤牌刀棍等的操练。然而,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夷狄”的“坚船利炮”在军事战场上开始了与武术的面对面对话。随着战争的深入和结果的强烈对比,人们不得不承认武术中的刀枪棍棒在近代化的战场上不是“夷狄”洋枪大炮的对手。在此种情形之下,人们对武术在军事战场上的技击价值开始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八里桥战争中,当时的英法联军已装备了可以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蒸汽炮艇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而自恃“骑射无双”的清军还是由以冷热兵器混合为主的步兵、骑兵组成,他们除了少数的进口和仿制的旧式滑膛枪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战争的结果就像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记载的那样:“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靼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覆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2]这种结果展示出了中国冷兵器和西方先进武器的巨大落差,西方的先进武器用血淋淋的事实反映出中国武术在军事战场上的短处。
2.2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利标志着武术军事价值观的彻底瓦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也正是清政府与太平军激烈斗争的时期。当时太平军武术高手云集。“石达开‘游衡阳,以拳术教授弟子数百人。其拳术,高日弓箭装,依日悬狮装,九面应敌’并有连环鸳鸯步的绝招”[3],“李秀成在安国村学过武术,师父是江苏人铜铁棍,很有力气,李从其学过棍法,得一手绝技”[4],而且“太平军在不断发展中,还吸收不少各民族武艺高手”[5],并且在太平天国的队伍中,武艺训练一直是重要的内容,并有明文规定:“凡各衙各馆兄弟,在馆无事,除练习天情外,俱要磨洗刀矛,操练武艺,以备临阵杀妖,不得偷安。”[6]就是这样一支高手云集、天天习武的军队,在先进的近代武器面前也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1860年,在洋人居多的上海,中国绅商便聘请了一支武器装备精良、训练严格的雇佣军与太平军对抗,因为这支雇佣军的武器装备比较先进,在面对基本上靠冷兵器作战的太平军时,在屡次交手中均取得胜利。太平军的战败也昭示着,武术再也不能成为赢得战争的终极“必杀技”,武术的军事技击价值在屡次失败的战斗中被逐步瓦解。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利用中法《北京条约》给予的特权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就像路遥[7]所说:“造成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传教特权。”这些传教特权成为教会的统治工具,各教堂利用清政府整个政治制度的腐朽通过洋教士虐肆人民,意图进行政治统治,教会与国民的矛盾冲突频仍。这些传教士在中国领土“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官民皆无可如何”[8]。面对此种境况,“以下层民众为主要成份,以结盟、传教习武等活动为凝聚方式而不为朝廷官府所允许的各种民间结社团体”[9]自发地担负起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于1900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然而,义和团是一个以习练拳棒为主要形式的民间组织,以大刀会、红拳、梅花拳、神拳为前身,除拳术外,他们主要凭借着简陋的传统兵器与装备洋枪大炮的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佐原笃介曾记录他们:“或持竹竿、秫秸、木棒等物,长者以当长枪大戟,短者以当双剑单刀,各分门路,支撑冲突,势极凶悍,几于勇不可挡。”[10]另据柴萼的《庚辛纪事》记载,义和团有人“恒执木棍”习练“二郎神棍”[11]。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义和团还为武术渲染了过多的神灵色彩,使武术过于神化,这也让团民奋不顾身,以为神功护体,刀枪不入,用血肉之躯勇敢地面对联军的洋枪大炮,结果就像佐原笃介描述的那样:“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10]当义和团的团众们用拳头与洋枪对峙之时,当他们用木棍、竹竿与大炮相抗衡时,战争的结果已不言而喻。
3武举制的废除成为近代武术价值观变迁的政治推动力
在中国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武举制对中国武术的发展起着非同凡响的作用。武举制始建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当时由兵部主持,“初令天下诸州有练习武艺者,每年准明经进士举送”。当时的武举考试内容共有7项:靶射、骑射、步射、身高相貌、言论、举重(翘关)。因为是武举的始创时期,因此武举的整个制度并不是很完备,更加偏重于技勇,特别是对骑马时的枪法更加偏重。这种能将武术与进士、明经两科置于同等地位的决策使得习武之人有了光宗耀祖的资本,也将武术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地位。武举制在封建社会时期的科举制度中正式登台,并被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到了宋代,武举制进一步发展,不仅对武力要求较高,还需要测试军事策略,到了明朝更是有“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之说;到了清朝,武举制的发展达到顶峰,因为满族人向来以游牧为主,精于骑射,并自诩“以孤矢定天下”,因此对武举制也是倍宠有加。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对武术的不断认可,使得以习武为荣成为“正统”,“以武进举”也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武术成为主流文化主要还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由此可以看出,以冷兵器作战为主的封建社会,武术的军事价值观还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
到了清末,随着火器的出现,世界列强装备皆以枪炮为主,清军也开始逐渐增加火器装备,徒手器械格斗的近身搏杀已在战争中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武举考试中的涉猎项目也跟这个时期的军事相差甚远,武术走入了“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的地步,自然也不再受到统治者的宠爱,于是,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下令宣布废除武举制。武举制的废除使武术在统治阶层的地位急剧下滑,也从另一个层面宣告了武术正式退出国家军事作战的“主战场”。这样,原来下层民众指望通过武术飞黄腾达的意愿也因为武举制的废除而破灭,“以武进举”的主流文化从此退位为非主流文化。
清末,清朝统治者受到义和团的沉重打击后,对民间习武更加恐慌,“传授生徒不能如前之自由,须经绅商担保,方准成立。武术场教授普通人民,而在某巨宅秘传三五者,仍复不少,但较前之盛况相去远矣”[12]。因此,武术的发展在一定的范围内受到遏制。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基督教势力的扩展和民族矛盾的加深,人民需要一种安身保命的技术保护自己。“带有秘密宗教色彩的练武组织,成为人民精神和组织方面进行自卫的有利武器”[13]。当武术的军事价值不再突出,武术的生存必然要寻求一种足以替代其军事功能的价值来支撑,于是,武术在武举制废除之后,因为其强体防身价值而成为下层民众极致推崇的运动,自此,武术的价值观从统治阶级的军事价值观开始转移至下层民众的强体防身价值观。
4国粹主义的昌兴使武术担负起强国强种的使命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这一基本语境中提出的“尚武精神”“军国民思想”和“国粹主义”,便是武术在那个时期最真实的写照。“尚武精神”和“军国民思想”充分体现了当时国民以国家危亡为己任,以保家卫国为首要目标的爱国情怀,中国武术自然也被寄予厚望,成为塑造国魂的重要力量,成为“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已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14]。“国粹思潮”的兴起昭示着国民社会义务观念的增强和改变,以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为义务,为防止中国武术的全面西化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人或逃亡或留学来到日本。日本举国“崇军”“尚武”的风气,给了他们很大的冲击。他们主张“尚武精神为立国第一基础”[15],用传统的武术侠义精神塑造近代“尚武”精神,将“国家主义”注入到“侠义”精神里,视“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下”者均为“侠”,将游侠精神与国仇相连,为国家救亡提供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内涵,为尚武强国提供一种随时准备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气概。那一时期还有无数具有侠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他们再不会像义和团那样利用武术冲锋陷阵,而是提炼出了传统武术身上的尚武精神和武侠豪情,用之激励国民护国自强。武术的价值观由此“华丽转身”。
在国粹主义昌兴的当时,武术自然成为国粹主义的受益对象,发掘和发扬中国武术的传统优势价值便成为那个时期的主旋律。就连美国学者麦克乐[16]都指出:“中国武术流传最古,体育之一线命脉维持不坠者,赖有此尔”“周末勇士倍出,游侠之士散处闾阎。重气节,轻生死,济困扶危,排难解纷。盖武术者,不独可强健体魄,亦可以增进德行”。他认为,武术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国粹,更是塑造爱国主义的具体象征。这一时期大量的武术社团不断成立,“这些武术社团大多得到地方军政当局或乡绅、校董的资助与扶持,……并都有明确的宗旨、固定的章程与机构”[17]。在这一时期,武术的拳种挖掘和整理工作也得到极大的促进。尊我斋主人著有《少林拳术秘诀》,陆师通、陆同一著有《北拳汇编》《易筋经》《八段锦》《少年拳术》《精义拳经》等出版物。
在这一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便是马良。他借助国粹主义盛行之时,曾经将所学的拳技和摔跤术参照兵法操练,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备学堂和军旅中传授,后来还广邀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后来马良的新武术跟国粹主义均遭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派的批判。
5对近代武术价值观变迁的思考
“当作为‘活命术’的传统武术技击技术,在面对西方的炮火轰炸时再也难成为救命技术的时候,传统武术的技击技术的存在价值就开始弱化,并且也必然开始了技击功用的历史退位,这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18]。幸运的是,在武术的技击功用退位后,武术并未因此消失,而是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找寻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找寻的道路上,武术的价值观也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迁而发生变迁。武术价值观的变迁也在器物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受到各自不同的影响。
5.1器物层面的巨大反差迫使近代武术价值观转向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武术开始寻求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价值观,正如“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大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19]一样,战争的权威性也在于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以及认识自己所信奉了上千年的价值观。透过弥漫的硝烟人们终于发觉,中国武术在军事战场上的这种“不堪一击”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这种见识与事实之间的距离让两千年来传统的武术军事价值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动摇。
义和团运动是最底层的、中国民众不愿在外族欺凌之下成为亡国之民的直接行为方式表达,其成员构成主要是“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20]。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他们排斥船坚炮利的洋人,然而面对清政府的对抗失败,他们又找不到真正能抵挡和对抗洋枪火炮的现实力量;因此,他们便以神道为武器,信仰超自然的力量成为其心理寄宿。在神道观念的迷信下,他们手执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等,勇敢地与西方的洋枪火炮进行着悲壮的对抗。这种从顽固到迷信的过程也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对西方先进武器的无可奈何。义和团事件最终发展为国际事件,八国联军进军中华,清政府和义和团共同抵抗,但终因军事实力差异太大最终溃败;而这次溃败也再次用事实将武术的军事价值观彻底摧毁。
5.2社会和民众需求是近代武术价值观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在以内向传播和人际传播为主的时代,再加之武术在民间又是秘密展开,这便导致了武术交流的不畅通,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武术流派,像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掌和谭腿、查拳、少林、迷踪、八极、红拳等多门类著称的武术流派,都是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军事武术的衰退和当时社会的内外交困使得一些有识之士日渐清醒,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一些为数不多的民间社团也开始公开授拳,比较有名的有:1900年形意、八卦名家耿继善所创立的“北京四民武术研究社”,1911年由李存义发起,在天津成立的“中华武士会”;当然,最有名的就是1909年由霍元甲所创立的“精武体操学堂”。这些社团数量有限,影响薄弱,但在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情景之下,广大民众也希望寻得安身立命、强体防身之术,而社团正是民众需求的一种实体体现;武术在这一时期的强体防身价值观也通过武术社团的出现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5.3爱国文化的宣扬是近代武术价值观变迁的深层推动力维新派将新民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在培养新民的过程中,提倡国民的社会义务观念。作为独立的人的解放,要摆脱封建社会的流弊,摆脱君臣观念,移风易俗。在社会义务的观念倡行下,国民开始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西方功利主义价值冲击下的保存和传承。国粹自然成为国民心中那棵中华传统文化“大树”。国粹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初,乃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并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的结果。国粹派主张“复兴古学”,宣传国学,提倡国粹,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种种弊端,中国自身的问题并不能依靠所谓的西方经验得到解决;他们坚决批判推崇帝国主义文化,妄自菲薄,宣传中国文化落后,鼓吹“全盘欧化”的错误倾向;他们认为应到中国古代传统中寻找解救时弊的“灵丹妙药”。还原至当时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国粹主义的提出乃根植于爱国主义思想中的一种具体表现,一个国家的国民自然有义务将自己种族的文化特质发扬光大。虽然国粹派的“泥古不化”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封建复古主义逆流,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化传播,妨碍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设,但也不能不说在一定意义上挽救了中国的一些优良传统。这次爱国文化的宣扬在近代武术价值观由外延层的军事、技击价值观向内涵层的精神、教育价值观的转变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章龙,周莉.价值观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5
[2]吉拉尔.法兰西和中国[M]//齐思和,林树惠,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294
[3]徐珂.石达开碎碑: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21
[4]广西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G].北京:三联书店,1956:87
[5]林伯原.论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变化[J].体育科学,1992,12(4):11
[6]吴兴,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卷七[M].上海:文明书局,1932:4
[7]路遥.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J].山东大学学报,1990(1):4-5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
[9]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8
[10]佐原笃介.拳事杂记[M]//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149
[11]柴萼.庚辛纪事[M]//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306
[12]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1
[13]崔丽丽.晚清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影响[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2,28(4):44
[14]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M]//夏晓虹.梁启超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152
[15]梁启超.斯巴达小志[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16]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N].申报,1922-01-17(1)
[17]易剑东,谢军.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面向21世纪的中国武术[J].体育文史,1998(4):24
[18]王岗.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自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1
[19]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4
[20]瞿秋白.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M]//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4
文章编号1000-5498(2016)02-0041-05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志码A
通信作者简介:王岗(1965-),男,山西临猗人,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Tel.:13402501568,E-mail:tywanggang@126.com
作者简介:第一李岩(1984-),男,山东肥城人,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齐鲁师范学院讲师;Tel.:15168898655,E-mail:feichengliyan@163.com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4DTYJ01)
收稿日期:2015-10-25; 修回日期:2016-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