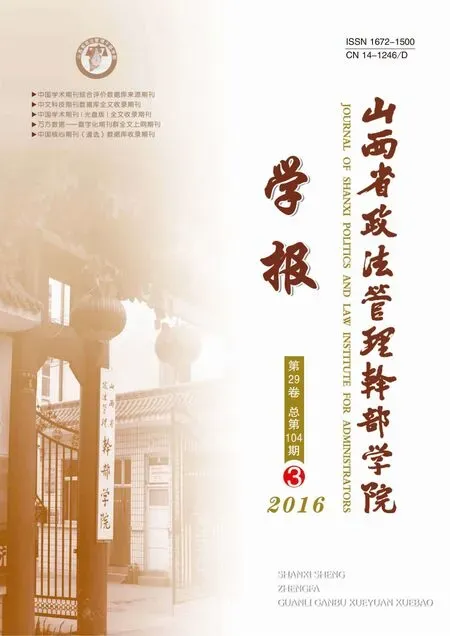汉代赎刑中替代刑的起源与发展
高子谦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法学纵横】
汉代赎刑中替代刑的起源与发展
高子谦
(内蒙古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前人对于赎刑有多种划分方式,透过赎形的最初形式和疑罪从赎的相关情况可知赎形的起源具有多元性。在发展问题上,一部分学者认为赎刑在汉中后期基本消失,文章对汉代赎刑的金额给予不同的划分,对两汉替代赎的情况进行更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并对赎刑应用的现实意义给予肯定。
赎刑;汉代赎金;疑罪从赎
关于赎刑方面的研究,前人在张家山汉简的基础之上,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张家山汉简的出土首先推翻了汉初赎刑不存在的这一说法,继而又为汉代赎刑性质的划分提供了新的思路,角谷常子女士提出了将赎刑区分为“对应犯罪的规定之刑”和基于某种理由而予替代的“换刑”。[1]富谷至先生则是将其称之为正刑和替代刑,张建国先生在认可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还认为“把汉初赎刑确定为混合型是最为稳妥的做法”。韩树峰先生又将赎刑的不同类型称之为独立赎刑和附属赎刑,朱红林女士则认为赎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上的“赎刑”,专指赎肉刑,另一种是广义上的“赎刑”,即所有缴纳钱财以免除刑罚的惩罚方式。[2]而广义上的赎刑在简牍中被称之为“赎罪”,“赎罪”在具体运用上具有两种性质,一是“规定刑”,即针对犯罪内容本身的特点,依照法律直接判处的“赎罪”,二是“替换刑”。这些学者大都注意到了在一些法律条文中,看不出犯罪行为与所处赎刑所对应的实刑有何必然的联系,他们虽然在定义赎刑双重含义时使用的名词并不相同,但是基本的划分还是比较类似。另外,孙剑伟在此基础之上,又从罪名、刑法、刑法的执行这三个方面考虑,进一步将赎刑的含义扩展为三条:一是指依照法律条文应处以“赎刑”之罪,是一个概括性的“罪”的概念;二是指舍弃本刑而易科赎刑或以其他法定的方式除罪,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三是指在法律制度外,通过缴纳钱财、削除爵位、提供战功或劳役及其他途径除罪、减刑。[3]三条可以分别概括为:规定刑、替代刑和法外特赦。
一、替代刑之起源
关于赎刑的最初形成,根据《尚书·吕刑》中“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张建国先生经分析认为“法律中对应于实刑的代替刑的赎,解释成最初是为各种疑罪而规定最为合理。”[4]所谓疑罪就是犯罪事实可能有模糊之处,不惩罚担心放纵了罪犯,若直接用对应的实刑进行惩罚又有在量刑方面的问题,故而变通之后即采用赎刑的方式。
对此,其他学者有所质疑,首先是有关疑罪从赎的法律规定,最先只能追溯到唐朝的《唐律疏议》中“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这一条文,之前均不见有关疑罪从赎的法律规定的痕迹;其次,以疑罪从赎作为折中的处理办法并不合理,若某人果真犯罪,采用赎刑的方式无疑使法律丧失了其公正性,若是此人没有犯罪,其要承受对于寻常百姓来讲不菲的赎金更是于理不合。汉朝对于官吏“出入人罪”有着很严重的处罚,而采取疑罪从赎的办法恰恰会导致“罚不当罪”,故而官吏必然不会采取这种会使自己受到严厉处罚的办法。南玉泉先生还提出了“越是专制的社会,就越不存在所谓的疑罪”观点,对于这一点,笔者是认同的,因为专制体制下的古代官吏要负责的第一对象首先是上级、是中央,而不是平民百姓,各朝代均有对于官吏任期内业绩的考核,有案无法查明真相是如何也无法交代的,若是还采取疑罪从赎之法草草了事,更是会有渎职的嫌疑。相反的,在面对普通百姓的时候,官吏就处于强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势之下,官吏一定会想方设法查清真相,古代众多的刑讯逼供的案例也就不足为奇。除此之外,张建国先生在提出疑罪从赎的论点时,还忽视了汉朝奏谳制度的存在,汉代统治者已经考虑到有地方官吏无法做出审判的可能,故而“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这就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因疑罪而采取折中从赎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要看到以上的论述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漏洞,那就是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汉代这个时段而言的,即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在汉代不太可能出现疑罪从赎的情况。那么在汉代之前,乃至于三代,其法律制度尚未达到严谨详细的程度时,是否会有疑罪从赎的情况呢?韩树伟在其著作《汉魏法律与社会》中对此有所考察,根据清代人王文彬引《礼记·王制》:“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又引《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可以推测若是有“疑狱”的情况发生,则是交给民众来表决,“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并且在《汉书·刑法志》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罪疑者予民”,这就说明在汉代的时候,遇到疑罪的情况也极有可能是和上古时代一样,由民众来决定,而不是采取赎刑的办法,但是这并不能表示疑罪从赎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
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疑罪从赎,还是过误从赎,都是刑法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通则性的赎刑规范肯定不是最早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能认同,正如这位作者所言,法律规范是在归纳个别行为的基础上抽象为一般行为规范的,所以抽象概念的出现恰恰证明了之前有相应的个例作为参考,这便证明了疑罪从赎这一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上文“罪疑者予民”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测是民众在犯罪事实无法准确认定,既担心放纵罪犯又担心惩罚失度的情况之下,做出了让疑罪者缴纳一定钱财的决定。这些处在社会发展初期的百姓不可能都受过很好的断狱训练,故而对于量刑裁决自然没有办法和汉代的官吏相比,所以他们做出这样欠妥的裁决也就是极为可能的了。当然,这只是笔者根据现有材料所做的推测,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文献材料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赎刑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这自然还需从赎的本义研究起。《说文解字》中:“赎,贸也;贸,易财也。”因此,这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赎刑在最初的起源中是作为替代刑而不是规定刑出现的。南玉泉先生根据秦汉时期两种替换赎,一是赎身份,二是赎罪行,认为赎刑的一个起源是使自己摆脱奴隶的身份,另一种是对罪行的赎替,以财赎罪的现象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各部族之间经常出现误杀、仇杀和抢劫一类的情况,这势必招来其他部族的报复,这时为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人们便采取用财货补偿的方式,即替代刑与早期的奴隶赎身、原始的赎罪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里所说的赎身的起源,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即在原始社会奴隶是否有能力为自己赎身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有关中国早期社会的奴隶性质是否存在的问题,学界对此还有争论。对于第二个起源论述,笔者还是比较赞同的,但是观察汉代赎刑的适用情况和对象是极为广泛的,所以仅仅只以原始社会的赎罪为起源未免太过单薄了,毕竟这只是分析了部族之间冲突的解决这一单一的方面。在《二年律令·贼律》中,有这么几条:“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其过失及戏而杀人,赎死;伤人,除。”“诸吏以县官事答城旦舂、鬼薪白粲,以辜死,令赎死。”“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答辜死,令赎死。”这几条中分别涉及了过失杀人和官吏殴打罪犯或者父母殴打子女和奴婢致其死亡可以赎罪的案例,即我们据此也可以推测在原始社会部族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作为部族内部的人,部族内的其他成员定然不会像对其他部落的成员一样怀有很大的敌意,并且为了保障人口数量,对于过误伤人或杀人者,也许会采取缴纳一定货物钱财的替换赎的方式解决。而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父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伴随着贫富分化,一部分人取得部落中较高的地位,当他们出现殴打子女或者奴隶致死的情况时,也不太可能以同态复仇的方式将他们处死,而是可能采用选择替换赎做法,这一点,世界上其他较早的法典中,例如《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类似的条例。综上所述,赎刑并不是只由某一种原因发展而来,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不断使赎的习惯法扩充,即赎刑的起源具有多元性。
二、替代刑之发展
曹旅宁先生在研究替代刑的执行情况时,通过分析需要缴纳的赎金额度,得出了赎刑由汉初的常刑逐渐衰微,并且面临着实际上被取消的情况,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能赞同,理由如下:
(一)赎金金额
首先在这里列举一下有关赎金额度的史料,以方便说明:《汉书·惠帝纪》“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值钱二干,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疋缣矣。”《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九月,募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汉书·武帝功臣表》“太始三年,坐为太常鞠狱不实,入钱百万赎死,而完为城旦。”张家山汉简《爵律》:“诸当赐爵受,而不当拜爵者,级予万万钱。”张家山汉简《具律》“赎死,金二斤八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一斤八两。赎斩、腐,金一斤四两。赎劓、黥,金一斤。赎耐,金十二两。赎迁,金八两。有罪当腐者,移内官,内官腐之。”《二年律令·金布律》“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汉书·淮南王传》“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当免,削爵为士伍,毋得官为吏。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背畔之意。”
曹先生根据睡虎地秦简《效律》,当时两与斤的换算关系为十六进位制,黄金一斤为黄金十六两的换算金与钱的关系,得出赎死金二斤八两相当于25000钱,并且估计秦代与汉初的赎刑等级与金额上相去不远,秦律中规定可以以劳役抵债“旧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以每日劳役抵六钱计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实际上不可能劳动这么多天数),需要连续服十三年以上的劳役,才能达到减死的标准——25000钱。而这十三年的苦役换得的仅仅是“减死”而已。所以赎刑尽管在法律中有规定,但对于一般人却永远是一纸具文。”[5]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赎刑确实是为达官贵人而设,不是寻常百姓可以负担的起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漏洞,那就是没有看到第六条史料中:“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金平贾(价)予钱”,即以每年年初10月的金价为基准,这首先说明了当时黄金的价格还是有浮动,而不是恒定不变,这就导致了作者在参考秦简时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
除却误差的原因,根据《汉书·食货志》“黄金一斤值万钱”来看汉初的几条赎死诏令,前三条确实感觉金额是极高的,似乎是进一步印证了曹先生的判断,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区分规定赎刑与替代赎刑。前三条所提及的赎刑无疑是替代赎刑,即用缴纳金钱的方式来免除死罪,但是《具律》中所提及的“赎死,金二斤八两”却是规定刑,即“狱成时即以赎罪论决者也”,与之可以相印证的就是第七条“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这里的人直接在判决的时候就被定为赎死,所以所需要交的费用是金二斤八两,而不是依照之前的三条,即惠帝时期的30斤黄金,武帝时期的50斤黄金。这里可以看出的是,规定赎刑本身的金额是远远小于替代赎刑的金额的,并且按《汉书·文帝纪》,当时中人即“不富不贫”之家的年收入为10金的依据,《具律》中规定赎刑的金额还是普通百姓能够负担的起的。
(二)替代刑之法外特赦
赎刑的第三种法外特赦当是替换赎的一种特殊情况,即这种赎刑不是明确固定在法律条文内的,而是通过最高统治者发布诏令或特许实施的,故而还是将这种法外特赦的情况单独给予说明。
作为规定刑的赎刑并没有数额巨大的情况,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曹先生所说之赎刑对富人有利就是错的,因为曹先生所指的赎刑应是替代赎刑的范畴。分析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赎刑范畴,多是指向比较轻的犯罪行为和特定对象,比如误杀、失职、或者是父母殴打子女、奴婢,少数民族首领等等。而前三条所列举的就不是如此了,《汉书·东方朔传》中:“久之,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狱系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请请论。左右人人为言:“前又入赎,陛下许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这里隆虑公主为儿子所赎的是直接被判定的死罪,这就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了,只有像公主这类身份显赫的人才能求得皇帝的宽赐,一般百姓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免死的,就算是可以依据诏令缴纳赎金,普通人也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所讲的替代赎确实是照顾了特权阶层的利益,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
但这种特赦的情况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拿西汉来讲,可以在武帝时期大量看到这样的例子(以《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所见为例):“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合骑侯敖坐留不与票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青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相逢。青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广,广自杀。食其赎为庶人。”
这其中大量的例子都是将军打仗失职,当斩而被豁免赎为庶人的。这就一定是为了特权阶层的利益着想吗?笔者以为不尽然,战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若是一次失败就给予死刑,无疑会对汉军优秀将领资源造成极大的损失,不利于培养经验丰富的将领,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种对于将军的特赦,所基于的正是保家卫国的考量,不能和隆虑公主一类的赎刑做相同的理解。
再来看看东汉时期的例子。《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十二月甲寅……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十五年春二月庚子……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后汉书·孝灵帝纪》:“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辛亥,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八月,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癸酉,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首先是频繁出现对于“亡命殊死以下”以及“囚罪未决”的入赎的诏令,而不是对所谓达官贵人的,对于这一点前人的学者也有注意到,并认为这明显带有怜恤宽宥之意,但是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除了宽宥之意外,更深的还是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东汉长期都伴随着严重的流民问题,导致国家的赋税严重缩水,国力减弱,并伴随着严重割据势力及农民起义的忧患,故而这里可以看到国家多次宽释“亡命”“囚罪未决”之人,主要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定、统治长久的目的,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之前的学者普遍没有看到。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的赎金数额比西汉时期有了大幅度的下调,在上节计算金钱换算时,第一条中有应劭的注释:“一级值钱二干,凡为六万,若今赎罪入三十疋缣矣。”这里所说的当是东汉时期的价格,也就是在东汉,三十缣价值6万钱,西汉时期的30万钱、50万钱要少了许多。还考虑到有些百姓交不起钱,就以缣来代替,除此之外,汉代还有许多的赎刑方式,比如用粟米、竹、军功等等的方式。这就进一步说明赎刑的门槛其实并不是总那么高,也不总是为达官贵人而设。
(三)史料缺乏
曹先生在做出结论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史料方面的断层,即在汉初的时候,有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可以参考,但是这之后的赎刑使用状况就没有如这般详尽的史料支撑了,正史中所记载的多是身份显赫之人的生平事迹,较少涉及极为具体的寻常百姓的生活实例,由此就会给人一种赎刑在后期只是富人开脱罪责的工具,而没有给民众以实际的宽松。可以说,张家山汉简和常见的传世文献所记述的是不同侧面的历史内容,汉简中是比较具体的,涉及基层百姓的判罚条例,而文献中多是法外特例的情况。由于后续的简牍材料还有待发现,所以汉代中后期的赎刑发展情况不可轻易的得出结论,但是根据赎刑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发展脉络,笔者还是倾向于赎刑在汉代中后期一直发挥着其作用,而不是如曹先生所言是基本消失的状况。
[1]朱红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班 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宋 洁)
2016-05-25
高子谦(1995-),女,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学生。
DF092
A
1672-1500(2016)03-00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