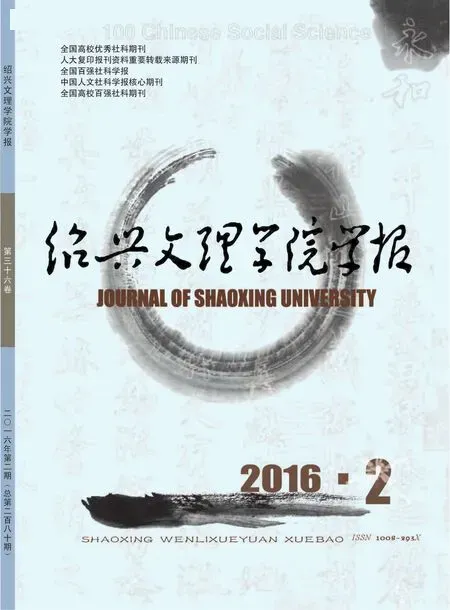“古田会议”与近代中国兵文化的转折初探
张斌奇 汪炜伟
(1.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公共基础教学部,浙江 金华321013;2.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000)
“古田会议”与近代中国兵文化的转折初探
张斌奇1汪炜伟2
(1.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浙江金华321013;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000)
摘要:“古田会议”是一场关于军队思想、军队文化改革或曰重塑军魂的会议,它力求将红军由传统观念浓厚的军队,转化成能够承载和实现中共政治理念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似为公论。少为人谈及的是,古田会议所表达的建军思路,与近代以来中国理念建军思潮息息相关,其所确立的建军模式亦是这种思潮的深入和科学化。某种程度上说,古田会议是数千来中国兵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种转折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古田会议;理念建军;工农红军
汪炜伟(1984-),男,福建惠安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一、中国工农红军之传统色彩
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兵》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世的衰败与积弱,主要原因是“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1]49。所谓“兵的问题”,在雷氏看来,是无兵文化弥散社会,民众耻于为兵,只得由流民充任。此种流民为兵自然衍生出诸多问题,或兵匪不分,如太平天国爆发后,曾国藩观察到,清军士兵往往“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或兵为将有,如清末王闿运就评论湘军道:“湘军之制,则上下相连,将卒亲睦。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存。”[2]这种在湘军中形成了恩师、门生、故旧等不健康的部属关系,最终把军队对国家的忠诚演化成私产。
中共革命以还,此种“兵的问题”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又衍生出诸多问题。
(1)兵员构成红四军是最早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部队。它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3]56,农民约占70%,多以游击队、赤卫队、暴动队、独立连(营)、少年模范队等命名。由于来源复杂,士兵的思想状况也良莠不齐,许多人仍带着传统兵痞观念以及小农的自私性。四纵队七支队的一些士兵“平素过的农村生活……受不惯严厉的军事训练”,而由红四军派来的军事干部在士兵训练上不讲求方法,一味“取严重主义”进行“打骂式训练,官长阶级极严”。这使得士兵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矛盾重重,“逃兵日多”[3]107。此外,“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在当时红四军部队有一定程度存在,且“屡戒不改”[3]182。
对这样的一特殊群体,红军一些领导干部只看到了流氓土匪与工农红军有一样的阶级敌人,因而对于他们表现出了不正确的观点,如“流氓会打仗,我们不应排除他们”、“只要长官领导的好,士兵的成分是不要紧的”等等。我们的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中争夺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工作,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对流氓有丝毫让步。”[4]
(2)军队纪律由于大量农民入伍,军队成分复杂,纪律懈怠,兵匪不分,也未脱中国传统军事色彩。1928年2月,萧克被派往中国工农红军二团三营担任副营长兼连长,他通过接触大量士兵和下级官长,发现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带兵就是同带枪的农民打交道”,这些士兵“有些还带枪回家过夜”,“有些虽曾在旧军队或团防‘吃过粮’,有点军事常识,但也不能用军事规程来管理部队,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如果不高兴就要回家的”[5]。这种自由散漫的军纪作风显然与旧时农民起义部队相类似,根本不能担负起革新革命的重任。为此,红四军前委制定了战时纪律和一般纪律两类。战时军纪分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等,战时如犯则由军官就地枪决;一般纪律如通敌叛反、拐款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敲诈人民财物等,此类纪律按性质分死刑、罚勤务等处罚不等[3]63。有意思的,有些犯较轻微错误的士兵,则处以打屁股或打手心的处罚。如萧克曾处罚过一个对看管的土豪婆做出不规矩行为的士兵,全连士兵集合打了这个士兵的屁股。应该说,这样的处罚是红军军纪的一种戏谑化的呈现,并不是正式军队所应有的。红军成立初期由于士兵的成分、组织架构等都还处于一种非军事化的管理,存在众多旧时农民起义部队的色彩。
(三)组织建构红四军中大量士兵都习惯于旧时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许多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提出“军事领导政治”,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指导”。这种将红军引向纯军事的思维,十分落后,也相当危险。如果得到不有力纠正,红四军将可能沦为某些将领的私人部队,并日渐走向“军阀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当时士兵中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认识:“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因此,毛泽东才发出这样的感慨:“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3]180。问题存在的根源是,红军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四)指导思想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论断已逐渐在中共党内成为共识。但军队建设,尤其是党对于军队的掌控,以及党的政治理念在军队的宣传,并未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而成为关注重点。古田会议前,红四军虽然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但由于红军刚建立不久,其主要成分又是北伐军的雇佣兵和大量农民及解放过来的兵员,旧军队作风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红军中来,“突出的是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5]106-107
1928年,朱毛红军会师以后,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斗争初期条件依然艰苦,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和艰苦的根据地条件,红军中流传着一种拼命主义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坦承,他对于革命形势低落十分担忧:“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形势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这样的革命形势显然不能够使工农红军对革命的形式和前途有多大的希望。此种悲观情绪也在林彪等高级将领中蔓延,他多次表示:“现在的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否则没法维持。”这种闯州过府,形同流寇的作战思想,还是近似于农民闹革命的旧时军事原则。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就开始意识到近代中国的革命是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但是根据以上的分析,初创期的工农红军保留着大量旧时军事色彩。
二、近代理念建军之尝试
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必须指出的是,梁氏有这样的大声痛斥与疾呼,目的是在抵御外辱的情况下,重新唤起国人的尚武风气。然,无论是梁启超的无兵论,还是雷海宗的“无兵文化”,都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为国之重器的兵道因其自身流民化、兵痞化、私兵化,而流失了作为安邦定国、抵御外辱的兵的灵魂、兵的文化。如何解决中国传统兵文化之弊病?一些政治家开始对理念建军进行探索。
近代中国理念建军,大致可分为三期:
(1)曾国藩建立湘军
作为理学名宿的曾国藩提出了“用诸生训山农”的设想。为此,他任用了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李续宾、李续宜等一大批在儒学方面素有造诣的人士担任重要军事将领。据不完全统计,湘军中儒生出身的将领占58%,主要将领占3/4[6]。在带兵实践中,“以理学治军”的理念亦时时被强调。咸丰八年,曾国藩编成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以“仁”为核心价值的“爱民歌”,要求士兵“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7]。这首在湘军内部到处传唱的军歌,也作为湘军处理与民众关的基本要求。胡林翼则再三重申军纪,军队要讲究营制,士兵不可吸食洋烟,禁止赌博,“扰居民亦最要”[8]。尽管如此,实际行为中,湘军的传统军队色彩仍十分严重,“兵匪不分”现象没有解决,“兵为将有”尤为严重。更为重要的是,湘军中无论是儒生将领,还是儒生士兵,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依然是“士”的角色,崇文耻武的心理依旧不能使湘军蜕变为现代军队。在一个崇文耻武的科举社会里,儒生行伍,尤其是一些破落的穷酸儒生,当兵入伍并不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而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如湘军士兵的月饷较为丰厚,是绿营兵的一至三倍。这样的丰厚饷银,自然能调动一些在战争动乱状态下无法入仕的儒生投笔从戎。因此,此类士兵,并非是国之良士,他们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甚至他们骨子里更加认同的是“士”的身份,而耻于“兵”的角色。因此,曾国藩的湘军的创建,所谓“用诸生训山农”在先期的确起到了约束部下的作用,但是后来也逐渐蜕化成流民、兵匪之流的角色。曾国藩的以儒学建军的理想化尝试最终也失败了。而且,曾国藩的建军模式,在军队中形成了比较浓厚人身依附关系,近代军队的私兵制由此开始,“武夫当国”成为近代乱世之源。
(2)孙中山创立黄埔学生军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及中共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试图以之为基础建成不同于传统的新式军队。黄埔学生军大多由热血青年组成,他们怀抱杀敌报国之期望,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与军事近代化的趋势相一致。由于认识到“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9],因此,孙中山试图将“三民主义”作为这支军队的精神灵魂。其所撰写之“黄埔军官学校训词”即有明显表达:“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如何避免军队的后期发展被军阀所控制,是孙中山考虑的重点。其解决之法就是模仿苏联党化军队,即国民革命军全体加入国民党,组建一支由国民党控制的党军,避免军队成为军阀私产。因此,黄埔军校成立后,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住校党代表,在军队执行党的方针。党代表国民党掌控军队的象征,其职责是对军队实行政治训练,“使一般官兵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10]。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之权能与军队长官同,其所发命令,凡部属人员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11]。同时,党代表的力量也渗入到士兵的一切日常生活,了解官兵的思想状况和作战环境下的心理波动,军队与驻地百姓、团体形成紧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作为国民党在军中存在,党代表所颁布之命令与军事主官同,军事主官所发之下属任命,必须有党代表副署,方能生效。孙中山正是以党建军的方式,牢牢地掌控了黄埔学生军,为北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
然而1926年蒋介石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在没有得到党代表的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调动军队,并以武力拘禁军中各级党代表。其结果是党权不得不向军权让步。蒋介石以军事将领的身份逼走了当时国民党主管党务的总党代表汪精卫,自己成为实际控制党权、军权的最高首脑。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正式取消党代表制度,仅在连一级建制中设置连政治训练员一职。孙中山寄希望于设立党代表,对军队实行政治训练,以达军队对国民党效忠之目的,改变旧时军队兵归将有的设想彻底落空。
为何短暂的以党领军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呢?主要还是国民党组织系统弱化,党只是一个符号作用,大多数党员只是形式上入党,本身却是军阀。军事主官一反动,党组织很难以党代表的职权控制军队。最为重要的是,即使入党的军中士兵也好,党代表也好,他们所尊奉之“三民主义”本身只是一些高悬的信条而已,与官兵的真实思想之间存在较大隙缝。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未能解决这一矛盾。
(3)古田会议对于新式工农红军之形塑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对于纠正中国工农红军所存在的单纯军事化、极端民主、个人主观主义、流寇思想等起到重要作用。会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古田会议决议”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这次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层面,重塑了红军的军队文化。
首先,重申了“党指挥枪”的根本性建党建军原则,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传统在孙中山领导北伐时期就已经存在,叶挺所领导的独立团以及北伐到长江后所发展的部队,都有党的组织。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设党小组,连建立支部,营团设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设立党代表[5]11。在古田会议,这一优秀传统得到重申,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在全军中贯彻。决议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来阐述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非党与枪是平行的,更不是枪指挥党。如果任由此种思想延续下去,那就会重新出现中国历史上“兵归将有”的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而中国工农红军一旦走向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那红色政权必定不得长久。因此,在决议的最后,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12]。
其次,制定了一系列规训和培养红军士兵的制度。如发展红军党组织的制度、对红军士兵进行党化教育的制度、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对士兵的奖惩制度和处理伤兵的制度。这些制度涵盖了红军士兵的政治、军事、日常生活、文化学习、行为规范及生命关怀等方方面面。这些制度从具体的层面上力求肃清中国传统兵文化对于红军的影响,为红军由一支成分混杂、纪律混乱的队伍发展为可以承载和实现党的政治理念的新型军队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也专门阐释了对士兵人身权益的保障,废除了肉刑制度,特别是枪毙逃兵的做法。枪毙逃兵历来是中国旧时军队的一种陋习。虽然说在红军队伍中并不多见,但也存在着。针对这样的逃兵现象,熊寿祺回忆说,部队“每次出发时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制”。后来,红军前委感觉枪毙逃兵是封建制度作风,因此改以教育为主,并尊重俘虏的自由意愿。结果逃兵现象得到遏制,许多士兵甘心留下当红军[13]。
再次,对红军的职能进行了拓展。其中明确规定,红军不仅需要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特别是对红军如何进行群众宣传作为详细的规定。这使红军摆脱了纯军事组织的传统思维框限,成为更有生命力、职能丰富的现代化军队。
应该说,“古田会议”为解决红军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矛盾,提供了重要途径。它重塑了红军军魂,并从制度上为红军从旧有的兵文化中脱胎而出提供了孵化器,使红军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它让红军真正成长为承载着中共革命理念的新型军队,从而为中共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新式兵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意义
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新式兵文化,不仅对于红军及中共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整个近代社会而言,具有深刻影响。
第一,工农红军与近代底层社会革命秩序的整合。
由于红军创设初期的成员构成相当复杂,军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这种旧时传统军队的组成存在分裂中国革命的危险。因此,如何“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成为关系红军生存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结合列宁的建党学说,经过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以及初期的战争失利,在古田会议前后逐步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式的领军模式,即以制度化的方式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植于中国工农红军之上,解决了党组织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党的正确路线教育肃清了近代以来革命秩序中的小农主义、流氓主义、逃跑主义、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
从红军的组织建构、斗争原则到纪律宣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希望以此来整合中国底层社会的力量,重塑近代中国的革命秩序,从而使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革命武装生发出强大的依附性与向心力。底层社会民众以中国工农红军为核心,在军队外围形成各种组织化的有效社会动员模式,如工会、贫农团、妇代会、民兵(赤卫队)、童子军等,原来农村散漫的状态彻底得到改变,形成了一种准军事化的状态,大批农民得到一定的训练,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
第二,工农红军与近代社会动员及资源的汲取。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14]深入群众、深入农村的最有效作法就是解决广大农村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使他们能够认同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的政治理念,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动员,从而使革命最大化地汲取底层社会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
如何动员社会与资源的汲取?1929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群众路线”[15],即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统一起来。打仗是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是决定红军能够生存多久的问题。中共在农村建立起主力红军—地方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者有机结合的武装体系。军队成为中共与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在初创时期即建立了有效的宣传兵制度。红四军每个机关都派五个士兵专任宣传工作,五人分为两组,一组口头演讲,另一组文字宣传,主要是贴布告和刷标语[5]12,建立了强大的宣传机器,将党与红军的政策让农村民众、顽固分子以及俘虏知晓,动员广大群众形成以中共革命为中心的近代革命新形式;另一方面,制定充分考虑最广大农村贫下中农利益的阶级政策,即打击农村中的土豪、地主、富农,把他们的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下中农,同时也为革命补充了大量资源。
第三,工农红军与传统兵文化的重塑。
雷海宗先生指出:“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阶级的军队。因为是贵族的,所以仍为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1]6。从军入伍自然成了社会地位、财富的身份象征。此期之兵者,尚能以精英之身份象征,出则保家卫国,入则弹压乡里。然,东汉以后,耻兵文化盛行,从军行伍只能算是“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因此衍生出流民为兵、兵痞盛行、军队私化等诸多问题。
工农红军形象的改变,使中国这种耻兵文化开始逐渐消失。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深入群众,扎根农村,军民关系逐渐改善,许多优秀青年争相当兵。正是这样一支军队,致力于农村的土地改革、推行民主、扫盲、提高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的工作,红军的正面形成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树立起艰苦奋斗、爱国奉献的正面形象。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故事的传播以后,20世纪30年代被国民党恶意陌生化、妖魔化的“赤匪”“土匪”的形象逐步得到扭转,中国工农红军扎根西北根据地的正面形象广为传播,使国人在国难深重的时代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由此,中国军队不再只是士兵营生的途径,而成为培育社会栋梁的有效场域,成为一个进步的、爱国的、战斗的群体的代名词。
参考文献:
[1]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9.
[2]王闿运.湘军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3.
[3]陈毅同志关于朱毛红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摘要)[A]//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56.
[4]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A]//福建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续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303-307.
[5]萧克.朱毛红军侧记[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37.
[6]施渡桥.晚清陆军向近代化嬗变述评[J].军事历史研究,2002(1).
[7]王定安.湘军记:卷20[M].长沙:岳麓书社,1983.
[8]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113.
[9]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3.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A].北京.档案出版社,1994:272.
[11]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J].近代史研究,2013(5).
[12]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9-80.
[13]熊寿祺.红四军状况:1930年5月[J].党的文献,1999(2).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3.
[1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9[A].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481.
(责任编辑林东明)
GutianConference and Turning of Modern Chinese Weapon Culture
Zhang Bingqi1Wang Weiwei2
(1. Zhejiang Colle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ghua, Zhejiang 321013; 2. College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0)
Abstract:The Gutian Conference is a conference on the reformation of military ideology and culture, i.e. a conference to remodel the soul of the army. As is known to all, it reforms the Red Army from an army with traditional concepts into a new people’s army bearing and fulfilling the political ide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less mentioned is that the military thought of the Gutian Conference i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military construction in modern times which is in turn deepened and scientized by this trend of thought. To some extent, the Gutian Conference, which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Chinese soldier culture with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revolution.
Key words:Gutian Conference; concept of army construction; the Red Army
中图分类号:E221、E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2-0069-05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2.015
收稿日期:2016-01-26
作者简介:张斌奇(1988-)男,浙江杭州人,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公共基础部助教,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