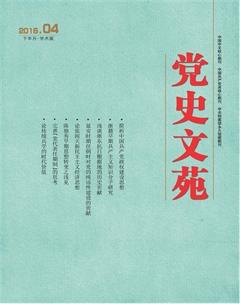陈独秀早期思想转变之浅见
廖玉洁
摘要]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发生过几次重要的转变,对于他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至今仍众说纷纭。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一生功过的评价,也有过两极分化的趋势。如何正确看待陈独秀及其思想转变,应将其放在所处具体的、历史的环境中去。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关键词]陈独秀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一、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及表现
关于陈独秀何时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界说法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陈独秀于1920年5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已经服膺了马克思主义”[1];有人认为“1920年10月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证实了陈独秀对西方民主主义的抛弃,这是自从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号内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后对其思想转变的最清楚的表达”[2];有人认为“从1920年到1921年党成立期间,陈独秀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学术思想等方面已基本上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3];还有人认为陈独秀完成思想演变在1920年下半年,一般以他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为标志[4]。
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即陈独秀在1920年9月基本上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消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5]。对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过程及其表现,应首先着眼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
(一)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转变。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于《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谈及社会主义:“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他将人权、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视为近代文明的三大宝物。他紧接着又谈到:“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陈独秀看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缺陷,要求通过革命手段消除不平等与压制。他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欧洲社会进步的两大车轮,在新文化运动中也高呼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到1919年4月,陈独秀在其《随感录》中谈到:“欧洲各国社会主义的学说,已经大大地流行了。俄、德和匈牙利,并且成了共产党的世界。这种风气,恐怕马上就要来到东方。”“日本人害怕得很”,而对中国“即便来了,就可以用‘纲常名教四个字轻轻将它挡住”。陈独秀发现社会主义有利于现今问题的解决,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920年3月在《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这是陈独秀对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在此时仍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近代别的著名学说”的一种,“有一方面真理”,但不是“包治百病的学说”。
1920年5月在《劳动者底觉悟》中,陈独秀批判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现象,提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改造社会。但陈独秀认为这是劳动者觉悟的第二步。“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说得到第二步呢?”第一步的觉悟应该是待遇改良,即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工资问题。
1920年9月,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认为,要扫除游堕的消费的资产阶级所带来的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的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去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更直接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分析、解决问题。至此,陈独秀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把立足点移动到无产阶级这一边在行动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俨然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对十月革命态度的转变。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给予中国革命重要的方法论启示。而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俄国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开始流传,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在十月革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并没有放弃他对民主主义的追求。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5卷1号上仍主张“当排斥武力政治,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显然,他对十月革命的暴力方式是持排斥态度的。到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7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过激派与世界和平》,针对“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都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的现象,陈独秀说,“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6]。这里陈独秀对布尔什维克被说成是扰乱世界和平,表示了自己的不以为然。在1920年1月《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文中,陈独秀将“列宁政府”视为“进步主义”,表达了他对十月革命的肯定,但这里的进步是相对于保守和侵略来说的。直到1920年9月,他对十月革命开创的列宁主义的劳动专政才完全赞同。他说各国革命后“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7]。同日在《答费哲民(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中指出:“我以为解决先生所说的三个问题(其实不止这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来改革社会制度不可。”以上表明,陈独秀完全承认了用十月革命式的暴力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
二、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陈独秀在20世纪20年代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转而投身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这次重要的转变,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一)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冲击。陈独秀绝对是一名爱国主义者,他曾在《亡国篇》中一针见血地将亡国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和一众友人的力量,唤醒广大中国青年,一道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求得民族独立。
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中高呼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对中国来说只能是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全体中国人民都满怀信心,认为祖国终于能在国际会议上扬眉吐气了。在对德制裁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提出了“十四条意见”。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说到:“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但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把人们心中对西方先进社会的追求和对文明秩序的向往彻底击碎。陈独秀称威尔逊为“威大炮”,并提出“公理何在?”的疑问。他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给迷茫中的陈独秀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促使他选择在中国走苏俄式的革命道路。
(二)来自苏俄的影响。第一,苏俄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新成立的苏维埃俄国于1919年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宣称“工农政府于1917年10月取得政权后,立即代表俄国人民向全世界倡议建立巩固持久的和平。……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不论居住何地,不论它至今是否独立自主或被迫附属他国,在自己的内部生活中均应享有自由,任何政权都不得把他们强留在自己的领域之内。”承诺放弃接收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满洲及其他地区,拒绝接受因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并且废除一切特权。
不管苏俄最后有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但在当时,和平自由、归还领土、废除特权等条件都是陈独秀等革命党人苦苦追寻了多年的东西,所以苏俄及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有了一定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6号刊登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无任欢喜”,“不胜欣喜”,“非常的欢喜”,并要“一起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尽管这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直接表态,但无疑他是赞同的。随后他发表了《我的意见》和《答知耻》,明确表示欧、美、日走的是错路,他则要走上“正确的路上去了”。
第二,维经斯基的作用。维经斯基作为苏俄的代表,一来到中国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与陈独秀会面之后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在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他说,“必须从中央和从西伯利亚给我们寄苏俄报刊”,“关于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的材料以及关于苏俄经济、文化建设情况的专门书籍也是需要的”,“请按我的电报汇款”,等等。这些,使得“长期以来苦于找不到一种救国救民的根本办法,对社会主义认识只有向往却无系统知识的陈独秀,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列宁的理论折服了”[8]。
基于此,一个在中国传统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三、陈独秀思想转变中的反复
1920年9月前后,陈独秀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但在此之后,人们总发现他有一些貌似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例如,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交恶,在国共合作中的表现,直至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开除出党,等等。难免会让人认为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绝对,客观地说,陈独秀在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后,从未放弃过对民主的追求与坚守。
在1920年9月发表的标志着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谈政治》一文中,他谈到“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利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很显然,他反对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追求的是劳动阶级的民主。而他对“民主”和“专政”的关系,正如他在《青年底误会》中劝诫青年不要“扶得东来又西倒”一样,决不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而倒向资产阶级民主这个“西”。
晚年的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不同罢了。这种民主观并不是受托洛茨基影响的结果,托洛茨基本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胡适从他的视角曾评价陈独秀的这种民主观为“大觉大悟的见解”。陈独秀的一生并没有放弃对民主的坚守和追求。
对陈独秀及其思想转变的评价,早期呈现为过多否定。以偏概全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披露和发掘,对他的评价逐渐趋于客观公正。“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9]因此,对陈独秀及其思想转变的评价决不可以偏概全,须辩证、客观、全面地看待。我们不能否认,从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到选择马克思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反复,“就是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在旧中国的泥潭中,陈独秀依然在趔趄向前,尽管步履蹒跚,有时踯躅,有时摔跤,但他毕竟没有当叛徒,没有做汉奸,没有作出丝毫有损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国格和伟大人格的事来”[10]。陈独秀作为影响中国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的兴起是有重要贡献的。○
参考文献:
[1]朱文华.永远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7.
[2]赵沈允.从国外看陈独秀早期社会主义思想[M].合肥:黄山书社,2012.
[3]王树棣.陈独秀评论选编(上册)[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4]齐卫平,王孝贤.论五四时期陈独秀思想转变的典型意义[J].江淮论坛,1996(3).
[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黄莺,刘柳.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考察[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1(7).
[7]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8]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胡绳玉.中共党史人物传不能没有陈独秀[J].学术月刊,1991(11).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