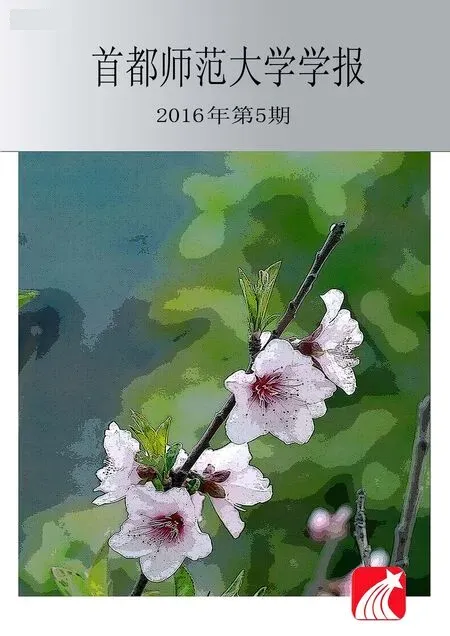中村不折155号中之《维摩经注》创作年代考
王晓燕
中村不折155号《北凉写经残卷六》是中村氏北凉写经残卷中的一号,刊布在矶部彰《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①矶部彰:《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东京:二玄社,2005年版,第15-23页。。共包括五件残卷:①.金光明经第四(纸张:265×1780mm)②.般若部论(计两纸,纸张:245×422mm,245×235mm)③ -ⓐ.大般涅槃经·一(纸张:264×425mm)③-ⓑ.大般涅槃经·二(纸张:264×475mm)③ -ⓒ.大般涅槃经·三(纸张:264×380mm)④.法华经方便品(纸张:250×411mm)⑤.维摩经注(纸张:248×807mm)。五件文书在写卷形制上或者内容上并没有同属关系,亦非同一人抄写,应该只是由于抄写时代相近被列为一组。
第五件《维摩经注》写卷②《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下卷,第22-23页。,首尾均缺,起“维摩鞊来谓我言”,迄“为非耗”;存46行,行字不等,经文为大字,注释采用双行夹注格式;有乌丝栏;隶楷书写,字体古朴,字品、书品较好,为六朝写本。吐鲁番出土,所疏为“支谦本”《佛说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中的内容(目连辞问疾及大迦叶辞问疾部分)。历代大藏经未收。
虽然早在1927年中村不折就对此件做过介绍③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上卷:“存四十六行,长二尺七寸,八分书ナリ。本文ノ下ニ二行ノ细注アリ。吐鲁番ヨリ出ジ。书风严正,八分ノ笔势明カナリ。风骨东汉ノ白石神君ニ似タリ。”东京:西东书房,1927年版,第37页。按:2003年中华书局以《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为名重印,上文所提及的《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一书刊布了此件的全部图版。,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只有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一书曾涉及此疏,认为“这个注解是以《般若经》解释《维摩》,其造注年代为罗什前之般若学兴盛时”,并且推测此疏“可能为北人所造的注”①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台北: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1页。。其后,曾晓红在其硕士论文《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中对此件做过叙录,并刊布了释文②曾晓红:《敦煌本〈维摩经〉注疏叙录》,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45-46页。。本文拟对其创作年代及其中“后出经”问题试作探讨。
一、注释的创作年代
此注释的年代乍看似乎很明白,因为其中有:“佛告贤者大迦叶晋言普逮。,汝行诣维摩鞊问疾。”③重新释文内容见后文附录。其中“晋言”一语似乎暗示我们这是一个晋代的注释。不过,释果朴曾指出“汉言”与“晋言”不能作为判断一个译本年代的直接依据(Jan Nattier则认为“晋言”一词对于竺法护来说是有效的)④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第221页;Jan Nattier,A Guide to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 Texts from the Eastern Han and Tree Kingdoms Periods,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Soka University.。笔者也在晋代之后的少数文献中发现使用“晋言”的情况,例如《贤愚经》中即大量地使用了“晋言”一词,但该经编译时(445年)东晋已经亡国(420年)⑤《出三藏记集》卷二有“《贤愚经》十三卷宋元嘉二十二年出。右一部,凡十三卷。宋文帝时,凉州沙门释昙学、威德于于阗国得此经胡本,于高昌郡译出。天安寺释弘守传”。(梁)释僧佑撰,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9页。。而本文所讨论的又是一部注释则尤其需要小心,如部分隋唐注释文献中偶尔也会出现“晋言”,这是由于引用前代作品导致的,因此不能因为注释中出现了“晋言”一词便贸然判断其创作于晋代。
笔者以为,写卷中关于“八解”的注释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经):八解正受
(疏):得“八解”,正智也。何谓八解?一者、见诸色色;二者、无“色”、“无色”想;三者、无若干众多之念;四者、行无量虚空行;五者、越无量虚空行;六者、行无量知慧行;七者、越无量智慧行;八者、悉越一切有想无想。
通过比对,笔者发现此处对“何谓八解”的解释实际上是衍生自竺法护《光赞经·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萨品第十一》中“八解脱门”的译法⑥《大正藏》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79页下栏第27行-180页上栏第10行。。为方便理解,列表如下:

中村不折155号中之《维摩经注》《光赞经》第一 见诸色色见诸色色第二 无“色”、“无色”想⑦ 内无色想而外见色,虽处于空而不解脱,则不能越一切诸想第三 无若干众多之念得于众想,在于根本,无有若干众多之念第四 行无量虚空行行于无量虚空,虚空成就第五 越无量虚空行悉得越度一切虚空,虚空之智在于无量识慧之行而为成就第六 行无量知慧行皆得越度无量慧智之天,而处无有不量,无量之慧成就成行第七 越无量智慧行而悉越度一切,不用无量之慧,在于有想成就之行第八 悉越一切有想无想而悉越度一切有想无想,悉蠲诸想安寂然行
另外,与《光赞经》属同本异译的鸠摩罗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句义品第十二》中对应段落则译为“八背舍”(《放光》缺乏对应段落,玄奘的译本相差更多,此不罗列):
……明解脱念慧正忆八背舍。何等八?色观色,是初背舍。内无色相外观色,是二背舍。净背舍身作证,是三背舍。过一切色相故,灭有对相故,一切异相不念故,入无边虚空处,是四背舍。过一切无边虚空处,入一切无边识处,是五背舍。过一切无边识处,入无所有处,是六背舍。过一切无所有处,入非有想非无想处,是七背舍。过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入灭受想定,是八背舍。①《大正藏》第8册,第243页上栏第2-11行。此外,《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四摄品第七十八》有一段与此类似的段落出现“八解脱”,但“解脱”二字在校记中则为“背舍”,二者内容基本一致。此段作“云何为八解脱?内色相外观色是初解脱;内无色相外观色是二解脱;净解脱是三解脱;过一切色相、灭一切有对相,不念一切异相故,观无边虚空入无边虚空处;乃至过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入灭受想解脱,是名八解脱”。《大正藏》第8册,第395页上栏第1-7行。
不难看出,中村不折155号中之《维摩经注》的措辞与鸠摩罗什《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迥然不同,而与竺法护《光赞经》十分接近。这说明该注释的创作年代当晚于竺法护《光赞经》(286年)译出的年代②《出三藏记集》卷二:“《光赞经》十卷十七品,太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第32页。,并可能早于鸠摩罗什《摩诃般若》的译出年代(约403-404年)③《出三藏记集》卷八《大品经序第二》:“以弘始五年,岁在癸卯,四月二十三日,于京城之北逍遥园中出此经。……以其年十二月十五日出尽。校正检括,明年四月二十三日乃讫。”第292-293页。,或至少不比这一时间晚太多(因为也有可能罗什本已译出,但尚流传不广)。而且,其最下限应不晚于此卷书写年代的北凉(公元439年前)。这样,本注释中的“晋言”亦可与上述关于“八解”材料相互印证,成为确定其创作年代下限的佐证。
其次,中村不折155号书写风格与北朝时期风格相符。一是,其书写风格、用笔特点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的《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相似(见图1),特别是卷中横划上翘的笔画。二是,155号的书体、写作风格与敦研8《维摩诘经卷下观人物品第七》、敦研19《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类似④段文杰主编:《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一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8-20页。,敦研8号文书的内容即是“支谦本”《佛说维摩诘经》,抄写年代是北朝时期;敦研19叙录中,通过其与北凉高善穆石造像塔铭文、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文以及《爨宝子碑》的对比,认为“此类写卷与北凉佛教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其独特的‘北凉气质’,是我们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不同时期同一地区的古代写本中,难以见到的”⑤《甘肃藏敦煌文献》第一卷,第271页。。
另外,《出三藏记集》在记录竺法护译《维摩诘经》时使用“维摩鞊经一卷”⑥《大正藏》55册,第7页下栏第1行。按:点校本《出三藏记集》已将“鞊”改作“诘”,为便于比较,这里使用《大正藏》本。,其中“鞊”,《大正藏》校记“鞊 =诘【宋】*【元】*【明】”。 可见,作为底本、现存最早的高丽藏即记为“鞊”;同时,记录鸠摩罗什译经时则使用“新维摩诘经三卷(弘始八年于长安大寺出)”⑦《大正藏》55册,第10页下栏第22行。。同一书内记载一部经典不同译本,用字却有别,可见早期用“鞊”,鸠摩罗什时代及之后使用“诘”字。而且,就笔者翻检敦煌写本《维摩诘经》中“诘”的写法所见,仅上博1号写作“鞊”⑧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馆编著:《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而上博1号正是“支谦本”《维摩诘经》。罗什本中未见“鞊”的写法。

图1
综上所述,这部注疏的创作年代晚于竺法护《光赞经》(公元286年)译出的年代,并早于鸠摩罗什《摩诃般若》的译出年代(约公元403-404年)。
二、关于“后出经”的解释
在注疏第27行,对“八上居士”的注文出现了“后出经”:
(经):说是法时,世尊,八上居士发无上正真道意,我无此辩,是故不任诣彼问疾。
(疏):后出经曰:“八百居士。”
这里的“八百居士”,与罗什本是吻合的,但似不能据此判断“后出经”就是指罗什本。因为这里的“后出”是相对被注释的“支谦”本说的,只要是“支谦”本之后的译本都有可能是这里的“后出经”。而且,考今梵本对应部分作apati-parado aānāṃghapatis'atānām,可译成“八百居士”,因此任何译本作“八百居士”均可。支谦本以后的《维摩诘经》译本有竺法护的《删维摩》与《维摩诘经》二本、竺叔兰本①《历代三宝纪》记载竺法护本的翻译时间不足为据。卷六:“《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太安二年四月一日译,是第三出。与汉世严佛调、吴世支谦出者大同小异。见《聂道真录》。”《大正藏》第49册,第63页下栏第9-10行。、罗什草译本及修订本、玄奘本②另《历代三宝纪》中还记载有祇多蜜本,《出三藏记集》中未载,恐不确。。以上诸本中以竺法护的两个译本距离被注释本的时间最近,其流行的时代也大致与经疏创作年代相当。
《出三藏记集》所引《道安录》的部分中著录了两个竺法护本,说明道安时代尚能看到竺法护之《删维摩》与《维摩诘经》③(竺法护本)“《维摩诘经》,一卷,一本云《维摩诘名解》。……今并有其经”,《出三藏记集》,第33-38页;“《删维摩诘经》,一卷。祐意谓先出《维摩》烦重,护删出逸偈。……今阙。”《出三藏记集》,第39-43页。释果朴已经指出,这两段均是《出三藏记集》引《道安录》的内容,因此道安记载了两个竺法护本,说明他当时或许尚可以见到。而后面的“今并有其经”和“今阙”是指僧祐所见的情况,而不是道安时期的情况。参见释果朴:《敦煌写卷P3006「支谦」本〈维摩诘经〉注解考》,第34-35页。,而道安就生活在本注释最可能创作的四世纪。因此,笔者推测,这里的“后出经”更可能是指竺法护的《维摩诘经》。上文提到的经疏中关于“八解”的解释受到竺法护所译经的影响,亦可作为以上推测的旁证。
另外,刘安志认为吐鲁番出土“孙吴支谦译《维摩诘经》注疏残片”与本文探讨的《维摩经注》,“两者似属同一抄本”④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120页。此残片为日本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卷《佛典及佛典附录》第三号中的一件,称之为“《图谱》第3号(3)”;其双行加注的经文是支谦本所译《维摩诘经》卷下《如来种品第八》中的一段颂文。。但由于它们之间内容相差太大,仅就其书法而言,如“以”、“是”、“清净”、“无”等字的抄写,并不是同一抄本:

?
不过这两件文书均是吐鲁番出土,且具有书法古朴、乌丝栏、双行夹注的共同特征,在系统上应比较接近,可为考察《维摩诘经》在北方地区的流行与传播提供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