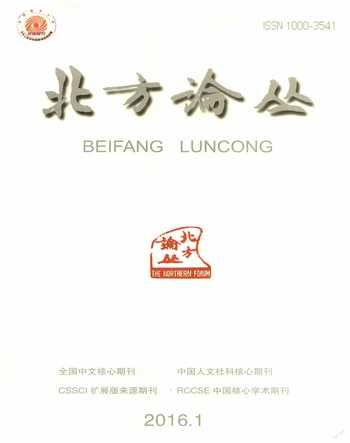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悖论分析
宁琳
[摘 要]陈染、林白等女作家们的“镜城突围”大胆张扬欲望书写,彰显出鲜明的固守边缘和反叛主流的性别立场,她们的“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一道夺目而亮丽的风景,但是总体上来看,这种写作没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可与更深入的讨论,并最终陷入了写作的困顿。究其原因,这与其内部存在的多种悖论不无关联。本文将对“个人化写作”的三个主要悖论进行梳理并阐释:个人立场的固守与个人经验有限性之间的悖论;追求私人空间的独立性与私人空间不可能独立之间的悖论;以真实性为据和真实性不再可靠之间的悖论。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悖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47-03
陈染199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以后,在写作上逐渐归于沉寂。后来于2000年相继出版日记体的《声声断断》和谈话录的《不可言说》,在这中间的四年里,并无小说面世,直到2003年小说集《离异的人》出版。如果说《私人生活》是陈染写作黑色时代的典型代表,那么《离异的人》则可以说是陈染步入灰色时期的尝试。《离异的人》包括《梦回》《离异的人》《残痕》《碎音》四部短篇小说,其中依然展现了女性孤独的生存境遇以及对男性失望的情绪,但如黛二和倪拗拗般孤高超凡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已经看不到,而是透出一种庸常生活的世俗气,女主人公的形象也变成了一个中年会计的身份。这些作品一反作家过往的冷峻和尖锐,生活的气息很浓,文字也细腻冲淡了许多,可以看出,年近五旬的陈染,在经历了重重生活的洗礼和成长的疼痛之后,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开始转变。对于这种改变,陈染如是说:“日子过得平平常常,甚至乏味无聊,这是人生的常态,也可以说是人生的本质,而充满激情和拥有兴奋点的日子,是短暂的,是非常态的。一个成熟的人必须面对和接受平常的甚至乏味的生活。”[1](pp10-15)“早年的作品是靠情绪和激情支撑小说的框架结构,现在我没有那么饱满的情绪,就不那么写了。”[2](pp7-13)但无论如何注解,这其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写作困顿却是不争的事实。
无独有偶,“个人化写作”另一个代表作家林白的写作也出现了明显的改变。《一个人的战争》之后的《万物花开》和《玻璃虫》,早已失却了当年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的恒心和勇气,以往作品中直率和动人的力量削减了很多,曾经执着飞翔的姿态也不见了。作品浮现出缕缕的温情,对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妇女进行平和地描绘与叙写,昭示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一)个人立场的固守与个人经验有限性之间的悖论
身体写作作为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对抗男权传统文化的重要武器,以及建构女性诗学的重要凭依,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可是,身体资源的有限注定了身体写作在一段时间后会步入局促,而且女作家们书写女性成长史所依据的女性成长体验总会有类似之处,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语境下,女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文本进行模仿,使得自恋、姐妹情谊、身体、规避等经典话语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这些都导致不同女作家的文本好像是内容雷同的不同版本。除了在写作内容上有这种趋同的倾向之外,叙事的风格、姿态,以及语气、意象等也有相似之处。对此,荒林认为,把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混为一谈容易让读者难分彼此,也使得人物被作品那种情绪化的氛围所影响缺乏一种内在的力量,怎样去突破这种状态,去跳出这种写作的局限,是陈染等女作家的写作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和考验。1996年《私人生活》以后,陈染的创作骤减,虽然这与她的身体状况不无关联,但这也印证了个人经验的有限性对于写作的影响。一旦写作离开了个人有限的经验,而又没有其他创作素材来充实,创作便会陷入困境甚至走向停滞。
作家们身处同一时代语境,还有一些作家生活在同样的地域,因此,她们的社会经验难免雷同。以个人体验为依据进行创作,必定会出现作品内容的重复。例如,陈染与林白都生活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她们不仅年龄相近,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感知体验也有相似之处,再加上写作立场的类似,很多评论家常常将二人并置在一起予以评论。除了地域和时代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身份的问题,以陈染和林白为例,她们是生活在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她们的作品所依据和书写的更多的是她们这个阶层的女性经验,至于这个阶层之外的其他女性,则未能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客观而丰富地呈现。对此,作家们有所感应,所以在后来的写作中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林白在之后的《万物花开》中,规避了以往仅仅立足个体经验进行写作的拘囿,拓展了写作对象的范围和创作视野,陈染也提出了她的“超性别写作”的理论作为回应,可以看出作家对自我写作进行突破的努力。虽然如此,通过对社会各种身份和阶层的女性进行关注和书写,并进而探寻女性经验和人类共通经验的关联,并致力于两性关系建构的女性写作始终并不多见。在这一方面,我国台湾女性作家的作品能够提供一些启示,比如,我国台湾女作家李昂的作品。她的《杀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这部作品在探讨两性关系的同时,更注重思考人类的生存问题,从性的不合理来透视人生存的不合理,由女性命运的遭际入手来揭示整个人类生存的宿命性与悲剧性,对性的政治和人性的愚昧、贫困和非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将女性个体的生存处境和整个女性群体的性别处境相关联,进而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处境的思考。
(二)追求私人空间的独立性与私人空间不可能独立之间的悖论
一些新生代作家引用萨利托的观点指出,在古代社会个体并没有自我的空间和自由,而现代社会里个体则可以在集体之外拥有自己独立的精神立场,这是二者的区别所在。他们认为,传统社会总是将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相等同,这无形中忽视了个体的独特需要,将个体强行纳入集体之中,对个体和个人缺乏尊重与认同,然而现代社会重新赋予个人以自由,因此,私人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自由和文明程度的参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人化写作”是一种非常现代化的写作姿态,因为它张扬一种个人化的写作立场,倡导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它认定每个人虽然在公共领域内是一个社会公民,但在私人空间里更是独立自足的个体。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写作常常占据要位,而“个人化”的写作相对潜抑和边缘。正如萨利托所说,这就是将个体强行纳入集体之中的表现,而这说明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前现代阶段。
在如此历史文化语境下,“个人化写作”从文学的向度对私人领域及其独立性的凸显,试图打破代言式书写传统的努力,体现了对自由精神和文学独立性的维护,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从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来看,这种诉求合理而自然。
可见,“个人化写作”的叙事姿态是以个人/集体和个人/公共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把历史上的公共领域划分为代表型公共领域和市民公共领域,他认为,文学在市民公共领域中,处于一种中间的地带,它处于代表型公共领域和市民公共领域之间,是二者之间的中介,不仅如此,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的沟通也离不开文学。文学不仅是市民公共领域中的一部分,还是它的表征和催化剂。哈贝马斯认为,市民公共领域有三种文化机制,分别是文学、沙龙和咖啡馆,其中文学是最重要和基本的一种,因为后两者常常为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提供条件与场所。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文学写作是市民公共领域中极为关键的因素,发挥作用巨大,它由生活世界、作家和读者、作品共同构成。这能否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信息,仅仅把文学束缚在个人的空间内,使它与社会公共领域彻底脱离,使文学成为纯粹个人性的,并不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如果说“被任何一种光芒所覆盖的生活,都将充满伪饰和谎言”[3],只有个人性才是可靠的叙述对象的话,那么这里的“个人”是无法在一个纯粹独立的空间内实现自我的完整性的,因为它和社会关系完全脱离。或者说,个人具有相对性,人不可能通过自我来证实和认知自我,只能是通过自身与他者的对应和比较才能凸显自我的主体性。虽然“个人化写作”的倡导者常常论及传统文学对于个体的忽视,导致个体的遮蔽和不完整,但是,“个人化写作”对于自我过于偏执性地坚守会导致“个人”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与实现。
因此,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化的非此即彼,文学应该促进二者和谐关系的建构。更重要的是,这种完全拒斥公共领域的写作,有可能会导致公共空间里权力制约的削弱,公共权力监督的失落会带来个人空间重新被放任的公共领域冲击,“个人化写作”被消解甚至难以立足。
对于“个人化写作”,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通过凸显个人性来对抗文学传统的写作策略,带有权宜性。“个人化写作”者在倡导这种写作立场的同时,应明确个人领域的自由与完整应该以公共领域的完善与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应具备更深广的人文关怀。现代知识分子,虽然不必像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那样承载着民族与社会进步的责任心,但对于人性和现实的反思精神却是不该沦落的。
(三)以真实性为据和真实性不再可靠之间的悖论
陈染曾说:“我的小说中最具真实性质的东西,就是我在每一篇小说中都渗透着我在某一阶段的人生态度、心理状态。”[3]“个人化写作”的作家把真实性看作这种写作的灵魂,但是这里所提到的“真实”,在中国古代社会被人们称为“诚”,在西方古希腊时期被柏拉图界定为与谎言相对,在“个人化写作”中指心理层面的真实。
在传统叙事中,写作与表达总是某种话语的表征物,被其塑造与支配,因此,真正的自我表现并不存在,被表现出来的所谓的自我只是一个被意识形态化的个体。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和文化语境的转变,传统叙事对于个体真实表达的规约逐渐鲜明。诗人王家新认为,我们习惯于在写作中思考我想表现什么,其实,这个“什么”,并不存在于写作之前,虽然在写作中被表达出来,但是它和我们预先设想的内容并非一致。
陈染认为,在传统写作中,“个人”是一个“公共的人”,这个“个人”是残缺不完整的,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个人化写作”中的“个人”是与这种“公共的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有着独立的主体意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处在公共领域之外的边缘地带,所以具有隐蔽性、个人性和自主性。这样的“个人”体现了自我和个体存在的本真面目,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人。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个体”真实性的求索意义深远,它对于文学独立精神的复苏和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很多批评者对之予以肯定:戴锦华指出: “于彼时(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个人化的写作意味着一种无言的、对同心圆式社会建构的反抗,意味着一种‘现代社会、‘现代化前景的先声;而非道德化故事,不仅伸展着个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而且被潜在地指认为对合理化的主题话语的颠覆,至少是震动。”[3]
真实性之于文学写作的必要性是无可厚非的,自古以来人们就重视文学的真实性,甚至把它当作文学合法性的确立依据。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欢迎诗人的原因就在于,柏拉图认定诗人常常说谎,因而他们创作的诗不具备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比历史更具备真实性,所以用真实来为诗辩护。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生存和言说都应该是本真的,所以,作家要远离各种“闲谈”,更要拒绝人云亦云。
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道,还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抑或基督教的上帝,这里所谓的真实性,总要以一种终极性存在为前提和依据。可以说,由于真实性与终极存在的规定性相符,可以用来作为衡量合法化的依据,因此,这种合法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赋予的。如果真实性不能表达出终极性的存在,那么它的合法性就要遭到质疑。
现代社会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及合理化运动将包括上帝在内的形而上学本体统统颠覆,同一性被摧毁,相应的,神学本体和哲学本体的权威性不再,所以真实的可靠性也便有待商榷了。当代社会很多人不认同必然等同当然的观点,因此,真善美同一的传统价值立场也逐渐消逝。真与善和美不再直接相关,那么相应的,真实性的价值基础也随之不再了。既然如此,真实性本身存在的合理性有待考证,它原来所担当的用来衡量事物的价值尺度和标准的地方,恐怕也就不复存在了。
至此,以真实性作为合法依据的“个人化写作”,便因此而身陷悖论。一方面,“个人化写作”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并以真实性作为自身确立的依据;另一方面,真实性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不能继续支撑“个人化写作”。
“个人化写作”倡导文学创作要建立在偶然的、具体的和丰富的生活之上,这和后现代科学的偶然性观点不谋而合,即“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满变化、无序和过程的沸腾世界”,并且促进了文学向艺术本位的回归。但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创作主张在登场之初,难免会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写作一经问世就引发了众说纷纭的评论热潮,面对各种质疑,作家们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文学写作中,试图通过创作来获得合法性,对理论的探索便显得乏力,再加上后现代思潮令人眼花缭乱的影响,所以“个人化写作”难以科学理性地处理文学真实性问题,并陷入悖论的两难之中,便是情理之中了。
[参 考 文 献]
[1]林宋瑜. 陈染: 破开?抑或和解? [J]. 艺术评论,2007(3).
[2] 杨敏,陈染. 写作,生命意识的自由表达: 陈染访谈录[J] .小说评论,2005(5).
[3] 陈染私人生活[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作者系东北农业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