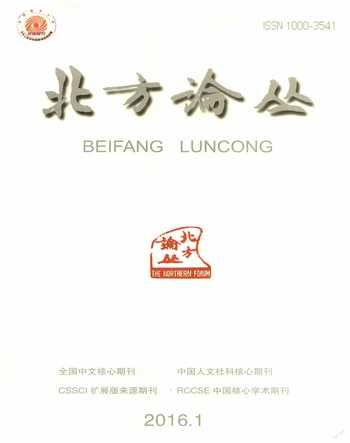从台湾客家族群记忆溯源河洛文化底蕴
樊洛平
[摘 要]台湾客家精神特征的形成,来自客家族群开山拓土的迁徙历史和悠久的文化记忆,又可追溯到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底蕴。透过台湾客家文学创作,在铭记故乡的祖根文化记忆、传承耕读文明的客家庄生活方式以及坚守客家的语言、族谱和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可寻觅客家族群生活中保留的河洛文化遗风,也由此见证了客家“根在中原”的历史文化渊源。
[关键词]台湾客家文学;族群记忆;河洛之根;文化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55-06
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中一支独立的民系,由历史战乱中的中原汉族数度迁徙而形成客家族群。从辗转于闽赣粤等地区的客居,到飘洋渡海、开山拓土的迁徙,全世界约有一亿客家人,可谓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的民族根性和文化特质源于汉民族,它不是少数民族,只是身居异乡,客而家焉。对于客家人的界定,学界多从四个方面考察:一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族人;二是会说客家话;三是有特殊的客家文化习俗;四是在南迁和开疆辟土的过程中,表现出勇于开拓进取的客家精神。而上述种种,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即客家根在中原。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与核心所在,其生命力和血脉传承源远流长,从中原出发、一路漂洋过海形成的台湾客家族群文化,同样无法不受到河洛文化的根源性影响。透过台湾客籍作家所创作的反映客家族群文化背景和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从中追寻到这种文化渊源的联系;它所维系和见证的,正是客家族群有关生命之源的祖根记忆,它“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续了一个世代延绵的传统和记忆”[1](p217)。
一、河洛之根:割不断的客家族群记忆
从早年飘洋过海、开发宝岛的客家移民,到今天拥有400多万人口、担当社会进步与繁荣中坚角色的客家族群,其生存打拼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特质更为凸显。台湾客家在漫长迁徙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记忆,有着披荆斩棘、开山拓土的“开荒牛”精神,有着大脚走天下、立身持家的客家女形象,还有客家族群特有的风俗习惯。但那种“通过代际传承,从整体上维续了一个世代延绵的传统和记忆”[1](p217),则是有关祖根的历史。身为客家,我们从哪里来?哪里是古老的原乡?寻根永远是心灵深处遥远的召唤,是魂牵梦萦的族群记忆。不仅客家,包括台湾的闽南人,常常以“来自唐山的河洛郎”自称,它所蕴含的,正是一种无法忘怀的寻根情结。
追根溯源,客家人“根在中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著名客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的研究表明,客家人从中原大规模南迁有五次,主要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连绵不断的中原战乱。第一次南迁,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引发中原人士南迁。第二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朝安史之乱,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南下迁入闽粤赣地区。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在金元南侵时期。尤其是元军大举南下,南宋灭亡,造成中原士族与百姓的逃难与人口流动。第四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客家有节之士抵抗清兵,后为躲避兵灾和迫害大举迁移。第五次南迁是在清代后期。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山多地少加之人口繁衍,遂向沿海地区和台湾迁徙,甚至远走海外。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事实上,早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执教于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就以被称为“客家人宣言”《丰湖杂记》[2](p50)一文,记载了客家人的源流、社会地位与族群特点:“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台湾的客家族群,多在康熙年间大量东渡入台。客家人讲的是属于中原语言的客家话,他们受到的是中原文化传统的熏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祖宗坑,不卖祖宗声”,成为客家人的家训和族群认同标志。清代著名的客籍诗人黄遵宪也留下客家人这样的祖根记忆:“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展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3](p10)
中原大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核心文化又溯源到河洛文化。上古时代被认为“中国之中”的河洛地区,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皆在山东。”所谓河洛,泛指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流域。“以今天的地域概念,‘河洛是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北迄邯郸以南,南接淮河之北,西达关中华阴,东至豫东平原,其主要区域,即今天的河南省全境,也即狭义的中原”[4](p45)。河洛文化作为一种辐射力、整合性很强的根文化,历史学家朱绍侯对此有着高度概括:“河洛文化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种文化的总合就是河洛文化。”[5]具体而言,河洛文化注重家庭制度,强调家齐而后治国;崇尚伦理道德,重视德治,君子忧道不忧贫;强调以民为本,提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遵循中庸之道,秉持王道精神,提倡世界大同。河洛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核心的、最有生命力和辐射力的源头文化。从地缘的角度看,中原南迁的客家人,正是以四海迁徙中对根文化的认同和传承,让河洛文化成为客家文化的底蕴。
作为族群代言人的客籍作家,当他提起笔来书写自己族群历史的时候,只要他是带着使命感和艺术良知,真实地面对客家人的生存史实;他就无法掠过客家文化传统背后巨大的民族文化母源,他就无法割舍走遍天涯海角、仍是炎黄子孙的生命血缘,他就无法忘却客家“根在中原”、心系乡土的传统依归。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中,就可看到那些迁徙台湾的客家拓荒者,常常称自己是“河洛郎”。《沧溟行》中的客家人,当他们面对日本殖民者入侵、被迫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时,悲愤之情油然而生。“他们不知从哪一段岁月起就懂得了这个字眼——命运。他们从老远老远的祖先年代,从住在中原的时候起,就懂得了这个东西的。洪水来了,这是命;干旱来了,这是天意;蝗虫来了,是注定的;胡人入侵,也不例外。他们失败过,也被打倒过,然而他们从未被消灭过,因为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民族”[6](p91)。李乔《寒夜》中,那些最初抗击入侵日军的唐景崧亲兵,就有许多高大健壮、武艺高强的被称作“河南勇”的士兵,来自河南、会说客家话,成为他们突出的特点。《梅村心曲》中生活在的铜锣乡郊后龙溪畔的老阿爸吴传仁,在后山种植许多梅树,后来索性将“芎蕉村”的村名改为“梅村”,“一方面表示我们不忘老祖宗所来的故乡——广东梅县……另一方面,是取自梅花不怕寒冷、不畏艰苦的特点,表示我们永远记住来台祖先开辟山林的辛苦,并且要多多发扬我们客家人朴实、坚强、爱国家的精神”[7](p416)。作品写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时,被日本殖民统治洗脑、有着亲日倾向的儿子阿柱竟然冒出一种“台独”思想。父亲吴传仁当即气愤地斥责阿柱是“忘本”,他说:“我们客家人是从广东来的,福佬是从福建来的,跟中国内地人有什么不一样?”[7](p346)事实上,很多客家人从来就自称身为“河洛人”,如一幅客家长联所云:“客系何来?本黄裔后胄,三代遗民,世居河洛,自晋初,战乱兵凶,衣冠南下,经唐灾,历宋劫,籍寄遐荒,筚路蓝缕创四业,溯渊源,千年称客实非客;家乡哪处?数远祖先贤,中原旧族,转徙粤闽,从宋末,居安业定,驻足梅州,复明播,继清迁,群分边郡,瓜瓞绵延遍五洲,同根抵,四海为家就是家。”[8](p119)在台湾,无论是从广东来的客家人,还是500年前寻根在福建、1300年前寻根到河南固始的闽南人,其祖根多在中原,正如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卷二十三《风俗志》前言所云:“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台湾客家小说中一再描写的“中原即根”的文化记忆,正是基于古老的河洛文化渊源而产生的有关故土与族根意识的艺术呈现。
二、耕读文明:客家庄生活的中原底蕴
从文化背景和生存状态上来看,从中原辗转南迁而来的台湾客家人,其乡土想象和生存景观与河洛大地遥远的农耕文化有着同构性。
河南地处中原,素有中华民族的“摇篮”和“发祥地”之称。受到黄河这条“母亲河”的哺育,位于黄河流域腹地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民族最早出现原始农业的地区。河洛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距今约8500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5000年的河南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都有粟类农作物和石制生产工具的出土,标志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雏形。至夏商周三代,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逐渐形成。从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夏代都城遗址中,黍、粟、大豆、小麦、稻等农作物的种植,也确证了《周礼·职方氏》郑玄注中的“五谷”即“黍、稷、菽、麦、稻”。河洛地区在夏商周三代还出现了学校,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掘有宗庙式大学遗址;殷商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出现“笔”“教”“学”“师”等字体;西周时的教育制度,已形成“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9](p162)的局面。故《孟子·滕文公上》有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0](p117)秦汉以后多尊奉“重农固本”的治国之道,民间百姓认同的是一种 “耕读传家”的生存方式。这种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传统,随着来自黄河流域的客家人的历史迁徙,成为台湾客家族群文化传统的土壤。客家人传统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是围绕着垦荒、种植这一生产过程来进行的;在这种生存历史中形成的客家文化,自然也打上了农耕文化的烙印。
台湾客家小说所呈现的浓厚的乡土色彩,客家庄、客家围屋等典型的客家生活环境,都离不开农耕文化的孕育。台湾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多聚集于偏僻的山乡,客家人所居住的围龙屋,就是相对封闭的客家庄民居结构。对内,它显示了客家人渴望和谐、团结的“圆”文化心态;对外,它象征着客家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抵抗力。在客家庄,“同族聚居是血缘性的团结,籍贯相同者的聚居,则是地缘性的团结。客家聚落则往往含有这两种性质”[11](p209)。它既构成农耕经济的生产组织,也体现客家宗亲家族关系的扭结,具有客家族群的生命共同体的意义。台湾的苗栗、桃园、新竹、杨梅、美浓、六堆、头份等地区,历来都是客家的聚集地。谢霜天的《梅村心曲》,在苗栗县铜锣乡的后龙溪畔展开叙述,那是从广东梅县来台的吴姓客家人开发的家园;钟肇政《沉沦》中的九座寮,是台湾北部典型的客家庄,见证了来自广东长乐的陆氏家族的创业史和抗争史;钟理和写六堆的《笠山农场》,吴锦发描绘美浓的《秋菊》;李乔《寒夜三部曲》发生在台湾的大湖庄、大湖郡、苗栗郡、新竹街、中坜郡、凤山、二林等地的故事,都是在农耕文化影响下的客家庄背景上来呈现的。
台湾客家小说表现的客家生存模式,与客家族群开发台湾的创业历史和农耕活动密切相关。客家人以农为本,多从事烟草、茶叶、水稻、番薯等农作物的种植,表现为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形态。在开疆辟土,与大自然的艰苦搏斗中,客家人不断迁徙,相对于原来的土著,多居住于荒山野岭、穷乡僻壤,为生存的打拼显得格外艰难。他们继承了农耕文化中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务实避虚、忠厚传家等传统美德,又在流离迁徙、开发建设中格外凸显了客家人百折不挠的“开山牛”形象和硬颈精神。
李乔的《寒夜三部曲》这部长卷,讲述的是客家人开发台湾岛的血泪生涯和悲壮情怀,让人体味到客家人用生命铸造的顽强不屈的族群性格。小说着重描写了来自大陆原乡的佃农彭阿强,率领全家七男五女,历尽千辛万险闯进苗栗的小山村蕃仔林,为垦荒拓田,舍身舍命地劳作,不惜用血汗生命向荒山老林夺取土地。正因如此,客家人有着投注了强烈情感的土地情结:“人,是土做的,所以人离不开泥土,爱泥土,依赖泥土,没有泥土就不能过活,人总是为了泥土拼命,将来人还不是都要回到泥土里去。”[12](p353)透过《台湾人三部曲》,钟肇政是以深沉的历史情怀,描述了台湾客家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从原乡广东长乐只身渡海来台的陆家始祖荣邦公23岁踏上台湾土地,靠打长工的多年积蓄买下九座寮这片荒地。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开垦种植,传到陆家第三代信海公手中,已变成美丽富饶的田园茶庄。那些诚朴的陆家子子孙孙们世代相传,他们的祖先是靠勤俭两个字起家的。及至《梅村心曲》,谢霜天写到的梅村,是原乡在广东嘉应州的吴氏祖先于乾隆年间来台后所开拓的。面对一次次的地震洪荒、天灾人祸,吴家后代开疆辟土、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小说还透过日常生活的呈现,将种菜、插秧、挑肥、捉虫、浇水、收谷、种甘薯、采花生,以及赶鸭、喂鸡、养猪的劳作场景,菜圃、果园、田间的农事活动,栩栩如生地融入台湾客家的乡土生存历史,它所延续的正是河洛文化中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内涵。
河洛文化中重视教育的传统,对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乡土人生意义深远。耕者有其田,学而优则仕,耕读人生、诗书传家为民间百姓所普遍认同,并特别影响到南迁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族群风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遂成为客家地区的流行语。“晴耕雨读”也是地处偏僻的客家人出人头地的奋斗途径。“客家人以耕读为本,家虽贫必亦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也”[2](p50)。客家人希望子弟出人头地,做“秀才郎”;客属地往往设有“学田”“学谷”,用以鼓励支持客家子弟求学;客家男子谋求读书、向外发展,每每家中有人及第,便在门前树立石旗杆为荣。客家人感念仓颉圣人创造了文字,认为敬惜字纸就是尊古圣先。为了不让有字的纸张掉在地上任人踩踏,他们传承传统汉人社会敬惜字纸的美德,收集这些纸张拿到字纸亭火化。早期的客家庄,都设有“敬字亭”,用来恭敬地处理纸灰。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美浓还专门为敬字而组成“圣迹会”,举办“恭迎圣迹”的祭奠。客家重视教育的文风,亦可从中窥见一斑。
走进台湾客家小说,晴耕雨读的生活描写比比皆是。
客家人的大家庭中,经常有德高望重的老者以耕读人生的楷模,影响后世子孙的生活模式和人格理念。《台湾人三部曲》中的信海老人,靠勤奋好学,自开书房,教育族中子弟。他视“晴耕雨读”为做人的最高境界,但也能从失败的科举人生中汲取教训,在世代变化中融入自己的理想,“文武双全,就是能耕能读,是最了不起的,他希望孙辈们个个都能够这样:是知书识礼的,却也不必热衷于仕途;是靠农耕为生的,但也不放弃钻研文学”[13](p43)来自河洛文化的精神濡染,让儒家的进取之道和仁爱之心,道家的无为之路和旷达悠然,都影响到客家族群不同的生活面向。信海老人的几个孙辈如纲昆、纲仑、纲嵩这些年轻人,都是一面读书一面从事茶园劳动的;而一旦时代发出召唤,需要客家子弟冲到保家卫国的前列,他们往往成为文武双全的斗士,陆氏后代悲壮的抗日出征即是明证。《梅村心曲》中的吴传仁老人,身为诗社社长,喜种梅思乡,靠耕读传家,重仁爱精神,成为梅村客家的一面精神旗帜。客家媳妇林素梅从中受到的影响,就是教育自己的孩子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人,有志气,知礼仪,肯上进,有出息,而不一定要做大官,赚大钱。她鼓励儿子阿彬选择农校,在勤奋朴实的土地劳作中创造生活。
晴耕雨读的生活场景,也生动地呈现出客家人爱乡爱土、创造生活的美趣。《梅村心曲》中的林素梅嫁到吴家,在繁忙的农事活动和家务劳作之中,每每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红瓦屋、白粉墙、黄篱笆的农家院落,是花圃中姹紫嫣红的兰草、紫藤、美人蕉以及后山种植的梅花,这让她发觉“吴家虽是耕种人家,却与一般农户不太相同,它除了有着朴实的气息外,还多了一份典雅的格调”[7](pp17-18)。“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客家民间流传甚广的歌谣《月光光》,也是在美妙的月夜意境中,传达一份客家耕读人生的期望。
向往耕读人生的客家人,在日据时代对汉文学习的坚守,所蕴含的意义往往超越生活方式的层面,彰显出一种“汉文不灭”的民族意识。在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高压政策的日子里,统治者强令台湾百姓讲日本“国语”,穿和服,改日本姓氏,妄图泯灭华夏民族的文化。 面对这一切,《梅村心曲》中的吴传仁老人为免汉学一脉从此断绝,他冒着风险,私下教授儿孙后生们学习汉文、写毛笔字、背诵“三字经”。在坚守汉学的同好面前,吴传仁悲愤地即席赋诗明志:“严寒闭户事丹铅,耿耿私心可对天。今日斯文沦丧尽,阿谁道统继薪传?”[7](p262)黄娟的《杨梅三部曲》也写到客家子弟江永发所直面的日据时代教育环境,是如此的针锋相对:一方面是公学校校长每天的朝会训词:“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大家要效忠天皇,做一个标准的日本国民”[14](p91);另一方面,则是客家林老先生私塾里的教诲:“汉文才是我们的文字,我们自己的文化。”“日本无理侵略中国,又迫使满清割地赔款,是可恶的帝国主义!”“我们的祖先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不是日本人,绝不能数典忘祖!”这让“江永发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他们一家都讲客家话,他们绝不是日本人”[14](pp90-91)。
由此可知,台湾客家人在传统生活中所坚守的,不仅仅是源自河洛文化底蕴的一种耕读生存方式,还蕴含河洛文化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教育功能;它构成客家族群文化中最稳定的精神资源,源源不断地滋养客家人的性格和志向,并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文化传统、人格精神的延续和继承。
三、民俗风尚:客家文化中的河洛遗风
风俗风尚是判别一个民族或民系的重要标准。台湾客家小说中屡屡出现的客家文化习俗,从立春、清明、端阳、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岁时节令,到生命占卜、风水预测的民间习俗;从相亲迎娶的婚嫁礼仪,到报丧、做七、洗骨改葬的丧葬习惯,这一切多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背景相关。李乔《寒夜三部曲》中程序繁多的客家入赘婚礼,彭小妍《断掌顺娘》写到的客家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船的民间风俗,庄华堂《吴老大和他的三个女人》展示出的魂幡哀乐中的丧礼仪式,还有张振岳《义民爷的金身》、冯辉岳《接妈祖》、黄秋芳《永远的,香格里拉》、庄华堂《土地公庙》写到的民间信仰,都是和土地连接在一起的传统风俗。不仅如此,透过笃信妈祖、观世音菩萨、天公神、土地公自然神、三山国守护神、关圣君财神、义民爷神灵等神灵敬拜,则可窥见源于河洛远古先民敬畏天地自然的多神信仰。客家人迁徙四方,特别注重通过家谱传续、祠堂文化,来连缀他们对中原祖地的寻根情怀。由此可知,客家文化习俗保留了古代中原农耕文化色彩,其中多有河洛文化的遗风。诸如学者丘恒兴所言:“在共同的心理素质方面,客家人继承了中原儒家文化,崇尚忠孝,重文崇教,追宗念祖等道德礼俗,世代相传。”[15](p21)
客家的民俗风尚渗透在客家生活的各个层面,最能体现客家文化特质的族群辨识标志,往往集中在客家话、客家族谱以及客家崇拜等方面。
(一)客家话
客家话作为客家人表达思想感情、人际往来的交际工具,它是汉语中的一个支系,属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在客家聚集地区世代相延。客家话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而深厚的客家文化记忆和生活信息,是凝聚与辨识客家族群的鲜明标志,一向为客家族群所看重,“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就成为客家人世代恪守的先祖遗训。“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代表着中原发达的汉文化,因而多会以中原汉民族共同语——河洛雅言为通行交际语”[16](p410)。黄遵宪《己亥杂诗》,也以诗歌的形式追溯了客家话的渊源:“筚路挑孤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存三代前。”[17](p289)
客家话发端于古汉语,与中原古音同一源头,是古汉语保存最完整的语言。尤其在语音方面,客家方言口音可以说是古代中原汉语的活化石。在词语方面,历史上的许多中原汉语的古词语,虽然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逐渐消亡,但在客家话中却依然保持生命力。以人称代词为例,可看出客家话与古汉语之间的渊源联系。
“我”,客家话第一人称代词,俗字写作“涯”或“亻厓”,与古汉语中的“吾”同义。“吾”,一是同本义,“吾,我自称也”(《说文》);如《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据王力先生考证拟音,古代汉语中的“我”字,即读ngai。这与客家话的音义完全相同,客家话因此被指称为“ngai话”。“吾”,亦为客家话第一人称所有格代词,意为“我的”,读作nga。据王力先生考证拟音,古汉语中的nga也做第一人称所有格代词,这与客家话的“吾”,意义相同。如《孟子》云:“我擅养吾浩然之气”,客家话亦有“我(涯)请吾叔来吃饭”可参证。
“汝”,客家话第二人称代词,读作“女”,与古汉语的“汝”或“女”的形音义完全相同。如《列子·汤问》:“吾与汝毕力平险。”客家话说:“汝做脉个?”(你干什么?)
“渠”:客家话第三人称代词。在古汉语和客家话中,“渠”均用来表示“他”“她”“它”。如(宋)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客家话说:“渠在哪?”这里同指第三人称代词。
客家话对中原古汉语痕迹的保留,也见诸许多字词。诸如:
古汉语 普通话 客家话
做甚么 干什么 做脉个
食毕 吃完了 食撇
日 太阳 日头
天光 天亮 天光
值 值得 抵得
客家话与河洛方言还有一些相同的词汇,诸如,“逢”曰“碰”,“茎”为“梗”,“束缚”为“绷紧”,“合算”为“划算”,“眼睛”为“目”,称“姐”为“姊”,称“兄”为“哥”,等等。从语言的缘起和发展来看,古汉语在黄河流域的孕育和流行,提供了客家话的母体;客家话与古汉语之间的联系,亦“方言足证中原韵”,溯源了古老的河洛文化是客家文化的源头。
台湾客家小说语言特色,最鲜明不过地体现了客家的生活本色。黄娟的《闽腔客调》,以海外同乡会的往来活动,来看客家话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那些已经不会说客家话的客家人的自卑感,深刻地透视了一个族群的失语悲哀。庄华堂《土地公庙》语言表达显示的客家风格,无疑来自客家乡土的生活孕育。且看客家老农面对禾田的情感描写: “阿坤伯凝住着满田绿禾,禾茎深深的插入水中,似乎可以感觉,一股原始的、强劲的生命力,正在土里滋长着,吸收黑土丰穰的养分,把禾身一寸寸的拉拔起来,这有如他们辛苦抚养孩子,一个一个的从襁褓中,一瞑一寸大,慢慢的饲大汉,古早人讲,一枝草一点露,道理就是这样。”[18](p26-27)从禾苗的培育联想到孩子的抚养,客家人的生命观尽在其中。
(二) 客家族谱
客家族谱、堂号、堂联代表了一种姓氏文化,姓氏文化与血缘、氏族相关,每一个姓氏发祥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子孙慎终追远的过程。姓氏文化是河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有研究者统计,当今120个大姓中,80%以上出自河洛文化圈。海内外客家大姓多由中原迁来,台湾与大陆的前十大姓氏比较,有诸多相同之处,如大陆的“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与台湾的“陈林黄张李,王吴刘蔡杨”之说。客家人追宗念祖,寻根溯源,重视源远流长的姓氏发祥、族谱家乘,常以祠堂建造怀念先人,带着族谱去流浪,对自己的来龙去脉和族群归属时刻铭记。客家人思乡心切,常常在家门上标明自己的故乡地名,成为“堂号”。在客家人那里,“名字代表个人,姓氏代表宗族,而堂号则是姓氏的延伸,代表着家族的历史和荣誉”[19](p91)。由姓氏而形成的台湾“郡望”“堂号”,都与秦汉时期的设置有关。客家人有名的郡望中,与河南有关的为数众多。在堂号基础上产生的堂联,上联点出姓氏、宗族的发祥地,下联则多为光耀祖德,或点出时代、地点、官爵等。
客家祖先何处来?从族谱、堂号、堂联上寻根问祖,可见发祥轨迹。
以原乡所在地命名的堂号、堂联,特别纪念祖先来自的地方。诸如:
郑氏,堂号荥阳。堂联:荥阳世泽,诗礼家声。
潘氏,堂号荥阳。堂联:瓜山世泽,花县家声。
陈氏,堂号颍川、汝南、敦睦。堂联:东山世泽,颍水家声。汝南世德,御史家声。柳溪源远,循铎声宏。
以彰显祖德而命名的堂号、堂联,重在弘扬一种精神。诸如:
杨氏,堂号弘农堂,关西堂。堂联:四知世泽,三相家声。杨姓祖先杨震是东汉时期弘农华阴人(今陕西华阴东),杨震任荆州刺史的时候,有地方官吏以“暮夜无知者”为由行贿,杨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由此而来的“四知世泽”,正是告诫后代,弘扬做官清廉的美德。
通过族谱、堂号、堂联,表现对祖宗先民的寻根意识,这种秉承了河洛文化追怀报本的传统的风俗习尚,在台湾客家小说中比比皆是。
李乔《寒夜三部曲》中的彭氏家族,《梅村心曲》中的吴氏家族,都是漂洋过海开发台湾的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牢记自己的祖先和原乡,族谱就成为最有力的维系。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中的陆氏家族,从广东长乐县只身渡海的来台祖荣邦公的开荒拓土,到儿子天贵公在九座寮盖起祖堂建起茶园,再到信河、信溪、信海三个孙子各立门户,“仁”字辈重孙多达11位,以及纲青、纲昆、纲仑、纲嵩等陆家第五代子孙的兴旺,陆氏族谱记载的世代繁衍和打拼故事,清晰地勾勒出陆姓人家的来龙去脉和开发九座寮穷乡僻壤的历史。
庄华堂《族谱》描写阿仁古家的厅堂,不仅有着“天水堂”的堂号,还有“天环栋宇文章旧,水绕华堂世第新”的对联。让村里老人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族谱的维护和修订。在他们看来,“祖谱前面是宗族源流简介,从来台祖泰源公,一条小扁船,渡过黑水沟,到新竹州落户以来,三百多年,十六代孙的历史,都清清楚楚的记在上头,接下来是三房宗亲系表,以后则是各家族介绍”[20](p628)。有了族谱,就延续了客家族群的文化记忆。吴锦发《祠堂》中的亁兴伯,生活在美浓溪畔的客家庄,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全力呵护一座祠堂。这座有着“渤海堂”堂号的祠堂,刻着“渤海家声远、延陵世泽长”对联,它所维系的是客家后人对祖先遥远的记忆,是一个家族跋山涉水、开荒拓土的奋斗史,无疑成为族群历史的一种见证。
(三)客家崇拜
民俗文化构成河洛文化的重要内容,河洛文化的中原民俗特征保留了农耕文化色彩,岁时节令,祭祀敬神,人生礼仪,都与农事相关。客家文化认同和风俗习惯,深受河洛文化影响。客家人与中原汉族一样,都信奉多神崇拜。三步一宫,五步一庙,“举头三尺有神明”,各路神灵都贴近生活,而非一味远居深山老林;客家人有神必信,多多益善。他们在笃信妈祖、观世音菩萨、天公神等主神的同时,还敬拜土地公自然神、三山国守护神、关圣君财神、义民爷神灵等。“义民爷”是客家人普遍敬奉的神明,同姓者集中祭拜时不一定要有真正直系的血缘关系,只认同大陆的“唐山祖”。透过台湾客家文学表现出来的“多神主义”宗教信仰,可以窥见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原宗教文化濡染。《梅村心曲》写到乡村的收获季节,客家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到田头拜伯公,做“喜功”,感谢土地公给农人带来的好收成。客家人对土地公很亲近,称它为“伯公”,感谢并敬拜保佑了庄稼丰收的土地神。在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从专门修建的伯公庙,到老树桩象征的伯公,就像客家人离不开土地,客家人的生活也和土地公的保佑联系在一起,因而有了“田头田尾土地公”的民谚。不仅如此,土地公在黄秋芳的《永远的,香格里拉》中,还象征着给人带来好运和安慰的祝福神,返乡的可嫁女儿安黛躲过车祸,要焚香感谢土地公;路遇新知结交朋友,要感念土地公;沐浴故乡的阳光和空气,同样感谢土地公的庇佑。土地公在这里,早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有着神力和福运的神,它渗透在客家人的生活,成为一种让人感念、珍惜和虔敬的精神寄托。
总之,客家在迁徙、定居、打拼中的生存境遇,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族群文化;而客家根在中原的史实,又使它走遍天涯海角,都不能不带有河洛大地的根文化印迹,这正是同根同源、同宗同族的华夏民族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
[参 考 文 献]
[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谭元亨客家经典读本[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送女弟[C]//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4]郑淑真,等根在河洛[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5]朱绍侯.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J].文史知识,1994(3)
[6]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沧溟行 [M]北京:广播出版社,1983
[7]谢霜天梅村心曲[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
[8]廖开顺论河洛文化的根性特征及客家文化的根性精[C]//陈义初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9]曾亦礼记导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10]徐洪兴孟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1]雨青客家人寻根[M]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85
[12]李乔寒夜三部曲·寒夜[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
[13]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沉沦[M]北京:广播出版社,1983
[14]黄娟杨梅三部曲·历史的脚印[M]台北:前卫出版社,2001
[15]丘恒兴客家人与客家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6]周文顺,徐宁生河洛文化[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1998
[1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己亥杂诗[C]//人境庐诗草笺注钱仲联笺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8]庄华堂土地公庙[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19]刘佐泉客家“根在河洛”考[C]//洛阳市历史学会河洛文化论丛:第2辑[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
[20]庄华堂族谱[C]//钟肇政客家台湾文学选: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1997
(作者系郑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