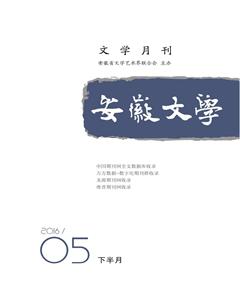“真实性”的思考与突变
黄晶
摘 要:在当代文学作家群中,王安忆不仅作品丰厚、富有深度而且艺术自变力强、创作变化大。她从不满足于自我的重复,她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不断生长的状态,她在文学上的这种进步和成就,是与她的写作意识分不开的。她对创作的反思和对自我的剖析,展现出了她与小说同步共生、相辅相成的姿态。本文选取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以小说的“真实性”为切入点,阐释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其创作意识的关联和互动,叙述的突破和精神渴求的焦虑。
关键词:王安忆 写作意识 真实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3年贺州学院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13ZXSK10)
无论是八十年代初的“雯雯系列”,还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刘庄》、《小鲍庄》、“三恋”,王安忆所讲的乡村故事都在同一个大背景下发生,那就是她的“知青”经历的背景——“大刘庄”、“小鲍庄”、“小岗上”等。①也就是与其自传经历相对应和契合的实际生存场景empirical setting:它们既是实际的地理位置又是小说标题的命名。对于当时的王安忆而言,这样的故事背景是需要的,换句话说,这种背景意味着小说“真实性”的一个出发点,王安忆不仅肯定了它,而且企图在它所提供的逻辑下展开叙事。也就是所有虚构的故事都必须留有一个真实世界的印记,由外部世界的真实赋予其小说文本的“可信性”。
而九十年代以来的王安忆,却对这个出发点有所警觉。九十年代以来的王安忆小说合作有一个非常值得注目的现象,那就是她非常集中地推出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小说观念,比如《小说的定义》、《作家的处女作》、《小说的情节和语言》等等。她宣称:“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已经很成熟了。”②,自己正从事着“世界观重建的工作”③,此时的王安忆比任何时候都乐于推销自己的小说理论。她常用一些特别的词来解释小说创作:抽象、虚构、逻辑、神界……
在这些被频繁使用的描述小说的术语里,透露着王安忆的焦急。她急于把自己的小说和现实世界分开,把小说和纪实文学、电影等她所认为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分开,她一再地重申,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并非小说的义务:“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以为真实,是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在文学走过了一个相当长久的虚伪的道路以后,我们非常重视真实,真实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花了许多力气和代价去争取到小说的真实,可今天我感到非常困惑的是,真实是否真的是小说的理想。”④王安忆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想用一种否定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小说是什么。现实生活的真实并非是小说的真实,现实生活里的逻辑也并不是小说的逻辑。
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对现实生活“真实性”的背向的企图,《叔叔的故事》诞生了。在1989年搁笔一年之后,1990年,王安忆发表了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较之以前的小说,王安忆这篇小说的叙事方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评论家把它命名为“元小说”或者是“后设性小说”。但是,这样的叙事方式在九十年代的文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相对于苏童、余华等先锋小说家,王安忆是不是有些后知后觉了?对于王安忆而言,一切才刚开始,她才刚从她的“出发点”那调过头来、刚尝到“虚构”的甜头,王安忆这样表述过她的想法:“我现在对所谓个人自传和纪实的东西越来越缺乏信任感,我竭力追求某种形式的东西,类的东西,超出经验的东西,直接地说,就是虚构和抽象的东西。”⑤正如她本人给自己小说诠释的那样,显在的,在《叔叔的故事》中,现实与小说构造的那种紧密联系松弛了。王安忆也不再重视“真实地名”在小说文本中的缔造,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印证的关系。甚至她也无意于虚构出一个地名,像马原虚构出来的西藏的某个地方。《叔叔的故事》也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王安忆写作的“四不要原则”的实践。
沿着《叔叔的故事》这条路,王安忆又走了一段,走到了九十年代初的几部中长篇小说,《乌托邦诗篇》、《歌星日本来》、《伤心太平洋》等等。在这几部小说里,她完全抛弃了对世俗生活画卷的精细描摹,也放弃了传统小说的完整的故事形态,故事都是零碎松散的。此时的她更是不屑于简单地重现个人化的生活经验,而是把故事的叙事置换成对经验和一些历史事件的理性分析和议论。连篇累犊的议论、分析远远超出了故事本身的含义,大量充斥在这些文本中的抽象的分析和议论当然也是王安忆的个人生活感悟,但是它们不再以“故事”的形式显现,而是变成了讲故事的方法。叙事人的分析和议论显然替代了客观情节的推演。正如李洁非所说:
假借《纪实和虚构》、《伤心太平洋》,小说家王安忆所欲建设的那个命题就是:小说叙事能否摆脱一切参照系而将某种独立的“真实”陈述出来。这个命题从理论上讲,其含义则是:既然小说本质众所周知在于“虚构”,那么,这种“虚构”本质应该可以达到它自身的纯度,亦即无须依附别的前提而单独地具有意义。⑥
小说无须外部世界的“认可”来保有其真实性,叙述是去“虚构”某件事情,而非“证明”某件事情。这几部小说都可以看成是王安忆“小说的逻辑力量”、“虚构”的深刻表达。在此可以发现,她特意规避客观现实的逻辑在小说中的呈现,而强调一种不同于客观现实的小说世界的逻辑,强调虚构本身的力量。她要摒弃任何“前提”,远离“现实生活”这个地面进行精神飞升和超越,要用庞大而严密的逻辑推动力去建立一个空中楼阁。
然而,这样的路走到了《纪实和虚构》,走到了一个极致,也走到了尽头。⑦这部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处处体现着王安忆的独具匠心。比如,由“是哪个家的孩子到底怎么样成长的?”问题,如何延伸出小说的纵横结构布局;小说的两部分——“我”的成长史和“我”寻找家族起源,两部分如何交叉、何时衔接?这些都依靠缜密的逻辑来推动,王安忆从始到终都让叙述人进进出出,不仅要展示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要表明这个虚构的世界是如何诞生的。可以说,王安忆在这部小说的“虚构”层面煞费苦心。然而,正是这部她耗尽心智创作的、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评的长篇,却也正如郜元宝的质疑:“我们这个时代的确需要培植健全的理性,但是这种沉重的文化使命最好不要首先落到像王安忆这样的作家身上。有时候,他们倒是更应该从统治一切的理性权威中拯救出人们内心深处那份未死的灵气。”⑧
乍看郜元宝的批评有点不着边际,何为“理性”?又何为“灵气”?其实不然,郜元宝所谈之“理性”与王安忆所谈之“理性”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王安忆曾为长篇小说做过这样的注解:“一部长篇必须是一部哲学。长篇总体上讲应该是理性的,不能靠感觉去完成一部长篇小说。”⑨ “写长篇需要有一个井然有序的过程,这个过程必须依靠逻辑来推动。”⑨王安忆所提到的“理性”,从叙事形态上讲,也就是“逻辑”与“推论”。“理性”、“逻辑”,在王安忆这,有着共通性,它们都被统摄于“虚构”之下。郜元宝的质疑其实就是对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过于强调“逻辑”的质疑。因为小说不是数学公式,它所需要的、所依赖的不仅仅是“推论”、“演绎”,它蕴藏着人类巨大而丰富的精神秘密。
此时,越来越浓重的“理性”痕迹破坏了小说的感性表达,过于强调小说是“技术”和小说的“虚构”,也损坏了小说的精神性显现。王安忆刚刚放开手脚“大胆虚构”的时候,却又发现了重重阻挠。她说:我们都是血肉之躯,无术分身,我们只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占据一个位置,拥有两种现实谈何容易,我们是以消化一种现实为代价来创造另一种现实。有时候,我有一种将自己掏空的感觉,我在一种现实中培养积蓄的情感浇铸了这一种现实,在那一种现实里,我便空空荡荡。⑩
摒弃“现实生活”这个地面建立的空中楼阁有些摇摇欲坠了,尽管,王安忆在小说的物质逻辑层面能够层层推进,在叙述上变得灵活多样、游刃有余,语言也绵密、老道得多了,但是这些与小说的严密宏伟的思想不见得就是互为表里的。“小说家王安忆所欲建设的那个命题”是树立起来了,却也在此,在小说的“虚构”层面,她几乎把自己给掏空了。(在“雯雯系列”小说那,她把个人经验掏空了)“元小说”、“后设小说”等等都尝试过了,小说怎么再往前走?
深爱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厌恶重复自我的作家王安忆,似乎早就有了警觉,有关小说创作的思考不会戛然而止,小说创作也不会停滞不前。在九十年代中期写了《纪实和虚构》、《长恨歌》等上海故事的王安忆,再一次转身,重新注视她插队的那片辽阔的“淮北平原”。 从1997年的《蚌埠》开始,她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她的知青生活的短篇小说如《青年突击队》、《招工》、《小邵》、《王汉芳》,以及《文工团》、《姐妹们》、《隐居的时代》等中篇小说。这些小说的地名和叙事细节,却又重刻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印记——小鲍庄、大刘庄、小岗上。王安忆不是以她的小说理念否定了现实生活的真实等于小说的真实,现实生活里的逻辑等于小说里的逻辑吗?对于王安忆这样的作家,在看似回归的道路上,她似乎又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又展开了新的小说命题和理解,这样勇于探索的精神,充满了挑战与变化,成为王安式写作最为醒目的标志。
注释
① 王安忆.关于小鲍庄的对话之王安忆致陈村》[J].上海文学,1985(9):92.
② 陈思和,王安忆,等.王安忆:轻浮时代会有严肃的话题吗?[A]//理解90年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48.
③ 王安忆.近日创作谈[A[//乘火车旅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38.
④ 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文汇出版社,2003:6.
⑤ 陈思和,王安忆,郜元宝.当代文学创作中的“轻”与“重”——文学对话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3(5):30.
⑥ 李洁非.王安忆的新神话——一个理论探讨》[J].当代作家评论,1993(5):27.
⑦ 王安忆.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A]//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245.
⑧ 郜元宝.应该保留更多的灵性—简评(纪实和虚构)[A]//拯救大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156.
⑨ 王安忆,等.当代文学中的“轻”与“重”[J].当代作家评论,1993(5):38.
⑩ 王安忆.关于<纪实与虚构>的对话[A]//乘火车去旅行[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