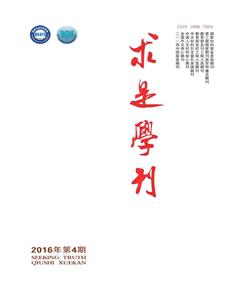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摘 要:《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晚明江南士风;文人生活;侨易学
作者简介:孙超,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政法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明清近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24-08
《金瓶梅词话》甫一面世,就因其“云霞满纸”且“寄意时俗”的“情色叙事”[1](袁宏道:《董思白》, P227)而众说纷纭,深陷重重疑云阵中。不过,据现有文献观之,自秘密抄本至公开版刻的传播初期,它与晚明江南文人的关系便深密而确凿。前人于此多有瞩目,然或用考据之方法探究作者为谁氏、版本孰先后,从而捎带透露晚明江南士风的一二消息,不免流于碎片化;或运文学之想象敷衍流传之掌故、民间之旧闻,因之传播展示已有“金学”研究的普通常识,于是流于表面化。面对这一现状,我们不妨引入叶隽倡导之“侨易学”的观念来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新说是在李石曾发明“侨学”概念的基础上,参以《易经》丰富的易变思想,提出的一个用于研讨文化及文学“变创”与“渐常”现象的理论观念。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前者强调空间维度的整合,后者关注时间维度的演进,其中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之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2](序,P5)。当然,诚如叶隽所说,他只是对“侨易学”学理做了初步梳理,因而希望学者们在运用这一观念方法时务必针对每一项具体的研究各取所需,调整增益,灵活处置,以回答待解决之问题。本文即秉承此旨,在具体研讨中既借鉴又生发,拟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第一,《金瓶梅词话》之创作是晚明典型的侨易事件;第二,抄刻《金瓶梅词话》乃是晚明江南文人满足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第三,江南文人在晚明形成的求“通”士风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进而指出现当代的“金学”热实导源于《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正在走向近代化的精神密码。
《金瓶梅词话》之创作是晚明典型的侨易事件。“侨易”,对人而言指的是由于身体迁移或精神漫游而导致思想观念的质变,而对文学创作来说则主要指通过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改头换面、移花接木与借尸还魂等改造已有文本的方法创生出新的作品。作为一部杂取兼容的小说,《金瓶梅词话》很明显是因“侨”而致“易”的产物。
首先,《金瓶梅词话》对《水浒传》中的“武松杀嫂”故事进行移植嫁接,从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始至第八十七回“武都头杀嫂祭兄”止来改造这个故事,以完成全书主体部分的叙事。当然,作者旨在营构一个完全异趣的崭新文本,它讲的可不是抱忠守义的传奇英雄,而是沾满铜臭的世情男女。这就发生了因“侨”而致“易”的质变。《金瓶梅词话》从来不被看作《水浒传》的续书、补作,甚至连“改写”这一非常显在的事实也常为一般读者所忽略,而只认它是一部卓然独立的伟大杰作。其秘密正在于它“侨”有手段,“易”有新质,这样的一种戏仿改写,或曰借(旧)文生(新)事,就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了。对于《金瓶梅词话》侨用《水浒传》,早在其行世之初即为袁中道等揭破,此后相关研究代不乏人,其中韩南、黄霖、周钧韬诸先生所做的文本比对及由此生发之观点可为代表。1另外,诸如商伟在前人基础上拈出之人物的拼合(《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潘巧云合成《金瓶梅词话》中的潘金莲),人名的借用(一丈青——来昭之妻),拆碎重组《水浒传》中的人物与语言,性战对《水浒传》中战斗的戏仿,李瓶儿、吴月娘在两部书中的前世今生及其他对《水浒传》的征引、挪用或误用等,都体现了《金瓶梅词话》作者的“侨”之巧技。2《金瓶梅词话》正是凭此而生“易”——交易、变易。“交易是很重要的一点,必须有交互相关的一面,方才有易变的可能。故此,侨易之立名,也包括交感的意思在内。”[2](P5)《金瓶梅词话》是如何与《水浒传》交感而生变易的呢?这实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试对几个关键点略作分析。第一,嫁接的母本主要是《水浒传》中说风情、杀淫妇的那几回。相对于整体在说好汉的异质文本《水浒传》,这几回与《金瓶梅词话》恰是同质的,故能成为二者交感的接口。第二,《金瓶梅词话》头十回对《水浒传》符合人情物理的贴身抄改使交感加深,进而形成质变性的文本错觉。《水浒传》中说武松割下西门庆的头来原是假的,武二当时打死的分明是来报信的李外传,只因当时此事轰动全县,众说纷纭,《水浒传》的作者才听信了以讹传讹的假消息。不信,有我十回笔墨、清河县关联此事的大小人物为证。就这样,读者一步步被引入《金瓶梅词话》精心营构的艺术幻境,不禁信假为真了。3这一交感变易过程在词话本中体现得非常清晰,第一回起首写的是武松打虎,至第十回武松发配才让《金瓶梅》世界的主要人物一一登场。相较而言,崇祯本第一回就写热结十兄弟,这恰恰证明了崇祯本侨易自词话本,因为它不能完全理解原著如此开头的深刻用意。第三,依“二元三维一大道侨易”原理[2](P9-17),《金瓶梅词话》创生出的新境界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其嫁接的母本《水浒传》,特别是在“通大道”上不仅让晚明人有“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袁宏道:《董思白》, P227)的赞叹,亦可让有灵之人类同体共悟。这也正是《金瓶梅词话》称“奇书”、列“名著”,能在世界文坛上竞短长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它开辟的新境界是说不尽的。在这里,我单从文本叙事这一微观层面略作阐发。《水浒传》文本—《金瓶梅词话》文本分别是发生侨易的两元,在二者交感变易后,侨易主体《金瓶梅词话》就在文本叙事上形成了独特的多维叙事特征。例如,当读到《金瓶梅词话》中英雄武松赖以成名的打虎事件成了天下第一帮闲应伯爵口中的八卦时,读者头脑中一般至少会出现三种叙事:应伯爵口中的、《金瓶梅词话》直接写的、《水浒传》上的,甚至还有第四种就是读者自己的。读《金瓶梅词话》时,出现这样的情况所在多是,非常直观地体现出它的侨易之功。
其次,《金瓶梅词话》创作上的侨易还体现在它成功地改造了已有大量的其他文本,统摄为己用并生成新文本的血肉。《金瓶梅词话》不仅侨自《水浒传》,还侨自《西厢记》、话本小说、流行歌曲、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字作品,这一点贤哲时有披露。侨用韩南的话说,其“引用原作的实际数字和它们包罗之广令人惊讶”[3](《〈金瓶梅〉探源》,P224)。不过,迄今还有不少学者据此而称其为“抄书”,高一点的说法称其为“集撰”,而并未真正明了《金瓶梅词话》建基其上的,在言说方式、内容择取、写人叙事与精神旨趣等诸多方面的创新。假如以“抄书”视之则只彰其“侨”,弱化其“易”;即使目之为“集撰”,也有让人误会作者是“文抄公”的倾向。只有将《金瓶梅词话》放置在侨易视域之中,才能观其作为“通大道”之文艺杰构的独特个性。将来源不同、题材各异、文体多样的文字材料巧妙织进自己的满纸云霞之中绝非易事,胜此任者绝对是灵心慧智、别具手眼之文士。《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有时对旧材料略加损益(如对《水浒传》),有时是对旧材料的仿写戏拟(如对《三国志演义》、诸种话本小说),有时是将已有诗词、戏曲、宣卷、笑话、戏谑语等镶嵌其上,有时摘抄模仿其他文本中的性描写、书信、奏折、游戏等文字,有时直接征引流行定型的曲子、俗语、口头语、歇后语、相面术语等等;有时将旧材料用在一处,有时又打散重组,有时只侨取一次,有时又反复侨用。它们的作用是要么服务于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文化;要么旨在形成似真效果,构筑艺术幻境;要么以喜闻乐见的话语样态来吸引读者。可以说,《金瓶梅词话》对于“侨”之对象的选择,“交感”过程的讲究,“易”之结果贴合新文本主旨的考量都别具匠心,相关研究已从不同层面加以论析,并举出很多实例,此处不赘。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以侨易之眼来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与早期抄刻,可助我们早日冲出旧有新设的重重疑云阵。当然,有些谜团也许是永远解不开的,我们“要知其限止,知其不可而展开自己的求知之路,这才是‘极高明而道中庸”[2](P17)。比如,据现有条件来确指《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谁就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但研讨《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包括最初的文本生成、传播)与江南士风及文人生活的关系便不仅可行,且颇具实际意义。
最早拥有《金瓶梅词话》全书抄本的是王世贞与徐阶(刘承禧藏本抄录此本)。二人一为文坛领袖,一为当朝首辅,却与一直被目为“淫书”的《金瓶梅》有发端之关系,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吊诡。由于王世贞家太仓,徐阶家松江,最早传出抄本的董其昌家亦在松江,而与《金瓶梅词话》早期刊刻大有关系的冯梦龙、沈德符居苏州,名声极大又极力追捧《金瓶梅词话》的袁宏道当时正在做吴县的县令。有据可查的第一批接触《金瓶梅词话》的文人还有袁中道、李日华、王宇泰、王稚登、谢肇淛、邱志充、屠本畯、文在兹等人。其中邱志充是山东诸城人,文在兹为关西人,其他都可算作江南文人。而邱志充与文在兹均与江南文人圈有不少互动。因此,将目光聚焦于晚明的江南文人生活,也许能建构起侨易生成这样一部专写“房中事”的世情小说的真实历史场域。
从谈到《金瓶梅词话》的最早一批文献来看,这部“奇书”最初的抄刻传播应该是为了满足晚明江南文人自身的生活需要。晚明的江南经济发达、人文鼎盛,是为温柔富贵之乡。这里的文人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但同时也耽于世俗享乐,由此对立辩证之二元产生出多维的文人生活。较之前代和其他地域,晚明江南文人生活中最有特色的内容恐怕要算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了。这两组四者在《金瓶梅词话》的纸上世界与晚明江南文人的现实生活中侨易互动,留下了不少正确回答“金学”难题的宝贵线索。
先说抄书—刻书。由于晚明江南地区集中了全国最主要的私人藏书家和私家藏书,因而不仅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同时也拥有不少图书领域的专家和众多的书籍爱好者。众所周知,南京、苏州、杭州等晚明出版印刷的中心均处江南区域。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中,再加上科举鼎盛的向上仕进与交易繁荣的图书流通,晚明江南文人的生活里抄书—刻书就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的抄书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满足自身身心需要,一为满足市场商业需要。《金瓶梅词话》的传抄,如董其昌、袁氏兄弟等人主要属于前者。袁宏道觉得《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袁宏道:《董思白》, P227),《七发》可以通过铺张扬厉地描写声色犬马的奢靡生活使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袁宏道喜爱《金瓶梅》显然因为它有使病魔退却的更强功能。通过袁氏兄弟与董其昌关于《金瓶梅》的交流来看,当时文人谈论和抄阅的图书中小说已成热门,秘本最受追捧,原因就在于这类书籍能大大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常导人游于他境界”[4](饮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P42)。《金瓶梅词话》在刊刻之前秘密传抄了二十年,足见文人们的好奇心之盛。这些传抄者一方面被《金瓶梅词话》奇妙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魅力所吸引,满足自己娱目快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乏商业之目的。据载,当时的藏书家兼刻书家毛晋就曾不惜高价买书,贴榜文于门上曰:“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5](P168)《金瓶梅词话》的传抄者当然也懂得抄本的商业价值。他们大多是藏书家,王世贞设“小酉馆”藏书三万卷,另有“藏经阁”专藏释道经典,“尔雅楼”专藏宋版书,逾三千卷 [5](P168);谢肇淛、王宇泰也都是著名的藏书家,且都以抄本闻名图书出版界1。谢肇淛、王宇泰还兼营刻书业,他们积极去搜寻抄录《金瓶梅词话》全本当也有满足市场需要的商业企图。屠本畯曾说:“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两帙”[1](屠本畯:《山林经济籍》,P231),这便透露了《金瓶梅词话》作为商品的信息。沈德符记录的《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也鲜明地反映了文化市场欢迎此书尽快行世。热衷通俗文学出版的冯梦龙“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吴地官员马仲良“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虽然沈德符没答应,但“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P230)这一结果恰恰证明,出版市场在《金瓶梅词话》是否刊刻面世的问题上拥有十分巨大的力量。再回到《金瓶梅词话》侨易式创作本身——它如此依赖各种图书及印刷材料,我们不难推断那些拥有大量藏书(或可接触到这些藏书)、醉心于抄书—刻书生活的晚明江南文人很可能就是这部奇书的作者,至少是其最终文本生成的重要参与者。
对于晚明江南文人的嗜酒—好色,作为此地豪奢民风、放荡习尚的地域时代特征,历史学、社会学及文学史都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我将围绕《金瓶梅》事件,以侨易之眼略观之。《金瓶梅词话》写了一个酒色财气的世界,这与当时文本外的现实世界是同质的。“酒是色媒人”,其侧重在色;“财大气粗”,则偏重于财;《金瓶梅》重点写的就是“财”、“色”,不可须臾相离的“财色”。这正与晚明江南逐步世俗化的文人对于“财色”的观念一致。上文已谈及《金瓶梅词话》传抄过程中透露的商业信息,下面重点说“色”。在晚明文人的生活里长期作为文人习尚的“诗酒风流”已经侨易为“嗜酒好色”,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言行上,还体现在观念中,并很快投影在文艺世界里——《金瓶梅词话》正是这种侨易的一个典型。像《金瓶梅词话》那样大张旗鼓,精雕细绘,以“房中事”为叙事中心的文学作品此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它正是晚明士人耽于世俗享乐的注脚。略举几例,《金瓶梅词话》传抄的始作俑者董其昌,据《骨董琐记·董思白为人》载:“董思白居乡豪横,为乡人火其居。……思白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曾篡夺诸生陆绍芳佃户女绿英为妾。……白龙潭东北隅建一阁,名曰护珠,时挟侍姬登焉。……施愚山言思白年八十五,临殁索妇人红衫绛襦为服,乃绝。”[6](P139-140)这一为人在其终生密友大名士陈继儒写的《祭董宗伯文》中亦可见一斑,他说:“古之遗命,或分卖香履于铜雀,或垂戒木石于平泉。为达者姗笑,为识者痛怜,而兄不然。”[7](P167)这恰恰说明董其昌生前拥有秀美的园林与成群的姬妾。重要的作者候选人屠隆,其放浪淫纵非常有名,他常常因宣淫而苦恼,最终竟死于花柳病。上面提到的其他抄刻者与候选作者往往也有“贪酒好色”的记录。另一方面,据仅有的文献,我们亦能看到《金瓶梅》在江南文人圈的酒场与欢场上还起着佐味之用。比如袁宏道将其与《水浒传》一起称为觞政中的逸典,认为“不熟此典者,保面甕肠,非饮徒也”[1](袁宏道:《觞政》,P227-228)。当他向谢肇淛索还《金瓶梅》时,直言曰:“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攸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1](袁宏道:《与谢在杭》,P228)从中足见其借《金瓶梅》及时行乐的意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曾记录下《金瓶梅》剧曲在文人饮酒作乐中助兴的场面:“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剧,使人绝倒。”[1](张岱:《陶庵梦忆》,P232)
上述这种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侨易互动给我们提供了辨别《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孰先孰后的一个思考路径。经王阳明“心学”及其左派的理论倡导与唐伯虎、李贽、汤显祖、屠隆等人的名流示范,万历时期的文人较之其后文人在“色空”观念上有着微妙之异,他们更重“色”之一端:沉迷于食色之中而难于自拔。至明亡之际,“空”之观念才上升起来。这一观念上的侨易比较微细地呈现在《金瓶梅》时距不远,但有先有后的两个本子上。词话本的叙事中心是“情色”,这与万历间的文人生活与士风观念是一致的。词话本在第一回中就拈出一个“虎中美女”的意象来解题:
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衍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8](第一回,P3)
这“虎中美女”喻指情色淫纵乃是食人虎狼之变相,可惜当事人耽于此乐而至死不能觉悟。后文细针密线织成一团锦绣,虽情节复杂,主旨多重,然皆以“情色”为关节、为重心。[9]至末一回以回前诗为标志重申这一题旨:
人生切莫恃英雄,术业粗精自不同。猛虎尚然遭恶兽,毒蛇犹自怕蜈蚣。七擒孟获奇诸葛,两困云长羡吕蒙。珍重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8](第一百回,P1361)
这显然与第一回为人须“持盈慎满”的警示相呼应,凸显其道德教化意图,正如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愚,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1](P1)崇祯本则侧重于“空”之一端:
这财色两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高堂广厦,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只有《金刚经》上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10](P3)
这一解题说得分明,崇祯本乃是以“梦幻泡影”之“空”笼罩全书,这与后来《红楼梦》中《好了歌》的解题旨趣相近。过去我们不大注意从“虎中美女”到“梦幻泡影”这一主旨意象的细微变化,今以侨易之眼观之,由《金瓶梅》词话本到崇祯本、张评本,再影响到《红楼梦》的这一侨易演进之迹甚明。
江南文人在晚明形成的迥异士风是上述《金瓶梅词话》侨易现象生成的深层原因。中国古代文人一般都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处世准则,而时至晚明,江南地区的文人在此人文鼎盛、工商发达、温柔富贵之乡终于突破“穷”—“达”之二元框范,形成了“通”的崭新士风。这一士风的远源乃是苏轼之“旷达”,终身沉浮官场而能随缘自适,并以出世之心来行入世之事;近源则是唐寅之“疏离”,疏离官场,以“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11](《言志》,P126)的姿态进入初步形成的江南文化市场。王世贞、屠隆、董其昌、陈继儒、王稚登等是形成晚明江南士风的代表人物。他们或官或隐,但整体上都力求一“通”字,像王世贞、屠隆、董其昌等人意在“通仕”——不离官场而能随缘自适,而陈继儒、王稚登辈则心寄“通隐”——不入官场而能万事俱足。他们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12](《答邓石阳》,P10),“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13](《笃义》,P328),“舍欲无道,道即欲,欲即道”[14](《合道章第四》,P6)等高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时代启蒙思潮激荡下,将其落实为求“通”的士风——在世俗性物质生活与艺术性精神生活上保持一种自适的状态。
晚明江南文人这种求“通”的士风首先表现为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为官做宦是古代文人普遍的人生追求,而晚明的江南文人对此却多持一种非常洒脱的态度。在现实中,虽然他们首选的人生道路还是科举成功,但无论“仕”、“隐”,他们普遍怀有一种自适融通的心态。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看到了晚明科举制度的腐朽不堪——八股取士严重束缚了真正人才的脱颖而出,其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配套严密管控着人性人欲的正常表达。面对这样的境况,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主动放弃仕进,如对晚明江南文化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陈继儒、王稚登等就选择以“隐”之身份来获取生活的自由,所谓“无官一身轻”。特别是陈继儒,未届而立,便弃青襟,堪为典型,其在《告衣巾呈》中写道:“窃惟住世出世,喧寂各别,禄养志养,潜见则同。老亲年望七旬,能甘晚节;而某齿将三十,已厌尘氛。生序如流,功名何物?揣摩一世,真拈对镜之空花;收拾半生,肯作出山之小草。”[15](P183)可见,陈继儒看到了科举功名对人性自然的束缚及其虚假性,并不排斥多姿多彩的世俗生活与价值判断。这种求“通”而偏于逍遥正是晚明江南文人的普遍追求,身在官场的文人也是如此。例如屠隆,他写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就被侨入《金瓶梅词话》而变成应伯爵口中水秀才的作品:
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尊前。此番非是吾情薄,白发临期太不堪。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维岁在大比之期,时到揭晓之候。诉我心事,告汝头巾:为你青云利器望荣身,谁知今日白发盈头恋故人。嗟乎! 忆我初戴头巾,青青子襟;承汝枉顾,昂昂气忻。既不许我少年早发,又不许我久屈待伸。上无公卿大夫之职,下非农工商贾之民。年年居白屋,日日走黉门。宗师案临,胆怯心惊;上司迎接,东走西奔。思量为你,一世惊惊吓吓,受了若干辛苦,一年四季零零碎碎被人赖了多少束脩银。告状助贫,分谷五斗,祭下领支肉半斤。官府见了,不觉怒嗔;皂快通称,尽道广文。东京路上陪人几次,两斋学霸唯吾独尊。你看我两只皂靴穿到底,一领蓝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历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数载犹怀霄汉心。嗟夫哀哉! 哀此头巾。看他形状,其实可矜:后直前横,你是何物?七穿八洞,真是祸根。呜呼! 冲霄鸟兮未垂翅,化龙鱼兮已失鳞。岂不闻久不飞兮一飞登云,久不鸣兮一鸣惊人。且求你脱胎换骨,非是我弃旧怜新。斯文名器,想是神通。从兹长别,方感洪恩。短词薄奠,庶其来歆。理极数穷,不胜具恳。就此拜别,早早请行。[8](第五十六回,P710-711)
这篇妙文说尽了晚明科举制度枷锁下落魄文人的可怜可悲,同时也透露了屠隆对于科举仕宦的洒脱态度。屠隆一生为官时间并不算长,在青浦县令任上曾“以仙令自许”,不追求政绩,“尝作祠祀陆机、陆云。时招名士为峰、泖之游”[16](卷14),与其小友陈继儒的言行竟如出一辙。屠隆经常觉得为官是阻碍其自在生活的障碍,他说:“白首一官,终填蒿丘,万分不甘心。世网牵人,无能解脱。日复一日,流年不待人,奈何奈何!”[17](《与陈长孺》,P480)他“宦况日疏,闲情转笃”,追求自由,幻想或为上帝弄臣,鼓吹钧天;或入地狱偷启铁锁,解放万鬼走出苦海。[17](《与陈长孺》,P445-446)屠隆的理想人生状态是“适”,所谓“夫物有万品,要之乎适矣”[18](《旧集自叙》,P576)。这种自适融通的人生追求在晚明文人中具有普遍性,落实到“房中之事”,即一面沉迷于花丛之中,一面又不断警示要戒色止淫,这是《金瓶梅词话》情色叙事生成的现实土壤。例如陈继儒写的《戒好色》词:
红颜虽好,精气神三宝,都被野狐偷了。眉峰皱,腰肢袅,浓妆淡扫,弄得枯槁。暗发一枝花箭,射英雄,应弦倒。病魔缠绕,空去寻医祷。房术误人不少,这烦恼,自家讨。填精补脑,下手应须早。快把凡心打叠,访仙翁,学不老。[19](P159)
这词与《金瓶梅词话》的中心意象“虎中美女”是同一寓意的,视性爱如猛虎,对无节制的性生活进行劝诫。再如屠隆也是一面宣淫,一面却又极力破淫。对此,前贤多有精彩论述,不赘。晚明江南文人在生活中追求自由自在的闲适,他们喜读书、好聚谈、漫游山川、填词演剧、品鉴创作书画、参禅悟道修真等,这与《金瓶梅词话》雅俗杂糅的风格及西门府里的八卦生活有着异构同质的关系。
晚明江南文人求“通”的士风还表现在趋新求奇上。虽然晚明新思潮植根于固有的文化之中,其实践形式也表现为对传统思想作新的注释,但其向着近代发生质变的侨易之迹甚明,呈现为趋新求奇的时代风尚。晚明江南文人脉承六朝人的名士风度,加之新兴工商业的刺激,从而兼具名士与儒商的双重品性。他们追求自我精神独立,这一点从庄子所谓“逍遥游”开始就成为南方文人的胎记,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结合了孟子所谓“独善其身”、“不食嗟来之食”等质实性的人格独立,逐渐形成不与政权合作、山林隐逸、放诞任我的六朝风度,这种风度传至明代江南文人则再变为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三袁“性灵”诗学、汤显祖“唯情”主义、冯梦龙“情教”论等,整体形成晚明人性解放思潮与文学浪漫思潮。实际上,要想实现自我精神独立必须打破思想陈套,特别是要完成对“灭人欲”的理学突围,趋新求奇就势在必然。私密性生活作为人欲中最令人好奇的部分自然成为这场思想侨易的最佳突破口,《金瓶梅词话》便应运而生了。无怪乎李日华认为袁中郎极口称赞《金瓶梅》是好奇之过。随着晚明江南都市经济的大发展,文人的观念中已不排斥做“儒商”,较早的以唐寅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就已富有浓重的商业色彩,稍后松江的陈继儒、董其昌,苏州的王稚登、冯梦龙等更时时做着“文艺商人”。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提到“心学”大师王阳明为商人方麟(节庵)所写的一篇墓表,他据此墓表及其他相关文献剖析了王阳明对儒家四民论所提出的新观点,即商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余英时认为“其最为新颖之处是在肯定士、农、工、商在‘道的面前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更不复有高下之分”,并进一步指出王阳明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这样明确的肯定,是新儒家伦理史上的一件大事。[20](P525-527)这一论断,在文化史、思想史上确认了晚明江南文人兼容名士与儒商的文化品性。这一融通的文化品性,特别是与江南文化市场的积极互动,使得文人们趋新求奇之心更炽。小说(戏曲)因兼具劝惩教化与娱目快心的特别功能而与晚明江南文人心心相印,成为其追求闲适兴味与市场效益的重要文体。《金瓶梅词话》的热闹抄刻及其对商人商业的崭新态度正缘于此。还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江南文人的趋新求奇使其知识结构驳杂、雅俗兼收,这就导致《金瓶梅词话》呈现出传统道德训诫、民间信仰系统与活色生香世界的杂糅状态。
晚明江南文人突破“穷”—“达”二元框范试图走上的第三条道路(“通”),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内部进行近代化侨易的表现。然而,晚明的政治、经济基础都难以为继。随着清军入关,这一侨易过程便遭遇巨大阻碍,直到晚清,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刺激下,它才得以以变形的质态重新加入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侨易之路。自从民国二十年(1931)左右重新发现万历丁巳年本《金瓶梅词话》,“金学”热潮在现当代中国便不断被掀起,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正在走向近代化的精神密码。比如《金瓶梅词话》与阳明学相吻合的张扬个性与人欲,并将人的物性满足与灵性责任区分为不同层次来看待;比如《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文人趋新求奇,并将“自由自在”作为理想的生活状态,这都是与西方思想文化刺激下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思想新质相通的。众多研究者都试图对此准确解码以服务于当下,故“金学”热潮迭起。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之所以堪称“伟大”,正因它是中国文化在晚明发生侨易而通大道的硕果。
参 考 文 献
[1] 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 韩南:《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黄霖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5] 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三联书店,1955.
[7] 陈继儒:《白石樵真稿》,王凯符选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8] 梅节等:《金瓶梅词话重校本》,香港:梦梅馆,1993.
[9] 孙超、李桂奎:《论〈金瓶梅〉的情色叙事及其奇效——以情色选择、情色网络、情色身份为中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0] 黄霖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11] 唐寅:《唐伯虎全集》,大连:大连图书局,1936.
[12]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李贽:《初谭集》,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 李豫亨:《三事溯真》,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 王应奎:《柳南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83.
[16] 陈其元等:《青浦县志》,光绪五年(1879)刻本.
[17] 屠隆:《白榆集》(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
[18] 屠隆:《由拳集》(中),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
[19] 项楚:《柱马屋存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马丽敏]
Abstract: The creation and copy of Jin Ping Mei Ci Hua have a very deep relationship with Jiangnan literati in late Ming Dynasty. Thus there will be some new discoveries when studying th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s with place and time. The so-called “changes with place and time” refers to “changes” caused by “changing of place and time”, which focuses on the qualitative changes and sympathy happening during the displacement of materials or spirits. Judging from this, the creation of Jin Ping Mei Ci Hua is a typical case of changes with place and time in late Ming Dynasty. It changes Water Margin,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story-tellers scripts, books for daily use, history books and various other written materials into a “general” art structure. Copying-engraving books and alcoholomania-lechery are the important parts in the lives of Jiangnan literati in late Ming Dynasty, whose real living needs are satisfied by copying and engraving Jin Ping Mei Ci Hua. The underlying cause of changes with place and time appearing in Jin Ping Mei Ci Hua is the trend of pursuing “general” by Jiangnan literati in late Ming Dynasty when they break through the dual framework of “limit”-“extension”. Therefore, Jin Ping Mei Ci Hua carries the Jiangnan literatis spiritual code of tending novelty, pursuing freedom, etc.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Jin Studies” fever is just originated from this.
Key words: Jin Ping Mei Ci Hua, Jiangnan literati in late Ming Dynasty, literati living, changes with place and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