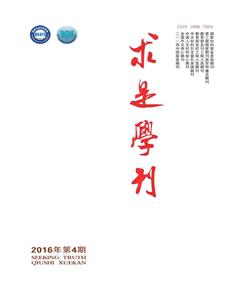陆绍明与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
摘 要: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与其时流行的否定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陆绍明对传统史学虽也有批驳,但比较客观和理性。为包括传统史学在内的旧学“招魂”,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重绘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则是陆绍明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陆绍明将传统史学分为尚文派与重笔派,又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入手,将史学分为九家和二十家,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终究留下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具有学理上的价值。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于辛亥革命之后,史学思想有所倒退,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已渐行渐远。
关键词:陆绍明;史学批评;传统史学
作者简介:刘开军,男,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158-08
20世纪初年的史学批评因其处于新旧交替、中西融汇的过渡时代,而具有多个面相。与其时流行的以西方史学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批判不同,有些学者坚持以客观的态度理性地研究传统史学。他们曾在学术上有过一番作为,却终因时势与学术等因缘际会而渐被边缘化,成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陆绍明就是这样一位史学批评家。加强对这一学人群体的研究,不断扩大20世纪学术史的书写版图,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清季以来西学东渐,传统学术日显式微,时人形容此时的学术界是“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1]。面对如此危局,一些知识分子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气概,提倡研究国学,延续旧学血脉。1905年,黄节、邓实等人在上海四马路东惠福里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即是这样一个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学术团体。这批知识精英对旧学怀有浓厚的感情与深沉的敬意,他们以传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为己任,在晚清思想界和学术界独树一帜。陆绍明生逢其时,既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又成为国粹派史学批评的干将。
陆绍明是浙江仁和人,生平事迹缺略不详。根据清末民初的报刊、南社社员郑逸梅《南社丛谈》著录,陆绍明的字有亮成、亮臣、亮人、亮承、亮丕等1。在当前的学术史研究中,陆绍明几乎处于被忽略的尴尬状态。2笔者仅就所见到的一些零散材料,梳理他的人生轨迹,还原其学术研究的几个片段。陆绍明是国学保存会成员。“国学保存会集中了其时中国东南文化界的精英,是一个主要由年轻的新型知识分子构成的爱国革命的文化团体。”[2](P15)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中,除黄节、邓实外,还有陆绍明的同乡马叙伦以及刘师培、柳亚子、黄侃、胡朴安、陈去病、黄宾虹等。国学保存会下设报社、图书馆、藏书楼、印刷所,公开发行《国粹学报》、《政艺通报》两种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报刊。《国粹学报》第22期上刊登了一张摄于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前的照片,照片中共有十四人,其中来宾六人、会员八人(沈廷墉、邓实、黄节、高天梅、朱葆康、马君武、文永誉和陆绍明)。照片中有人已剪发、着西装、穿皮鞋,但陆绍明仍蓄辫子,着装亦比较传统。
陆绍明曾编纂过一部《汉文大典》。1907年,关于该书的一则广告透露出了一些有关陆氏生平和学术的重要信息,兹录于此:
此书为上海《国粹学报》主政陆亮臣先生绍明所著,全书分十六部都二十万言,搜罗之富,探讨之勤,为近今所罕睹,诚当世之宏著也。先生邃古学,能文章,亦中国少年中之杰出者。闭户数年,仅乃成此,亦可见经营之不易矣。[3]
时人称陆绍明为《国粹学报》的主政,可见他在国学保存会和《国粹学报》中的地位不同一般,是不折不扣的国粹派骨干。“邃古学,能文章”六字则概括了陆绍明的学问特点。陆绍明在1907年前的几年间,除《汉文大典》外还撰写了多篇文章。所谓“当世之宏著”、“闭户数年,仅乃成此”是晚清书刊广告宣传常用的技巧,不足为信。真正重要的是,文中称陆绍明为“中国少年中之杰出者”,综合其事迹推测,陆绍明可能出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年龄当与邓实(生于1877年)、黄节(生于1873年)相仿,或略小于邓、黄3。
陆绍明与晚清四大小说月刊之一《月月小说》具有密切的关系。《月月小说》由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等于1906年11月创办,1909年1月停刊,共发行了24期。《月月小说》前三号的编辑和发行者为汪惟父,从第四号开始编辑者改为吴趼人。1906年,陆绍明为《月月小说》撰写了《发刊词》。文中,陆绍明提出既要重视翻译国外佳作,也要倡导国人自撰小说。《月月小说》上的作品恰恰来自这两个渠道。可见,陆绍明与汪惟父、吴趼人的小说思想相契合。这篇《发刊词》也被认为是近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为小说理论和小说史研究者所重视。在这篇《发刊词》中,陆绍明所举的小说包括《次柳氏旧闻》、《南部新书》等历史笔记。陆绍明对传统小说评价甚高,“古人著作,义深体备,发我思想,继其绪余”[4],主张以小说“改良社会,开通民智”[4],阐明了小说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颇多真知灼见1。
1905年至1907年间是陆绍明学术研究的高产期。他在《国粹学报》上接连发表系列学术论文,包括《旧学魂》、《论古政归原于地利》、《论古政备于周官》、《论史学之变迁》2、《〈史记〉通义》、《史学稗论》、《古政宗论》、《哀古社会文》、《文谱》、《诸子言政本六经集论》、《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古代政术史序》、《史有六家宗派论》、《政学原论》、《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等,成为《国粹学报》前期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这些文章既有纵向考察中国史学思想变迁的宏论,也有关于正史、历史笔记的专门研究,其中不乏长篇力作,比如《史学稗论》一文在《国粹学报》第11、14、15、16期上连载,长达一万余字。该文总论正史之外的各种史书,举凡编年、史钞、载记、时令、地理等逐类列举代表作,穷源究流,讨论其史学价值,可视为一篇中国古代野史论,或野史书目提要。陆绍明撰写的史学论文,从其内容上来看史学史的色彩较浓,从其理论性上来看,则又是一篇篇优秀的史学批评文章。倘若将上述史学文章汇编在一起,庶几可成为一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论集。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视野开阔,体现出总结传统史学、重塑史学理论体系的特点。陆绍明无疑是清末十年间最活跃的史学批评家之一。
1909年后,陆绍明加入南社。1915年,陆绍明在《国学杂志》上发表了《六经非古史说》和《大夫考》。《大夫考》看似是一篇有关古代“大夫”设置与变迁及其职能的考证文章,其实作者的本意乃在政治,所谓“今中国有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之称,不禁低徊久之。……吾考古之大夫,吾且将观今之大夫焉”[5]。同年,陆绍明还在《双星》上发表了《对各国自尊之感言》、《谢游记》两篇短文。陆氏所谓国家自尊,乃国家“雄视于地球之上,必能有发挥其精神,而自期自勉,大有过人者在”[6],强调自尊之心乃立国之本。陆绍明在历数英国、俄国、法国、德国、美国及日本之国家精神后,沉痛地写道:“吾闻之,吾思之,有怦然动于中,而不能自己者。国家苟无自尊之心,势必至欲求结纳一大邦之奥援,托庇一强国之宇下。时而闻他国之图我也,则噭然以啼。时而闻他国之护我也,则冁然以笑。伣伣伈伈,无生气之稍存矣。国而如此,焉得不萎缩而将无以自存耶?”[6]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北洋政府软弱无能,有辱国格。陆绍明此时谈国家自尊,自有深意。联系我国在1915年前后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不难体会到这番话中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而《谢游记》中则有:“余隐西湖,薜荔于扉,图书于几,非不乐者。”[7]1915年,陆绍明隐于西湖之畔,此后逐渐淡出了学术界。
总的来看,在政治上,陆绍明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不管是在清末,还是在民初,他都关心国家命运。在学术倾向上,陆绍明明显偏重于保存国学,有挽颓势、传薪火的担当精神。在这里,爱国家和治国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陆绍明有感于“竞谈西学。旧学之魂,去无影响”[8]的情势,不顾时人的讥讽,作《旧学魂》一文:“以招学魂,魂兮归来,光我祖国。紫阳朱氏谓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吾作是书,亦乱世之文也。悲夫!悲夫!”[8]字里行间流露出慷慨沉郁、感时伤世的气息。为旧学“招魂”,正是陆绍明的学术志向所在,而传统史学正是旧学的大宗。
二、继承史评传统,通论史学流变
陆绍明是20世纪初为数不多的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史学批评的学人。1906年,陆绍明便提出了“评史之学”的概念。“评史之学,两汉以前所未有。唐代刘子元深知史例,官秘书监时,与人争论史事,因著《史通》,而评史之学于是兴矣。其书内篇论史家体例,外篇述史籍源流,辞条言叶,驳诘无穷。降至有宋,评史之作汗牛充栋。”[9]“史评之学,继续不息,知幾学派,代有其人。”[9]而“晚近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一书,其论史学不下于知幾,评史之学足云盛矣”[9]。这清楚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轨迹。尽管陆绍明所举的宋明时期的评史著作既论史学,也论史事,内容上略显驳杂,且对史学批评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著作略而未论,但在一百多年前,能够专门讨论汉唐至明清间的史学批评发展,凸显“知幾学派”,并以章学诚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实属不易。需要补充的是,其时,章学诚尚未被学术界普遍重视,也未进入大多数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而陆绍明将刘、章并论,又准确概括了刘、章史学的批判性特点,反映出他深厚的旧学功底和在史学批评研究上的素养。
陆绍明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史学批评传统,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史籍划分理论上受到了刘知幾的影响。刘知幾将史学分为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10](卷1,《六家》)。陆绍明赞同此说,以为刘知幾所言“不诬,请申论之”[11],于是胪列唐宋以下至于清代的“六家”史籍,评述“六家”之间的联系和“六家”的兴替。陆绍明的《史有六家宗派论》是20世纪较早专论刘知幾史学思想的文章。他延伸刘知幾所论“六家”源流,下限直至清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文实为《史通·六家》篇的续作。
二是效仿章学诚“吾言史意”[12](卷9,《家书二》)的学术风格,注重“史意”的揣摩和评骘。他的《〈史记〉通义》不仅在名称上模仿《文史通义》的“通义”提法,而且重点疏通司马迁作史之意,揣摩司马迁的情感:“太史公牢骚抑郁,不克自伸,乃具如椽之笔,如炬之眼,传记古人,以垂后世。及今读其书,目如见剑舞,耳如闻悲歌,恍然知迁之传古人,非传古人,自为传记耳。”[13]在评论《史记》时,陆氏重视司马迁的人生际遇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在《史记》鉴赏方面别识心裁。
至于《史记》以下历代正史的史意,陆绍明均有论及,颇能言人所未言。他“披览‘二十四史,初觉其体裁微异,而按卷深思,知史家宗旨各有所在也。今之读史者往往强识史事,自诩便便,而于修史者之怀抱学术概不寻思,未为得者也”[14]。言外之意是,历代正史的独特性不在于诸史纪传表志设置的不同,而在于史意的迥异。于是他以简要的语言提炼“二十四史”的“史意”,撰成《史家宗旨不同论》。这篇文章要言不烦,发人深思,如谓《三国志》的宗旨“在铨叙一时巨事,使后世得以观感”[14];《梁书》的宗旨“在拒佛教”[14];《新五代史》“大旨以《春秋》书法为宗,长于褒贬,略于事迹”[14]。这些评论大体反映了诸史的特点与旨趣。文章结尾写道:“‘二十四史之宗旨各有不同。要而论之,优于史学者则长于叙列学术,优于史才者则长于文笔,优于史识者则长于褒贬,优于史法者则长于体例,优于史德者则长于议论,优于史裁者则长于铨叙。史学宗旨大半由是分焉。”[14]陆绍明娴熟地运用刘、章理论,并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以学术、文笔、褒贬、体例、议论、铨叙诸大端扩充了“史家四长”的理论内涵。
当然,陆绍明也自觉地发展了刘、章之学。如在史注研究上,刘知幾在《史通·补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注》中虽也有所论述,“但其学派之异同,刘、章二氏未论及焉。所以后世欲从事于史注者,苦不得其门径。史注之学不将坠地欤?”[15]陆绍明则依据注释的内容和特点将史注归纳为训诂史注、考据史注、文辞史注、自注四大类。其中,裴骃的《史记集解》和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清代陈景云的《通鉴胡注举正》是训诂史注的代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杭世骏的《三国志补注》等是为考据史注的典范。北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开创了文辞史注之学,其后吴仁杰的《两汉刊误补遗》、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和《五代史记纂误》继起之。班固《汉书·地理志》已开史书自注之滥觞,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是自注的佳构。“由训诂史注而流为考据史注,史注之学愈推愈广。”[15]“由考据史注而变为文辞史注,史注之功愈显。”[15]陆绍明如此系统探讨古代史注的类别、代表作和史注流变问题,不仅揭示了传统史注的发展及其对于史学的意义,而且对当前的史注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的一大贡献,是他从深层次上提出了中国史学的五次变迁论。《论史学之变迁》是一篇出入经史、由经论史的力作,文中总结两千多年来传统史学经历了五次变迁,这在20世纪初年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上是一个富有新意的学术见解。他说:“至春秋而史学愈备,至战国而史学乃奇。”[16]这对于评价先秦史学的奠基之功是恰当的。“合先王之政典而成《六经》。《六经》为周史之大宗,孔子定《六经》,注意于教化。由史政而入于史教,是为史之第一变迁。窃《六经》之糟粕而诸子争鸣。诸子为周史之小支,孟子辟诸子归宗于器识。由史才而入于史识,是为史之第二变迁。”[16]陆绍明将“由史政而入于史教”与“由史才而入于史识”作为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的两次变迁,而这两次变迁又分别是由孔子和孟子来完成的。他提出的“史教”一词虽不常见,但意旨鲜明,突出了传统史学重教化的特点。“由议论而一变至于实录”[16],是中国史学从先秦步入秦汉发生的第三次变迁。《史记》开实录史学之先河。“由传记之史一变迁而为编年之史”和“由编年之史一变迁而为类史”[16],是中国史学的第四次、第五次变迁。陆绍明所说的“类史”是指纪事本末体史书,如《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而以清人马骕的《绎史》为殿军。不过,他对“类史”的评价很低,认为传统史学发展至“类史”,可谓沦落至极了。在文章结尾处,陆绍明总结道:
史之变迁原于经学。重《诗》则为议论之史,重《书》则为传记之史,重《春秋》则为编年之史,重《易》则为类史。经之变迁,即史之变迁也。史之变迁即世道人心之变迁也。[16]
陆绍明从经学探究史学之源流变迁,对经史因缘颇有心得。末尾称“史之变迁即世道人心之变迁”,抓住了史学的社会意义。通观全文,陆绍明对中国史学变迁大势的划分有些地方失之绝对和偏颇,比如轻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价值,实不足取,有些论述又语焉不详,如“重《诗》则为议论之史”,“重《易》则为类史”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但总的来看,这些论述中仍闪耀着思想的光亮,如春秋时期史学的重“教化”、战国时期史学的“奇”、先秦百家争鸣与子、史融汇提升了史学的思想品格等论断值得深入挖掘和继续研究。
三、重绘传统史学的学派格局
中国传统史学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因时代、传统、政治和学术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格局,在陆绍明之前史学家已提出了多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如刘知幾以“六家”厘定唐以前的史学;王世贞侧重于从“国史”、“野史”、“家史”考察明代史学的得失;章学诚提出“撰述”和“记注”以区分传统史学;目录学家又设立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史评等诸多门类。站在传统与近代的交叉路口,陆绍明又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史学的整体格局呢?陆绍明选取了“学派”视角,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绘制了传统史学的格局图,这也是他史学批评思想中最有建树的地方。
首先,从“文”和“笔”两个标准出发,将传统史学家分为尚文派和重笔派。《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一文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陆绍明所讲的“文”与“笔”与今人“文笔”并称的含义并不相同。他探源“文”与“笔”二字的古义,说:“偶文韵语者谓之文,无韵单行者谓之笔。”[17]他将“文”、“笔”思想加以引申,结合古代史学家的撰述特色,形成了他的史学分文、笔两派说。史学家各有所长,成就也自不相同。尚文派以班彪、班固父子为代表,“班叔皮好古能文,所著有《王命论》及赋论奏事凡九篇,又著《西汉书》,草创未成,皆秀句奇章,炳如绘素,掷地振玉,掞天凌云。其子孟坚,九岁能文,及长能守家法,续成其父所著《西汉书》。文章炳炳,雍容揄扬。班氏之史,文所擅长”[17]。继班氏父子之后,尚文派史家中又有三国时期的华覈,唐代的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骈文记事,烂若披锦,秀藻云布,潜思渊停”[17]。宋代是尚文派史学的大繁荣时期,“王安简、黄唐卿同为编修官。‘安简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皆工于文者也。吴春卿继其学,文词雅正,天下推之。欧阳修、宋祁集其大成,同修《新唐书》,好以骈体长篇润色唐代诏令,此皆史家尚文之一派也”[17]。从陆绍明所举的尚文派之代表性史家及其史著,可见尚文派史学的特色在于史文表述上工于文而重雕饰,辞藻华美。
重笔派的开山鼻祖是司马迁。“司马迁具良史之才,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17]这是出自《汉书·司马迁传》后论中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评语,最能反映重笔派的史学精神。南朝的范晔、唐代的韦述皆重笔派之翘楚。宋代的李清臣、袁枢,元代的揭徯斯,重视史家心术,继承了司马迁作史之宗旨。至于考据学,则是重笔派史学的支流。由此可知,重笔派史学的特色是直书以成实录,重叙事以彰善恶,这种精神可以上溯到先秦史学的“书法不隐”。
尚文和重笔二派孰重孰轻呢?“一孔之士又谓尚文非史之正裁。孰知记言之史宜于尚文,而记事之史始宜于重笔哉!不此之审,概求史笔,亦太傎矣。”[17]在陆绍明看来,尚文派和重笔派各有所能,相辅相成,二者不可或缺。那么,“文、笔两派”与陆氏所尊奉的史学“六家”说又是什么关系呢?他说:
史分文、笔两家。《尚书》家为文章史家之鼻祖。《春秋》家为笔记史家之嚆矢。《左传》家之体例,实为笔记史家,而亦重文彩,为笔记史家之变者也。《国语》家为文章史家之流派也。《史记》家之体例文章史家之体例,而实则龙门尚笔不尚文,文章史家之变者也。《汉书》家为文章史家之流派也。后世为史者,不知史分六家,又不知六家统于文、笔两派,而昧昧然为史,其可乎哉?[11]
陆绍明以“尚文派”统辖《尚书》家、《国语》家、《汉书》家,其中《尚书》家为“尚文派”的鼻祖。重笔派则包括《春秋》家、《左传》家、《史记》家,其中《春秋》家为其“嚆矢”。《左传》和《史记》二家分别为“笔记史家之变者”和“文章史家之变者”。这就在刘知幾的“六家”说与他的“文、笔两派”说之间找到了结合点。刘知幾以“六家”、“二体”牢笼千年史学,主要是就史书体裁而言的。陆绍明则将“六家”归于“文、笔两派”,以“两派”统摄群史,既重视史书的外部形式,又重视了史学的精神和历史文学。这是陆绍明在史学批评上后来者居上的表现。
不过,陆绍明的史学分文、笔两派论,并非无懈可击。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汉魏以降,史学的门类日渐繁多,历史叙事也日臻完善,史书中的记言与记事已经融合。“记言之史宜于尚文,而记事之史始宜于重笔”在历史编纂中很难实践。这样的划分也就难免牵强。但陆绍明从“文”与“笔”的视角出发,也不失为一种以简驭繁的方法,在他之前的近代史学家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划分方法。陆绍明对于实录叙事一派的梳理,彰显传统史学的求真精神,对于尚文一派的厘清,体现了重视文采的史学传统。这两个传统在古代史学史上是确实存在,并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传统史学的发展的。
其次,陆绍明从诸子与史学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史分九家”——儒家之史、道家之史、阴阳家之史、法家之史、名家之史、墨家之史、纵横家之史、杂家之史、农家之史的观点。至于各家之史的优长,陆绍明说:
儒家之史为极善论断之史。道家之史为极善寓言之史。阴阳家之史为极善时令之史。法家之史为极善褒贬之史。名家之史为极善考订之史。墨家之史为极善共和之史。纵横家之史为极善议论之史。杂家之史为极善纂修之史。农家之史为极善皇古之史。史分九家,学原“六艺”。后人为史,全昧厥旨,可胜叹哉![9]
陆绍明从诸子的角度讨论古代史学流派,不无新意,这既与他对经、史、子三者关系的认知直接相关,他认为“诸子之言,足谓野史。诸子之学,得于六经”[9],也与清季诸子学思潮的复兴具有学术联系。然而,有些具体的提法还可商榷,如墨家之史为善共和之史,农家之史为善皇古之史等语焉不详。
再次,陆绍明在“史分九家”的基础上加以细化,把史学分为二十家,包括辞章家、经学家、理学家、理想家、褒贬家、评论家、议论家、文字家、训诂家、考订家、权谋家、数学家、五行家、纂修家、叙述家、考据家、文献家、地理家、曲笔家、音律家。辞章家之史以班固的《汉书》,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为代表,后衍生出经学家之史和理学家之史。所谓经学家之史,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典范。理学家之史肇端于隋朝王通的《元经》。《宋史》表彰道学,也属于理学家之史。辞章家、经学家、理学家三家之史皆为儒家之流派。
理想家之史以苏辙《古史》为代表。“其持论以无为为宗,行文浑涵澹泊,时抒理论,此理想家之史为道家之流派也。”[18]评论家之史的主要部分即“二十四史”中的论赞,为法家之流派。又由评论家学派而演化为议论家学派,两家的区别何在?“评论家之史是非其事,议论家之史辩驳其理,非可一列论也。”[18]五代的贾纬,宋代的王韶之、罗泌是议论家的代表,议论家之史为纵横家之流派。
荀悦的《汉纪》为文字学派之正宗。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是训诂家之史的楷模。考订家之史首推宋人吴缜的《新唐书纠谬》。文字家、训诂家、考订家之史皆为名家之流派。此外,权谋家之史为兵家之流派;数学家之史、五行家之史为阴阳家之流派;纂修家、叙述家、考据家、文献家四家之史为杂家之流派;地理家之史为农家之流派;曲笔家之史为墨家之流派;音律家之史为小说家之流派。最后,陆绍明感慨地说:
诸史澹雅沉郁,研精覃思,词顺理正,言典事该,笔力千钧,光芒万丈。不知者以为镂心鸟迹之中,文如扬、马;织辞鱼网之上,体类屈、宋。岂真如是哉?元主谓史书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得其旨也。而所谓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流派,恐知之者无其人也,不可慨哉![18]
两相比较,陆绍明的史学二十家之分和九家之分有区别也有联系。不幸的是,“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流派,恐知之者无其人也”一语成谶,在后来的史学史上少见应和者。个中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传统史学理论在新史观、新理论冲击下走向式微,学术浪潮,浩浩荡荡,陆绍明这类坚守中国传统史学本位立场的史学家自然被边缘化了。二是陆绍明对史学的上述看法得失兼有,虽高明有余,但审慎不足。比如,他对“曲笔家之史”的解释与古代史学上相对于直书的“曲笔”之意不完全相同,但他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他对于“考订家”和“考据家”、“评论家”与“议论家”的区分也过于琐碎,其实“考订”和“考据”并无什么实质分别,以李延寿《北史》为考据家派之代表亦不妥当。至于“评论”与“议论”大同小异,很难在“是非”与“辩驳”之间划清界限。“数学家之史”、“音律家之史”的提法也不准确,难以从名称上判断其具体的内涵。
陆绍明划分学派的标准并不规整,有文、笔二家说、九家说和二十家说,失于琐碎。但近代以来,像这样系统、全面地以学派论传统史学,并不多见。具体的提法和阐述确有瑕疵,但陆绍明的学派理论对于揭示古代史学的多途发展、史学与诸子的关系亦有学理价值。同时,他也留下了那个时代学人关于史学流派的一种宏观认识,一种不同于今天的史学批评观念。
陆绍明对历代史籍十分熟悉,故而辨别诸家异同,如数家珍,通过对史书的点评,提炼其共性与特点,无论读史还是评史均非倚门傍户,而能卓然自立。他的史学批评有纵横捭阖之风,无凝滞呆板之病。在陆绍明的史学批评中,不曾流露出对于旧史学的挞伐与摒弃,相反,他对传统史学的肯定多于否定,赞扬大过驳斥。陆氏在史学批评术语上也不趋新,不使用当时的新语言和新词汇;在表述上,善于运用对仗、排比句式,让人感受到传统史学批评的气息。总的来看,在清季新旧学术价值观的交锋中,旧的学术话语虽明显处于下风,但陆绍明仍代表着传统派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使旧的话语体系不至于失语,因此在史学批评的近代化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辛亥革命之后,陆绍明的史学思想有所倒退。1906年,他还援引章学诚的观点,主张“六经皆为古史,各具一体”[9]。但到了1915年,他却说章学诚“陷经之罪,可胜诛哉!其以为持之有故,而言之有理者,实持之者无其故,而言之者非其理也”[19]。“六经皆史”混淆经史之名,“闳硕瑰奇之学,不将由混乱而归于澌灭乎!”[19]陆绍明把章学诚所申述的“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12](卷1,《易教上》),说成是没有依据和道理,是一种“陷经之罪”,其实“六经皆史”之说本身何罪之有呢!陆绍明全然不顾自明清以来经史关系论发展中“经、史一物”的思想趋势[20](卷5,《经史相为表里》),却又斤斤计较于章学诚混淆了“经史之名”,甚至夸张地说这样会毁灭了传统学术,这恰恰是犯了章学诚所批判的“经史门户之见”[12](卷28,《上朱中堂世叔》)和钱大昕所不屑的“陋史而荣经”之病[21](《廿二史札记序》)。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上的一次退步,也与其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大潮渐行渐远。要知道,1915年9月,《青年杂志》已在上海创刊,一个文化新纪元的大幕正徐徐拉开。
参 考 文 献
[1] 邓实:《国学保存会小集叙》,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
[2]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 《绍介新书》,载《月月小说》1907年第5期.
[4] 陆绍明:《月月小说发刊词》,载《月月小说》1906年第3期.
[5] 陆绍明:《大夫考》,载《国学杂志》1915年第4期.
[6] 陆绍明:《对各国自尊之感言》,载《双星》1915年第3期.
[7] 陆绍明:《谢游记》,载《双星》1915年第3期.
[8] 陆绍明:《旧学魂》,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7期.
[9] 陆绍明:《史学稗论(续第十五期)》,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6期.
[10] 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 陆绍明:《史有六家宗派论》,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9期.
[1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3] 陆绍明:《〈史记〉通义》,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0期.
[14] 陆绍明:《史家宗旨不同论》,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7期.
[15] 陆绍明:《史注之学不同论》,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7期.
[16] 陆绍明:《论史学之变迁》,载《国粹学报》1905年第10期.
[17] 陆绍明:《史学分文笔两学派论》,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6期.
[18] 陆绍明:《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载《国粹学报》1906年第18期.
[19] 陆绍明:《六经非古史说》,载《国学杂志》1915年第1期.
[20] 李贽:《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补编》,载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十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王雪萍]
Abstrac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has a complex phenomenon. At that time, the mainstream of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negates tradition. However, LU Shao-ming's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s more objective and rational. He sums up the fiv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some truth. He divides th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to the two schools. On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expression and the oth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is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his historiography thought. Overall, in the cours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LU Shao-m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is historiography thought has been backward, and it is far from the tide of Chinese academic culture.
Key words: LU Shao-ming, Historiography criticis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