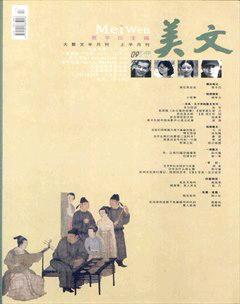见证两位人文领袖的晚年
刘在复
见证周扬晚年的眼泪
一
这几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起周扬的名字。许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名字,不值得我多想,想下去便觉得他们身上太多寒气,以致使我也冷了起来。而想念周扬时,心倒会热起来。因为这种直接的温暖的感觉,又使我确信,周扬是值得怀念的。
八十年代即周扬的晚年时期,在四五十岁的新一代人中,我应当是与他的联系较多的一个了。我为他起草过“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报告、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等。还为他起草《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共同署名)。最后一次是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那时胡耀邦和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已决定仍然由周扬作为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由他作主题报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阳翰笙、冯牧等拟定了一个为他起草报告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周扬挑选。周扬已病重在床,但还是认真地看了名单,最后还是选择了我。当时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受委托告诉我此事,并要我承担执笔起草全国文代会报告。我已下决心不再“代圣贤立言”,便竭力推辞。觉民所长见我执拗,先是拿起党的文件“吓唬我”,说文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已写上你的名字,而且中央已经批下来了。他怕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不信,居然把阳翰笙代表文联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原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呈交的报告)放到我的手里,让我仔细看看。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下来:
启立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
遵照本月17日您关于第五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组名单,要“文联党组讨论,经周扬同志同意,报中央备案”的指示,我与夏衍同志商量后,文联党组于26日开会讨论,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建议:报告起草仍由夏衍任顾问,阳翰笙任组长,其他成员为:冯牧、赵寻、陈涌、江晓天、刘厚生、罗艺军、王春元、刘再复等同志。经夏衍同志斟酌后,已由周扬同志审阅批复同意。兹特呈报中央准予备案。
这次党组会上,并讨论了第五次文代会整个筹备工作的领导问题。建议:扩大并及时组成五次文代会筹备领导组。由周扬任组长,夏衍、阳翰笙、林默涵任副组长,其他成员为赵寻、冯牧、陈荒煤、李瑛、袁文殊、延泽民、陆石、李庚、孙慎、华君武等同志。周扬、夏衍同志也同意这个名单,现同时报请中央一并备案。
附呈周扬同志21日口述函打印件,按他的意见抄送请耀邦、仲勋同志和您审阅。
报告起草组当即开始工作,筹备领导组也将及时召开。
您对以上回报事项有何指示,盼告。
阳翰笙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许觉民在我读完后说:“此件中央已经批准下来。”但他知道我的怪脾气,见我久久不吭声,进而便以“情”来打动我。他出示了另一张起草者名单,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你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圈,是周扬同志画的。他身体不好,我们把起草者名单送给他时,他要了笔,手抖着,然后颤巍巍地把笔落在你的名字上。许所长说到这里,我心一热,便答应了。我早知道周扬病得很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如此器重我信赖我,对我发出呼唤,我能无动于衷吗?中国话说“盛情难却”,其实最难却的是重托的真情,我没有理由拒绝了。那一刹那,我给自己说,赶紧写吧,也许这位当代文化领袖还能看到我为他起草的文字,也许还可以带给他一点最后的欣慰。
没想到,这之后,他的脑软化病情加重,不能像以前那样总是把报告的主旨想好。几次给他起草,我个人收获最大的是写作前倾听他讲述“报告”的要求和要点。那实际上是大文章的框架和基调,也就是“文眼”“文心”,他给报告立了心,我的文章就好做了。这个过程,真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八十年代前期大约五年,我在这一“周扬学院”里吸收“功夫”,受益无穷。经过这段“修炼”,我觉得自己写作的宏观把握能力提升了。像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他就对我和张琢(帮助我起草的朋友)说,这个报告要以毛主席说的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纲”,通过鲁迅这一典范,把三个范畴(科学、民主、大众)讲清。每次听他一讲,不仅听到写作“动员”,还知道如何下笔。可是,八四年这一回他病倒了,连见个面都不行,我只能在文联为我租好的旅馆里独思冥想了。他们要求我先想好主题,然后写好提纲,一个月内完成此事,下个月文联党组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果然,一切都按时间表施行。一九八五年一月间,我被通知和夏衍、冯牧、林默涵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让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们汇报我拟好的提纲。
接到通知后我兴奋了一个晚上,尽管在八十年代我属于胆子很大的弄潮儿,但这回有点像古代举子面临“殿试”的紧张,于是我把自己要讲的纲要想了又想,“烂熟于心”后才和许觉民一起进了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一进门,就看到会议室中间椭圆的大约两丈长、一丈宽的大会议桌。坐在正上方的是胡耀邦总书记,胡启立坐在长桌左侧的中间,他的身边有胡乔木、习仲勋、乔石等书记,我的座位正面对着他们。在他们边上还坐着夏衍、冯牧、林默涵。我和许觉民坐下来之后,立即听见胡启立说:“开始汇报吧!”于是,我就把“烂熟于心”的提纲用20分钟的时间讲完。讲完后夏衍作了大约5分钟的说明,他事先已审阅过提纲,只是说明周扬同志已住院,无法到会,提纲中所强调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兼有推动历史前进和艺术创造的双重使命这一主题是文联党组认可的。接着书记们发表了意见。胡耀邦说话时我侧耳倾听着,并做了笔记。他说,现在中国处于变革大潮中,泥沙俱下,一面是发展,一面是流氓、地痞、投机者兴风作浪,他们影响社会风气,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影响社会风气。都在一条河里,我们要同舟共济呵。讨论“提纲”后我们这些老少“秀才”们就要走,没想到胡耀邦面对着我说:“小刘,你们坐下来听听。”于是我和许觉民居然留下来列席书记处的下一段会议。主持会议的胡启立宣布还有两个议题,一是边疆干部是否提高工资的问题,二是要不要设立博士、硕士学位制度问题。讨论中的发言,习仲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他敢于直言,而且语端带着情感。讨论学位问题时只有胡乔木一个人发言,他倒是娓娓道来,说明建设学位制度的必要性。散会时,我和许觉民走到胡耀邦面前,和他握手,他大约感受到我的敬爱的目光,又说了一句:“要同舟共济呵!”
会议之后,为了周扬,为了胡耀邦,我在旅馆的灯光下日夜写作,很快就交出了初稿。我向许觉民和文联党组请求,修改和定稿就由别人去做,我刚刚接替他的研究所所长也的确太忙。党组同意我的请求,最后诉诸社会的“报告”有没有用上我的文字,我也记不得了。
回到所里,我除了必须进入陌生的“领导角色”之外,还得开始着手写作周扬给我的另一篇大文章,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这一总论题为《中国文学》,放在辞书的最前边,篇幅一万五千字。具体执行主编工作的王元化和许觉民“指示”说,此文已写了两三年了,到处征求意见,还是写不好。最后和周扬同志商量,还是由你来写。你要写好三个部分,一是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从古代到现代都得说;二是概说中国文学的特征;三是概说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史略。面对这一重托也是重担,我明知繁重,又是因为对周扬个人怀着知遇之情感而完成了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本应只署周扬的名字,但王元化、许觉民为了表彰我的劳动,便不顾名分辈份的差别,把我的名字和周扬的名字署在一起。当时我四十三岁,还是全国青联委员,常以青年自居,能与中国文艺界的泰斗人物“并置”,自然高兴,但我当时所以没有“谦让”,实在是因为周扬晚年留给我一种人性尚存尚在的温馨印象,并非“暴君霸王”,使我觉得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实在是非常光荣。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的晚年未灭的人间性情作证。到海外之后,我所作的反省都是人性的反省,包括对故人的回忆,也唯有那些还具有人性挣扎的往事,才能重新激起我热爱人生的情思。
二
我和周扬真是很有缘分。一九七八年他从暗无天日的文字狱中刚刚走出来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胡乔木),而我正是院长胡乔木和另一副院长邓力群领导下的写作组成员。工作室就在周扬办公室的楼上。那时我正在如痴如醉地批判“四人帮”,经历着人生最快乐的向前冲锋的火热日子。当时周扬也刚摘下“四条汉子”的魔咒,从临近死亡的峡谷中走出来,尚未完全抹掉从地狱里带来的阴影,谈不上什么架子,而我又仗着自己年轻,就常常直闯他的办公室,和他谈论我正在写作的讨伐“四人帮”的文章和社会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故事。那时,“文化大革命”如山如海的大冤大仇大恨仿佛全都集中在我身上,除了写文章之外,就是滔滔不绝地诉说荒诞与野蛮。可周扬除了认真听之外,很少说话,只是我在谈到把孙冶方打入牢房,把张闻天按之入地,把厕所里的铁丝纸篓戴到俞平伯老先生的头上时,他才连声叹息。那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潮湿的。从他的泪眼中,我发现他的心事很重。
这是周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一种伤感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与他频繁的接触中愈来愈加深。他的伤感一是为自己被伤害,一是为自己曾伤害过别人。特别是后者,我亲眼看过他多次为此落泪。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到颐和园清华轩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当时在清华轩参加这一个工作的有三个“将”(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和五个“兵”(唐因、刘梦溪、郑伯安、徐非光、刘再复)。周扬也几次到过那里。初稿完成后,周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大约有四百个文艺界著名人物参加的征询意见会。在这个会上,丁玲、艾青、萧军站起来走到周扬面前,痛斥他过去的“专横”,一点也不给周扬“面子”。那时我坐在离周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看到他恭恭敬敬地倾听着这些满怀义愤的“痛骂”,眼睛直愣愣的,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那一刹那,我觉得周扬真是可怜。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头目被打得尚未直起腰杆,这些作家又要向他讨债而他又确实欠了债。散会后的第三天我在颐和园清华轩里见到他,当时其他写作人员都回城里了,只有冯牧和我在。我们就陪着周扬聊天,并自然地说起这次征询意见会。周扬用一种负疚的、低沉的声音说:“五七年伤太多人了,那篇批个人主义的文章太激烈了,他们有气,他们都吃了苦了。”说完就落泪。这一天我还第一次听到他诉说自己的委屈与困惑。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每作一次报告都要重新认真阅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也亲自给他写了三十多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说完又落泪。他走了之后,冯牧说:“周扬同志好极了,一说起错打一些同志就掉泪,以后少提这些事,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我点点头,并觉得周扬确实非常真诚地觉得过去自己伤害过别人,对此负有责任,尽管他心里明白自己又是一个执行他人意志的悲剧者,无可逃遁的政治器具。
我从清华轩回社科院之后,就很少再见到周扬。当时我埋头撰写《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并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其实,周扬真正看中“我”也是从“鲁迅”这个名字开始的。大约是一九八〇年秋天,当时担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荒煤找我,说周扬想写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原先请王士菁同志起草了一个,实在不行,周扬请你另写一篇。说完就把王士菁写的稿子给我,上面有他写着的“批示”:请载复同志重新起草一篇,他把“再”字误写为“载”字。荒煤还告诉我,周扬出的题目是“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你就按照这个题目写一篇吧。我觉得这个题目好,而且性急,两天内就写了一篇稿子并交给陈荒煤,过了几天,荒煤告诉我,周扬很满意,但你还是要尊重王士菁同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扬特别交代把稿费交给我,我坚持把一半稿费分给王士菁同志。当时王士菁是鲁迅研究室主任,刚从广西调到北京。他为人温和,只是每次开会都强调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这种唠叨常使我困惑。
三
这之后不久,我又作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报告的主要执笔者,再次代周扬立言,从一九八一年的春天一直忙到秋天。当时周扬、陈荒煤根据我的意见,请我的朋友、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参加,还请另一朋友、文学所的张梦阳协助。这一写作过程,其复杂与曲折,是我在工作之前绝对料想不到的。这一过程的细节还是留待以后细说。我这里想说的仍然只是周扬的感伤。为了写好这个报告,周扬在他家里以及在北京医院,多次和我谈论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作为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之一被揪出来的。以《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作为借口,说这条注释是他射向鲁迅的一支毒箭,然后便开始清查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从三十年代就开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周扬作为这条黑线的“祖师爷”,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自始至终受尽污辱性的批判。我常想,一个人能承受这种大规模的洪水般的攻击、污蔑、毁谤与中伤,能在泰山压顶似的文字狱中存活下来真是个奇迹。陶铸的夫人曾志告诉过我,当他听到广播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往她心上戳,而周扬听到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不知道怎能受得了?
我一直想了解:是怎样坚韧的信念与观念使他能在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轰炸中支撑住生命。每次见到他时,我几乎都忍不住要问他。而背着“鲁迅之敌”的罪名蒙受十年攻击的他,现在又要作为纪念鲁迅的文艺界领袖而发言,他又该说些什么呢?心里翻腾的是怎样的真实情感呢?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所以总是留心他的想法说法,并把他说的话作了记录, “鲁迅的伟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无人可比,他最了不起的,一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鲁迅是个天才,可是在鲁迅处于晚年的三十年代,我们那时还很年轻,太幼稚,不能充分认识鲁迅。”周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诚恳的,我能感受到他的每一句话都发自情感深处,一点也不掺假。
他知道那时人们仍然在神化圣化鲁迅,鲁迅的研究者和宣传者仍有许多矫情,他知道这种圣化乃是鲁迅评论另一形式的幼稚病。但他不是忙于去指导他人,而是想到自己年轻时代的幼稚并为此感到遗憾。他的这种认识与情感,使我感动,所以在写作这一个报告时,我要为他负责,尽可能地抹掉“文化大革命”投给鲁迅的神圣光环,绝对不能再滥用鲁迅的名义去号令作家。于是,我尊重周扬的意思,在写作时强调鲁迅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精神和强调作家的良知,语调平和平实一些。这一报告初稿写成的时候,周扬很高兴,他作了修改后便印发送给中央的领导人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征询意见。没过几天,胡愈之、傅钟等的意见纷纷下来,他们都很满意。当我正在松口气的时候,周扬让陈荒煤通知我和张琢立即到北京医院参加紧急会议。这次会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当时周扬住在北京医院,所以由王任重召开的此次讨论报告初稿会议只能在医院里进行。
那天会议除了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身份主持外,参加的还有周扬、贺敬之、林默涵、陈荒煤等,他们都是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此外,还有李何林、王士菁、我与张琢。王任重说他上午刚刚见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报告还是得有点战斗性。于是,王任重批评说,这个报告初稿完全没有战斗性,完全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还提什么作家良知,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听了王任重的话之后,我和张琢都沉不住气,当场就和王任重辩论起来。我说,过去十年把鲁迅弄得满身火药味和战斗气,借他的名义打人,这回报告可不能这么写了,我们应当有一个平和的、求实的、科学性强一点的报告。张琢也紧接着发言,支持我的看法,他锋芒更健,用词极为犀利坦率。王任重没想到我们敢于当面顶撞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说这个稿子作为学术论文还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不能作为党的报告。于是,王任重便委托林默涵组织一个班子另写一篇。
那时距离开会时间只有十几天,三位临时上阵的起草者日夜奋斗,而我则赌气真的想把初稿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得知我要这样做时,急了起来,说:“等等,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果然,过了几天,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颖超通知周扬和陈荒煤,说她已读完报告初稿,并说:“报告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作家的地方,前边应当加上‘革命二字,作家应当成为革命作家嘛!”王震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周扬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凡是精彩的地方,我都用红笔划上了。”周扬让我看看王震画红线的地方,一段一段,几乎画上了三分之二。陈荒煤听到邓颖超的意见后很高兴。他告诉我,可能还得用原来起草的报告,你可以在文字上再作些推敲。邓颖超、王震的意见果然起了作用,王任重又在中宣部召开紧急会议,那时距离开会的时间只有两天了。此次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王任重之外,周扬、朱穆之、贺敬之、林默涵和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都参加了。王任重说:“现在形成两个报告初稿,今天都读给大家听听,大家作决定。”林默涵立即表示,后来起草的报告不行,还是读读原来起草的报告吧。于是,我就当着大家读了一遍报告。读完后王任重首先发言,说这个报告稿这几天修改得不错,再加上一段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就可以了。
我觉得当时的作家主要问题应是从教条的重压中站立起来以便用更自由的心灵去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崩溃了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在他们刚刚呻吟几声就忙于用“反对自由化”的口号堵住他们的咽喉。散会后,周扬让我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家里。当时,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姐正好在家,她对着满怀心事的周扬说了几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如果还要你再去反对自由化,再去批判别人,你就不要做这个报告,我们的教训够深的了。”当时她很激愤,锋芒直逼周扬。我被苏灵扬大姐的一番坦率的肺腑之言所鼓舞,暗自高兴。而周扬始终认真听着,待苏灵扬大姐平静下来后他才和我一起到会客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他让我把谈论文艺界现状的那一段话找出来让他再看看。我把稿子摊开,他就在桌边坐下,一行一行地看下来,最后,他提起笔加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应当特别警惕左的倾向。”写完之后对我说:“他们说要加上一段话,我看还是加上这一句。”我看了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立即郑重地对他说:“周扬同志,你的想法是对的。”他接着就很严肃地说:“我改过的这份稿子以后就由你个人保存着,你可以作证。”他讲这几句话时,声音微微颤动着。我一直不会忘记这一天,一直不会忘记他的委托,一直把他的修改稿郑重地保留着。
周扬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他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执行者,确实整过人,打击过敢于直言的作家,但是,当他自己也经历过不幸,经历过贴着革命标签的文字狱之后,又确实有所彻悟,确实有负疚之心。他从历史的伤痛与自己的伤痛中学习到一点:不能再“左倾”了。他曾参与“左倾”的革命列车碾碎了许多作家的心灵而最后自己的心灵又被这种列车所碾碎,无论是坐在车上还是被碾碎在车轮之下,他显然都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他晚年不断落泪,不断伤感,不断对着继续“左倾”的喧哗发出叹息,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到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曾参与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需要记取教训、需要忏悔、需要感到心灵不安的时代。晚年的周扬没有理直气壮过,他只是伤感、迷惘与反省,尽可能发出一点与过去不同的声音,最后他还希望一个年轻的后人为他晚年灵魂的变迁作证。他意识到这种变迁的重要,意识到历史将肯定他的某种觉醒,尽管在这种觉醒中仍然充满摇摆、矛盾和痛苦。
我和周扬的文字之缘和思想之缘,毕竟是人生旅程中值得记忆的一页。所以值得记取,并不在于我曾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的名字紧紧相连,而在于我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看到一种历史沧桑的痛苦与严峻,一种人性的挣扎与复活,一种难以死亡的良知责任感,一种负载着时代错误与灵魂困境的眼泪与伤感,这一切,倒使我感到温热与希望,而不会像那些践踏过无数优秀的身躯而高喊永不忏悔的人们只给我寒冷与绝望。
见证胡绳晚年的困境
也许是爱读书的缘故,也许是在大学期间就读胡绳的成名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此,“胡绳”二字,一直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闪闪发光。一九六三年我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当时我并不崇拜朱光潜、冯友兰这些老专家,认定他们已属于旧时代。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郭沫若)、范(范文澜)、候(候外卢)、翦(翦伯赞)、吕(吕振羽),但这五老都是学院里的学术元老,而胡绳则是直接为党为国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更是让我佩服。那时,我把他和胡乔木、艾思奇、周扬等列为特别星座,属于我的偶像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二月提纲”,据说胡绳也是起草者,因此也成了“横扫”之列,变成了“牛鬼蛇神”与黑笔杆子。当时,他绝对不会想到,一个在科学院《新建设》编辑部名字叫作刘再复的“粉丝”,为此而想不通,为此而坐立不安,为此而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勤奋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放入被命名为“黑帮”的另册。他们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
没想到,煎熬了八九年,胡绳“解放”了,并且来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我和他真是有缘,他一来就直接指导我的工作,那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刚刚重新走上政治舞台(1974年12月毛泽东发表“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讲话)。而胡绳也随之进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来的一批党内主要笔杆子如胡乔木、邓力群又被重用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刚“解放”的干部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组成(王仲方为秘书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乔木、胡绳选中了原《新建设》这批人马,说要以《新建设》的班底为基础,办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刊物,但名字要改为《思想战线》,主编由林修德担任,主编之下组成一个五人筹备小组,根据时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竟然成了“青”的成员。筹办这个刊物是件大事,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要办的一个与《红旗》叫阵的理论性刊物,一个与极“左”思潮唱反调的思想阵地。名为林修德主编,真正的领导者是胡乔木和胡绳。胡乔木所做的一切指示,林修德立即传达给筹备组,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作了检查,我才知道邓小平确实要办一个能执行自己路线的刊物。胡乔木只是出主意,并未到过编辑部,而胡绳则亲临《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当我按照林修德的意见拟出创刊号的目录与约稿名单后,他来到了编辑部,对着我们的筹备小组发表他的看法。他说,创刊号应当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亮相,登他们的文章。目录的选题不错,但一流的作者太少。我仗着年轻,就问,目录上的约稿名单已有任继愈、唐弢、冯至等,您觉得还应当约请谁,没想到他立即就回答说:“请钱钟书、何其芳、李泽厚嘛!”他还指示我们:“关于批“水浒”的讨论,可以组织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要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听了胡绳的指示,第二天我就去找何其芳、李泽厚约稿。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胡绳,也由此因缘,我第一次找到了何其芳与李泽厚。(我还把胡绳的讲话告诉李泽厚,李听了很高兴)这之后,胡绳又来了多次,每次都是对已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因为有这一上下级共同工作的机会,我才认真地观赏了自己昔日的偶像,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谦虚又能决断。也许因为积淀于身上的亲切感,我竟然向他要了住处地址和电话,而他竟然给了我,说李泽厚到过我家,你可以问他。可是,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就来临,筹办《思想战线》成了邓小平翻案的一项罪证,把林修德吓得够呛。当时我又仗着年轻,就告诉林修德,说关于《思想战线》的事,特别是诸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一个标点也不会“交代”。也许因为这段时间表现好,所以“四人帮”一垮,我便特别受到器重,被通知和一些军队干部进驻《红旗》杂志工作,参加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社论,每天都忙到深夜两点,也每天都在深夜里饱食了一顿豆浆油条后才去睡觉。那段日子真美,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充满“胜利的喜悦”。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社会科学院,并被“重用”放入邓力群亲自主持的院部写作组,日夜讨伐“四人帮”。那时胡乔木已任院长,副院长是邓力群和于光远,周扬则担任顾问。当时全院上下老少同仇敌忾,致力于拨乱反正,制造舆论支持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以写作组为基地召开鼓吹思想解放的“双周座谈会”,他们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就尽管“放”,一旦出什么问题,他们会承担全部责任。在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之间,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他们那种敢说敢担当的气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惜之后不久他们又分道扬镳了。我个人则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最开心开怀的日子。
没想到,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胡绳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吴全衡大姐之语)。他因为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不像胡乔木、邓力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而是直接担当华国锋的笔杆子)。因此,他徘徊在“两个凡是”和“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论辩之间,态度暧昧,以至被视为“两个凡是”的支持者。没想到“两个凡是”恰恰是阻挡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严重事件。这可不是小事,邓力群的双周座谈会以及种种理论务虚会便大批“两个凡是”论,批了一阵,果然是华国锋时代结束了。邓小平重新走上历史舞台。对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然是高兴得“上窜下跳”,在社科院主楼写作组办公室里又写又说又热烈表态,但胡绳却再次陷入困境。当我在写作组里听到议论说,胡绳是“两个凡是”理念的炮制者之后,立即想到,应当去看看胡绳,于是,我立即步行到东单史家胡同二号。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进门就见到吴大姐。大姐见到我,特别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和李泽厚,不管什么时候都来看我们。老胡就在里边,他最近情绪很不好,害怕又要被揪出来。”这个“揪”字,吴大姐讲得特别响亮,可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个“揪”字,听了十年,还听不够吗?于是,我立即“反驳”吴大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会再揪人,更不会揪胡绳同志。绝对不可能!”我说得斩钉截铁。说完就走进胡绳的书房,他让我坐下,脸上虽有笑意但缺少光泽。不等他问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形势特别好,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又掌权了,他们对你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当时讲话的口气特别大,这大约是那时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直为“打倒四人帮”这事而激动不已。胡绳听我一阵慷慨陈词之后就问我“学部”的情况,我自然是事无巨细地把所闻所见全部掏空给他。他听完后挺高兴,说他最近又在整理旧稿写作新书,准备把《中国近代史》写出来。说完带我看了看他满院的藏书。所有的房间、过道都是书,有些书架太矮,我就蹲下来看,或趴着拼命翻阅。当时我真是羡慕极了。出门后我一路上走,一路上想: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党和人民的代言人,干么到现在还老是想到一个“揪”字呢?一路上,我的脑子全被这个“揪”字揪住了。
因为牵涉“两个凡是”,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四年里,他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寂寞,却创造了他自身史学研究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这段时间我总是把自己刚出版的书籍文章寄给他,也借此向他问候。1983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三联推出,他亲自签署了名字寄赠一套给我,是从邮局寄到我的劲松家的。我收到后立即就读,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细节,到了这时我才真明白。他的文笔真好,读他的书就像读小说。那时我还没有“告别革命”,对他的全部论述只是接受,没有质疑。直到我出国之后再度阅读时,才发现他完全悬搁近代史中“建构现代文明”这一线索,视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为“死胡同”,把近代史描述成三大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单线历史。我读后充满和他商讨的冲动,但只是写了阅读笔记和批评提纲,一直未写成论文。我总是把人与理念分开,对于愈敬重的人,愈想和他商讨。商讨虽是批评,但也是请教。
记得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召开的人大、政协年会期间,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见到了胡绳(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那是会间休息的时候。他当时的精神很好。“两个凡是”案已经放下,新史著已经出版,危机已被新的学术成就所替代,他的精神重新焕发起来了。我们谈得很热烈,第二次入场的会议铃响之后,他的谈兴正浓,就说:“没什么好听的,我们还是坐在后边说话吧!”他的建议正中我的下怀,自由主义惯了的我,连说几个“好”字。于是,我们坐在最后的一排(最后几排没有人)小声又热烈地聊天了。谈起社会科学院的情况时,他非常熟悉,嘲笑建立社会学研究所是“没有和尚先有庙”,“一个空庙没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我是记住了。因为当时我沉浸在忘年之交的情感中,没有把这句话和他过去曾指责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理念联系起来。(在《枣下论丛》中他把社会学全都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在此次交谈中,我特别和他谈起李泽厚要求入党而哲学所的党组织却不接纳的事。我说我已在一九七八年入党了,李泽厚也申请,但党支部讨论时却用一些古怪理由,如他从不去打开水等理由加以拒绝(当时每个房里都有集体用的热水瓶,每个人都必须主动去打开水)。我还特别和他讲了我们研究所(文学所)钱碧湘(我的同事与朋友)说了一句妙语:“我有两个不理解,一个是李泽厚为什么要申请入党,另一个是既然他要求了,为什么党又不批准?”胡绳听后笑了,说:“不让李泽厚入党是不对的,李泽厚至少可以说,他不走邪门歪道嘛。”没想到,过了一年多,胡绳被派到社会科学院当院长兼党组书记。他果然记得我说的这件事,就与哲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孙耕夫打招呼,应当欢迎李泽厚入党。但李泽厚早已撤回申请书,此次他就不再申请了。不过,胡绳还一直欣赏着李泽厚的过人才华。读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还特地写信给李泽厚,说他特别喜欢关于苏东坡的那一段论述,苏东坡不仅回避政治,而且逃避社会。后来李泽厚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在胡绳当了院长之后。
我是一九八四年年底被选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当时的院长是马洪。我对马洪院长夫妇印象极好(马洪的夫人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奠基人,第一任社长,推出我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他们对我又器重又关怀,因此胡绳的到来我并不感到特别兴奋。不过有一段情谊在,我还是指望胡绳能扶持。挑上所长这一担子实在太重,用吴世昌先生的话说:“再复,你胆子真大,也敢当这个所长。”期望“扶持”,不是期望“提升”,而是期望“保护”。我知道自己完全不适合于做行政工作,当了所长之后,常想起瞿秋白《多余的话》中所自嘲的“犬耕”形象。
可是,所长换届之后院长也换届,胡绳和我都是“新官”,都想把工作做好。我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从事创作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大会,规模很大。会前发出四百份通知,还发到全国各地。当然也发给胡绳和其他副院长。会前几天,所办公室通知我:胡院长有紧急事找你,让你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我放下笔,匆匆下楼梯跑到他的办公室。一开门,他就怒气冲冲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他满脸通红,着实生气了。看他气得这个样子,我只好装糊涂说,我当所长不久,不知道开这种会还得写请示报告。其实,我和何西来等几位副所长早就明白,一旦写报告肯定开不成会。胡绳听我辩解,更生气了:“这是毛主席定的案,能不请示吗?”他这么一说,我又只好装傻跟着说了几个“怎么办?”他说:“你通知都发到全国了,还能怎么办?赶紧补写一个报告,呈交中宣部。”我立即说我不会写这种报告,他看了看我,或是相信我的话,或是担心我写得不好问题更麻烦,就说:“那就由我替你写一个报告吧。”我连忙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我如释重负,赶紧往外就走。到了门边,他又把我叫住:“等等,俞先生的会我还是会去参加的。”这可把我高兴死了,我立即“得寸进尺”说:“你可得讲讲话。”他点点头,“讲几句吧!”在胡绳的支持下,纪念俞先生的会成功召开了。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俞平伯、胡绳和我,还有刘导生、钱钟书先生等。气氛热烈极了。散会时,钱先生从人群里挤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会开得太好了!”
仗着过去的情谊,我常常直接闯入胡绳的院长办公室。一九八六年初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在《文学评论》发表之后不久,他让秘书打电话找我去,见面时说:“你看到《光明日报》的一篇《春天的反思》文章没有?是针对你的。”我拿过来一看,就说:“您不要支持他们!”他有点不高兴。过了三天,他约我到他家(新家在木墀地的公寓里)。那天吴大姐也在家,见到我时非常高兴,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谈谈,有电话来我会挡住。胡绳和我对坐在两张沙发上,边上是他的办公桌,一坐下来他就指着满桌的信件说:“你看,满桌就是控告你的信。”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瞄了一眼,看到除了信件、文件之外,还有一本刊载《论文学主体性》的那一期《文学评论》,文章上画了许多红杠杠,还有我看不清的许多眉批文字,显然,他是认真读了我的文章才找我谈话的。我当即意识到,今天下午我将会与我往日的偶像进行一场论辩,必须借此认真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
胡绳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赞成有些人对你政治上纲,但也不支持你的观点。你的主体论与胡风的主观论有什么区别?我看没有太大区别。我是批判过舒芜的主观论的,不会同意你的论点。”我听了之后,不说半句敷衍话,就直接答辩说:“主体论确实强调作家的内心和内在主观宇宙,但不等于就是主观论。主体是指人、人类,既有个体主体性,也有群体主体性。个体与群体的历史实践,尤其是人类整体历史实践,是主观活动,更是大客观活动。我虽强调个体主体性,但也是指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能动性,并不否定关系中客体的那一面。再说,主体论即使涵盖主观性,也不应当因为胡风说过就觉得不对。”听了我这些话,胡绳开始激动了,脸色涨红。我知道他写过批判主观论的文章,这些话不能不刺激他。于是他又说:“照你这么看,文学反映论也不对了,也该推倒了。”我说:“我讲主体论正是为了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这个哲学基点不变,我们只能跟着苏联的教科书跑到底了。”关于主体与主观的问题,来回辨了一个小时左右,声音愈来愈大,以致让吴大姐跑到我们的门口看了两回。这个问题讨论之后,胡绳又严肃地说:“我问你,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难道也不对吗?你讲超越性不就讲超越党性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带头质疑党性,可以吗?”我又认真地回答:“作为现实主体的党员,当然应该讲党性,但从事文学活动,党员不应当以现实主体的身份去参加,而应以艺术主体的身份去参加。现实主体讲党性,艺术主体则要讲个性。我说的超越性,是指对现实主体的超越。”看到我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的嗓门提高了:“总之,你的主体论是会腐蚀集体主义原则的。别人的意见你应当好好听听。”一说起别人,我更亢奋了,就说:“我就是不爱跟别人跑。”声音太大,把房外的吴大姐惊动了,她跑过来问:“怎么回事,吵得这么凶!?”胡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他安慰吴大姐说:“没什么,我和再复讨论问题,讨论得很认真,你看再复还送我们一瓶水仙花。”他把水仙花从桌上提起,放在吴大姐手上,吴大姐眉开眼笑说:“我就喜欢你们福建的水仙花!”
在家中的这一场辩论之后,我才知道胡绳在理念上站在我的论敌一边,因此心里暗暗“恨”他,好几个星期都不到他的办公室。有什么公事,只让我的秘书找他的秘书。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从广东休养回京后,胡绳约见了我,并交给我一份新的聘书,让我当社科院文学语言片学位委员会的召集人,也就是中国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语言所等四所学位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由冯至、吴世昌、唐弢等几位著名学者组成。这个学位委员会是裁决谁可担任博士导师和最后通过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权力很大。这份聘书我至今还保留着,但从不张扬,只把它看作是胡绳对我的信赖。第二年又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温暖。一九八八年中央决定打破历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只有“挨批”的倒霉地位,想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文、史、哲征文比赛,以表彰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此事对社会科学院构成了压力,如果几个大所拿不到一等奖,就有失“面子”,因此院领导十分重视,讨论了一下,决定文学所一定要我写一篇论文,由副院长汝信通知我。当时我也觉得必须尽点责任,便想了一个题目,叫作“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正要着笔,又想到胡绳对我的主体论的批评,便犹豫起来,就跑到办公室问胡绳,说我选这个题目,你觉得合适吗?没想到他的态度极亲切,说:“这回你要放开手笔写,不要管别人的意见,你选这个大题目,关键是要能驾驭得住。”听他这么一说,我更有精神了,就在劲松寓所里闭门谢客,三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近两万字的论文,而且获得一等奖。并得到五千块奖金(我把奖金都赠给文学所何其芳青年文学基金会)。当时全国各大学、各社科院共应征写出了将近一千篇论文,有22篇得了一等奖,分布于各学科,文学方面有两篇得一等奖,其中一篇是我的“遵命论文”。消息公布后,钱钟书先生特写给我一封贺信,说我的文章“有目共赏”,让我高兴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得钱先生的四个字,字字千钧,是对我最高的奖励,奖金奖状倒在其次。颁奖仪式很隆重,发奖人是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胡绳,我对坐在身边的科研局副局长陈韶廉说:“我不要王忍之给我发奖。”陈韶廉低声对我说:“你不要胡来,我马上到后台去告诉他们,请胡绳给你发奖好了。”果然,我从往日的偶像手里接受了奖品,并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另一次是胡绳召开讨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筹备会,人文学科的各所所长都参加了。那次会上,胡绳思想非常开放,说应当请钱穆、夏志清先生都来,不管过去持守什么政治立场,只要是真有学问的,就请来。我听了特别高兴。他还宣布了筹委名单,我也在其中。散会后,他让我留下,只说了一句话:“再复,这次会你要写一篇有分量的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这篇文章,一九八九年发表在大陆的报纸及东京、香港的纪念集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