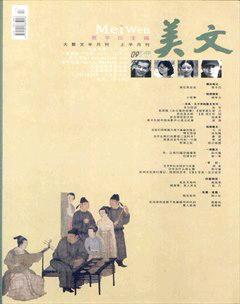养鸡札记
周实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十多年前,也就是将近五十岁时,我告别了心爱的工作,下岗了。下岗之后,很少外出,一天到晚闷在家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种原本不好的习惯竟也变得理所当然。然而,有点纠结的是,我这人虽然已经安分却仍有点不太守己,突然间又萌发了饲养几只小鸡的念头。现在,想想,这也许和我儿时格外羡慕邻家小妹拥有一窝毛茸茸的小鸡有关。
四月份,正是小鸡出壳的月份,提着一个小篾篓,我悠悠地去了市场。
市场离家并不远,路程大约十分钟,设在一条马路边。入口处和出口处象征性地竖立着一个十分高大的门架。大门架是钢铁的。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结实得很。门架内,人蹭人,想移动都困难。不过,这点对我来说,对我这个下岗的老人或者一个内退的大叔或者一个无事的闲人,倒是非常合适的。
我在钢铁的大门架内来回转了两三圈。卖小鸡的人不少,大多数是鸡贩子。他们贩卖的那些小鸡叫得都不太响亮,缺乏生命力,不中我的意。我想,改日再来算了,又不甘心白跑一趟,稍稍犹豫一下之后,决定还是买几只,只好碰碰运气了。
转头,试问一位妇女:“你的小麻鸡,多少钱一只?”
“八角。”妇女答道,转过眼来,飞快地打量了我一下,无非是想在我这老头子身上捞一把。
“你这是——刚出壳——才一天的小鸡呀。”我手一点,信口开河,虽然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小鸡是何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妇女不知我的底细,没再吱声了。我想我是讲对了,立马进一步地说:“八角太贵了。五角。”
“你看呀,你看——”妇女突然叫了起来,指着我早就看见的她的叽叽叫的小鸡,“我的全是母鸡呀!八角,少不得!”
听说是母鸡,我的心一动。
“母鸡要八角?”
“那当然,母鸡长大了,能生蛋……”
能生蛋就意味着能生鸡。能生鸡的鸡,要价自然高一些。我不好讨价还价了,就说:“买四只。”
“你自己挑吧。”妇女随即摆出了一副买卖公平的样子,“先付钱。”
赶快付了钱,然后是挑鸡。先挑两只大一点的。又挑一只头特大的。最后挑了一只眼角长有一道小黑线的,模样有点像“画眉”。四只小麻鸡进了小篾篓,只只脖子伸得老长,叫得十分响亮。我不理解它们的意思,也不想去仔细琢磨,提起小篾篓,转身回家去。就要走出市场时,又意外地听到了格外响亮的叽叽声。我不由得停住脚步,朝着响亮的叫声望去,看见了两只大篾篓。篾篓旁蹲着一位老农。老农的头上正冒着热气,额上一片湿漉漉的。看得出,他刚来,而且赶的路也长。
我吃力地挤了过去。
“多少钱一只?”
“一块。”
“一块?”
老农见我惊异地故意重复他的话,显得有点气恼了,嘴巴张开来,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又一收,咕哝一声,咽了回去。
我将我的小篾篓在他眼前晃一晃。
“刚买的。五角。全是母鸡。”
老农随便扫了一眼,头一扭,闷声说:“我的鸡,要一块。”
这句话,有效果。我对他的篾篓里兴趣顿时大增了。篾篓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小黄鸡。它们一见我,叫得更响了,声声都像在喊我。有两只还把头拼着命地抬起来,大大地高过了其他鸡。
“要那两只最高的。”我禁不住对他说。
老农头又扭了过来,打开篾篓的小盖子,一伸手就抓住了那两个最高的小家伙,然后麻利地一反手塞进了我的小篾篓。
“算你认得我的货。我的鸡是良种。”
我不搭理他,给他两块钱,转身出了大门架。
回到清冷的家里,小鸡的叫声更响了,叫声里夹杂着一种忧虑的成分。这时,我才意识到还没准备好窝呢。于是,立即翻箱倒柜,好一阵地左寻右找,找出一个大纸盒来,小鸡才算有了家。
小鸡到了纸盒里,还是那样东张西望,还是那样叽叽乱叫。我朝纸盒里扔了一把米。小鸡不叫了,却也不啄米,反而纷纷抬起头来,目光显得那样警惕,每一只都死盯着我,像在审视我的动机:这人为何要扔米?
我和小鸡开始相持,不知相持了几秒几分。终于,一只小黄鸡,啪地啄起一粒米。我刚想叫一声好,它又放回了原处。如此,反复几次之后,总算放心吞下去了。接着,其他那些小鸡也都跟着啄米了。啄着,嘴里还叽叽,发出欢快的叫声。
我禁不住摇摇头:这些小鸡,刚刚出窝,就已怀有疑心了。我只能说不可思议。
日头西落,暮云低垂,六只小鸡拥挤在纸盒的一个角落里。
挤到里面的,心安又理得,装出闭目养神的样子。外围的则焦躁不安,叽叽喳喳,不住呻吟,一个劲地往里钻,有时甚至跳起来踩到同伴的身子上。
我不明白它们在玩着什么鸡把戏。
蹲在一旁,仔细观察。
观察好一阵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了,原来它们是怕冷。
这些出壳不久的小鸡,身上只有一层绒毛,离开父母的羽翼温暖,还不适应春夜的寒气,只得相互挤在一起。挤在最最里面的总是两只稍大的麻鸡。不用说了,这两只,比起另外几只来,力气肯定要大些。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幅毫不留情的画面:强者得利,弱者受气。这幅画面虽然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弱肉强食,自然淘汰,我却有点于心不忍。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些出壳不久的小鸡。我决心想办法结束这种竞争的情形。现代人的思维方法使我想到了白炽灯。这是达尔文环球考察不曾具备的先进装置。我把一个点燃的灯泡吊着放到纸盒里,六只小鸡马上向温暖的核心扑过去,紧紧围绕在它的周围。那种强者得利的场面,那种弱者吃亏的状况,立即在我眼睛前面完全彻底消失了。
可是,这只是一方面。若论事情的其他方面,这种十分可怕的现象还是时常存在的。主要表现在吃食的时候。每只小鸡都想要独自占有全部食物。哪怕根本吃不了。为了缓和这种状况,我把食物四处撒开。于是,六只小鸡也就各占一块地盘了。割据形成了。体形稍大的两只麻鸡占据的地盘自然大些,而且时不时地侵犯其它小鸡的可怜地盘。冲突时常在发生。我也忙得老调停。可悲的是,成效不大。
一个月过去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自然竞争的丛林法则看来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两只体形较大的麻鸡突然变得萎靡不振,终日也是缩头拖尾,羽毛纷乱,像个醉汉,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无力争抢食物了,它们原来占据的地盘也在一天一天缩小。我有点暗自高兴了,以为是这两只麻鸡开始有了悔悟之心。然而,不想又过几天,其他几只小鸡的精神也是同样变得萎靡,也是同样不太吃食。这时,我才反应到:小鸡生病了!而且,体形越是大,病得也就越厉害。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突然变得毫无作用。我真急得团团直转,暗自高兴眨眼之间也就成了暗自悲伤。
我苦苦地思索对策,结果还是一筹莫展,幸亏老刘串门来了。老刘是我的老熟人,兽医总站的老医生,干兽医这一行,少说也有二十多年。老刘像个救世主,一看就说,毫不思索:“缺钙。缺钙。佝偻病。”
“佝偻病?所以,头就缩起来?”
老刘看都不看我,我的问题不值一答,指着两只麻鸡说:“这两只,最严重。你看——爪子都变形了。说不定,有骨折……”
“奇怪,越是鸡越大,也就病得越厉害。”
“越是长得快,也就越要钙,缺钙就越多。”
“都怪它们太贪吃,平常吃得太多了。”
“喂的东西太单调。”
“是不是要喂钙片?”
“光喂钙片还不行,还要吃维生素。维生素J更需要。鱼肝油也可以。”
“……”
遵照老刘的指示,我开始喂鱼肝油。
不需要我动手灌的只有两只小黄鸡。
一两周后,小黄鸡完全恢复正常了。“画眉”和“大头”也有了好转,开始进食了。唯独那两只稍大的原先一直称霸的麻鸡还是一点不见好转,甚至好像有所加重。不但不啄食,站都站不起,一副可怜相。凡是人见了都会同情的。可是,鸡作为一种动物却无丝毫同情之心。“画眉”和“大头”,两只小黄鸡,总是有意无意地啄这两只鸡几口。有时,干脆跳起来,那么一脚踩下去,踩到它俩的身上。两只麻鸡,无力还击,只能叽叽叽地叫,声音很微弱。没办法,我只好另找一个小纸盒,把这两只可怜的麻鸡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它俩投来感激的目光。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又过了一周。两只可怜的麻鸡总算开始啄食了。不过,还是站不起来。我把食物捧在手中耐心地放到它们嘴边,它俩才会啄啄停停,那个模样,艰难得很。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大约一个多月吧,两只麻鸡才真正逃过了死神的魔爪,留一条命,活了下来,又能站起来,走动觅食了,只是已经骨瘦如柴,成了体形最小的。
我又把这两只鸡放回原来的纸盒里。不想,它俩立刻遭到另外四只小鸡的攻击。攻击呈轮番,两只两只上。它俩连一小块地盘都无能力守住了。以前那种称霸的优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照我看这两只鸡面对这样一个环境已是无法生存了,只好又把它俩拿出放到另一个纸盒里。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来月吧,这两只鸡才算是真正恢复了元气,基本正常了。可是,却又莫名地染上了一种坏习惯,一到傍晚就开始叫,而且连续叫个不停,叫声里含有一种悲伤。我弄不清它俩是如何染上这习惯的,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进行了种种努力,想让它俩安静下来,比如多给一点食物,比如轻轻抚摸等等,结果仍是全不见效。我也没有办法了,只好听之任之了。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了叫声的含意。那天,傍晚,我为了清理盒内的鸡粪,暂时性地把小鸡全都放在了一起(平时我是在白天进行这项工作的)。结果:两只麻鸡的悲鸣立即消失了。它俩低下头,一下一下一下地蹭着另外四只的胸腹,那种亲热劲真无法言表。这时,我才明白了麻鸡傍晚悲鸣的缘故——因为见不到原先的伙伴。遗憾的是,“画眉”“大头”和那两只小黄鸡,只是高高地昂起鸡头,一点不领它俩的情。有时,甚至紧缩两翼,竖起颈毛,一脸凶相,无缘无故地啄几下它俩蹭腹的多情。
小鸡一天天长大了,翅膀上已长满羽毛,吃饱了就扑打翅膀,像学飞的小鸟一样。时间一长,就都能飞出那个纸盒了。我像治安警察一样,奔过来,跑过去,把它们捉回纸盒里。但这却是一种徒劳。我一离开,它们又从纸盒里飞出来。很多时候,我都是刚刚抓了这一只,那一只又出来了。急的时候,我就想:干脆盖上纸盒算了。可我马上又觉得这样做是不妥的,甚至还有点残忍。纸盒本身就已经像那牢房一样了,如果再盖住,不就成了棺材吗?我不忍心这样做。小鸡飞出来,抓回去就是。实在抓不住,就随它们了。让它们在外面逛逛,见识见识大千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显然,没有什么不好,它们只是好奇罢了。好奇心被满足之后,它们也就厌烦了,就会急急忙忙地回到那个纸盒里去。事情真是这样的:小鸡一点也不想摆脱纸盒的囚禁,争取什么平等自由,赢得什么鸡的尊严。这也许也就是所谓家禽的特性吧!
鸡的这种安分的特性以及能够守己的基因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我总喜欢追究一些看似毫无价值的问题,决心详细考察一下鸡是怎样变成家禽。于是,我就跑了起来,去了省里的图书馆(虽然作为下岗老人或者内退大叔来说腿脚应该已不方便),查遍所有相关资料,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字里行间压根没有这种光辉历史的记载。就连省里的高等院校所编辑的教科书里,也没给鸡的这段历史留下那么一席之地。要不就是这段历史还是尚待考证的历史。
人们特别关注的只有那么一小点:如何使公鸡多长肉,怎样使母鸡多产蛋。
我很为鸡抱不平。我又开始想入非非:认定鸡的那个过去就是天上飞的大鸟。那么究竟因为什么使鸡放弃自由的飞翔,成了任人管治的家禽?我想大概是因为:鸡在成为家禽之前,虽然能够自由飞翔,却为食物疲于奔命,而且常遭猛禽袭击,很难进行自我保护,尤其那些可怜的小鸡出壳大都遭遇不幸。于是,也就不得不寻找生命的保护伞。它们找过来,复又找过去,最终还是选择了人。尽管它们的这种选择逃脱不了死亡的厄运,好处却是显而易见:再也不用为了食物而日夜疲于奔命了。而且人类一般是不会伤害小鸡的,至于正在生蛋的母鸡那就更会受到保护。于是,鸡也就觉得:这就非常幸运了。于是,鸡就成了家禽。
人老了,走神总是难免的。由此,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些无关的事情。
小鸡,终于长大了,每只至少一斤多了,仍旧待在纸盒里,已经很不适当了。
不用鸡们提意见,我就决定改善条件,打算做个大竹笼子,提高它们的居住水平。
我是这样计算的:每只鸡,零点三,三六一十八,一点八平方米。
要知道,这对我,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不得不为此忙忙碌碌,东跑西奔。只是不管怎么说,竹笼还是做好了。
鸡迁新居的那一天,我高兴得像过节。
鸡却不高兴:它们个个夹紧翅膀,在竹笼里走来走去,东啄啄,西敲敲,使劲挑着我的毛病。
好在我已是个老人(不再像什么大叔了),已经见过好多事情,不会计较它们的无理以及它们的傲慢无情,还是照常一天三次格外精心地喂养它们。
转眼到了十月份。鸡有半岁了。
四只麻鸡和一只黄鸡成了漂亮的大姑娘。另外那只小黄鸡成了一个小伙子。它们经过两次换毛,完完全全变了模样。两只麻鸡成了黄鸡,颈项尾部夹杂着少许黑色的羽毛。“画眉”成了一只花鸡,既有黑毛,又有白毛,还夹杂着一些金毛。“大头”竟跟公鸡一样披着一身火红的羽毛。
我进一步提高了它们应有的居住水平,将家里的唯一凉台完全彻底让给它们。我再忙也要抽空去凉台上看望它们。它们跟我已经很熟,我就像是它们的亲人。我到凉台上去的时候,六只鸡都扑打着翅膀,对我表示极大的欢迎,逃开躲避的那种现象已经很少发生了。我想如果换一个人来到这个小天地里,它们是否也会同样持这种欢迎的态度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或者,准确一点地说,我不愿碰到这个问题。
十一月的下旬的时候,母鸡开始下蛋了。一天少也有四个,多的时候是五个。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久而久之,我逐渐产生了吃腻了的感觉。我问自己我养鸡就是为了吃蛋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并且还要在后面补上这么两个字——吃肉。
我完全是老糊涂了。雄鸡喔喔的报晓声,母鸡下蛋的高歌声,搅得我无法安宁了。
后来,上下左右的邻居,尤其是那些大姐大嫂,居然全部联合起来,向我提出严重交涉,说我躲在家里养鸡违反了什么治安条例(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可怕的禽流感)。我心里乱成一团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当初真不该养鸡的。但是,要我把它们全都一刀宰杀了,又简直是不敢想象的。
我不知道如何才好。
再后来如何,我不想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