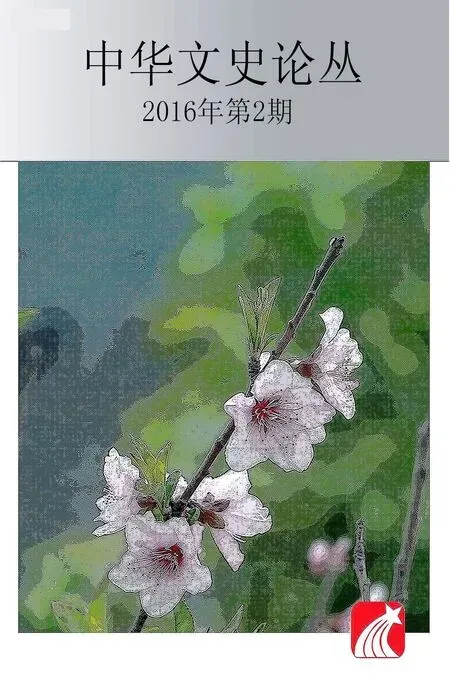從經録到僧傳:《高僧傳》之編纂成書及學術背景考察*
劉學軍
從經録到僧傳:《高僧傳》之編纂成書及學術背景考察*
劉學軍
以慧皎《高僧傳》編撰的材料來源爲考察的立足點,由此不斷上溯,尋繹《高僧傳》在體例上的源自和精神上的指向,可以清理出一條“道安—僧祐—寶唱—慧皎”的演變線索。這條線索的意義在於能夠揭示《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關鍵消息:經録是僧傳得以孕育成型的“母胎”,從經録到僧傳,是佛教經籍背後著譯者角色,亦即人的地位,日漸凸顯的過程;《高僧傳》書寫範式的成立正是佛教內部從經典到人、從古到今學術嬗變的必然結果。
關鍵詞:經録 僧傳 《高僧傳》 書寫範式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學視域下的中古僧傳書寫研究”(編號:1 5 CZW0 1 7)階段研究成果。
一 引 言
對於《高僧傳》研究來說,慧皎本人所撰寫的序言,①慧皎《高僧傳》之序録,通行本一般在卷一四,惟明本位於卷第一之首(序與録倒置)。是一份比較重要的文獻。今人欲究明《高僧傳》成書的各方面問題,均可據此以爲津梁。在這篇序中,慧皎詳述了編撰此書的各種信息:大到編撰意圖、體例設置,小至書名冠置等等。其中,讓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慧皎除去交待了上述信息外,還不厭其煩地歷數在他之前諸多傳記作品的種種“不足”。該部分內容如下:
衆家記録,敍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敍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游方一科。沙門法進,乃通撰傳論。而辭事闕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録》、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録》,並傍出諸僧,敍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録。既三寶共敍,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琅瑘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下,過相揄揚;或敍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删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①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523—524。
在這段敍述中,慧皎詳細地羅列了之前“衆家記録”的作者、書名,以及具體的“不足”所在。②在致王曼穎的書信中,慧皎也說“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高僧傳》卷一四,頁554。我們以爲,就情理而言,這種通過批評前代同類作品來建構自我合法性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一種較爲常見的現象。但是,其中卻有一處令人費解的地方,即慧皎在逐個批評劉義慶《宣驗記》和《幽明録》、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俊《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等這些作品後,對於“逮乎即時”的這個“繼有作者”,卻沒有指名道姓,明確指明批評對象的身份。這個疑惑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現在大家已經基本上認定,慧皎所未指名道姓的這個批評對象,其實就是《名僧傳》的作者寶唱。③如湯用彤徑直認爲慧皎所評的這個“同時作者”係寶唱,見氏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17;紀贇則仔細比照慧皎之於這個“繼有作者”的批評——一褒貶適當、二不夠簡練、三沒有記録高蹈遠行的抗迹之奇,將之落實爲寶唱的《名僧傳》,見氏著《〈高僧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72—74。事實上,我們看這篇序言後面對於“名僧”、“高僧”的斟酌,以及王曼穎致慧皎的信中明確標舉出“唱公纂集”,也不難推定出這一點。可由此卻帶來一個頗啓人疑竇的問題——爲什麽慧皎不徑直揭出,卻要這般“遮遮掩掩”?有什麽難言之隱嗎?
迄今爲止,關於這個問題,就筆者目力所及,似乎只有紀贇曾給予詳細的考察。這裏可以首先對他的觀點加以概述。紀氏認爲,寶唱在慧皎之前編纂了《名僧傳》,該書材料較之後者更加豐富(《名僧傳》共三十卷,約是《高僧傳》的兩倍)。因此,如果就純粹保存文獻的目的來看,《高僧傳》編撰的意義是不大的。在這種情況下,慧皎爲尋求自己撰著的合法性,亦即合理性、必要性,他只能“精明”地“利用僧伽的道德操守作爲突破點一舉攻陷了《名僧傳》辛苦建立的城池”;①紀氏並沒有說明清楚“僧伽的道德操守”爲何,或指寶唱“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而這一點違背了“僧伽的道德操守”?他又認爲,就實際而言,兩部僧傳收録的標準並沒有多大的區別,《名僧傳》所載的大部分內容均見之於《高僧傳》,因此,慧皎所批評的主要是《名僧傳》的題目而非內容——“名僧”與“高僧”的爭議,適應了當時玄學“名教”與“自然”爭論的社會思潮大背景,又與其時僧團組織的危機緊密相關。紀氏從“僧”與“沙門”的語義指涉上推斷,慧皎、寶唱均選擇以“僧”這一指涉“羣體”意義的字眼來作爲著作的題目,他們的動機便是力圖借傳記的編纂樹立僧人典範,進而“維持僧團內在凝聚力”。②紀贇《〈高僧傳〉研究》,頁72—88。
應該說,紀氏的研究既注意到了慧皎在《高僧傳》編撰時所面臨的合法性“困境”,也留心“名僧”與“高僧”名稱之爭背後,其實隱藏着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以及其與玄學思想背景的關聯。其關於“僧”與“沙門”的語義指涉上推斷,也較爲新穎,可備一說。③實際上,紀氏此處的推斷仍有值得進一步推敲的地方,如紀氏認爲一部傳記著作如果用了“僧”字作爲題目,即意味着這部作品中的傳主“都是某一特定區域裏某一特定僧團的僧人傳記”,因此,《高僧傳》確切的名字應該叫做《高行沙門傳》——我們以爲此論可能值得進一步思考,因爲:(一)固然像《東山僧傳》、《廬山僧傳》這兩部作品記録的是某一特定區域某一特定僧團(東山僧團、廬山僧團)的僧人傳記,但是諸如《高逸沙門傳》、《游方沙門傳》這類我們現今已經無法見到全貌的僧傳作品,“顧名思義”覺得它們應該以“高逸”、“游方”等類型作爲僧傳選材的標準外,我們又如何能排除它們不也是以“某一特定區域裏某一特定僧團”爲書寫對象呢?傳記選材的類型標準與地域標準並不總是相互對立的;(二)固然“僧”與“沙門”兩詞的原始含義以及早期漢地經典中用法,分別指涉羣體和個體,但這是否意味着這兩個詞在中土的語義指涉就一成不變,或者說,在實際的使用中,無論自覺或不自覺,人們都嚴守着這來自異域原始的語義規則呢?事實上,我們如今看到的情況是:一方面初期佛教典籍在語彙的使用上,往往與印度西域的原始含義有所偏差,這也正是道安“五失本、三不易”原則提出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在魏晉六朝,無論內典還是外典,我們隨處可見“僧”這個字眼被施於僧人個體之上。總之,這項研究,取徑較爲宏闊深入,結論也比較富於興味。然而,我們覺得,他似乎仍然未能對寶唱所持的矛盾態度作出全面的解釋——用爲了尋求撰著的“合法性”這個理由,來解釋爲什麽慧皎會有上述的那些批評(即紀氏所指的對於“僧伽的道德操守”的批評),這或許能夠講得通;但是,又該如何解釋爲什麽慧皎在批評的時候不像對待其他傳記作品那樣“指名道姓”呢?
我們以爲,對於這個問題的全面回答,可以折射出《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大命題,因此,意義不容小覷。本文將以對該問題的再思索爲解讀的邏輯起點,考索《高僧傳》的材料來源、編撰方式、精神指向等方面的問題。希望能夠從學術傳統的流變中,觀照《高僧傳》的編纂成書情況及其特殊的學術背景。
二 慧皎的“欲說還休”
(一)寶唱生平及晚年的風波
讓我們先從寶唱撰著《名僧傳》的具體歷史情境說起。
現存關於寶唱生平較早也是最詳細的文獻,當數道宣《續高僧傳》中的相關記載。道宣在該書卷一“譯經篇”專門爲寶唱設立專傳。①見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譯經·寶唱》,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7—11。白化文、李鼎霞曾以此傳爲主,參稽諸家經録、僧傳、史志等,還原寶唱的生平著述情況,大體平實有據。①白化文、李鼎霞《〈經律異相〉及其主編釋寶唱》,《國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575—596。我們可以據此,再參以其他後來的研究成果,按照編年的方式,將寶唱的生平經歷大致梳理如下:
宋泰始二年(466)至三年之間,出生吴郡;
齊永明二年(484)至三年之間,十八歲,投僧祐門下,住莊嚴寺,習經、史、《莊》、《易》,皆略通大義,有聲宗嗣;
建武二年(495),高堂喪事料理畢,即離都雲遊五年,後中風疾,外加遭齊梁鼎革之亂,遠播閩越;
梁天監四年(505),返都,爲當時名寺新安寺主;
天監四年至天監十七年,頗受梁武帝寵眷,成爲御用僧人,從事大量佛經編纂工作,包括:(1)天監五年到普通元年(520),奉敕列席僧伽婆羅爲譯主的譯場,擔任筆受,共譯出十一部三十八卷,參譯者有慧超、僧智、法雲等,皆一時之選;(2)天監四年至七年間,奉敕參加建元寺釋法朗爲《大般涅槃經》作“子注”工作;(3)天監七年十一月至天監八年四月,奉敕在定林寺同僧亮、僧晃、劉勰等參加僧旻主編的《衆經要抄》八十八卷的編纂工作;(4)天監十四年至十六年間,《名僧傳》初稿撰成;②白化文、李鼎霞將《名僧傳》撰成的時間定爲天監十五年(516)至十六年,黃先炳定爲天監十四年至十五年間,但蘇晉仁則采信《歷代三寶記》“天監十八年”的說法,劉颻的看法同。參黃先炳《〈高僧傳〉研究》,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頁29—31;蘇晉仁《佛教文化和歷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10;劉颻《釋寶唱與〈比丘尼傳〉》,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頁26—28。我們依白、黃兩家意見。(5)天監十五年至十六年,奉敕主持編纂《經律異相》等八部書,撰成《比丘尼傳》;(6)天監十五年至十七年,奉敕在安樂寺釋僧紹的基礎上修纂皇家《華林佛殿衆經目録》,功畢而雅愜時望,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又製作副本,以用供上;
天監十七年,唱師僧祐入寂;
普通元年(520)至三年,敕令開善寺釋智藏編纂《義林》八十卷,寶唱預其事;
普通三年至四年,寶唱似因“腳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敕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朝廷的司法處置),但旋即又敕令“依律”、“以法處斷”(僧律加國法的判決),然而“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判決很嚴厲,“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
普通四年至五年,寶唱在上述官私的催逼中,勉力續補《名僧傳》,臨被發配之時,以書奏聞朝廷,皇帝敕令停擯,轉爲太子蕭綱服務;
普通七年,僧正慧超亡;
中大通四年(532)至六年,協助蕭綱編纂佛教類書《法寶聯璧》二百二十卷(含目録二十卷);
中大通七年及以後,“不測其終”。
在寶唱的一生中,晚年涉入被擯風波,實在是一件令人覺得蹊蹺的事情。傳記對此頗爲晦澀——寶唱因治療腳氣病而開罪官方,本擬貶謫,旋即又敕令依僧律處置,但來自佛教系統的力量卻“任情乖旨”,試圖擯徙,然而,不多久,因著作奏聞皇帝,官方又敕令停止了擯事。在這一系列的起伏中,寶唱本人似乎處於各種勢力的激蕩之中。對於一個極受皇家重視的僧人來說,命運由顯赫一時到最後“不測其終”,實在反差甚巨。鑑於史料的缺失,我們無法進一步究明其中的實情。但是,揆之常理,治療疾病作爲一個理由,用以解釋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顯然是不夠充分的。白化文、李鼎霞推測其中的原因,認爲:南朝重門第,當時圍繞在梁武帝周圍的僧人均出自高門(如僧旻是孫權之後、法雲是周處七世孫、智藏出身吴郡顧氏且爲宋明帝的出家替身),只有僧祐出身不高。不過,僧祐在齊世即已成名,成就多方,又兼弟子衆多,成爲一時僧望所在。在這種情勢之下,出身寒微的寶唱,所能依靠的自然是其師僧祐的庇護,當然還有自己的撰作才華。但是,一旦僧祐逝世,唱則無依矣,使人不能不興“才秀人微”之嘆。①白化文、李鼎霞《〈經律異相〉及其主編釋寶唱》,頁589。我們以爲這樣的解釋,頗具啓發性。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加以補充和推測:除去出身寒微外,寶唱少時“傭書取濟”的經歷,和投入僧祐門下後,經、史、《莊》、《易》的學術涉獵,以及固執於家室的做法,都似乎與其時的僧團風氣產生齟齬,以至於時人“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然而,他卻憑藉良好的文獻整理才華,以及僧祐的提攜,②天監四年(505),寶唱結束播遷生涯,返還都下,任新安寺主。而新安寺乃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母所造,歷來寺主多爲名僧,如僧遠、法瑤、顯亮等(《高僧傳》卷八《僧遠傳》)。寶唱能夠在離開多年之後,甫一回來,即被委以此職,不能不讓人聯想,可能是得到了其師僧祐的提攜。成功地引起梁武帝的重視,並最終得到了管理皇家經藏的職務。這個時候,他似乎已經從純粹的文獻整理專家,一躍而成爲皇帝身邊的親信。③《續高僧傳·譯經·寶唱》記述天監“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録,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袠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頁8。揚都安樂寺是王坦之捐獻建設而成,歷來由名僧掌持。僧紹也是一時之名僧,故而蕭梁統一後,開始是選擇他來編撰經目,但武帝對他的成果不甚遂意。等到寶唱運用其傑出的文獻才華,在僧紹的基礎上,重加編撰的時候,方令武帝十分滿意,並因此得以掌管皇家華林園寶雲經藏。華林園是梁武帝講論佛法、翻譯佛經的專門場所,能夠執掌這樣一個場所的經藏文獻,非皇帝親信之人不可出任。在寶唱之前,似乎也只能由僧正來擔任。也正是這樣,寶唱似乎已經危及了蕭統身旁原先那些權僧們比如僧正慧超的利益,因此,當天監十七年,僧祐入寂後,即便還可能有蕭統對於寶唱才華的重視,但畢竟大樹已倒,於是三四年後,以前積蓄的矛盾釋放,與之相對立的權僧們終於找到一個理由,來施以報復。《續高僧傳》對此的描述是“僧正慧超任情乖旨”。這是很富意味的話,大致可以揣測出的信息是,也許之前官方原本意圖施加於寶唱的懲罰是不那麽激烈的(無論“導火索”是不是因爲腳氣疾病而擅自離開),但慧超卻借着這個機會,大大地宣洩了自己的私憤:“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即令寶唱向京師的各大寺逐個懺悔罪過,然後永遠逐出。無疑,這是相當極端的做法。棄則棄矣,還得首先向有關方面懺悔,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寶唱與京師各大寺之間的矛盾該有多麽强烈。可是後來他的命運卻戲劇般地峯迴路轉,原因也許是蕭統憐惜寶唱的才華,並沒有讓慧超等人擯除的想法成爲現實,但作爲一種“折衷”,寶唱也便失去了靠近權力中心的位置,轉而爲太子蕭綱服務,做的也只是他擅長的文獻翻譯整理工作,“有敕停擯,令住翻譯”。
以上,當然是我們根據極其有限的材料引發出來的推論,結論雖然可能與歷史實情有所出入,但卻相對比較有力地揭示出這樣一點,即寶唱的被擯極有可能涉及幾方力量的博弈,絕不是因治療腳氣病而開罪官方那麽簡單。
(二)慧皎的顧忌
接下來,我們再來考察慧皎《高僧傳》對於寶唱《名僧傳》的態度問題。這個問題,是下文討論《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核心,必須先予以釐清。
還是由於材料缺乏的原因,我們對於慧皎的生平經歷所能復原的程度仍然不太理想。至於《高僧傳》這部書的編撰情況,尤其是它的編撰時間,仍然存在各種不同的意見。
關於《高僧傳》編撰時間的界定,最早見之於智昇《開元釋教録》卷六,作“序録一卷、傳十三卷,共成十四。天監十八年撰,見《長房》、《內典》二録”。①《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38下。下簡稱《大正藏》。實則,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並未注明《高僧傳》編撰時間,道宣《大唐內典録》亦未注明(《內典録》與《房録》內容幾乎一致,可能抄自後者)。那麽,智昇的說法,大概是受慧皎“自序”的影響。《高僧傳》“自序”云:“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一十四卷,備贊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②《高僧傳》卷一四,頁524—525。智昇可能認爲慧皎序中的意思是這個版本已經是定本了,而這個定本,最晚的時間節點是天監十八年,因此,這一年可能就是《高僧傳》的撰成之時。
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在“《高僧傳》十四卷”目下,引的是《開元録》,亦持“天監十八年”之說;在“《補續冥祥記》一卷”目下,詳細考證了慧皎與王曼穎之間的往復書信,他舉《梁書》卷二三《南平王偉傳》爲證,說王曼穎死後,其友人江革前往弔唁時猶稱蕭偉爲“建安王”,實際上蕭偉於天監十七年(518)三月,由“建安王”改封“南平郡王”,因此,可知王曼穎的死,當不可能在天監十七年之後。③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二十五史補編》(四),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5367下,5382上。
曹道衡、沈玉成認爲《梁書》所記官爵往往混亂,因此姚氏的判斷有誤,並推測天監十七年去世的或爲王曼穎之父王琰,所以王曼穎在致慧皎的信中自稱“孤子”。據此,可以推斷《高僧傳》的殺青之日,當在普通年間。④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學史料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642—643。
蘇晉仁亦據《梁書》卷二〇《南平王偉傳》、卷三六《江革傳》、卷二九《南康王績傳》,以爲王曼穎的逝世,在天監十八年到普通四年之間,因而,《高僧傳》的撰成,最晚不得遲於普通四年(523)。又認爲《高僧傳·興福·法獻》中有佛牙以普通三年正月遺失之語,當是此書最末之紀事,理應距離完成時間不遠,因此,大約完成在普通三年或四年。①《高僧傳》卷一三,頁488;蘇晉仁《中國佛教經籍》之“高僧傳”部分,載《中國佛教》(四),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9年,頁151—157。
黃先炳以慧皎應該看過寶唱《名僧傳》這一點爲前提,先從《名僧傳》的編撰時日考證入手,間接推斷《高僧傳》的撰成之日。他認爲《名僧傳》當成書於天監十四年至十五年間,而不是像《房録》所記述的,該書是梁武帝於天監十八年“敕沙門寶唱撰《名僧傳》三十一卷”。這樣的話,對照推下去,慧皎在寫《高僧傳》“序”的時候,纔能有足夠的“時間差”(如以天監十八年計算的話,距離天監《名僧傳》成書,約有三至四年的時間),看到《名僧傳》的本子,也纔能據此提出批評。至於如何解釋慧皎“自序”中表示其紀事“終於天監十八年”(實際上,我們如今看到的傳記中卻有天監以後事,如普通三年佛牙遺失事),黃氏的解釋是,《高僧傳》的成書,如同僧祐完成《出三藏記集》之後又繼續修訂一樣,也經歷了一個不斷增補修訂的過程。②黃先炳《〈高僧傳〉研究》,頁28—31。
學問之前進,理應後出轉精。今天再來考究這個問題,一方面,我們以爲黃先炳的說法立足對於前人的辨析,思慮相對更周,因此也較爲可信;另一方面,我們也覺得應該在一個更大的學術、歷史情境中加以考量,這樣纔能避免陷於諸材料牴牾牽合的泥潭之中,難以通脫。
綜合以上各家的意見,我們認爲慧皎《高僧傳》“自序”的撰作時間最早節點應在天監十八年,最晚節點應在普通四年。這樣的時間界定,雖然依舊顯得寬泛、不夠精確,但是,卻堅强地辨明一個基本事實,即在慧皎將《高僧傳》的初期版本(亦即寫下“自序”的那個版本)拿出來請人如王曼穎批評的時候,從時間上說,已經在天監十七年僧祐逝世之後。那個時候,如前一部分所推測,寶唱已經失去了皇家最强有力的庇護,其晚年的遭遇,也呈現風雨欲來之勢。
我們看慧皎在“自序”中,對於寶唱的名字那麽的諱莫如深,從情理上說,這極有可能表明,寶唱當時的境遇已經非常窘迫。對於遠離都城寺廟(會稽嘉祥寺)的一個不甚知名的僧人(慧皎)來說,也感到各種關於言說寶唱的禁忌。①由此,反過來,也可以更加證明慧皎的那個帶有“自序”的《高僧傳》版本,應該完成於寶唱遭受“風波”的那幾年,即天監十八年到普通三年。
這樣,對於慧皎來說,一方面,他在很短的時間內編撰《高僧傳》,需要依靠之前的同類作品作爲材料憑藉的基礎——《名僧傳》以其材料的宏富,自然不能忽視,事實上,他也的確大量地加以借鑑。②據黃先炳的統計,《名僧傳》有近百分之八十的傳主(含附傳)見之於《高僧傳》。氏著《〈高僧傳〉研究》,頁37—47。因此,他在確立自己編撰《高僧傳》的合法性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寶唱和他的《名僧傳》,這畢竟是他材料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懾於彼時寶唱所處的特殊境遇,慧皎又不得不小心地隱藏自己的材料的源自,生怕觸及什麽禁忌,更有甚者,還要對寶唱的《名僧傳》加以“指責”。這不僅僅是爲了確立自己書寫的合法性,也許更是爲了表明一種立場。
這裏有一點需要加以說明,即在慧皎對於《名僧傳》的指責中,說它“或復嫌以繁廣,删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進而認爲“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③《高僧傳》卷一四,頁524。這種高揚“高蹈”姿態的表述,看上去,好像慧皎是站在與官方、皇權相對立的位置(這個位置在當時皇權高於僧權的情況下,顯然並不利於自己)。但是,如果加以深究,便可以發現,其實在慧皎《高僧傳》中,恰恰就有很多不守佛教戒律的僧人(如竺法度、僧宗等)以及與達官權貴交遊甚密的僧人(如支道林、竺法深等)。因此,慧皎“自序”中所標舉的“高蹈”精神,實則只是一種標榜,或者說是一種理想。他的意圖也許不在於或不僅僅在於自己要針對性地增加“高蹈獨絕”的僧人傳記,而是想借此宣示一種態度,即自己的立場是有別於寶唱者。或許惟其如此,纔能保證自己《高僧傳》的編撰得到來自僧團力量(他們顯然也是與寶唱處於對立的位置)的認可。這說到底便是一種基於具體情境,對“合法性”的尋求,是慧皎書寫的一種策略。而當《高僧傳》撰成後,“通國傳之”、“即世崇重”,①《續高僧傳·義解·慧皎》,頁193。相比之下,《名僧傳》則慢慢湮滅無聞,②最早隋法經《衆經目録》著録“三十卷”,《房録》著録“并序録目三十一卷”,《內典録》同《房録》,到了《開元釋教録》,就不見了該書,原因是“《名僧傳》等七部非入藏,故闕而不論”。《隋書·經籍志二》、《舊唐書·經籍志上》著録“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三》著録“二十卷”,唐以後公私書目均不見著録。由此可見,該書唐代即不受人們重視,難得進入大藏,從而淹沒無聞了。今人欲窺其面貌,只能間接通過日本沙門宗性從笠置寺福城院過録的《名僧傳抄》了,見《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77),頁346中—362下。下簡稱《卍續藏經》。這種反差,似乎也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這種策略的成功。③當然,這種成功也不能全然歸功於此,事實上,慧皎《高僧傳》本身在編撰理念、方法、手段等方面上的特色,更是其得到成功的主要原因。下文,我們將在討論《高僧傳》書寫範式之成立過程中,進一步予以揭示。
以上,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將寶唱的生平經歷加以羅列,無非是想把慧皎對於寶唱的批評,還原到當時的歷史情勢中去,從中尋繹這些批評的具體所指,以及隱含的策略所在。我們看到,慧皎在《高僧傳》“自序”裏的欲說還休,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是一種“影響的焦慮”。這種“影響的焦慮”,固然有着特定的話語情境,但是,卻反映了寶唱《名僧傳》與慧皎《高僧傳》之間,存在着一種難以割捨的關聯。那麽,這種關聯具體體現在何處?這種關聯對於《高僧傳》書寫範式之成立有什麽影響?都是值得進一步從縱深層面加以考慮的。
三 從經録到僧傳
(一)慧皎的取材
慧皎在《高僧傳》“自序”中,關於其材料的來源,有這樣的表述:“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録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古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①《高僧傳》卷一四,頁524。這段話,呈現給我們一種慧皎編撰《高僧傳》自出機杼、取材多樣的表面印象。
然而,細細思量,卻能發現這種印象其實並不可靠。原因如下:
(1)從情理上講,如我們之前所已經提示的那樣,年紀輕輕的慧皎,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編撰如此長時段、多人數、條例分明、結構合理的著作,②今本《高僧傳》所附龍光寺僧果的附記云慧皎法師“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年二月舍化,時年五十有八”,梁甲戌年,即5 5 4年,如僧果記述慧皎五十八歲無誤的話,則可推知,慧皎生於齊建武三年(4 9 6)左右。這樣,慧皎《高僧傳》編撰時的年齡,以最早(天監十八年)至最晚(普通四年)的撰作時間截點算,當在二十三歲至二十七歲之間。道宣《續高僧傳·慧皎》沒有記述皎少年的具體學識素養情況(只概云“學通內外,博訓經律”),我們據情理推,編撰如《高僧傳》這樣一部時限長至四百五十多年、人數多達四百多人(以慧皎“自序”中的數字統計,“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條例分明、結構合理的著作,其年齡可能不會早於二十歲。如此,則慧皎編撰《高僧傳》的用時,約只有三年至七年。單靠一人之力,完成的可能性應該是不大的,他需要依靠之前同類作品詳備的材料作爲堅實基礎。其工作與其說是“創作”,毋寧說是一種“編輯”——如其在“自序”中所言,“今止删聚一處,故述而無作”;
(2)就事實而言,經過比對,我們不難發現,其在材料的來源上,受寶唱《名僧傳》的影響甚巨。如黃先炳曾將《名僧傳》與《高僧傳》做過詳細的比對,確證了這一點:“《名僧傳》收録傳主四百二十二人,其中超過半數,即二百二十四人見於《高僧傳》正傳,另有近三成即一百一十二人見於附傳……《名僧傳》正傳所載的四百二十二人,有三百三十六人見於《高僧傳》,比例已近百分之八十。”①黃先炳《〈高僧傳〉研究》,頁46。
這樣,我們可以說,慧皎編撰《高僧傳》並不是空無依傍的,他的主要材料來源應是之前的同類作品,即所謂的“羣作”、“雜録數十餘家”。至於“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特別是“博諮故老,廣訪先達”等等,由於它們各自關於僧人的材料既少且不詳備,②這是由於該類文獻自身性質使然,比如,中國正史傳統裏,本來對於僧人的記述就屈指可數,地理類的典籍(如《水經注》、《洛陽伽藍記》等),也以地理爲主要內容,旁及僧人事迹,並不詳細。故只可能起到“校其有無,取其同異”的輔助校勘功用,並不構成取材的主要來源。而在這些同類作品中,雖然各有各的不足,諸如敍述有偏、繁簡不同、文體未足等等(見前引慧皎“自序”的具體批評),但他還是不同程度上地予以利用。其中,寶唱的《名僧傳》則是他最主要的材料來源。①我們目前還找不到具體的材料,能夠有助於說明慧皎什麽時間、通過什麽途徑看到《名僧傳》。大概在普通四年(523)至五年間,陷於風波之中的寶唱,將陸續訂補的《名僧傳》上奏到朝廷的時候,可能憑藉梁武帝或其他力量,得以“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敕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續高僧傳》卷一,頁11。經若干年,已經逐漸流通到都城之外的會稽地區(在這個地區的僧團對於寶唱的排斥可能並不如京師地區那麽强烈)。當然,這其中,或許也不能排除慧皎私人“搜檢”之勤的可能存在。
事實上,慧皎的這種編撰方式,在當時並不是一種特例。《隋書·經籍志二》在定義“雜史”概念時就曾說:“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爲一書。”②《隋書》卷三三,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962。周一良在比較南北朝史學之異同時,也有這樣的判斷:
古人修史,基本史實的敍述大體因襲前人著作爲多。如袁宏《後漢紀》成書於范曄《後漢書》之前,而所記史事與范書無大異同,說明出自同一來源,而且取捨大致相近。又如范書中《光武本紀贊》有“系隆我漢”字句,及《章帝八王傳》中所謂“本書”,皆沿用《東觀漢記》舊文之明顯證據。甚至論贊某些詞句,亦沿襲舊史,如章懷注指出范本出於華嶠《後漢書》者即有多處。沈約《宋書》亦多本於徐爰等之舊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書。③見氏著《略論南朝北朝史學之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19。又,逯耀東對此也有所分析,參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5—56。
可以說,《高僧傳》的編撰也正是這種“史鈔”編撰風氣下的產物。④《四庫全書總目》卷六五將魏晉史鈔之風歸爲三類:一曰“以類相從”,衛颯《記史要言》、張溫《三史略》是也;二曰“專鈔一史”,葛洪《漢書鈔》、張緬《晉書鈔》是也;三曰“合鈔衆史”,阮孝緒《正史削繁》是也。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 9 6 5年,頁5 7 7下。
(二)寶唱的資源
接下去的問題是,寶唱的材料來源在何處?
前文我們在梳理寶唱的生平及晚年風波的時候,已經略略提及《名僧傳》撰作的時間和背景。現在,我們想進一步說明寶唱《名僧傳》的資料淵源。
如前揭所示,寶唱編撰《名僧傳》是一個不斷增訂的過程。從天監十四、十五年《名僧傳》初稿撰成,到普通四、五年寶唱將增補後的《名僧傳》奏聞朝廷,前後花費了約十年的時間。但是,該書最重要部分的完成,當以其天監十四、十五年初稿的撰成爲時間節點。亦即到此時,《名僧傳》的主體部分已經就緒,此後,只是不斷地小規模增訂而已。因此,從時間上說,《名僧傳》大體上的完備,當在天監十四、十五年左右。這樣的判斷,是基於如下兩點:
(1)《續高僧傳》記述寶唱天監九年因“先疾”復作,發願“搜括列代僧録,創區別之,撰爲部帙,號曰《名僧傳》”,到天監十三年的時候,就已經“始就條列”。這裏的“始就條列”,可能指的就是該書已經大體具備。退一步講,即便不是內容上大體完備,也應指該書編撰體例的確立。而就常理言,體例的確立,之於一本書的編撰,其重要性乃至在成書過程中所占的工作量份額,往往是巨大的。
(2)還有一個背景情況,即天監十七年,寶唱的老師僧祐去世,他失去皇權周圍重要的庇護,這種處境,導致他已經開始漸漸被疏離。一個比較明顯的表現是,天監十七年以前,《經律異相》、《華林佛殿衆經目録》等書的編撰都是以寶唱爲主持人,但是,在天監十七年之後,相關典籍的編撰活動中(如《義林》的編撰),寶唱已經只能廁身參與了。這種變化,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天監十七年以前寶唱所能享有的極其寬鬆的典籍編撰條件,已經喪失。武帝的贊助、老師的扶持、以及提供各種文獻材料的保證,均已大不如前。如果此時,寶唱還沒有完成《名僧傳》的主體部分,很難想象,在接下去即將面對的風波下“官私催遍,惟日弗暇”,他還能有足夠的條件來提供支援。①雖然《續高僧傳》卷一說寶唱“晝則伏懺,夜便纘録”,極盡黽勉之力,但我們以爲這種勤勉堅忍,主要還是體現在他對於既已完成的《名僧傳》主體部分的不斷增訂過程中。
如果上述的推測不誤的話,那麽,從時間上說,寶唱《名僧傳》主體部分的編撰,其實是與他本人在天監四年至天監十七年間,受梁武帝寵眷,成爲御用僧人,從事大量佛經編纂工作,呈現相重合狀態——這種情況,進而提示我們注意到,寶唱《名僧傳》的編撰與其佛教文獻整理工作可能存在着極大的關聯。那麽,寶唱的佛教文獻整理工作與《名僧傳》編撰之間有沒有關聯?如有,具體體現在何處呢?讓我們先具體考察一下寶唱的佛教文獻整理工作的實際情況。
道宣在《續高僧傳·譯經·寶唱》中的評價是較爲全面的:
(梁武帝)下敕令唱總撰集録,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汗,淺識難尋,敕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纘《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十四年,敕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敕唱重撰,乃因紹前録,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袠四卷,雅愜時望。遂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敕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①《續高僧傳》卷一,頁7—8。字下點爲筆者所加,下同。
在這段評述中,道宣不止一次地强調寶唱“部類區分”、“綴比區別”、“注述離合”,而且這些評價,總是直接指向寶唱所編撰的類書性質著作“類《遍略》之流”,此《遍略》乃指天監十五年,梁武帝敕徐勉等人編撰的大型類書《華林遍略》六百餘卷。如將近百卷的“集録”(具體名稱未知)、二百餘卷的《法寶聯璧》、②《法寶聯璧》雖然成書於被擯風波之後,但蕭綱看中的正是寶唱一直以來“綴比區別”的文獻整理能力。五十五卷的《經律異相》。③《經律異相》的成書,乃是由於寶唱撰作《華林佛殿經目》“注述合離,甚有科據”,讓梁武帝很滿意,所以纔在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之外,又敕令編撰此書。因此,“注述合離,甚有科據”這樣的評語,也適用於《經律異相》。至於該書的類書性質,參白化文、李鼎霞《〈經律異相〉及其主編釋寶唱》,頁575—596。可見,在道宣的印象中,寶唱的文獻整理能力集中體現在其對於佛教類書編撰過程中的傑出的分類能力。“區分”、“區別”、“離合”,講的都是類書將所承載的知識信息按照一定的標準(“部類”),加以分別、歸類與整合(“綴比”、“注述”)。這也正是中國古代類書編録方法的一般形式。
試看《名僧傳》對於所載録僧人的分類情況:

表一 寶唱《名僧傳》載録僧人分類情況表④ 據宗性《名僧傳抄》,《卍續藏經》(77),頁346中—362下。

(續表)
寶唱將《名僧傳》中所收録的僧人區分爲七大類:“法師”、“律師”、“禪師”、“神力”、“苦節”、“導師”、“經師”。其中,“法師”、“律師”、“禪師”、“神力”四類,因爲涉及中土域外僧人兼有,所以各自內部均予以區別。特別是在“法師”一類中,在區分了“外國法師”、“中國法師”之外,又進而在“外國法師”下面分出“外國法師”和“神通弘教外國法師”兩小類,在“中國法師”下面分出“高行中國法師”、“隱道中國法師”和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法師”三小類。①紀贇將《名僧傳》的分類概括爲“兩層結構”,實際上,照“法師”這一類的情況看,應該是“三層結構”分類。見氏著《〈高僧傳〉研究》,頁121。“苦行”一類,又區分爲“兼學”、“感通”、“遺身”、“宗索”、②“宗索”不好理解,蘇晉仁以爲“索”通“素”,“宗索”即“宗素”,也就是茹素的意思。見氏著《佛教文化與歷史》,頁112—114。“尋法出經”、“造經像”、“造寺塔”七項。
應該說,這是一個多層次、寬範圍的分類方法,幾乎涵蓋了當時僧人羣體的所有類型。既從整體上合理地區分了僧人的身份(第一層次的分類),又照顧到了本土域外的出身差異以及更細微的特長區別(第二、三層次的分類),因此,讓人對於寶唱的分類才華特別印象深刻。之後慧皎在編撰《高僧傳》所確立的“十科”分類法,即是以此爲基礎而創立的。③慧皎的“十科”分類法,也是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高僧傳》“唱導篇”之論曰:“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導二技,雖於道爲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頁521。“卻尋經、導二技”,湯用彤本無“導”字,據《大正藏》(50),頁417下—418上補。
這樣,我們將後來道宣對於寶唱佛教文獻整理才能的評判,和寶唱《名僧傳》的實際情況加以比照,便可以看出,寶唱實則將自己在佛教文獻整理中的“分類”才華,遷移到了《名僧傳》的編撰中了。難怪《續高僧傳》在記述寶唱發願的時候,說“搜括列代僧録,創區別之”,包含的正是分類的意思。由此,正可透漏出寶唱佛教文獻整理與《名僧傳》編撰之間的關聯。
上面,還只是就體例而言。須知,對於一部傳記作品而言,除了有體例這些支撑整體的“骨架”外,尚需要具體鮮活的“血肉”。亦即對於《名僧傳》而言,合理的分類只是一端,另一端還需要有具體的關於每位傳主的生平事迹材料來填補。那麽,《名僧傳》編撰材料的來源何在?
我們以爲,自天監九年(510)寶唱發願編撰《名僧傳》,到天監十五年左右該書大體完成,其間凡五六年時間。這幾年,寶唱正處於其個人生涯的巔峯。在梁武帝身邊,深受重用,至少編撰了九部卷帙不等的著作:《衆經諸佛名》、《衆經懺悔滅罪法》、《衆經護國鬼神名録》、《衆經擁護國土諸龍王名録》、《衆經目録》、《供聖衆法》、《名僧傳》、《經律異相》、《比丘尼傳》等,①《周叔迦佛學論著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105—1106。又編撰皇家藏經《華林佛殿衆經目録》,並敕掌華林園寶雲經藏。鑑於這一時期,《名僧傳》還處於個人發願、私下編撰的狀態,②普通四年(523)至五年,《名僧傳》纔被奏聞朝廷,並得刊定。所以,從情理上推測,寶唱在面臨如此衆多公家任務的情勢下,他私下編撰《名僧傳》的材料獲取,極有可能是依靠他所接觸到的皇家藏經,以及實際的典籍編撰、整理(經録)工作。他應該沒有那麽多的時間與精力,在皇家僧團之外,逐個訪求傳主的事迹材料。③建武二年(495)至天監四年(505),寶唱將近十年的播遷生涯,雖然可能爲其搜集傳記材料提供可能,但是,一則那時他還沒有決定做這樣一部僧傳,一則他播遷的地域是閩越荒外之地,或許不能爲他提供豐富的僧傳材料。所以,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這樣的判斷,其實還很籠統。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寶唱在編撰《名僧傳》的時候,具體從哪些地方獲取傳記材料的呢?經録(如《衆經目録》、《華林佛殿衆經目録》)的編撰,當是其具體的取材所在。事實上,我們看《續高僧傳》中記述寶唱天監九年所發的兩個願望,其一是“遍尋經論,使無遺失”,其二是“搜括列代僧録,創區別之”。前者就是指佛教經録搜集與整理,後者便是指《名僧傳》的撰作。而這兩個同時因“舊疾復作”而生發的願望,若合而觀之,正暗示了經録與僧傳之間的關聯。而這就涉及寶唱的老師僧祐所起到的發凡起例作用了。
(三)僧祐的體例
道宣當是看過《名僧傳》的。他在《續高僧傳·譯經·寶唱》中,引了一些《名僧傳》序言的內容:
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嘆長懷,靡兹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①《續高僧傳》卷一,頁10—11。
這段序言,在贊頌了武帝的聖德,以及對於佛法的護持之外,感嘆佛教的事迹不能如外典那樣得到有效的整理保存,於是有意加以彌補。②這與天監九年(510)寶唱所發的願望之一“遍尋經論,使無遺失”,剛好對應。寶唱提到了他的老師僧祐,明確表示自己是踵武老師的。這裏,寶唱對於僧祐的贊頌,除了“道心貞固,高行超邈”的品質,還落實在著述方面,即“著述諸記,振發宏要”。
我們知道,僧祐被後人譽爲“法門之綱要,釋氏之元宗”,③《開元釋教録》卷六,《大正藏》(55),頁537上。其一生勤力於佛教文獻整理,集成經藏,④《高僧傳·明律·僧祐》謂:“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開廣,法言無墜。”頁440。著述極豐。⑤《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釋僧祐法集總目録序》中說僧祐的著述有《釋迦譜》、《世界記》、《出三藏記集》、《薩婆多師資傳》、《法華集》、《弘明集》、《十誦義記》,以及雜碑記等,總計“凡有八部”。而《大唐內典録》卷一〇《歷代道俗述作注解録》著録僧祐的著述則大致有:《出三藏記集》十六卷、《法華集》十五卷、《衆僧行儀》三十卷、《弘明集》十四卷、《世界記》十卷、《集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集諸僧名行記》三十九卷、《釋迦譜》十卷、《薩婆多師資傳》五卷、《十誦義記》十卷、《諸法集雜記傳銘》七卷,共計十一部二百餘卷(原文作“一百八十餘卷”,可能具體著作卷數著録時有誤)。可惜,其著作存世的,只有《釋迦譜》、《出三藏記集》和《弘明集》了。然而,非常幸運,大部分著作的序都被保存在其自撰的《出三藏記集》卷一二裏。我們據此,大致可以尋繹出僧祐佛教文獻整理的理念和方法。
兹將相關內容輯録如下,以便分析。(1)《法集總目録序》:
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訊衆典,披覽爲業。或專日遺飡,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竟晷。雖復管窺迷天,蠡測惑海,然遊目積心,頗有微悟。遂綴其聞,誡言法寶,仰稟羣經,傍采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顯明覺應,故序《釋迦》之譜;區辯六趣,故述《世界》之記;訂正經譯,故編《三藏》之録;尊崇律本,故銓《師資》之傳;彌綸福源,故撰《法苑》之篇;護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論。且少受律學,刻意毘尼,旦夕諷持,四十許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既稟義先師,弗敢墜失,標括章條,爲《律記》十卷,並雜碑記撰爲一帙。總其所集,凡有八部。①《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457—458。
(2)《釋迦譜目録序》:
爰自降胎,至於分塔,瑋化千條,靈瑞萬變。並義炳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故知博訊難該,而總集易覽也。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尋翫。遂乃披經案記,原獉始獉要獉終獉,故述《釋迦》譜記,刊爲五卷。若夫胤裔托生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遺法將滅之相。總獉衆獉經獉以獉正獉本獉,綴獉世獉記獉以獉附獉末獉。使獉聖獉言獉與獉俗獉說獉分獉條獉,古獉聞獉共獉今獉迹獉相獉證獉。萬里雖邈,有若躬踐,千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衆經,述而不作,庶脫尋訪,力半功倍。①《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59—460。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3)《世界記目録序》:
竊惟方等大典,多說深空。惟《長含》、《樓炭》,辯章世界,而文博偈廣,難卒檢究。且名師法匠,職競玄義,事源委積,未必曲盡。祐以庸固,志在拾遺,故抄獉集獉兩獉經獉,以獉立獉根獉本獉,兼獉附獉雜獉典獉,互獉出獉同獉異獉,撰爲五卷,名曰《世界集記》。將令三天階序,煥若披圖;六趣羣分,照如臨鏡。庶溺俗者發蒙,服道者瑩解,共建慧眼之因,俱成覺智之業焉。②《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64。
(4)《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録序》:
夫獉蔭獉樹獉者獉護獉其獉本獉,飲獉泉獉者獉敬獉其獉源獉。寧獉可獉服獉膺獉玄獉訓獉,而獉不獉記獉列獉其獉人獉哉獉!祐幼齡憑法,年逾知命,仰前覺之弘慈,奉先師之遺德。猥以庸淺,承業《十誦》,諷味講說,三紀於兹。每披聖文以凝感,望遐蹤以翹心,遂搜獉訪獉古獉今獉,撰《薩婆多記》。其先獉傳獉同獉異獉,則獉並獉録獉以獉廣獉聞獉;後獉賢獉未獉絕獉,則獉製獉傳獉以獉補獉闕獉。總其新舊,九十餘人。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此撰述之大旨也。條序餘部,則委之明勝,疾恙惛漠,則辭之銓藻。儻有覽者,略文取心。③《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66。
(5)《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録序》:
夫經獉藏獉浩獉汗獉,記獉傳獉紛獉綸獉。所以導達羣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爾咸在。然而講匠英德,銳精於玄義;新進晚習,專志於轉讀。遂令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衆恒儀,日用而不知其始。不亦甚乎!余以率情,業謝多聞。六時之隟,頗好尋覽。於是檢獉閱獉事獉緣獉,討獉其獉根獉本獉,遂綴翰墨,以藉所好,庶辯獉始獉以獉驗獉末獉,明獉古獉以獉證獉今獉。至於經唄導師之集,龍華聖僧之會,菩薩稟戒之法,止惡興善之教。或制起帝皇,或功積黎庶,並八正基迹,十力逵路。雖事寄形迹,而勳遍空界,宋、齊之隆,實弘斯法。大梁受命,導冠百王,神教傍通,慧化冥被。自幼届老,備觀三代。常願一乘寶訓,與天地而彌新;四部盛業,隨日月而長照。是故記録舊事,以彰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苑,區獉以獉類獉別獉,凡爲十卷。豈足簡夫淵識,蓋布之眷屬而已。①《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76—477。
(6)《弘明集目録序》:
祐以末學,志深弘護,靜言浮俗,憤慨於心。遂以藥疾微間,山棲餘暇,撰獉古獉今獉之獉明獉篇獉,總道俗之雅論。其有刻意剪邪,建言衛法,製獉無獉大獉小獉,莫獉不獉畢獉采獉。又前獉代獉勝獉士獉,書獉記獉文獉述獉,有獉益獉三獉寶獉,亦獉皆獉編獉録獉。類獉聚獉區獉分獉,列爲十卷。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②《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92。
這幾部著作,雖然彼此的性質有所差異:《釋迦譜》、《世界記》、《法苑雜緣原始集》,或介紹佛教應化故事,或記載佛教名物,性質皆類於小型類書;《弘明集》是論辯文字的總集;《薩婆多部師資記》屬傳記性質。但我們仍然可以試着歸納出僧祐佛教文獻整理的理念和方法:
(1)宗經。僧祐在整理佛教文獻材料時,一個總的原則是,以經典(指歷代傳譯且流傳有序的佛教經、律、論)爲依據,當出現與經典相牴牾的情況,便據經以斷。上列序言中,“仰稟羣經”、“總衆經以正本”、“抄集兩經,以立根本”、“抄集衆經,述而不作”、“檢閱事緣,討其根本”,講的都是宗經的意思。
(2)求同存異。僧祐在處理文獻材料互有出入的情況時,秉持的是一種審慎的求同存異態度,不隨意加以去取,並希望以此作爲進一步“貫一”和“會通”的基礎。序文中,“製無大小,莫不畢采。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三寶,亦皆編録”、“其先傳同異,則並録以廣聞”、“抄集兩經,以立根本,兼附雜典,互出同異”、“羣言參差,首尾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之契”,指的都是這樣的做法。
(3)原始表末。與上一點相聯繫,僧祐在編纂佛教類書性質文獻,出於正本清源、開示迷津“顯明覺應”的目的,往往在求同存異,詳列事物的古今演變的基礎上,進一步按核其原始形態或意義。“原始要終”、“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共今迹相證”、“搜訪古今”、“辯始以驗末,明古以證今”,表述的即是此意。需要說明的是,這裏所謂的“原始”,其實就是以經典爲依據的意思,是上述“宗經”思想的實際體現。
(4)類聚區分。僧祐在這幾部書序言中,曾反覆强調這一點,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區以類別”、“類聚區分”,這是一種對於知識條理化、系統化的訴求。這樣做的理由在於,只有經由條理化、系統化,文獻材料纔能更好地得到保存和流通。從常理上看,這種“類聚區分”的方法,在編撰佛教類書(無論部頭大小)時,是斷不可少的手段。面對大量的,且不同時期有着不同記述的佛教名物,“經藏浩汗,記傳紛綸”,若非以合理的知識分類標準加以統率,恐怕將導致“法門常務,月修而莫識其源;僧衆恒儀,日用而不知其始”,陷於迷津。
應該說,以上所歸納出來的佛教文獻整理的理念和方法,雖然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間還是有着聯繫。在文獻的整理過程中,首先是“求同存異”,把所能見到的相關材料一網打盡。其次需要“原始表末”,正本清源。而所謂的“本”、“源”,則來自經典。當所有的材料彙聚在一起的時候,又需要“類聚區分”,以保證知識的條理與系統,而這,也需要以經典作爲分類標準的依托。比如,像《經律異相》這樣一部佛教類書,其分類是由天、地、佛、諸釋、菩薩、僧、諸國王等二十二部構成,而這種分類標準,顯然與《佛本行經》等講述佛陀行迹和佛法世界的經典,甚有關係。①另外,佛教經典本身的“科判”傳統,似乎與佛教類書分類之間,也存有某種程度上的關係。附識於此,擬今後進一步討論。關於佛經科判的大致情況,參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文學遺產》2004年第1期,頁61—64。總之,宗經的思想充溢於僧祐佛教文獻整理的整個過程中。
如果進一步考慮這種宗經的思想的體現,除了上述的對於佛教類書等文獻編撰“求同存異”、“原始表末”、“類聚區分”具體方法的要求外,尤爲重要的,則是對於佛教經録的十分重視和周全整理,因這更爲直接地關涉到經典本身,是宗經思想最爲集中的體現。那麽,如果要舉出一部能夠代表僧祐佛教經録編撰情況的作品,毫無疑問,首推《出三藏記集》。
關於經録之所由生,智昇有過一段很好的總結,他認爲:
夫目録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删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翻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僞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製斯條録。②《開元釋教録》卷一,《大正藏》(55),頁477上。
概括地說,經録的意義在於能夠藉此分別經典的真僞、聚散——道義所賴以附麗的經典如果得以妥當的處理則“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自然道義本身“正教綸理”也一定會得到很好地宣揚。
實際上,這種原則的確立,在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序》裏,早就有明確的說明:
昔周代覺興,而靈津致隔;漢世像教,而妙典方流。法待緣顯,信有徵矣。至漢末安高,宣譯轉明;魏初康會,注述漸暢。道由人弘,於兹驗矣。自晉氏中興,三藏彌廣,外域勝賓,稠疊以總至;中原慧士,暐曄而秀生。提、什舉其宏綱,安、遠震其奧領,渭濱務逍遙之集,廬嶽結般若之臺。像法得人,於斯爲盛。原夫經出西域,運流東方,提挈萬里,翻轉胡漢。國音各殊,故文有同異;前後重來,故題有新舊。而後獉之獉學獉者獉,鮮獉克獉研獉覈獉,遂獉乃獉書獉寫獉繼獉踵獉,而獉不獉知獉經獉出獉之獉歲獉,誦獉說獉比獉肩獉,而獉莫獉測獉傳獉法獉之獉人獉。授獉受獉之獉道獉,亦獉已獉闕獉矣獉。夫一時聖集,猶五事證經,況千載交譯,寧可昧其人世哉!昔安獉法獉師獉以獉鴻獉才獉淵獉鑑獉,爰獉撰獉經獉録獉,訂獉正獉聞獉見獉,炳獉然獉區獉分獉。自獉兹獉已獉來獉,妙獉典獉間獉出獉,皆獉是獉大獉乘獉寶獉海獉,時獉競獉講獉習獉。而獉年獉代獉人獉名獉,莫獉有獉銓獉貫獉,歲獉月獉逾獉邁獉,本獉源獉將獉沒獉,後獉生獉疑獉惑獉,奚獉所獉取獉明獉?祐以庸淺,豫憑法門,翹仰玄風,誓弘大化。每至昏曉諷持,秋夏講說,未嘗不心馳庵園,影躍靈鷲。於是牽課羸恙,沿獉波獉討獉源獉,綴其所聞,名曰《出三藏記集》。一獉撰獉緣獉記獉,二獉銓獉名獉録獉,三獉總獉經獉序獉,四獉述獉列獉傳獉。緣獉記獉撰獉則獉原獉始獉之獉本獉克獉昭獉,名獉録獉銓獉則獉年獉代獉之獉目獉不獉墜獉,經獉序獉總獉則獉勝獉集獉之獉時獉足獉徵獉,列獉傳獉述獉則獉伊獉人獉之獉風獉可獉見獉。並獉鑽獉析獉內獉經獉,研獉鏡獉外獉籍獉,參獉以獉前獉識獉,驗獉以獉舊獉聞獉。若獉人獉代獉有獉據獉,則獉表獉爲獉司獉南獉;聲獉傳獉未獉詳獉,則獉文獉歸獉蓋獉闕獉。秉獉牘獉凝獉翰獉,志獉存獉信獉史獉,三獉復獉九獉思獉,事獉取獉實獉録獉。有獉證獉者獉既獉標獉,則獉無獉源獉者獉自獉顯獉。庶行潦無雜於醇乳,燕石不亂於荆玉。但井識管窺,多慚博練,如有未備,請寄明哲。①《出三藏記集》卷一,頁1—2。
在這段序言裏,僧祐明確地提出了他編撰經録的體例,“一撰緣記,二銓名録,三總經序,四述列傳”,且分別解釋了這樣一種體例設置的用意:“撰緣記”主要說明釋迦逝後,諸弟子之結集、大藏之分類、梵漢之起源與差異、梵文新舊譯語之不同等等,爲的是能使經典的本源情況有一明晰的說明,即“緣記撰則原始之本克昭”;“銓名録”是收集大量佛經目録(包括疑僞經目録),爲的是能將經典傳譯的年代情況界定清楚,即“名録銓則年代之目不墜”;“總經序”是將大小乘經律論的序言、題記加以網羅,俾使經典翻譯結撰的具體情境得以再現,即“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述列傳”是將歷來傳經、譯經法師的事迹加以搜羅,俾使後人據此得見其風標,即“列傳述則伊人之風可見”。
這樣的一種編撰經録的體例,可謂是一項偉大的創造。它以佛教經典作爲中心,從四個方面,多維度地將典籍本身的緣起、著録、序跋、傳譯等情況建構起來,十分科學合理。這種經録編撰的方式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準,也爲後世樹立了很好的典範。②蘇晉仁謂:“綜觀全書,以目録爲主幹,記述大量迻譯的經典,有知譯人名者,有失譯人名者,有疑僞者。圍繞集録衆多的序記,以詳述翻譯的過程,參加的人選,當時譯場的規模,經論傳播的源流和內容大意。繼之以譯人傳記,以見翻譯之因緣及風格的各異。故本書雖析爲四部分,而中心則亦佛典翻譯爲主。後世費長房撰《歷代三寶記》,道宣撰《大唐內典録》,智昇撰《開元釋教録》,靖邁撰《譯經圖記》,或利用本書之資料,或繼承本書之篇章,踵事增華,無不深受其影響。”《出三藏記集》“序言”,頁17。而作爲僧祐弟子的寶唱,隨從其師,整理經藏文獻多年,想來應該不會不深諳於此。我們可以尋出間接的證據,上文所提到天監十五年至十七年,梁武帝敕令僧紹編撰皇家《華林佛殿衆經目録》,但僧紹的工作並不能令人滿意,直到寶唱承乏,方“雅愜時望”。同樣的編目工作,兩個不同的人來做,爲什麽結果不一樣呢?《歷代三寶記》卷一一注“《華林佛殿衆經目録》四卷”時說:“天監十四年,敕安樂寺沙門釋僧紹撰。紹略取祐《三藏集記》目録,分爲四色,餘增減之。”①《歷代三寶記》,《大正藏》(49),頁99中。這裏明確指明《華林佛殿衆經目録》是模仿了僧祐的《出三藏記集》,但何謂“分爲四色”呢?這個問題令人頗費思量,一時也難得確解。②“分爲四色”四字,《大藏經》衆版本於此並無差異。“四色”在中古佛教名義中,往往指青、黃、白、黑四種顏色,並以此爲“虚有”,進而以喻“空”。很顯然,這個地方的“四色”並非爲了喻空,而是應該與書物的物質形式相關。筆者2013年專門集中一段時間,遍閱已出版的敦煌卷子,發覺敦煌文獻中,有“多色寫本”現象存在(程千帆、徐有富先生在《校讎廣義·版本編》中提到這個概念)。筆者猜測,是否 “分爲四色”,即意味着《華林佛殿衆經目録》當初的形態就是多色寫本,而之所以分色,乃是意在用四種不同的顏色,來區別“緣記”、“名録”、“經序”、“列傳”。但是,限於證明材料的匱乏,不敢遽然云是,只能附識於此,待進一步檢驗。但我們猜想,可能就是僧祐所創立的經録著作的體例,即“一撰緣記,二銓名録,三總經序,四述列傳”。僧紹之所以取用僧祐的方法,正是因爲這種方法代表了當時最高的水準。但是,可能由於僧紹畢竟只是模仿,遠不及僧祐的嫡系弟子寶唱,更加熟悉於此。故而,當僧紹的工作並不令人滿意的時候,梁武帝自然想到了寶唱(這固然可能由於寶唱在此之前工作的突出,但也說不定是僧祐的舉薦)。很顯然,他對於老師的這一體例,操作起來,自然比僧紹要好得很多。這就是《續高僧傳·寶唱》所謂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③《續高僧傳》卷一,頁8。在成功完成編撰皇家經藏目録的基礎上,他當然獲得進一步的信任。
就這種經録編撰體例本身而言,其中“述列傳”部分,是值得關注的,因這種對於佛經典籍傳譯者的表彰,體現了一種對於典籍背後人的因素的重視,這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此,我們認爲“述列傳”的體例要求,爲高僧傳記的搜羅、撰寫,提供了一個重大的契機。僧祐及其後人,一方面,固然可以繼續仿效僧祐,在經録的編撰中,在“撰緣記”、“銓名録”、“總經序”的基礎上,再加上“述列傳”部分,在注明典籍自身緣起、真僞、存佚等情況的同時,順便彰顯“伊人之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可以專門將“述列傳”部分獨立出來,從而成爲一部僧人傳記的集合,也便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僧傳。這在中國僧傳成立史上,是具有開創意義的一步。僧祐自撰的《薩婆多部師資記》,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突破點”。這部傳記所記載的都是傳承“薩婆多部”典籍諸法師的事迹,①“薩婆多”是音譯詞,梵文原作Sarvāstivāda(sarvā即“全部,一切,每一個”,asti即“存有、存在”,vāda即“說、理論”),字面意思是“一切存在的理論”。“薩婆多部”,即“說一切有部”(或稱“有部”),是部派佛教中上座部分出的一部。因其立“有爲無爲一切諸法之體實有”爲宗,故稱爲“說一切有部”,且一一說明其因由,又名“說因部”。在《大毗婆沙論》中自稱應理論者或應理論宗,在《俱舍論》等著作中也稱其爲毗婆沙師或毗婆沙宗。《出三藏記集》卷一二有《薩婆多部師資記》的具體目録。其“撰述之大旨”,在於使這一部派的法師(“其人”)生平事迹,連同他們對傳承的部派教義,一起發揚光大(“使英聲與至教永被,懋實共日月惟新”);其撰述之手段,便是之前所提及的類書編撰時的“求同存異”方法。部派先賢有傳記的,廣搜異聞,後賢沒有傳記的,就專門撰寫傳記來補闕,即“先傳同異,則並録以廣聞;後賢未絕,則製傳以補闕”。雖然此書今已不存,但我們猜想其撰作的緣起,就是僧祐在整理該部派典籍的時候,專門從經録中析出而成,“每披聖文以凝感,望遐蹤以翹心,遂搜訪古今,撰《薩婆多記》”。這樣一部對象明確、人數衆多“總其新舊,九十餘人”的傳記總集,可能是中國僧傳著作最早的一部獨立作品,此前並未見有。②慧皎所羅列的《高僧傳》之前的僧傳著作,在僧祐《出三藏記集》之前的著作,諸如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琅瑘王巾所撰《僧史》,雖然相較於《宣驗記》、幽明録》、《冥祥記》、《益部寺記》、《京師寺記》、《感應傳》、《徵應傳》、《搜神録》等這些著作,更加着意於僧人羣體本身,但它們或“混濫”、“蕪昧”,或“文體未足”,因此,都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僧傳。而僧祐自己的《出三藏記集》,僧人傳記部分只是整體體例設置的一部分,也不能算作一部獨立的僧傳作品。
我們還可以從佛教自身的發展來解釋上述這種變化。我們知道,佛教作爲一種信仰形式,從根本上說,其一切的制度、行爲,均是以對於信仰、理念的追求爲要義。而這種信仰、理念,須以佛教的道理(佛所遺留下來的教訓,即“道”)爲根本源泉。釋迦涅槃後,信徒對於佛教道理,只能通過由佛近旁弟子編纂的“如是我聞”經典纔能獲取。經典傳授的確當與否,關係着經典所承載的佛教義理的正當性——“宗經”的思想也便由此而生。可是,隨着佛教的發展、傳佈,由於經典本身的複雜性,以及信徒部派身份、修養的差異性,經典作爲佛教義理承載者角色的重要性,漸漸被經典的傳譯者所替代。“道由經弘”,也慢慢變成“道藉人弘”了。僧祐《薩婆多部師資記目録序》說:“夫蔭樹者護其本,飲泉者敬其源。寧可服膺玄訓,而不記列其人哉。”①《出三藏記集》卷一二,頁466。慧皎所說的“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托。辯忠烈孝慈,以定君敬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②《高僧傳·序録》,頁523。“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③《高僧傳·序録》,頁553。皆是一種給予“人”之於“道”重要意義的肯定與張揚。
綜上所論,我們以爲僧祐的發凡起例作用在於宗經思想的統攝下,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類書等佛教文獻整理的方法(“求同存異”、“原始表末”、“類聚區分”)和經録編撰體例(“撰緣記”、“銓名録”、“總經序”、“述列傳”)。而僧祐對於寶唱學術風格,尤其是對《名僧傳》創作的影響,即在此兩端,即佛教文獻整理方法中的“類聚區分”和經録編撰體例中對於“述列傳”的强調。
(四)道安的首倡
如果將此線索,繼續往上追溯,就會發現僧祐的這種文獻整理意識和方法,其源自還得從道安那裏算起。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卷二中說:“法輪届心,莫或條敍。爰自安公,始述名録,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①《出三藏記集》,頁22。明確指示了道安在佛教典籍文獻整理上的首倡之功。慧皎在《高僧傳·義解·道安》中說:“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爲《經録》,衆經有據,實由其功。”②《高僧傳》卷五,頁179。更具體地指出了道安的貢獻在於《綜理衆經目録》的編撰。
《綜理衆經目録》,又稱《道安録》,歷代著録均作一卷。此録雖久佚,但由於僧祐編撰《出三藏記集》的時候,最大限度地吸取了道安此録成果,因此,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出三藏記集》來把握此録的特點。
《大唐內典録》卷一〇在著録此書時說:“自前諸録,但列經名、品位大小,區別人代,蓋無所紀,後生追尋,莫測由緒。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世,銓品新舊,定其製作。衆經有據,自此而明。在後羣録,資而增廣。是知命世嘉運,睿哲早興,可不鏡諸?”③《大正藏》(55),頁336下。參合上面僧祐、慧皎兩人的評價,可以知道,道安《綜理衆經目録》的特色乃在於首倡了一種在“銓品新舊”的基礎上擇證善本的典籍著録體例。關於這一點,梁啓超說得很清楚:
《安録》雖僅區區一卷,在其體裁足稱者蓋數端:一曰純以年代爲次,令讀者得知兹學發展之迹及諸家派別。二曰失譯者別自爲篇。三曰擇譯者別自爲篇,皆以書之性質爲分別,使眉目黎然。四曰嚴真僞之辨,精神最爲忠實。五曰注解之書,別自爲部,不與本經混,主從分明。凡此諸義,皋牢後此經録,殆莫之能易。①梁啓超《佛家經録在中國目録學之位置》,《佛學研究十八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64。
實際上,道安的這種著録體例的產生,並非無的放矢的“即興”之舉,而是有着基於現實的考慮。慧皎所說的後世傳經之人已無從辨明年代與源自,一方面表明彼時佛經傳譯數量的增多,另一方面還在於當時有越來越多的疑僞經產生。②疑僞經研究,近年呈現勃興之勢。一方面在具體疑僞經的判定上取得了許多優秀的成果,另一方面很多學者通過疑僞經本身之撰作、傳播,把握佛教思想史上的重大命題。這方面,日本學者木村清孝、矢吹慶輝、落合俊典、船山徹等,中國學者方廣錩、王文顏、張總、曹淩等,美國學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Harumi Hirano Ziegler等,他們的相關研究均值得關注。在此情勢下,一方面,真僞、良劣問題必須要加以甄別;另一方面,在此基礎上,類聚區分的要求也提上議事日程。對於像道安這樣一位志在全面整理佛教經籍的專家而言,他需要在廣搜衆本的基礎上,確定具體版本的產生年月等,進而擇定善本;此外,對於所搜羅來的各種版本的經籍,還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加以分類區別,如失譯經、涼土異經、古異經、疑經、注經、雜經等等。
如果我們聯繫到僧祐,便可以發現:道安力圖通過經録來確定佛教典籍的版本,大約相當於僧祐後來所說的“銓名録”;③梁啓超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將僧祐的四種著録體例與道安《綜理衆經 目録》加以對比,謂“《祐録》第二部分(卷二至卷五銓名録之部)蓋踵襲《安録》,有所損益,餘三部則其所自創”。見氏著《佛學研究十八篇》,頁2 6 7。而其所强調的對於不同性質的佛教典籍文獻“類聚區分”的方法,也與僧祐在整理佛教文獻時所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這些,都應該是道安影響僧祐的具體所在。
此外,還應該指出的是,道安的這種對於佛教經典真僞的强調、對於傳譯善本的追求、乃至將正經與疑僞經、經注等區別開來的做法,說到底,就是一種宗經思想的體現。
四 結 論
以上,我們以慧皎《高僧傳》編撰的材料來源爲考察的立足點,由此不斷上溯,尋繹《高僧傳》在材料和體例上的源自,清理出一條“道安—僧祐—寶唱—慧皎”的演變線索。本文實際行文按照思考的反向邏輯順序展開。這裏,我們可以試着予以小結,以便將此一線索表述得更爲簡明一些:
(1)道安是漢地第一位有意識系統全面整理佛教典籍文獻的專家,其最主要的成就在於宗經思想的高揚以及佛教經録的創立。①在道安之前,也有多種經録存在,如朱士行《漢録》、《聶道真録》、《古經録》、《舊經録》等,但這些作品本身的真僞問題多有爭論,而且,即便爲真,也都是著録一時一地的佛教典籍,談不上系統和全面,因此,我們在這裏采用僧祐《出三藏記集》的說法:“法輪届心,莫或條敍。爰自安公,始述名録,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徵,實賴伊人。”關於這些經録的考辨,前賢多有發覆,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梁啓超《佛家經録在中國目録學之位置》,頁258—281;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之“宗教目録”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85—267;馮承鈞《大藏經録存佚考》,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十),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頁339—348;蘇晉仁《佛教經籍目録綜考》,《佛教文化與歷史》,頁180—195;馮國棟《經録考稿》,南京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2006年。《綜理衆經目録》那種“總集名目,表其時世,銓品新舊,定其製作”,以及將不同性質經籍“類聚區分”的方法,深刻地影響到了後世,“在後羣録,資而增廣”。
(2)僧祐延續了道安的宗經思想,一方面,在經録方面,繼承了道安的體例,又進一步加以增廣,乃至形成一套成熟的經籍著録辦法,即《出三藏記集》“一撰緣記,二銓名録,三總經序,四述列傳”的著録體例,而其中,“述列傳”一節,體現了從僧祐起,已經開始透過經典本身,注意到經典背後的人事。《薩婆多記》的編撰,是僧傳首次從經録獨立出來的作品,是由關注經典到關注經典背後之人事轉變的里程碑;①隋代法經總評歷代經録,安公以下,獨推僧祐。但還是有所指責:“道安法師創條諸經目録,銓品譯材,的明時代,求遺索缺,備成録體。自爾達今,二百年間,制經録者,十有數家,或以數求,或用名取,或憑時代,或寄譯人,各紀一隅,務存所見,獨有揚州律師僧祐,撰《三藏記》録,頗近可觀。然猶小大雷同,三藏雜糅,抄集參正,傳記亂經,考始括終,莫能該備,自外諸録,胡可勝言。”《大正藏》(55),頁148下—149上。梁啓超對此批評頗不以爲然,逐項加以駁斥,大略較爲通達,惟於法經的“傳記亂經”說法,反駁稍顯無力,謂“祐書誠所不免,殆因爲書甚少,不能別立部門,故隨譯人以附録耳”。見氏著《佛家經録在中國目録學之位置》,頁268。我們以爲法經的“傳記亂經”的觀察,正是僧祐在體例上的極大創新,而傳記之所以有“亂經”之勢,也實在是反映了此時傳記有脫離經録,獨立的趨勢。另一方面,在經録以外佛教文獻整理方面,僧祐形成了“求同存異”、“原始表末”、“類聚區分”的理念和方法,其中,“類聚區分”的方法,與道安撰著經録時所采用的方法,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力圖將所承載的知識信息按照一定的標準條理化。
(3)寶唱身爲僧祐的弟子,一方面,將僧祐文獻整理的方法貫徹到自己的學術實踐中;另一方面,更爲重要的是,他進一步將僧人的傳記,從經録中獨立出來,自成一書。從材料上說,他在編撰《名僧傳》時,利用了前代經録如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和自己受敕所編撰經録如《衆經目録》、《華林佛殿衆經目録》諸多僧人傳記;①寶唱受敕編撰的經録,雖然今已不見。但據前面的分析,我們有理由推斷,它們皆是按照僧祐《出三藏記集》的經籍著録體例,應有“述列傳”內容。而這成爲寶唱及後人僧傳創作的材料來源。從體例上說,他將在佛教經籍文獻整理中所貫徹的“類聚區分”、“求同存異”等方法,遷移到《名僧傳》的編撰中去,既廣泛彙聚鳩集傳主的多種事迹材料,求同存異;又予立傳僧人羣體以周密之身份類型分類,類聚區分。
(4)慧皎撰寫《高僧傳》雖然有着特殊的寫作背景,對於前代寶唱《名僧傳》的態度也顯得比較曖昧,但是,無可否認,其最主要的材料來源,就是《名僧傳》。從彙集僧人事迹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所沿承的還是僧祐、寶唱以來的“述列傳”的傳統。只是在收録僧人的類型上,相對於寶唱《名僧傳》來說,更加多樣,人數也更廣,並不再拘於“名僧”的限制。他還注意利用外典材料如 “春秋書史”、“荒朝僞曆”等,參合勘對具體僧人傳記,視野顯得更爲廣闊。此外,其所確立的“十科”分類法,是對寶唱分類方法的繼承和發展,也更加科學。
總之,從這條發展的脈絡來看,經録是僧傳得以孕育成型的“母胎”,②現代學者對於佛教經録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分析界定,蘇晉仁、方廣錩、徐建華、馮國棟等人都曾提出各自不同的分類名目,見蘇晉仁《佛教目録研究五題》,《佛學研究》2000年第9期,頁186—201;方廣錩《敦煌佛教經録輯校》“前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31;徐建華《中國歷代佛教目録分類瑣議》,《佛教圖書館館訊》2002年總29期,頁22—31;馮國棟《經録考稿》。我們在此,僅就整體而言,不作具體細分。從經録到僧傳,是佛教經籍背後著譯者角色,亦即人的地位日漸凸顯的過程。③本文初稿草就之後,獲識紀贇先生,他告知其2013年在給萊頓大學(荷蘭Brill出版社)新編的佛教大百科全書中的一個詞條“Chinese Buddhist Historiography”中也談到了此點(這個詞條有近萬字),他提到佛教的“大藏經”編纂導致了經録編纂的必要,而經録中有人的要素,又推動了僧傳的編纂。筆者目前尚沒有見到這項資料,也不知論證過程是否一致,但學問之思,巧合賢達,則令人無比歡欣。特識於此,以免誤會。亦請讀者一并參考。而慧皎《高僧傳》書寫範式的成立,也正是佛教內部從經典到個人、從古到今學術嬗變的必然結果。①
(本文作者係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講師)
游師雄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事
仝相卿
《宋史》卷三三二《游師雄傳》記載其“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爲陝西轉運使”。然而,國家圖書館藏游師雄墓誌銘則稱“乃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0册)。《東都事略·游師雄傳》則記載“師雄爲陝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副使”。究竟是“陝西轉運使”還是“權陝西轉運副使”,抑或是“陝西轉運副使”呢?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七八根據張舜民墓誌,並參考其他材料,把游氏改官時間定爲元祐七年(1092)十月辛未:“太常博士、工部員外郎游師雄爲集賢校理、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七《觀褚師聖教序碑題名七段》收録了游師雄在陝西時的題名曰: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郡守章龍圖楶相率同觀,與者三人:通判州事張坰、提刑司檢法官崔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題。
元祐九年爲甲戌年,中和節爲二月初二日。又,元祐九年四月改元紹聖,故史籍多記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然二月初二日尚未改元,故時間上並無不妥之處。游師雄元祐七年爲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紹聖元年仍爲記“權發遣轉運副使”未變,故《宋史·游師雄傳》所載“陝西轉運使”定誤,《東都事略·游師雄傳》“陝西轉運副使”亦不準確,當訂正爲“權發遣陝西轉運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