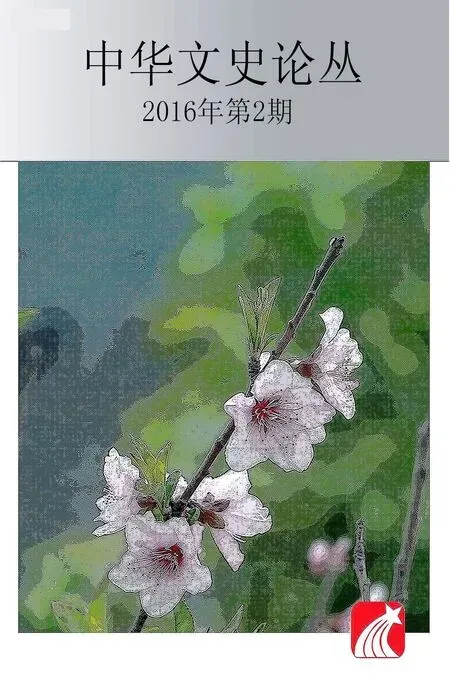《羌鐘》銘與楚竹書《繫年》所記戰國初年史實考論*
張樹國
張樹國
《羌鐘》銘文記載羌隨其主君韓虔征秦、伐齊、會平陰、入齊長城、襲奪楚京的戰功,時間是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學者對銘文文字訓釋不一,聚訟紛紜。近年出土楚簡《繫年》對《羌鐘》銘文的正確解讀帶來了契機,也豐富了戰國初年的列國史料。本文訓讀銘文的目的在於考史,對《羌鐘》及楚簡《繫年》的事件與時間的考證,對修正《史記·六國年表》有一定的幫助。在史文缺佚的戰國初年,《羌鐘》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本文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兩周時期歷史文學文本研究》(15BZW043)、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金文文獻與西周—春秋歷史文學形態研究》(編號:12JCZW01YB)階段性成果。《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云:“近年出土於洛陽城東卅五里許之太倉古墓,其已見著録者凡十又三枚,銘長六十一字。”①《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葉234A—B。下簡稱《大系》。劉節認爲:“當爲‘驫’之繁文。”②劉節《氏編鐘考》,《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1931年。張政烺《批注》云:“聞之估人,出自河南鞏縣。春秋鞏爲成周畿內之地,戰國地入於韓,《戰國策》載蘇秦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是爲韓之北疆,故其地有韓宗之臣氏遺物也。”③《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66。下簡稱《批注》。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四册著録云:“河南洛陽金村太倉古墓出土,傳世共一四枚,一至五鐘正面鉦間四行三二字,背面鉦間四行二九字,凡六一字。六至一四鐘正背鉦間銘文相同,各二行四字……除第五、十四鐘藏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外,其他均藏日本泉屋博古館。”④《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589。白川靜《金文通釋》據《韓君墓發現略記》記載,《羌鐘》出土於民國十七年(1928)頃,洛陽城東約卅五里,金村附近太倉李密城韓君墓。⑤白川靜《金文通釋》卷四,神户,白鶴美術館,昭和三十九年(1964),頁141。筆者曩游舊書肆,購得日本平凡社編撰《書道全集》,《羌鐘》圖版見於第一册《中國一·殷·周·秦》頁110,摹圖見於頁205,與白川靜《金文通釋》摹録圖版完全相同,⑥《金文通釋》卷四,頁145。圖版非常清晰。據內藤戊申釋文云:“相傳洛陽金村出土,現藏住友家。全部十三鐘,四鐘刻有長篇銘文,其他九鐘刻有‘驫氏之鐘’,四鐘儘管泐字較多,然相互比照之後只有一字不能識讀,八行六〇字。”⑦日本平凡社編《書道全集》第1卷《殷·周·秦》,東京,平凡社,昭和四十年(1965),頁205。內藤摹本所缺之字已補齊,即“武文咸烈”之“咸”字。現將朱德熙、孫稚雛、內藤戊申的摹本附録於下:

(朱德熙摹)

(孫稚雛摹)

(内藤戊申摹)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
“景侯”之名,司馬貞《索隱》云:“《紀年》及《系本》皆作景子,名處。”①《史記》卷四五,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249。“處”、“虔”古文形近易訛。景子名虔,見於楚簡《繫年》第二十二章簡119—120:“韓虔、趙籍、魏擊率師與戉(越)公翳伐齊。”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192。《竹書紀年》記載: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元伐齊,入長城”。③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01。這是與本文相關的重要記載。《史記》稱“景侯”,當爲“景子”未侯之前的稱呼。“韓宗”即羌的主君韓虔。
“武侄寺力”之“侄”,有幾種解說。郭沫若《大系》云:“侄與挃通,《淮南·兵略訓》:‘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高注云:挃,擣也。”④《大系考釋》,葉238A。在《鐘銘考釋》又云:“侄乃到之異……侄與到僅左右互易而已。此讀爲擣。”⑤郭沫若《器銘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五》,頁744,745。郭釋羌爲狗,不確。于省吾認爲,“武侄”猶言“武鷙”,“‘武鷙寺力’言恃其武勇之力也。《管子·弟子職》:毋驕恃力,是‘恃力’周人恒語。”⑥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06。張政烺《批注》云:“侄,致、至也。武至,武之致也,猶文致,文之致也。”⑦《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頁164。《乖伯簋》云:“己未,王命中(仲)侄歸(饋)乖伯貔裘。”馬承源釋“侄”爲“致”。⑧《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頁207。簋銘又見《殷周金文集成》04331,頁2718。“侄”即致、至之意。《玉篇·攵部》:“致,陟利切,至也。《說文》曰:送詣也。”⑨顧野王《宋本玉篇》卷一〇,北京,中國書店,1983年,頁190。又《玉篇·人部》:“,丈吏切,會物也。”①《宋本玉篇》卷三,頁52。《方言》第一云:“抵、,會也。雍梁之間曰牴,秦晉亦曰牴,凡會物謂之。”《音義》,“,音致。”②錢繹《方言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6。“侄”或爲“”之省,有“會物”、“會集”之意,“武”指諸軍會合。
(一)周靈王二十二年(前550)。持此說法者如唐蘭、吴其昌等學者。①吴其昌《羌鐘補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劉節《氏編鐘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跋羌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一號。徐中舒以及高本漢等諸家認爲“二十二年”爲周靈王紀年。見內藤戊申《羌鐘》釋文,《書道全集》第1卷《殷·周·秦》,頁205。唐蘭《羌鐘考釋》云:“廿又再祀者,周靈王之廿二年,晉平公之八年也。”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一號(1932年),《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1—5。銘文“先會於平陰”之“平陰”,見於《左傳·襄公十八年》:“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③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037—1038。唐蘭言:“此銘所紀,正此事也。”④《唐蘭先生金文論集》,頁3。除“平陰”外,其他史實均不合。唐蘭釋“韓宗”之“”爲“擊”,爲樂器之名。此論已被證明不確。
(二)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郭沫若《大系》謂:“周安王之二十二年也,徵諸《史記·六國年表》於是年三晉欄內均書‘伐齊至桑丘’。”⑤《大系考釋》,葉234B。張政烺《批注》:“地理與鐘銘不合。說似不確。”⑥《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頁164。
二 征秦考
“征秦”之役,白川靜《金文通釋》詳列秦靈公六年(前419)至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之間秦晉交戰記録十二條,但其中秦簡公七年(前408)至十四年之間沒有記載。③《金文通釋》卷四,頁161。張政烺《批注》列舉史事云:
《秦本紀》:孝公曰:“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吾河西地。”征秦即此事,蓋三晉軍可常合作也。周威烈王十三年“秦與晉戰,敗鄭下”。(威烈王)十七年“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威烈王)十八年“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④《張政烺批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頁166。
據《史記·六國年表》,周威烈王十三年爲秦簡公二年(前413)。“十七年”爲前409年。十八年爲前408年。沒有史料表明羌參與了魏伐秦的戰爭。吴其昌《氏鐘補考》認爲:“征秦之秦指齊魯之間之秦地。《春秋經·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於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是其地也。”⑤《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1931年。白川靜認爲,“既然秦爲地名,地屬魯地,應當書作征魯纔是。”⑥《金文通釋》卷四,頁161。魯在當時爲三晉同盟國,吴說不確。《羌鐘》“廿有再祀”爲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據《史記·六國年表》,是年爲楚聲王當(即“聖桓王”)四年,韓景子虔五年。新出楚簡《繫年》簡126—127記載:
楚聖桓王立四年……秦人敗晉師於茖(落)陰,以爲楚援。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頁196。
“茖(落)陰”即“雒陰”,“雒”(東漢初改)即“茖”“洛”。據《史記·六國年表》:周威烈王十八年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魏世家》:魏文侯十七年(前429)子擊“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②《史記》卷一五,頁852;卷四四,頁2211。雒(茖、落)陰當爲文侯子魏擊所築。四年之後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秦軍爲援救楚國,在“茖(落)陰”即“雒陰”擊敗晉師,羌可能隨宗主韓虔亦在晉軍之中。據楚簡《繫年》記載,戰國初年,三晉與越結盟,而楚、齊、秦結爲盟國。《羌鐘》的“征秦”史事即指雒陰之戰。因爲此役失敗,所以羌只提及“征秦”而未作渲染。
三 “迮齊”考
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於龍澤,田布敗逋。①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頁100。
“公孫會”即田會。依陳夢家《六國紀年表》,晉烈公十一年即齊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史記·六國年表》:齊宣公五十一年“田會以廩丘反”。②《史記》卷一五,頁853。《齊太公世家》:“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田會,齊大夫。廩,邑名,東郡有廩丘縣也。”③《史記》卷三二,頁1820。《竹書紀年》記載“晉烈公十一年”的“廩丘之役”,因爲齊國田布殺了大夫公孫孫,公孫會(田會)占據廩丘叛歸趙國,田布圍困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將田布打敗。“翟角”可能是魏帥。④《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頁101。“三晉”爲了“廩丘”,趁齊宣公死、新王(康王貸)即位之際大舉伐齊。“廩丘”具有重要戰略地位,這場大戰在《呂氏春秋·不廣》中亦有記載:“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⑤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25。是役以齊國大敗而結束。《水經注》卷二四“瓠子河”條云:“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⑥《水經注疏》,頁2043—2044。“廩丘”亦見於楚簡《繫年》簡119—124:
楚聖(聲)桓王即位元年,晉公止會諸侯於任……韓虔、趙籍、魏擊率師與越公翳伐齊,齊與越成。以建陽、陵之田且男女服。越公與齊侯貸、魯侯侃盟於魯稷門之外。越公入享於魯,魯侯馭,齊侯晶(驂)乘以入。晉魏文侯斯從晉師。晉師大敗齊師。齊師北,晉師逐之,入至汧水。齊人且有陳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盟於晉軍。晉三子之大夫入齊,盟陳和與陳淏於溋門之外,曰:“毋修長城,毋伐廩丘。”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頁192。
上文盟約中的“毋伐廩丘”,意在迫使齊國承認趙國對“廩丘”事實上的占有。三晉與越王翳伐齊事當在公元前404年。但楚簡《繫年》記載的時間存在問題。上文“楚聖(聲)桓王”即《史記·楚世家》中之“楚聲王”,其“即位元年”據《史記·六國年表》爲齊宣公四十九年(前407)。上文提到“齊侯貸”即齊康公貸,即位於前404年,《史記·六國年表》:前404年“齊康公貸元年”。②《史記》卷一五,頁853。時爲楚聲王四年。據此可知,三晉與越伐齊當在此年,簡文漏書“聖桓王四年”。上文“魯侯侃”即魯穆公顯,《史記·魯周公世家》:“子顯立,是爲穆公。”《索隱》:“《系本》‘顯’作‘不衍’。”③《史記》卷三三,頁1859,1860。侃、羴、顯、衍上古音均爲元部,音近相通。楚聲王四年當越王翳八年。《繫年》中的“晉公止”即《竹書紀年》中的“晉烈公”,名止,《史記·六國年表》:“(前420)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前419)晉烈公止元年。”④《史記》卷一五,頁848。是時韓、趙尚未封侯,故《繫年》直呼其名。《史記》稱“趙烈侯籍”、“韓景侯虔”乃爲後世追記。
《繫年》中“晉三子之大夫”與齊國陳和(即田和)、陳淏的另外一項盟約爲“毋修長城”,即齊長城。齊國始造長城的時間,在楚簡《繫年》簡111—112有記載:
晉敬公立十又一年,趙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以與越令尹宋盟於鞏,遂以伐齊。齊人焉始爲長城於濟,自南山屬之北海。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頁186。
關於“晉敬公立十又一年”事,《史記》中《晉世家》、《趙世家》沒有對晉敬公世系的記載,且多有紛亂,互相牴牾。②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四二力圖彌合《史記》與《竹書》之矛盾,論說繁瑣,本文不取。參見《續修四庫全書》,335册,頁528。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六國年表》“晉哀公忌元年”下云:“案:繼出公而立者。《晉世家》謂昭公曾孫哀公驕,《趙世家》昭公曾孫懿公驕,《竹書紀年》謂昭公孫敬公,無哀、懿二公。”③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93。據《史記·晉世家索隱》引《竹書紀年》云:晉“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④《史記》卷三九,頁2019。又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陳夢家《六國紀年表》采《紀年》之說,“敬公十八年”即前434年,則楚簡《繫年》所謂“晉敬公十一年”當爲公元前441年,時越王朱句八年、齊宣公十五年前後。齊修築長城當在齊宣公十五年時。據《繫年》記載:“齊人焉始爲長城於濟,自南山屬之北海。”《管子·輕重丁》:“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⑤《管子》卷二四,四部叢刊縮印本,78册,頁149下。《水經注》卷二六《汶水》云:“汶水出朱虚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琊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熊會貞按:“《史記·楚世家》正義,《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餘里,至琅琊臺入海。《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竹書》言梁惠王二十年,齊築長城,在威王時。《史記》正義又以爲閔王築,蓋威、宣、閔諸王皆經營之耳。”①《水經注疏》卷二六,頁2257—2258。
四 “楚京”考
在傳世文獻中,三晉“襲奪楚京”沒有記載。“楚京”二字是本銘的關鍵。傳世文獻有《史記·楚世家》記載過楚文王“始都郢”,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荆州江陵縣北五十里。”⑥《史記》卷四〇,頁2035。學者一直認爲江陵紀南故城是楚國惟一都城,因此對“襲奪楚京”無法作出更好的解釋。影響較大的說法,諸如郭沫若《鐘銘考釋》認爲“楚京”乃楚丘與京山之省稱:
《衛(鄘)風·定之方中篇》:“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楚丘正略稱爲楚,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即其地。《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北逕楚丘城西。”又云:“黃溝枝流北經景山東。”與《詩》合。足證景山確是楚丘旁邑之山名。《毛傳》訓“景山”爲大山,未得其實也。古音京、景相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京侯周成”,《集解》引徐廣曰:“京一作景。”本鐘銘之“京”即《詩》之“景”矣。“敓楚京”者,言率偏師克寺之後,復長驅南下,奪取楚丘與景山也。①郭沫若《器銘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五,頁746—747。
上引郭語“今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楚丘城,即其地”不正確。顧炎武認爲《春秋》有兩楚丘,一爲濟陰之成(城)武,乃曹國之楚丘;一爲衛楚丘,在河南滑縣、開州之間。②顧炎武《日知録集釋(全校本)》卷三一《楚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798—1799。顧棟高《春秋兩楚丘辨》亦認爲“春秋時有兩楚丘”,一在山東曹縣東南四十里,一是《僖四年》衛遷於楚丘,在滑縣東六十里。③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889。在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鄭宋衛》標注很清晰,④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一),頁24—25。《鄘風·定之方中》的“楚丘”應指衛楚丘,郭說即“楚京”。“楚丘”曾爲衛國國都,《定之方中》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⑤《毛詩正義》卷三之一,十三經注疏(嘉慶本),頁664下。關於衛遷楚丘的史實見於《左傳·閔公二年》。楚簡《繫年》簡18—22記載翟(狄)滅衛後,齊桓公率領諸侯建造“楚丘”城,以安頓衛國百姓。後來衛國由“楚丘”遷於“帝丘”。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頁144。郭沫若認爲,該“楚丘”即《羌鐘》銘文中的“楚京”。隨着新出楚簡《楚居》的面世,這個結論就靠不住了。
近年出土的楚竹書《楚居》記載了楚傳說時代到戰國楚悼王的國都遷徙史,保存了珍貴史料,有望使這一問題得到解決。楚在昭王以前,國都在江漢沮漳之間遷徙。楚惠王滅下蔡(州來,今安徽鳳臺)後,將國境從淮水流域推進到泗水流域,與此相伴隨,國都也遷徙到淮泗之間。楚惠王以後的遷都在《楚居》簡13—16有明確記載:
至獻惠王自媺(美)郢徙襲爲郢,白公起禍焉,徙襲湫郢,改爲之焉,曰肥遺。以爲處於楢澫,楢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吁。王太子以邦復於湫郢,王自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復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藍郢,藍郢徙居郢,郢復於。王太子以邦居郢,以爲處於郢,至悼哲王猶居郢。②《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楚居》(壹),頁182。
自“媺(美)郢”之下共出現了十一個楚都之名。其中“鄢郢”在湖北宜城,“蔡”即下蔡,今安徽鳳臺,後成爲楚國之淮北門戶。③拙作《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1期。“藍郢”又見於《包山楚墓》簡7:“齊客陳豫賀王之歲,八月乙酉之日,王廷于藍郢之游宮。”劉彬徽、何浩《論包山楚簡中的幾處地名》云:“藍郢自當與楚國藍縣有關。北距宜城縣南楚皇城,相去不遠。”④湖北荆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564。“媺(美)郢”地址不詳,爲楚昭王所都,《楚居》簡11:“至昭王自秦(乾)溪之上徙居媺(美)郢。”“疆郢”爲春秋楚武王所建,《楚居》簡7:“至武王熊通……乃潰疆郢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鄬郢”、“湫郢”(惠王改名“肥遺”)爲春秋初年楚文王所徙居之地,《楚居》簡8:“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爲郢。”①《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楚居》(壹),頁181。“楢澫”、“吁”不詳。這些早期楚都或在湖北沮漳流域,或在漢水、長江流域。
《史記·楚世家》亦引此語,《集解》:“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⑤《史記》卷四〇,頁2046。據《大戴禮記·帝繫》及《史記·楚世家》,“昆吾”爲楚先祖季連之長兄,同爲“祝融八姓”或“陸終六姓”之後。⑥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8;參拙作《新出文獻與楚先逸史及相關文學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6期。從楚靈王之語分析,楚先公昆吾曾生息於“舊許”之地。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⑦《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五,頁4481下。顧棟高《春秋列國都邑表·楚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里有城父城。”①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頁853。據錢穆《史記地名考》卷六《夏殷地名》中有“三亳”,一爲蒙亳又名“北亳”,即安徽亳州,《楚世家》所謂“商湯有景亳之命”;二爲“殷亳”即河南偃師;三爲“西亳”即京兆杜陵。②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232—234。“舊許”與“蒙亳”即安徽亳州地近。
“京”、“亳”相混之例在傳世古書中就已出現,王國維《說亳》云:“《春秋·襄十一年》:同盟於亳城北。”自注:“《公》、《穀》作‘京城北’。《公羊疏》謂服氏經亦作‘京’,今《左氏經傳》作‘亳’,殆字之誤也。”⑤《觀堂集林》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1年,頁519。學術界對“京”、“亳”仍有不同意見,可參趙平安《京亭考辨》。⑥《復旦學報(社科版)》2013年4期。竹書《楚居》中的“京宗”不見於傳世文獻,學者們提出了幾種考證,亦未得確解。有學者認爲,“京宗”即景山,京、景音同相通,爲楚族所宗,猶如泰山稱爲“岱宗”。①李家浩《談清華戰國竹簡〈楚居〉中的“夷”及其他》,《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55。“景山”見於《山海經·中次八經》,郭璞注:“今在南郡界中。”②《山海經》卷五,四部叢刊縮印本,107册,頁39下。但聯繫到《左傳》中楚靈王“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之語,釋“京宗”爲“亳宗”可能更合理一些。所謂“商湯有景亳之命”,“亳”即安徽亳縣,“郢”或即楚先祖所居之“亳宗”,也許就是《羌鐘》中的“楚京”。
“楚柬大王”即楚簡王,據《史記·六國年表》,簡王七年即周威烈王元年(前425)。上文的“二年”相當於“第二年”,即簡王八年(前424),楚莫敖昜爲與晉三帥戰於“長城”即楚方城。《葛陵簡》即指此事,與《羌鐘》無涉。趙平安所謂“羌進軍路線是由秦入長城,而平陰,而楚京,皆在齊之西境”,③《金文文獻與文明探索》,頁63。缺乏根據。如果查閱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册》,可知這個“進軍路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晉公獻齊俘馘於周王,遂以齊侯貣(貸)、魯侯羴(顯)、宋公畋(田)、衛侯虔、鄭伯(駘)朝周王于周。④《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頁192。
上述史實均發生於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即晉烈公十二年、齊侯貸(康公)元年、魯侯羴(穆公顯)四年,楚聖桓王四年。而據《史記·六國年表》,是年爲宋昭公特(或“德”)四十六年。據錢穆考證,宋昭公卒年在威烈王四年而非二十二年。⑤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46。這一結論是正確的。《史記·宋微子世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⑥《史記》卷三八,頁1958。悼公之死見於《繫年》簡119:“宋悼公將會晉公,卒於”。⑦《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釋文》,頁192。時當楚聖桓王即位元年(前408)。《繫年》簡126:“楚聖桓王立四年,宋公畋、鄭伯駘皆朝于楚。”⑧《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釋文》,頁196。時當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即宋公畋四年。宋公畋,《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休公田”,“畋”即“田”,休公田在位二十三年。①《史記·宋微子世家》卷三八,頁1958。《史記》中戰國時期的宋君世次、年代已亂。
據《史記·六國年表》,衛慎公元年(前414)。②《史記》卷一五,頁850。則前404年當慎公十一年。《世本》秦家謨輯本:“悼公(虔)生敬公費及慎公頹。”③《世本八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頁165。據《史記·衛康叔世家》:“慎公父,公子適。”《索隱》:“音的。按《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④《史記·衛康叔世家》卷三七,頁1927。楚簡《繫年》“衛侯虔”當指衛悼公虔,可知《史記》衛國世次亦亂,當以楚簡《繫年》爲準。據《史記·六國年表》鄭繻公元年(前422),⑤《史記》卷一五,頁848。前404年當鄭繻公十九年,《史記·鄭世家》:“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⑥《史記》卷四二,頁2129。即楚簡《繫年》之“鄭伯駘”。
楚簡《繫年》記載“晉侯獻齊俘馘於周王”,又與“齊侯貸”等一同朝見“周王”即周威烈王,文中的“齊侯”即姜姓齊國末代君主康公貸,這對齊侯來說無疑是相當屈辱的。當時齊國政柄早已操縱在陳(田)氏手中,齊康公貸是被出賣的。《呂氏春秋·下賢》記載:魏文侯“好禮士,故南勝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卿”。⑦陳奇猷《呂氏春秋新集釋》,頁88下。《繫年》簡122—123記載:“齊人且有陳子牛之禍,齊與晉成,齊侯盟於晉軍。”⑧《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釋文》,頁192。整理者認爲簡文中的“陳子牛”即《淮南子·人間訓》中的“牛子”。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繫年》(貳),《釋文》,頁194注釋〔一〇〕。《人間訓》記載:“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逾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①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61。文中的“齊侯”可能即齊康公貸,簡文“齊侯盟於晉軍”是指齊康公爲陳(田)氏脅迫,而與晉軍盟會。楊寬《戰國史》注意到《羌鐘》的史料價值,周威烈王時,“三晉伐齊大勝而入齊長城,迫使齊侯一同朝見周威烈王,請求‘王命’於次年立三晉爲諸侯”。②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39。“次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上述六位諸侯朝周王於東周洛陽,羌當與其宗主韓虔亦側身於其間。
《史記·齊太公世家》:“康公二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③《史記》卷三二,頁1820。錢穆《三晉始侯考》云:
《史記·楚世家》:“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而《年表》無之。《年表》:“楚聲王五年,魏、韓、趙始列爲諸侯。”而《世家》無之。考之《魏世家》云:“魏文二十二年,魏、韓、趙列爲諸侯。”《趙世家》云:“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韓世家》云:“景侯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周本紀》云:“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爲諸侯。”《燕世家》云:“釐公立歲,三晉列爲諸侯。”皆與《年表》楚聲王五年之說合。故後人多信是歲爲三晉始侯之歲,而不取簡王八年之說。④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141。
關於戰國分期,有以魯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獲麟”,杜預注,孔子傷感而“絕筆於獲麟”者,⑤《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九,頁4718上。有以《史記·六國年表》始於周元王元年(前476)説者,⑥《史記》卷一五,頁831。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晉始侯”爲説者。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周紀一》云:“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①《資治通鑑》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2。即以三晉始侯之歲爲戰國編年之始。
(本文作者係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中國文學與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