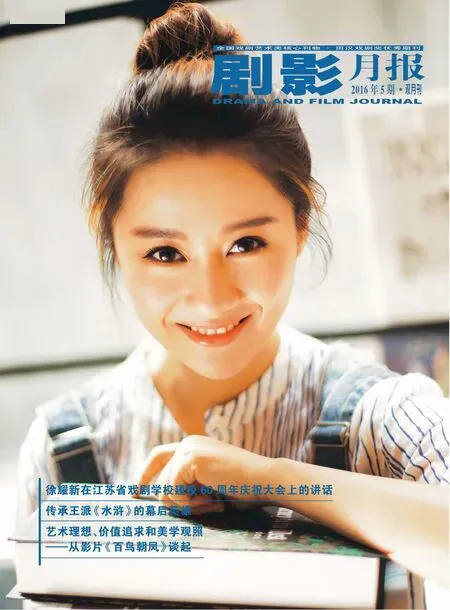昆曲伴奏音乐的叙事性
■戴敬平
昆曲伴奏音乐的叙事性
■戴敬平
昆曲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戏曲门类,在年轻一代中广受追捧,这充分体现了文化瑰宝超越时代、直达人性的魅力。以歌曲演唱为主要表现方式的叙事舞台戏剧艺术,中西皆有,在我们聆听昆曲、京剧的同时,西方剧院的歌剧艺术也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不过相比于歌剧已经逐渐不再流行,昆曲如今的发展现状是令人惊喜的。近年来,脱胎于歌剧,但是更加符合时代和观众需求的西方音乐剧的发展,同样也给我们昆曲音乐工作者们以启迪,昆曲音乐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昆曲要永葆生命力,被更新的一代人所喜爱,也必须借鉴其他优秀的艺术门类,比如音乐的叙事要素,就是值得探索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昆曲音乐和伴奏乐队,传统上最初是演唱的附庸。相比于西方的歌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先有剧本,再有唱词和谱曲,我国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艺术,是先有各种“曲牌”,也就是先有固定的曲目和曲调,并且可以单独表演而无剧情要求的。从元代开始发轫的杂剧开始,形成了先撰写故事——接着选择曲牌,排列曲牌——接着根据曲牌填词的独特创作方式。相对来说,撰写新的曲牌的作品是比较少的,大多数的作品都是集合了当时最为精彩,最为流行的曲牌进行演绎。相同的曲牌在不同作品、不同故事、不同角色和不同的情绪之中,自然需要不同的表达,而这里,就是伴奏乐队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相同的曲牌出现在不同的情节位置,除了表演的演员需要给出不同的表演方式之外,作为伴奏乐队,是否要在节奏、配器等具体领域,给出不同的演绎呢?比如《长生殿·酒楼》与《牡丹亭·离魂》中,都有精彩的《集贤宾》曲牌唱段,一个激昂愤慨,一个肝肠寸断,同样的曲牌之下,不仅是情节、故事、角色的完全不同,同样也为伴奏乐队提出了极大的要求。可以看到,传统的昆曲曲谱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提出了用不同的“调性”来区分相同曲牌,可见古人已经开始注重伴奏本身的叙事性。虽然这些曲牌并非原本即是为剧情所作,但是无论是选择这一曲牌的过程,还是伴奏演绎的过程,都必须是与剧情所贴合的。如果同样的曲调旋律,能通过不同的节奏、调性,甚至不同的乐器演绎,使观众立刻感受到这场戏需要表达的气氛,这就是音乐能够参与叙事的力量所在。
其次,在曲牌与曲牌之间,有大量的科介部分的喜剧效果,同样依赖于伴奏的精彩。如《三岔口》,两位主角在黑暗中搏斗,互相摸索对方的位置、思考对方的来头和门路,此时舞台上具备着充分的喜剧元素。喜剧元素来源于剧作情节的结构,来自于角色的念白与滑稽的动作,同时也非常依赖伴奏乐队的配合。虽然此时没有旋律,但具有诙谐性质的锣鼓时不时地辅助,对于舞台的烘托是一部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伴奏锣鼓产生的某些预见性,比如,任堂惠与刘利华同时后退,背靠背撞在一起这一喜剧效果,观众不仅仅是通过两个角色的走位而感受到的,同时此时伴奏里相撞那一刻的锣鼓响起,对于这个滑稽场面不仅是烘托,同时也是一种预见性。正是伴奏乐队营造的一个诙谐、幽默、轻松的氛围,使得观众能够预知到剧情的走向是往皆大欢喜的方向,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结局,这一点正是伴奏能够给予观众的。
昆曲剧目的曲牌、配乐曲谱,都是经过长期的试验,舞台演出的经验,数百年的摸索而汇聚而成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过程。作为伴奏乐队,如果仅仅是根据曲谱亦步亦趋,反而是违背了当初创制曲谱的乐队探索者们的初衷。如何精益求精,让伴奏乐队的配乐更加能够烘托剧情,展现不同场景的不同氛围,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