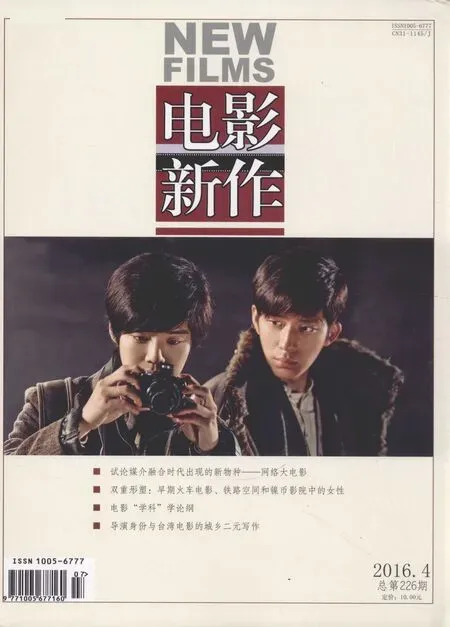电影“学科”学论纲
赵正阳
电影“学科”学论纲
赵正阳
本文按照从一般到个别,从现象到本质的逻辑线索,层层递进,描述了一个理想中的电影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并且提出了一种从学科视界研究电影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将是《电影“学科”学》的雏形。全文将电影学学科建设宏观问题条分缕析为“学科概念生成”“学科成立条件”“学科分化规律”“电影学跨学科现状”“学科区域形成”“学科矩阵生成”“学科知识分层”“学科研究路径”“电影学学科结构”“电影学学科体系”十个微观问题,并分别论述其内涵,进而勾勒出《电影“学科”学》的基本面貌。
电影学 学科 论纲
“学科”一词在我们日常的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从学科角度研究电影学的成果较少,但随着电影学知识的不断丰富,知识的体系化、分类化会成为必然要求。目前很少有把电影学本身作为学科或知识分类来进行反思、即由“电影学研究”走向电影学“元”研究的成果。笔者认为,以学科的层面来分析电影学及其学科体系的发展过程,是电影学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电影学学科建设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特征都很明显的领域,这一命题不但有“承上”的价值——即我国电影学科研教学的总体设计思路,而且有“启下”的作用——即电影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质量控制方法。要想实现对该问题的系统化研究,需要一个清晰的研究模型。笔者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的主持人,曾在《当代电影》2014年第12期上发表了“论电影学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在2016年第1期的《电影艺术》上发表了“电影学学科建设的现状研究”,以上两文重在厘清电影学学科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和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先后在2014年、2015年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两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上,阐述了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应该着力解决的若干“高级”问题。
无论是基本问题还是高级问题,其终极目的是构建一种从学科视界研究电影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将是即将出版的《电影“学科”学》的雏形。作为一个电影学的新领域,特别是作为一门旨在研究“学科”的学科,一方面要有严密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要致力于将电影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孤立的、散乱的命题进行逻辑整合;另一方面要具有方法论的特征,要能够体现出对电影学学科建设实践的指导价值。本文试图从逻辑结构的层面,描述《电影“学科”学》这一学科的基本面貌。
一、电影学学科概念的生成
“学科”一词所对应的英文是“discipline”,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学科”一词的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等。”这个解释并不足以呈现“学科”一词的丰富内涵。
在我国,“学科”一词始于清末学堂的分科教育,由一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其定义包含了“学术领域、课程、纪律、训练、规范、准则、约束、熏陶”等多重含义,如果究其英文文本含义,中文里甚至没有完全相对应的字眼可以涵盖。①不同的工具书对学科的解释存在差异,但其中都有一个共性,即认为学科源于科学,受现代社会发展影响。现代社会的任何一门知识都藉由教育得以推广,那么,这种以知识性质作为分类标准的学科概念,非但正式成为近代教育体制中分门别类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学术发展的基本架构。②
如果详细探究“电影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含义,很显然要超出我们惯常的对该短语的使用方法。大多数情况下,学者们所谓的电影学学科,仅仅是指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并不包含“规训、约束”等更丰富的含义。但西方学者如福柯、沙姆韦等恰恰在投入更大的热情来论证其“规训”的内涵。
欲考察“电影学学科”的概念,需要先探究“电影科学”的概念。什么是电影科学?“简单地说,电影学就是电影科学,或者叫做关于电影的科学。”③电影学是正确反映电影本质和规律的规范化的知识体系。众所周知,大家普遍把电影学的正式诞生时间定格在1948年,即法国巴黎大学成立的以艾迪安·苏力奥为首的电影学研究所以及该研究所出版的《电影学国际评论》开始。④由此出发,电影学学科则代表着电影学知识体系与知识权力的双重统一,电影学的学科研究旨在研究自电影学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过程,探讨电影学的体系结构与电影学分支学科的走向。
电影学学科的概念生成遵循着一个隐含的逻辑:“现象—知识—科学—学科”。实际上,任何一门学科都是按照这种模式生成的。福柯的知识主体理论中所描述的知识考古学大抵是对这种模式很好的注解:“由某种言语行为按它所独有的规则构成的,被认为是某门科学建立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们并不是一定会产生科学,但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之为知识。”⑤

二、电影学学科成立的条件
“电影学”与“电影学学科”的概念泾渭分明。所以,电影学研究的蓬勃兴起不等于电影学学科的水到渠成,但电影学学科的确立以电影学研究的成熟为前提条件。“任何可以称得上学科的知识部门都不是一些相关知识的简单堆砌,而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其中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些知识必须形成以概念、逻辑、原理、命题、方法等元素构成的知识结构,结构是学科存在的外在形式。其次还应该进入大学,登上大学的讲堂,这是一门学科被认可的象征。”⑥
笔者认为,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得以确立可以参考八大标准:一是“是否具有清晰明确的研究对象”;二是“是否形成严密共振的理论体系”;三是“是否拥有统筹兼顾的研究方法”;四是“是否产生引领发展的代表学者”;五是“是否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培养模式”;六是“是否出版了透视学理的学术著作”;七是“是否存在定期交流的学术组织”;八是“是否定期出版交锋观点的学术刊物”。
以上八个条件可视为电影学学科成立的宏观条件,但如果更为细致地考察、研究电影学学科建设历史与现状,仅有宏观条件还不够,必须将宏观条件细化为中观条件乃至微观条件。也可视为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的基础框架。这也是我们对学科建设进行历史回顾的主要观测点。
进一步考察三个层级的观测点,可以提取出决定电影学学科发展走向的三大要素,即“知识、人、权力”,我们发现,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学科之发生发展都是这三者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知识的要素经过系统梳理之后成为“对象、体系、方法”的集合;人的要素经过分化之后成为“组织、人物(学者)”的集合;权力的要素经过与“知识、人”的相互作用成为“培养模式、刊物、著作”的集合。以上仅仅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宏观状态。中观状态则体现为“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基本形成,“科学家群体、研究机构、教学单位、学术团体”的渐成规模,以及“专著和出版物”的持续问世。从微观层次来看,以上学科建设成果有赖于“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逐步确立,“研究内容具体性和抽象性”的有机结合,“研究力量支撑”的均衡发展,“作为高校教学科目”的普遍确立,以及“社会发展的持续需求”。
依据上述宏观指标体系,我们不妨用一个图表来说明当前电影学学科的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很显然,当前的电影学学科建设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多层次架构:
首先是有关电影学的知识积累已相当丰富。这源于两个要素,一是当前电影创作的异常繁荣,好的作品不断涌现,屡有电影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殊荣,使我们的学者拥有了充分的研究素材。二是国内学者对电影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电影学学科领域内,研究对象得以确立,学科体系得以明晰,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其次,从事电影学研究的组织和个人也不断增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等等,这些学科组织都以电影学研究为重要职责。另外,如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中专门从事电影研究的学科队伍不断壮大。最后,在学科权力行使层面,电影学人才培养模式日趋多样化和成熟化;电影学术刊物日趋品牌化,以《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三驾马车为龙头,以《电影新作》《电影评介》《电影文学》《现代传播》《文艺研究》《艺术评论》《艺术百家》《民族艺术》等电影专版为辅助学术刊物集群支撑着电影学学术成果不断推出;学术著作数量和质量都在稳步提升,中国电影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每年都会出版不同类型的电影学著作。

三、电影学学科分化的规律
现代科学知识发展大潮,冲击了整个学科领域,使得“跨学科”和“交叉学科”成为常态。电影学学科概莫能外。究其根本原因,乃是人类思维现象理论化、科学化导致的必然结果。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将自然哲学分化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造哲学⑦;16世纪的培根按照思维特征提出新的学科分类思想,即著名的记忆、想象、理性。⑧到了19世纪,恩格斯从方法论层面进一步总结了这种学科分化现象:“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当然,恩格斯也批判了这种现象:“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⑨
恩格斯反对以静止的、割裂的思维开展科学研究,提倡充分重视事物之间的“广泛的总的联系”。在对待学科研究的问题上,恩格斯给我们的启示是:
首先,事物的运动无处不在,一门学问通过跨越自身固有边界拓展问题域是普遍现象。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上不存在“孤立的”“静止的”“不跨”的学科。比如我们究其根本,电影学本身就是“电学”和“影像学”的跨学科,我们最常见的电影史学,本身就是电影学和历史学的跨学科,就连电影编剧学也是电影学和文学的跨学科。所以,简单地将跨学科割裂开来、独立于某一具体学科之外的观点都站不住脚。
其次,学科分化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学科之间通过跨越的方式形成新学科。新学科的孕育有过程,新学科的创立有标准。⑩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区分一门既有学科的主体域和跨学科域。A学科的主体域有可能是B学科的跨学科域,B学科的主体域有可能是A学科的跨学科域。比如自然科学领域有两个很典型的学科“物理化学”和“化学物理”,“物理化学”采纳物理学的理论成就研究化学问题;而“化学物理”则是研究化学领域中物理学问题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物理学而言,化学物理是主体学科域,物理化学则是跨学科域。
再次,学科分化是思维的内部运动和外部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一门学科从内部的交叉渗透到外部的独立发展,从潜科学阶段到显科学阶段,是一个充满矛盾运动的过程。比如电影学与美学的关系,最初可能是两个学科之间研究对象的交叉,但经过长时间的孕育,电影美学最终成为电影学的主体学科之一。
所以,笔者认为,电影学的学科分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学科主体域的确立。电影学学科主体之内的区域划分,即电影学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关系,即我们熟悉的电影史学、电影美学、电影语言学、电影创作学(包括导演学、表演学、摄影学、剪辑学等)、电影接受学等等诸子学科领域的逻辑划分问题。
第二、跨学科域的确立。电影学学科与其相关的外部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现象总结,包括诸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教育学,甚至与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建筑工程学等等诸多学科形成的跨学科领域。
跨学科是指学科间的配合与合作,它虽然增强了一门学科的丰富性,但并不意味着新学科的诞生。它尚未具有学科交叉的真实意义。但这些跨学科现象如果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和科学,将会随着“现象—知识—科学—学科”的隐含逻辑创生新学科,我们习惯于将这些新学科的最初形态称为“交叉学科”。交叉学科是已经存在并被普遍承认的学科,这种存在突破了已成定规的习惯,打破了自我和他人之间习惯的界限,推翻了事物现成的秩序。交叉学科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各科之间相互地对待对方的倾向要占绝对优势。交叉学科源自于由于无法凭借自己的学科单独解决问题,而引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所以,交叉学科意味着某种新学科的诞生。⑪

四、电影学学科主体域的形成与分区
以上问题衍生出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一门既有学科的主体学科域和跨学科域?这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老问题。在艺术学领域,狭义的跨学科意味着“从学科生成机制来看,它是由相邻学科与艺术学在研究对象上发生了一定的叠合,并存在研究方法上的交叉、移植、聚合等关联才形成的。”⑫
划分学科主体域和跨学科域的标准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仍然停留在电影学本体,属于主体域;如果已经出现了交叉乃至跨界,则进入跨学科域。这其中确实有模糊空间,但总的来讲还是比较明确的。跨学科在产生初期往往是相邻学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入既有学科。电影学领域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民俗电影学”与“电影民俗学”,前者属于类型电影理论,以民俗电影为研究对象,而后者则属于社会学范畴,着重研究电影中的民俗现象;再比如“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前者就是电影中的一种类型,而后者则是电影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领域,这个时候,“研究电影知识的传授”和“研究通过电影更好地开展教育”便产生了研究对象的叠合。但还有一种情况是,最初属于跨学科域的一些分支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被纳入了电影本体,也就失去了跨学科的意义,随之进入了主体学科域。
关于学科主体域。郑雪来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深入探讨过该问题,即电影学的分科问题。郑先生指出“苏联理论界虽然把电影学分成电影理论、电影史、电影批评三个分支。”“英、美的电影论著中,很少提‘电影学’这个词,多半只提电影理论、电影美学,但他们所认为的研究对象也是电影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⑬他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电影学,要充分重视“电影研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相结合”,以及“电影研究分科的细密化趋势”。
笔者所设想的电影学学科基本领域包含了三个层级,12个分区,每个分区都是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电影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构成电影学学科的第一层级研究,我们称之为“电影研究”,研究对象是电影现象,旨在调整优化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涵盖四个子领域:本质研究、语言研究、接受研究、文化研究,对应通常所说的作品论、创作论、反应论、运作论。
研究所有电影本质聚合形成的科学问题构成电影学学科的第二层级研究,我们称之为“电影学研究”,也可以称为电影的“学术化”研究,研究对象是电影理论,目的是“间接”地指导电影实践,其中包括四个子领域:电影史学研究(史)、电影理论学研究(论)、电影语言学研究(术)、电影跨学科研究(跨)。
研究电影学学科内部和外部所有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构成电影学学科的第三层级研究,我们称之为“电影学学科研究”,也可称为电影的“学科化”研究,研究对象是各个相对独立的电影学理论体系,旨在调整优化电影学学科内部子学科,以及电影学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包括了四个子领域:学科体系研究、学科组织研究、学科制度研究、学科文化研究。这四个相互联系和作用的部分,便是电影学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

五、学科主体域的拓展——电影学学科矩阵的生成
以上12个基本分区将所有有关电影、电影学、电影学科的知识系统涵盖在内。而12个分区在不同的研究维度上的投射,进而形成更加细分的学科矩阵。比如,按照宏观研究、微观研究、方法论研究的维度,可以形成以下空间学科矩阵。空间矩阵中代表学科维度的Z坐标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可以根据学者的研究方法的变化而调整的变量。现代社会学科日新月异,跨学科、交叉学科成为知识发展的常态化逻辑。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研究逻辑,而是根据学术群体的文化背景、研究指向进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本体系中的X轴和Y轴也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也是一个开放的结构。

六、跨学科域——电影学跨学科发展的现状
关于跨学科域。郑雪来先生没有明确使用跨学科这个称谓。他只提出“现在电影学除传统的分类法外至少出现了六个新的分科。”⑭即电影社会学、电影心理学、电影社会心理学、电影符号学、电影美学、电影哲学。笔者认为,这六个新的分科不应全部视为电影学的跨学科域。按照前文所述的区分主体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至少电影符号学不属于跨学科领域,最初的电影符号学是研究电影艺术从创作者、作品本身到感受者也被认为是一种符号或记号的传递过程。把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符号系统和表意现象进行研究的一个学科,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⑮但随着电影学领域语言学研究的兴起,电影语言学已经包含了电影符号学,并且成为电影领域从业者的必修课程。

七、电影学知识体系的分层
从知识层面来看。电影学学科应该是一个存在于三维空间内的、开放的知识体系,其横坐标(X轴)是“史”,决定着电影艺术随着时间的增加,客观环境的优化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演化)和知识范围的扩张过程;纵坐标(Y轴)是“论”,决定着电影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深度坐标(Z轴)是“术”,决定着电影创作实践的发展程度,即以电影艺术的方法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详情如下图所示:

八、电影学研究的路径
学科区域呈现“层次性”“连贯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反映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则是:“电影学研究”需要以“电影研究”为基础。电影学研究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必须由第一层级的某个具体的学科区域介入,而后上升到电影学研究的某个具体领域,这是一般规律。第一层级的学科区域也是和具体的“电影现象”直接相联系的,电影“学科”学认为,任何有可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知识系统,必须从某一具体的、与最底层研究对象相联结的学科区域介入,最终成为一门分支学科。所以,也就形成了A/B/C/D四个研究路径。如下图:
A研究路径:直接关注电影的本质特征,然后由此上升到对“电影史论”“电影理论”“电影语言理论”“电影跨学科理论”(以下简称“史、论、术、跨”)的研究。这是电影学的最核心部分。这类研究往往从哲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研究电影,充满思辨性和学理性;B研究路径:从电影创作领域介入“史、论、术、跨”第二层级。这是一个最为常见、也最符合学术研究一般范式的路径;C研究路径:从电影接受领域介入“史、论、术、跨”第二层级。如电影接受史、电影接受理论等;D研究路径:从电影文化研究领域介入“史、论、术、跨”第二层级。这是当前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这一路径有别于从创作介入,这和倪震先生对电影文化学的阐述不谋而合。⑯即将电影艺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乌提兹在《一般艺术学原理》中即认为“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狭窄的审美现象。”⑰包括《电影文化史》《电影批评史》《电影类型史》《电影地域史》在内的大量历史研究成果都可算作从电影文化角度进行史学研究的成果。

九、电影学学科的结构体系
首先,从学科结构层面来看。笔者认为,对电影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明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层次,四个范畴”:
“一个中心”即“电影学学科”,这一概念包含了与电影有关的所有知识,以及从事这一科学领域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的要素和组织的要素;另外还包括了学科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相关学科规训制度。
“两个基本点”即要明确“电影学学科”和“电影学专业”的区别。学科着眼于知识的逻辑性,其目的和指向都是“本质”“规律”“真理”“科学”“实证”等体系化和系统化的知识形式;而专业是课程的组合化和目标化,是人的逻辑。应该说,专业是某种体系化、系统化的知识进行有机排列组合之后,作用于具体的接受者而产生的效果预期。专业的目的和指向是一定教育系统内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笔者一直在阐述的《电影“学科”学》与《电影教育学》的核心区别正在于此:《电影“学科”学》是以知识为对象的科学,而《电影教育学》是以人为对象的科学。
“三个层次”即明确电影学的“源”“流”“域”的区别,哪些是源学科?哪些是流学科?哪些又是“域学科”?这就如同江河湖泊的分布,所谓“源学科”,就如同大江大河的源头,它决定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性质,学科的基本性质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如培根将人类的知识体系划分为记忆(历史)、想象(诗歌)和理性(自然神学)三个基本领域;马克思则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⑱所谓“流学科”,包括了作为“干流”的主体学科和作为“支流”的跨学科。所谓“域学科”,主要指在干流和支流影响下的、经过不断分化而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学科区域”。
“四个范畴”即“史”“论”“术”“跨”的区别。具体地说就是:史论——电影发展过程研究(历史);理论——电影理论研究(美学、哲学、批评学等);术论——电影创作研究(摄影、编剧、导演、表演、策划);跨学科论——电影学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电影产业、电影营销、电影教育、电影传播等)。其中,前三条是电影学学科建设的内部机制研究,第四条是电影学学科建设的外部机制研究。
具体结构如下:

十、电影学学科体系
在前不久举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到了学科体系,他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学科体系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要求,结合前一节中所述的电影学学科结构的思想,笔者认为,电影学学科体系的设计应秉承七大原则:一是“源学科的恒常性”,即电影学的源头活水,电影学的基本学科构成是什么?哪些是决定电影学本质属性的学科?二是“流学科的稳定性”,即决定着电影学学科建设整体面貌的“历史研究”“理论探究”“创作研究”应当具有相对均衡的成果产出;三是“学科域的可扩展性”,即电影学学科的发展始终处于和外部学科的互动和交融之中;四是“学科构成的逻辑性”;五是“学科结构的学理性”;六是“学科边界的开放性”;七是“学科建设的实用性”。笔者理想中的电影学学科体系如下图所示:

十一、结语
以上是电影“学科”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按照笔者的设想,以上十个部分一方面有机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相对独立,可以衍生出若干个次级研究领域。如通过对“电影学学科概念生成”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电影学从一种现象演变为一个学科的历史进程;通过“电影学学科成立的条件”的理论模型,按照时间阶段分项描述,可以撰写出《中国电影学学科建设史》;通过总结“电影学学科分化的规律”,可以探讨电影学知识体系和社会观念的互动关系,即电影学的辩证法;通过分析“电影学学科主体域的形成与分区”,可以总结出当前我国电影学研究的冷区和热区,进而为年轻的学者提供指导;通过界定“学科主体域的拓展——电影学学科矩阵”“电影学研究的路径”,可以研究我国电影学的学派问题,学者问题;通过对“电影学跨学科发展的现状”的研究,可以总结分析电影学与其它学科的互动关系;通过研究“学科结构”“学科体系”,可以指导电影学教材体系、专业体系的建设,从而设计出更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
当然,本研究的主旨在于深入探讨我国电影学领域“学科、知识、权力”的辩证关系,进而探索出一条电影学学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注释】
①J.Simpson and E.S.C Weiner ed.,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Volume 4,pp:574-575.
②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19世纪后半叶(约1850—1914年间),西方国家通过三种方法把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加以制度化:一、大学以学科名称设立科系;二、成立国家学者机构;三、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学科.知识.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213页。
③郑雪来:“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的一些设想”,《电影艺术》1984年第3期,第28页。
④王志敏:“电影学理论的作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1月,24页。
⑤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3页。
⑥劳凯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学理意识和方法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5页。
⑦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3页。
⑧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156-157页。
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1页。
⑩陈燮君:《学科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8页。
⑪翟亚军:“学科分类及相关概念梳理”,《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99页。
⑫张晓刚:《跨学科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学》,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⑬郑雪来:“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的一些设想”,《电影艺术》1984年第3期,第28页。
⑭郑雪来:“电影学及其方法论问题——兼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学的一些设想”,《电影艺术》1984年第3期,第31页。
⑮王志敏:《电影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⑯倪震:“电影理论研究:分清学科各得其所”,原载《当代电影》1988年第3期第63页。原文为:“文化学性质的电影研究,偏重于透过电影的表层结构,探讨该民族电影的哲学伦理精神、意识形态状况、文化哲学历史,它借助符号学、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等方法研究电影表意符号系统和审美主体对电影符号的认知;探讨电影表意系统和民族总体文化系统的关系;透过电影表意系统,研究该民族的神话模式、叙事原型、视学传统、批评历史以至民族思维模式等等。所以,文化学性质的电影研究更靠近社科人文类,较远离电影的生产实际和评论实际,是一种边缘交叉的人文科学,对于习惯了评论直接联系创作,评论立刻指导创作、检讨创作的思维习惯的中国电影界来说,电影的文化学研究是相对远离一些的。”但是,当前的状况是,从文化学介入电影学研究成为一种常态。
⑰乌提兹:《一般艺术学原理》(第1卷1914,第2卷1920)
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赵正阳,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教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电影学学科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BC02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