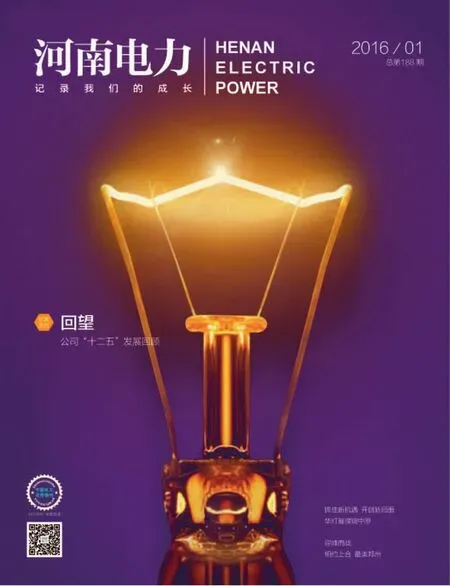对中原大地的灵魂扫描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印象
文/图_寇宝刚
对中原大地的灵魂扫描
——李佩甫平原三部曲印象
文/图_寇宝刚
中原是李佩甫构筑庞大文学世界的根据地,他一直匍匐在中原大地上耕耘,他所有作品中人物观念、行为方式、生存理念弥漫着浓郁的中原气息。尤其是《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构成的平原三部曲,递进式地呈现出了中原文化独特的生存环境和生命状态。
中原的土很厚,孕育出极具国民特点的民族性格特征。李佩甫总是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在中原文化独特的生存环境中,以乡村与都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的方式,讲述时代更迭的波澜壮阔、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不可捉摸。《生命册》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粒种子”,李佩甫发现了人与植物的隐秘关系,这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语调和情绪走向。植物的根都在土里,人与土地、与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意识无法割裂。由此,他挖掘中原的文化底蕴,揭示中原文化生态,描摹人情世态,为当代文学开垦了新的疆域。
“平原三部曲”创作历时15年之久,这是一个社会充满变革、飞速发展的时间段,其间社会形态、结构发生了巨大变革,15年前的状况已恍如隔世。从《羊的门》到《生命册》精准地记录了时代变迁的过程,不同时段创作的作品,是特定时期的世相与灵魂的图谱,为我们留存了时代的完整风貌。《羊的门》是乡村伦理和权力崇拜的黏合与撕裂,呼天成个人权威的树立是以传统道德为基础,他抓住了村民们对传统道德的集体无意识信仰,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形象。当呼家堡在物质方面进入“现代”后,他依然用传统的方式维持权威,人们依然被束缚在传统教化之中,在乡村政治权力下委曲求全。《城的灯》以一个家族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史,表现了城镇化进程中,平原人投奔“现代”的精神追求,及其在追求过程中艰难的行动选择。城市的灯火强烈地吸引着平原人,让平原人无法拒绝,平原人为了向城市迁徙,甘愿承受苦难与屈辱,不惜付出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不惜背负骂名。这迁徙是为了摆脱贫困与苦难,却付出了惨重的精神代价。《生命册》表现了市场经济和资本统领下的现代化进程对乡村伦理的挤压和破灭,展现了资本的血腥以及获得资本后的精神困境,在物质富裕之后,不但没有抵达幸福的彼岸,反而使人们深陷迷惘的雾障。
《羊的门》塑造了呼家堡“四十年不倒”的当家人呼天成的形象。他成功地把村人控制在掌股之间的胆识,与他以远大的眼光经营“人场”紧密相连;他用四十年的时间,营建了一个从乡到县、从省城到首都的巨大的关系网,这确保了他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神力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辉煌。
《城的灯》一书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观照,透视在中国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
哲学是文学的骨架,哲思为文学赋予思想的力量。李佩甫在创作三部曲中有强烈的哲学意识,这在卷首题词中有明确的意向。也正是李佩甫的哲学意识,使故事情节、人物命运有了某种“神谕”,更增添了作品的厚度,使小说超越故事的层面,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羊的门》题记:“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摘自《圣经·新约全书》。”这段《圣经》中的话,对应的是对极端、绝对权威的不容置疑,是从物质到精神的绝对统领。《城的灯》题记:“我无处可去;我无处不在……——摘自《未来书》。”这是逃离和守望的焦灼、自信、无奈,是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中,农民逃离乡村进入城市的艰难。《生命册》题词虽然没有引用宗教经典,却是具有哲学家名号的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名句:“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击,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很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味道。泰戈尔在上面所引诗句后,紧接着是:“我的眼睛向空阔处四望,最后才合上眼说:‘你原来住在这里。’”这分明是对生命过程的透析。
《生命册》是其继《羊的门》《城的灯》之后,“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是一部自省书,也是一个人五十年的心灵史。它追溯了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书写出当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破败的人生和残存的信念。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中,人物的精神产生裂变,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2015年,《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平原三部曲有很强的内在逻辑关系。《羊的门》以中原常见的24种野草的生态喻示生命的顽强、坚毅、恣肆,那是随遇而生、随遇而安的生命状态。《城的灯》展现的是词语背后的意蕴,是对扎根平原、从土地中生长出的词语的生态还原,揭示了隐藏在词语深处的隐喻内涵。《生命册》以对中原惯见树木的铺写,在具有坚韧、旺盛生命力的同时,又无不具有病态和残缺的状貌,无疑是对人们灵魂的解析。



在人们普遍把目光聚焦在《生命册》的时候,我个人更偏爱《城的灯》,这是一部有更高文学质地的作品。它具有精致而苍茫的复合美,浑然为打动你的一个整体,在几乎是淹人的美感中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在湿湿腥腥的土地、青草、麦秸混合的气息和纯净而虚幻的月亮花搀和的乡村里,贫穷的根扎得很深,生长出了茂盛的欲望和理想。欲望的沟壑与理想的光芒在同一出发点怀着憧憬,朝不同的方向进发。欲望在泛滥的洪流里冲破了防线和禁区,挣脱了贫穷的根的牵制,完成了一次漂泊之旅。理想在穷困的根中毁弃,在苦难而美好的行进中被穷困所吞噬。悲剧的崇高震撼人的心灵,迷离的霓虹背后是读者闪着泪花的无助的眼睛。在文学作品普遍失去情感力量,追逐浅阅读的现今文坛,《城的灯》是少有的能让读者落泪的作品。这泪是从心底里渗出的,是忍不住从眼眶里滚落出来的,是真和善对心的一次揪动。
刘汉香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闪耀真善美理想光芒的女性形象,她在与苦难的抗争中不断升华自己,也升华了她的环境。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一直在她的心中蒸腾。在贫穷和苦难中卓立的救世女神般的刘汉香,在浊乱的现世只留下一缕香魂。刘汉香在生活与情感的抗争中摆脱不了命运,让我们饮下一杯时代酿造的苦酒。然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冯家昌走过了一段个人奋斗的历程。欲望的火焰烧燎着他,甩掉贫穷、走入城市是他的终极目标。欲望的火点燃了他的城之灯,留下了可憎与虚谎的轨迹。冯家昌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刘汉香成为他的羔羊,他进了城,在光怪陆离中满足地生存着。谴责冯家昌能找出很多堂皇的理由,然而这种谴责又不免心中发虚,生活的法则在支持着冯家昌的行为,违背法则就是违背生活,违背他的欲望。违背欲望就等于重复先辈,生活使冯家昌复杂。时代的涡流沦陷了思维的智性,生活的丛林里充满的是生命的活力。
《城的灯》除深刻的内涵、广阔的生活图景外,充盈着丰沛的文学美。蕴积沉厚是李佩甫的一贯特点,在这部长篇中又露出了空灵和优雅,更衬出了苦难中带着酸楚的美好。文学不是摹写,是过滤后的表现,浓郁的感觉与体验使中原农村粗陋的日常场景生动而鲜活。对方言土语的思辨、剖析,揭示了惯常词语中深藏的集体无意识和潜意识,词语诱导人们的生存,词语里呈现的是生活的图式。《城的灯》秉承了李佩甫语言感觉化的特性,精妙之处触动神经,达到了难以言传的化境。

李佩甫,1953 年生,河南许昌人。国家一级作家,原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经过十几年的沉淀积累,李佩甫在2012年最终完成了他的“平原三部曲”:《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2015年,《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作者单位:许昌供电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