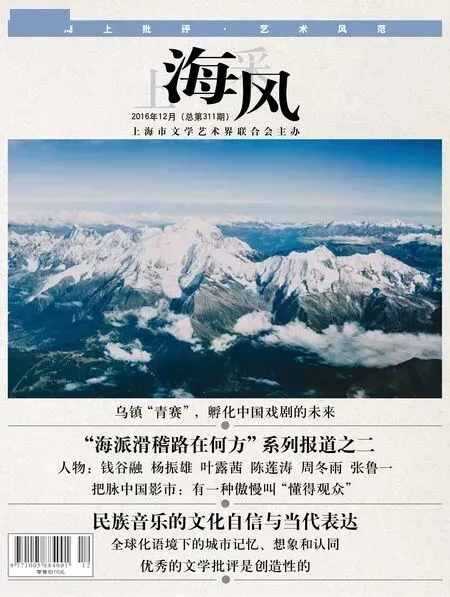《渺生一页》的真诚
文/彭小莲
《渺生一页》的真诚
文/彭小莲

彭小莲导演,作家。导演代表作有“上海三部曲”以及纪录片《红日风暴》等。另有《他们的岁月》《回家路上》《理想主义的困惑——寻找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等文字作品
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Danis Tanovic,1969.2.20—)拍摄的《渺生一页》,在2013年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这部片长75分钟的影片,讲述了一个非常平实的、关于波黑地区弱势群体的故事——
纳奇夫和他的太太萨娜达养育着两个年幼的女儿,他们生活在远离城市的罗姆人居住区。纳奇夫每天出门找活干,这才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太太赛娜达在家烧饭洗衣带孩子。有一天,当她正在晾晒衣服时,感觉到肚子的剧痛,等纳奇夫带她去医院检查时,却被告知赛娜达怀孕五个月的孩子胎死腹中,必须立刻做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买过医疗保险,手术费需要980波斯尼亚马克(相当于5000人民币),他们恳求医生先救人,以后分期付款。医生说,医院不允许这样做。在纳奇夫再三恳求下,医生的助理试图帮助他,得到医院领导的许可,但是依然遭到拒绝。回家之后,情况越来越坏,纳奇夫半夜再次开车把太太送到医院,医生仍然将他们拒之门外。无可奈何下,纳奇夫跑去罗马尼亚的贫困接济单位请求帮助。妇联的工作人员想尽办法,还是遭到医院的拒绝。但是妇联的人赶到纳奇夫家里,要亲自带赛娜达去医院,告诉她有他们在,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两次遭到拒绝,赛娜达已经完全放弃希望,她哪里都不去,就是准备在家里等死。万般无奈之下,妇联的人走了,纳奇夫赶去丈母娘家里,向赛娜达的妹妹借用她的保险卡,当他们赶到另一所医院的时候,医生还需要他们出示身份证。纳奇夫撒谎说,因为着急,身份证遗忘在家里。因为病情严重,赛娜达被推进了手术室,为此蒙混过关。医生指责纳奇夫不负责任,因为拖得时间太长,几乎引起败血症,但是总算抢救过来。手术后,纳奇夫就开着借来的车把太太接回家里;进门却发现,由于没钱交电费,家里已经被断电;第二天,纳奇夫拆掉了自己的破车,作为废铜烂铁卖掉以后,交了电费,还为妻子买回了每天必须服用的药。
这就是整个影片的全部,节奏非常平和,没有高潮戏,更没有泪流满面的场面。纳奇夫和他妻子赛娜达以及影片中的全部演员,都是业余的。这里的“纪实”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因为《渺生一页》没有了任何具有戏剧性的“起承转合”,事件的进展完全像纪录片一样,甚至都没有给观众任何暗示。没有任何渲染,就是窒息的生活,日复一日,观众是带着无望跟随这家人一点一点往前走,贴在摄影机的背后,充满恐惧地观望着。
这时候,你完全被剔出了银幕之外,你是和这一家人一样,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你不知道生活将走向哪里。黑暗的电影院,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让你做梦的地方,它把你拖进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让你面对面地去思考。特别是看见妇联的人在纳奇夫家劝说赛娜达那场戏,看见赛娜达那一根筋的样子,让你又急又恨,几乎想把她那个肥胖的身躯从沙发上拖下来。可是,她就是躺在那里,背对着镜头和所有人,横竖不肯跟妇联的人去医院。人家不断地解释,有他们陪同,医院会为她治疗的。但是,她什么都不再相信。镜头一转,是妇联的人拉开了自己的小车门,这时,你看见的是他们上车走了。纳奇夫呆呆地站立在自己家的门口。
看着影片,那种平静里充满了杀气,似乎赛娜达的生命就这么结束了,你所有的希望都跟随着小车一起消失,可是同时你又看见了一份穷人的尊严,她在两次被医院拒绝以后,宁可用面对死亡的姿态来保持自己最后的形象,也不能再去医院重新被人侮辱和歧视。
这就是导演的价值观,他把自己的视角放到最低,低到和纳奇夫一家同等的地位,以至于他会看见赛娜达骄傲的状态。丹尼斯不用俯视的眼光来对待他的人物,即使在贫困中,导演依然要表达出生命的价值,穷人的自尊。

丹尼斯·塔诺维奇,塞尔维亚小伙子,在他三十刚出头的时候,2001年就拍摄完成了第一部低成本电影《无人之地》。影片一鸣惊人,观众几乎都不知道克罗地亚那个荒山硬石里,是怎么蹦出这样一个天才的。《无人之地》在2001年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隔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无人之地》讲述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战士,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却是敌对的双方,他们在同一个战壕里对峙着。这就是二战以后,欧洲境内发生的最大一次规模的战争——波黑战争。波黑430万人口中,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这让丹尼斯痛心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实际上,没有天才。丹尼斯有过自己艰难的经历。他出身在波斯尼亚中心的城市,父母都是波斯尼亚人。他在那里长大、接受了基础教育;后来进入塞尔维亚大学的音乐学院,主修钢琴。正当他准备转为戏剧艺术专业的时候,波黑战争爆发,他们这些年轻人全部被送上战场。1992年,丹尼斯停止了学业,参加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摄影队,开往前线拍摄战地现况。
如今,人们报道波黑战争的很多影像资料,都是来自他们拍摄的影片。
两年服兵役完成以后,他离开了摄制组,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电影学院,开始了电影专业的学习。199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即使在读书期间,他也拍摄了不少纪录片,获得了很多项大奖。这些用生命换来的视觉思考,成就了他战后的第一部故事片《无人之地》。
很快,所有的投资人都追着丹尼斯来了,他还是非常慎重地选择剧本,一直到四年以后,他拍摄了法国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留下的剧本《情狱》。这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根据但丁《神曲》改编的,是他写的“《神曲》三部曲”之中的一部。这个《情狱》是一场人性和情感的“炼狱”,故事讲述了三个女儿、母亲各自的情感煎熬,以及他们共同面对父亲的故事。这不是他熟悉的生存环境,而且是从一个纯粹的男人电影《无人之地》立刻跳跃到一个纯粹的女人世界。令人吃惊的是,他依然用他非常个性的电影语言完成了影片。世界都在注视着年过三十的丹尼斯,特别是好莱坞,他们永远像猎鹰的眼睛,在追逐着猎物和天才。又是一个四年以后,2009年丹尼斯去了美国,在那里拍摄了《验伤》。
影片讲述的是后波黑战争——它让活着归来的战士,在心灵和精神上留下了创伤。这是非常典型的好莱坞影片,俊男靓女,大明星,女主角也是由西班牙的一线明星帕兹·维加出演。但是,影片却被一片华丽的、空洞的好莱坞制作裹胁着,如果你不看介绍,无法想象这是丹尼斯拍摄的电影。在那一份华丽下,你看不见人物,只有那一个个大明星的特写镜头,漂亮的灯光,专业的团队制作,而那个从战场上回来的战士,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子,他和美丽的帕兹·维加的爱情,让你觉得索然无味。似乎,这仅仅是一对明星的角逐,没有感受到人物的痛苦,没有让你体验到战争的创伤,一切的一切都是人为营造的煎熬,还有他们的流泪,不是让你想笑就是想睡觉。
接着,网上会看到翻新的信息,丹尼斯举家移民美国。我们这些丹尼斯的粉丝,都为失去了这么一个塞尔维亚天才而惋惜,他完全被好莱坞绑架了。好莱坞需要的是天才,但是他不需要个性。他们不会让你拍你想拍的电影,他们只能利用你的才气,在他们的轨道上运转,你将成为好莱坞的螺丝钉。
当年同样是来自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85年拍摄的第二部影片《爸爸出差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1989年完成的《流浪者之歌》再一次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之后,他也被好莱坞挖到美国去了,1993年他拍摄了《亚利桑纳梦想》,又同样动用了好莱坞的一线明星,虽然影片获得柏林电影节的最佳金熊奖,可是在美国本土,观众并不买他的帐。埃米尔一下明白了自己的追求,也清楚了好莱坞之梦,于是掉头离开了美国。回国以后,在1995年拍摄了《地下》,再一次为世界瞩目。影片荣获了199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199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丹尼斯重复了埃米尔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时,都会在银幕上迷失;他们对人物的把握,电影语言的表述,还有深刻的思考,都变得有点平庸。所以,丹尼斯也选择了回国。回国后拍摄了《丈夫的情人》,一个轻喜剧——在一个被战争扭曲的社会里,父子、婚姻、情人都乱成一团。直到有一天,波黑战争爆发了,大家都开始逃离这个即将消失的南斯拉夫小城时,只有父亲留下来了,他累了,他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他要看守住自己的小房子,于是被抛弃二十年的妻子原谅了丈夫,和他一起留守。
影片不像他的《无人之地》和《情狱》那么震撼,这些小清新只是让你感受到一种生活的质感,但导演回来了,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在寻找着他对这块土地的眷恋,这个已经不复存在的祖国——南斯拉夫。接着,他一点一点走下去,几乎是跪在自己的土地上拍摄,这就是2012年完成的《渺生一页》。影片获得了2013年柏林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
这是一群业余演员,显然他们还不是一家人;最让人费解的是,不知道导演是如何启发演员的,特别是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怎么能使得她们全然无视摄影机的存在。看着影片的时候,你会毫无疑问地确信——这就是一家人;他们之间微妙的交流,传达给观众的是一份穷人家简单的生活,又充满了人情味。
他们是丹尼斯塑造的角色,却看不见丹尼斯的痕迹。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控制现场的家庭氛围。那些自然到没有痕迹的表演,特别是那两个5岁和7岁不到的女孩,完全融入在这个破败的房子里,她们和纳奇夫和赛娜达一起生活着。你看见的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东西,然而正是在这日常中,你看见了被我们忽略的人情和生存空间,以及战争给这些普通人带来的艰难。
导演没有美化生活,纳奇夫的牙齿都脱落了一大半,妻子赛娜达更不是美女,一个吃垃圾食品长大的女人,肥胖得有点变形,动作也不灵活。《渺生一页》让你看见的是我们自己周边的生活,那些身影和动作,熟悉得让你忘记这是一部外国影片。当纳奇夫和妇联基金会的人一起开车回家的时候,导演将摄影机放在背后,我们只能看见一个背影,纳奇夫掉头和人说话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面目不全的侧影。他说:他上过前线打仗,现在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得到,没有工作、没有补助,只能生活在这一片简陋的垃圾房里。
他说得非常平静,像在诉说别人的故事,然后就是讲到了朋友的弟弟,他们把他弟弟的尸体带回家了。真是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变得那么小,就在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子里就装下了,结果打开一看,是弟弟的头颅,大家都说不出话。他们都为这场荒谬的战争付出了代价。然后,纳奇夫掉过头,默然地朝前看去。所有的悲哀,竟然是如此平静地展现,整部影片里面,没有眼泪,没有呼天抢地的嚎叫。而赛娜达更多的时候,完全像一个病人背对着镜头,背对着大家。但是,参照这个伤心的家庭,却是两个像有多动症的孩子,她们总是那么快乐。父母对家庭的责任感,让她们一点不能意识到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她们是快乐的!一种生命的呼唤在对比,于是,贫困中的欢乐,让你感觉到更加难以表达的绝望。
直到最后,赛娜达的手术成功以后,也没有看见欢天喜地的场面。是纳奇夫和邻居去村子的小酒吧里喝了一小盅,然后他为赛娜达买咖啡回家。显然那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劣质咖啡,通红的颜色,哪里还像咖啡。这时候赛娜达幽默的对丈夫说:嗷,这咖啡都挺色的!丈夫笑了,全部的幸福都在这里。最后,丈夫靠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妻子,他把手放在妻子的手臂上,赛娜达说,你的手好冷啊,于是纳奇夫把手收了回去,慢慢地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影片结束。
一切都那么生活,可是你却会感受到很多很多。这就是丹尼斯的电影,他用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真诚地拍摄。所以,在一个简单的故事里,你却会被真诚深深地打动。当电影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简单,世界电影都渐渐被好莱坞大片占领,可真正在打动你的,却是导演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他拥有的真情实意。那是不断翻新的高科技永远无法替代的!真诚,使得影片的价值诉求撼动了我们纤细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