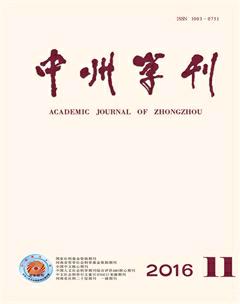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进路
牛庆燕
摘要: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理论形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生态觉悟,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关键词: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伦理”—“道德”形态;文明的生态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091-06
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也是人类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不断拓展、道德关怀的范围不断扩宽、道德知识和视野不断丰富和开阔的过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流派从彼此诘责对立到对话交流、沟通融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但是,如果沉浸在西方生态主义为我们设计的理性王国中并不断进行“学派”和“流派”的碎片化式的解读,那么,我们不仅无法走出不同生态学派和流派的理论冲突,而且容易遮蔽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涵,因此,“入流”之后如何“出流”,并在“出入流派”之间进行生态主义的“形态论”的研究方法的革命和“伦理精神”的呈现成为可能的研究趋向。
从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分裂和对峙形态向生态主义“伦理”—“道德”辩证同一的价值生态方向的演进,是人类道德哲学发展的逻辑进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走向。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然而,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辩证互动的价值生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价值生态觉悟和文明生态觉悟,也是生态主义理论形态发展的精神自觉。
一、生物中心主义的“道德风险”
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意志的觉醒和生命尊严的获得相对于中世纪神权对人性的严酷压制是历
史的进步,但是,脱离了中世纪神权和上帝终极伦理实体的“羁绊”,当生命个体通过对“道”的主观把握和形上理解,最终内化为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德性”素养时,却由于缺乏客观性和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其中,“生物中心主义”在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遭遇了“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以及不可避免的“道德风险”。从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的伦理学”、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伦理学”到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与保尔·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其理论轨迹逐渐铺展开来,共同把人与人之外的所有生命个体纳入人类的道德关怀范围内,从而现实地将生态主义思想由原始蒙昧时期的“伦理形态”推进到“伦理”—“道德”对峙形态,这是西方伦理道德精神呈现的主要历史哲学形态。
第一,动物解放论基于“功利主义”和“平等原则”,倡导拓展道德关怀范围并增加动物福利。动物解放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澳大利亚著名哲学家彼得·辛格在《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一文中,以妇女和黑人要求平等权益的解放运动为切入点,认为解放运动的宗旨就是要拓展传统伦理学道德身份的范围,动物的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延续,进而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我们应当把大多数人都承认的那种适用于我们这个物种所有成员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它物种身上去”;“人类的平等原则并不是对人们之间的所谓事实平等的一种描述,而是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人的一种规范”。①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启发,辛格认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因为具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和人一样都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因此应当平等地考虑人的利益和动物的利益,这是动物生命平等的伦理原则。由此,辛格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他反对物种歧视,尤其反对用动物个体做实验和杀戮动物,甚至认为人类食用动物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并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倡导增加动物的福利,杜绝一切对动物的伤害行为。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从人类自身特有的道德关怀出发,抨击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利益的狭隘视界,打破了传统伦理学公认的关于道德等级划分的界限,关注自然界中的所有动物个体,具有明确的“个体意识”和“主体意识”,第一次使道德关怀的范围得到了拓展,使人们的伦理思考建立在理性的“道德反思”之上。
第二,动物权利论基于“道德义务论”提出动物的“天赋价值”“固有价值”,倡导尊重动物的“权利”并确立了动物的“生命主体”地位。动物权利论的代表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从康德的道德义务论出发,认为某些动物和人一样都拥有“天赋价值”或“固有价值”,它们自身就是终极目的,人类以外的所有动物都是“生命的载体”,作为平等的生命主体,动物和人一样都有欲求、有记忆、有未来感、有思想,并同样能够感受快乐和痛苦,拥有与人类同样的权利,因此,共同的生物学基础决定了人类应当尊重动物的权利,并把动物权利运动看作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主张禁止动物实验、取消动物的商业性饲养和纯娱乐、消遣性的狩猎活动。围绕当时社会蓬勃兴起的人权运动和争取自由、独立与民主的社会运动,雷根倡导个体生命的道德权益与自由意志,并认为只有生命个体才享有权益,道德地位和权利只能赋予生命个体。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平衡法则决定了在强调动物“内在价值”时也不能忽略“工具价值”。同时,如果说动物拥有“天赋权利”,那么,动物自身却不能主张权力,当人类意志赋予动物权力概念时,便带有强烈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意蕴;如果说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那么,对于动物却很难达到。因此,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同情心”的形式赋予动物以“生命主体”的道德关怀资格,但是却带有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倾向,雷根以“原子式”的思维方式解读“动物权利”但并未上升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实体论”的高度,于是带来简单的集合并列,并潜隐着将人类个体生命权利凌驾于动物生命权利之上的“道德风险”。
第三,“敬畏生命”伦理观将“爱”“同情”和“善”的伦理原则赋予所有生命个体,倡导尊重生命、爱护生命。法国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基于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和伦理态度,认为伦理学是无界限的,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个体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生命都是唯一的和神圣的,人以及自然界中所有的动物生命、植物生命都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对所有生命个体肩负着同等的道德责任和伦理使命。“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②“在本质上,敬畏生命所命令的是与爱的伦理原则一致的。只是敬畏生命本身就包含着爱的命令和根据,并要求同情所有生物。”③由此,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施韦泽意识到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是褊狭的,应当把所有生命都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进而打破了传统伦理学固有的道德等级高下的观念,并拓宽了自然界“生命”的概念。施韦泽认为人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所有生命存在紧密关联,人类作为拥有道德理性思维能力的生命物种应当善待自然并对所有生命采取“敬畏”态度,依靠道德自觉力将其他生物的生命意志融入“我们”的生命意志,形成“共同”的生命体验,进而将“爱”“同情”和“善”的伦理原则赋予所有生命存在。然而,当遭遇“道德律”与“自然律”的分歧与冲突时,“道德律”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自然律”,即人类可能会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而以牺牲其他生物的生命为代价,在道德的困境和冲突中如何固守“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四,“生物平等主义”伦理观主张所有生命都具有固有价值,它源于生命存在本身的“善”,这种传统的生命目的中心论最终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美国哲学家保尔·泰勒的“生物平等主义”和“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倡导“生命平等”并极力否定“人类优等论”,他认为人类作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与其他生物都是自然进化过程的结果,每一种生物个体都是生命目的中心,人类与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物种是相互依赖彼此联系的统一体,人类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因此应当尊重自然并心存“谦卑”和“敬畏”。同时,泰勒提出生物的“固有价值”概念,他认为生命至“善”,所有生物的生命本性决定了其拥有内在的“善”。“善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于任何人的信仰和观点。这是一个可由生物学证据证明的论断,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东西。”④这种善源于生物的生命本性,成为每一个生命个体所具有的“固有价值”,如果对自然持有尊重态度,那么便承认所有生物自身的“固有价值”,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权利和道德价值。“应该赋予具有内在价值的物体以道德关注,所有的道德主体有责任尊重具有内在价值的物体的善。”⑤因此,人类有责任考虑其他生命形式的“基本需要”和“非基本需要”,在“生物平等主义”的伦理关怀下,人类对于自身做出的伤害行为应当进行伦理补偿和生态恢复,这是人类应当担负的道德责任。
由此,“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的理论思想虽然各具特色,但是不约而同地把立论的依据置于生命个体,只是关注生命个体的道德权益,而没有考虑生命的过程性、生命个体和其所处的生态共同体的关系以及生物共同体的实体性,本质上是“生物个体主义”的哲学表达和理性反思基础上的道德关切。伴随着人类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迅猛推进,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时代,并在征服自然的“战役”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是,当“胜利”的喜悦还未褪去且“伊甸园”的梦想尚未实现之时,却遭到自然界无情的“惩罚”和“报复”。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萌生的“理智的德性”的基因催生了追求意志自由和道德自由的哲学传统,但是,道德的“良心”以回避现实的方式确保内心的“圣洁”,由于缺乏生命“共同体”生活的原生经验和实体性追问,便陷入自欺欺人式的抽象的“自我”中,这种“优美的灵魂”与“满载着忧愁”的灵魂使“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不能建构作为“整个的个体”的“伦”的精神基地,最终沦为缺乏“精神”的集合并列和缺失生态行动的道德说教。当生命的“居留地”和伦理的“实体”家园缺位时,便潜隐着难以预见的“道德风险”,进而遭遇现实世界的生态难题。因此,在西方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史上,这种关注生命个体的伦理情怀是对西方传统伦理学相关理论和概念的移植和延伸,也是生物中心主义的“伦理”—“道德”对峙形态所遭遇的现实难题。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悲怆情愫”
20世纪30年代,生态中心主义思想开始在西方伦理学界呈现并引起广泛关注,它以“实体性”的思维理念取代了“原子式”的思维方式,透过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思想使“伦理”回归,避免了人类“中心”论视野下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黑格尔曾经以“悲怆情愫”表达个体向实体皈依的伦理情态,“在个体性那里实体是作为个体性的悲怆情愫出现的”,“实体这一悲怆情愫同时就是行为者的性格;伦理的个体性跟他的性格这个普遍性直接地自在地即是一个东西,它只存在于性格这个普遍性中”。⑥生态中心主义的“悲怆情愫”基于“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和系统价值,把自然界的无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预设为道德的主体,超越了以关注生命个体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生物中心主义”各流派思想,推翻了以关注人类利益为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论”,同时颠覆了生态主义理论世界中长期被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发展为可能的“生态整体主义”理论形态,因此是重要的哲学范式的转换。“就生态的范围而言,整个地球系统就是一个整体,必须从整体的角度考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⑦但是,伦理的回归遭遇了道德的强势,生态衷心主义陷入“伦理”—“道德”的悖论与风险之中。总体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包括以下三个流派: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第一,“大地伦理学”以实体性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通过拓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生命个体向自然生态实体“归依”。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将自然生态系统中所有生命个体预设为生态共同体中的成员,由此将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人类”延伸到整个“大地”。“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他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⑧这一观点使整体论的伦理观念与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相结合,并完成了对道德共同体边界的扩展。大地伦理学认为,“当一件事情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⑨。由此,整个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是宇宙中最高的善,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和“大地”上的普通一员。“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⑩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这是生态实体论的思维模式,也是人类对自然的重要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感悟。“土地伦理进化是一个意识的,同时也是一个情感发展的过程。”人类不应当仅仅从工具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角度丈量“土地”,内在价值与系统价值应当成为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的价值尺度。
第二,“深层生态学”通过确立“自我实现论”与“生物圈平等主义”的伦理原则倡导实体论思维视角下的主体性自觉。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将深沉的哲学思考与实践生活的体验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开创了进行生态哲学思考的新范式。奈斯的“自我实现论”极力克服个体自由意志的觉醒所造就的理性的“自我”,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应当是由“小我”提升为“大我”,“大我”是人类生命主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自我”,是生命“个体”向自然伦理“实体”的归依,也是人类自我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相同一之后的“整个的个体”。因此,在西方生态思想史上,奈斯的“自我实现论”是深层生态学的重要的理论表达,是人类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类生命潜能的呈现。“自我实现论”是“生物圈平等主义”的理论前提,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共生和谐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自我实现”,这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最大程度的展现和最大程度的“共生”。自然界中所有生命物种对于整个生物圈的平衡、稳定与持续性存在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通过“自我实现”,人类应当发现自然界中的“美”与“力量”,进而实现对自然生态世界的伦理“认同”,推进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这是人类内在的“善”和“良知”,也是实体论思维模式下的主体性自觉。
第三,“自然价值论”以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思维论证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为人类善待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道德依据。美国环境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认为“价值”的产生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自然生命系统因其博大的创造力而成为价值诞生的源泉。“在我们发现价值之前,价值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很久了,它们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大自然既是推动价值产生的力量,也是价值产生的源泉”。亿万年的生命进化历程使自然生命物种更加多样化、精致化和复杂化,从而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因此,在整个地球生态共同体中,自然生态系统拥有本身固有的纯粹目的和与生俱来的内在目的,所以具有最高的“系统价值”和最大的“内在价值”,不仅人类生命主体,而且所有动植物应当拥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以“实体性”的系统论思维方式取代了“原子式”的集合并列分析方法,将价值主体无条件地扩展到自然世界的一切生命,乃至自然生命系统本身。他认为“内在价值”的主体是包括人、动物、植物、有机物、生物圈等一切具有自控调节功能的个体、整体及其生态系统,否认人类是唯一的“内在价值”主体和绝对的生命主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自然价值论”思想的提出不仅是生命共同体的“精神”表达,而且也是一种伦理觉悟。
戴斯·贾丁斯认为:“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由此,生态中心主义的思维路向以整体共生性原则和系统优化原则为逻辑起点,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系统整体性和协同进化的动态过程,它将伦理关怀的范围由人与生物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类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和“实体性”觉悟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人类理性精神觉解的转折点。但是,仔细思考不难发现,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取向的生态觉悟,同样遭遇“实体性”思维理想与“个体性”自由的现实之间的悖论,由“自然生态”概念引发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存在现实的理论困惑和道德风险。如果说古典伦理学追求的至善目标是“幸福”,那么,当代实践论哲学追求的至善理念是“自由”,“理性主义”催生的西方近代道德哲学过度痴迷“意志自由”和“规则契约”意识,人类在不断地追问自由的理性个体之间以及理性的生命个体与现实的生态主义世界“如何在一起”的问题,然而却遭遇“个体”与“共同体”、正义论与德性论、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道德与幸福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为,自恃“聪慧”的人类,或者会隐匿在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庇护下,完全不见人类的生命主体性;或者会脱离自然生命共同体,甚至使“个体”与“实体”相分离,成为没有任何规定性的“人”,这是黑格尔所言的“悲怆情愫”所遭遇的“伦理”—“道德”悖论。由此,人类如何在彰显道德“自由”的同时又获得自然生命共同体所带来的“安全感”,成为当代人类必须认真思考的现实难题。如果说道德的生命个体与不伦理的自然生命实体是生命个体的实践理性,那么,伦理的自然生命实体与不道德的生命个体就是生命“共同体”的精神体认。因此,生态中心主义似乎无法走出“伦理”—“道德”的悖论怪圈,陷入了“伦理”—“道德”形态的对峙与混合状态。生态中心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狭隘并且具有致命缺陷的生态“理性”,最终没有逃脱人类“中心”的樊篱,生态理念在“他者”的凯歌行进中最终深陷“为我”的泥沼,因而只能是不够彻底的生态智慧以及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临界”状态,也不可能使生态融入文明,并成就“生态文明”。
三、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
价值生态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难以摆脱“伦理”—“道德”的分裂与对峙的命运,那么,未来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旨归应当是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包括生物中心论、生命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理论形态和价值生态,这是生态主义伦理思想诸理论流派多元整合的生态发展趋向,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第一,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由“人—自然—社会”交织起来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与文明生态的平衡态。在人类半个多世纪的生态觉悟进程中,人们逐渐明确,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根源是人类的“精神危机”与人格生态危机,外部的自然生态危机与内部的人格精神危机的迅速累积将会导致人类文明“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链条的断裂,从而带来严峻的道德危机甚至是不可逆性的“文明危机”,这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文明灾难。因此,“生态”应当走出“自然”科学,并走进由人、自然、社会交织起来的系统生态整体,不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生态”,更是“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和“文明生态”,不仅是纯粹思辨和抽象的哲学概念,更是价值理念、道德精神、伦理精神、生态智慧和文明智慧,这是“自然生态”向“文明生态”的转换和跃迁,是自然生态平衡、精神生态平衡与人类文明的价值生态的平衡,同时也是“生态哲学”和“生态理性”的文化觉悟和文明觉悟。
第二,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辩证互动的生态链条。如果说西方道德哲学是追求“道德自由”和“理智德性”的理性主义传统,那么,中国道德文明则是道德自由强势背景下,伦理与道德共生、伦理优先的“精神”传统;如果说,西方社会遭遇了个体道德自由和伦理实体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对峙与分离,从而使社会至善的伦理诉求缺乏个体至善的可靠根基,那么,中国社会则经历了伦理诉求与道德追求的分离和矛盾,甚至“伦理”—“道德”精神链条的断裂,进而使个体生命至善的德性追求难以带来社会至善的伦理诉求。然而,在整个中西方道德文明演化史上,在绵长的“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对峙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演进趋向却是在道德自由的强势话语背后对“伦理精神认同”和“伦理同一性”的价值追求,是“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辩证互动的生态链条,是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
第三,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伦—理—道—德”辩证互动的“精神”脉络。在经济理性充斥的当今时代,应当对接“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链条,个体道德自由应当体现人类文明的“精神”内涵和“共同体”的伦理前景,人类个体能够向自然生命“实体”皈依,成为具有“精神”的“整个的个体”和“道德的主体”;伦理的精神认同应当是在“实体性”反思的基础上宽容并尽可能包容不同生命主体的“道德多样性”和“类”的多样性,在承认意志自由和理性反思的历史进步性的基础上,使现代人类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底蕴。因此,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是人类伦理“精神”的觉醒,是对全球范围内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忧思,也是对整个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忧虑与警醒,从而成为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当环境难题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的时候,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精神内涵必须获得生命“共同体”的精神认同以及现代意义上人类主体间的生态认同与自我认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与文明秩序的碰撞和冲突中寻求相互包容与理解,当生态主义思想的精神气质和理论特质慢慢彰显,其流派所具有的“形态”气质也便呈现出来,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中国形态”。
注释
①[澳大利亚]彼得·辛格:《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江娅译,《哲学译丛》1994年第5期。②[法]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陈泽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29页。③[法]阿尔贝特·施韦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页。④Paul W. Taylor. 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Princeton univercity press, 1986, p.61.⑤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Englewood Cliffs N. J.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Prentice-Hall, Inc, 1993, pp.73-86.⑥[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页。⑦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⑧⑨⑩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3、213、194、214页。[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许广明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