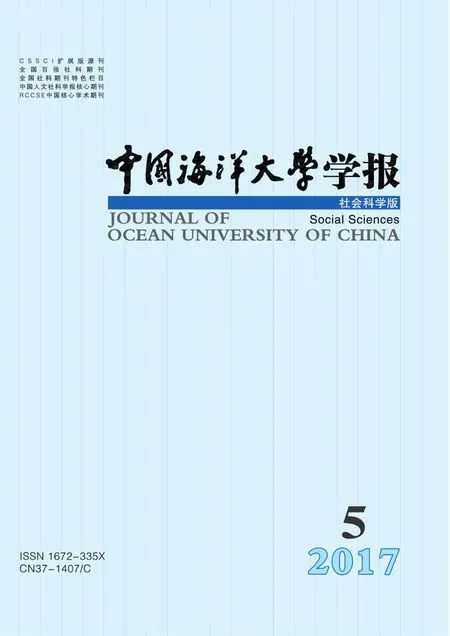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法律的反思与定位*
余 敬 唐欣瑜
(1.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2.海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法律的反思与定位*
余 敬1唐欣瑜2
(1.海南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2.海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58)
行政规划是填海造地前瞻性的目标控制工具,长期以来,填海造地的行政规划均已经济利益为导向,“向海要地”势头迅猛发展。在处于入工业社会中后期阶段背景下,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法律与政策明显偏离了海洋生态利益保护的重心与轨道,因而必须改变当前仍以工业文明式的填海造地行政规划,转向生态文明导向的行政规划。由于我国当前填海造地存在填海造地规划法律体系的缺位、填海造地规划中生态原则的失衡、环境规划措施的乏力的问题,需要从构建海洋填海造地专项规划法律体系、拨正填海造地规划法律中生态原则的定位、健全填海造地环境规划的具体措施来改进。
填海造地;行政规划;生态环境;海域开发
填海造地是将海域变为土地,进而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土地利用需求,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方式。填海造地历史悠久,许多沿海发达国家如美国、韩国、日本、荷兰等均通过海洋规划填海造地满足城市化扩展需求,带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填海造地规划对于社会发展可谓是一把双刃剑,只不过对生态环境的伤害暂时被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效益性所掩盖。当前我国填海造地不断升温,尽管缓解了住宅、工业用地紧缺的态势,与此同时也带来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在规范填海造地行为时能够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是填海造地行政规划必须面对的考量与取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改变以社会经济效益的单行路线,转为生态环境效益为导向,对填海造地行政规划发展趋势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
一、传统行政法视域下的填海造地与行政规划
行政计划以及基于行政计划而展开的计划行政,被称为现代行政的重要特色之一。[1](P562)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规划权是政府的一项公权力,成为政府实现空间资源配置、进行城市土地利用管制等的基本手段。行政规划的目的是公共利益,其基本出发点政府以公共利益而设定的特定行政目标,按照公众需求与政府财政预算计划,为普通公民提供基础公共服务,合理分配公共资源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事先“设计”为特征的行政规划便成为政府实现行政目的的一种新型活动方式。[2]海洋规划是在一定时期内,统筹安排海洋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活动的战略方案和指导性计划。[3](P416-421)海洋规划的内容具有特定性,不仅包括了从整体上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生态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也包括具体区域海岸带用途规划、海洋植被保护、港湾的利用等内容。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是海洋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海洋的行政规划直接决定着填海造地的总体方向、填海位置、填海进度、填海经济利益协调等内容。
填海造地是一种特殊改变自然资源形态的人类活动,即将海域形态的实施对象改变为土地。由于沿海城市土地供需矛盾成尖锐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造成填海造地活动的失序,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社会不稳定、土地利用失序等多种恶果。海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公物,[4](P23)是全体公众甚至是全人类的共同自然财富,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一旦实行填海造地后即基本不具备回复性。然而,填海造地的实施并不是通过项目使用人的直接申请填海、使用,而是通过政府现有规划,在项目论证、环评合格后,须经规定得到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才能实施该项活动。一般而言,填海造地首先必须通过政府对海域长期规划与短期规划,认为在符合填海造地规划的区域可以进入下一步许可论证,在通过征询民意、专家论证、填海造地计划论证等阶段后,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填海造地项目实行许可制。即填海造地必须首先符合规划,其次必须符合特定许可。
从域外填海造地法律规定来看,多通过行政规划与许可的方式进行法律规制。如日本围填海管理的核心是围填海规划许可的审批,其《公有水面埋立法》就规定了任何围填海行为要获得围填海许可。[5]美国海域使用管理相关管理法规中明确了联邦政府要求各州在海域使用前必须制定域使用规划和区划,且实行海域使用许可证制度。[6]韩国《公有水面围埋立法》对填海埋立许可制度,所有权制度进行系统规定,确保公有水面利用与管理活动符合国土整体功能规划要求并于环境保护相协调。[7]我国同样从行政规划与行政许可方面对与填海造地进行了规制。如《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条“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该法规定海洋功能区划应与城乡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相互衔接、配合,形成合理的、科学的规划开发利用方案。*参见《海域使用管理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
具体而言,根据行政规划的定义与法律授权,填海造地相关政府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对辖区范围内海域用途、自然形态、环境状况、社会发展需要等因素综合考量后进行总体规划,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的目标。在规划设定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与对区域内填海造地涉及到的村民、渔民、运输商等直接或间接主体进行协商,最终决定是否将该海域规划为填海造地可实施海域。当某海域被确定为填海造地的区域后,通过与相关利益方进行沟通协商,采取法定的程序与方法开展填海造地的行政确定裁决工作。填海造地规划一旦确定后,即对该区域填海造地形成多方面的规制,直接影响填海造地的具体进程。
二、填海造地法律制度的演进趋势:农业、工业填海到生态填海
填海造地在世界沿海国家发展史上是一种常见的扩展陆地的方式。如日本、美国、荷兰、韩国、我国香港地区等,均经有着较为丰富填海造地的历史,如荷兰有1/5的土地面积是通过800年来的填海造地形成、日本沿海城市约有1/3的土地都是通过填海获取的、我国香港填海造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6%,[8](P30-45)我国仅经国家海洋部门批准的填海面积到2011年为31,771.82公顷。虽然有很多国家沿海国家都经历过大规模“向海要地”阶段,但简单考察下主要沿海国家填海史,即可发现填海造地发展有着共同的轨迹。
日本的填海造地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明治维新以前以贸易农业开发为主的围海屯田;二是明治维新到战后20世纪60年代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填海造造陆;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第三产业开发为主的人造陆地再改造。[9]由于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沿海滩涂减少、港湾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水水质恶化等环境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加强了海岸保护,改善海岸环境,填海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建设,形式主要是人工岛,且充分听取民意,暂停了非公益性填海项目。可以说,日本已经由工业填海时代进入了生态填海时代。
荷兰的围海造地也经历了类似三个时期:第一阶段,生存与发展性围垦。即为改善与提高沿海居民生活条件、生存环境而进行的围垦,时间为1953年以前;第二阶段,国家安全性围垦。荷兰作为沿海国家,来自于海洋的威胁陡增,因而需要安全性围垦,该阶段时间为1953-1979年。第三阶段为安全与河口生态保护围垦。该阶段为1979-2000年。到21世纪后,荷兰除抵御海潮和防洪安全需要围垦外,更加注重海岸生态恢复工程。开始研究退滩还水方案,实施与自然和谐的海洋工程计划,[10]围海造地的主要动因是生存安全的需求和环境需求。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海洋综合管理的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提出对伸到大陆架外部边缘的海洋空间利用。但在20世纪60年代,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石油污染严重、到70年代海洋生物资源和沿海海域活动受到极大破坏和影响,[11]基于此,美国1972年出台了《海岸带管理法》,重点是环境保护,着力恢复和增加海岸带资源,对公众参与的规定也非常明显。同样,我国香港、韩国现代填海造地理念上均以海岸带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为宗旨,注重公众参与。
我国有着绵长的海岸线,早在汉朝就开始对围海造地,1949年以来,共经历了四次较大的围海造地潮: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围海晒盐;第二次是20世纪60-70年代,进行的农业围海造田;第三次是20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滩涂围垦养殖;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围填海的用途呈综合性发展趋势。[10]虽然我国填海造地已经注意到环境影响问题,用途上开始综合性发展,但总体上我国当前填海仍以工业用途填海为主。
观察世界填海造地发展史,填海用途上大体经历了农业填海、工业填海、生态填海(公益填海)三个阶段,填海造地逐渐回归到公共管理原本目的与轨道上来,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强烈,填海造地不失为一种成本较低的土地获取方式,但工业用途的填海造地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恶劣影响日益凸显,首先,资源减少风险剧增。填海造地会对海岸带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湿地、滩涂等资源枯竭;其次,环境风险加剧。填海造地不可避免的造成生物多样性的缩减,渔业资源衰退,海洋水环境污染加剧,海岸景观不可逆转性破坏等恶果;最后,社会不稳定风险凸显。填海造地对沿海居民生存带来毁灭性的改变,权益损失严重,渔民、村民上访事件时有发生。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益性应作为填海造地许可唯一许可评价标准,应结合国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来综合评价,应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来决定填海造地用途。当社会快速发展阶段,对农业用地、工业用地需求较大,而社会处于人地关系矛盾紧张,对土地需求较大时,则可以将填海造地规划用途指标部分偏向农业填海、工业用途填海;当社会基础工业发展较为成熟阶段,对土地需求减小,人地关系矛盾减缓阶段,应将填海造地用途的行政规划、行政许可调控偏向对工业填海、农业填海的规制轨道上来,填海造地的重心应放到公益填海、生态填海上来,并对填海造地的总量规划进行缩减,许可审批趋严。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对对土地需求陡增,若将填海造地的用途许可完全限定在公益用途或者生态填海上,则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实际。
综上,海域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公物,对其行政管理的目的应用于公益目的。对其填海许可也主要应以公益填海、生态填海为利用方向,在填海造地的行政规划与许可上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实际,适时调整规划方向,使之符合国际上填海造地利用发展趋势。
三、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法律与政策的游离与偏向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海域规划法》或者填海造地规划法规,有关填海造地行政规划的规定零散的规定在《海域使用管理办法》和《海岛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第4条“国家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该法规定海洋功能区划应与城乡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相互衔接、配合,形成合理的、科学的规划开发利用方案。《海域使用管理法》第15条第2款规定:“沿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与海洋功能区划相衔接。”《海岛保护法》第 27 条,“……确需填海、围海改变海岛海岸线,或者填海连岛的,项目申请人应当提交项目论证报告、经批准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申请文件,依照《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报经批准”。中,以及在部分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中有所体现,如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2011年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下发《关于加强围填海造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明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海洋功能区涉及围填海造地的内容、范围、规模要相互衔接,近期围填海的规模、用途和布局要一致,远期利用方向不冲突。”总体而言,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只对填海造地规划只进行原则性规定,根据当前的法律法规授权,各省市自行决定填海的区域、计划、用途、强度、生态资源保护等具体填海造地行政规划内容。填海造地规划的用途主要解决当前居住、工业用地问题,即以工业建设、住宅建设为导向的填海造地。*参见中山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外公示《广东中山翠亨新区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明确了本次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总面积为992.94公顷,用海方式为填海造地等;《珠海市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到2015年,计划以此增加2047.6公顷的用地,到2020年,全市计划围填海造地16758公顷。由于填海造地是对于当前高昂的土地拆迁及征收成本而言经济代价较小的方式,尤其是沿海城市人地关系紧张,可供拆迁与征收的土地愈来愈额小,故不断向海要地。如前所述,尽管我国填海造地已经注意到环境影响问题,用途上开始综合性发展,但总体上仍以工业用途填海为主。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缺乏统一的法律对规划进行生态要求,各地处于当地社会经济利益的需求,进行填海造地规划时往往过度注重经济效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效应,因此导致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游离于生态之外,定位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一)填海造地规划法律体系的缺位
我国目前填海造地规划仅仅依靠零散的法规及国务院文件进行原则性指导,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自己根据实际来设定填海造地规划,即未形成应有的填海造地规划体系。这表现在:一是国家层面的填海造地规划编制不规范。虽然我国有着丰富的海岸带资源,港湾众多,海岸自然形态各异,开发潜力、条件不尽相同,且不同海岸带所在的地区经济发展不一,但国家层面的的规划仍应对各个地区海岸利用的总体规模、布局、时序、用途进行硬性规定;第二,缺乏区域规划统筹。区域填海规划最易收到地方经济利益发展的驱使,现有的填海造地规划多是根据通过地方经济需求而制定规划,而不是根据区域海域整体发展进行长期统筹,缺乏行政区内的宏观论证与负外部性评价。由此导致多数填海规划即为特定的工业项目、住宅项目而编制,很少真正从整体环境及生态资源的多样性进行评价;第三,海陆规划衔接不当。填海造地规划通常以海洋功能区划为依托,但海洋供功能区规划基本上是从海洋综合利用为基础,填海造地规划也多是从如何有利于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为前提。而填海造地形成的是新生土地,且与邻接土地成为一体,而土地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确也很少纳入填海造地规划,使得填海造地规划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也成为围填海规模失控和开发无序的重要原因。[12]即使是偶尔海洋功能区规划或者土地总体规划将填海造地纳入其中,但对于填海造地的功能、用途规划必然是非常粗糙,对填海的生态环境影响放在较次要的位置。
(二)填海造地规划中生态原则的失衡
在国家层面,填海造地规划缺乏统筹规制的情况下,区域行政规划即受到公权力约束较小,实践中地方区域填海造地规划权便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则地方政府在填海规划上通过利益对在原则范围内进行自主决定填海造地规划的区域选择、面积大小、新生土地用途分配、开发强度等。首先,填海区域规划,也即填海区域的选择上,地方政府通常通过五年计划或者更短的年度计划来对填海区域进行选定,被选定的区域一般为原属于市郊,具有较大的经济开发价值,交通相对便利的海域,而政府往往对该区域的生态影响考虑较少或者未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其次,在填海造地面积上,我国正处于快速扩张时期,为满足工业、住宅用地需要进行大量的填海造地,填海造地面积较大,对于是否会造成潜在的生态破坏或污染多数进行了模糊处理或回避。如“被誉为世界最大填海造地工程”的上海临港新城项目133平方公里面积为吹沙填海造地,相当于填出了8个澳门的面积。*资料来源:新浪网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4a95c40100w2wf.html,2016年7月23日访问。广东珠海市计划到2020年珠海在包括横琴岛等在内的多个区域内围填海造地16758公顷。*资料来源:南方网:http://news.southcn.com/d/2014-05/21/content_100217158.htm,2016年7月23日访问。上述填海区域在地理区位上也均选择了对区域经济发展较为有利的海域,而对于原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规划方并没有提及或者很少提及。最后,在新生土地用途规划上,通常以地方政府规划的评判标准也是以经济发展需要为重点考虑因素,以工业、住宅用途为主要填海造地规划主要动因,缺乏综合性考虑,尤其是对生态环境潜在影响的重视,从今年来各地不断扩建的“海景房”就可窥见一斑。如从深圳市政府会议发布2016年6月出台的《深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深圳将再填海50平方公里用于解决深圳市日益增长的外来人口带来的高房价房价与日益紧张的用地资源。
(三)填海造地中的环境规划措施的乏力
填海造地规划生态考量是对海洋生态保护的前瞻性规制措施,对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破坏性开发具有重要的预防作用。如在规划阶段不能对填海造地的生态环境破危害性后果进行强制评估,一方面会纵容地方政府在区域规划和填海造地实施过程中忽视此过程或者在用途规划中直接忽略生态危害性的考察,致使海洋生物资源、渔业资源、景观资源、水资源等造成不可回复性的破坏。在我国当前有关规划法律法规以及地方规划文件中,也很少见到将填海造地生态危害性等级作为规划评估的一个必经步骤的规定,基本为原则性规定。在地方政府的具体区域规划中,生态功能填海也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如深圳湾经历了三次填海,影响最大的是第二次,内伶仃红树林保护区至今已消失了一半,很多地方红树林都已经像福永、盐田港的红树林因为填海造地已全部覆灭了。*资料来源: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6-07/16/content_13610768_4.htm,2016年7月24日访问。填海造地规划功能的缺失还会导致航道、港口功能弱化,影响正常的通行。太南海造地主要工农业、城市发展,由此导致了海域污染,并导致了赤潮发生的频率提升。甚至直接导致了传统渔场的灭失,破坏了海洋生物生存的基本环境,如舟山群岛海域开发,北海的填海建港等,都是导致这些海域近年来渔业资源急剧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上述这些填海造地工程的规划过程中,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进行预判,出台的规划方案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只是采取了不痛不痒的态度敷衍。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对于规划对生态影响因素不够重视,偏重眼前利益,在当前GDP之上的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下,工业文明的利益之上观念也长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忽视了长远的填海造地生态资源的发展。
四、拨正与定位:我国填海造地行政规划之法律完善
填海造地规划设计应首先尊重自然规律,必须以保证海域资源利用、保护海洋环境、保证沿岸景观、保证开发利用的总体经济效益为前提。经历改革开发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现实基本经济国情是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13]经济发展已经由粗放型的“工业文明”向集约型的“生态文明”转变,填海造地规划定位进而也应由经济利益主导向生态环境文明方向定位的历史阶段,必须对填海造地行政规划进行法律上的重新定位。
(一)构建海洋填海造地专项规划法律体系
海洋专项规划是完善海洋资源利用体系,规制海洋开发利用行为的有效综合管理途径,应以专门的法律进行明确。如英国《海洋法》中将海洋规划作为单独的一章,有着较为完善的海洋规划体系,明确了海洋利用的内容、条件等,加拿大颁布的《加拿大海洋战略》提出在海洋综合管理中坚持生态方法等。[14]这些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海洋专项规划,也对各个行政部门分工、管理机构及层级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维护海岸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这些规划体系不仅有中长期规划,也有短期区域规划,各海洋规划体系之间具有良好的协调性、整体性,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填海造地规划是海洋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海洋功能区规划中应重视对填海造地规划的限制条件,将其纳入到海洋规划体系之中。
我国海洋规划首先应建立起专项海洋区域规划与功能区规划。当前我国海洋规划多注重中长期规划,而忽略了短期规划。中长期规划的原则性与指导性较强,对于具体区域的海洋规划规制性较弱,这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在自行制定规划时往往根据自身经济项目需要而上马规划,中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结构性问题突出,且相互间存在着不匹配的矛盾,应尽快构建国家、区域、单个项目的三级围填海造地规划体系,建立完整、体系性强、长短期相结合的规划对于宏观调制与微观规制均可起到较好的作用。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开发规划的基础,区划和规划是海域使用管理的前提。[15]在功能区规划中尤其要对填海造地生态影响进行审查,对于会造成长远生态问题的海域应严格剔除在填海范围内;其次,完善海洋规划、填海造地规划的层级管理与部门分工。现阶段对于填海造地国家海洋局负责提出全国围填海年度总量建议和分省方案,国家海洋局下达建设用和农业用围填海计划,国土资源部在下达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将建设用围填海计划同时下达。这种模式下,很容易造成部门之间规划职责的交叉或相互推诿,且各自制定的填海造地规划也难以形成具有一致性、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方案。因而,根据国外的经验,填海造地规划属于海洋行政规划的一种,应将其归于海洋行政部门统一制定,且填海造地对于海洋部门来说是其海洋域面受损、海洋污染最重管理职责承受部门,其对于填海造地的生态考虑更加公正。
(二)拨正填海造地规划法律中生态原则的定位
由于国家层面的海洋规划的缺失,致使区域填海造地规划制定权实际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压力下往往以牺牲长期利益为代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而言,基础工业体系已经较为完善,在此基础上应开始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国家层面规划而言,不仅要对于海洋规划进行整体性协调,对于区域填海比例、程序进行严格限制,也要对于填海造地的用途予以明确,设立严格的生态填海、工业填海、住宅用填海的比例,将海域的生态性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纳入到规划中。
填海造地最大的负外部性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政府在具体许可审核时必须将填海造地项目对现存的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科学细致的评估。通常项目填海人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其填海造地的最大动力,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长期性、潜在性的特征,因而在审查项目填海时不仅要事前对周边海域珊瑚礁、红树林等生物资源采取保护措施,对建设中的项目也要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对项目工程完工后政府有关部门应再次检查评估,对其项目运营进行评估许可。其次,对与生态环境构成破坏性较大,如海岸带珊瑚礁、红树林、传统渔场特定海洋生物资源可能造成毁灭性破坏的,或者可能构成重大环境事件后果的,应列入禁止填海造地规划区域。具体而言,一方面要对前期填海造地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恢复性治理,制定海洋规划时应将海域生态修复列入规划,设立专项生态填海工程;另一方面,在进行新的填海造地项目实施前应建立严格的生态评估机制。填海造地工程应注重其生态经济考量,将预计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治理成本、代际补偿纳入到填海造地工程的成本之中,同时对项目的安全性、潜在利益性及长期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研究、评判,做好项目前期规划。同时,应对海岸线的运动趋势、风暴灾害性、生态安全性等因素进行考量。
(三)健全填海造地环境规划的具体措施
除完善国家层面的填海造地宏观规划外,地方区域填海造地规划和单个填海造地项目规划是改革的重点,应着重对填海具体规划措施进行完善,使具体项目落实上能够根据国家海洋规划确定填海造地区域内,符合生态保护功能导向,使得海域的生态保护落到实处。在区域填海造地规划层面,应尽早对围填海造地实施重点地区进行总体规划,明确岸段功能定位。单个填海造地项目层面要对围填海造地项目进行平面规划,明确项目的围填海造地方案,包括用海面积、地理位置、海岸形态与功能布局、围填海方式和主要区块功能等相关内容。
具体而言,首先,在填海造地方式的规划上,应该变现大量采用的近海直接围填式,重点放在人工岛式的填海造地,以此可以更好的保护近海资源,增加海岸线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在海岸线形态上,填海区域规划应尽量采用曲折的岸线走向,这样不仅没有消减原有岸线,而且还新增大量岸线。再次,在围填海布局上,可以借鉴日本主要采用水道分割布局,一定程度上仍能维持水体交换、美化景观、小气候调节等方面的海洋生态系统功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围填海造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规划编制过程中严格落实公众听证制度。行政规划是一个多方参与并达成共识的行动方案,[16](P215)公众之所有拥有这种权利,是因为他对于活动者能够在其中出场的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来说,是具有构成行意义的,[17](P450)尤其是对因行政规划造成相关公众利益损失的,与行政相对人沟通协商以安排和部署。由于填海造地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历史情况复杂,不同全体对于海域景观、环境生态功能理解不同,甚至涉及到邻接土地使用人的土地用途的变更、价值的减损,渔民对该海域的习惯性利用等问题。因此,在填海造地规划过程中应注重听证制度,注重公众参与,将听证制度作为一项前置程序,切实保障相关权益人利益。
五、结论
填海造地固然是拓宽人类生存空间、促进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但随着大规模填海造地负面效应的凸显,填海造地的活动必须转变传经济主导的观念,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组织、实施,从而实现有序填海。现代海洋生态保护是填海造地的基础与前提,而海洋行政规划的法律规制是填海造地活动的先序行为,直接决定着填海造地发展的导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填海造地的行政规划是通过公权手段对海洋生态中的公共利益必要保护,在市场经济主体逐利特性下,政府通过行政调控手段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必要的修正,这也是一国行政主体的基本职能。填海造地行为对海洋生态影响巨大,在制定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以及海洋行政规划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更要通过专项规划、中长期规划、详细规划促使填海活动达到可控的目的,且在法治保障下海洋生态系统能够长期维持稳定状态,实现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2] 章剑生.行政规划初论[J].法治研究,2007,(7):13-20.
[3] 孙施文.现代城市规划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 肖泽晟.公物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5] 国家海洋局考察团.日本围填海管理的启示与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7,(6):3-8.
[6] 李宜良,于保华.美国海域使用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4):14-17.
[7] 孙丽等.中外围填海管理的比较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40-46.
[8] 杨华.海洋发展战略中填海造地的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9] 徐皎.日本人造陆地利用方向的演化[J].世界地理研究,2000,(3):43-46.
[10] 张军岩,于格.世界各国(地区)围海造地发展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国土资源,2008,(8):60-62.
[11] 舒胜.美国海岸带管理法的由来和演变[J].海洋开发,1986,(2):14.
[12] 吕宾.填海造地,福兮?祸兮?[J].中国土地,2010,(4):38-40.
[13] 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J].中国工业经济,2012,(3):5-16.
[14] 刘佳,李双建.世界主要沿海国家海洋规划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1-5.
[15] 黄丹丽,朱坚真.浅析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开发规划与海域使用管理[J].发展研究,2013,(12):77-80.
[16] 宋雅芳.行政规划的法治化理念与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17](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2003.
FromIndustrialCivilizationtoEcologicalCivilization:ReflectionandOrientationofChina'sAdministrativePlanningLawofReclamationfromtheSea
Yu Jing1Tang Xinyu2
(1.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d reclamation is driven by economic interests. The land reclamation plann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mainly for industrial and residential land use. Since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the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late stage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we must change the curren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ra of land reclamation planning int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oriented planning. Due to the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unbalanced planning in ecological principles, lack of eco-environment planning measur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special marine planning system, regulate the legal status and effectiveness of land reclamation planning, th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of marine legisl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planning measures for land reclamation and so on.
land reclamation; administrative plan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912.6
:A
:1672-335X(2017)05-0046-07
责任编辑:周延云
2016-11-09
海南省教育厅高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农村集体公共用地制度研究”(Hyb2016-03);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南海岸带土地的利用与生态保护法律问题研究”(HNSK(JD)15-4);海南省法学会规划课题“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和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研究”(hsfh2016a07)阶段性成果
余敬(1987- ),男,河南罗山人,海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土地法律制度和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