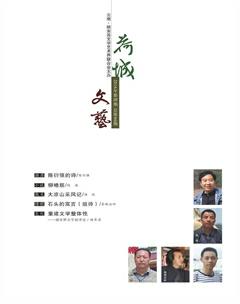重建文学整体性
杨荣昌
谢有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批评家,二十余年中发表了三百多篇论文、出版十余部学术论著,为文坛所瞩目。他的文学批评力图站在一个灵魂视点的高度上,审视文学形式的变革与作家心灵的律动,及时而准确地作出反应。他致力于阐扬精神叙事、灵魂探索等关涉生命价值重建的理论命题,来实现对浅表化、戏谑化的文坛风潮的反抗,以及对新的文学理想的张扬。他关于先锋文学、小说伦理、批评精神等的一系列论述,有效拓宽了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边界,其整全的研究视野,强劲的话语精神,犀锐的批评文风,以及对文学现场的强有力介入,体现出饱满的批评主体形象,使他成为同代登场的批评家中最重要的存在。
一、回到“此时的事物”
多年的批评探索中,谢有顺逐渐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架构。其中对“文学身体学”的论述,可视为他理论阐述的基础。面对文学史上“身体”意义一再被悬空和利用的现实,如革命年代身体被政治化,个人独立思考的可能性被取消,消费时代身体被肉体化和情欲化,最终变成商业符号,他重申唯有正视身体的生理性、语言性和精神性,恢复其应有的伦理维度,才能获得身体的独立性。以海子的诗歌神话和“下半身”写作为例,前者是抽离身体的玄想,一味追求形而上;后者是对身体被专制的一种激烈反抗,有其革命意义,但要警惕矫枉过正走向新的肉体乌托邦。两者的写作方式都过于极端,好的文学应是产生于两种追求维度的空间之内。强调身体的伦理维度,其实是在重申一种写作常识,即作家个人的在场。因此在谢有顺看来,首要任务是要恢复作家的感觉系统。他感叹中国文学自鲁迅、沈从文之后,很难再看到传神的风景描写,作家在生机勃勃的自然面前,已经感觉迟钝,神经麻木,心灵被抽空。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能够以身体的在场写出活跃的感官,如莫言关于声音、色彩、味道及各种幻化感觉的描写,有趣,喧嚣,色彩斑斓,充满生机。如陈冠学写作《大地之秋》,仿佛眼睛、耳朵、鼻子和舌头都向着大地全面敞开,用自己的感觉来接触、放大田园里所发生的一切细微变化。如于坚坚信“看见一种事物比想象一种事物要困难得多”而坚持“拒绝隐喻”的写作姿态,把事物还原到本然的空间来观察和言说,做一个真相的目击者和事实的记录者。再比如胡廷武“听书、听鸟、听吆喝、听戏、听蝉、听歌、听风、听雨、听鼾声”,以“九听”的方式把生动而富有意味的细节、曲折而感人的人物命运都聚集到笔下,将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和文人性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历史文化散文研究中,谢有顺强调作家需要避开历史上早有定论的概念,转而寻找那些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和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的精神信念。从上述成功的例子来看,只有实现人的身体在场,才能为心灵的表达找到坚实的依托,只有拂去蒙在事物表层的尘垢,重返事物的本真状态,才能恢复文学对生命的真情体恤和有效表达。
除了需要作家的身体在场,创作同样需要坚实的基础,谢有顺将其称之为文学的“物质外壳”,它包括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等。“读者对一部小说的信任,正是来源于它在细节和经验中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真实感。……一部小说无论要传达多么伟大的人心与灵魂层面的发现,都必须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物质外壳来盛装它。灵魂需要有一个容器来使之呈现出来,一个由经验、细节和材料所建构起来的物质外壳,就是这样的容器。”他以鲁迅小说为例论述生动的细节刻画对提高文学可信度的重要性,如对祥林嫂“空的”破碗、“下端开了裂”的竹竿,孔乙己“满手是泥”表明是“用这手走来的”等的描写,真实可感,让人过目难忘。小说虽是虚构的艺术,可要让读者相信表达的真实性,就必须在逻辑链条上追求严丝合缝的叙述,包括人物前后性格的变化、器物在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消费时代的宠儿纵情狂欢的经济来源等,都要有必要的交待,要合乎逻辑,否则就无所信,一个细节的失真往往会瓦解读者对小说的信任感。散文创作亦如此,如果作家只知一味感怀、沉思、感慨、怨叹、激愤,盲目升华,朝一个假想的精神目标一路务虚下去,但读者看不到写作的物质基础究竟建基于哪里的话,这样的散文就像没有身体的灵魂,无家可归,极不真实。好的散文,不但要有真实可信的物质外壳(事实、经验和细节),还要有作家独特的精神发现和心灵体验,以细节见情理,以物质写灵魂,以事实照见人生的底色。谢有顺所强调的文学表现中的现实的严密性、经验的逻辑性、合理合情的物质外壳,是完成一部作品最重要的血肉基础,看似一个简单的细节,背后却隐藏着一整套生活标准和生活常识,需要作家下功夫去钻研和揣摩。
由身体在场和物质外壳建立起来的信任感,促使作家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真实经验,表达才具有效性。面对九十年代以来曾引领文坛潮流、建构起自己叙事特点的小说家纷纷改弦更张,臣服于市场和消费法则而降低写作难度,重新成为消费时代宠儿的现状,谢有顺内心充满感伤。他惋惜在喧嚣的市场叫卖声中,作家虽然轻易地站到了文学发展的显赫位置,可附庸于趣味和利益的写作格局仍然无从改变,文学的内在品质,如叙事空间的拓展依然收效甚微,新的价值理想依然精神低迷。谢有顺把这种背弃故乡和经验的写作称为“文学的殖民”,“这种殖民,不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殖民,而是一种生活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殖民。……假如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去写这种奢华生活,而对另一种生活,集体保持沉默,这种写作潮流背后,其实是隐藏着写作暴力的——它把另一种生活变成了奢华生活的殖民地。为了迎合消费文化,拒绝那些无法获得消费文化恩宠的人物和故事进入自己的写作视野,甚至无视自己的出生地和精神原产地,别人写什么,他就跟着写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就写什么,这不仅是对当代生活的简化,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背叛。”从八〇后作家的文本分析中,他感触尤为深刻,他们虽有为时代代言的雄心,可单一的写作眼光,孤愤的精神气质,诙谐的话语方式,使得文风油滑,“那些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削弱了文学对现实的参与和建构能力。
在此意义上,谢有顺呼唤一种有根的写作。他尤为推崇贾平凹、莫言、雷平阳、鲁若迪基、郑小琼等人作品中那种渗透创作主体深切情感体验的写作方式。他认为,贾平凹的作品有着结实的中国化的现实面貌,写出商州乃至整个西北的生活精髓,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转型为农村带来的心灵阵痛,以及从“废都”到“废乡”的中国人的精神流变。尽管作家心里已明显感到故乡的灵魂已破碎,对这片土地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但仍然试图写出故乡的灵魂。莫言以笔为犁,在故乡高密开疆拓土,建立了“高密东北乡”这个纸上王国,与其精神导师马尔克斯、福克纳一道有着自己坚实的写作根据地,成为写作风格化的重要路标。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腹地,其作品中的生命热烈、顽强、粗砺、荒诞,充满原始力,是野生中国的真实写照。雷平阳的诗歌是对乡土大地的精神守护,他对故乡、大地和亲人的赞歌,是从生命的根须中生长出来的,对残酷生活的洞察,同样写出了生命被连根拔起之后的苍凉景象。鲁若迪基长期居于云南边地的泸沽湖畔,以拒绝夸张和粉饰的话语风度讴歌故乡,充满大地的质感,精神面貌朴素清晰,有着宽阔的生命容量。郑小琼的诗歌虽然写故乡的不多,但她以毫不妥协的姿态与现实短兵相接,尤其寻找到“铁”这一诗歌核心元素后,写出了如她一般生活于底层的打工者的血泪和痛感,其写作不是表达一己之私,而是成为了解这个时代无名者生活状况的重要证据。同时,从《出生地》《异乡人》两本诗集中,谢有顺看到这种追求精神之根的文学力量,诗歌中那种粗砺、有重量、有来源、在大地上扎根和生长的经验与感受,唤醒的是一个人身上最具创造力的部分,经由具体的、狭窄的路径进入现实,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从上述个案的写作中,谢有顺更加坚信精神根据地的建立隐藏着作家成功的秘密。
二、写出“灵魂的深”
强调身体的在场、物质基础的夯实和精神根据地的建立,是为灵魂叙事寻找坚实的依托。在谢有顺的理论阐释中,对灵魂叙事的追崇是至为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说,他的批评核心就在于探究当代作家如何能在灵魂叙事的维度上作出新的有效的探索。他对作家的精神流变和创作路径作出形象的概括:“从密室到旷野”“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等,并作了尽可能详尽而深刻的阐述。他把张爱玲的写作比喻为密室写作,喻指的是作家对世界的观察尺度是有限的,内向的,细碎的,书写的是以个人经验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代表的是一种私人的、自我的眼界;把鲁迅的写作比喻为旷野写作,是指在自我的尺度之外,承认这个世界还有天空和大地,人不仅在闺房、密室里生活,还在大地上行走,还要接受天道人心的规约和审问。所以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以鲁迅为标高而非张爱玲。
在消费主义潮流的裹挟下,文学的精神不可避免地发生质变,作家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一种有痛感的经验,“缺乏向存在的深渊进发的勇气”。面对这种文学精神委顿的趋向,谢有顺的忧伤情绪溢于言表,他强调文学应拒绝对社会性问题的表层抚摸,要追求“灵魂的深”。在几部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他为作家写出这种灵魂的挣扎而感佩,如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书写的是知识分子在严酷的历史选择中表现出的犹豫与怯懦,而在怯懦的背后,指向的是对造成人性变异的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思,对此,他怀有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张者的《桃李》反映的是当代知识分子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消费社会的精神蜕变,作家以忧愤的笔触写出了这种蜕变的必然性。同样写当代人的灵魂挣扎,王跃文的官场小说“精细地描摹官员们的日常状态和心理嬗变,从而凸显繁复世相背后的官场伦理与心灵逻辑,并以此透视出权力镜像下的个体生命在现实与灵魂之间的种种冲突。”这些小说都是作家倔强地与历史或现实进行挑战的结果,他们以强烈的使命感记录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并引领读者体验到当下现实与我们的生存盼望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切肤之痛,体现出一种真切的存在感。
纵观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不仅是阐述具体的作家文本,更是借作品谈人生,表达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追求一种昂扬的价值理想。他认为,如果作家“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难有温润之心。”所以,“作家有时是一种精神秩序的守护者、建构者,他要提醒人们思索活着的意义,他也要通过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不断深入到更高远的精神空间里,让人对那个未知的、神秘的世界充满敬畏。”“除了写身体的悲欢,还要关注灵魂的衰退;除了写私人经验,还要关注‘他人的痛苦;除了写欲望的细节,还要承认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从铁凝、阎连科、麦家、郭文斌等人的写作中,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希望。铁凝小说凝聚残存的人性之善,阎连科通过苦难写出人内心庄严的勇气和力量,麦家的《风声》为一种雄浑的人性精神作证,郭文斌写忧伤但不绝望,写苦难但不自苦,写小地方人的情怀但不狭窄,写美好的真情但不做作。即使以逼视人性深处恶的因子著称的余华,也在写作了大量揭露人性恶的中短篇小说之后,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小说中,转向了温情,书写了生命之坚韧。在这些写作中,作家们用宽广、仁慈的眼光打量生活,力图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发现生活本身更多的可能性,并为之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谢有顺赞许这样的写作并一再传递一种理念: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
著名学者刘再复对中国文学表现维度曾有过专门论述,认为现代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变成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种维度:叩问存在意义、超验和自然维度。谢有顺认同这一判断。他强调文学创作要有整体性的精神关怀向度:不仅关注现实,还要关注存在的境遇、死亡和神秘的体验、自然和生存的状况、人性的细微变化等命题。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写大观园内的装饰、宴席、礼仪、人伦,以及合乎社会法度的人情冷暖、遵从事实逻辑的人物言行,均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本真状态。在此基础上,他还写出一种对灵魂世界的想象,如人物最终的命运归宿,一切归于虚空的哲学意境等,体现出一种整全完备的文学观。这种写作路径即“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谢有顺认为当代作家中,贾平凹的写作体现了建立文学多维度的努力,如《带灯》《极花》中对现实问题的揭露和反思,真切生动地描绘了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性等现世事象。同时他的小说还表现出另外三个维度,如《废都》体现了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是知识分子颓靡的精神写照;《废都》《秦腔》体现了神秘感和死亡体验,具有超验的维度;《怀念狼》体现了自然生态维度。从贾平凹身上体现出的建立文学整体精神向度的努力,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这些颇具开拓性的理论发现,是谢有顺文学批评创造力的体现,也是一个值得深度探索的的话题,期待他能作进一步的谈论和阐述。
对叙事伦理学的探讨,是谢有顺近年来观察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视角。他相继发表了《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多篇论文,重新厘清文学叙事在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时的价值,强调“叙事也是一种权力”,不仅与文学的形式、结构和视角有关,也关系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一个单纯的故事,经由作家的叙事重构,可以达到一种伦理效果,如莫言《檀香刑》中对看客心理揭示的叙事,起到了把邪恶当做审美的效果,抵达了人性的黑暗深层。好的叙事作品,可以超越国族、政治、权力,进入一种新的人与外部世界的可能性。他的长文《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演变》,对叙事伦理的话语谱系进行了回溯和重构,细致梳理了建国以来三个时段文学态势的叙事伦理,跳出单一以政治评判文学的格局,既看到文学发展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同构关系,肯定这种倔强生长的艺术性是文学的内部规律作用使然,又探析这种艺术性的生长对重建文学与个人生命关系的价值所在。这些论述,对深入推进叙事学研究,丰富当代文学理论成果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三、“立心”的批评
谢有顺推崇“立心”的批评,认为批评之心应至少包含义理、实证和文体三个方面,义理阐明文学的德性,实证运用鉴赏的能力,文体经营批评的辞章。返观他的批评实践,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努力,其中强调文学写作要有坚实的物质外壳(经验、常识、情理和说服力),这是实证;作家要有高远的精神视野,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这是义理;而他批评文章的美文风格,早已为文坛所公认,从他对李健吾、李敬泽、李静、胡传吉等现当代批评家文章的激赏中,也可发现他对于文学批评美文化风格的心仪和重视。
优秀的批评家要能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重获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让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谢有顺认为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其终极目的不是批判和摧毁,而是要“寻美”,让更多优秀的作家通过批评的阐释站立起来。“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作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工作的人,批评家必须“先立其大”,即树立批评的大方向,坚守文学的常道,诚实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聚合那些恒定不变的美学品质。借用批评家李敬泽的话说,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象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帮助真正好的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他时刻警惕写作受到来自意识形态、商业利益或知识权力的多重绞杀,其文学批评守护着独立纯真的价值信念,多次发出关于批评的“个人宣言”,如《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对话比独白更重要》《批评如何立心》等,这些文章实则是在阐述一种被人漠视的批评写作常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批评不应是作品的附庸,也不仅仅只有冷漠的技术分析,它应该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在任何批评实践中,批评家都必须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郑重地重申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主要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我甚至把这看作是必须长期固守的批评信念。”基于对这种价值信念的追求,他的文学批评有较高的精神视阈,不拘泥于琐细的文本分析(当然他也重视那些能勘破作家机心、对作品意义有决定性影响的细节描写,如对《红楼梦》及鲁迅、金庸等的小说细节的深入分析),他更是站在灵魂审视的高度来辨析文学的艺术得失。唯有建构起较高的参照系,秉持一种中正坚实的价值立场,批评家的主体才能如一块坚硬的礁石屹立于当代文学的深海中,而不至于被庞大的作品话语泡沫所吞没。他所致力强调和阐扬的伦理、灵魂、苦难、道德等关键词,是人类心灵深处最为隐秘的部分,抓住了这些精神的内在性因素,文学研究才能真正回归本源,才能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重建人的心灵世界。
作为批评现场中的一员,谢有顺对文学批评在当下的处境、遭遇和得失可谓有切肤之感。他一方面为文学批评遭遇的外部误解感到愤懑,尤其那些对文学批评所作的不切实际的外行指责,如要求批评家像战士那样勇敢、发力批判、横扫一切,他予以回应,维护批评的尊严。“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同时对来自批评内部的麻木、堕落和腐朽予以抨击,如批评受到权力的制约,受到商业利益的绑架,或者变成知识的衍生物而走向僵死,造成批评主体的空洞和匮乏等。基于此,他强调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包括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以及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他的批评写作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度,讲究辞采和性情,是一种“寻美的批评”。即使表达失望、愤怒和批判,也拒绝粗鲁暴力的文风,坚持“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对批评对象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不故作惊人之语吸人眼球,而是以思想的敏锐和穿透力见长。由此进入他文学精神的核心,可发现其写作不是对知识的编译和理论的操演,而是源于内心对文学艺术特性和人性内部世界深切的探究渴望。这种重返文学本体的自由之思,充满理性主义的光辉,文章学理敦厚,发问有力,直抵艺术与人性的深层。
知识分子普遍缺乏行动力,大多只能流于清谈,未免有些虚空,而谢有顺非常重视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他是一个有能力将自身人文才情转化为现实文学力量的批评家。除了每年应邀到各地作大量的学术讲演外,由他参与发起并担负重要组织作用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至今已举办了十四届,每年一届的文学大奖,是对上一年度中国作家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的褒奖,同时,该奖注重发现文学新人,重点表彰那些创作出经典性作品的当代作家。由他撰写的授奖词,以精炼的语言,典雅的文辞,奇警的譬喻,穿透语言的迷障,沉入作家(作品)的精神内部,探析那些隐藏文本深处的幽微亮光,并将其聚拢成为作家文学人格的光辉标识,它们既是对作品历史意识、思想底蕴和美学风格的历史化重构,也是对作家心灵世界的一次深入掘进,体现出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秘密敏锐的洞悉力,亦可视为当代文学批评高度的标志之一。
在文学批评愈发封闭化、偏狭化、碎片化和浮躁化的当下,许多批评家已把自己日益固化在一个极度狭窄的专业领域内,很难对自己重点研究领域之外的文体发言,也难以在一个整全的背景下观察文学创作的得失,守护文学的价值定力。综合审视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可见一种重建文学整体性的努力。从批评伦理来看,创作方法上,强调身体的在场,重视感官的解放,要求作家书写真实经验,建立文学的精神根据地,张扬叙事上寻求变革的先锋精神;创作意旨上,要作家呵护人类心灵深处真善美的情愫,书写生存的坚韧和生命的尊严,注重文学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查勘、探寻和建构作用,追求文学的整体观;批评文体上,尊崇“文德敬恕”的话语风格,以趣味醇正、及物见理的批评实践,强力介入文学的现场,让读者看到文学批评的尊严和希望。从批评重心来看,小说研究是重点,同时在诗歌、散文、批评等文体的研究方面均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体现开阔的研究视野。从知识谱系来看,虽立足当代创作现场,但理论资源可追溯古典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力求打通古今中外的文论通道作为阐释当代作品的理论来源。从批评伦理到批评重心,再到知识谱系,呈互融共生之关系,显示出整全的批评格局。
重构谢有顺的文学批评史,上述理论观点和批评特征自他写作之初就已初露端倪,其后不断丰富、结实、清晰,形成独具一体的批评话语风格。庞大的文论著述中所表现的繁复的理论观点,体现出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对文学世界的整体性思考,尽管有些理论还有待深入开掘,有的表述失之感性,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重建文学整体性的努力,已显现出一种沉稳大气的精神气象,必将对拓展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空间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