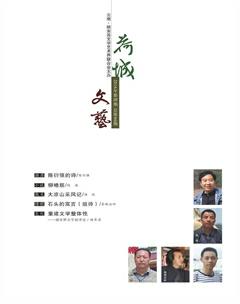阅读,让我的创作更有方向(访谈)
伏自文+饶云华
时间:2015年11月8日
地点:昆明·西南宾馆
伏自文(《云南政协报》记者,以下简称伏):今天的访谈,想重点说说你的小说创作。
饶云华(以下简称饶):好啊,我荣幸之至!
伏:饶老师不要谦虚嘛!
饶:这个嘛,还真不是谦虚。像我们这种小县城的写作者,平时都是被边缘化的,再努力,也引不起关注。所以嘛,能得到省城记者的访谈,当然是高兴的了。
伏:话不能这么说。其实你发在《边疆文学》《滇池》还有《百家》上的好几篇小说,都是昆明的几个作家朋友介绍给我的。这样子说吧,近段时间,我重点看了你的几篇小说,比如《梅葛歌王》,《朵觋往事》,《蛊婆阿秀》,还有《谁在捣鬼》,《千万别说你爱我》等等,我发现,都是一些地域性、彝族性很强的题材。在此我想问一下,你是彝族吗?
饶:不,我是汉族。但我在彝族地区工作过,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悉,也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还听说过许多传说,特别是关于朵觋和蛊婆的。哦,说明一下,朵觋,正规的叫法是毕摩。……长期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算是耳濡目染吧,就有了这方面的创作冲动。所以我创作的小说,有三分之一都是这个题材的,至少,也掺杂了这个题材的一些成份。
伏:这个题材好是好,会有人感兴趣。但毕竟,唯心主义的东西太多,神啊鬼啊巫术啊什么的,会不会有迷信色彩过浓的嫌疑?
饶:这就是真实的生活呀。不迷信,很科学,反而不是彝家人的生活。当然也不能说就是迷信,说是信仰反而更贴切一些。对彝族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彝人,是一个崇尚万物有灵的民族。彝族人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就连石头,也有石神……这是一种信仰,彝人的宗教信仰。因为信仰,才有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敬畏。所以我倒觉得,宗教信仰是个好东西,最直接的好处是让人有所敬畏,不敢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喜欢跟有宗教信仰的人交朋友。
回到正题。以我的生活经验,在彝族山区,直到今天,神灵,或者说鬼神,一直存在,在彝人的脑子里,在彝族这个群体的精神世界里,一直影响、甚至于主宰着彝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写彝族题材的小说,神灵,或者说唯心的、迷信的东西,是回避不了的,是必不可少的元素。这才是他们的真实。当然,我是不认可“迷信”这个说法的,“唯心”可以接受。佛教、基督教等都是唯心的,但有很多人信。牛顿、爱因斯坦他们都信上帝,甚至认为,世上所有的研究和发明,都是在破解造物主上帝当初的设定。彝人也一样。他们信神怕鬼,用巫术疗伤,但并不妨碍他们接受科学,接受新事物。
所以我的小说里,喜欢拿朵觋蛊婆说事,拿神啊鬼啊以及各种巫术、蛊术说事,一方面,是生活的真实,没有必要遮蔽。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元素,小说里面的人才是活灵活现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彝族人特有的。并且我一直认为,相信万物有灵,这就是彝人的宗教情怀,是应当受到尊敬的。
伏:你是说,巫术呀什么的,在今天还能看到?
饶:在有些地方还能看到。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山村。比如,某一棵古树下,你会看到一些燃烬的香棍,还有神祗或泥偶,这是朵觋做法事后遗留下来的。比如,在某一溪流的木桥边或某一避静的小路拐弯处,会看到一些菜叶,菜叶上面是饭粒,旁边是一只摔破的碗,这是喊魂后遗留下来的。总之,到了那个地方,就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也会心生敬畏,感觉到有一股或浓或淡的巫气尾随着你,有许许多多的神灵在注视着你。
伏:说实话,看你的小说,我也闻到了一股或浓或淡的巫气,并且一旦走进你的小说,就感觉神灵无处不在。当然这些,都归功于你的生花妙笔,归功于你的文学功底。在此我还想问一个最俗套的问题:你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
饶:因为阅读吧?小学时我就喜欢看文学书。先是看连环画,后来就偷偷看父亲的藏书。父亲有很多藏书,文化革命中烧了一些,但四大名著之类的,藏在阁楼的账簿里,留了下来。我对繁体字的熟悉,就是那时候无师自通的。后来读师范,有了图书馆,阅读量就大了。中外名著看了不少,杂志上的,也看了不少。但看归看,始终没有创作的意识。教书时没有,在教育局在党校工作时也没有。后来在宣传部,接触到《荷城文艺》,是一本县刊。编辑说,你不是喜欢看小说吗?能不能写篇小说给我们?我们就缺小说稿件。于是就写了,好像是《你可以选择》,当时打工潮嘛,就写了一个教师辞职下海。感觉还可以,又投了州上的《金沙江文艺》,也刊出了。这时我才知道,写小说原来就这么简单。但因为忙,一心想着混官场,也就没有再写的意愿。后来写《花子》,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发。因为山里面普遍存在的“小婚”陋习,因为同情那些不幸的女性。后来这篇小说还在《边疆文学》上发了。在省刊上发作品,而且还是小说,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所以,我就在饭局上炫耀了几次。说者无意听者有心,2002年,领导就把我摁在文联主席这个位置上了。到了文联,闹了一段时间的情绪后,就静下心来看稿,改稿,主编刊物,然后开始接触各种各样的作家。时间一长,就有了文学创作的冲动。当然,我最初的创作动机也不纯,既是证明给作者看,也是想让文学圈接受我。
现在回头来想,是阅读,让我有了创作的基本功,也是阅读,让我有了创作的方向。但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还得有人引领。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假如我提前10年调入文联,就跟作家接触,跟他们为伍,就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也许,我的文学成就还会更高。这就像练书法,经常看别人写,自己也会手痒,也会跟着练。我想,这就是文学氛围吧?我调文联之前,差少的,就是这个东西。
伏:是啊,氛围很重要。怪不得你在文联一呆就是10多年。不过,也有一些人,孤军作战,身边没有文友,甚至连谈论文学的氛围都没有。但因为坚持,最后还是成名成家了。对此你怎么看?
饶:我的身边,我的文友圈就有这样的写作者,视文学为生命,视文学为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对此,我向他们致敬。但实话实说,我做不到。我是一个务实的人。我喜欢文学,并不表明我会把文学当作唯一,当成终身事业。工作第一,有了饭碗,才有时间和心情享受文学。想靠文学创作成名成家养家糊口,那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不太赞成苦行僧式的那种奋斗。业余爱好就是业余爱好。跟着感觉走,能写就写,享受创作的乐趣。不能写就拉倒,找些书来看,享受阅读的乐趣。假如看书也没有乐趣了,我会选择其他。总之,会找到替代品的。但我还是相信,文学阅读,过去是,将来也会是我业余时间的最佳消遣。至于创作,要看情况。如果过程很痛苦,我何必要去做呢?也许吧,就是因为我对文学创作的这种心态,这种可写可不写的心态,才需要有人引领,需要一种浓浓的文学氛围来激发。
伏:阅读的乐趣,这个好理解。但创作一定要有乐趣吗?
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悲天悯人也好,由衷感动也罢,只要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不写就对不起这么好的题材,不写就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写就浪费了这么好的故事,我想,这样的创作过程是会愉悦的,会有价值感的。我知道有一些写作者,经常接受一些命题作文式的创作,虽然稿费高,但创作的自由度没了,作品优劣,由一个人的标准说了算。不讲艺术水准,只说对不对口味,甚至于把好的说成不好,把不好的作为标杆。像这种被动创作,甚至是自降艺术水准的创作,如果说很愉快,百分百是假话。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有一些作者,明明天分不足,还要孤注一掷,以为靠勤奋就能成功,痴迷到对家庭不管不顾,生活弄得一团糟,甚至于妻离子散。像这样的创作,何谈乐趣?所以我一直认为,像我们这种小地方的写作者,不能靠稿费来养家糊口的写作者,文学创作,是温饱之后的事。成名成家了,当然更好。没有成名成家,也很正常。毕竟,网络时代,电脑写作,作家越来越多,不可能都著名,都知名。在圈子里混个脸熟,在小地方有点小名气,就不错了。当然,我的这种创作态度,会有一种“玩文学”的嫌疑,文学圣徒们听了会不高兴。但我还是要说,其实“玩文学”也不错,自己有主动权。总比被文学玩得焦头烂额一事无成甚至妻离子散要好得多。
伏:创作嘛,本来就是很个体的事情,尤其是业余作家,持什么心态,以什么方式进行,自由度都非常大。能像你一样超脱的快乐写作,当然很好。但为了某种追求,精神上的追求,痴迷于文学创作,视文学为宗教,苦苦挣扎,我们也应该理解。
好了,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吧。你说你喜欢阅读,一直在阅读。我想知道,哪些作家哪些书,是你特别喜欢,或者说,对你的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的?
饶:我喜欢阅读,古今中外的,看了不少。但前期的阅读和后期的阅读,还是有区别。前期,重在消遣,侧重点在故事。后期,开始琢磨作品的得失。比如语感、语言、情节、细节、节奏、悬念等。有些书,有些作家的作品,看了后,能读出新意,读出惊喜,读出一些意外的收获。会让人觉得,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这些话可以这样说。尤其是诗歌和散文,往往会读到一些出乎意料比较精彩、令人叫绝的句子和段落,吸收了这些,就算是用在小说创作上,也会让你的语言空灵、唯美、耐读。所以,碰上好的作品,我会反复看,甚至于只要是他的作品,就要找来,先睹为快。比如欧·享利的小说,出人意外的结尾,让我惊叹。比如契可夫的小说,讽刺幽默的笔调和简洁干净的语言,让我叹为观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对钱钟书的《围城》着迷,当成枕边书,经常看,那些风趣幽默的语言,几乎背得。还有贾平凹、莫言、苏童的小说,也曾经让我着迷。王朔的小说,谐谑、调侃的味道很重,我喜欢。王小波的小说,是天马行空式的浪漫反讽和逻辑证伪式的写法,我反复看,反复揣摩,是一个王小波迷。阿来的小说,长篇中篇短篇,我都有,我喜欢他的那种诗一样的语言,那些略带魔幻现实主义味道的表现手法,以及寓言式的主题表达方式。
我看过的小说,特别是被我反复琢磨过的小说,肯定会影响到我的小说创作。要不然我琢磨他干啥?琢磨,就是找窍门,找成功者的经验,为我所用。这当中,王小波,无疑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
伏:你列举的这些,好像没有云南的。云南作家的作品,你也喜欢阅读吗?
饶:有些喜欢,比如于坚,雷平阳,范稳,潘灵,张庆国,胡性能、海男等等,包括一些小地方的,比如王单单,陈衍强,陈洪金等。有些嘛,无所谓喜欢不喜欢,但还是会关注,某某又有新作了,于是浏览一下,了解一下。有喜欢的,自然会看得透一点,甚至还会想,如果自己来写,会怎么样写等等。总之,只要是文友的作品,都会关注,只是关注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的关注,一是处于尊重,有一些惺惺相惜的心理;二是了解,作为一面镜子,知道自己的创作在什么位置。
总之,读的书很多,也很杂,还特别偏向诗歌和散文的阅读,还喜欢地方史研究和彝族文化研究,但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就不多说了。
伏:你阅读多而杂,是不是创作也多而杂?你现在出版了哪些著作?能简要地说一下吗?
饶:如你所说,我的创作,是有些多而杂。但小说,是我的主攻方向,一直没变。写散文,尤其是地方历史文化散文,是工作需要,我必须写。前者,让我进入云南文坛。后者,让我在小地方挣得一点薄名。此外,我还从事彝族文化田野调查,写了近10万字的研究文章,也发表了,有的,还被收入集子。但纯属爱好,也是我创作彝族题材小说的知识积累。要不然,把控不好,会引发民族问题。尤其是汉族作家写民族题材,更容易招致争议。文学评论和诗歌写得少一些。诗歌很少投稿,嫌麻烦。况且,圈内只知道我是小说家,我也想强化这个标签。但自认为,我的诗,不算特别好,但比一些专门写诗的,就好得多了。毕竟,我几十年如一日的诗歌阅读,诗感还是比较强的。不信,你进我的博客看看,就知道我不是吹牛了。
现在,我出版文学专著6部。其中,小说集3部。他们是《梅葛歌王》《毕摩往事》《土司乱》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叫《巫蛊传奇》,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平台数字出版。这几部小说,书名起得一般,是为了在地方上好卖。但里面收录的小说,是纯文学的。此外,散文集2部,地方文化类的,分别是《品读姚安》和《记忆姚安》。待出版的,还有3部,因为没有合适的出版或购买渠道,怕贴钱。对此我的想法是,写书就不容易了,如果还要掏钱出书,实在划不来。
伏:创作量这么大,还出版了6部书,实在令人敬佩。我想知道,在这些作品里,噢,指小说,你最满意的有哪些,为什么?
饶:最满意的,应该没有,正在努力。相比较而言,《性命》还可以,主人翁妄图用自己的(或城市的)性观念去改变一个小山村,结果没有得逞,反而因性游戏而死。另一篇是《杀人者》,也是针砭时弊的,写农村的“潜规则”,生活在这种“潜规则”里,直接或间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杀人者”。当然,彝族题材的那些篇,我也觉得好,艺术性强,又有独特的彝族风情,还赢得了好几篇评论。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靠这些作品说话的。但如果这样说下去,就没意思了。毕竟,作品就是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好。
但我也不敢奢望用时间来说话,因为能够穿越时间的作品,都是伟大的作品。以我现在所处的平台,我只能说,用发表来说话。至少,说明你的作品达到了一定标准,有大家认可的品质。如果得到文友乃至知名作家或编辑的肯定,那就可以认为是好一些的作品了。有了这些,会产生动力,知道努力的方向。
伏:是呀,立足当下,也只有让读者来评判了,尤其是名家,更有发言权。接下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目前的创作计划是什么?
饶:首先,在创作一部长篇,彝族梅葛题材的,暂定为《创世记》,跟州文联签了合同的,有扶持。其次,是一篇非虚构小说,州文联安排的,以姚安县农戏协会原会长、戏剧作家昝方才为题材。其它的,视情况而定,很随意,想写就写,不想写,就看书,就搜集整理素材,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姚安大事记》,民间立场,客观书写,有人物有事件,有正式结论,也有民间反响,还有对后世的影响等等,与撰写县志的表现手法不同,今后也可以作为县志的补充。算是一项拾遗补漏的创作吧。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写这部书,与写其他书不同,这部书是没有功利的,纯粹处于一个文化人的良心和责任担当,除此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