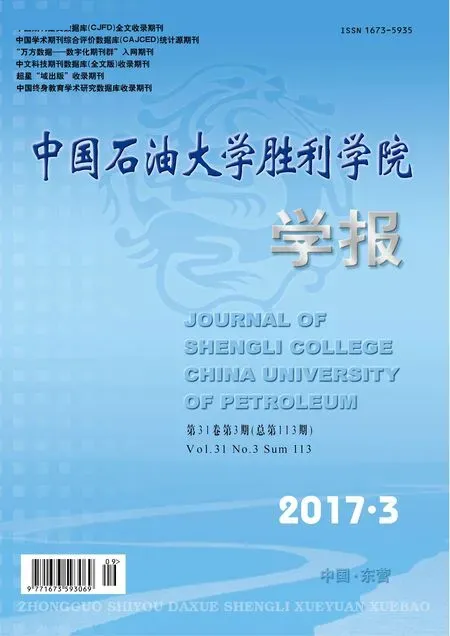孔子的温柔敦厚与审美人生的三重奏
伏爱华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2017-06-25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6A0050);安徽大学哲学系固本强基计划之开放性基金项目(GBX0006)
伏爱华(1976—),女,安徽来安人,安徽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西方美学研究。
10.3969/j.issn.1673-5935.2017.03.012
孔子的温柔敦厚与审美人生的三重奏
伏爱华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孔子的温柔敦厚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而是人的多样性情的中和,体现了人的原初性情——“仁”,因此成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当孔子把这种理想人格拉入到现实社会时,呈现出审美人生的三重奏,即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孔颜乐处的生命状态和吾与点也的人生境界,而贯穿其中的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在孔子那里,“仁”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探讨,更是一种可行性的原则、规范,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
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孔颜乐处;吾与点也
儒家美学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以来都影响着中国古人,尤其是中国士人审美人格的建构。如我们所熟知的在孔子身上体现的“温柔敦厚”以及他提倡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在孟子身上体现的“浩然之气”以及他强调的“舍生取义”的大丈夫人格。人格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美学问题,是一个个体生命实现性与情的统一,并最终达到和谐——自由的最高人生境界的问题。《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1]1368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孔子的诗教思想的来源,而这一思想也在后世不断地得以继承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孔子诗教的宗旨就在于通过《诗》的陶冶,使得人们具有温柔敦厚的人格特征。我们知道,在人格修养方面,孔子推崇的是君子人格,这在《论语》中有很多表述和体现。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人格修养与温柔敦厚的人格特征的关系?这样一种审美人格会成就一种什么样的审美人生?孔子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他希望成为或能够成为的人?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他愿意并努力去成就的人生?根据《论语》及后世有代表性的《论语》注疏和诠释,我们试图呈现孔子的审美人格与审美人生,由此看出在孔子那里,合乎至善的人格理想与人生境界是统一的。
一、温柔敦厚的审美内涵
温柔敦厚体现了孔子的诗教精神,也是其人格教化的集中体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1]1368因此,就人的言行趣尚、气质性情或品德修养而言,“温”即温和、平和的性情,“敦厚”即宽厚、深厚的人格底蕴,温柔敦厚即是指一种性情中和的人格特征。《论语·述而》①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可见,温柔敦厚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而是人的性情中多样因素的呈现。朱熹指出:“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2]139人的多种性情因素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和谐整一的呈现?因为温柔敦厚是孔子“仁”在人格理想上的体现,是“仁”将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实则一体的性情调和为一体。人的情绪本难控制协调,但孔子却游刃有余,恰到好处,因为他具备了“仁”。这也让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关于“仁”的论述和界定。“仁”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原初的性情,虽然在人世的生活中被遮蔽,但通过诗教,人的原初性情和情感获得启发,表现出温柔敦厚的人格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温柔敦厚是人原初的德性。这使得我们可以切实地领会、体悟、把握孔子的“仁”。
《论语·学而》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子禽问子贡,老师每到一个国家,一定与闻政治,这是他自己要求的呢,还是国君们要他过问的呢?“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朱熹注:“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也。”[2]74孔子的为人使得他能够非常主动、积极地要求参与政治,但同时又让那些国君们倾慕他、信服他、尊重他。无怪乎辜鸿铭发出感慨:“老师和蔼可亲、心无旁骛、诚挚热心、谦逊端庄、彬彬有礼,因此总可能获得想要了解的东西。大师获得信息的方式——哎,总是那么与众不同。”[3]13“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程子曰:“他人俨然则不温,温则不厉,惟孔子全之。”[2]258
《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理解为孔子不能容忍季氏的行为,那么只能说明孔子的德性修养不到家,不够“温”了[4]。所以恰当的理解应是,孔子由季氏的“八佾舞于庭”,判断出季氏这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的?因此,季氏后来的叛变、造反,都在孔子的预言之中。
作为一种理想人格,温柔敦厚要求为人中和,感情适度,能够包容别人的缺点,原谅别人的过错。如孔子评价颜回,“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2]30(中庸章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孔子将颜渊视为他最得意的弟子。而子张之过,子夏之不及,都是缺乏了“温”,即中正平和这一关键点。“白庸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在孔门七十二贤弟子中,具备温柔敦厚之德性的大概只有颜渊了。
那么,如何实现温柔敦厚的理想人格?《论语·雍也》做出了回答:“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略矣夫!”即通过外在的诗教、礼教、乐教,实现内在的性情修养。这即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
二、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
虽然后世将孔子推为圣人,但孔子自己也承认,圣人是很难遇见的,但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成为君子,关键就在于后天的教化。《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质为天生,虽然纯朴,但过于粗糙,因此需要后天的教化,如诗教、礼教、乐教等。君子人格就是外在的礼仪形式和内在的道德品质的统一;既有美的形式,又有善的内容。这里,我们用辜鸿铭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孔子说:‘当一个人的自然属性战胜了教育效果,他就是一个粗俗不堪的人。当教育效果战胜了人的自然属性,他就会变得很有涵养。只有当人的自然属性和教育效果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聪明而品德高尚的人。’”[3]103在此,辜鸿铭讽刺了那些只知著书立说的文人,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应通过文字来解释、批评、理解人类生活。李泽厚也有类似的观点:“‘质’,情感也;‘文’,理性也。‘质胜文’近似动物,但有生命;‘文胜质’如同机器,更为可怖。”[5]157-158“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味着既要有文化修养,又不要迷失本性;在真正的君子身上,体现的是经过教化的自然本性。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儒家讲的自然本性,并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根’,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6]
我们每个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成为高贵而有尊严的人。在孔子那里,君子人格不是少数的精英阶层,而是现实的、可学的,这样,孔子把成为君子的机会给予了每一个人。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指出:“孔子所设想的不是负责任的、理性的道德行动者作出一种不可化约的原初的选择,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过着最高尚的人性的生活方式,这种人格典范对那些具有潜质的人散发出一种完全非强迫但却富于强大吸引力的力量,继而,那些具有潜质的人受到典范的鼓舞,从而能够作出一种真诚的努力,通过掌握典范的生活方式并以这种方式艺术地生活,去学习参与到那种典范的生活方式之中。”[7]可见,成为君子即意味着人性的圆满自足。在孔子那里,这种人性即“仁”,而“仁”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它的获得又是非常容易的。《论语·述而》篇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如果说温柔敦厚使我们可以在人格的层面上切实地把握“仁”,那么,文质彬彬则告诉我们在人格的层面上如何具体地实现“仁”,践行“仁”。如果这样做了,我们的生命状态将不为世俗所缚,呈现一种自得的快乐和幸福。因为君子人格,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典范,更是一种美善合一的人生境界。
三、孔颜乐处的生命状态
《论语》中孔子多次谈到乐。如我们所熟知的《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再如《论语·述而》中孔子对自己的描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不为外界的物质所动,一心专注于内心的德性,所以其弟子看到的孔子是:“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这种出于人世而又高于人世的生活态度,可爱又可敬。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后世的假道学往往做出一副紧张面孔和“圣人气象”,令人望而生厌。“中国人之乐天知命,俯仰不愧,申申夭夭,倒是值得肯定的生活境界。”[5]172
这种生活态度还体现在颜渊身上。《论语·雍也》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朱熹注曰:“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2]120辜鸿铭对这段话的解释更可爱:“谈到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时,孔子说:‘这个人很有英雄气概!每天只吃一次饭、喝一次水,生活在全城最低矮的茅舍中。没有人可以经受住这样的艰难困苦,只有他依然自得其乐。这样的人是多么伟大啊!’”[3]99这种伟大就在于,无论环境是多么的艰苦,但依然满足而快乐。
那么,孔子和颜回“乐”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无论外界环境如何流转变化,为什么他们都能够保持愉快的心情,过平淡的生活?这难道只是学习所带来的快乐?或是闻《韶》所感受到的艺术之乐?抑或是我们通常所称颂的“安贫乐道”?程子“引而不发”,朱子“不敢妄为之说”,但这种孔颜乐处却为他们所津津乐道,并对后世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建构和人生境界的追求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首倡“孔颜之乐”的周敦颐那里,其根本用意在于标示一种超拔世俗富贵的“见其大而忘其小者”的人生境界。儒家君子一旦领略了这种人生境界,就能体悟出一副“以道充为贵,以身安为富”的“心泰”,“心泰则无不足”[8]矣。李泽厚指出,“此‘乐’即‘仁’,乃人生境界,亦人格精神。”[5]183孔子的“乐在其中”,颜回的“不改其乐”,大抵在于他们的生命状态达到了“仁”的境界。钱穆认为:“仁乃一种心境,亦人心所同有,人心所同欲。桃杏之核亦称仁,桃杏皆从此核生长,一切人事可久可大者,皆从此心生长,故此心亦称仁。若失去此心,将如失去生命之根核。浅言之,亦如失去其可长居久安之家。故无论外境之约与乐,苟其心不仁,终不可以久安。安仁者,此心自安于仁,如腰之忘带,足之忘履,自然安适也。”[9]可见,“仁”对于理想人生的至关重要。尽管孔子对“仁”的解释很神秘,而且充满歧义,但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仁者是快乐的,“仁者不忧”。这在《论语·子罕》和《论语·宪问》中有明确的表述。因此孔子能够“安仁”,颜回能够 “不违仁”,子路因为不知“仁”,所以无法达到此种境界,获得此种生命状态。
四、吾与点也的人生境界
《论语·先进》篇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说的都是经世治国之大业,而曾皙却描绘了一幅“春风沂水”图卷。“‘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感慨,他的志向与曾点的志向是一致的。那么,孔子的志向是什么?《论语·公冶长》篇载,有一天,颜渊和子路侍坐,孔子问他们的志向。当两个弟子回答后,子路转而问孔子的志向。“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见,孔子的志向就是天下都过得幸福快乐,各得其所,也就是天下大同。杨树达按语:“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10]
但这种大同社会非一己之力可以实现,因此孔子希望人通过修养成为君子,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孔子又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如果君子把一个特定的功能或职业作为自己的志向,那么就限制了“仁”的丰富内涵及其超越性。所以孔子对前三子的志向不发一言,独独“与点”,原因盖于此。傅佩荣指出:“如果以一个可以达成的目标作为一生的志向,那么,在生命的某个阶段达成之后,剩下的生命就落空了,那种落空是非常可怕的。”[11]因此,志向不是某个具体的职业或事业,而是内在性情与外在志趣结合的一种大志向。《论语·公冶长》篇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孔子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漆雕开的“不器”,不以个人的志向为志向,而是以人的志向为志向。孔子、曾点、漆雕开的志向皆如此。“在《论语》当中,孔子没有号召他的学生谋求成为在身份、分工意义上的‘君子’,而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具备君子的心胸品格。”[12]因此,程子指出这是一种“天地气象”“圣贤气象”[2]115,“使万物莫不遂其性”[2]179。
其实对于前三子的志向,孔子也并未否定。毕竟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是以他们的事业为基础而实现的。只不过孔子更强调对个人志向的超越,即“君子不器”的精神气象,由此才能达到合乎至善的人格理想,并在现实中实现审美自由的人生境界。因此,曾点描绘的并不只是一幅政治理想画卷,更是一种自然、社会与人生合一的审美境界。正是在这种至善的理想社会中,达到人生的至美之境。徐复观由此作出了新的解释:“孔子之所以深致喟然之叹”,正是感动于“曾点由鼓瑟所呈现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艺术境界”,“此种艺术境界,与道德境界,可以相融合”[13]。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孔子那里,最高的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即是审美自由的人生境界。
温柔敦厚是人的多样性情的中和,体现了人的原初性情——“仁”,因此成为孔子理想人格的特征。当孔子把这种理想人格拉入到现实社会,将其界定为君子,而且人人都可以通过博文约礼成就这种理想人格,成就善的人生。一旦成为君子,也就实现了人性的圆满自足,快乐而充实。此时的人已不再局限于现实中的个体,而是超越到人生的层面,达到审美自由的境界。这也契合了孔子思想的核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正如张世英所指出的:“审美意识给人以自由。”[14]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那里,“仁”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性的探讨,更是一种可行性的原则、规范,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
张法指出,孔子美学“从人可以切实地把握住的仁出发,展开为三种境界:进入政治人生中的‘文质彬彬’、远离政治人生中的‘孔颜乐处’、超越一切的‘吾与点也’。”[15]如果我们把这些命题看作是对孔子理想人格的具体表述,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归纳:“文质彬彬”体现了君子的社会性,即“善”;“孔颜乐处”体现了君子的自主性,即“真”;“吾与点也”体现了君子的超越性,即“美”。真、善、美构成温柔敦厚这一理想人格特征的丰富内涵,呈现出孔子审美人生的三重奏,贯穿其中的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美其实是体现人们所期盼的生存样态的形象。只有抓住人格理想……,一些美学范畴、命题才有各得其所的归宿。”[16]
研究传统,并不是要今人按古人的方式去生活、思考,而是提升我们的人格修养和生命智慧,从中领悟出当下的“安身立命”之本,也就是如何实现我们的社会关怀、人生关怀和价值关怀。生命是活生生的,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境遇中生成着的。我们不可能在今日重现或复制孔子的理想人格,但至少可以由此反思当下,缓解因激烈的社会竞争所带来的生命紧张和生命压抑状态,期待生命存在诗意而和谐地栖居。
[注释]
① 本文所引《论语》原文均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下文出现,不再一一注明。
[1]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M]//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8.
[3] 辜鸿铭.辜鸿铭讲论语[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4] 南怀瑾.论语别裁(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20.
[5] 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 彭锋.君子人格与儒家修养中的美学悖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4):18-23.
[7] 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109-110.
[8] 谭忠诚.君子修养与心灵安顿[J].中州学刊,2014(8):13-18.
[9] 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84.
[10] 杨树达.论语疏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78.
[11] 傅佩荣.傅佩荣细说孔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8.
[12] 孙焘.中国美学通史·先秦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66.
[13]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
[14]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25.
[15] 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41.
[16] 胡家祥.人格理想:美学史研究不容忽视的方面[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144-150.
B222.2
A
1673-5935(2017)03- 0039- 04
[责任编辑]谭爱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