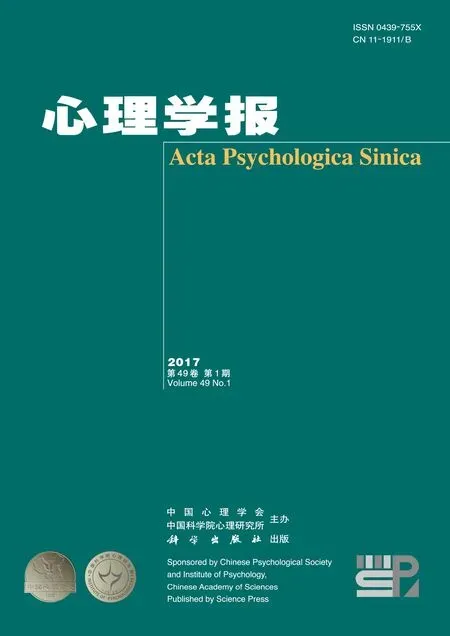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1 问题提出
社交网站是基于用户真实社交关系的沟通交流平台, 其代表主要有国外的 Facebook和国内的QQ空间和人人网等, 社交网站已成为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和平台, 我国社交网站的覆盖率已达到 61.7%, 而且 57.9%的用户每天都会使用社交网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4)。社交网站的普及使其对个体的影响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 而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研究者有意识地分类整合社交网站使用行为, 将社交网站使用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主动性使用(active use)和被动性使用(passive use) (Frison & Eggermont, 2016; Verduyn et al.,2015)。主动性使用是指能够增进沟通交流的信息生成行为, 如状态更新或留言评论等, 而被动性使用则是指缺乏交流沟通的信息浏览行为, 如浏览动态信息或他人状态等(Verduyn et al., 2015)。研究表明, 社交网站上的自我呈现、自我表露等主动性使用行为对个体自我和心理社会适应都会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强化自尊水平(Toma & Hancock, 2013;Yang, 2014), 增加社会资本、削弱孤独感(Burke,Marlow, & Lento, 2010), 提高生活满意度(Kim &Lee, 2011)。而信息浏览类的被动性使用行为则对个体心理社会适应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会削弱社会资本、强化孤独感(Burke et al., 2010), 诱发消极情绪、削弱情绪幸福感(Verduyn et al., 2015), 引起妒忌心理, 还能通过妒忌的中介作用影响生活满意度(Krasnova, Wenninger, Widjaja, & Buxmann, 2013)和抑郁(Tandoc, Ferrucci, & Duffy, 2015)。因此, 主动性使用和被动性使用的研究有助于区分不同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不同影响, 从而更加全面客观的看待社交网站对个体的影响。但是, 相比自我表露/自我呈现等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 目前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关注还相对较少。研究发现,个体绝大部分社交网站使用时间是在进行信息搜寻与信息浏览, 而不是自己发布信息(Wise,Alhabash, & Park, 2010), 即相比主动性使用行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占更大的时间比重, 关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有其必要性。
除“被动性使用”之外, 也有研究者将信息浏览类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称为“信息消化” (content consumption)、“人际监视” (interpersonal surveillance)、“Facebook 监视” (Facebook surveillance)、“被动关注 ” (passive following)等 (Burke et al., 2010;Krasnova et al., 2013; Tandoc et al., 2015; Tokunaga,2011)。已有研究虽然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生活满意度(Krasnova et al., 2013)以及抑郁(Tandoc et al.,2015)等心理社会适应指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如妒忌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探讨, 但是, 关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自我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个体对自己的知觉和认识, 它既是心理发展的重要反映性指标, 也对个体的心理与行为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Harter,2006)。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都是自我概念的重要成分, 自尊也被称作一般自我概念, 反映着自我概念的积极性水平(Harter, 2006), 一般而言, 自尊有助于个体心理健康的维护, 它能显著缓解焦虑和抑郁(Bajaj, Robins, & Pande, 2016), 并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Ye, Yu, & Li, 2012)。自我概念清晰性则是指个体对自我认识的清晰程度, 反映着自我概念的明确性和一致性水平(Campbell et al., 1996), 对生活满意度、抑郁等心理社会适应指标也有重要的影响(Lee-Flynn, Pomaki, DeLongis,Biesanz, & Puterman, 2011; Usborne & Taylor, 2010)。本研究拟进一步探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1.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关系
虽然社交网站上的自我呈现等主动性使用行为有助于获取积极反馈, 强化自尊水平(Yang,2014)。但是, 也有研究表明, 社交网站使用时间同自尊显著负相关(Kalpidou, Costin, & Morris, 2011),使用强度负向预测自尊水平(Blomfield Neira &Barber, 2014; Vogel, Rose, Roberts, & Eckles, 2014),说明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自尊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此外, 研究指出,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会显著诱发消极情绪, 削弱情绪幸福感(Verduyn et al.,2015)。而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指出, 积极情绪能够扩展个体的瞬间思维和活动序列, 推动建设个体资源, 包括身体资源、人际资源和心理资源等,相反, 消极情绪则会缩减个体的瞬间思维和活动序列, 阻碍个体资源的建设(Fredrickson, 2001)。自尊是个体重要的心理资源(Pyszczynski, Greenberg,Solomon, Arndt, & Schimel, 2004)。研究也表明, 积极情绪显著正向预测自尊, 而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自尊(Benetti & Kambouropoulos, 2006)。因此,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可能因为影响个体的情绪进而对自尊产生负性影响。基于此, 本研究假设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自尊水平(H1)。
此外, 针对网络使用对自我概念的影响,Valkenburg和Peter (2008, 2011)提出了“自我概念分化假说” (the self-concept fragmentation hypothesis):互联网使个体可以较为容易的塑造多种可能自我,更使他们面对人和思想的多种可能性, 可能会碎片化其人格, 削弱他们整合自我不同方面为统一整体的能力, 使个体面临自我概念无法整合的风险, 造成自我概念混乱。该假说得到相关研究结果的证实,如Israelashvili, Kim和Bukobza (2012)的研究表明,网络使用强度越高的个体, 其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低。关于社交网站的研究也发现, 由于社交网站中他人信息的易得性,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能够直接以及通过社会比较倾向的中介作用间接负向预测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牛更枫等, 2016)。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无疑会加剧该影响——被动性使用是对社交网站上大量他人信息的浏览和阅读, 会使个体直接面对人和思想的多种可能性, 增加自我概念无法整合的风险。因此, 本研究假设,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H2)。
1.2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针对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的消极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社交网站上的社会比较是一个关键因素(Appel, Gerlach, & Crusius, 2015)。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人们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定义自己的社会特征(邢淑芬, 俞国良, 2005)。依据比较方向的不同, 社会比较可以分为平行比较(与同自己水平相近的人进行比较)、下行比较(与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和上行比较(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他人信息是社会比较产生的重要诱因(Mussweiler, Rüter, & Epstude, 2006)。在现代信息社会, 社交网站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并进行社会比较的新平台。在社交网站上, 浏览阅读好友自我呈现的信息以及好友间交流互动的信息都可能会诱发社会比较, 研究也表明,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同社会比较倾向显著正相关(Fardouly & Vartanian,2015), 而且社交网站使用更多诱发的是上行社会比较(de Vries & Kühne, 2015; Vogel et al., 2014)。因为社交网站是基于熟人关系的网络媒介, 个体为维护良好的自我形象, 会在尽量保证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 呈现相对积极的信息, 所呈现的信息并非是虚假的, 但可能隐去了其中消极的成分, 凸显了信息的积极性, 以反映理想的生活和积极的自我形象(Yang, 2014)。对社交网站上积极信息的频繁浏览会让个体觉得他人有着更好的生活, 过得更加幸福(Chou & Edge, 2012), 自己不如他人, 甚至产生妒忌心理(Krasnova et al., 2013; Tandoc et al., 2015)。而社会比较特别是上行社会比较是妒忌产生的关键原因(杨丽娴, 张锦坤, 2009)。因此,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很有可能是先引发上行社会比较进而导致妒忌的。
此外,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 上行社会比较产生的对比效应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水平, 对个体心理产生消极影响(邢淑芬, 俞国良, 2006; Collins,1996)。相关研究也发现, 上行社会比较会导致反刍、妒忌以及抑郁(Appel et al., 2015; Feinstein et al.,2013)等消极心理。同时, 上行社会比较也会对个体自我概念产生消极影响, 研究发现, 上行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身体意象不满(Arroyo, 2014), 显著负向影响自尊水平(Vogel et al., 2014), 而且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Butzer & Kuiper,2006)。此外, 研究者还指出, 上行社会比较能够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自尊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Vogel et al., 2014 ), 社会比较倾向也能够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牛更枫等, 2016)。基于此, 本研究假设: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以及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H3)。
1.3 乐观的调节作用
虽然经典社会比较理论强调社会比较的对比效应, 但是上行社会比较的负面效应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变的, 由于对社会比较信息加工和理解的不同, 上行社会比较的负面效应可能在某些个体身上会较弱或是不显著, 甚至不排除出现同化效应(即, 上行社会比较提升个体的自我评价水平)的可能性(邢淑芬, 俞国良, 2005, 2006; Collins, 1996)。社会比较与其影响结果之间存在某些调节变量, 其中个体差异受到研究者较多的关注(邢淑芬, 俞国良, 2006)。
乐观是一个重要的个体特征变量, 高乐观者对未来有着积极的预期, 更加相信事情会有好的结果、未来会有好的境遇(Carver & Scheier, 2005)。研究表明, 乐观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密切, 与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齐晓栋, 张大均,邵景进, 王佳宁, 龚玲, 2012; Kapikiran, 2012), 而与抑郁、敌意以及焦虑等负性心理则显著负相关(齐晓栋等, 2012; Boman & Yates, 2011)。作为个体发展的保护性因素, 乐观还是调节压力情境与个体身心健康之间关系的重要内部资源(齐晓栋等,2012)。乐观有可能对社会比较信息的加工和理解产生影响。因为乐观的个体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积极的预期(Carver & Scheier, 2005), 当面对上行比较信息所反映的他人的美好生活或积极形象时, 高乐观水平的个体可能认为自己以后也能达到同等或类似的水平, 因此上行社会比较的对比效应可能会较弱甚至是不显著。Lyubomirsky和Ross (1997)对社会比较效应的实验研究发现, 快乐水平在社会比较及其结果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快乐水平低的个体对上行社会比较信息极为敏感, 上行比较信息会显著削弱其积极情绪、降低其对自己能力的评价, 而快乐水平较高的个体则没有受到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关于社交网站的研究也发现, 社交网站上的负性社会比较(即对个体有消极影响的上行社会比较)在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自我知觉之间的中介作用受到快乐水平的调节, 在快乐水平高的个体中, 负性社会比较的效应相对较弱(de Vries &Kühne, 2015)。可见, 快乐的人能够策略性地加工和理解社会比较的信息来维护其自我评价(邢淑芬,俞国良, 2006; Lyubomirsky & Ross, 1997)。研究者指出, 快乐与乐观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 乐观也极有可能在社会比较及其结果之间起着调节作用(Lyubomirsky & Ross, 1997)。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假设: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自尊以及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半段路径)会受到乐观的调节, 相对于乐观水平高的个体,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在乐观水平低的个体中更显著(H4)。
综上所述, 本研究拟同时探讨和对比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以及乐观的保护性作用的研究, 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研究假设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并且该中介作用的发挥受到个体乐观水平的调节, 以期深入揭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有社交网站(QQ空间、人人网以及微信朋友圈)使用经验的大学生1300名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1208份, 有效回收率为92.92%。其中男生588人(48.68%), 女生620人(51.32%); 大一396人(32.78%, 男生197名,女生199名), 大二402人(33.28%, 男生194名, 女生208名), 大三410人(33.94%, 男生197名, 女生213名)。被试的性别在年级上的分布无显著差异(χ2(2)=0.28,p=0.87); 被试的年龄在17~24岁之间(M=19.86;SD=1.26)。
2.2 研究工具
2.2.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
采用 Tandoc等人(2015)在针对被动性Facebook使用研究中编制的“监视使用”量表(Surveillance Use Scale), 来测量个体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强度。在进行研究之前, 先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并就相关语言表述进行讨论修改, 最终形成了本研究使用的正式量表。量表要求被试对4个项目所描述的社交网站使用行为的频率进行评定(如, “阅读好友更新的状态”; “查看好友上传的照片”)。为避免主动性使用行为对被动性使用行为效应的影响, 量表指导语提醒被试根据自己使用社交网站过程中没有信息表露时的情况, 回答上述4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 1表示“从不”, 5表示“频繁”,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频率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1.04, RMSEA=0.01, CFI=0.99,NFI=0.99, GFI=0.99, TLI=0.99,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3。
2.2.2 上行社会比较
采用白学军、刘旭和刘志军(2013)翻译Gibbons和 Buunk (1999)编制的爱荷华−荷兰比较方向量表(Iowa-Netherlands Comparison Orientation Measure)中的上行社会比较分量表。为了使测量的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 将量表中比较的范围限定为“在社交网站上”。该量表共包含6个项目(如, “在社交网站上, 我经常喜欢与那些过得比自己好的人进行比较”), 采用 5点计分,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社交网站中进行上行社会比较的频率也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5.85, RMSEA=0.06,CFI=0.99, NFI=0.99, GFI=0.99, TLI=0.98, 表明修订后的量表结构效度良好。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6。
2.2.3 自尊
采用中文版本的 Rosenberg自尊量表(汪向东,王希林, 马弘, 1999)。Rosenberg自尊量表中文版最初共包含10个项目(如, “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至少与其他人一样”), 采用4点计分法, 1表示“很不符合”, 4表示“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但由于第 8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所表述的内涵存在文化差异,许多研究者在使用中将其删除以提高量表信效度(田录梅, 2006; 陈陈, 燕婷, 林崇德, 2013), 本研究也采用此做法。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0。
2.2.4 自我概念清晰性
采用 Campbell等人(1996)编制的自我概念清晰性量表(Self-Concept Clarity Scale)来测量个体自我概念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在进行研究之前, 先将问卷翻译成中文并就相关语言表述进行讨论修改,最终形成了本研究使用的正式问卷。该问卷共包含12个项目(如, “我很少体验到性格不同方面的冲突”), 采用5点计分, 1表示 “很不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良好:χ2/df=5.48,RMSEA=0.06, CFI=0.94, NFI=0.93, GFI=0.96,TLI=0.92。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9。
2.2.5 乐观
采用刘志军和陈会昌(2007)修订 Scheier, Carver和Bridges (1994)编制的生活取向问卷(LOT-R, Life Orientation Test)。该问卷共包含12个项目, 其中乐观维度有 5个项目(如, “我总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会很好”), 悲观维度也有5个项目(如,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想事情都不会顺利发展”), 另外 2个为干扰项目不计入总分。采用5点计分法, 1表示“非常不同意”, 5表示“非常同意”, 将悲观项目反向计分后加上乐观项目分就得到个体总体的乐观水平,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乐观水平就越高。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α系数为0.72。
2.3 程序及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主试均为心理学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以班级为单位, 每班配备1~2名主试, 由研究生主试使用统一问卷进行集体施测。主试首先确认潜在被试是否是社交网站用户(是否使用QQ空间、人人网与微信朋友圈之类的社交网站), 如果不是则不能参与此次调查; 然后, 向符合条件的被试宣读指导语, 以阐明测验目的、答题方式、自愿填写以及匿名原则等; 被试被要求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规定时间内(约20分钟)独立完成调查; 最后, 剔除空白问卷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 得到本次研究的数据。
使用SPSS 17.0以及Hayes (2013)的SPSS宏程序PROCESS来整理和分析数据。该SPSS宏程序可以基于偏差校正百分位的 Bootstrap法对多种有中介的调节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 许多学者都使用过该程序检验中介效应前半段或是后半段是否受到调节(Chardon, Janicke, Carmody, &Dumont-Driscoll, 2016; Nyadzayo & Khajehzadeh,2016)。通过抽取5000个Bootstrap样本(每个样本容量均为1208人), 获取参数估计的稳健标准误和Bootstrap置信区间, 若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则表示结果有统计显著性(Erceg-Hurn & Mirosevich, 2008)。
3 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 在程序方面进行了相应控制, 如采用匿名方式作答、部分条目反向表述等;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的严谨性,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设定公因子数为1, 采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拟合指数如下:χ2/df=14.30, RMSEA=0.11, CFI=0.37, NFI=0.36, GFI=0.55, TLI=0.34, 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差异检验结果表明, 自尊存在性别差异(t=−2.17,p< 0.05,d=−0.09), 女生的自尊水平稍高于男生; 自我概念清晰性存在年级差异, 大一、大二学生的自我概念清晰性水平无显著差异, 但两者显著高于大三学生(F(2,1205)=4.31,p< 0.05,η2=0.01)。为保守起见, 在后续的分析中将性别与年级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其影响。此外, 考虑到社交网站使用时间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之间的关系, 为排除社交网站使用时间对目标变量之间关系可能的影响, 将被试平均每天的社交网站使用时间也作为控制变量。在控制性别、年级和平均每天的社交网站使用时间之后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上行社会比较显著正相关, 与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相关; 上行社会比较与自尊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负相关; 自尊与自我概念清晰性显著正相关; 乐观与自尊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相关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 Hayes (2013)的 SPSS宏程序 PROCESS,在控制性别、年级和平均每天的社交网站使用时间的条件下, 分析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半段)是否受到乐观的调节。
检验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半段是否受到乐观的调节,结果表明(如表2所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显著正向预测上行社会比较(β =0.49,p< 0.001); 上行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测自尊(β =−0.17,p< 0.001),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0.01,p> 0.05); 上行社会比较与乐观的交互项对自尊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12,p< 0.001)。
在乐观得分为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 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3所示。

表2 乐观调节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表3 不同乐观水平时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

表4 乐观调节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检验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后半段是否受到乐观的调节, 结果表明(如表 4所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显著正向预测上行社会比较, β =0.49,p<0.001; 上行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β=−0.23,p< 0.001,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β=−0.19,p< 0.001; 上行社会比较与乐观的交互项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 β=0.07,p< 0.01。
在乐观得分为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 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5所示。
综合以上结果, 本研究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得到了支持。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起中介作用, 而且该中介作用后半段受到乐观的调节;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我概念清晰性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同时还能通过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 而且该中介作用的后半段也受到乐观的调节。

表5 不同乐观水平时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2 乐观对上行社会比较与自尊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图3 乐观对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乐观在上行社会比较与自尊以及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中的调节作用。按乐观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高乐观水平组(高于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低乐观水平组(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的被试)以及中等乐观水平组(介于上述两组之间的被试)。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上行社会比较与自尊的关系, 结果如图2所示:随着乐观水平的升高, 上行社会比较对自尊的负向预测作用逐渐减弱直至不显著(由β=−0.48,p< 0.001减弱为β=−0.05,p=0.51)。同样, 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关系, 结果如图3所示:随着乐观水平的升高, 上行社会比较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负向预测作用也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但其效应仍然显著(由 β =−0.45,p< 0.001 减弱为 β=−0.18,p< 0.05)。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没有直接的预测作用, 但是能够直接负向预测自我概念清晰性。该结果表明,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本身对自我概念不同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自尊反映的是自我概念的积极性水平(Harter, 2006),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只是让个体接触到了多种多样的信息, 如果没有因此诱发个体进行上行社会比较, 其自尊水平就不会受到显著影响。类似的,以往研究也发现,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的影响是通过妒忌的中介作用实现的, 而并没有直接的负性效应(Krasnova et al., 2013; Tandoc et al., 2015)。但是, 接触到大量他人信息, 本身就会导致个体直接面对人和思想的多种可能性, 可能碎片化其人格, 影响个体形成清楚一致的自我概念,该结果也与网络使用的“自我概念分化假说”以及相关研究相一致(牛更枫等, 2016; Valkenburg &Peter, 2008, 2011)。
4.1 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 社交网站使用强度显著正向预测上行社会比较(de Vries & Kühne, 2015; Vogel et al., 2014), 本研究则更进一步表明, 被动性的信息浏览行为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网站上的上行社会比较, 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社交网站作为沟通交流的载体, 信息的产生与信息的消化是紧密相连的, 自我表露产生的信息紧接着就会成为浏览阅读的目标, 成为触发社会比较的诱因。而个体在社交网站上的好友多是与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的现实生活中的同学或朋友, 社会比较倾向更容易在相似的群体间产生(邢淑芬, 俞国良,2005; Suls & Miller, 1977)。因此, 社交网站环境会触发和强化社会比较倾向。此外, 社交网站上的社会比较方向更多的取决于信息本身的性质(Feinstein et al., 2013; Vogel et al., 2014), 如前所述, 社交网站上的很多信息都过于凸显积极的一面, 会让个体觉得他人比自己更幸福, 而自己不如他人(Chou &Edge, 2012; Vogel et al., 2014), 甚至产生妒忌心理(Krasnova et al., 2013; Tandoc et al., 2015)。总之, 社交网站环境既会影响社会比较倾向(强化比较倾向),也会影响社会比较方向(诱发上行比较), 所以说,社交网站自身特性是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诱发上行社会比较的重要原因。
而上行社会比较会使个体的自我评价水平显著背离比较目标, 处在显著低于比较目标的水平上,个体的自我评价会因此变得比较消极(邢淑芬, 俞国良, 2006; Collins, 1996; Vogel et al., 2014)。同社会比较理论以及前人研究的结果一致, 本研究也发现, 上行社会比较显著负向预测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 而且更进一步证实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影响中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虽然两个中介模型有差异(即,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无直接效应, 而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我概念清晰性有直接影响), 但(当未考虑调节变量时)都存在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效应, 表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可以通过相同的内部机制对自我概念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上行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也说明, 更多的进行被动性使用的个体, 会更多的被诱发进行上行社会比较, 导致其不仅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消极, 而且对自己的认识也比较混乱。
4.2 乐观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 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上行社会比较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中介作用都受到乐观的调节, 相对于乐观水平高的个体, 间接效应在乐观水平低的个体中更显著。该结果同以往关于乐观保护性作用的研究结果一致(齐晓栋等, 2012), 即乐观作为重要的心理资源能够显著缓解负性因素对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 而且更进一步表明, 乐观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比较信息的加工和理解, 进而对个体起到很好的保护性作用。从以往积极心理学对乐观的研究可以发现, 乐观可能从认知、情绪和动机三个方面影响个体加工和理解社会比较信息。首先, 乐观的归因风格理论认为,乐观是一种解释风格, 高乐观者倾向于对好事做持久的、普遍的和个人的归因, 而对坏事做短暂的、具体的和外在的归因(Snyder & Shane, 2002)。所以,“他人比自己好”在高乐观者看来可能只是暂时的,或者只是某一方面比自己好; 其次, 乐观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 2003), 根据积极情绪的扩展−建构理论, 积极情绪能够构建和增强个人资源(Fredrickson, 2001), 有关研究也证实, 乐观水平高的人有着更多的心理资源, 如希望、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等(Feldman & Kubota,2015; Smith, Ruiz, Cundiff, Baron, & Nealey-Moore,2013)。而资源保存理论认为, 资源越多的个体越能够应对压力, 也越幸福和快乐(Hobfoll, 1989), 而越幸福和快乐的人越能够策略性地理解社会比较的信息(de Vries & Kühne, 2015; Lyubomirsky &Ross, 1997)。再次, 高乐观水平的个体更多地使用趋近(问题解决)而非回避的应对策略(Nes &Segerstrom, 2006), 面对上行社会比较的压力, 高乐观水平者可能会想办法缩短自己与他人的差距,此时,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所诱发的上行社会比较可能对高乐观者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 高乐观水平的个体能够更加积极地应对上行社会比较,削弱乃至抑制上行社会比较对比效应的产生。
另外, 对比两个调节作用可以发现, 乐观更能缓解上行社会比较对自尊的负向影响, 而在上行社会比较与自我概念清晰性之间的保护性作用相对较弱。关于乐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指出, 在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中, 乐观与自尊的相关最高(齐晓栋等, 2012), 因此, 乐观能够对自尊起到更好的保护性作用。
4.3 研究意义与研究不足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 既是对以往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个体心理社会适应研究的拓展, 也是对社交网站使用强度与自我概念研究的深化, 更是对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与自我概念研究的补充, 有助于区分不同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对自我概念的不同影响, 从而更加全面客观的看待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心理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将中介模型进一步深化, 既解释了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如何影响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 也进一步说明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通过上行社会比较影响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的情况在哪些个体身上更明显, 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
本研究对于引导与促进大学生自我概念发展、弱化与抑制社交网络使用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的消极影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会直接负向影响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性,并且间接负向影响个体自尊, 因此个体应该尽量减少自己的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 不去频繁的“刷空间”和“刷朋友圈”; 其次, 上行社会比较是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行为影响自尊以及自我概念清晰性的重要原因, 个体在使用社交网站时应该努力抑制自己的上行社会比较行为, 不随意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 特别是不将自己知觉为明显比他人差;再次, 乐观能够显著缓解社交网站上行社会比较的负面影响。研究指出, 乐观虽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 但同时也有较高的可塑性(Orejudo,Puyuelo, Fernández-Turrado, & Ramos, 2012), 通过学习人们可以将悲观的归因方式转换为乐观的, 形成习得性乐观(Snyder & Shane, 2002)。因此, 努力学习和保持乐观的心态能够帮助个体削弱和抑制社交网站中的上行社会比较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自我概念有多个维度和成分, 本研究只关注了自尊和自我概念清晰性两个方面, 而且关注的也只是外显自尊,未来的研究可以同时探讨或对比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与外显自尊以及内隐自尊的关系, 或是被动性使用与自我概念其他成分(如身体自我概念、外貌自我概念)之间的关系, 以更加全面的揭示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个体自我概念的影响。其次, 社交网站上的某些信息是否会对个体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 以及平行社会比较或下行社会比较是否有可能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 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的问题之一。最后, 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设计, 尽管对各变量关系的分析与讨论是建立在已有理论和研究基础之上的, 结果仍不能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纵向研究或是行为实验来对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Appel, H., Crusius, J., & Gerlach, A.L.(2015).Social comparison, envy, and depression on Facebook: A study looking at the effects of high comparison standards on depressed individuals.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4(4), 277–289.
Arroyo, A.(2014).Connecting theory to fat talk: Body dissatisfac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eight discrepancy, upward comparison, body surveillance, and fat talk.Body Image, 11(3), 303–306.
Bai, X.J., Liu, X., & Liu, Z.J.(2013).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ocial comparis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hievement goal and academic self-efficacy: Evidence from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6), 1413–1420.
[白学军, 刘旭, 刘志军.(2013).初中生社会比较在成就目标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之间的中介效应.心理科学, 36(6),1413–1420.]
Bajaj, B., Robins, R.W., & Pande, N.(2016).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fulness,anxiety, and depress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96, 127–131.
Benetti, C., & Kambouropoulos, N.(2006).Affect-regulated indirect effects of trait anxiety and trait resilience on self-esteem.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1(2),341–352.
Blomfield Neira, C.J., & Barber, B.L.(2014).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Linked to adolescents’ social selfconcept, self-esteem, and depressed mood.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1), 56–64.
Boman, P., & Yates, G.C.R.(2001).Optimism, hostility, and adjustm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high school.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1(3), 401–411.
Burke, M., Marlow, C., & Lento, T.(2010, April).Social network activity and social well-being.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pp.1909–1912).ACM, New York, America.
Butzer, B., & Kuiper, N.A.(2006).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comparisons and self-concept clarity,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1(1), 167–176.
Campbell, J.D., Trapnell, P.D., Heine, S.J., Katz, I.M.,Lavallee, L.F., & Lehman, D.R.(1996).Self-concept clarity: Measuremen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70(1), 141–156.
Carver, C.S., & Scheier, M.F.(2005).Optimism.In C.R.Snyder & S.J.Lopez (Eds.),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pp.231–243).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rdon, M.L., Janicke, D.M., Carmody, J.K., & Dumont-Driscoll, M.C.(2016).Youth internalizing symptoms,sleep-related problems, and disordered eat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Eating Behaviors,21, 99–103.
Chen, C., Yan, T., & Lin, C.D.(2013).Perfectionism, selfesteem, and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9(4), 368–377.
[陈陈, 燕婷, 林崇德.(2013).大学生完美主义、自尊与学业拖延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 29(4), 368–377.]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2014).The research report on user behavior of Chinese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in 2014.Retrieved from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408/P02014082237 9356612744.pdf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2014年中国社交类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取自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sqbg/201408/t20140822_47860.htm]
Chou, H.T.G., & Edge, N.(2012).“They are happier and having better lives than I am”: The impact of using Facebook on perceptions of others’ lives.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2), 117–121.
Collins, R.L.(1996).For better or worse: 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self-evaluation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1), 51–69.
de Vries, D.A., & Kühne, R.(2015).Facebook and self-perception: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negative social comparison on Facebook.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86, 217–221.
Erceg-Hurn, D.M., & Mirosevich, V.M.(2008).Modern robust statistical methods: An easy way to maximize the accuracy and power of your research.American Psychologist,63(7), 591–601.
Fardouly, J., & Vartanian, L.R.(2015).Negative comparisons about one’s appearance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usage and body image concerns.Body Image, 12,82–88.
Feinstein, B.A., Hershenberg, R., Bhatia, V., Latack, J.A.,Meuwly, N., & Davila, J.(2013).Negative social comparison on Facebook and depressive symptoms:Rumination as a mechanism.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2(3), 161–170.
Feldman, D.B., & Kubota, M.(2015).Hope, self-efficacy,optimism,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Distinguishing constructs and levels of specificity in predicting college grade-point average.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37, 210–216.
Fredrickson, B.L.(2001).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18–226.
Frison, E., & Eggermont, S.(2016).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acebook use, perceived online social support, and adolescents’ depressed mood.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34(2), 153–171.
Gibbons, F.X., & Buunk, B.P.(1999).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mparison: Development of a scale of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1), 129–142.
Harter, S.(2006).The self.In W.Damon, R.M.Lerner, & N.Eisenberg (Eds.),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3.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6th ed., pp.505–570).Hoboken, NJ: Wiley.
Hayes, A.F.(2013).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New York: Guilford Press.
Hobfoll, S.E.(1989).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American Psychologist,44(3), 513–524.
Israelashvili, M., Kim, T., & Bukobza, G.(2012).Adolescents’over-use of the cyber world–Internet addiction or identity exploration?Journal of Adolescence, 35(2), 417–424.
Kalpidou, M., Costin, D., & Morris J.(201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ebook and the well-being of undergraduate college students.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4), 183–189.
Kapikiran, N.A.(2012).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ity as mediator and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sm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Turkish university stud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6(2), 333–345.
Kim, J., & Lee, J.E.R.(2011).The Facebook paths to happiness: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Facebook friends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Cyberpsychology,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6), 359–364.
Krasnova, H., Wenninger, H., Widjaja, T., & Buxmann, P.(2013).Envy on Facebook: A hidden threat to users’ life satisfaction?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rtschaftsinformatik, Leipzig, Germany.
Lee-Flynn, S.C., Pomaki, G., DeLongis, A., Biesanz, J.C., &Puterman, E.(2011).Daily cognitive appraisals, daily affect, and long-term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and self-concept clarity in the stress proces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2), 255– 268.
Li, J.Z., Wang, W.Z., & Shi, J.N.(2003).Positive psychology: A new trend in psychology.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3), 321–327.
[李金珍, 王文忠, 施建农.(2003).积极心理学: 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心理科学进展, 11(3), 321–327.]
Liu, Z.J., & Chen, H.C.(2007).Chinese revision of life orientation test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5(2), 135–137.
[刘志军, 陈会昌.(2007).生活取向量表在初中生中的初步修订.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5(2), 135–137.]
Lyubomirsky, S., & Ross, L.(1997).Hedonic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omparison: A contrast of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6),1141–1157.
Mussweiler, T., Rüter, K., & Epstude, K.(2006).The why,who, and how of social comparison: A social-cognition perspective.In S.Guimond (Ed.),Social comparison and social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cognition,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culture(pp.33–5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s, L.S., & Segerstrom, S.C.(2006).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coping: A meta-analytic review.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0(3), 235–251.
Niu, G.F., Sun, X.J., Zhou, Z.K., Tian, Y., Liu, Q.Q., & Lian,S.L.(2016).The effect of adolescents'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e on self-concept clar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9(1), 97–102.
[牛更枫, 孙晓军, 周宗奎, 田媛, 刘庆奇, 连帅磊.(2016).青少年社交网站使用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 社会比较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 39(1), 97–102.]
Nyadzayo, M.W., & Khajehzadeh, S.(2016).The antecedents of customer loyalty: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quality and brand image.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30, 262–270.
Orejudo, S., Puyuelo, M., Fernández-Turrado, T., & Ramos, T.(2012).Optimism in adolescenc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and peer group variables o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7), 812–817.
Pyszczynski, T., Greenberg, J., Solomon, S., Arndt, J., &Schimel, J.(2004).Converging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self-esteem: Reply to Crocker and Nuer (2004), Ryan and Deci (2004), and Leary (2004).Psychological Bulletin,130, 483–488.
Qi, X.D., Zhang, D.J., Shao, J.J., Wang, J.N., &, Gong, L.(2012).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8(4), 392–404.
[齐晓栋, 张大均, 邵景进, 王佳宁, 龚玲.(2012).气质性乐观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 28(4),392–404.]
Scheier, M.F., Carver, C.S., & Bridges, M.W.(1994).Distinguishing optimism from neuroticism (and trait anxiety, self-mastery, and self-esteem): A reevaluation of 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1063–1078.
Smith, T.W., Ruiz, J.M., Cundiff, J.M., Baron, K.G., &Nealey-Moore, J.B.(2013).Optimism and pessimism in social context: An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on resilience and risk.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7(5), 553–562.
Snyder, C.R., & Shane, J.L.(2002).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ls, J.M., & Miller, R.L.(1977).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Publication Services.
Tandoc, E.C., Jr., Ferrucci, P., & Duffy, M.(2015).Facebook use, envy, and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booking depressing?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43, 139–146.
Tian, L.M.(2006).Shortcoming and merits of Chinese version of Rosenberg (1965) Self-Esteem Scale.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6(2), 88–91.
[田录梅.(2006).Rosenberg (1965)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心理学探新, 26(2), 88–91.]
Tokunaga, R.S.(2011).Social networking site or social surveillance site? Understanding the use of interpersonal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n romantic relationships.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2), 705–713.
Toma, C.L., & Hancock, J.T.(2013).Self-affirmation underlies Facebook us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3), 321–331.
Usborne, E., & Taylor, D.M.(2010).The role of cultural identity clarity for self-concept clarity,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7), 883–897.
Valkenburg, P.M., & Peter, J.(2008).Adolescents’ identity experiments on the internet: Consequences for social competence and self-concept unity.Communication Research,35(2), 208–231.
Valkenburg, P.M., & Peter, J.(2011).Online communication among adolescents: An integrated model of its attraction,opportunities, and risks.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48(2), 121–127.
Verduyn, P., Lee, D.S., Park, J., Shablack, H., Orvell, A.,Bayer, J.,...Kross, E.(2015).Passive Facebook usage undermines affective well-being: Experimental and longitudinal eviden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44(2), 480–488.
Vogel, E.A., Rose, J.P., Roberts, L.R., & Eckles, K.(2014).Social comparison, social media, and self-esteem.Psychology of Popular Media Culture, 3(4), 206–222.
Wang, X.D., Wang, X.L., & Ma, H.(1999).Handbook of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Beijing: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Press.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1999).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Wise, K., Alhabash, S., & Park, H.(2010).Emotional responses during social information seeking on Facebook.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3(5),555–562.
Xing, S.F., & Yu, G.L.(2005).A review on research of social comparison.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78–84.
[邢淑芬, 俞国良.(2005).社会比较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心理科学进展, 13(1), 78–84.]
Xing, S.F., & Yu, G.L.(2005).Social comparison: Contrast effect or assimilation effect?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6), 944–949.
[邢淑芬, 俞国良.(2006).社会比较: 对比效应还是同化效应?心理科学进展, 14(6), 944–949.]
Yang, C.C.(2014).It makes me feel good:A longitudinal,mixed-methods study on college freshmen’s Facebook selfpresent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Yang, L.X., & Zhang, J.K.(2009).The progress and trends of th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envy.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2(3), 655–657.
[杨丽娴, 张锦坤.(2009).妒忌的心理学研究进展与取向.心理科学, 32(3), 655–657.]
Ye, S.Q., Yu, L., & Li, K.K.(2012).A cross-lagged model of self-esteem and life satisfaction: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4), 546–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