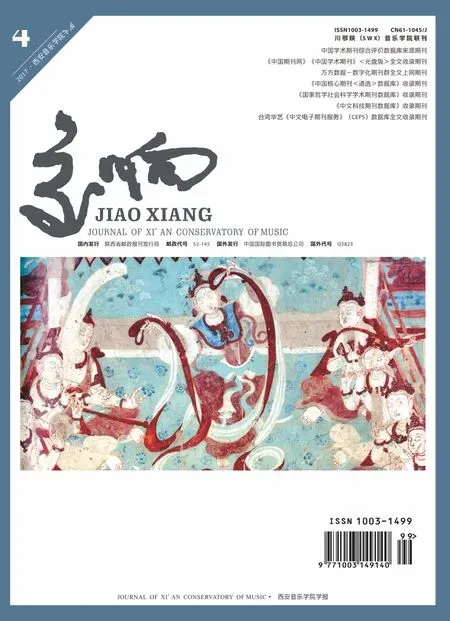圣洁灵魂的谦逊捍卫者
——记杰出的音乐学家高士杰教授
●李秀军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100101)
今年早些时候,无意翻阅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第一期,竟意外又发现了我的老师高士杰先生的新作,这让近年来更多忙于学校行政事务的我惭愧不已。令人折服的是先生在耄耋之年依然在自己钟爱的研究领域探索不止。看着文章的页下注,突然意识到今年适逢先生90华诞,感慨时光飞逝的同时,一时求学期间和老师的点点滴滴纷涌脑际,当即便想要给先生写点感悟。幸得《交响》学报委约,遂成此文。
高士杰先生一生低调谦逊,很不愿别人给他戴学术高帽子,特别是诸如以“家”来对他的称谓。但若以历史的求真和务实而言,高先生作为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音乐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我相信,凡是熟悉高士杰先生的人及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这一观点。纵观其一生的研究和教育生涯,私以为可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先生丰富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经历略作概括,即谦逊踏实的学术品格,与时俱进、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博大精深、大开大阖的研究视野,以及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
一、谦逊踏实的学术品格
高先生是我国音乐学界的旗帜性学者,也是西安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他既秉承了老一辈音乐学人谦逊踏实的学术传统,又奠定了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严谨深邃的学术根基。
正所谓文如其人。先生谦逊踏实的高贵品质无不体现在他的研究和写作之中,音乐学研究既是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又是心灵的自我安顿。先生作为国内早期的音乐学研究者,一直以来为人处事和蔼低调。犹记得先生在80岁高龄依然参加2010年的西方音乐史学年会及我多次回到西安音乐学院讲学的场景,当时先生每天自带笔记本,坐在前排,非常认真地聆听和记录最新的研究成果、学术走向和我讲课的学术内容。这为当时参会的很多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至今仍被广为称赞。
在我看来,在先生研究中透露着更为可贵的品性,谦逊和踏实。读先生的论著,我总是会将先生代入到他独具风格、非常富有逻辑、发问式娓娓道来的画面中。先生的写作仿佛是其敞开心房的灵魂物语:将自己敞开给真理,不受任何来自各方面的干扰,让人性之光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普照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让光明之处更加温暖,让阴霾之地也洒遍真善美的人性光辉。还记得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经常会引用著名史学家或者理论家的论述,末了总会加上语出何处和文献,从未随意妄加定论和恣意武断地评头论足。这给我们这些学生潜移默化地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至少在两个方面对我影响尤为巨大,一是注意文献的援引和出处,二是切忌妄下草率定论。
谦逊和踏实亦是先生为人处世最基本的准则。先生大多时候在生活中,是我们这些容易在现世迷宫中迷途小辈的心灵医生。也许很多学生都像我一样,在茫然不知所措时便会找到先生一问究竟,或是为了寻找解惑之道,或是为了抒发一己之愿。但是先生却总是谦逊详实地予以一一解答,并对其中不确切之处反复强调需要查实,这种踏实认真的学术态度至今令我受益良多。
二、博大精深、大开大阖的研究视野
通读先生的文论篇什,除了能够发现先生主要在西方音乐的学科建设、方法论探讨、基督教与西方艺术音乐的关系等相关方面的鞭辟入里的深入外,我们也不难看出其所具有博大精深、大开大阖的研究视野。
所谓博大精深是指先生在研究和文献写作中,除了西方音乐的专题精深研究外,对于相关课题辐射的广泛程度令人惊叹。先生文稿不但涉及到了西方音乐的直接学科,如西方史学、哲学等领域,更是渗透到了更大的文化语境中,尤其是在基督教神学和语言学方面。我在先生门下学习期间,先生在上课或课余不经意间的谈吐中,常常引用大量哲学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晦涩难懂的音乐理论,尤其是美学观念。而对于西方艺术音乐与基督教音乐及基督教的关系,先生的研究总是基于基督教最根本的原出含义和具体仪式的语境基础。一直强调我们若是做此类研究,一方面要从哲学的高度对基督教要有深刻的认识论方面的感悟;如先生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纲领”;另一方面也应该对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有所了解,最好是掌握。对于不同音乐历史时期的弥撒和经文歌的研究,尤其要注意其使用的仪式场合。这在先生关于基督教和西方音乐文化的关系的论述中可窥方略,如1994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3期的《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的若干思考》,1998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3期的《基督教精神与西方艺术音乐传统》,2009年发表于《交响》第2期的《理性面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基督宗教问题》。
所谓的大开大阖则是指先生研究和写作中选题广阔、深入浅出的研究理路。毋庸讳言的是,如此的写作态势大部分得益于其博大精深的研究基础和宏大的研究背景之上的。不论是先生关注的西方音乐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基督教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密切关系,还是对西方音乐本质的思考,先生在写作中都能够在笔饱墨酣的同时做到收放自如。我们不仅会发现其在研究中始终秉持的开放阔大的哲学高度,用高度的凝练和概括反观西方音乐发展的纷繁错综,而且能够拿捏到位地予以总结和阐述。就在前不久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又发表了题为《在人类音乐文化的大视野中认识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现状》的文章,在哲学的高度上对中国当下的音乐文化现状就音乐艺术的存在方式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这样的研究路式对于我辈学人不论是知识性的贯穿,还是学理性的构建均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其勤奋踏实的治学精神亦足以令我辈学人高山仰止!
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先生一路走来,在政治上可谓是随着共和国饱经沧桑。但不论是在“文革”极左狂潮的席卷,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极右思想的影响,先生始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在先生对马列经典文献持之以恒的研习,即使在今时今日,他依然勤学不悔;更重要的是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和辩证法的坚持和思考,这尤其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文艺路线上。
先生自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1958年起在西安音乐学院开始任教,随后便是“浩浩荡荡的十年文革”。面对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先生有太多的困惑和不解,但是苦于言喻。对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无疑给先生带来的是思想上受到的极大影响,甚至是精神上的浩劫,且其挚爱的教育和学术活动也一度终止。但即使如此,他也能在这场运动中保持其特有的冷静和清醒。面对举国癫狂的浪潮,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经过短暂的困惑和思考后,他立即醒悟到这是场违反人性的破坏,而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运动。恰恰是这一时期,他潜心修学,广泛积累,阅读了大量的原文文献和马列经典,反而为其日后研究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随着拨乱反正和党的正确路线的确立,国内的学术氛围得到了有效扭转。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自1982年发表在西安音乐学院学报《交响》第1期开篇之作的《论音乐的特殊性》起,先生便开始逐步对于文革时期“音乐的阶级性”等核心问题进行批判和纠正。先生讲道:“有一种主张音乐有阶级性的观点, 认为凡是情调不健康的糜糜之音就是资产阶级的音乐,而健康的音乐则是无产阶级的音乐。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1](P7)以及“有一种对文艺作品进行阶级分析的简单化或教条主义的做法,只要作品中表现了死亡、末日一类的内容,就被断定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这是没有说服力的。”[1](P8)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生对这种“七个音符阶级斗争”的驳斥,以及其对我国音乐事业健康发展的巨大危害。先生坚定地论述说明了组成音乐的物质基础,才是决定其特殊性的基本观点,并由此出发结合辩证法指出:“音乐是不是阶级性的艺术和音乐能不能在社会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这是两回事。在社会阶级斗争中,每一个阶级总是调动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为本阶级服务。”[1](P8)故而,音乐阶级属性是被其所利用的阶级所决定的,而非与生俱来便具有了阶级性。先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辩证法。
在随后先生发表的17篇论述中,无不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对其的深远影响。类似的论述我们可以在先生的很多文论中见到,如1991年发表于《中国音乐学》第1期的《建国以来的外国音乐研究》,1991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第6期的《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思考》,2007年发表于《交响》第1期的《对象性关系与西方音乐作品的解读》等。在《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思考》一文中,先生明确指出:“作为一门学科,西方音乐史应该全息性地反映西方音乐的发展演变过程。只有全方位、多视角地观察研究,才有可能对西方音乐史的各种现象做出比较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解释。”[2](P46)因而,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吸收西方史学理论成果的同时,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既然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那么,对西方音乐及其历史这一具体情况也必须去具体分析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2](P46)重读先生的这些论文,令我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结合时下中央倡导的“中国梦”,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宏观语境相结合,重新认识过去数十年音乐史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实践,先生的文论其实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恢弘大道。先生经过数十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的精心研读,以理论家特有的专业素养和理论修为,将其所经历和面对的学科困境和难题置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思辨和批判,并与时俱进地进行反思和发展。
四、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
先生在西安音乐学院从教的数十年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学专业人才,为我国的音乐学建设和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自20世纪中叶后在西安音乐学院任职,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音乐,尤其近二十多年来专注于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及两者的密切关系上。在逾50年的从教生涯中,高先生从实践中积极反思,并结合理论形成卓富成效的教学体系,这在近年的教学中屡见验证。先生地处教育资源和信息平台相较滞后的西北地区,如此斐然佳绩显然并非一日之功。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先生在音乐专业上的探索和积累,更重要的是他对教学实践的不倦探索。作为一名誉满华夏的西方音乐史学教授,在他看来,好的音乐学研究者首先应该具备合格的师德修养;同时,更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储备。除了自己所学的音乐专业知识外,相关姊妹艺术学科和人文、自然学科的知识亦十分重要。充足的知识储备是任何一位研究者必备的基本素养。此外,高尚的人格魅力也是一名优秀音乐学人由内及外的修养表现。在先生看来,育人为先、授业其次。若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个好人,以身作则尤为重要。
具备基本的研究素养之后,适当的研究态度也是成就研究生涯的必要保障。最好的前提是要热爱这项神圣的研究事业。当然真正的热爱不一定是惊天撼地般的风掣云涌,相较在稳定的热爱之下适当的情绪调节可能会更加适合长期优质的研究工作。这也许可通过先生对学生们关爱有加的态度上略窥一二。一直以来,先生的爱生如子已为佳话,但是先生并不竭力干扰学生的个性发展。
先生的教育理念丰富而多元,尤为突出的两点是因材施教和由浅入深,这二者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在先生看来,因材施教不单单是针对不同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学生的教育规划和帮助,去寻找学术的发展前景。虽然不同的学生会有自己的学术理想,但即使理想相同的人各项条件也会出现差之千里的反差。相较而言作为一个理想的局内人,很多时候对人生的塑造并非都具有实现性和操作性的。对于激情者而言,可能会将梦想缔造得绚烂富丽、甚至远远超出自己的实现能力。而对于谨慎者,却往往不敢妄下结论、裹足不前。先生在教育中,依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更深一步地考虑学生丰富多元的禀赋和个性,在发展前景和人生规划上做出不同的矫正和建议。因此,先生的因材施教是从单一知识性的量体裁衣进入到人性规划的多维交互式教育理念,从单一的“解惑”到更为丰富的“授业”,乃至“传道”。
由浅入深亦是建立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之上,又有其丰富的不同表现。从表意来看,即教学知识的循序渐进,在先生这里则更是知识体系、学习方法和人文素养的综合考量与推进。就西方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培养而言,先生在起初并不要求涉猎过于精深的专业书籍,而是通过做读书笔记的方式对基础性的知识体系进行架构。除基础教材外,根据自己的能力适当扩及阅读专业书目和相关姊妹艺术的经典著作。如此经过一年扎实的基础训练,不但在读书上收获颇丰,更能让学生触及其它艺术形式。这就如同建楼时的框架结构搭建,而之后的深度阅读和精细研究就如同填充墙体与装潢。
由此逐步深入,仿佛逐渐让先生的教育理念愈显清晰。最后得谈一谈先生以身作则和潜移默化双肩并举的教育方式,可能会更明晰地了解先生的教育理念。一直以来,先生是我学习的楷模,不单单是因为其与生俱来的踏实和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每日对自己制定的严格的作息制度和学习计划。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的支柱除了精神而非其它。先生自己不断在浩瀚学海中的劈涛斩浪让后辈学人几乎只能亦步亦趋。而近年来他在音乐学研究上的成就斐然,这样以身作则的力量,将先生勤奋踏实、谨慎严格的学术作风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们的内心中。如果说先生的以身作则具有严以律己的模范作用,那他教育中的点点滴滴若润物细无声,则是其广博人性关怀下的包容所致。爱生若子的先生很少批评学生,但愈是如此却愈有威望。有时一种无语的思考式微笑,就将谬误焯烈的灰飞烟灭。作为一名成功的教育者,先生不仅仅实现了自我的逐步完善,而且还帮助众多尚在知识瀚海中牙牙学语的懵懂学子点亮希冀,找到研究的路向。
综上,谦逊踏实的学术品质和博大精深、大开大阖的研究视野,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鲜明特征;而与时俱进、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坚持,为其学术和人生指明方向。先生言传身教、诲人不倦的教育理念是其誉满华夏、桃李天下的必然保障。
历观先生之著作,不由之感慨,先生穷尽自己数十年人生阅历和思想凝练,始终保持着一颗对音乐学术研究的赤子之心。先生将梦想的音符融入笔尖,娓娓将人性的真善美细细道来。他用精神洁净其气质,远离庸俗喧嚣的同时构筑了一位真正的学者追求真理、无所畏惧、两袖清风的简朴人生。虽然在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中,不敢断言先生的人性之歌可以在千百年后被人人传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进入先生精神世界或者门下,至少也是和先生一样拥有圣洁灵魂的捍卫者。
参考文献:
[1]高士杰.论音乐的特殊性[J].交响,1982(1).
[2]高士杰.对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思考[J].人民音乐,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