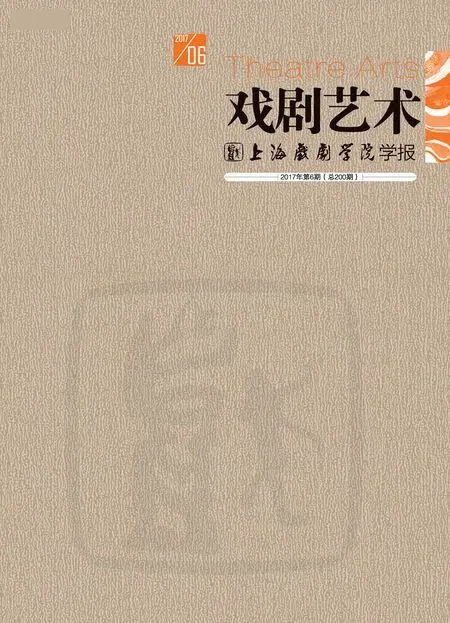开拓戏曲史研究的新视野
——读朱伟明等著《汉剧史论稿》
清代中叶以来勃兴起来的地方戏,构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继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之后的第三个黄金时期。但对这一时期涌现的形形色色的地方剧种,尤其是除了京剧之外的一些地方剧种,学界的关注度远不如前者。比如汉剧,这一直接孕育了京剧、并最早实现皮黄合流的古老剧种,从其形成发展,再到剧目特征、表演形态、音乐结构等,无不体现出一种以俗为雅、雅俗相长的审美特质,堪称“中国戏剧史上雅俗之变的经典个案”(朱伟明、陈志勇、孙向峰 462)。但对这样一个不仅催生了京剧,而且对粤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滇剧等剧种的形成发展都有重要影响的剧种,以往的研究却不够充分,湖北大学朱伟明教授等学者撰写的《汉剧史论稿》(人民出版社2016年),有望扭转这一局面。该书为朱伟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项目《汉剧的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最终成果。①
《汉剧史论稿》共计十章,分别为:汉剧形成前湖北地区的戏剧活动、汉剧艺术发展历史(上、下)、“楚曲29种”与汉剧早期艺术形态、汉剧表演形态与主要艺术流派、汉剧剧目剧本与经典个案研究、汉剧艺术与近代汉口都市文化、近现代汉剧对外重大演出与传播、汉调汉剧与其他剧种的关系、汉剧的剧史定位与传承保护。这样一种兼具理论考察与实践分析、兼顾历史溯源与现状保护、兼论艺术本体与生态环境的框架设计,彰显了研究者戏曲史研究的新理路,概而言之,本书有如下三个特色:
一、文本与舞台兼顾的立体剧史观
1915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出版,开创了中国戏曲史的现代学术研究体系。王著在嘉惠学林的同时,也不断引起人们的反思。早在1986年,陈多先生就提出了重修戏曲史的“非主流派”说(陈多 1),主张重视戏曲表演及舞台方面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高等院校的戏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呈现着以文本为中心的格局,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
朱伟明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则在披沙沥金地广搜各种史料、严密考证的基础上,不仅对汉剧艺术的发展轨迹、剧本形态进行了客观、清晰的描述,还对其角色体制、音乐体制、表演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最终形成了这部洋洋洒洒近50万字的周详完备、论证谨严的汉剧研究专著,值得学界重视。
比如在论述汉剧发展的黄金期、低谷期、复兴期时,不仅概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色,还分别结合余洪元、吴天保、陈伯华等汉剧名伶的表演生涯及其对汉剧艺术发展的历史贡献,和茶园戏院、科班教育、专业院团、革新举措等不同方面,尽可能如实、全面地勾勒了汉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面貌。又如“汉剧三国戏的特色与影响”一节,作者既从文本的角度,论述了汉剧三国戏的艺术特色;又从舞台的角度,结合米应先、余三胜、余洪元、胡桂林、钱文奎、陈春芳、董金林、李春森等擅演三国戏的汉剧名家的舞台实践,立体、全面地阐述了汉剧三国戏的艺术形态。
正如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所说:“本书的写作便是建立在从文献、文本到舞台的全方位、多层次考察基础上的。”(朱伟明、陈志勇、孙向峰 518-519)这种综合、全面的剧史观,贯穿在该书从“史”到“论”的每一章节的阐述中,为地方戏乃至戏曲史的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路。
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当前剧种史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的单一。诚然,对地方戏历史面貌的还原,主要依赖于文献资料的记录,但戏曲艺术的舞台性和活态性,赋予了其迥异于文学艺术的“场上”特质。于是,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的并重、文本分析与活态演剧的结合,便成了《汉剧史论稿》的一大特色。
在文献史料的印证上,从该书脚注和参考文献广泛涉及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负苞堂集》《珂雪斋集》《容美纪游》《汉口丛谈校释》《武汉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湖北文史资料》《武汉文史文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武汉市志》《(康熙)武昌府志》《(乾隆)江夏县志》《燕兰小谱》《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湖北地方戏曲史料》《湖北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汉剧志》《汉剧丛谈与续汉剧丛谈》《汉剧传统剧目考证》《汉剧表演艺术》《陈伯华表演艺术文集》《汉剧音乐漫谈》《汉剧史研究》《罗宾汉报》《江声日刊》《太阳灯》《镜报》《汉口导报》《上海民国日报》《顺天时报》等文献资料,即可以看出研究者所下的功夫的确非同一般。除了纸上的资料,作者还极为重视口述资料的佐证,比如在研究汉剧旦行“陈派”艺术特征时,采访了胡和颜等“陈派”传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汉剧表演艺术大师陈伯华的生年、武汉汉剧院的建院时间等,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另外,宏观描述与微观考据相结合,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相结合,也是《汉剧史论稿》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点。如在论述汉剧剧目概况时,精心选择了《群英会》《辕门射戟》《甘露寺》等三国戏、《二度梅》《打花鼓》等经典个案,点面结合、经纬交织,展示了汉剧剧目的独特风貌和演变规律。又如,为了彰显汉剧艺术形态之独特,作者还把它放在全国剧种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了汉调对京剧形成的独特贡献、汉调与广东汉剧的生成、汉剧与楚剧的艺术交流与竞争、汉剧对明清传奇的继承与发展、汉剧与中国戏剧史的雅俗之变等。这样,既有剧种间的横向比较,又有全国性的纵深视野,汉剧独有的“这一个”特色,得到了鲜明的印证,而著者所推崇的“志(材料)、史(轨迹)、论(结论)有机结合”的研究理念也得以彰显。
三、剧种文化身份的认同
汉剧在2006年就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汉剧在中国戏曲文化园林,乃至整部中华文化史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和地位?《汉剧史论稿》从文化的两个层次,儒家大传统的雅文化与民间小传统的俗文化进行剖析,并结合汉口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的壮大、大众文化的兴起,深入、准确地揭示了汉剧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戏曲文化框架中的地位:汉剧既是“汉派文化”风骨神韵的集中体现,又是中国戏曲雅俗审美观念变迁的经典个案,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剧向来被武汉人认为是最能代表“汉派文化”的文化遗产,汉派文化“既与中原正统文化血脉一系,又具有与外来异域文化保持一线联系的天然孔道,既感受东南一带先进文化信息,又不断接受西北一带古老纯朴的农业文化的熏染”(涂文学 341),汉剧在发展革新过程中,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对此,本书分别从汉剧之形成,仰“皮、黄”之汇;汉剧之鼎盛,总襄河派、荆河派、府河派、汉河派“四派”之汇;汉剧之鼎革,成中西之汇三方面,深入论述了汉剧的文化品格。此外,还从汉剧剧目的“崇汉”精神、汉剧舞台表演的浓郁“汉味”、汉剧与汉镇习俗的融合、汉剧人敢于担当的集体意识等维度着眼,令人信服地推论出“传承汉剧,既是传承其舞台表演艺术,更是传承其内在的文化品质”(朱伟明、陈志勇、孙向峰 340-341)。
由此,也深化了对包括汉剧在内的民间戏曲的文化身份和审美价值的认识。有鉴于斯,出于对剧种种类多样性和文化生态多样性的考虑,汉剧的保护和传承自然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文化意义。
此外,《汉剧史论稿》的出版,对戏曲史、汉剧和其他地方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在学术视野上。作者始终把汉剧的发展演变,放在中国戏曲史的宏阔视野下,放在中国雅俗文化的变迁、近代都市文化的濡染中,深挖细掘、孜孜以求,力图给予汉剧在中国戏曲版图中以恰当的位置描述。
众所周知,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两座不朽的高峰,历来受到学人的广泛关注;而对第三座高峰——清代乾隆以后地方戏的繁荣,则关注甚少。这种理论研究的贫乏与地方戏繁盛的局面是极不相称的。近来,北京大学的廖可斌教授,在《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向后、向下、向外——关于古典戏曲研究的重心转移》一文,主要探讨突破戏曲研究瓶颈的问题,文章重点论述了“向后”,呼吁将“研究重心由宋代至清初戏曲,转移到清中叶至民国初戏曲”(廖可斌22),要重点研究“清中叶至民国初年的民间戏曲”,因为它“不仅是当时戏曲艺术的主体,而且在整个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可斌 2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与《汉剧史论稿》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戏曲转型与重构的关键时期,戏曲剧本与音乐体制由曲牌联套体向板式变化体转变,戏曲创作体制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转向以演员(表演)为中心,这些重大变化与转折,在汉剧中均有明显的体现。也恰是在此意义上,《汉剧史论稿》对汉剧史的研究,开拓了戏曲史研究的新视野。
以上力图打破传统戏曲研究偏重文本和文人戏曲的格局,兼顾文献分析与演剧形态研究的宏阔视域,正显示了《汉剧史论稿》作者的学术眼光。
其次是在剧种史研究领域,对其他地方戏的研究,具有示范和导引的意义。剧种史该如何书写,才更符合地方戏曲的艺术特质,才能准确揭示其对戏曲艺术历时的承继性和不同剧种之间共时的差异性?《汉剧史论稿》既从文集、方志、史书等文献中爬梳相关资料,全面描述了汉剧形成前湖北地区的戏剧活动,为汉剧的孕育、形成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背景;又分别考述了乾嘉时期汉调的兴起与汉剧的形成、道咸时期“四大河派”的繁荣局面、同光时期汉剧“四派”在武汉合流的新格局,以及汉剧发展的黄金期、低谷期、复兴期、变革期,纵向深描出汉剧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还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对汉剧“十大行”的艺术规范、汉剧经典剧目形成的路径与文化内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考证。概而言之,全书既有对汉剧发展历史的纵向钩稽,又有对汉剧艺术形态、文化品格、演出传播的横向探查,还从文化、方言、现状等角度,对汉剧剧史地位与传承保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这种开阔的视野和完备的体系,在当前的剧种史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相较于其他地方戏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厚重。这些,对于相对边缘化的地方剧种研究而言,有着特殊的启示意义。
近年来,高校系统与文化系统间的交往渐趋频繁,其间虽难免有隔膜,但合作交流已是大势所趋。《汉剧史论稿》就是高等院校与文化部门精心合作的结晶,它启发我们如何把高校的优质资源和文化系统的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打破不同学科间壁垒森严的闭塞现象,营造一种更有朝气、更有活力的戏曲研究新局面。以笔者正从事的文化部艺术研究项目《排场戏与戏曲编创模式研究——以邕剧为例》而言,就深感地方剧团与文化部门的支撑非常重要,没有实地调研和剧目观摩的一手资料,仅凭纸上文献、闭门造车,就想做到对汉剧、邕剧这样处境艰难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确、客观的形态描述与策略分析,是很难想象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伟明教授和她的团队重视资料搜集与文献分析的严谨态度,尤令人感佩。早在本书出版之前的2012年,朱伟明教授和陈志勇博士主编的96万字的《汉剧研究资料汇编》②(1822-1949),就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正是在这样坚实的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作者秉承其一贯的严密考证的学术理性,完成了这部有理有据、论证公允、史论结合的厚重之作。对于一个只有8万元资助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来说,朱伟明教授和她的团队历时八年,坚持不懈,埋头苦干,终于拿出了这两部史料价值和科研价值都极高的著作,实属不易。这也是在2017年初湖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戏曲史视野下的汉剧史书写”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朱教授及其团队严肃认真做课题的态度给予肯定和褒扬之处,与会专家纷纷赞扬朱教授是把这个“一般项目”当作“重大项目”来做。这种脚踏实地搞科研、既不浮躁也不随流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和提倡。
总之,《汉剧史论稿》以其翔实的资料、富赡的内容、周密的体系,成为朱伟明教授和她的团队贡献给学界的一部创获颇多的学术著作。康保成先生赞誉它“是一部集大成的厚重的学术成果,在汉剧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朱伟明、陈志勇、孙向峰 5),诚不谬也!
然而,毋庸讳言,《汉剧史论稿》虽然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打磨,也难免有不周之处,比如对汉剧舞美艺术、汉剧导演艺术、汉剧服饰装扮等,尚未涉及;对“文革”时期“四人帮”的迫害如何摧残了汉剧艺术,也未及深入展开;对汉剧剧目的个案解读亦不够充分。尽管如此,本书把文献、文本与舞台紧密结合起来,论述地方剧种整体面貌的写法,仍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当然,以上“白璧微瑕”,也说明汉剧或者其他地方戏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天地,值得广大学界同仁共同探讨、齐力耕耘!
注解【Notes】
①据作者朱伟明教授自述,《汉剧史论稿》原来还有一个附录《汉剧十大行著名艺人访谈录》,因为篇幅原因,并且,由于两个行当的演员访谈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尚未完成,故准备另外结集出版。因此,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剧的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最终成果应是三本书:《汉剧研究资料汇编》《汉剧史论稿》和《汉剧十大行著名艺人访谈录》。
②《汉剧研究资料汇编》(1822-1949)由朱伟明教授和陈志勇博士共同主编,2012年6月在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朱伟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剧的发展历史与艺术形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荣获湖北省第七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和武汉市十四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
朱伟明、陈志勇、孙向峰:《汉剧史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Zhu Weiming, Chen Zhiyong, Sun Xiangfeng.Essays of the History of Hanchu Opera.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陈多:《戏史何以需辨》,选自《戏史辨》,胡忌主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
[Chen Duo. “Why does the History of Xiqu Need Explanatio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Xiqu.Beijing:China Theatre Press, 1999.]
涂文学:《文化汉口》,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年。
[Tu Wenxue.Cultural Hankou.Wuhan:Wuhan Press, 2006.]
廖可斌:《向后、向下、向外——关于古典戏曲研究的重心转移》,载《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Liao Kebin. “Backward, Downward, Outward:The Shift of the Emphasis on Classic Xiqu Studies.” Literary Heritage 6(2016):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