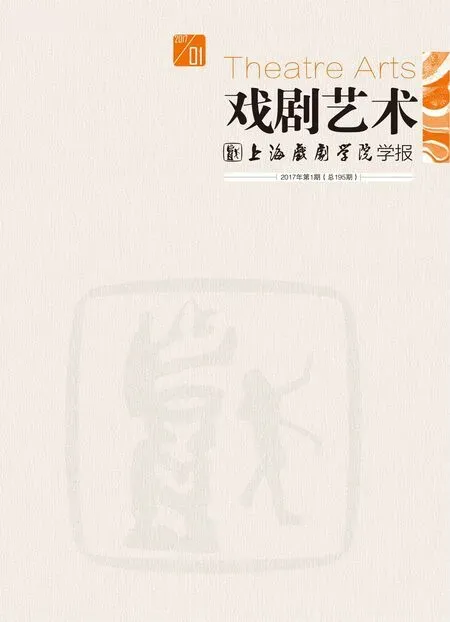对国内大型演出中舞美技术主义倾向的反思
■潘健华
对国内大型演出中舞美技术主义倾向的反思
■潘健华
国内大型演出业的繁荣,已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型文化业态。其中具有视觉先行特征价值的舞美形态,在技术手段支撑的视觉语言表现与戏剧表演要求的人文诉说方面,二者出现一种剥离的现象。一些形式大于内容的设计越发显露技术主义的倾向,由此折射出整个大型演出生态群的遗憾。它引发我们重拾艺术想象和戏剧艺术虚构的技术评价,强调舞美的技术能量,不等同于纵容单纯技术的臆造来冒充创新。本文通过对大型演出舞美因偏重技术主义而导致演出文化本体弱化的思考,从而倡导大型演出的舞美更应遵循艺术规律,才能使其具有独特的生命力。
大型演出 舞美 技术主义 艺术规律
大型演出已渐渐发展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形态。大型演出是指置于非传统戏剧舞台空间,千万以上大投入、大制作的一种主题性演出,以实景及大型庆典类演出为代表。近年来尤以实景演出最为火热,实景演出是以真实山水作为演出空间,以当地的风俗文化、历史典故作为演出内容,集合演艺界与投资人联袂出品的一种文化模式。不论地方实景演出还是国家庆典类演出,均具有巨大的市场推介效应与浓厚的文化意味。由于这种演出特殊的规模效应,追随与复制愈发狂热。作为视听功能先行的舞台美术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在现今的大型演出中,最注重打造的便是演出中的视听部分。遗憾的是,本应传递风俗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大型演出,越来越表露出对舞美技术主义的盲目追求。这里的舞美技术主义倾向是指,在舞美视觉符号系统与主题内容之间的技术配置中,采用的技术手段过度或过量,喧宾夺主,形式未能准确传达意蕴,表象未能传达内容,技术至上削弱了演出主题的一种现象。
以实景演出为例,自2004年《印象·刘三姐》公演以来,它便作为一种旅游产品的新载体开启了中国大型演出的先河。由此引发一股“印象经济”热,其势犹如燎原之火,几年间燃遍国内各大旅游景区。这种将当地景色与传统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相互融合的模式,本应随着逐渐成熟发展的态势而有新的改进与质的提升,但令人唏嘘的是演出模式中舞美技术主义的倾向愈发明显。主要体现在不结合当地特色文化,一味追求演出规模上的装置庞大,视觉震撼,毫无节制地打造奢华的舞台、花哨的灯光、炫丽的服饰,造成同质同形同类。这种现象值得同仁反思。当然大型演出的绩效有多种因素产生,本文暂不讨论政府决策、演出内容、导演立意、表演因素,主要谈大型演出绩效评价中舞美的技术主义倾向。
一、规模与品质
规模不等同于绩效的“质”,绩效也不只是靠“量”来权衡。这里的“量”指大型演出中舞美技术运用的成分,“质”指大型演出中舞美的品相及格调。在各路影视编导与投资方联姻,纷纷踏上大型演出的“捞金之路”时,往往一根筋地扎入到如何将演出做得“大”,做得“更大”,不大不惊人,不大显得不气派,似乎只有大场面、大投入才能博得观众的青睐,才能赢得票房,为此舞美的大规模的技术强调与表现成为首当其冲的手段。很多舞美创作团队不愿劳神焦思如何突破原有的设计模式,以致呈现出的作品流于表面、缺乏深意。在打造新作品的过程中,不动脑思考如何突破以往的模式,不管演出所涉及的文化风俗有何特色,均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常带有一种“只要视觉效果华丽丰富”即可的想法,摒弃了对演出本质的思考,似乎在演出中只要出现炫丽的灯光、宏大的舞台、斑斓的烟火等元素就能构成一部好的作品,缺失对设计理想、人文关怀、文化传承孜孜不倦的追求,团队精神被形式表象所诱惑,单凭概念与经验来支配舞美运作。
曾参与大型演出项目制作的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林振宇指出,很多导演在项目设计中会给投资者很大“压力”,并许以很多愿景,甚至有些忽悠的成分,在节目制作中一味贪求器械使用、盲目追求特效,从而花费大量资金。《印象·刘三姐》早就被台湾学生质疑“可能会给环湖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印象·西湖》更因其工程违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招来严厉指责;《印象·丽江》在彩排时也遭到当地文化名人的炮轰,认为其破坏环境,舞台也损害了丽江自然景观。其中《希夷之大理》以苍山为背景,舞台利用了大理古城东北角的220亩北门水库,整个剧场面积达13万平方米,使用钢材超过1800吨,宽235米、高30米的全钢结构彩虹桥飞跨舞台,在高空展示壮观的雾森水幕成像系统。不少人对此演出的舞美提出质疑:水库灌溉功能受影响是其一,声光电系统的扰民是其二,花巨资打造所谓“名片”值不值是其三。并希望这类演出不要伤害大理的古朴与宁静,更不能影响当地民生。当地水务局在剧场修成后,为了保证演出用水及村民灌溉,投资方全部“埋单”。《夜王城》据称投资高达3亿元,舞台音效的嘹亮音响,伴以锣鼓喧天,不仅破坏了景区的宁静,甚至吓跑了景区候鸟。
在自然山水中通过改造周边环境搭建的庞大舞台,很难说对自然景观与生态环境没有破坏,宏大的作品与舞美,的确有着非凡的气势与气魄,但作为演出赞助方、制作方、编导者、设计者更应该考虑,大型的“大”不是“量”的规模,不是巨资的投入、场面的宏大、视觉的纷繁、票价的高昂,应是品相的“质”。大型演出更应该有文化引领的价值、艺术手法的创新以及人文精神传递的高度。形式大于内容不可取,好的大型演出更应讲求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但一些演出却出现了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视听语言方面唯美奢华,人物形象和主题内容等方面却空洞单薄。部分大型演出中匪夷所思地出现阴冷残虐的地狱、庞大扭曲的末日景象,不难看出是各种类型元素杂糅和拼接,貌似创新,其视觉画面设计远远超出了故事与主题发展的需要,导致形式大于内容,让观众的观演过程疲惫不堪。
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研究学者李肃认为,大型演出诞生于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过渡的旅游业转型过程中,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而如何吸收民族文化要素,结合娱乐业、高科技的表现手法,将成为其发展创新的突破口。著名旅游策划专家张小可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不少大型演出,尤其是实景演出,已从当年的“新模式”变成了“旧套路”,面对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困惑,创新才是解决之道。如何在文化传承中创新发展,是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
可喜的是,2016年陕西省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节俭办节的要求,控制舞美规模,不搞大型开闭幕式,在充分展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成就、带给人们艺术享受的同时,处处体现出节俭办节的原则。无论是场馆建设改造还是演出比赛,节俭务实、厉行节约,不搞铺张奢华、不搞重复大型场馆建设,讲究艺术品质,倡导艺术演出的长期惠民,目的是让百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技术与艺术
无论什么演出形态,舞美的技术与材料运用,都是推动演出重大革命的因素。以20世纪初瑞士舞台美术家阿披亚(Adolphe Appia,1862—1928)为例,他正是以图案化立体布景,强调通过光和影来制造舞台氛围的技术运用,奠定了此后舞台美术与表演有机结合的造型价值,且理论影响至今。阿披亚的成就在于将技术与表演内容与戏剧整体要素有机结合,各子系统关联没有剥离。可见舞美技术不可脱离为演出服务的根本,技术脱离了艺术多数成为卖弄。
大型演出中的舞台技术表现,要求风格化与多样性,结合不同地区民俗民风的特色展示,成为最大的看点。比较成功的如《少林·禅宗大典》与《大宋·东京梦华》。《少林·禅宗大典》通过舞美营造出了“半缘演出半缘禅”的演出意境;《大宋·东京梦华》通过现代化的数字影像、电脑灯具、LED服装、大型仿真道具等一系列舞台符号,再现了宋朝时期的生活面貌,尤其用高科技灯光和烟雾变幻效果营造了情景,再现了时空推移,形象地反映了北宋东京从繁华逐渐衰败的历史过程。
舞台技术表现的成功案例值得借鉴,反之更值得我们反思。一些舞美盲目跟风,在技术打造中忽略当地文化元素,从主题内容到表现形式都实行“拿来主义”式的照搬他人格式,以为只要舞台效果吸睛便达目的。例如,一些地方模仿“印象系列”打造的《印象·野三坡》《印象·海南岛》等大型舞美,一看就是“印象系列”的仿版,遭到大众的质疑与批评。种种案例表明,演出作品若缺乏对文化内涵和本土风情的理解与融合,只注重舞美技术的外壳,形式大于内容,都将成为旅游景点的一片浮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舞美设计与制作,有向物质化发展的倾向。90年代以后,电子科技与投影技术的发展迅速,多媒体更加便捷地实现了越来越多过去不容易用实物布景、灯光实现的舞台技术手段,在为舞台设计的视觉空间表现提供便捷呈现的同时,也被过度使用带来弊端,集中表现在弱化演出主题、冲淡故事、艺术风格与样式混乱,从而阻碍演出对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传递,尤其背离大型演出具有文化引领价值的属性。舞美技术虽然重要,但舞美技术至上不可取。
近十年来,在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舞美设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投影和数码技术引起的。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对这样的技术存在盲目性,很容易失去演出本身的特质。我们知道,舞台框架、灯光、道具,乃至新媒体等的确能支撑起具象的实际舞台,但它们最多也只能是技术支持。大型演出的舞美,仅满足于对技术媒介的片面追求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当下正有不少大型演出的舞美,就是靠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所谓“设计”,妄图掩饰创作团队的不用心和节目实际内涵的缺失。舞美设计如果不管演出的主题、类型、背景、立意等,一味追求视觉效果,在舞台、灯光、服装,音效乃至多媒体的运用上,过于花哨抢眼,喧宾夺主,忽视了演出本体的规定,仅用技术框架实现所谓的创作,用光怪陆离的特效赚取观众眼球,抢夺了演出本身应该以文化风俗、传统特色来引发观众在心灵层面共鸣的观演体验,显然在把演出推向肤浅、庸俗的层面。我们所要聚焦的问题不在于排斥舞美道具或者是新媒体技术,而在于要重视寻求演出内在价值的传达。倘若舞台规模、舞台技术跟演出内容相剥离,甚至相冲突,那么再宏大的舞台规模,再炫耀的舞美技术都是不可取的,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林振宇指出,从文化与旅游的发展态势看来,演艺一定会成为旅游的“标配”,在这种机遇下,我们要注意内容定位、制作方式、成本考量,尤其是在内容方面,不能一味地追求西方化……需要我们挖掘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元素,而非盲目地进行道具堆砌,沉溺于新技术的运用。判断是否舞美技术主义,归根结底,是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思想、手段与目的方面对“度”的掌控,科学看待舞美技巧表现,这里有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是靠积累形成的。大型演出不管手笔有多大,还是需要始终遵循不同空间、不同题材、不同地区、不同表演类型的程式框架,技术运用中创造不同风格的作品,靠鲜明贴切的技术立意来形成风格,自然就会理解和接纳不同风格和个性,创作团队也自然能够寻找对应的不同样式而形成节目特色。简单说来即遵从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随类赋彩”原则,这要求创作团队需要不断累积和思考,以免与“随类赋彩”的设计造物法渐行渐远。舞美设计师应当认识到,虽然是处于信息技术、电子科技发展活跃的时代,多媒体的便捷性、多元性能为创作服务,但演出的本质精神与核心价值不能忘记。琳琅的物质材料、繁多的数字信息需要通过艺术运用,结合演出主题来传达内在的精神意旨,才能与之融合成别致的舞美艺术作品。
三、空间与意蕴
空间是舞美存在的前提条件,通过空间营造富有艺术价值与人文理想的舞美作品意蕴,是舞美人的职责。大型演出与其他影视类文化产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活的”,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再生,都是一次成长。而精品演出就是在这一次次再生、一次次成长的实践中反复打磨出来的。大型演出若要可持续发展,应不懈进行自我完善,舞美当然责无旁贷。
纵观国内外近年来演出空间的选择,也有对非演出空间的运用。不少演出策划方、制作方将演出活动转移到老工业区举行。将废弃的工厂、粮仓、车间等改造成为演出场地。舞美设计师利用这些非常规的场地,来打造舞台演出别样的美学价值。这些新意识、新趋势应当为业内人士借鉴。然而,国内并没有借鉴这些成功经验,纷纷建造大型演出场地,或者将自然景观改造,用来作为演出场地,许多大型演出过分地人造出演出空间,且在舞美设计上也偏重对视觉元素漂亮不漂亮、华美不华美的浅表追求,声称精美、华贵。殊不知单纯的形式美,并不是衡量演出品质的唯一标准。德国舞台美术设计师约翰尼·舒茨(Johannes Schuts)指出:“如今在整个行业看到的舞美,是过分浮躁的视觉表现热情,大多演出都显得庞杂和过分雕琢,充斥的视觉因素主宰场景,妨碍情节展开。”[1]演出中,舞美绩效最主要看视觉元素和演出主题内容之间是否相贴切。每个舞台技术反映出的视觉元素都像是一盘“菜”,一场演出一共用几盘“菜”?这需要巧妙搭配,需要舞美设计者的智慧和灵性,尤其注重作品的内涵,既要有出人意料的技术变化,又要让技术变化合情合理。
胡妙胜先生在《戏剧空间结构》中指出:舞台是一个有魔力的场所,任何东西一经放在舞台上就会产生超越出该东西的感性物质的意义,从而成了一个记号或符号,舞台上不存在无缘无故的东西[2]。可见,艺术记号的特征在于记号媒介及形式,除了表示外延所指和内涵所指以外,它本身还具有审美信息。它们都会引起人们不同的艺术感受,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因此,作为视觉符号的舞美空间具有再现的假定性,它必须融入于戏剧规定,才具有合理的价值绩效。大型演出的空间,除了作为演出平台的基本作用之外,更应具有文化引领的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传递。我们并不否认演出需要技术支撑,但应清楚演出并非 “灯光秀”“舞台秀”“服饰秀”,空间中的外在形式必须与内在立意相互融合,相互映衬,从而做到以“形”传“意”、以“形”映“世”,它是艺术作品更进一步升华至“善”与“美”的必要条件。画家齐白石有句名言:“作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不似为欺世,太似则媚俗。”美术界以“形似为基础,重在神似”的理念,也是演出中舞美设计品质的一种判断。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3](P.70)意境,对于舞美空间可理解为“意蕴”。因此,意蕴的贴切表达应当是舞美应具备的重要品质,是创作团队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演出生命力的保障。
大型演出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担负着精神文明建设的特殊使命。担当的是不同地区风俗与文化特色传递的职责。要求舞美创作团队在不失艺术创作本质,不断充实自我素养,吸收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更要悉心研习不同地区传统文化来为创意确立素材。大型演出具有文化引领的功能价值,好的舞美设计应该贴切地为传递演出主题服务,与整个演出融合,也就是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说的“大象无形”。反之,一台演出舞美成份显得强烈刺激,那肯定突兀了。仲呈祥先生对戏曲舞台美学提出应有“三讲求”的原则,相信对大型演出的舞美设计也有借鉴作用:一是“托物韵志,寓理寓情”,这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基本特征;二是“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凝练简洁是很多中国传统艺术形态都遵循的规律;三是“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形象阐释。这些理念值得从事大型演出的创作团队来深入思考。充分把握演出主题的内涵,尤其迫切,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大型舞美设计既需要技术,又不能技术至上。这需要从根本上调整认识,创作态度上要回归初心,专业修炼中要潜心思考,不固步自封,不拾人牙慧,不知难而退。重在摒除“万金油”式的设计套路,以饱满而热情的精神去求知、求新、求变。时刻怀抱对演出作品、对舞美作品的创造之心,对观众的诚恳之心,对文化的敬畏之心,脚踏实地去吸纳新技术新知识,同时需要把握多样的乡风民俗和不同的地域文化,才能宏扬地方特色,为文化创新服务,技术与艺术编织文化精神的经纬,才能打造出大型演出舞美新面貌。
[本文为上海市高峰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建设计划(项目编号:SH1510GFXK)成果之一]
[1]转引自刘杏林.舞台美术新思维三题[J].戏剧艺术,2015(3).
[2]胡妙胜.戏剧空间结构——舞台设计的美学[J].戏剧艺术,1988(4).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Title: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Tendency in the Stage Design of the Large Performances in China
Author:Pan Jianhua
Large performanc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new cultural industry in China.For some productions characterized by the priority of visual effects and stage design,there is an obvious split between the visual language,supported by technology,and the humanistic narrative,required by dramatic acting.In some designs,for those that stress style over content,there is an even more obvious technocratic tendency,reflecting the defects of large productions as an ecological group.This leads us to the evaluation of technology in artistic imagination and dramatic invention.Emphasis on the technical energy of the stage design is not the same as over indulgence in technology under the disguise of innovation.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eakening of cultural subjects due to excessive technocracy,and argues that the unique vitality of large performances can only be brought out under the law of aesthetics.
large performances;stage design;technocratic tendency;laws of aesthetics
J80
A
0257-943X(2017)01-0027-06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